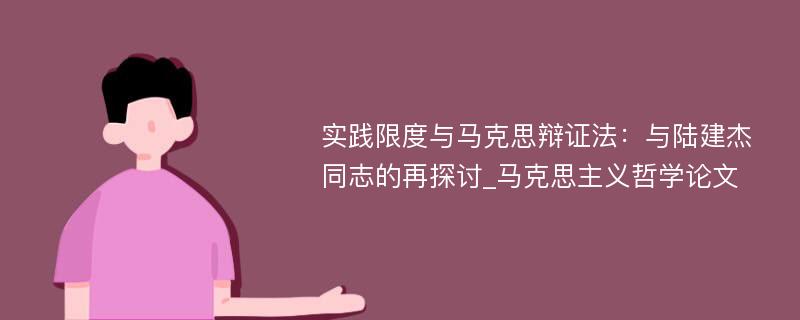
实践限度与马克思辩证法——与陆剑杰同志再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辩证法论文,限度论文,同志论文,陆剑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219(2008)04-0021-05
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辩证法是主客体辩证法,陆剑杰同志在《实践问题和矛盾问题新论》(以下简称《新论》)中认为马克思辩证法是处理主客体关系的实践辩证法。然而,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始终是有着自己的限度的,科学实践观构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整个大厦的根基和平台,但不是其本身。主客体关系实质是实践表象视界的关系,并非是实践的本质视域。将马克思辩证法归结为主客体辩证法和实践辩证法,虽然有利于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筑基础,但总体看来是片面的、混乱的和唯心的。厘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盲目跟从的《新论》的错误是必要的。
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史上所引起的革命,归根结底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构筑了科学的实践观。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前的哲学之所以未能建立起科学的全面的和深刻的哲学构架,盖其原因,根本的便是缺乏对实践的科学理解和把握。“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1] 旧唯物主义如此,唯心主义亦复如斯。“和唯物主义相比,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1] 科学实践观引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史上史无前例的革命。正是基于科学实践观的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才在世界观、辩证法、认识论和历史观上造成了实践性的唯物主义的严格的科学性的统一。马克思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发挥着极其巨大的整合作用,成为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实践性质的灵魂和核心。
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实践观只是构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决不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也不能够代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所有的有机组成部分。实践限度,就是马克思主义科学实践观在其中的平台限度和基础限度,就是实践观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历史观、辩证法和认识论的无可替代和无法混同。这从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可以窥见端倪。
作为《提纲》的总论部分,一、二两条在指明实践观是新旧唯物主义的分界线,批评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缺陷的同时,揭示了科学实践观是新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此岸性”。[1] 这不仅是在指明认识的实践基础,而且是在言说实践对于认识之是否具有真理性的检验标准。
从第三条至第九条是《提纲》的分论部分。在这一部分,马克思把科学实践观的观点应用于社会历史的研究,指出旧唯物主义不理解实践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是陷入唯心主义历史观的认识根源,同时,马克思提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科学论断,[1] 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无论是环境的改变,还是人们的自我改变,无论是宗教的现实状况,还是宗教在现实中的批判消灭,无论是人的社会本质,还是甚嚣尘上的神秘主义,马克思都主张对于它们的正确理解和把握应根源于实践,都表明对于它们的批判改造应归结于实践。显而易见,这决不是把“实践”这一词语充塞于科学的世界观、历史观、认识论和辩证法的所有角落,决不是以实践中主客体二元构架代替科学的世界观、历史观、认识论和辩证法所有部分。因为它是有限度的,科学实践观只能作为生长点渗透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部宏大的巨制之中,而不能庸俗地、机械地、莽撞地代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宏伟建筑自身。
作为《提纲》的结论部分,在第十和第十一条中,马克思总结性地指出,实践是新哲学区别于旧哲学的根本特征,是新哲学实现革命的实质。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以“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为立脚点,[1] 才能永葆其辩证法的批判的革命的精神,而作为其任务的“改变世界”,则更是对于其辩证法实践的批判的革命的品质的体认。
由此可见,实践之作为平台和基础的限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特别是在马克思辩证法中是不可忽视的。虽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部大厦,是在科学实践观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没有科学实践观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历史观、认识论和辩证法,就是实践,就是主客体关系,就是科学实践观,更不意味着马克思辩证法就是主客体辩证法,就是实践辩证法。
在此问题的左边是唯物主义。这就是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和邓小平为代表。他们贯彻着、执行着和发展着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辩证法的唯物主义性质,主张辩证法是从实践中获得的,是依赖于科学实践观而建立的,是有赖于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发展而被发现的,但马克思辩证法决不是实践辩证法、主客体辩证法。难道马克思辩证法只有归结为实践、归结为有意识参与的实践才会存在吗?难道马克思辩证法只有归结为主客体作用、归结为有主体能动参与的相互作用才会存在的吗?固然,我们应该承认惟有了人类之后,世界才在其运行的过程中撕开了自在世界和自为世界的发展缺口。从人类世界、人类社会的运行来看,简直可以说人类“创造”了历史辩证法,结果也“创造”了自为世界的辩证法,但辩证法的客观运行还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这是思维与存在、意识与物质这一哲学基本问题上,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的体现。
在此问题的右边是唯心主义。这就是以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为代表。他们竭力主张主客体辩证法和实践辩证法。卢卡奇率先提出辩证法的关键性决定因素是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而且认定主体和客体的辩证法只限于历史和社会范围内,并批评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萨特与卢卡奇有着相似的看法。哈贝马斯在《理论与实践》中更加直率地认为“辩证法是主体与客体的”。而《新论》也“把马克思辩证法理解为实践辩证法。”[2] 虽然马克思辩证法是在实践中获得的,是在科学实践观的建立中把握的,是在处理主客体关系中建立的,但是马克思辩证法并不就是主客体辩证法,并不就是实践辩证法,并不排斥、否定自然辩证法。当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国内的某些学者把马克思辩证法认定为主客体辩证法、实践辩证法之时,他们已悄然踏上了唯心主义的不归之途。因马克思辩证法是在主观意志参与的实践中,是在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中存在的,所以就把马克思辩证法归结为主观意志下的实践以及主客体的相互作用,这样就使马克思辩证法在不知不觉之中陷入了唯心主义的陷阱,马克思辩证法所坚持的彻底的唯物主义本质特征,开始被悄然消解在实践及其主体意志的极度膨胀之中,对于主观意志的存在性的依赖开始葬送着马克思辩证法对于唯物主义的忠贞。
二
实践限度就是科学实践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建构中的有限性。无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还是《新论》都未能给予充分的认识。不仅如此,它们对于实践的内在矛盾也缺乏足够的清醒的认识。它们盲目崇信实践之内主客体对立统一关系,而对实践之内其它矛盾关系视而不见。这不仅和它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近视有关,而且和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对于实践内的矛盾关系,特别是对于主客体关系的不全面、不深刻的认识有着很大的关联。主客体对立统一关系在实践之内是有限度的,它构成了实践限度之一,由此决定了主客体矛盾关系在马克思辩证法之中的有限地位。
实践的内在矛盾关系极其庞杂,但主要的应当是主观和客观以及主体和客体的矛盾关系。实践应当基本地包括这两个方面的内在关联。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更多地侧重于主客体对立统一关系,对主客观矛盾关系有所忽略,这是极其片面的。不但如此,主体和客体矛盾关系与主观和客观矛盾关系之间的关联亦是对立统一的。
主客体对立统一关系表面看来囊括了实践运行的全部矛盾,隐含了实践中的主客观矛盾,但是主客体相互作用本质上是物质实体之问的相互作用关系。进行时态意义上的实践,作为主客体矛盾运动的几乎全部的载体,实际上是物质实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了对主客观矛盾关系的拒斥。因而主客体相互作用,即作为实践发生意义上的行动本身已然归属于现象视界,甚至可以说根本与主客观矛盾关系无涉,主客体关系不再是内涵着主客观矛盾关系的一种矛盾。实践意义上的主客体关系是现象界的中性事物,它表现出实践运行的“冷漠”,它只是“中性”的,它是一把“剪刀”,无声地裁剪出主体对于主观和客观矛盾把握正确与谬误的命运。
主客体对立统一关系对于主客观对立统一关系具有相对的一面。实践意义上的主客体关系只是作为现象界的事物而存有的。成功的实践对于主客观矛盾关系的检验是具有意义的,成功的实践之中主客体是统一的。失败的实践虽然验证了主体关于主客观矛盾关系把握的谬误,但是由于主客体间的矛盾关系本质上是物质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所以失败的实践中主客体关系结果同样也是达到统一的。它统一于实践,并在实践基础上存在着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的双重转化关系。如此看来,主客体对立统一关系的运行并不一定是主客观矛盾关系发展的推进。实践中的主客体关系的运行及其对于主客观关系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它只是表象,而主客观矛盾关系则是其实质。主客观的对立统一关系直接决定着实践中的主客体矛盾关系的状况。“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3] 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决不等同于主体和客体的统一。因此,主客体关系对于主客观关系的“内涵说”是晦暗不明、暧昧不清的。如果主客体矛盾关系是实践的行动,那么主客观矛盾关系则是实践行动的指导,指导着主客体实践运行的发展。
主客体矛盾关系与主客观矛盾关系之间不仅是对立的,而且是统一的。作为表示实践运行的主客体矛盾关系,必须以主客观矛盾关系为指导,才有所意义,才能真正做到推进实践发展的主客体之间的统一。否则,主客体之间的任何统一都不表示对于实践发展的推动,而是对于实践发展运行的延缓和迟滞。这种统一与其说是错误的,不如说是荒唐的。另一方面,主客观矛盾关系的运行和发展有赖于主客体矛盾的运转。不仅是最大限度的主观和客观相符合的确认,而且是发展的客观真理的获得,都将有赖于主客体矛盾运动的发展。正是主客体的矛盾运行才为主客观矛盾的解决提供了现实的前提,主客观矛盾的解决必须实现到主客体矛盾的运行之中方能找到出路。
因此,实践之内的主客体矛盾关系和主客观矛盾关系之间的关联是对立统一的,两者之间不可混同,不能相互替代。主客体对立统一的运行只是现象界的,虽然其背后的指导是主客观矛盾关系,但实践态中的主客体矛盾关系却是对后者的拒斥,“隐含说”是有失偏颇的。主客体矛盾运行的实质是主客观矛盾的对立统一关系,惟有主客观矛盾关系才决定着主客体矛盾运行的状况。但是实践之内的主客体矛盾关系和主客观矛盾关系之间是有统一性的。主客观矛盾的解决必须有赖于主客体的矛盾运动,没有主客体矛盾的运行,主客观矛盾既不会发生,也不会解决,更不会发展。而主客体作为现象界的矛盾运行必须紧依主客观矛盾的解决,没有正确的真理性的主客观统一性的认识,主客体任何运行的统一,不论是失败的,还是成功的,都是没有意义的。马克思辩证法正是在主客体矛盾和主客观矛盾的对立统一上找到了自己的支撑点,不断地以鲜明的时代性的实践内容推动着哲学基本问题解决的新的发展。主客体矛盾关系在其与主客观矛盾关联中的对立统一状况决定着主客体的限度,决定着主客体在马克思辩证法中的有限地位。因此,认为马克思辩证法就是主客体辩证法,将马克思辩证法简单地归结为处理主客体关系的辩证法是错误的。
三
《新论》把主客体关系任意地迁移至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切问题的诠释上,以为凡不加上实践二字,凡不带上主客体二元构架字眼的观点都不是实践论的,完全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限度及其之中的主客体矛盾关系的限度,给马克思主义哲学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和惊人的庸俗化。
“实践论的世界观的基本问题是什么呢?是社会实践的两个关系方的关系:一方是从事实践活动的人,另一方是人的实践所指向的对象和环境。前者是实践的主体;后者是实践的客体。”“把实践中的主客体关系当作实践论的世界观的基本问题,又是人类哲学史上的全新规定,是对思维与存在这一原有的哲学基本问题的深化。”[4](P136~137)
这是明目张胆的曲解和篡改。世界观的基本问题是意识与物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而不是主客体关系问题。如果认为把意识与物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作为世界观的基本问题,是静态的,是远离社会实践的动态运行,因而认为主客体关系才是动态的实践意义上的世界观的基本问题。那么,主客体矛盾关系是现象界的运动,而主客观矛盾关系才是主客体矛盾关系的内在本质,才是抓住了世界观基本问题的本质,才是世界观的基本问题。以主客体关系作为世界观的基本问题,是在放逐真理,是在逃避唯物主义世界观和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对立,是寻找第三条道路的妄想。不是主客体矛盾关系深化了哲学基本问题,而是恰好相反,正是意识与物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深化了主客体关系问题。实践意义上的主客观矛盾才是主客体对立统一关系的实质所在。
“‘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就是实践中主体和客体的统一。”[4](P159)“主观和客观的统一,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归根到底是实践中主体和客体的统一。”[4](P198)
这是《新论》主张的新观点。实践意义的主体和客体的统一,并不就是主观和客观的统一。实践进行时态意义上的主体和客体都是统一的。作为现象界的矛盾关系,主客体统一并不一定是主观和客观的统一,也可能是失败的实践,甚至是完全背离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虽然,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有赖于主体和客体的统一,但主体和客体的统一本质上则是主观和客观的统一。主观和客观的统一才是主体和客体统一的实质。
“具体实践的展开过程,就是不同主体所作选择的相互竞争、斗争的过程,实践检验将作为最高权威判定他们的是非,胜负。”[4](P169) 《新论》如是说。
实践标准只是在确定人们的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上才具有意义。如果在其它问题上任意滥用实践标准,只会造成惊人的错误。不错,历史确实表现为不同主体选择之间的斗争过程,但决定他们胜负的不是什么所谓的实践标准。只有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人们的选择,才会是成功的胜利的历史选择。之所以有胜有负,乃是因为与对历史规律的遵照和违背有关。此其一。其二,成败、胜负本身就是实践,说由实践检验决定胜负,就是说实践标准决定实践,这是犯有极其幼稚的逻辑错误的。按照作者逻辑,一国遭到别国侵略,沦为别国的殖民地,那么结论就是实践标准决定了该国沦为他国的殖民地。此等逻辑,何其野蛮!
“实践论的历史观认为:社会历史的本质是历史创造者的历史能动性与他们必须尊重历史的既得条件的客观性的统一。”[4](P164) 实践论的社会历史观的基本原则“可以表述为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人与他在其中的活动的社会环境和条件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4](P172)
在这里,《新论》把社会历史观的本质与社会历史观的基本原则等同起来。实际上,此种论调与社会历史的本质毫无关涉,它所说的仅仅是人们创造历史的基本原则而已。历史是由人创造的,社会历史的本质规律性即存在于人们的实践活动中。它是客观的,是不为人们的主观意志转移的。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它,它都强制矫正着人们在历史中的创造行为。社会历史本质存在于人们的实践活动中,但决不依存于人们的实践意志。社会历史的基本原则是人们创造历史的基本原则,是社会历史的本质规律性规定人们创造历史的实践行动原则。“实践论的历史观认为:社会历史的本质是历史创造者的历史能动性与他们必须尊重历史的既得条件的客观性的统一。”这种观点是在抹杀社会历史本质的客观性,它把社会历史的客观性本质消融于人们的实践行动之中,因而必然把社会历史的客观性本质建立在对实践意志的依存性上。这不仅取消了社会历史本质的客观属性,而且走向了唯心史观的主观意志决定论,最终必将背叛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唯物主义立场。实践论的社会历史观的本质,应当抓住社会历史主要的普遍的客观矛盾的运行,突出人们在创造历史过程中,对社会历史基本矛盾实践解决的自觉性。
“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理解为实践辩证法。”“对于主体和客体的统一,实践辩证法用‘理论-实践-理论实践统一’的范畴来描述。”[4](P182)《新论》如是说。
前文已有论述,把马克思辩证法归结为实践辩证法,即认为马克思辩证法是以实践意志为转移的辩证法,由此否定自然辩证法,从而走向了唯心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代表。主客体关系本来是与主客观关系对立统一的,“隐含说”是欠妥当的。主客体作为现象界的对立统一,其本质是主观和客观的对立统一。但主客体在实践中的天然统一关系,并不一定表示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的统一,甚至是完全背离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因此,这种表达公式是有失偏颇的。
“作为矛盾问题的‘精髓’,它的重要性究竟在哪里呢?我们的回答是:它突破了脱离实践中主客体关系来讨论辩证法的片面性,进展到了实践论的辩证法,揭示了矛盾学说同实践中主客体关系这一辩证法‘最重要方面’的统一关系。”“矛盾特殊性和矛盾普遍性的统一是实践中主客体关系的统一的集中表现。”[4](P197)
矛盾问题精髓本来就是以实践作为基础的并服务于人们实践的发展。它丝毫不能、也不应该脱离实践,也不会脱离实践中的主客体关系,但矛盾问题精髓并不因此归结为主客体关系,并不因此归结为实践。矛盾特殊性和矛盾普遍性的连接是面向整个实践,而不是仅仅面向作为表象层面的主客体的矛盾关系。
总而言之,马克思辩证法是实践的,但不是实践辩证法;马克思辩证法是处理实践中各种矛盾关系的,但不可归结为主客体辩证法。主客体矛盾关系只是与主客观矛盾关系对立统一着的一个方面,而且是受主客观矛盾关系决定着的现象界的一面。马克思辩证法唯有在坚持彻底的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在世界观、认识论和历史观的统一之中,才能获得自身的全面的实践内涵和意义。
收稿日期:2008-05-14
标签: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 对立统一论文; 客体关系理论论文; 实践论文; 本质与现象论文; 唯物辩证法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客观与主观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科学论文; 世界观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