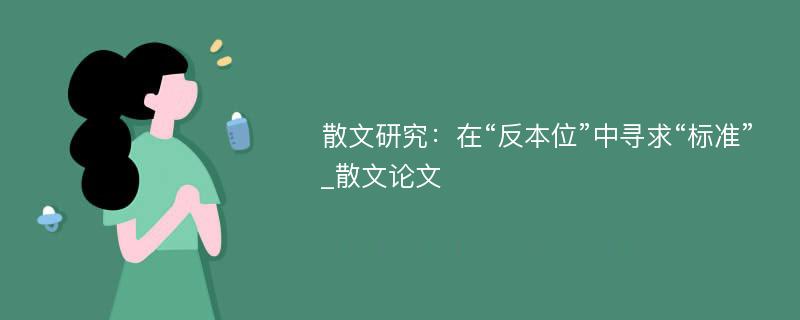
散文研究:在“反规范”中求“规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散文论文,中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学科的“规范”与文体的“反规范”
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各“体”研究中,散文研究属于相对薄弱的一支,无法与汗牛充栋的小说、诗歌研究相比,即使相对于正在走“下坡路”的戏剧研究,散文研究似乎也难占上风。现代散文研究的不兴在客观上与“五四”以来对散文一直缺乏足够重视有关。“五四”时期,尽管“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①但傅斯年在“文学革命”开初就提出:“散文在文学上,没甚高的位置,不比小说,诗歌,戏剧。”②之后,著名散文家朱自清也做出与之类似的表态:“它(指“抒情散文”——引者注)不能算作纯艺术品,与诗,小说,戏剧,有高下之别。但对于‘懒惰’与‘欲速’的人,它确是一种较为相宜的体制……我以为真正文学的发展,还当从纯文学下手,单是散文是不够的。”③建国后,文学界对散文文学地位的态度依旧十分暧昧,1981年在《文艺报》召开的“散文创作座谈会”上,与会著名作家冰心、夏衍、吴组缃、李健吾等人这样看待散文:“散文比别的文体样式同人们的关系似乎更密切一些。它是培养和训练青少年文字能力的有效工具:更像画中的素描,是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必须练的基本功,也是从事文字写作活动的基本功。”④现代散文的“尴尬”在各种“20世纪中国文学史”叙事中也充分体现出来,已出现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著,诗歌、小说和戏剧都占据了主要的篇幅,散文虽不可或缺但多数只是作为“点缀”而存在。文学界对散文的“轻视”虽不能说压抑了散文研究的发展,但对于散文研究队伍的壮大、散文研究信心的树立必然起到消极的作用。
客观原因固然值得注意,但就当下而言,检讨当代散文研究自身存在的缺陷更有意义。现代散文研究由来已久,伴随着现代散文文体的发生,胡适、周作人、郁达夫、鲁迅、朱自清等人关于散文文体建设的理论和批评,可算是现代散文研究的开端。不过,那时的散文研究侧重点在于文体建设,所有理论和批评主要针对散文文体建设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和“不足”,还不存在对散文进行“文学史”意义的系统研究。“当代散文研究”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方向是在建国之后。建国后编写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因为往往根据文体来划分章节,也就在文学研究中划分出“小说研究”、“诗歌研究”、“戏剧研究”,“散文研究”等不同的学术领域来。“现代散文研究”成为一个学科方向之后,在研究范式上改变了以往“散论”的形式,开始从建设“文学史”的角度注重研究的系统性和规范性。但不同于当代其他文体研究,“散文研究”在建构学科规范之初就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什么是散文?这个问题对于小说、诗歌和戏剧研究并不构成挑战,尽管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让所有人都信服的“小说”、“诗歌”和“戏剧”定义,但这些文体较为明显的外在形式足以使它们外延清晰;而且,诗歌、小说和戏剧都有比较典型的艺术特征,如小说的“人物”、“叙事”,诗歌的“意象”、“语言”,戏剧中的“冲突”、“结构”,能够保证一个学科方向需要的内在规定性。当代散文研究没有这样的“天然优势”,现代散文的形式不具有相对的“规范性”,现代散文艺术也没有较为固定的法则,所以散文研究要树立学科规范就必须纯粹由研究者“主观”完成,这也构成了当代散文研究的难度。
散文文体的特点决定了当代散文研究的整体走向。散文史家刘锡庆先生在《世纪之交:对散文发展的回顾与思考》中这样概括当代散文研究的现状:“全部散文研究无非‘范畴论’(回答‘什么是散文’的问题)、‘特征论’(其‘审美特征’是什么)、‘创作论’(‘怎样写’散文)和‘鉴赏、批评论’(‘怎样欣赏、评论’散文)。其中‘范畴论’是全部研究的起点和基础……”⑤刘先生的概括反映出当代散文研究的总体思路:首先清理散文的“范畴”(回答“什么是散文”的问题),而后建构散文研究的学科规范。但是,由于散文是一种缺乏规范的文体,研究者在具体为散文划定范畴时就显得力不从心,什么是散文合理的“范畴”成为一大难题。而在由范畴论、特征论、创作论和批评论构成的散文研究体系中,如果没有稳定的“范畴论”作为基础,后三者就犹如“空中楼阁”:没有散文的范畴,何来确切的“特征”而言;没有确切的特征,何来科学的“创作方法”;而没有确定的散文范畴,散文批评的标准也显然无从建立。
散文“范畴论”之所以成为难题,原因在于研究者根本无法在古今中外的散文理论中找到可咨的参照。中国古代虽然有“诗文天下”的传统,但相对于诗歌在句式、格律探索上的文体自觉,散文没有基于一种外在形式而确立起某种“文体规范”,因此“正因为说到文章,就指散文,所以中国向来没有‘散文’这一个名字”。⑥而在西方,虽然散文创作十分发达,但为散文整体设定规范的做法更鲜有发生,所以散文在西方一直不是一种与小说、戏剧和诗歌同等的艺术文体。现代散文的建设者也试图为散文确定范畴,譬如郁达夫在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卷二》时就做过这样的尝试:“散文经由我们决定是与韵文对立的文体,那么第一个消极的条件,当然是没有韵文的文章。”“散文的第一消极条件,既是无韵不骈的文字排列,那么自然散文小说,对白戏剧(除诗剧以外的剧本)以及无韵的散文诗之类,都是散文了啦;所以英国文学论里有prose fiction prose poem等名目。可是我们一般在现代中国平常所用的散文两字,却又不是这么广义的,似乎是专指那一种既不是小说,又不是戏剧的散文而言。”⑦郁达夫用“排除法”为散文划定的范畴并没有多少研究的可借鉴性,因为“排除法”无法给予散文研究所需要的确定范畴。周作人的“美文”理论为现代散文文学地位的确立立下了汗马功劳,他将“艺术散文”(即“美文”)从散文的大家庭中分离出来,从而使“美文”成为文学中一种独立的文体,这也奠定了当代“散文研究”在文学研究内可以作为一个学科方向的基础。但当我们沿用“美文”理论时,什么样的散文才可称为“美文”?“美文”有没有共通的艺术规律可循?这依旧没有确定的答案。
所以,检讨当代散文研究存在的问题,研究者们热衷于为散文设定“规范”的做法应首先得到反思:散文是否具有“规范”?散文研究为散文设定的“规范”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合理前提?散文研究的学科规范是否必须建构在为散文设定“规范”的前提下?如果再进一步追问,是什么原因使研究者对散文的“规范”如此热衷,仅仅是因为建构学科规范的需要吗?当代散文研究成为一个学科方向的时间并不漫长,要促使其蓬勃发展,需要研究者多关注具体问题,但同时也不可忽略研究者的自我反思,否则就可能使研究陷入一种进退维谷的窘境。
二、“文体情感”与当代散文研究的“他者”
表面上看,当代散文研究热衷于为散文确立“规范”似乎是学科规范必然的结果,但如果我们深入这一领域的内部,“文体情感”因素也是不可忽略的原因。“文体情感”类似于我们熟悉的“民族情感”,是建立在一定族群共同体之上的自我维护心理。自当代文学研究内出现以文体划分出的不同学科方向后,各种文体研究领域都或多或少受到“文体情感”的影响。比较而言,散文研究受“文体情感”的影响最为强烈,因为自现代散文诞生以来,文学界对散文的“轻视”言论和看法一直或隐或显地存在,并波及到散文研究存在的合法性,所以研究者常常表现出对散文文学地位的有意维护,借用刘锡庆先生的话说:“散文必须是文学诸体之一。”⑧
当代散文研究的“文体情感”,如果说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还处于潜在状态,那么在“大散文”观和“散文文体净化”理论出现之后,表现就十分明显。在很多研究者眼里,“大散文”观和“散文文体净化”理论相互对立而存在,但如果我们追溯两者出现的动机,它们在维护散文文学地位的立场上其实异曲同工。“大散文”观由《美文》杂志主编贾平凹提出,他认为“散文是大而化之的,散文是大可随便的,散文就是一切的文章”;同时他又认为散文需要“大美”:“美是生存的需要,美是一种情操和境界,美是世间的一切大有”。⑨从贾平凹的言论中可见,他所呼吁的“大散文”实际包含两个层次的涵义:散文范围的“大”和散文审美境界的“大”。但是,“大散文”观提出之际恰逢余秋雨的“大文化散文”取得巨大成功,因此“大散文”观的拥趸们就只重视了后者而忽略了前者,“大散文”观在学界的实质内涵也就缩小为对“大境界”、“大气象”散文的召唤。
“大散文”观在传播中内涵的变易很值得注意,它固然受到“大文化散文”成功的刺激,但也不可忽略研究者因为“文体情感”而对“大散文观”的有意“误读”。现代散文自诞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个人的文学之尖端”,在社会效应、受关注程度方面往往不及诗歌、小说和戏剧,因此“大散文观”呼吁散文的“大境界”、“大气象”在某种程度就暗合了研究者要求提高散文地位的内心渴望,它致使研究者不自觉地完成了对“大散文”观的“误读”。⑩
“散文文体净化”理论是刘锡庆先生针对“大散文”观而提出的对当代散文发展的另一种看法。在坚持“散文必须是文学诸体之一,必须具备文学审美特性”这一学院派眼光下,刘先生认为“在当今(无论中、外)‘大散文’思想风靡文坛的情势下,欲规范散文必须先从清理‘大散文’的散漫、驳杂入手,高扬文学的大旗是极其必要的。文学的标尺一悬,‘是’‘非’立显,‘真’‘假’立辨。”(11)从刘先生的言辞中可以看出,“散文文体净化”针对的只是贾平凹“大散文”观中散文范围的“大”,与“大散文”观追求的散文审美境界之“大”并不冲突。并且,刘先生要求“高扬文学的大旗”、坚持散文“必备文学审美特征”的看法,与“大散文”观对“大境界”、“大气象”散文的呼吁还呈呼应之势,两者同样要求散文能够提高文学品质。
今天看来,“大散文观”和“散文文体净化”理论都有不切实际的偏颇之处,“大散文”没有让散文从此变“大”,“散文文体净化”也没有“净化”散文的自由发展,但它们在上世纪90年代能够引起轩然大波却并非偶然,因为研究界有着提高散文文体地位的共同心声,出现矫枉过正、盲目追捧的境况就可以理解。
“文体情感”的存在,一方面使研究者难以获得平静的研究心态,另一方面也使研究者不能摆脱各种外在思维的影响,从而在研究中形成了一个潜在的“他者”。当代散文研究热衷于为散文确立“规范”,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受到外在“他者”的思维束缚。
从本质上说,20世纪出现的各种“轻视”散文的言论并不是文体轻视。傅斯年在《怎样做白话文》里说散文“没有甚高的位置”,时值白话文学的开创期,其言论的主旨是警示“白话文运动”的同仁:“国语的文学”不能仅仅满足于已经初见成效的散文,只有创作出成熟的白话小说、诗歌、戏剧,才算是白话文的真正普及;朱自清对散文的“轻视”其实是一种自谦,他表面说散文不能算“纯文学”,其实是用文人的自嘲来说明自己开始写散文的原因;建国后《文艺报》散文座谈会对散文是文学“基本功”的看法是从文学教育的角度出发的,向大众普及文学教育,将散文作为文学“入门”的基本功,并不存在什么问题。但他们的言语修辞却可能导致接受者产生一种错觉:以为“文体规范”是“文学价值”的标准,文体规范多,文体价值就大;文体规范少,文体价值就小。这显然不符合文学评价的规律,文学价值只能由文学作品决定。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我们不可能因为散文的“规范”少,就忽略了周作人、鲁迅、郁达夫、朱自清、沈从文、柯灵、秦牧、贾平凹、余秋雨等散文大家的作品价值,就认为散文不及小说、诗歌、戏剧。只要是优秀作品,不管它们是以何种文体形式而存在,其价值都是不可替代的。但是,由于这种思维在现代影响巨大,散文研究者也就不自觉落于这种思维的陷阱,在研究中乐于为散文制定规范、划定范畴,最终将研究引入偏狭。
另一种影响当代散文研究的“他者”,是文学史编纂者的“现代性”功利思想。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写作,编纂者大多持有强烈的“现代性”意识,力图通过文学史来完成对于中国的“现代”想象。在这种文学史观之下,文学包容“现代”内涵的多少就成为文学评价的标准,文体的文学史地位也与它们承载“现代”内涵的能力联系在一起。而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各种文体中,小说、诗歌和戏剧因为承载了更多的现代性“宏大主题”,自然受到文学史家的青睐和重视,在文学史叙事中也占据了重要的篇幅。唯有散文,既在现代失去了传统社会中的“载道”功能,又与现代性“宏大命题”相隔绝,就不得不面对文学史叙述中的尴尬。现代散文的“立法者”周作人将散文认定为“个人的文学之尖端”,(12)同时还将之与各种功利思想决然分开:“中国新散文的源流我看是公安派与英国的小品文两者所合成,而现在中国情形又似乎正是明季的样子,手擎不住竹竿的文人只好避难到艺术的世界里去,这原是无足怪的。我常想,文学即是不革命,能革命就不需要文学及其他种种艺术或宗教,因为他已有了他的世界了。”(13)另一位为现代散文的“立法者”郁达夫虽然不否认散文的社会功能,但他特别强调了散文表现“社会功能”的方式:“一粒沙里见世界,半瓣花上说人情,就是现代的散文的特征之一。”(14)对散文承载“宏大命题”功能的削弱,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现代散文的文学品质,但也使散文在“现代性”功利思想指导下的文学史叙事中很难占据重要位置。
受“现代性”功利思维影响,散文研究者往往不能满足散文徜徉于“个人”的狭小天地,希望散文也能承载现代性“宏大主题”,从而提高散文的文体地位。在很多研究者看来,散文不能承担现代性“宏大主题”,是因为现代散文文体规范少,文学地位得不到足够承认,因此通过为散文建构规范,提高散文的文学门槛,就可能使散文承载更多的社会功能,上世纪90年代的“大散文热”就是这一思维形式的现实反映。
三、建构学科规范的可能性探索
散文的“反规范性”使当代散文研究建构学科规范的过程有着超越其他学科方向的难度,但它却是散文文体魅力的核心,如果散文的形式变得“规范”且一成不变,散文也就成了“八股文”,其文学生命也就从此枯竭。而且,就20世纪中国散文来说,其所以在文学史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价值和意义,也是由于其在“反规范”过程中不断的艺术创新。所以,当代散文研究在建构学科规范的过程中,应注意到散文“反规范”性的两面性,在为散文确立“规范”遭遇“瓶颈”的境况下,可以根据20世纪中国散文的具体成就多方探索建构学科规范的可能。
散文文体规范少确实造成了很多弊端,譬如创作队伍、创作水平的良莠不齐,使一个时代散文的艺术价值很难得到集中体现。但是,散文文体规范少也减少了作者参与和表达的壁垒,使散文能够更广博、更多元地反映一个时代的精神特质。现代散文创作有这样的特征:它是很多初登文坛作家的试验文体,又是很多成熟作家“返朴归真”后的文体首选。这种现象在鲁迅、巴金、孙犁、张中行、季羡林等人晚年的散文创作中可以得到充分的说明。文体规范少使散文创作常常陷入存在于“文学”与“非文学”之间的尴尬,但也给予了很多成熟作家更自由的表达空间,成为他们表达生命体验必不可少的渠道,从而展示出一个作家精神结构的多元性。我们可以通过鲁迅小说与散文创作时的心态对比来认识这一问题。小说和散文(杂文)是鲁迅一生创作的两种主要文体,但他对待两种文体的态度明显表现出巨大的差异。鲁迅谈自己创作小说态度时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15)可以看出,鲁迅进行小说创作时会考虑这种写作的社会意义,为了达到这些效果,他甚至不惜使用“曲笔”或故意的“油滑”。(16)相对于小说写作时的慎严,鲁迅创作散文(杂文)时就显得非常自由,个人性情的一面也自然地袒露出来:“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17)“我以为如果艺术之宫里有这么麻烦的禁令,倒不如不进去;还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摩自己的凝血,觉得若有花纹,也未必不及跟着中国的文士们去陪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之有趣。”(18)所以,对一个初接触鲁迅作品的读者来说,小说里的“鲁迅”与散文(杂文)里的“鲁迅”是不同的:小说里的“鲁迅”更纯粹、更统一,而散文里的“鲁迅”则更复杂、更多元。
散文创作的自由性使其更贴近作家的精神主体本身,从而可以成为我们梳理20世纪中国精神时的重要载体和最佳切入点。不能否认,小说、戏剧和诗歌也能够传达一个作家的精神结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更能体现作家精神的丰富性,但通过它们传递出作家的“丰富性”是作家经过理性整理并可以凝炼化的丰富性,作家精神世界中许多瞬间的、混沌的以及非理性的生命感受则更多在散文里保存下来。譬如鲁迅的《野草》,其光怪陆离的世界将鲁迅思想复杂、纠缠、多元、矛盾的特点完美地表达了出来。鲁迅思想的这种特质可以在其小说创作中得到部分体现,但其整体的形态却只能在散文里才可能自由地流淌出来。再者,散文文体规范少使其拥有最为庞大的创作队伍,因此在共时结构中能够更多元、更广博地反映一个时代的精神结构。这两方面优势,使散文在表现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的维度上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再者,散文在“反规范”过程中不断出现的文体“创新”,也是其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独特魅力所在。在各种现代文体中,文体内部“创新”最多的当数散文。从20年代的“小品”到30年代的“杂文”,再到40年代的“报告文学”、“特写”,直到今天的“大散文”,散文伴随时代发展不断有文体内的新形式出现,这是其他文体所不可匹及的。散文发展这种规律对散文研究很有启示意义:当我们觉得散文艺术没有相对稳定的规律可循时,我们是否注意到散文发展的独特性。小说、诗歌和戏剧虽然也会出现“文体”变革,但它们艺术的革新主要来自文体规范内部的突破。譬如诗歌,只要语言、意象任何一样发生实质性的变革,诗歌艺术就会发生一场革命;再如小说,只要小说叙事的重心、方式、视角等任何一样发生了具有革新意义的变化,小说的面目也就焕然一新。而散文艺术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主要来自文体革新,从小品文到杂文,再到报告文学、杨朔体、大散文;从周作人到鲁迅,再到沈从文、柯灵、杨朔和余秋雨,我们可以看到散文艺术的每一次发展都是以一种新体式出现作为标志。所以,就建构学科规范而言,小说研究可以通过“典型”、“叙事”,诗歌研究可以通过“语言”、“意象”,那么散文研究完全可以尝试通过“文体”来建构起自己的学科系统和学科规范。
应当说,散文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的独特意义还不止这些,但仅仅通过这些,当代散文研究已经可以获得巨大的发展空间,同时也不失为改变学界对散文看法的有效途径。所以,在当代散文研究遭遇“瓶颈”的时期,我们完全可以尝试反其道而行之,挖掘“反规范性”在20世纪中国散文发展中的积极意义,并将之理性化和系统化,或许可以为建构散文学科规范做出有益的探索。
注释:
①鲁迅:《小品文的危机》,见《鲁迅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92页。
②傅斯年:《怎样做白话文》,胡适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卷》,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出版公司,1935年,第218页。
③朱自清:《论现代中国的小品散文》,《文学周报》第345期,1928年11月25日。
④《复兴散文》,《文艺报》1982年第1、2期。
⑤⑧(11)刘锡庆:《世纪之交:对散文发展的回顾和思考》,《文学评论》1997年第2期。
⑥⑦(14)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卷·导言》,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出版公司,1935年,第1、3、9页。
⑨贾平凹:《美文·发刊词》,《美文》1992第1期。
⑩(12)(13)周作人:《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卷·导言》,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出版公司,1935年,第6-7、9、12页。
(15)鲁迅:《我怎样做起小说》,见《鲁迅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25页。
(16)鲁迅:《故事新编·序言》,见《鲁迅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53-354页。
(17)鲁迅:《野草·题辞》,见《鲁迅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63-164页。
(18)鲁迅:《华盖集·题记》,见《鲁迅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页。
标签:散文论文; 鲁迅论文; 鲁迅全集论文; 中国文学史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文学论文; 艺术论文; 当代作家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小说论文; 戏剧论文; 诗歌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