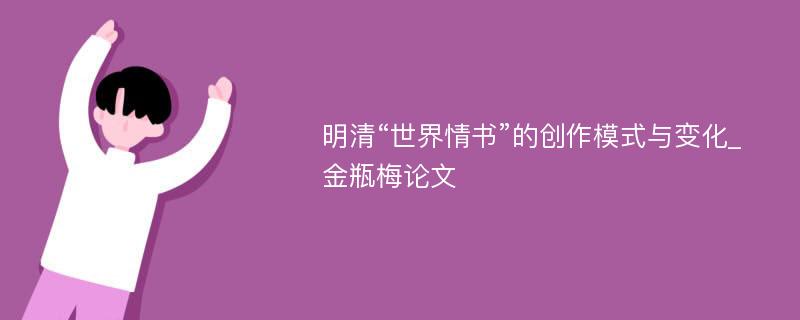
明清时期“世情书”的创作方式及其变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情论文,明清论文,时期论文,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10)06-0061-09
“世情书”,亦称世情小说,是明清小说创作中的一个重要流派。鲁迅先生曾将它视为明代小说的“两大主潮”之一: “当神魔小说盛行时,记人事者亦突起,其取材犹宋市人小说之‘银字儿’,大率为离合悲欢及发迹变态之事,间杂因果报应,而不甚言灵怪,又缘描摹世态,见其炎凉,故或亦谓之‘世情书’也。”[1]179“世情书”的问世,标志着古代章回小说由讲史、传奇、神怪向现实的转变。这一转变带来了小说观念与创作方式的一系列突破与革新,从此明清小说便进入了以“世情书”创作为主流的新时期。那么, “世情书”的创作方式是怎样的?其创作方式又发生过哪些变化?其变化的动因又是什么?对此,学术界还较少进行系统的探讨;即使有所论及,也往往是就创作论创作,较少考虑小说评点、读者接受以及出版传播等因素对创作的影响。鉴于此,本文尝试将“世情书”的创作、批评与传播等多种因素结合起来,对上述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世情书”的基本创作方式
“世情书”的发轫之作是《金瓶梅》,其创作植根于明中后期以“好货好色”为时代特征的市井文化土壤,同时又汲取了此前文学如《水浒传》、宋元话本戏曲等描写世态人情的创作经验,采用了一种以“写实”为主的创作方式,即主要取材于世俗社会,以家庭描写为中心,同时又涉及广泛的社会生活,讽喻世态人情。这一创作方式,后来经过《醒世姻缘传》、《林兰香》、《红楼梦》等的传承,便形成了“世情书”的基本创作方式。
首先,从创作意图看,“世情书”的作者或慨叹于家国兴亡,或有感于世风浇漓、人心不古,或因遭际坎壈而为炎凉所激……总之都是心存块垒无酒可浇,“不得已藉小说以鸣之”[2]553,其作品均寄托了作者对社会、人生的理解和追求。从素材来源看,“世情书”主要取材于现实生活,大都融注着作家个人的社会阅历和人生体验。如明欣欣子说:“吾友笑笑生为此,爰罄平日所蕴者,著斯传。”[3]176清张竹坡说:“作《金瓶》者,必曾于患难穷愁,人情世故,一一经历过。入世最深,方能为众脚色摹神也。”[4]42《红楼梦》则是曹雪芹根据其“半世亲见亲闻”创作的。《歧路灯》也是李绿园基于其亲身见闻特别是其家族子孙失教给他带来的精神隐痛,才创作出来的。从创作旨趣看,“世情书”的作者已不再靠故事性、传奇性吸引人,而把兴趣集中在对家庭生活琐事的描写上,靠真实地摹写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等来打动人。清罗浮居士《蜃楼志序》曾这样总结“世情书”的题材特点:“其事为家人父子、日用饮食、往来酬酢之细故,是以谓之小;其辞为一方一隅、男女琐碎之闲谈,是以谓之说。”[3]669 不过,“世情书”的作者并不局限于写一家一户的兴衰荣枯,而是有意通过家庭成员的“往来酬酢”,广泛地反映现实社会的世态人情,“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5]。如《金瓶梅》,既以西门庆家的日常生活、人事纠葛为中心,又通过西门庆的社交涉笔社会各阶层,致使上至朝廷,下及奴婢,雅如士林,俗若市井,无不众相毕露;其社会政治之黑暗,经济之腐败,人心之险恶,道德之沦丧,历历如在眼前,真可谓“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1]180。《醒世姻缘传》则描写了晁源、狄希陈两个财主家庭的兴衰,并以此为基点,将笔触伸向上至权贵、州官,下至地主、商人、儒林、僧道、农夫、婢仆等社会各阶层,一则暴露了当时官场的丑恶、官吏的贪婪、考场的舞弊,一则揭示了城乡的肮脏、农村的凋敝、民众的愚昧,交织成一幅纷纭驳杂的社会风情画。其他如《林兰香》、《红楼梦》写勋旧之家,《歧路灯》写“宦裔”之家,《蜃楼志》写洋商之家,也都以家庭描写为切入点,通过家庭的窗口,透视彼时社会的风俗人情。
其次,从创作原则及其描写手法看,“世情书”皆秉持较严格的写实原则,寓褒贬、讥刺于客观、冷静的写实之中。《金瓶梅》就擅长以白描手法描摹世态,见其情伪, “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1]180如第三十三回写韩道国当众自吹“行止端庄,立心不苟”,如何受西门庆器重,紧接着就有人赶来通报其老婆与小叔子通奸被抓之事。这种写法就是“直书其事,不加断语,其是非自见也”[6]。《红楼梦》采用的也是笔蓄锋芒而不露的“春秋笔法”,如它通过贾珍为秦可卿大办丧事的表现,就巧妙地影射了两人的乱伦关系。清人陈其泰即指出:“卑末之丧,哀礼过当,不已甚乎?此文心之妙也。秦氏初没,贾珍一则曰:比儿子强十倍,犹可言也。再则曰:长房绝灭。三则曰:尽我所有罢了。是何言欤?盖疼惜之深,匆忙之际,不觉失言,隐衷毕露;而焦大恶言,于斯验矣。手写此事,眼注彼事,内乱情形,跃然纸上;而无一言污墨秽笔,高妙绝妙。”[7]
再次,从结构方式看,“世情书”因为重在描摹家庭生活琐事,与之相应,它采用的也是一种更趋于生活化的网状结构,即以一个家庭的兴衰遭际、人物的命运变化作为艺术表现的中心,以家庭中主要人物的活动作为贯串各色人物事件的线索,通过主要人物的社会交往以及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纠葛来展开叙事,这样内外相应,纵横交错,就形成了一种井然有序的网状结构。如《金瓶梅》前七十九回,就是靠西门庆和潘金莲这两把“梭子”,各领一线,穿梭交叉,编织了一种杂而不越的网状结构。西门庆是全书的主要人物,他兼有破落户、市井奸棍、高利贷者、富商、官僚等多重身份,这使他既能结交太师、巡抚、御史、太监、州县官等中上层人物,又可以接触商人伙计、医生术士、和尚尼姑、帮闲地痞、妓女媒婆等三教九流,建立广泛的社会关系网。至于潘金莲,则在家庭内发挥了“单管咬群儿”的作用。西门府中妻妾之间的争风吃醋、奴仆们的钩心斗角等,几乎无不与她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因此,依靠这两个主线人物的上蹿下跳,左牵右扯,作者便把西门庆家庭内外各种复杂的人事关系有条不紊地扭合在了一起。受其影响,《红楼梦》也以贾宝玉、王熙凤为主线人物,让两人在贾府、大观园中各司其职,又彼此呼应,从而将小说中纷纭错杂的人事勾连在一起,编织得天衣无缝,使小说呈现出一种浑然天成的结构形态。其他如《醒世姻缘传》、《林兰香》、《歧路灯》、《蜃楼志》等,其结构方式也大体如是。
复次,从人物塑造看,“世情书”着意描绘的是世俗凡人,并且突破了以往小说在描写人物方面类型特征突出、个性色彩不够丰富的局限,不仅写出了人物性格的现实性,还写出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鲁迅曾说,《三国演义》“写好的人,简直一点坏处都没有;而写不好的人,又是一点好处都没有”[8]323。 《水浒传》、《西游记》在人物个性化描写方面固然有了长足进展,但是人物个性的历史内涵淡薄,时代特征模糊。《金瓶梅》则不同,它的一些主要人物形象,不但有独特的个性气质,而且带有浓烈的时代色彩。比如西门庆,在《水浒传》中只是个奸占妇女的恶棍,历史容量不大。《金瓶梅》却把他写成了一个由商而官、由官而商、亦商亦官的市井暴发户。这样的人物显然正是明中后期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商人阶层日益壮大的历史产物。虽说他奸诈贪残,自私好色,是个“混账恶人”,但作者并未把他“恶魔化”,而是写出了他性格的多重性。他有时能“救人贫难”,显得那样“轻财好施”;李瓶儿死后,他悲恸欲绝,又显得那样情深意真……这说明《金瓶梅》对人物性格复杂性的描写,乃是从生活实际出发,深入到人物纷杂的内心世界中,揭示出人物性格中相互矛盾的各个侧面,使之成为丰满深厚、个性生动的“真正的人”。《林兰香》、《醒世姻缘传》、《歧路灯》等也写出了人物思想性格的发展变化过程,并注意揭示这种变化的现实依据。至于《红楼梦》,更塑造出了一大批活生生的、个性鲜明复杂变化的人物形象。
最后,从语言特点看,“世情书”的作者为使小说语言与其所写的凡人琐事浑然一体,以强化作品的真实感,一般都采用生活化的口语、方言来写人叙事。如《金瓶梅》写的是市井俗人俗事,用的也是市井俗语。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说它写“市井之常谈,闺房之碎语”[3]176。张竹坡也说它是“一篇市井的文字”[4]45。近代人平子甚至说《金瓶梅》“不妙在用意,而妙在语句”,它荡除了文字(即典雅的文言或半文言)积习,纯用俗语,“读其文者,如见其人,如聆其语,不知此时为看小说,几疑身入其中矣”[9]。《醒世姻缘传》也“纯粹用土语为文,摹绘村夫村妇口吻,无不毕肖”[10]。《红楼梦》写的是贵族世家,故其语言要雅致一些,但也以口语为主,叙事写人皆恰如其分。
二、“世情书”的批评与创作
“世情书”虽然大多是秉持上述基本创作方式写成的,但是在不同时期不同的“世情书”那里,这种创作方式也在发生着不同方面、不同程度的变化和革新。造成变化和革新的动因是复杂的,但是彼时人们(包括作者本人)对通俗小说特别是此前“世情书”创作的看法与评价,无疑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之一。
《金瓶梅》问世后,很快就引起人们的关注与评论,当时不少文人学士纷纷通过序跋评点、书信、笔记等形式,揭示了它描写俗事俗人、“盖有所刺”等创作特点。如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说它“寄意于时俗”[3]176,廿公《金瓶梅跋》说它“曲尽人间丑态”[3]177。谢肇淛《金瓶梅跋》则具体指出它不仅写了“闺闼之媟语,市里之猥谈”,还写了“朝野之政务,官私之晋接”,并且写得“穷极境象,駴意快心”;至于“妍媸老少”之俗人,也写得各有个性,“不徒肖其貌,且并其神传之”[3]179。崇祯年间,还有人对《金瓶梅》进行删改与评点,指出《金瓶梅》是一部“世情书”,“此书只一味要打破世情,故不论事之大小冷热,但世情所有,便一笔刺入”[3]286。对于《金瓶梅》中的性描写,评点者或以为“此书诲淫”[11],或以为作者“知盛衰消长之机,取报应轮回之事”[3]176,“盖为世戒,非为世劝也”[3]178。这些看法对后来学步《金瓶梅》的“世情书”作者,无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清初,《续金瓶梅》的作者丁耀亢即认为:“一部《金瓶梅》,说了个‘色’字;一部《续金瓶梅》,说了个‘空’字。从色还空,即空是色,乃因果报转入佛法,是做书的本意。”(第四十三回)基于这种认识,他有意“以因果为正论,借《金瓶梅》为戏谈”[12],续演了西门庆、李瓶儿、潘金莲、陈经济等人轮回转世、报应不爽的故事。他还说:“世上风俗贞淫,众生苦乐,俱要说归到朝廷士大夫上去,才见做书的一片苦心。”(第五十八回)这其实也是对《金瓶梅》原有寓意的引申、发挥。《续金瓶梅》结尾写“大金人马,抢过东昌府来,看看到清河县地界。只见官吏逃亡,城门昼堵,人民逃窜,父子流亡……”就预示了纵欲不仅丧身、败家,还会亡国的严重后果。丁氏还由此出发,揭露了金兵屠城掳掠的残暴罪行,“意在刺新朝而泄黍离之恨”[13],这就进一步拓展了《金瓶梅》“指斥时事”[14]的创作题旨。
稍后于《续金瓶梅》,清初西周生创作的《醒世姻缘传》,也有意效法《金瓶梅》以家庭描写为中心来反映世态人情、借因果报应以劝善惩恶的创作思路,并自觉地继承了《金瓶梅》的写实精神,明确主张小说创作要“其事有据,其人可征”,反对“凿空硬入”[15]。书中对人情世态的摹绘相当真切、可信,如计氏自缢后打官司的过程,小珍珠自杀后种种人物诈取钱财的表演,科场考试的舞弊等,几乎形同实录。当然,它对素姐泼悍、狄希陈惧内等变态行为心理的描写,则未免过于夸张了。至于其语言,也效仿《金瓶梅》,“造句涉俚,用字多鄙”[15]。只是在性描写上,它比《金瓶梅》有所收敛,其《凡例》即云:“本传凡语涉闺门,事关床笫,略为点缀而止。不以淫哇媟语,博人传笑,揭他人帷箔之惭。”[15]
大约作于康熙年间的《林兰香》,则有意师法四大奇书并予以扬弃,如该书序称:“此书有《三国》之计谋而未邻于谲诡,有《水浒》之放浪而未流于猖狂,有《西游》之鬼神而未出于荒诞,有《金瓶》之粉腻而未及于妖淫。”[16]小说以耿家的日常生活为情节主线,旁及帝王更替、忠奸斗争、地方叛乱、外敌入侵、宫廷暴动等,描写极其广泛。其中有些朝政大事,如土木堡之变、石亨和曹吉祥谋反等,乃明代史事;其他如江南科考舞弊案、甘凉之乱等,虽属虚构,但亦有清初政事的影子。这些地方即借鉴了历史演义的写法。另外,它还抛弃了《金瓶梅》宣扬的“女人祸水”论,而带有才子佳人小说的艺术情韵,诸如肯定儿女真情,显扬女子才干,把日常生活诗意化等,就明显受当时流行的才子佳人小说影响,而其主旨也在于为“闺人之幽娴贞静堪称国色者”生色。因此,它实际是“《金瓶梅》一类正格世情小说与异流才子佳人小说融汇、渗透、发展而来的一部作品”[17]。
康熙年间,张竹坡对《金瓶梅》进行了细致评点,不仅以冷、热观点来诠释全书“描写世态,见其炎凉”的创作旨趣,还指出作者有意“作秽言以泄其愤”、“作秽言以丑其仇”[4]8。并说作者虽然“作寓言以垂世”[4]1069,但其艺术描写颇合情理,所谓“做文章不过是情理二字。今做此一篇百回长文,亦只是情理二字”[4]38。这些论断对此后曹去晶创作《姑妄言》似有较大影响。例如,与曹氏过从甚密、深知其创作情况的林钝翁(疑即作者本人),即指出曹氏出于泄愤,有意以秽言诋辱阮大铖等奸贼,所谓“欲极辱大铖,以雪众忿,不如此写,不足以尽其恶”(第八回回评);并毫不讳言:“此一部书,都无中生有,极言善恶报应,警醒世人耳。”(第十六回回评)其第八回回评还把《金瓶梅》称为“小说之祖”,认为“作小说者,不过因人言事,随笔成文”,只要“意虽假而理真”;第三回夹评也说: “此一部书,总不越‘情理’两个字,即写此等没要紧处,亦情理所必然,所以为妙。”[18]
至于曹雪芹,也是从尖锐地批评“历来野史”、“风月笔墨”、“佳人才子”等书入手,开始《红楼梦》创作的。他在小说第一回中就指斥“风月笔墨,其淫秽污臭,涂毒笔墨,坏人子弟”,批评“佳人才子等书,则又千部共出一套”,“不大近情理”,一再申明自己要破除这些陈腐旧套,只据亲历见闻及事体情理来写,以便“令世人换新眼目”。譬如,他对《金瓶梅》虽亦有所借鉴,但“亵嫚之词,淘汰至尽。中间写情写景,无些黠牙后慧。非特青出于蓝,直是蝉蜕于秽”[19]。对才子佳人小说,他则打破了该类小说所写的一见钟情、私订偷盟、小人拨乱、及第团圆的创作模式,描写了一种建立在长期了解基础上的纯真、专一的知己之爱及其不幸结局;他也不像才子佳人小说那样刻意美化女性,而是真实地、有分寸地展示了红楼女子们本色的、鲜活的、富有个性的才情品貌。如脂砚斋在评点贾珍之妻尤氏时即指出:“尤氏亦可谓有才矣。论有德比阿凤高十倍,惜乎不能谏夫治家,所谓‘人各有当’也,此方是至理至情。”(第四十三回夹批)他还指出曹雪芹真实地写出了红楼女子们的“陋处”:“可笑近之野史中,满纸羞花闭月、莺啼燕语,殊不知真正美人方有一陋处……。今见‘咬舌’二字加之湘云,是何大法手眼敢用此二字哉?不独不见其陋,且更觉轻巧娇媚,俨然一娇憨湘云立于纸上,掩卷合目思之,其‘爱’、‘厄’娇音如入耳内。然后将满纸莺啼燕语之字样,填粪窖可也。”(第二十回夹批)清海圃主人《续红楼梦楔子》也曾这样评价曹雪芹的艺术创新:“趋俚入雅,化腐为新……其尤奇者,缘之所限,迹不必合,而情之所系,境无终睽,为千古才士佳人另开生面,而终以空诸所有结之。”[20]164
稍后于《红楼梦》的《歧路灯》,也是一部别开生面之作。该书序言就揭示了李绿园的创作宗旨及特点:“先生以无数阅历,无限感慨,寻出‘用心读书、亲近正人’八字,架堂立柱;将篇首八十一条家训,或反或正,悉数纳入。阐持身涉世之大道,出以菽粟布帛之言,妇孺皆可共晓。尤善在避忌一切秽亵语,更于少年阅者大有裨益。”[21]103可见该书虽描摹世态人情,却旨在探讨子女教育问题,故有人称之为教育小说。作者在第十一回中曾借人物之口这样评价《金瓶梅》:“那书还了得么!开口‘热结冷遇’,只是世态炎凉二字。后来‘逞豪华门前放烟火’,热就热到极处;‘春梅游旧家池馆’,冷也冷到尽头。大开大合,俱是左丘明的《左传》,司马迁的《史记》脱化下来。”可见他对《金瓶梅》以史传笔法摹写世态炎凉的写实精神是有深切体认的,不过对它的淫秽描写又颇有微辞,认为它是“诲淫之书”,表明自己“矫揉何敢效《瓶梅》”。因此,他既继承了《金瓶梅》的写实笔法, “以左丘司马之笔,写布帛菽粟之文章”[21]37,又涤除了“一切秽亵语”。
此外,产生于嘉庆年间的《蜃楼志》,也对“世情书”的写法有所突破。其书序言批评了一些小说的俗套与弊病,认为“谈神仙者,荒渺无稽;谈鬼怪者,杳冥罔据;言兵者,动关国体;言情者,污秽闺房;言果报者,落于窠臼。”而《蜃楼志》所写则是真实的粤东琐事与本地风光,“其书言情而不伤雅,言兵而不病民,不云果报而果报自彰,无甚结构而结构特妙,盖准乎天以立言,不求异于人而自能拔戟别成一队者也”[2]669。
由上所论可见,《金瓶梅》之后“世情书”的创作,是在人们不断地认识、反思、批评此前小说的语境中进行的,后出之作对此前之作既有因循和效仿,亦有探索和革新。这既保持了“世情书”创作的优良传统,丰富了“世情书”的创作理论,也不断地革新了“世情书”的创作方式,从而使“世情书”的创作保持了鲜活的艺术生命力。
三、“世情书”的读者与创作
“世情书”的作者大多有较独立的创作意识,一般不会违背其创作旨趣去刻意迎合读者的欣赏口味和阅读习惯,如曹雪芹所说:“我这一段故事,也不愿世人称奇道妙,也不定要世人喜悦检读。”(《红楼梦》第一回)不过,出于对现实人生的关注和教化民众的社会责任感,作者在创作时也不能不考虑读者的阅读心理和作品的接受效果。例如《金瓶梅》的作者在小说中就经常警醒“看官”,务使“看官”明白其创作的良苦用心,以便能引以为戒。请看以下数例:
小说第二十二回写西门庆与仆妇宋惠莲私通,作者议论道:“看官听说:凡家主,切不可与奴仆并家人之妇苟且私狎,久后必紊乱上下,窃弄奸欺,败坏风俗,殆不可制。”第三十一回写吴典恩受西门庆接济,后来却恩将仇报,作者议论道:“看官听说:后来西门庆死了,家中时败势衰,吴月娘守寡,被平安儿偷盗出解当库头面,在南瓦子里宿娼,被吴驿丞拿住,教他指攀吴月娘与玳安有奸,要罗织月娘出官,恩将仇报……。正是:不结子花休要种,无义之人不可交。”第四十回写吴月娘引尼姑进门宣卷,作者议论道:“看官听说:但凡大人家,似这等尼僧牙婆,决不可抬举。在深宫大院,相伴着妇女,俱以谈经说典为由,背地里送暖偷寒,甚么事儿不干出来?”第七十八回写玳安与贲四老婆通奸,作者议论道:“看官听说,自古上梁不正则下梁歪,原来贲四老婆先与玳安有奸,这玳安刚打发西门庆进去了……他就和老婆在屋里睡了一宿。有这等的事!”第七十九回写西门庆纵欲亡身,作者议论道:“看官听说,一己精神有限,天下色欲无穷。又曰‘嗜欲深者生机浅’,西门庆只知贪淫乐色,更不知油枯灯灭,髓竭人亡……”第八十回写帮闲应伯爵见利忘义,作者议论道:“看官听说,但凡世上帮闲子弟,极是势利小人。当初西门庆待应伯爵如胶似漆,赛过同胞弟兄,那一日不吃他的,穿他的,受用他的。身死未几,骨肉尚热,便做出许多不义之事。”
从上述例子即可看出,作者写西门庆、尼姑、帮闲、小人等如何如何,都明显带有为世人说法的用意,诚如丁耀亢所说,作者“原是替世人说法,画出那贪色图财、纵欲丧身、宣淫现报的一幅行乐图”。不过,丁氏又认为《金瓶梅》作者的创作苦心很少被人领会,多数读者“看到‘翡翠轩’、‘葡萄架’一折,就要动火;看到加官生子、烟火楼台、花攒锦簇、歌舞淫奢,也就不顾那髓竭肾裂、油尽灯枯之病,反说是及时行乐;把那‘寡妇哭新坟’、‘春梅游故馆’一段冷落炎凉光景看做平常”,致使“这部书反做了导欲宣淫话本” (《续金瓶梅》第一回)。
鉴于《金瓶梅》多为世人所误读,丁氏才“就着这部《金瓶梅》讲出阴曹报应、现世轮回”,重新“替世人说法,做《太上感应篇》的注脚”(第六十四回)。丁耀亢的续作多数章节的正文开头都借《太上感应篇》或其他儒释道理论对读者进行“说法”,然后继之以相应的故事对“说法”进行“参解”,以期警示读者。书中劝惩内容颇多,尤以惩淫为主,作者自言“恐正论而不入,就淫说则乐观”[12],故其书中仍多杂“淫说”,这无疑继承了《金瓶梅》以淫止淫的创作思路,不过为了不致“落了导欲的淫书,反添口孽”的后果,作者在“妆点淫乐光景”时,又及时地写出淫行带来的恶果,不像《金瓶梅》前大半部分对淫行津津乐道,到后来才给予惩罚。这种写法也可以说是对《金瓶梅》的反拨、矫正吧。
西周生作《醒世姻缘传》,也意在“醒世”劝民,故其书“多善善恶恶之谈”,“盖谓人前世既有造业,后世必有果报,既生恶心,便成恶境,生生世世,业报相因,无非从一念中流出;若无解释,将何底止?……此正要人豁然醒悟”。对于淫秽描写,考虑其负面效果,作者则声称“不以淫哇媟语,博人传笑”。如第二十六回涉及人物淫行时,作者就说:“此事只好看官自悟罢了,怎好说得出口,捉了笔写在纸上?”当然,作者终究未能免俗,书中仍保留了部分秽语。在语言使用上,作者也充分考虑了读者的接受水平,如《凡例》即云:“本传敲律填词,意专肤浅,不欲使田夫、闺媛懵矣而墙,读者无争笑其打油之语。”[15]
曹去晶的《姑妄言》,也承袭了《金瓶梅》以淫止淫的写法,有意“借淫说法警人淫”。如他在该书第七回中说:“淫人妻女,妻女人淫。虽然是个八字,但只四个字,上面的四字,何等之乐,下面只转换一转换,何等之苦。仔细一想,这个淫字就可化为乌有了。”本回夹评也说:“这一段才是书者之本意,那许多淫秽的事,千言万语不过是这几句的引头,看者需知作者之心。”同样,作者写赌博及其危害,也意在劝人戒赌,其第二十回评语中即说:“详写曾嘉才之妻女子媳者,因一赌字,以至家破人亡,可见赌字大害,一至于此。贪赌之流见之,亦知稍警醒否?作者之意是要劝诸人不可如此,切勿错会起来,竟去效颦。不但负作者之心,真成一大笑话矣。”书中对趋炎附势之徒的针砭,也是为劝醒读者,如第二十三回评语所论:“写关爵、阎良、傅厚一段,不但是为劝醒炎凉世态中人,更见得世事变迁,小人之心肠眼孔,不可只看目前也。总是作者一笔不肯放松,一人不肯漏去。”
曹雪芹对读者的阅读口味也有很清醒的认识,他在《红楼梦》第一回中就指出“市井俗人喜看理治之书者甚少,爱适趣闲文者特多”,“贫者日为衣食所累,富者又怀不足之心,纵然一时稍闲,又有贪淫恋色、好货寻愁之事,那里去有工夫看那理治之书?”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迁就读者的阅读口味,而是大胆创新,要“令世人换新眼目”,把读者从陈旧的才子佳人小说、艳情小说创作套路中解脱出来。他抛弃了以往小说“胡牵乱扯”、 “不大近情理”的做法,其“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1]234,同时又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结果“把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8]338。
令人遗憾的是,“深受才子佳人小说熏染的读者,难以理解《红楼梦》的精神实质,许多人以才子佳人小说模式与风格改写《红楼梦》,以‘补恨’为宗旨的‘续红’之作纷纷出笼,搬演了一出出庸俗的喜剧”[22]。清花月痴人《红楼幻梦·自序》即说:“凡读《红楼梦》者,莫不为宝黛二人咨嗟,甚而至于饮泣,盖怜黛玉割情而夭,宝玉报情而遁也”,“于是幻作宝玉贵,黛玉华,晴雯生,妙玉存,湘莲回,三姐复,鸳鸯尚在,袭人未去,诸般乐事,畅快人心,使读者解颐喷饭,无少欷歔。”秦子忱作《续红楼梦》,也是欲“使有情者尽成眷属,以快阅者心目”[20]156。归锄子作《红楼梦补》,也意在“以快读者之心,以悦读者之目”[20]183。陈少海《红楼复梦·凡例》还说:“读此书不独醒困,可以消愁,可以解闷,可以释忿,并可以医病。”并说:“卷中无淫亵不经之语,非若《金瓶》等书以色身说法,使闺阁中不堪寓目。”这些刻意媚俗之作,当然都是狗尾续貂。
李绿园作《歧路灯》,则是要为青年学子点亮一盏歧路明灯,劝诫世人教子要严,延师要正,交友要慎。在创作时,他处处考虑给读者以正面影响,涉及人物淫行时,也总是一笔带过,并反复声明:“此处一段笔墨,非是故从缺略,只缘为幼学起见,万不敢蹈狎亵恶道,识者自能会意而知。”(第四十三回)“每怪稗官例,丑言曲拟之。既存惩欲意,何事导淫辞?”(第二十四回)“坊间小说如《金瓶梅》,宣淫之书也,不过道其事之所曾经,写其意之所欲试,画上些秘戏图,杀却天下少年矣。”(第九十回)
由此可见,“世情书”的作者在创作时的确考虑了如何影响读者的问题,究竟是消极地迁就读者的阅读口味,还是积极地改变读者的阅读期待,这直接影响到其作品的创新程度与艺术品位。曹雪芹创作的巨大成功,就表明“作家完全可以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读者大众”[23];而续书的失败,则证明一味哗众取宠,不仅销蚀了作者的独创性,而且也经不起读者的检验,注定会沦为人们笑谈讥讽的对象。
四、“世情书”的出版与续作
“世情书”的代表作家,之所以从事小说创作,并非是为“稻粱谋”,这就使其创作较少受文化市场需求的制约,能体现其本人对社会人生的独特体验和审美追求。不过,一部作品若要产生广泛的社会反响,并对后来的创作发生较大影响,仅靠辗转传抄是难以实现的。如《姑妄言》、《歧路灯》,因写成后未能付梓,只在小圈子里抄录流传,故知之者甚少,其影响也很有限。《金瓶梅》最初也是以手抄本的形式在部分文士中传播的。明人谢肇淛在《金瓶梅跋》中曾说:“《金瓶梅》一书,……向无镂板,钞写流传,参差散失。”后来,冯梦龙于沈德符处“见之惊喜,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沈氏觉得“此等书必遂有人板行,一刻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未予允诺;可“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14]。从此《金瓶梅》便很快流行开来,并由此开启了“世情书”创作流派。
《红楼梦》开始也是以抄本形式流传。后来书商程伟元竭力搜罗《红楼梦》原书、续书的各种抄本,与其友高鹗一起将搜罗到的《红楼梦》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拼接起来,“截长补短,抄成全部”,镌板印行,使《红楼梦》风靡一时[2]588。逍遥子《后红楼梦序》说:“曹雪芹《红楼梦》一书,久已脍炙人口,每购抄本一部,须数十金。自铁岭高君梓成,一时风行,几于家置一集。”于是,“操觚之士,慕其获利之厚,觍颜续貂,强为邯郸之学步。后先迭出,名目繁多,如《风月梦》、《红楼再梦》、《红楼圆梦》、《续红楼梦》、《后红楼梦》、《疑红楼梦》、《疑疑红楼梦》、《大红楼梦》、《绮楼重梦》、《大红楼题解》等,为书不下数十馀种,核其情节,无非为黛玉吐气,重谐好事而已。”[2]648
作为《红楼梦》的第一部续书, 《后红楼梦》的作者逍遥子,还伪称此书也出自曹雪芹之手,如其序言所说:“同人相传雪芹尚有《后红楼梦》三十卷,……顷白云外史散花居士竟访得原稿,并无缺残。……洵为雪芹惬意笔也。爰以重价得之,与同人鸠工梓行,以公同好。”有趣的是,该书结尾还写“黛玉、宝钗就捧了一只拜匣上来,贴一个红签,写着‘前后《红楼梦》润笔’”,雪芹揭开一看,“约费有三四万金”,乃戏言:“从古及今,做稗乘的获报,哪有雪芹这样便宜。”其附骥曹氏以牟利的嘴脸,真乃昭然若揭。
可以说,多数“续红”之作,都是书坊主与下层文人出于牟利动机,利用广大读者阅读《红楼梦》产生的缺憾心理,及时炮制出来的。这从它们的编创方式即可窥见一斑。这些小说都有大致相同的创作旨趣,即让宝玉科举入仕,妻妾成群,重振家业,以“使吞声饮恨之《红楼》,一变而为快心满志之《红楼》”[20]156。在续法模式上,它们或写主要人物还魂再生(如《后红楼梦》、《红楼圆梦》、《红楼梦补》、《红楼幻梦》等),或写主要人物转世托生(如《绮楼重梦》、《红楼复梦》等),或写阴阳两界交相感应(如《续红楼梦》、《补红楼梦》等),从而演绎了一场场以功名遇合为核心的俗世情缘。其具体创作又多以模拟、抄改为主。如逍遥子《后红楼梦》第十回《惊恶梦神瑛偿恨债 迷本性宝玉惹情魔》,就明显模仿《红楼梦》第五十七回《慧紫鹃情辞试忙玉 慈姨妈爱语慰痴颦》;其第十一回《昏迷怨恨病过三春 欢喜忧惊愁逢一刻》,有意抄袭《红楼梦》第九十六、九十七回写宝玉成亲、黛玉焚稿等情节。这种模仿、抄改原著的现象,在续书中屡见不鲜。且续书与续书之间也存在辗转抄袭的情况。如嫏嬛山樵一面讥讽《续红楼梦》等书所写的“还魂转世之谬”,一面又在编创《补红楼梦》时大量抄袭《续红楼梦》,该书第一回至六回、第八回、第十一与十二回、第十五回至第十九回、第二十四回,就整回或整段地抄改自《续红楼梦》。作者在卷首题记中还广而告之曰:“兹者先刻四十八回,请为尝鼎一脔,尚有增补三十二回,不日嗣出,读者鉴之。”果然,《增补红楼梦》三十二回旋即推出,作者于自序中复言:“曩作《补红楼梦》四十八回,余友咸以为可,趣付梨枣后,已忘为东施效颦,乃增补三十二回。”
有的书坊主,如务本堂主人讷音居士,还亲自编撰了《三续金瓶梅》。他在自序中指出《隔帘花影》对西门庆、庞春梅的处理不尽人意,因此他要“法前文笔意,反讲快乐之事,令其事事如意,为财色说法,一可悦人耳目,引领细观。再看财色始终是真是假,因果报应,一丝不漏,可不慎乎?”在第一回中,他还说:“《红楼》五续甚清新,只为时人赞妙文。我今亦较学三续,无非傀儡假中真。”可见其续《金瓶梅》也是受“续红”热的刺激。该书有些语言或小情节即抄自《红楼梦》,不过变相抄袭《金瓶梅》更多。如《金瓶梅》中西门庆一妻五妾,此书亦然;《金瓶梅》中吴神仙相面、胡僧药、交通蔡太师、接待蔡状元等情节,都被改头换面,抄入本书中。至于人物性格也多与《金瓶梅》相似,书中六娘冯金宝就有潘金莲的影子。诸如此类,皆可见出书坊主炮制小说之本色。
综上所述,“世情书”作为明清小说创作的主流之一,有其基本的创作方式;不过,由于受小说批评、读者接受等因素的影响与制约,“世情书”在发展过程中,其创作方式也曾出现不同方面、不同程度的变化与革新;至于“世情书”代表作的出版、畅销以及由此引发的续书热,则又得力于书坊主的商业运作。因此,只有综合考虑这些因素的影响,才能对世情书的创作方式及其变化动因作出较有说服力的阐释。
收稿日期:2010-05-20
标签:金瓶梅论文; 西门庆论文; 红楼梦评论论文; 醒世姻缘传论文; 读书论文; 文学论文; 文化论文; 红楼梦论文; 歧路灯论文; 蜃楼志论文; 林兰香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