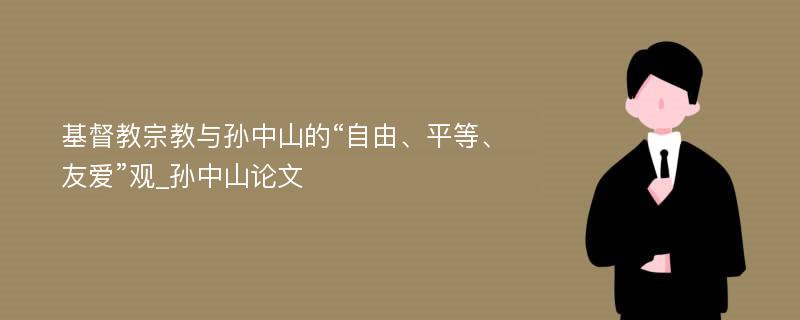
基督宗教与孙中山之“自由、平等、博爱”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博爱论文,基督论文,平等论文,宗教论文,自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072(2012)12-0111-10
1906年秋冬间,年届四十的孙中山在日本与黄兴、章太炎等制订《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时,首次揭橥“自由、平等、博爱”之鼎革大旗,明确指出:“我等今日与前代殊,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外,国体民生尚当与民变革,虽纬经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故前代为英雄革命,今日为国民革命。所谓国民革命者,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即皆负革命之责任,军政府特为其枢机而已。”[1]296众所周知,“自由、平等、博爱”乃18世纪法国大革命高呼之“三位一体”政治口号,亦为鼓倡“天赋人权”观念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们所追求之社会变革理想,并成为法国资产阶级反对、推翻封建等级特权与君主专制制度之宪政纲领。孙中山欣然接受西方文明长期发展过程中融冶陶炼而成之“自由、平等、博爱”理念,并将其载入《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力图使之成为中国人民的精神支柱和社会变革的思想指引,乃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之鼎革创举。它表明以孙中山为核心的民主主义者“不愧为法国18世纪末叶的伟大宣传家和伟大活动家的同志”,标志着“东方已完全走上了西方的道路”。[2]291-292事实证明,“自由、平等、博爱”自此成为孙中山推翻满清王朝、建立共和国家、造福中华同胞之终极理想与毕生追求。
“自由、平等、博爱”是基督宗教两千多年来冶铸锻砺出来的核心价值理念,亦是现代西方文明的重要普世价值。①纵观孙中山的一生,笔者以为,他首先是一个深受现代西方文明熏染之基督徒,然后才是一名悬壶济世之现代医师,进而为一位从事“医国事业”之伟大改革家。我们在考察孙中山“自由、平等、博爱”观时不难发现,其形成之根本原因,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对基督宗教核心价值理念之深刻理解与切身体悟。②
一、基督宗教信仰与孙中山救国济民思想之萌生
毋庸置疑,孙中山于中国历史发展之最大功绩,乃是推翻满清帝制,缔创共和政体。史学界习以“革命”二字概之。但笔者以为,“革命”一词不足以涵盖孙中山终身服膺与践行之“救国济民”宏志,而仅为其一端。
人的世界观的形成、价值观的构建乃至思想理念的确立,无疑与其所受到的教育及所接触、认同的文化休戚相关。孙中山亦不例外。他所接受的是基督教会学校的西式教育,他所接触、认同的文化更多的是以基督宗教为核心价值理念的现代西方文明。孙中山少年时代即与基督宗教结下不解之缘,直至其生命之终结。1879年至1892年,也就是13岁至26岁期间,孙中山先后在檀香山(Honolulu)、广州、香港的基督教会学校接受完整的西式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1884年,18岁的他在香港领洗皈依耶稣基督,且终身坚持自己的信仰;他长期居住、奔走于以基督宗教思想文化为根基之欧美地区,是一位饱受现代西方文明影响的中国进步知识分子。
孙中山曾先后就读于五所基督教会学校,其中有三所为西方人在中国所创办。欧美教会教育之肇始与兴盛,无疑与教会推广、传布基督宗教普世价值观之宗旨密切相关。西方人在华创办教会教育之目的,乃是期冀受教育者皈依耶稣基督,献身教会事业,并在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结构之外造就一个殷实的教民阶层,“使他们能够胜过中国的旧式士大夫阶层”,接受西方的文化观念和价值标准,以西学素养“走上崇高的和成功的职业道路”,[3]97-99进而成为中国社会政治的中坚力量。深受教会教育染濡的孙中山,一生所追求与践行的基本上就是这样一条道路。由此可见,基督宗教对孙中山一生的思想和实践均影响甚大。
孙中山幼年之时,家境贫寒,其兄孙眉被迫于17岁(1871年)时赴檀香山谋生。孙眉凭借自己的勤劳和智慧,逐渐在檀岛积聚了一些财富,孙家的状况才渐趋好转。1879年5月21日,孙中山随母亲乘英国火轮船“格兰诺去”号(S.S.Grannock)从澳门出发首赴檀香山。登上火轮船,孙中山惊叹“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4]47。这不仅表明他在思想上开拓了新的境界,而且揭示其在生命中获得了新的启示。后来孙中山在檀香山受英美教育日久,逐渐明白,其所乘火轮船之船长和船员皆为基督徒,该船之铁梁、机器等均由基督徒发明;其所耳濡目染、置身其中之西方建筑、音乐、礼仪,西人之世界观、生活方式乃至行为举止,无不深受基督宗教之影响,西方文明之根基更是基督宗教之核心价值。在年轻的孙中山看来,基督宗教似乎就是现代化的标志。自然而然,他对这一宗教产生了莫大的兴趣。当然,孙中山最初对基督宗教之仰慕,还不完全是出自宗教信仰之故,而是正如其所言,乃“慕西学之心”。[5]189其后,他更清楚,基督宗教亦即西方文明之根、西学之源。
孙中山母子抵达檀香山后,“是年母复回华,文遂留岛依兄,入英监督所掌之书院(Iolani College,Honolulu)肄业英文”[4]47。这所Iolani College——意奥兰尼学校,乃英国圣公会(Church of England,亦译“英国国教会”)夏威夷教区主教韦礼士(Alfred Willis)1872年所创办。自此,孙中山开始正式接受完全的基督宗教教育,浸润于基督宗教文明。1882年夏从意奥兰尼学校毕业后,孙中山又于翌年初“再入美人所设之书院(Oahu College,Honolulu)肄业”[4]47。此Oahu College——瓦胡书院,由美国海外传教委员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亦译“美国公理会差会”,俗称“美部会”)1841年所创办,初衷为教育本会传教士自己的子女。1867年9月17日修订之该校《校规》规定:“每天上课前必须朗诵《圣经》数段,然后祈祷……每周必须有一课的时间用于朗诵《圣经》。”[6]26③事实上,孙中山所就读的是瓦胡书院之预备学校(Preparatory School),且“初拟在此满业,即往美国入大书院,肄习专门之学”[4]47。在该校,孙中山真正开始对基督宗教产生浓厚兴趣。他积极参加学校的宗教活动,对《圣经》所包含之“自由、平等、博爱”理念大加赞赏,并准备皈依耶稣基督。然而,其兄孙眉“因其切慕耶稣之道,恐文进教为亲督责,着令回华”[4]47。
1883年8月,回翠亨村稍作停留的孙中山便抵达香港,入读由英国圣公会创办之香港拔萃书室(Dioceson Home,Hongkong),时约半年。[7]19-201884年4月15日,孙中山复转至香港中央书院(Government Central School,1894年更名为Queen's College——皇仁书院)就读。在香港,由于没有兄长孙眉的约束,孙中山遂深入接触中西传教之人,与基督教会渐行渐近。1884年5月4日,由美国公理会(American Congregational Church)传教士喜嘉理(Charles Robert Hager)牧师主持,孙中山正式领洗成为基督徒,取名“日新”,盖取《大学》“汤之《盘铭》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义。入教后,孙中山曾于1884年夏天协助喜嘉理牧师在香港、澳门及珠江河畔等地传教,分售《圣经》及宣传单张,并劝说两位朋友入教。孙中山领洗皈依耶稣基督之时,无疑对基督宗教充满极高之热情,但他的这种热情并非纯粹发端于宗教信仰本身,而是来自于基督宗教所以产生之实用效果。他深切感悟到,基督宗教能够与时俱进,不断自我更新,以满足人类对现代化如饥似渴之需求;而反观中国之儒家、佛家和道家,它们均往后看而非向前看,捆绑中国两千余年,令中国裹足不前。孙中山通过对中西宗教理念之深刻比较,愈发认识到,只有基督宗教所产生之实用价值(而不纯粹是其宗教信仰),才是催生中国现代化之重要手段。[8]152
1886年秋,孙中山由喜嘉理牧师介绍至广州博济医院(Canton Hospital)附设之医校习医。博济医院乃1835年由美国医学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创立,附属医校则成立于1855年。[5]3581887年10月,孙中山因香港“学科较优,而地较自由,可以鼓吹革命”[9]229,转至新成立的香港西医书院(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Hongkong)就读。该校由英国伦敦传教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传教士康德黎(James Cantlie)等人发起创办。1891年,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读四年级时,曾参与创立“教友少年会”。6月,他在上海广学会出版的《中西教会报》上发表《教友少年会纪事》,鼓励教友巩固“圣道”。[10]
如前所述,一个人所受之教育及所接触、认同之文化对其世界观的形成、价值观的构建乃至思想理念的确立至关重要。我们由孙中山的成长经历可知,基督宗教是其最早接触到、同时也对其影响至深的文化形态;宗教信仰经历,无疑更是形成其仰慕代表现代西方文明之根的基督宗教的重要因素。虽然他后来接受进化论,在理智上曾与基督宗教渐行渐远,甚至被同道者指出“先生为教徒,但永不见其至教堂一步”[11]822;但在感情上,他却不愿意否定自己青年时期的信仰追求。孙中山一直虔心维护基督宗教。1922年,他声明:“予孰非基督徒者?予之家庭且为基督徒之家庭。予妻、予子、予女、予婿,孰非基督徒乎?”[12]266孙中山病逝后,宋子文曾说:“孙于弥留之际曾言彼当以基督教徒而死……因孙有前言,决议虽其党中同志多非基督徒,而仍举行宗教式家祭礼。”[13]此足见基督宗教对孙中山思想信念与生活方式影响之深。
在香港西医书院求学时,孙中山开始接触达尔文(Charles Darwin)之进化论,并言“于西学则雅癖达文之道(Darwinism)”[4]48。同时,他亦称,“予于耶稣教之信心,随研究科学而薄弱。予在香港医学校时,颇感耶稣教之不合伦理,固不安于心,遂至翻阅哲学书籍。当时予之所信,大倾于进化论,亦未完全将耶稣教弃署也。”[14]由此可见,孙中山虽身为基督徒,却不妨碍他后来在哲学上对自然世界的阐释蕴含唯物论和无神论的色彩。
在孙中山的潜意识中,基督宗教之普世价值观乃是其救国济民理想之依归,否定基督宗教就等于否定自己矢志不渝之救国济民追求。他毕生都有一种“济世情结”,而这种“济世情结”又寄托于基督宗教。所以,“济世”在其一生中发挥着“信仰”的功能,成为其救国济民行动之原动力。也正是这种“济世情结”,使孙中山接受基督宗教,直至生命终结亦不否认自己之基督徒身份。[15]250有关基督宗教对孙中山救国济民思想之萌生,可从如下几个方面得到印证:
首先,基督宗教之现代化特性乃孙中山救国济民思想萌生之学理基础。面对极为深重的民族危机,深受现代西方文明浸润的孙中山发现,抱残守缺、愚昧顽钝的中国传统道学与价值体系已无法根治几千年积淤之顽疾,只有借助现代西方文明之普世价值才能解救中国于危难。而这种普世价值则来自基督宗教。在孙中山看来,基督宗教不仅仅是一种宗教,它本身就代表了现代化。诚如其好友林百克(Paul M.W.Linebarger)所言:“对他而言,基督宗教已成为文明之伟大制度。……通过将自身之中华文明与基督宗教文明相对照,他领悟到中国因无一种进步宗教而遭受之损失。他从务实的观点来看待基督宗教之结果。他看到基督宗教是与曾经的近代文明不断增长的需求而持续成长的,而儒教、佛教和道教却将中国留存于两千多年前的水准状态。”[8]152于是,基督宗教便被孙中山赋予“先进”之意。对于崇尚现代西方文明与现代化理念的孙中山而言,接受基督宗教并将之运用于自己的救国济民伟业,乃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他曾说:“兄弟数年前,提倡革命,奔走呼号,始终如一,而知革命之真理者,大半由教会所得来。今日中华民国成立,非兄弟之力,乃教会之功。”[16]446-447即使后来孙中山曾谴责外国传教士的侵略行为,但他仍然肯定基督宗教和传教士对于开启中国民智具有进步作用,对于反清大业亦有助益之功。
其次,基督宗教之核心价值观“自由、平等、博爱”理念乃孙中山救国济民思想萌生之思想基础。孙中山在对现代西方文明的长期耳濡目染中,深谙“自由、平等、博爱”乃基督宗教之核心价值观,乃构建现代西方文明与社会秩序之重要基石。于是,他将“自由、平等、博爱”理念立为变革中国之重要思想指引,并使基督宗教之核心价值观与自己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幸福之终极目标有机地结合起来。事实上,孙中山最初与基督宗教渐行渐近,就是因为被其所包含之“自由、平等、博爱”理念所吸引。同时在他看来,“自由、平等、博爱”亦乃革命精神产生之源泉,即“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即皆负革命之责任”[1]296。于是乎,基督宗教之核心价值观“自由、平等、博爱”理念便与孙中山救国济民之思想紧密相联了。另外,孙中山对基督宗教的认识一直停留于其早年所皈依之公理宗的宗教主张,其后变化甚微。较之其他宗派,公理宗在宗教主张上与孙中山之救国济民理想更为一致,其最显著特点在于反对教会集权,主张教徒平等,承认教徒自由。公理宗的这些理念与孙中山成熟时期之政治主张颇为一致。[15]252
再次,基督宗教之批判功能与革命性乃孙中山救国济民思想萌生之精神依托。与中国传统宗教不同,基督宗教(同时还有犹太教、伊斯兰教)隶属于先知型宗教的传统,具有鲜明的批判功能。“先知不为某个宗教—政治机构服务,他的行动有批判功能,而且常常激烈地批评盲目崇拜,批判王权,甚至于批判整个社会。”[17]46基督宗教的这种批判功能正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也是推翻封建专制政体满清王朝最需要之力量,亦为孙中山全心致力于建立新的共和国家之精神动力。另外,孙中山认为,基督宗教与革命乃是实现同一目标之两种手段。在他看来,耶稣是革命者,他和耶稣一样都是与罪恶作斗争的革命者。他在弥留之际拉着教友的手说,他“是一个耶稣教徒,受上帝使命,来与人间罪恶之魔宣战”[18]。此乃孙中山从基督宗教的角度来阐释自己之救国济民理想。他还说:“我们千方百计地努力以不流血的手段来夺取国家、建立政府。我认为,我们会做到这一点;但是,如果这样做注定要失败,我们就会毫不犹豫地求助于武力。我们四万万同胞必须要、也一定会从残暴野蛮的酷政中解放出来,在仁慈公正的政府领导下,以文明进化的技艺,同享天伦之乐。”[19]4在此,孙中山避开基督宗教与革命之冲突,认为其是可以为革命服务的。可见,基督宗教之批判功能与革命性完全成为孙中山救国济民思想萌生之精神依托。
最后,基督教会和广大教友的热心支持与积极参与乃孙中山践行救国济民思想之信心保证。孙中山的救国济民伟业,一直都得到基督教会与广大教友的热心支持;他的众多革命追随者和亲密战友中有许多是基督徒,如陆皓东、陈少白、郑士良、何宽、邓荫南、区凤墀、何启、杨衢云、谢缵泰、宋耀如等。孙中山的夫人和得力助手宋庆龄更是“一个生下来就受洗的基督徒”。孙中山曾言:“予深信予之革命精神,得力于基督徒者实多。”[12]266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所领导的近代中国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在檀香山创立时,参加者多为基督徒。孙中山最初发动反清起义的领导机关,亦多设于教会之场地,如其策划第一次起义的地方,即为广州双门底基督徒左斗山创立之圣教书楼。历次参与孙中山起义之中坚骨干,亦多为基督徒,如在惠州起义中,“基督教人占其三”。[20]416广大基督徒还积极宣传革命思想,在舆论上支持孙中山的救国大业;特别是很多基督徒在经济上给予孙中山很大的帮助。另外,孙中山“所创建的兴中会、同盟会、中华革命党等团体,其誓约均冠以‘当天发誓’字样,‘是亦一种宗教宣誓的仪式,从基督教受洗之礼脱胎而来者也。’又如兴中会成立时,孙中山‘率先宣誓,将左手置于开卷的《圣经》上,高举右手,恳求上苍明鉴,以示矢志革命,卒底于成’”[21]37。这样,基督教会和基督徒在孙中山的心目中,就与“革命势力”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一切,更为孙中山之救国济民理想与实践增添了信心与动力。
二、孙中山“自由、平等、博爱”观之基督宗教渊源
孙中山一生深受基督宗教影响,故其所倡导之“自由、平等、博爱”观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基督宗教之核心价值理念。他试图用《圣经》中的“自由、平等、博爱”观念来弥补中国政治革新之不足,以实现其救国济民理想。
“自由、平等、博爱”之基础是“自由”。自由,源自希腊精神,原指灵魂与肉体的分离——这种分离,使人独立拥有精神成为可能。现代西方文明之自由,是指人权与公民权利,具体而言,就是人在权利上是生来平等、永远平等的。自由,同时意味着不损害他人前提下之自由。此乃欧洲文艺复兴之自由精神,亦为基督宗教“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思想之延续。基于自由,平等与博爱才能成为可能。没有自由,平等只是一种相对的平等;没有平等,博爱只是一种施与,而不是一种爱。
自由,是基督宗教改革之后的新教所恪守的重要原则,其核心是独立思考、独立精神,尤其否定存在于神之外的其他权威。所以,无论教皇还是任何教会、政府、政党,惟有上帝之精义方为至高之权威。《圣经》走向世俗化,使政治不再权威神圣,摧毁了统治者的权威性,并进而解放人对人的思想与精神之控制。宗教救赎打碎一切所谓神圣不可侵犯的秩序系统,恢复人的未决性和开放性,并带来人的心灵自由。平等,依基督宗教理念,是上帝赋予人之特权。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世人,所以,人人都有神的形象,人人都具神性(虽然因犯罪而失去)。故人是生而平等的,绝不因性别、种族、疆域之异而有差别。“人人生而平等”、“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乃一切平等观念之基石,亦乃一切法制思想之先决。博爱,是基督宗教神学思想之重要内核。《圣经》中有“爱你的邻人”、“爱他的仇敌”、“爱人如己”等说法。此所谓“爱”人,乃由上帝所决定。“爱”人即是遵从上帝之律法,归根到底是爱上帝。同时,基督宗教认为,上帝乃“爱”之本身;上帝爱世人,既出于自己之旨意。上帝如此主动而又心甘情愿地爱着世人,所以这种“爱”使世人没有恐惧,没有负担,无须回报,亦无须偿还。在基督宗教理念里,上帝就是“爱”。上帝爱世人,便衍生出世界一家、人类一体之终极理想。
基督宗教的“天国”作为上帝的选民要前往的一个永生国度,作为圣徒彼岸的整体象征,是一种永恒的、非时空的终极完美存在。在“天国”,能真正体现人间所不能实现的至善、至美和绝对正义,能真正体现“自由、平等、博爱”。“天国”之“自由、平等、博爱”本身是超越现实的,是超越人间纬度的,且达至终极,因此,根本不存在如同人类现实所面临的那样,实现“自由、平等、博爱”有程度之分。所以在“天国”,没有低级的“自由、平等、博爱”与彻底的“自由、平等、博爱”之说。对基督宗教来说,“天国”之“自由、平等、博爱”不是人赋予的,而是“天国”本身就体现着的终极存在。
孙中山之“自由、平等、博爱”观主要是对基督宗教核心价值理念之衍演。1927年,王治心在《文社月刊》发表《孙文主义与耶稣主义》一文,指出:“三民主义,是孙文主义的中心,立足于自由平等博爱的;而自由平等博爱的最初倡导者,要算是耶稣,所以孙文主义就是耶稣主义。”他详细比较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思想与耶稣的“自由、平等、博爱”主张,认为:“孙总理的革命精神,完全出于耶稣的救世精神而来。”[22]孙中山自己亦曾指出:“法国革命的时候,他们革命的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三个名词,好比中国革命用民族、民权、民生三个主义一样。由此可说自由、平等、博爱是根据于民权,民权又是由于这三个名词然后才发达。”[23]501
孙中山救国济民思想首先体现的是强烈的民族主义,而其民族主义思想则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基督宗教的启发。孙中山年轻时,“读《旧约》至摩西导引以色列人出埃及到迦南乐土记,眉飞色舞,拍案大叫,我孙逸仙岂不能令我汉族脱离鞑虏而建新国乎?”[24]在民族主义思想形成的过程中,孙中山指出,“那些压迫人的人,是逆天行道,不是顺天行道。我们去抵抗强权,才是顺天行道。”[23]443-444他这里的“天”主要是指上帝,而上帝则主张人是自由的。[25]孙中山救国济民思想其次体现于民权主义。同样,他也借用了基督宗教理念。1922年1月,他在一次演讲中说:“民权主义,即人人平等,同为一族,绝不能以少数人压制多数人。人人有天赋之人权,不能以君主而奴隶臣民也。”[26]56他这里的“天赋人权”即美国《独立宣言》所阐释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孙中山还曾表示:“我们最大的希望,是将圣经和教育,从欧洲输运给我们不幸的同胞,由此令他们得到公开的律法的福祉,并且从这高洁的文字中,得以革除他们的苦痛。”[27]104其目的乃是通过基督宗教理念来实现国民之民权(即平等)。孙中山救国济民思想之重点则是民生主义。孙中山所强调之“博爱”即是作为民生哲学基础之“仁爱”。他最喜欢“博爱”二字,一生不知道写过多少“博爱”二字赠予他人。“博爱”的观念,如果追溯其历史,与其说最初是来自古希腊的先哲,不如说是来自基督宗教。孙中山把基督宗教宣扬之“博爱”与中国古代思想之“仁爱”予以嫁接,指出“古时最讲爱字的莫过于墨子。墨子所讲的‘兼爱’,与耶稣所讲的‘博爱’是一样的”[23]417。他通过打通二者之关系,以期吸收有利于民生主义之思想。在孙中山看来,无论是墨子的“兼爱”,还是耶稣的“博爱”,都是主张救民于苦难之中;他自己挽救中国于危亡,就是在履行“宗教家之仁”。不过有学者认为,孙中山把中国人民求生存的愿望,寄托于一种超阶级、超时空的宗教,多少有点唯心主义的成分。[25]孙中山一生大力阐扬其民生主义学说,在阐释“博爱”时,他指出,“(博爱)当中的道理和我们的民生主义是相通的。因为我们的民生主义是图四万万人幸福的,为四万万人谋幸福就是博爱。”[23]514
“自由、平等、博爱”原为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所高擎之大旗,有强大的内聚力和感召力。早期的社会主义鼓吹者亦把“自由、平等、博爱”引入社会主义的思想范畴,主张:“社会主义之行也,则足以伟物质的文明之观瞻,始能合乎真理、正义、人道三者。真理、正义、人道之所在,即自由、平等、博爱之所由现也。自由、平等、博爱之所现,即进步、和平、幸福之所由生也。”[28]312作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孙中山,对此有相似的理解。他指出,“社会主义者,人道主义也。人道主义,主张博爱、平等、自由,社会主义之真髓,亦不外此三者,实为人类之福音。……社会主义之博爱,广义之博爱也。社会主义为人类谋幸福,普遍普及,地尽五洲,时历万世,蒸蒸芸芸,莫不被其泽惠。此社会主义之博爱,所以得博爱之精神也。”[29]510他还指出:“社会主义之国家,一真自由、平等、博爱之境域也。国家有铁路、矿业、森林、航路之收入及人民地租、地税之完纳,府库之充,有取之不竭用之不尽之势。社会主义学者遂可进为经理,以供国家经费之余,以谋社会种种之幸福。”[29]523显然,孙中山试图以基督宗教之“自由、平等、博爱”理念阐发其对社会主义(即民生主义)之认识,且将社会主义视为救国济世、普渡芸生之灵丹妙药。孙中山的这些主张,颇易被同时代的人所接受,并引起强烈的共鸣,但仅为其在道德水准基础之上对“自由、平等、博爱”观念所阐发之善良愿望。
当然,基督宗教仅为孙文学说中之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我们过分强调,夸大其词,甚至以偏概全,则会弄巧成拙,悖离史实。孙中山自己亦曾表示:“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30]60把基督宗教之“自由、平等、博爱”理念简单地附会等同于孙中山之三民主义思想,显然夸大了基督宗教对孙中山思想之渗透感染。影响孙中山思想的“自由、平等、博爱”观乃是在西方文明长期发展过程中融冶陶炼而成,具有很强的现代性,其深刻蕴意远非基督宗教理念所能涵盖。
三、孙中山对基督宗教普世价值观之反思与修正
基督宗教的核心价值理念是西方文明体系建构之基石,“自由、平等、博爱”则是基督宗教普世价值之内核与精义。深受基督宗教普世价值观影响的孙中山,在充分吸纳、借鉴、诠释现代西方文明思想时,既能与其不懈追求之救国济世理想有机结合,亦能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对之予以不断反思与修正,还能广采博集,兼收并蓄,阐发出自己的独特、新颖创见。
孙中山指出,“自由”、“平等”是欧美近百年来所高举之两面革命大旗,法国大革命又充实以“博爱”,并进而形成完整的西方“自由、平等、博爱”观念。中国正因为感受到“自由、平等、博爱”之观念,所以掀起了民主革命。“自由、平等、博爱”推动和壮大了法国革命,因而也会有助于中国的革命。他认为,中国的民主革命与以往的革命有所不同,它不仅在于实现其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而且“国体民生尚当与民变革,虽经纬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在此前提下,他进一步指出:“故前代为英雄革命,今日为国民革命。”而“所谓国民革命者”,“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即皆负革命之责任”。[1]296在此,孙中山引用法国大革命高呼之著名口号来论证其所倡导之民主革命,并鼓励中国民众弘扬“自由、平等、博爱”精神。
孙中山指出,其所创想之三民主义的精义即是“自由、平等、博爱”,并借用“自由、平等、博爱”来阐释三民主义。他说:“吾党之三民主义,即民族、民权、民生三种。此三种主义之内容,亦可谓之民有、民治、民享,与自由、平等、博爱无异,故所向有功。”[31]76在详析“自由、平等、博爱”与三民主义之关联时,他指出:“法国的‘自由’和我们的‘民族主义’相同。因为‘民族主义’是提倡国家‘自由’的。‘平等’和我们的‘民权主义’相同。因为‘民权主义’是提倡人民在政治之地位都是平等的,要打破‘君权’,使人人都是平等的,所以说‘民权’是和‘平等’相对的。此外,还有‘博爱’的口号,这个名词的原文,是‘兄弟’的意思,和中国‘同胞’两个字是一样解法,普通译成‘博爱’,当中的道理和我们的‘民生主义’是相通的,因为我们的‘民生主义’是图四万万人幸福;为四万万人谋幸福就是‘博爱’。”[23]514这里,孙中山将“自由、平等、博爱”之观念与自己所创想之中国革命理想成功地予以嫁接。
1912年10月,孙中山于《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中指出:“社会主义者,人道主义也。人道主义,主张博爱、平等、自由,社会主义之真髓,亦不外此三者,实为人类之福音。”他还说:“社会主义之国家,一真自由、平等、博爱之境域也。”[29]510、523所以,孙中山认为,“自由、平等、博爱”的创造者是人道主义者,也是社会主义者;“自由、平等、博爱”并非只是一个口号,而是一个政治社会的目标。[32]关于“自由”,孙中山指出,“一个人的自由,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为范围,才是真自由;如果侵犯他人的范围,便不是自由。”[23]509此说与孟德斯鸠(Charles Louis Montesquieu)所言“自由不是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可谓一脉相承,异曲同工,亦是对那种以“放荡不羁”甚至以“违法乱纪”、“损人利己”为“自由”标准的人的忠心告诫。孙中山对自由概念的阐述非常明晰,并常常提醒、提防国人误解自由之真义。
关于“平等”,孙中山指出,有真平等和假平等两种。某方“必定要把位置高的压下去,成了平头的平等……”“这种平等不是真平等,是假平等”。他阐释道:“说到社会上的地位平等,是始初起点的地位平等,后来各人根据天赋的聪明才力自己去造就,因为各人的聪明才力有天赋的不同,所以造就的结果当然不同。造就既是不同,自然不能有平等。……如果不管各人天赋的聪明才力,就是以后有造就高的地位,也要把他们压下去。一律要平等,世界便没有进步,人类便要退化。所以我们讲民权平等,又要世界有进步,是要人民在政治上的地位平等。因为平等是人为的,不是天生的;人造的平等,只有做到政治上的地位平等。故革命以后,必要各人在政治上的立足点都是平等……那才是真平等,那才是自然之真理。”[23]517-518人与人之间生来便具有智力、能力等方面之差距,但孙中山仍然坚持提倡民权主义,谋求人民在政治上之平等。此正是其作为一个民主主义者的伟大之处。
关于“博爱”,孙中山认为就是中国古代思想中之“仁”,所以他赞成韩愈“博爱之谓仁”的说法。他把“仁”分为救世、救国、救人,认为“其性质则皆为博爱”。他指出,“博爱”指的是“公爱而非私爱”,“‘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之意,与夫爱父母妻子者有别。以其所爱在大,非妇人之仁可比,故谓之博爱。能博爱,即可谓之仁。”[33]107他强调,中国人很早就把“仁爱”(即“博爱”)当作美德,问题是实行起来却不如外国人;“只要学他们那样实行,把仁爱恢复起来,再去发扬光大,便是中国固有的精神。”[23]471他还提出“以民生主义预防社会革命”的主张。在《要用三民主义打破旧思想恢复革命朝气》的演讲中,他很明确地说:“预防这种社会革命,以达到生活上幸福、平等的道理。便是民生主义。”[34]327而在孙中山看来,民生主义正是博爱的体现。
有学者认为,孙中山用“自由、平等、博爱”观来阐述三民主义,具有中国旧民主主义的特色,当然有其不足之处,其中尤以试图用民生主义来取代阶级斗争学说更具有空想的成分。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孙中山的观念比起维新派来,则是大大地前进了。[32]
孙中山早先曾试图效法西方,走“自由、平等、博爱”之路。然而,多年的奋斗历程,使他对这条道路产生了怀疑。一方面,孙中山敏锐地观察到,“现在对中国人说要他去争自由,他们便不明白,不情愿来附和”。[23]504争自由,争平等,不能将人民真正动员起来,吸引他们献身于变革大业。“欧洲人民因为从前受专制的痛苦太深,所以一经提倡自由,便万众一心去赞成。假若现在中国来提倡自由,人民向来没有受过这种痛苦,当然不理会。”[23]508况且,就西方现实而言,他们争得了自由,争得了平等,也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西方的失败教训,足可为中国所借鉴。另一方面,孙中山从亲身经历的政治实践中痛苦地发现,无论是在民众之中,还是在革命党内,倡导“自由、平等、博爱”,非但没有形成新的巨大凝聚力量,反而极易同旧的自由结合起来,助长分散主义、分裂主义、无政府状态的恶性发展。他说,中国推倒清朝统治以后,至今无法建设民国,革命党之所以被袁世凯打败,就是因为“我们同党之内,大家都是讲自由,没有团体”;“南方各省,当时乘革命的余威,表面虽然是轰轰烈烈,内容实在是四分五裂,号令不能统一”。正基于此,孙中山断言:“外国革命的方法是争自由,中国革命便不能说是争自由。如果说争自由,便更成一片散沙,不能成大团体,我们的革命目的便永远不能成功。”[23]512-513显然,他对中国的国情及国人的状况认识是深刻的。
孙中山吮吸着西方现代思想与文化的乳汁成长起来,西方的环境与教育对其救国济世思想的孕育与产生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革命的曲折与反复,使他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一味模仿或搬用西方现成的模式于中国是行不通的、不可取的,中国必须根据自己的国情走自己的道路。他说:“欧美有欧美的社会,我们有我们的社会,彼此的人情风土各不相同。我们能够照自己的社会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做去,社会才可以改良,国家才可以进步。如果不照自己社会的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去做,国家便要退化,民族便受危险。”为此,他强调,中国今日要实行民权,改革政治,便不能完全仿效欧美,“要重新想出一个方法”,“如果一味的盲从附和,对于国计民生是很有大害的。”[23]555
综而观之,孙中山将基督宗教之“自由、平等、博爱”理念,结合中国国民革命之具体实践,予以深刻反思和不断修正,为现代西方文明向中国的移植和“本土化”发展,找到了一条可行的路径,发挥了开创性的作用。
四、余论
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曾指出,“孙中山成为一名基督徒,是他西化的一部分”,“归根结蒂,基督宗教对他的事业起到了作用”。[35]146陆丹林亦认为,“总理致力革命四十年,直接间接,所受基督教理的影响,至深且巨。”[27]108孙中山的恩师康德黎认为,上苍赋予了孙中山可贵的才能,这种才能“根据基督教义可以数字包括之,就是信、爱、望——一种坚定不移的信仰,信其所自信;中国从速改造的希望;施及邻人的慈爱。”他还说,孙中山之“大公无我的精神在现世人中殊未多觏”。[36]19-20为人民谋幸福的“信、爱、望”和“大公无我的精神”是孙中山“自由、平等、博爱”观之重要组成部分。孙中山通过信仰基督宗教,从中吸取那些有利于其救国济民伟业之元素和有利于其提高思想品质之基因。他一生救国济民,愈挫愈奋;“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天下为公”,不谋权位;提倡人道,摒弃罪恶。这些思想品格的形成与基督宗教的影响不无关系。毫无疑问,基督宗教所包含之普世精神、道德观念,以及基督教会传播之西方文化,对孙中山的思想品质,特别是其所倡导之“自由、平等、博爱”观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当然,任何宗教对人的思想行为都是一柄双刃剑,既产生积极的影响,亦会有消极的作用。基督宗教亦不例外。虽然基督宗教对孙中山及其“自由、平等、博爱”观的形成主要体现为积极的一面,但这种积极影响毕竟是有限的。孙中山一生既接受过基督宗教的陶冶,也受到过众多学说的熏染;他既仰慕现代西方文明之要旨,亦不排拒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华。基督宗教仅为影响其思想学说诸多要因之一端。同时,基督宗教也不可避免地对孙中山产生过消极影响。他青少年时期在教会学校接受西式教育,对西方的宗教和文化怀有深厚的感情,使其相当长的时期对帝国主义的本质认识不清,对欧美国家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导致其对基督宗教于当时中国影响之微不足道缺乏了解,盲目追求以基督宗教之道德来弥补中国政治之不足;更使其在革命实践中过分相信他人(包括自己的敌人)的品德和诺言,过分强调人道、博爱,以致大大削弱了其国民革命之彻底性。[37]21-22
然而,由于孙中山既是一名品行优良的基督徒,又是一位与时俱进的杰出改革家与思想家,具有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勇于探索真理的精神,所以,基督宗教对其产生的消极影响非常有限。孙中山谦虚好学,能辨善思,不故步自封,不循规蹈矩。他积极汲取世界自然科学之精华,世界观已基本达到唯物论和无神论的高度。因此,他对基督宗教没有盲目崇信,全盘接受,而是像对待其他理论学说一样,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不断摒弃其中的消极落后元素。他从不相信仅仅依靠某种宗教就能教化世人,使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早在虔诚信仰基督宗教的青少年时代,他就已经开始思考探索救国济民之道。他没有像牧师们希望的那样,成为一名劝人为善的传教士,也没有像老师们期冀的那样,当一名救死扶伤的良医,而是成长为一名舍身为国的“济世者”。[37]22
总而言之,孙中山“自由、平等、博爱”观的思想基础是基督宗教之普世价值,同时它也集孙中山独立创想与博采众说之大成,乃其多元智慧之结晶。
注释:
①基督宗教(Christianity),中国人亦俗称“基督教”。在汉语语境里,“基督教”一词又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是指信奉耶稣基督为救世主的各教派的统称,包括基督公教(Roman Catholicism,亦称“罗马公教”,传入中国后汉译为“天主教”)、基督正教(Eastern Orthodoxy,亦称“东正教”)、基督新教(Protestantism,简称“新教”)三大教派和其他一些较小教派;狭义则专指基督新教。虽然孙中山皈依的是属于基督新教的美国公理教会(American Congregational Church),但其所倡导、推崇的则是整个现代西方文明的思想与价值体系,故本文以“基督宗教”为视阈来诠释孙中山与西方文明之关系。
②两岸三地中国学者有关基督宗教对孙中山价值观念与思想学说影响之研究,虽偶有涉猎,但仍可谓凤毛麟角,且缺乏深度。孙中山研究著名专家黄宇和认为:“中国精英历来反对耶教,比普通人尤甚,难怪中国史学界一直积极回避孙中山与基督教的关系,简直当没有发生过此事,引起广大耶教教友的不满,唯敢怒而不敢言而已。”(黄宇和著:《三十岁前的孙中山:翠亨、檀岛、香港,1866-1895》,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171页)。
③转引自黄宇和著:《三十岁前的孙中山:翠亨、檀岛、香港,1866-1895》,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222页。
标签:孙中山论文; 基督教论文; 西方文明论文; 上帝的教会论文; 中国宗教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宗教论文; 耶稣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