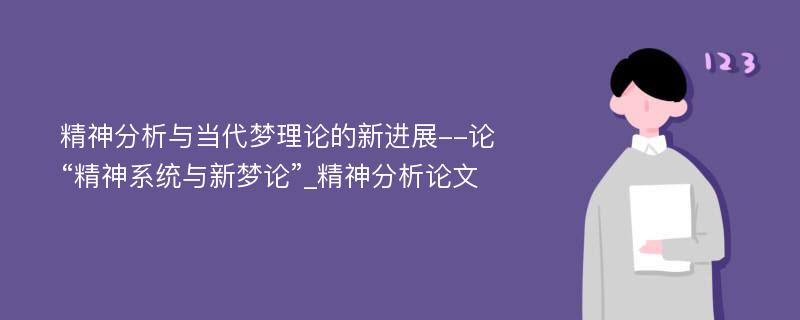
精神分析与当代梦说的新进展——评《精神系统与新梦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进展论文,当代论文,精神分析论文,精神论文,系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89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了刘文英教授撰写的《梦的迷信与梦的探索》,这是国内第一部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系统地研究古代梦说的专著。但是,该书所做的主要工作还只是对梦的一种历史的考察。而作者新著《精神系统与新梦说》(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则主要的不再是对梦的历史的考察,而是理论的阐述,并在前书的基础上,进一步阐明“一个中国人的新梦说”。统观全书,我们认为,该书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1.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精神分析理论
由弗洛伊德开创的精神分析理论和西方其他学者的实验研究,走在现代世界梦说的前列,但现代西方的精神分析和梦论也有很大的局限性,这就是它过多地依附于脑科学。然而,人脑仅仅是精神活动的物质基础,而人的精神活动的内容却不是头脑固有和自生的。人之作为精神活动的主体,不只是因为人有一个健全的头脑,更重要的在于人是社会实践活动的主体。精神系统的这种社会性和开放性表明,精神学和梦的研究既要关心脑科学的发展,但同时更应注意对精神现象的分析和精神文化史的研究。循此思路,作者阐释并提出了自己的精神分析理论。概言之,它集中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探讨并说明了精神活动的界域和基本要素。该书认为精神活动的界域应从两个方面进行规定:(1)不能把精神仅仅理解为同自觉性、自主性相联系的意识,精神应当是一个包括意识和潜意识活动在内的统一整体;(2)精神不包括生物性本能活动,它不是本能活动的延伸,而是超越本能为人所持有的高级心理系统,因而它是构成人之为人的本质特征之一。关于精神活动的基本要素,作者认为应包括四方面的内容:(1)主体的意向,即任何人的精神活动首先表现为心有所动而产生的一种念头或想法;(2)意向所指的对象,无论在自我的思维活动中还是在潜意识中,精神活动总是有其所指的对象,而且这些对象归根到底来自客观世界;(3)主体面向对象的认识,传统认识论和现代认知科学都认为认知仅仅停留在意识层面,但事实并非如此,潜意识也具有某种认知作用;(4)主体的情感,即主体意向在追求对象及其认知的过程中必有一种感受和体现,从而表现为喜怒哀乐受恶欲。作者认为,上述四大要素普遍存在于人的精神活动中,并且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内在的有机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在一起。遗憾的是心理学家至今很少研究精神活动的内在结构和基本要素,而只是把诸如注意、记忆、概念、思维、情感、意志等精神现象外在地列举出来加以描述,因而不能说明人的精神活动为什么会有这些现象,不能说明精神为什么会成为精神。
第二,考察和探讨了精神系统的形成过程。长期以来,人们只注意精神的既成形态,而很少关心精神的发生过程。弗洛伊德虽然注意到了精神系统的形成“必定经过长时期的演化过程”,但并没有进行具体的探讨。作者认为,在高等动物的“意向性心理”中,已经出现了精神的萌芽。这一萌芽首先表现为潜意识的萌芽,其次才表现为意识的萌芽,但两者都是对本能活动的超越。这就与弗洛伊德的潜意识根源于本能说和荣格的集体潜意识根源于生物本能的理论划清了界限。
第三,研究并提出了精神系统的结构理论。通过历史与逻辑的求证和分析,作者提出人的整个精神系统是一个“负阴抱阳”的阴阳合体的太极图式结构,把意识与潜意识作为这一结构的阴面和阳面,并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自我“有志”与“无志”、自我“有主”与“无主”分别说明意识的自觉性和潜意识的不自觉性及其特征。这样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阴阳太极模型,与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前意识和意识的三层结构模型,是不大相同的。按照作者的观点,弗洛伊德用“本能”说明潜意识是原则性的失误;他那个以本能冲动为特征的所谓本 我根本就不存在,因为本能根本没有主体性;他的“前意识”并不构成一个稳定的基本层次;他的“自我”概念除了“现实原则”外,实际上很笼统;他的“超我”虽有一定的客观性,但其现实主体同样不明确。基于上述原则,作者在具体分析意识与潜意识的结构时,把潜意识也视为对本能的超越,摈弃了“前意识”概念,用“自我潜意识”说明潜意识的主体性,用“群体意识”说明“超我”的现实主体。至于荣格的“集体潜意识”,在经过改造和重新诠释后则代之以“群体潜意识”,而与“群体意识”相对应。关于“自我意识”,又进一步具体化为“自我存在意识”、“自我有主意识”、“自我有为意识”。关于“自我潜意识”则进一步具体化为“自我存在潜意识”、“自我无主潜意识”、“自我无为潜意识”。作者对人类精神系统结构所作的这种具体描述,对把握精神系统的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第四,提出并说明了精神系统的运作机制理论。弗洛伊德和荣格曾引入“动力心理学”的概念来说明这一问题,但是,他们把意识归结为潜意识,又把潜意识归结为本能,始终围绕自我对潜意识的压抑和潜意识对意识的冲击打转转,这是极其片面和错误的。作者在充分注意现代西方精神分析和实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吸取了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的合理内容,指出精神系统的运作至少应具有四个重要的机制:一是阴阳连续恒动机制,包括意识的连续活动、潜意识的连续活动及二者之间的连续衔接;二是阴阳有序转换机制,包括意识活动和潜意识活动相互之间的必然有序转换,以及在这一活动中所伴随和包含的“一张一驰”、“一消一长”、“一开一闭”与内外有接、无接之间的有序转换;三是阴阳互渗互补机制,包括潜意识在意识中的渗透、意识在潜意识中的渗透,以及二者在资源和功能上的阴阳互补;四是阴阳矛盾平衡机制,包括精神系统与外部世界之间的矛盾平衡、意识与潜意识内部诸成分和活动之间的矛盾平衡、意识与潜意识两个子系统之间的矛盾平衡。人的精神系统正是通过这些运作机制,实现人之作为主体的功能和主体所具有的各种精神功能。
第五,运用自己所提出的新的精神分析理论,对人类心理、世界宗教和历代哲学中所涉及的若干特异的精神现象进行了分析和说明。现代心理学大多单纯依赖实验方法,对许多精神现象无能为力,无法解释。作者认为,任何精神现象和精神活动之谜,只有着眼于精神系统的整体结构和运作机制,才有可能破解。而许多所谓神秘的现象,如烦恼与焦虑、灵感与直觉、虚静与坐忘、禅定与顿悟、尽心与明心等,大多与潜意识的作用有关。
2.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吸取中西文化的有益成果,系统地提出并阐发了自己的新梦说
作者认为,“梦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梦,必须深入下去,在整个精神学上有所发现。反过来,只有站在整个精神学的高度上,从人的整个精神系统去研究,才能真正破解梦之谜”。(《精神系统与新梦说》,第2-3页)正是在提出和阐释了自己的精神分析理论基础上,作者进一步提出了“一个中国人的新梦说”。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探讨并揭示了梦的本质及其精神特征。作者认为,梦的本质及其精神特征应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规定:(1)梦是特殊的潜意识活动,梦的精神特征也就是潜意识的精神特征。人类长期以来之所以把梦同神灵启示与灵魂外游联系在一起,关键是对于潜意识及其特征的无知和误解。弗洛伊德在这方面的贡献就在于他明确地提出了潜意识概念并用这一概念解释梦,从而认为梦是一种完全正常的心理活动,但他的压抑说和化妆说歪曲了他的潜意识概念及其对梦所作的判断。而中国古代关于梦是“神藏”、“神蛰”状态的心理活动,关于梦“无志”、“无主”的论断,则客观上正确地揭示了梦之为潜意识的基本特征,二者结合起来,将更能充分揭示梦的本质及其精神特征。(2)梦是现实生活的特殊反映。整个精神系统的社会性和开放性,决定了梦的来源和内容归根到底同梦者的现实生活联系在一起。尽管梦所直接 表现的是潜意识的内心世界,但在意识向潜意识渗透和积淀之下,其内容都有一定的现实原形为基矗梦的反映形式是虚幻的、非现实的,但它的指向归根到底还是梦者的现实生活。(3)梦是人的不可缺少的精神活动。梦在人的精神系统中有其确定的地位,它对人来说不是可有可无的,任何一个正常的人,都不可能完全无梦,有的只是梦的回忆能力的差异。任何对正常梦的活动的有意剥夺,不但会破坏精神系统的平衡,而且会破坏生理系统的平衡。
第二,探讨和说明了梦的材料与梦象构成问题。梦的活动是由梦象构成的,梦象则是由梦的材料构成的。梦的材料有三个来源:一是个体潜意识间接从个体意识和群体意识中获得的材料;二是个体潜意识直接从外部世界和群体潜意识中获取的材料;三是个体潜意识自我想象和幻想所创造出来的材料。这三种材料都存在于人脑的“意象库”中。意象库是一个与概念库相对应的概念,二者的区别在于,在概念库中各种概念材料的储存必须以逻辑从属关系为原则,否则就乱无头绪,难以找寻。意象库则不然,由于意象之间本来就没有清晰的逻辑关系,因而只能根据相似原则和关联原则来储存,而梦的构成则往往是构成梦象的意象材料在梦中发生“变形”(如“类化”、“因衍”、“转换”等)的结果。与弗洛伊德不同的是,作者认为无论是自我原形材料还是对象原形材料的变形,都是个体潜意识在自我“无志”、“无主”和“无为”的状态下完成的,而不是自我意识逃避检查的结果。如果说潜意识为了逃避检查而想尽办法进行巧妙的伪装,那潜意识还能称为“无意识”吗?显然,这是弗洛伊德无意识地为自己设置的理论陷阱。
第三,提出并说明了“梦的思维”及其特征,探讨了梦象表达梦意的具体方式和方法。梦者在做梦过程中,把自我潜意识从现实生活中直接或间接获得的材料,不自觉地进行“变 形”和“重构”,由此创造出种种梦象和梦境,来表达潜意识的思想、感情或愿望。作者把这一过程称作“梦的思维”,其最显著的特点有二:(1)梦的思维把意象作为自己最基本的成分和形式,而不是像自觉的有意识的思维那样离不开概念;(2)梦的思维不遵守逻辑规范,而只是种种意象的拼接和推移。梦的思维与自觉的有意识思维明显不同,但同人类的原始思维却极为相似。因此,梦象表达梦意的具体方式和方法必然是一种原始思维的方式和方法。作者认为无论从逻辑上还是从事实上看,梦象表示梦意都有“直示”、“转示”和“反示”三种方式和方法。其中单纯的直示,即梦象直接表示梦意的方法,比较少见;转示,即梦象通过“象征”、“类比”、“连类”、“破译”、“谐音”等转换手段表示梦意的方法,较为多见;反示,即梦象通过其反面来表示梦意的方法,虽不大常见,但也是客观存在着的一种特例。
第四,探讨并提出了梦形成的触发机制与根本原因。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人们对梦因的探索,总是先注意有形的可见的生理病理因素,然后再过渡到无形的不可见的感情心理因素。这种先后过程,反映了认识活动的基本规律。循此思路,按照潜意识在整个精神大系统中的地位,作者认为梦形成的触发机制与根本原因应包括三方面的内容:(1)来自外界和人体内的生理病理刺激因素,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因乎外者”和“因乎内者”,由此而形成的梦称之为“感变之梦”。(2)来自自觉意识的精神心理刺激因素,也就是古人所说的“精念存想”,由此而形成的梦称之为“思梦”或“想梦”。(3)潜意识的情结或意结,即潜意识子系统本身的意向、欲望和各种无意识的不自觉的执著。在以上三因素中,外界的和生理病理的刺激对于梦的发生只是一个外在的诱因,因为严格说来它存在于人的精神系统之外;来自意识子系统的精神心理刺激,诚然比单纯的外界和生理病理刺激更深刻、更重要,但它仍是一种外因和条件;而梦作为一种睡眠状态下的潜意识活动,最主要和最根本的原因则发生在潜意识内部,即潜意识本身的意向和欲望。弗洛伊德第一次明确地提出潜意识为梦的根本原因,但他又把潜意识归结为“本能的冲动”,而“本能”属于人的生物性和生理性功能,因此,弗洛伊德对梦因的探讨实际上还是停留在生理病理刺激这一外在诱因的层次上。
第五,研究和探讨了梦的诸方面的功能。作者认为,梦作为一种潜意识的活动决不是毫无意义的荒谬的精神现象,它对主体的生命存在和精神活动有着不可替代的特殊价值。具体地说,梦具有三方面的功能,即生理功能、心理功能和认知功能。梦的生理功能,从宏观上看,主要是通过精神系统的松驰来适当调节人体生理活动的节律;从微观上看,主要是通过梦象特征来显示人体脏腑机能的病理变化。梦的心理功能,从宏观上看,主要是通过精神系统的松驰来适当调节人体精神活动的节律;从微观上看,主要是通过梦象变化促成各种心理因素的平衡,包括意识和潜意识两个层面之间梦对意识活动的补偿,也包括潜意识内部有关因素的协调。梦的认知功能,具体的表现为梦对主体自我的认知、梦对客体对象的认知和梦对事变未来的认知三个方面。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正像人的意识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把握事物变化的趋势一样,潜意识也是如此,尤其是梦对现实的反映常常是象征性的,只有通过复杂的精神分析,才能把握其意义。因此,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关心梦、留意梦,从中获 得有益的启示,但不能完全以梦为根据去观察问题和推测未来。
综上所述,该书所提出的精神分析理论和新梦说是在充分吸收借鉴东西方文化优秀成果的基础上,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研究精神现象和梦的问题所取得的积极成果。该书的出版对推进精神分析学和当代世界梦说的发展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