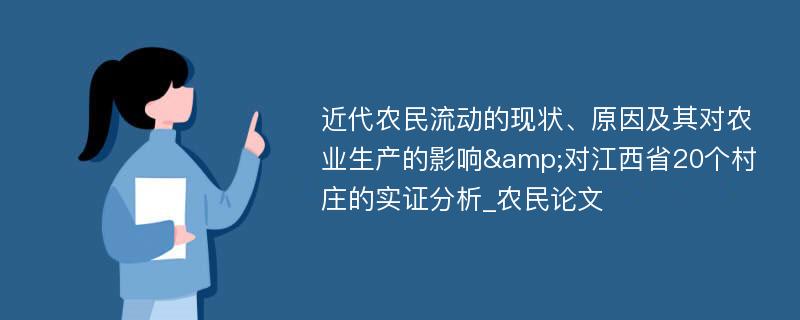
近代农民流动状况、原因及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对江西省20个村实证调查的一项综合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江西省论文,实证论文,农业生产论文,近代论文,其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通过对江西省20个村个案调查结果的综合分析,描述了近代历史上的农民流动状态及其成因,指出造成农民流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争夺不是农民流动的主要成因。并提出正常的农民流动能自发地调节人口大量增长和土地资源紧缺所形成的矛盾,从而对农业生产产生促进和推动作用。
[中图分类号]G9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04)01-0166-09
对于改革开放前特别是近代历史上的农民流动,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习惯于把近代较为活跃的农民流动的原因,归结为社会不同阶层之间利益争夺的结果。但章有义、珀金斯、黄宗智等学者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本文通过对江西省14县20个村的个案调查的综合比较研究,分析了自1840年至改革开放前100多年来江西农民流动的阶段性特点及其成因,并初步探讨了农民流动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和两者之间的关系。
一、样本村的基本概况
本课题研究的20个村,皆系非随机抽样选取的样本。它们并不具有代表性、推论性,但具有一定的类型分析意义,即能对我国中部地区特别是江西农村几种不同经济社会状况村的农民流动与农业生产关系进行探索性研究。这20个村都在江西农村,因此这些村的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江西农村目前的大概面貌和现实处境。
分析这20个村的基本概况,就可发现具有一定的广泛性、代表性:从区域分布看,处于江西东部的有朝阳村、芳山村;居江西西部的有杨村、栗水村、东洛村、高汪村,位于江西省北部的有柳田村、泉溪村、新基村;处于江西南部的有东林村、马岭村、肖田村;位于江西中部的有滁山村、坊城村、旧下村、康山村;还有古竹村、市田村、沙田村处于江西的西南部;吴村位于江西的东南部。从行政区划看,分别隶属于17个县9个地级市,南昌市(2个)、九江市(3个)、赣州市(1个)、吉安市(6个)、上饶市(2个)、宜春市(3个)、萍乡市(1个)、新余市(1个)、抚州市(1个),占江西省11个地市的82%。从区位看,位于城镇郊区的有杨村、芳山村、康山村,其他村与城镇都有一定的距离,大约在15-25公里之间,泉溪村、高汪村、东林村和马岭村还属于偏僻的山区村落。就交通而言,交通方便的村占42.6%,交通一般的村占26.1%,交通不方便的村占31.3%。地处平原的6个,丘陵地带的有8个,山区的有5个,水乡2个。从行政村的规模看,人口在2000人以上的有6个即杨村、滁山村、康山村、吴村、沙田村、东洛村;人口在1000-2000人的有芳山、古竹、朝阳、柳田、旧下、栗水、东林、马岭、市田等9村;人口在1000人以下的有坊城村、泉溪村、高汪村、肖田村、新基村等5个。
样本村的经济状况又怎么样呢?从统计分析情况(见表1)来看,以稻作农业为主体依然是多数行政村产业结构的特征。2002年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在2000元以上的有2个村,占10%;在1500-2000元之间的有7个,占35%;1000-1500元的有6个,占30%;在1000元以下的为5个,占25%,其中有1个村的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在500元以下。同年,有60%的村集体经济没有纯收入,年收入在50000元以下的村占35%,在50000-200000元的村有15%,300000元以上的村为10%。而且大多数村已负有一定数额的债务,村干部的工作报酬能得到兑现的村只为35%。这些情况基本反映了江西农村乃至中国中部地区农村的普遍性特点。
样本村的经济发展状况
表1N=20(村)
以稻作农业为主以经济作物为主以林牧养殖为主个体私营经济状况
80% 10% 10%
发达村5%,一般村15%,不发达村80%
资料来源:对20个样本村情况的调查
二、近代历史上江西的农民流动
明清以来,闽、粤两省流民大规模入赣,人流的增多带动了物流的增长,江西丘陵和山区中的平静的乡村开始出现一定程度的勃兴。但这次流民的大“入侵”,也使江西的人口在短时期间急剧增长,人口与土地的压力,加上接连不断的战争,从此拉开了江西农民流动的序幕。
“安土重迁”是中国农民突出的心理特征。受这一传统观念的影响,在中国乡土社会广大农民惮于远徙。但中华民族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由于受自然和社会条件的影响,在传统农业社会中,战乱、灾荒、虫害和瘟疫频繁发生,造成大量人口死亡和流徙。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本以走向衰落的晚清帝国,在经受西方坚船利炮的打击后,开始进入内忧外患的社会动荡期。处于中国中部地区的江西,虽然多为丘陵和山峦,农民的生活并不富裕。但由于其位于长江中下游地段,每一场战争都不可幸免。因此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江西农村进入了一个由战争主宰的剧烈的社会动荡期。其中尤以太平天国、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这三次战争对江西的影响最大。
太平天国时期,江西是太平军的主要活动地,“到咸丰六年六月,江西十三府有九府掌握在太平军手中,成为一片比较巩固的天国统治区。”(注:见.太平天国[R].中国近代资料史丛刊,神州国光社1952年7月初版.)而作为晚清王朝清剿太平军的主力,就是产生于与江西接壤的湖南。从历史记载来看,我们调查的20个样本村都处于湘军与太平军的交战区域内。太平军与清军、湘军在江西激战数年(自咸丰三年至咸丰十一年),当时的湘军头领曾国藩的指挥所设在建昌府(今江西南城县)就长达三年多时间。长年的战乱,不仅给江西农民带来无穷的灾难,而且为了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当时的乡绅缙士经常强制性要求捐助,湘军还先后在南康、星子、瑞昌、德安、建昌、武宁、靖安、奉新、安义、丰城、瑞州、高安、上高、新昌等县设立厘卡抽税,因此当时的江西人民既要承担地方官员正常收取的税收,还得交纳湘军的厘金;于是设卡之处,无不民怨沸腾,百姓苦不堪言(注:见.太平天国[R].中国近代资料史丛刊,神州国光社1952年7月初版.)。战争的创伤、沉重的税赋,使得耕地荒芜、百业凋蔽,不少商贾和富户纷纷迁居异地,而贫苦老百姓则更是携家带口流落他乡。
20世纪初,积孱积弱的满清帝国像沉于西山的落日,走到了它历史的终点。辛亥炮响,全国咸与维新,江西各县的上空也相继飘扬起民主共和的旗帜。民国初期,江西各县政局还算稳定,地方治安依赖地方武装,尚称安靖。袁世凯反行逆驰复辟帝制失败后,军阀割剧与混乱的战火从此在江西南北大地蔓延,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深重的灾难。动荡的政局,不仅迫使商家和富户纷迁避祸,也堵塞了下层百姓的谋生之路,众多下层百姓“迫于生活无奈,不得不落山为寇”,败退的小股军阀部队又往往与他们沆瀣一气,这样就干起剪径打劫和绑票吊参的土匪生涯。如我们调查的样本村——东林村,当时就是这种状况,兴国到梅县要从这村经过东林村,在苏区革命前,“路上不安靖,民团、靖卫团时常搜抢客人身上的钱物”。(注: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C].P211、P184-199.)
1927年8月1日,中共在江西南昌领导举行了武装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同年10月7日,毛泽东率领参加秋收起义遭到重挫的工农革命军来到井冈山,开始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28年4月下旬,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在发动湘南起义后,带领一万多人来到了井冈山,与毛泽东带领的工农革命军胜利会师。从此,就在井冈山这片土地上燃起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熊熊烈火,也在江西这片土地上朱毛领导的工农红军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反动派军队进行了长达7年的“围剿”与“反围剿”的革命战争。同时,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1931年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的建立,江西进入了一个剧烈的社会变革期。在“打土豪、分田地”的苏维埃革命中,为了逃避革命斗争的打击,首先出现的是闽赣边区富裕阶层大批外徙。随着战争加剧与长期化,厌战的人民也逐步加入了外出避难和另谋生路的行列。东林村当时就有5户近30人外出避战,其所在的兴国县,1930年“难民逃赣(赣州)者达7万人”(注:江西民国日报[N].1930年7月15日.)。而在肖田村、马岭村、古竹村、市田村、沙田村和高汪村,也都有不少村民逃往吉安;当时逃入吉安的人数达19万多人(赣州也相差不远)(注:刘士奇.赣西南(特委)刘士奇(给中央的综合)报告(1930、10、7)[R].见.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P361.)。而国民政府军的“围剿”和六年多反复拉锯式的国共战争给当时苏区社会与劳动力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据统计,1928-1934年国共内战期间仅江西苏区就死亡567869人,其中红军死亡270000人(何炳棣,1989)。至于江西全省的死亡人数和流亡人数,因囿于资料的有限和我们的精力,要准确地统计分析出具体的数字有相当的难度。
与此相对应的是,囿于革命势力的强大与广泛影响等因素,江西广大农村的大多数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和保卫苏区根据地的军事斗争。大批青壮年踊跃参加工农红军或加入赤卫队等地方武装,或在各级苏维埃政府工作;于是在苏区到处出现父母送儿、媳妇送郎参加红军的景象。古竹村唐氏当时就有50名青年跟着该村的唐学理、唐得勇参加了革命,占当时唐氏青年人数的55.4%,还有20多人在各级苏维埃政府工作(注:唐晓腾.社会变迁中的宗族与基层政府:1949-1989[C].载肖唐镖主编.当代中国农村宗族与乡村治理[C].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2.);东林村也有20多名青年农民参加了工农红军。1930年10月毛泽东对兴国8个农民家庭的典型调查中,8户人家有16-48岁的青壮年31人,其中共有14人在乡政府、红军预备队任职和外出当红军,约占45%(注: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C].P211、P184-199.);在1928-1934年间兴国县共有80000万人参加了红军(注:兴国县志[M].1988年,P5.)。这足以看出,当时在赣西、赣南的湘赣边区和闽粤赣边区农村劳力参军参战的广度和程度。从我们调查的处于苏区的7个样本村1934年底红军长征后的人员结构状况,也可以看出当时苏区劳力的参军参战的程度,在红军长征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东林村、肖田村、马岭村、古竹村、市田村、高汪村、沙田村都只剩下妇女、儿童和老人。这段时间在赣西乡村流传着“老太婆多、寡妇多、偷汉的女人多”的民谣,正反映了当时这一地区男女性别严重失衡的问题。内战过后,流亡异地的难民陆续返家,国民政府也曾力图恢复苏区治安和地方元气,苏区社会似乎升腾起重建家园的希望。但六年的杀戮给苏区各阶层人士留下了深深的冤仇家恨,于是,军事斗争、地富阶级的报复、宗族争斗、地方斗争等,依然贯穿于民国后期的江西苏区(温锐,2001)。肖田村和马岭村就在苏区革命后遭受国民政府军的毁灭性报复,部分自然村被烧掠,抓走妇女儿童50多人,数百人被迫流亡他乡谋生。
1937年7月,日军侵华,抗日民族战争全面爆发。为保家卫国,江西人民穿起戎装,奔赴抗日战场。1944年,国民政府发起“十万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在“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宣传鼓舞下,江西大地掀起了从军高峰,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仅兴国县征兵人数达13977人(注:兴国县志[M].1988年,P5.)。虽然抗战期间江西因参军参战形成的劳力外流的趋势仍如以前,但与苏区革命战争时比,奔赴抗日战场的青年劳力人数还是有所减少。而与从军劳力外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整个抗战时期有一股巨大的人口迁入流涌入江西。1937年8月,日军发动“八·一三”事变,侵入上海,战争烽火开始蔓延至江浙沿海各省,沦陷区的难民不断流入江西等内地省份避难。1937年9月至1939年5月,江西省赈济会收容难民达6万人,配置安插各县人数15.9万人,运配江浙皖过境难民至湘粤桂各省240余万人。1939年初,日军侵入江西,战火延至赣北。3月,江西省政府和南昌的学校、商人迁至泰和,当时南昌一个师范学校就搬迁在我们这次调查的一个样本村——马岭村。5月,武宁等赣北14县沦为战区。此时,大批难民开始迁移到江西的后方;当时江西省赈济会收容难民数目每月约在8万人。1939年5月至1940年,江西省赈济会收容难民数达1295715人,全省各县设置难民收容所共165所(注:许德瑗.十年来江西赈济事业[M].见赣政十年,转引自温锐.劳动力流动与农村社会经济变迁.)。
除了遭受战乱的影响外,江西还频遭自然灾害的危害。据夏明方(2000)的研究表明,仅在民国时期,江西省遭受大型自然灾害的次数就达15次之多。1915年有19个县遭受水灾;1921年有47个县分遭水灾或旱灾;1924年有40个县110万人遭水灾;1925年有41个县100万人遭受特大旱灾造成大饥荒;1928年47个县遭大蝗灾;1929年45个县遭受大蝗灾12县遭旱灾;1931年45县202万人遭受大水灾;1932-1934年连续遭大水灾;1934年又有74县遭旱灾,该年水、旱灾共造成灾民774万人;1935年鄱阳湖各县洪水决堤,50个县232万人受灾,“数十万饥民涕泣逃荒”(注: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编.中华民国二十年水灾区域之经济调查[J].金陵学报,第2卷第1期.);1937年51县遭水灾;1939年34县遭旱灾:1943年42县14万人遭水灾;1948年有70个县240万人遭水灾。同时在鄱阳湖周边各县和赣江下游,由于受血吸虫病的肆扰,“男死、女嫁、小孩长不大”,江西省星子县海会乡杨府里村1000余居民在20年代末期即已死绝,随后迁入的河南移民1000多人,又在后30年内死亡殆尽。
如果说战乱、灾荒、虫害和瘟疫是造成人口大量死亡和外徙的外在原因,那么人口繁殖所形成的人土矛盾,就是人口大量迁徙的内在原因。人口的繁殖速度过快,生存资源(主要是土地)短缺带来的生活压力,使得一些宗族不得不分化徙居,形成农民流动的另一种景观。如古竹唐氏先后有子孙徙往江西的莲花、安福和广西等8个地方去开创家业;吴村的吴氏也先后有子孙分支徙居江西南丰、临川和湖南澧陵、福建彰州等地;康山村的章氏也有分徙江西赣南、广东韶关等地;肖田村的肖氏也有分徙江西赣南、湖南茶陵等地……不过,从个案研究的情况看,如古竹村、市田村、马岭村、康山村、滁山村等都还出现了一些人出外做生意或经商的现象,当时他们主要流向是家庭所处地的州府,也有去南昌、长沙和广西南宁的,而滁山村则主要是到云南去做药材生意。
美国著名学者、汉学家何炳棣在研究1368-1953年之间中国的人口问题时,还敏锐地注意到玉米、甘薯对明清时期移民开发的影响。十六世纪,原产于美洲的农作物品种玉米和甘薯输入中国,这种作物与中国传统的以家族为单位的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方式相结合,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粮食生产能力,粮食产量稳步提高为大规模的人口增长创造了条件,加上明朝长期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中国的人口“从十四世纪后期的约六千五百万增加到万历二十八年(一六00)的约一亿五千万”,到十八世纪末,全国人口超过三亿(何炳棣,1989)。这样,一方面玉米的传入因提高了粮食的产量而带动了人口的大量增长,而人口大量增长产生的对食物的需求,和玉米的种植带来的经济效益又促进了明清时期对大面积丘陵山地的开发,导致大量垦荒农民向江西、湖南的山区迁移集中,后来垦荒农民在长江中下游的其他省份和福建也到处可见,许多过去荒无人烟的山地深菁逐渐为新来的移民开垦出来,变成新的居民点。虽然无法知晓我们调查的20个村中有多少个是因这种移民方式而形成的,但在这20个村中有5个今天仍有种植玉米的传统,占25%,有16个现还有种植甘薯的传统,占80%。
三、改革开放前的农民流动状况
1949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在党和人民面前存在着很多困难,面临着很多考验。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党先后领导和组织一系列的重大斗争。1950年6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提出党夺取革命战争胜利后面临的最大课题是如何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根据这一部署,从1950年冬开始,在新解放区占全国人口一半的农村,党领导农民进行了土地制度的改革。
江西省的农村土地改革是从1950年3月开始部署的。当时中共江西省委对土改工作的认识(注:当时对江西农村及土地改革的特点归纳为三点,一是江西是新解放区,又是老根据地.由于形势的变化,农村情况复杂,进行土改很有必要.二是(如上所述).三是江西由于长期遭受战争的破坏,人口大量流失和死亡,农村劳力缺乏,土地大面积荒芜,农村的地价低而工价高,地主一般不雇工,而是乘机兼并土地,再把土地出租给农民.)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江西是一个经济上、文化上都十分落后的省,农村封建宗族关系根深蒂固,地主阶级在农村有着很大的势力。要取得土改胜利,就必须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制定的土地改革总路线。要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确保农村90%以上的人口积极参加反封建斗争;要中立中农,扩大反封建统一战线,不动他们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以达到最大限度地孤立地主阶级;同时,对地主阶级也要进行分化瓦解和区别对待,重点打击少数恶霸地主、不法地主和把持封建宗族权力的大地主(钟家明等,1988:602)。”从调查的20个样本村情况看,土地改革大致都是在1950年11月左右开始的,到1951年底都已基本结束。这与全国的情况大概相似,到1953年春,除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全国土地改革都已完成,有三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获得了约七亿亩土地和大量生产资料。
土地改革虽然没有改变小农经济的个体性质,但因废除了封建的土地制度,个体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中国农村生产力得到了一次大解放,农业生产得到大的发展。在进行土地改革时,江西农村还处于自给自足的“半自然经济”状态下,为此农民会根据自己的家庭生活所需来作出耕作种植的选择,如古竹村、吴村有种植棉花,东林村有种植烟草,马岭村有种植芝麻和苎麻,肖田村有种植花生,朝阳村有种植白莲。但土地改革运动的推行、粮棉统购统销政策的实行和合作化运动的实施,正如黄宗智(2000)所指出的,中国乡村社会旧的,以分散、自立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政治体制被巨大的、以集体化和计划经济为基础的国家体制所取代,农民的耕作和生产也由自上而下的经社合一的政府组织统一计划和安排。同时使得多种经营的经济形式被改造成单一的农业经济,小生产者在得到土地的同时也逐渐失去了生产经营上的选择权。至1956年,这些村在种植结构上基本是单一的水稻种植(注:只有吴村在1962年根据上级政府的要求恢复了棉花种植,形成粮、棉结合的种植结构.(唐晓腾,2002)),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和农业生产的活力,至此从源于生产的自主性而走向了源于生产的政治性。
在土地改革运动基本结束后,我国从1953年开始执行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从而掀起了第一轮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高潮。为了加快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建设和发展,我国采用了“以农养工”的基本政策,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方式,形成了农民向国家、向工业建设贡献力量的重要渠道。至1958年,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建立后国家与农民的第一轮“密月”(注:关于解放后国家与农民的关系问题,曹树基(2002)在《国家与农民经济的两次蜜月》一文中有详细的论述;美国著名学者Edward Friedman、Paul G?Pickowicz、Mark Selden在《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一书中论及了在抗日战争时期在解放区中共与农民的“蜜月”关系.),随着人民公社制度的建立就这样草草结束了。
与政治经济制度变化相对应的,是有关农民流动的社会制度的改变。解放初期,农民的流动迁徙在政策制度上还和解放前一样是自由的。1953年随着我国“一五”计划的实施,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得到快速发展,这时城市原有的劳动力已难以满足工业生产的需要,这样,出于对土地改革后农业生产大发展局势的乐观估计,“在工业建设发展之初,特别是在矿区建设中,大批青年农民被吸收到迅速扩大的工人阶级队伍中来。”(胡绳,1991)但是大量农村青壮劳力的转移,加上受灾影响和种植工业原料作物的农业地区和农户的大量增加,1953、1954连续两年农业生产不能完成当年计划的主要指标,农业生产出现的问题,又严重影响到工业化对粮食和工业化原料作物迅速增长的需要。1953年底我国粮食市场出现局部紧张,针对这一状况,中央于1953年10月作出了关于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有系统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同时拉开了序幕;同年12月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农业合作化运动开始实施。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推行,乡村、集镇和部分小城镇的手工业者大量失业或破产,这部分人为寻求合适的职业而流入大城市;同时,政府优先发展重工业和部分特定城市的倾斜性政策,使工业的用工需求膨胀,城市劳力明显不足,于是大量招收青年农民到工厂做工人,这样又使人们对农村的未来感到不安,一些农村干部也因此流向城市;而城市之间生活水平差距因“以农养工”等政策的影响不断扩大又促使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加上自然灾害的发生导致部分农村人口为避灾而流入城市(小岛丽逸,1978)。这样。到1956年我国出现了就业、粮食供应、住宅、交通等城市问题已显得相当突出,为了解决执政以来首次面临的社会难题特别是吃饭这个大问题,1956年12月30日,国务院下发了《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次年3月2日又下发了《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补充指示》;到1957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下发了《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并于次年1月9日公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这样,占中国总人口85%的农民——随后不久是所有中国人——开始失去了迁徙的自由。
回顾解放后农民迁徙权利的变化过程,我们就可发现,随着20世纪50年代“土地改革运动”、“互助组”制度和合作化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开展,造就了一套自上而下的经济控制和行政控制网络。从此,公民的流动和迁徙权利被剥夺了,并且形成了城市和乡村的二元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这种状况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才有所松动,但严格地说,这些制度到现在仍还在延续而未能彻底改革。从我们调查的20个村来看,在改革开放前农民的流动基本上是处于禁止,当时的政策条件下农民流动(或转移)的方式(见表2)主要是政策性流动,以及像新基村、芳山村出现因工业化带来的农民非农化;还有就是开发建设性移民,如浙江新安江水库建设导致大量居民迁入江西被插花式安置在很多县市的农村,如吴村、新基村、柳田村、泉溪村和康山村都安置了新安江移民。当然也还是有少数的自发性流动,如外出做手工匠或搞副业。
1950-1979年间农民流动(或转移)的方式
表2
政策性流动开发建设性流动
流动方式(主要是浙江新安江水库
自发性流动
工业化参军、考学、招工等
建设移民)
流向 农村→城市农村→城市 农村→农村 农村→城市和农村
大致时间 1953年1962年、 1956-1978年
1968-1974年 1962-1978年
1974年
样本村数 新基村、芳山村
所有样本村 吴村、新基村、柳田村、
所有样本村
泉溪村、康山村
四、从历史视角看江西农民流动和农业生产
从20个样本村的情况来看,在1956年前,江西农民的流动都还是比较自由而又频繁的。自明清以来至1949年,造成农民流动的原因是相当复杂的,从前面的分析来看,主要有外在原因和内在原因两种,外在原因是因为战乱、灾荒、虫害和瘟疫等因素,内在原因主要是人口的大量增长带来的生存资源紧缺。当然,因这两种原因作用而形成的农民流动,在清朝晚期洋务运动之前是在农村与农村之间的流动,这是中国乡土社会一直以来所固有的农民流动方式。而自晚清洋务运动以来,工业化的发展所引发的对产业工人的需求,及其带来的自然经济的解体和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的差距,使得农民的流动变为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不过,这只是农民流动走向出现变化——开始由农村向城市流动的主要原因,而不能说成是推动农民流动的主要原因;虽然自然经济解体、近代中国工业发展对近代以来特别是民国时期的流民产生具有一定的作用,但从我们的个案调查结果来分析,这一作用不宜过于夸大。
长期以来,土地兼并一向被看作是流民形成和扩大的根源。对于中国乡土社会的土地关系,人们总是习惯于狭隘地理解为租佃关系,即地主与农民的关系,而把地主制下的农民小土地所有制视为无足轻重的因素,并认为中国的地权分配随着历史的演进愈益集中,长趋恶化,到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已经70-80%的耕地集中于总人口不到10%的地主和富农手中,并似乎已成定论。但著名经济史学家章有义、美国学者珀金斯和黄宗智,以及著名学者秦晖等人都认为从长期的历史趋势来看,地主和农民占地的比率大体稳定,汪敬虞先生甚至将近代地权分配的稳定性视为一条“铁律”(注:参见夏明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0,P94-95.)。据中央农业实验所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调查(注:中央农业实验所.全国农户离村统计[M].载.农情报告,第4卷第7期,1936年7月.),当时江西农民的离村率为6.0%,这也就表明当时江西农村土地的集中度不是很高(注:按经济学的观点,土地集中程度越高的地方,农民的离村率也必然越高中.)。那么近代以来日趋严重的地租剥削是否是农民流动的主要推动力?李文治先生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农业虽然有较高发展,地租剥削率最高,也只能侵占农民全部剩余劳动,要超过这个界限是比较困难的,否则就会妨碍农业生产的继续进行。……中国封建文明的发展更是不可想象的。”(李文治,1989)虽然我们不可否认人格化的地主为提高地租剥削率而主动辞佃退佃而造成佃户的流动,但中国的地主制经济大多数潜藏庄温情脉脉的血缘和宗族面纱下,到了民国时期这样一层面纱虽已开始褪色、消隐,但毕竟还占据着支配地位(夏明方,2000)。唐晓腾的研究也表明,民国时期及其前农民破产和变卖土地的主要原因不是因地主的剥削,而是因为抽鸦片或疫病、灾祸所致(注:唐晓腾.社会变迁中农民家族贫富变化的比较研究——对江西省古竹村的个案调查[M].未刊打印稿,2003.)。
因此,从历史的视角来看近代农民流动的原因,通过对20个样本村的调查分析我们就可发现,在解放前江西农民流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几次大的农民流徙是因为战乱和灾害而致,而在正常的流动中,既有人口压力(人多地少)带来的迁徙如宗族的分化徙居和转移,有经济压力迫于生计而迁移如逃荒、外出打长工或短工等,有经济(利益)趋动如外出做生意或经商等,还有外出求学及其他原因而造成农民的流动。中央农业实验所的研究结果(见表3)也证明了这一特点(注:中央农业实验所.全国农户离村统计[M].载.农情报告,第4卷第7期,1936年7月.)。如果从农民生存生活的基本目的出发,把农民的流动分为谋生型、谋富型和发展型三种类型的话,那么表3中的前四项(天灾、匪灾、人口压力和经济压力所产生的农民流动)属于谋生型,而表3中第五项——经济(利益)吸引和趋动则属于谋富型,表3中的第六项——求学则属于发展型。
1931-1933年间江西农民离村原因统计
表3单位:%
原因 天灾匪灾人口压力经济压力经济吸引求学其他
所占比例 47.617.0 2.8 22.7
2.1 0.77.1
美国学者威廉·彼得逊根据移民的处境、动因和目标将移民类型分为五种,即原始型、强迫型、推动型、自由型和大规模型(夏明方,2000)。如果从前面分析的江西省农民流动状况,结合威廉·彼得逊的观点来分析,可以看出,出于自然灾害和瘟疫而形成的农民大量流徙就属于原始型移民;战乱期间富裕家庭和贫困农民因不堪强制性捐赠和税赋的压力而产生的流动,以及解放后出现的大量大型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移民,属于强迫型移民;农村家族因人口大量增加所产生的人多地产矛盾而产生的分化徙居是属于推动型移民;农民外出做生意或经商、做手工匠而形成的流动及后来的青年农民为进入工业企业做工流入大城市而形成的大量农民转移,是属于自由型移民;明清时期因人口大量增长产生的对食物的需求和玉米的种植带来的经济效益导致的,大量农民到江西、湖南及长江中下游的其他省份和福建等省的山区进行垦荒而产生的移民,属于大规模型移民。
农民流动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又如何?从20个样本村的综合情况看,农业生产总的趋势是在不断发展,正常的农民流动并未给农业生产带来影响,相反,这种因人口压力和经济压力而形成的流动,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因人口的增长导致的宗族分化徙居现象,带动了农村自然村落点的增多和新开垦土地的增加,如大量的农民到丘陵山地开发垦荒;二是耕地的单位面积产量有了大的提高,据文洁、高山的研究,“从1910年到1946年,中国粮食作物的平均产量从165斤增加到204斤”,“仅就单位粮田的生产效率而论,属于世界中上等水平”(注:文洁,高山.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粮食生产效率与水平[C].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编.农村·经济·社会,第一卷,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三是20个村的人口虽然在1841-1953年112年的时间里增长了近一倍(其间因战乱死亡和被征参军的有大量人口),但在粮食的供需上是大致平衡的,只有1925年因受大旱灾、1935年因受大水灾在20个样本村都出现了饥荒。
不过在这期间也出现了三次时段性衰退:第一次是在太平天国后期;第二次是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三次在抗日战争时期。这是与江西在这三个时段间的历史特点相吻合的,因为这三个时段江西处于大战乱之中,战火所带来的对生命的忧虑、繁重的捐赠和赋税,使得民不聊生,大多数农民不得不背井离乡、流离失所,这种农民的非正常流动的结果是大量耕地撂荒无人耕种,导致了农民家庭生产的破产和农村经济的崩溃。
不过,从20个样本村的情况来看,1956年之后的农业生产却并没有因人民公社制度的建立而得到大的发展,而且在粮食的供需上也有个别村多次出现问题。同时,自上而下的行政网络强有力的控制,整个农村社会进入了一个静止、封闭的状态。由于集体化政策对传统的“以农为本”、“重本轻未”思想的“正宗”继承,农民发展正当家庭副业的行为和外出经商的念头,统统被斥之为“走资本主义的歪门邪道”;并在一个时期内提出“一切劳力归田”,甚至采取断然措施,关闭农村集贸市场,这严重窒息了农村其它产业的生机和发展。农村二、三产业的严重阄割,又反过来影响和制约了农业的生机和发展。(温锐,2001,P122-123)
五、结语
通过对20个样本村个案调查结果和有关文献资料的综合研究,我们可以发现,自明清以来至1956年,江西的农民流动一直是比较活跃的,虽然从流向来分析带有明显的阶段性特点,在清朝中叶之前江西的农民流动以流入为主,我们所调查的20个村大多数形成于该时期。当然从另一方面也可验证这一情况,如果我们从地方方言的语种和音调,来辩别、分析该地区农民流动的缘源,就可发现,赣方言是比较杂乱的;特别在江西中西部地区,存在“隔村不同音,邻乡不懂话”的现状,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上江西农村农民流动的活跃性和流入江西的人员来源地的分散性。而自太平天国以来,江西的农民流动就进入了复杂的混乱局面,在战乱中,随着战火的蔓延农民无奈地向远离战争的地方流徙。当然,在太平天国运动后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后,江西又出现了大量人员流入的状况,这一方面是原住居民的返乡回家,另一方面也有大量外来人口的流入。
从20个样本村的情况来看,导致农民流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不同时段来看,在太平天国运动前主要的原因是人口的压力和经济压力,而在太平天国运动后,主要的原因就是天灾和战乱(其中包含匪灾),其次是人口的压力和经济压力,再次才是经济利益趋动和求学等因素影响。而从农民流动的动机来看,首先是为了谋生,其次是为了谋富,最后才是为了谋求发展。不过综合比较20个样本村个案调查的结果,可以发现1956年之前,农民流动在制度上还是宽松自由,正是这种正常的农民流动,自发地调解了因人口大量增长而带来的土地资源紧缺的矛盾,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不仅没有影响还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1956年以后,农民的流动从政策制度的角度看,是失去了人身应有的自由,当时农民的流动(或转移)的政策性通道只有考学、参军、招工等极少的机会和途径,而工业化带来的农民非农化也因城乡二元体制等因素的影响进展缓慢,因此当时的农村劳力就像“袋装马铃薯”捆绑、挤压在本就紧缺的土地资源上,从而形成了一种不计报酬和地租收益、以不计代价的“劳动替代资本”投入,来稳定地从事农业生产的行为机制。在这一机制下,农民只能以追求生存和温饱为目标。这也是改革开放政策实施后大量农民外出务工现象出现的内部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