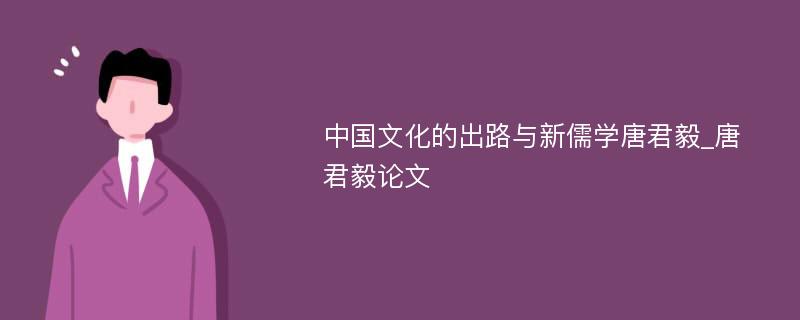
中国文化出路与新儒家唐君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论文,中国文化论文,路与论文,唐君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针对近世中华的文化危机,新儒家的领袖之一唐君毅营构了自己的中西文化观,在他的中西文化观中涵盖着寻觅中国文化出路的思想,提出了中国文化精神的价值、中国文化精神的基本特征及中国文化的缺失问题等基本思想和观点。他认为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和中国未来文化的建设必须以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为根基,在这个前提下方可吸纳西方文化精神的实践理路,“纳方于圆”、“返本开新”。并以此为他的文化践履导向。然而他所要重创的中国文化的途径受制于“道统”、“政统”的文化精神,必然不是也不可能是中国文化的出路。
【关键词】 新儒家 唐君毅 中西文化观 中国文化精神 文化保守主义
被推为现代新儒学一代宗师的唐君毅(1909-1978年)是在本世纪中叶活跃在港台的现代新儒学思潮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在港台及海外享有盛誉,被誉为“文化意识宇宙”中的巨人,“超越的唯心论者”的现代新儒学巨擘。故这里试图从分梳唐氏对“人文精神”、中国文化精神的基本特征及中国文化的缺失问题入手,进而展示和论析他的中西文化观,尤其是中国文化的出路问题,疏解他对西方文化精神的思想态度及民族文化重建、吸纳西方文化精神的实践理路的思想,旨在把握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和认同角度及其层次,以了解他面对西方文化冲击所采取的回应方式。
一
近代中国的积弱积贫所造成的民族危机,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危机,这是新儒家和西化论者的共识。但是,唐君毅对于传统文化的认识则与西化论者所持的观点迥然不同。在他的著述中,对于“人文精神”问题、中国文化精神的基本特点问题及中国文化的缺失问题,均提出了自己的建树。
关于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何在问题,唐君毅有其自己独到的理解。他认为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有其内在与外在的两方面。所谓外在的就是“存在本身即——价值”[1],亦即所谓中国文化因其长期存在,因而就有价值。而所谓的内在方面,则是指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体现为充分的“依内在于人之仁心,以超越的涵盖自然与人生,并普遍化此仁心,以观自然与人生,兼实现之于自然与人生而成人文”[2],即普遍的人们以充满仁义之心去认识和改造自然与人生。这样的一种人文精神在唐君毅的视界里就是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这种对人文精神的看法是唐君毅对中国文化的根本看法。具体言之,唐君毅认为中国文化精神的基本特征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⒈“天人合一” 唐君毅认为“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精神中的核心内容。在他撰写的一部重要著作《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中指出:“孔孟之精神,为一继天而体仁,并实现此天人合一之仁于人伦、人文之精神。由孔孟之精神为枢纽,所形成之中国文化精神,吾人即可说为:依天道以立人道,而使天德流行(即上帝之德直接现身)于人性、人伦、人文之精神仁道。”[3]唐氏以为人的内在善性之根据是在于“天道”,即“德”,而此“天道”,又不是外在于人的异己之在,而是内在于人的人性之中。从而使天德之流行可以至于人心,人心之弘伸可上达于“天德”,以致使人心与天心之间可以交贯融通,合为一体。乃可见出唐君毅所要承接的哲学传统,主要就是由孔孟至宋明儒学的心性之学。此心性之学是以人的道德实践为基础的,不同于西方传统的形上学,亦不同于西方的认识论和心理学。钱穆说:“心性之学,正为中国学术思想之核心,亦是中国思想中之所以有天人合德之说之真正理由所在。”[4]进而突出了心性之学即儒家“内圣”之学在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中的地位。今人若能把握“天人合一”为基本特征的心性之学,就是把握了中国哲学之特点和中国文化之神髓。
⒉内在超越的实践理性精神 若谓“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那么内在超越的实践理性则是这一精神内容的践履和超越方式,这一方式使中国文化精神与西方的上帝观念有所区别。在唐氏看来,“中国文化的最高精神是内倾的道德精神”。这种精神就是内在超越的实践理性精神,它既蕴含着宗教的感性超越的成分,又含有超越宗教的神人分离的外在性的因素。显然,这种精神是要以理性为指导,在道德实践中实现道德理想,这种精神既重视理想又不脱离现实,是一种“实践理性”精神。唐君毅认为这种精神的功用在于“见中和之情之致于万物,……孔子之精神为全面文化之精神,而又求直接实现之于全面社会之精神。其言其教,皆系属于其行事。”[5]从而使理性契入现实生活,以致学用一致,相继相入。
⒊道统意识 唐氏认为中国文化之性质乃是指其“一本性”。“在政治上有政统,故哲学中即有道统”。“一本性乃谓中国文化,在本原上是一个文化体系。此一本并不否认其多根。此比喻在古代中国,亦有不同之文化地区。但此并不妨碍,中国古代文化之有一脉相承之统绪,殷革夏命承夏之文化,周革殷命而承殷之文化,……秦继吉,汉继秦,以至唐、宋、元、明、清,中国在政治上,有分有合,但总以大一统为常道。且政治的分合,从未影响到文化学术思想的大归趋”,[6]即所谓作为中国文化存在其一脉相承的统绪的文化道统意识,并不因政治上的分合而有所易变。坚持中国文化有其自身的独立统绪,并作为政治的对立面,显示出了知识分子的独立自守的学术人格。在他看来,正是由于道统的存在,中国文化才有五千年的历史,唐氏断然认为:这一“存在本身即价值”。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中国未来的民主建设需要把道统从它和政统的纠缠中摆脱出来。当然他肯定道统之说,目的之一也是为实现“新统”寻找历史和理论的依据。
唐君毅将上述中国文化特征称之为中国文化的正的方面,即中国文化的优点。然而,他并不否认中国文化有其自身的弱点。他指出中国文化精神之弱点,就在于忽视“文化的分殊发展、超越精神、个体性之自由之尊位、与理智的理性之客观化四者”[7]。
唐君毅对中国文化缺点的认识,是建立在他对西方文化之优点的体认上的。关于西方文化精神,唐氏概括为四点:一是向上、向外的超越精神,肯定在人之上、人之外的超越的理想、超越的实在;二是理性客观的求知精神;三是尊重个体自由意志的精神;四是学术文化分途的多端发展的精神。唐君毅还写道:“贯于希腊文化、罗马文化与中世纪文化之精神,是一种逐渐去追求,向往‘超越现实之普遍者’之拔孚流俗的精神”,还有“贯于西方近代文化者,是一种求扩张生命力量于时空之现实世界,并实现普遍者于时空中现实事物,以致造俗世,而不惜精神之物化之精神”。[8]实际上唐在这里揭示了西方文化精神的四点内容体现着两个层面:即体现在希腊、罗马和中世纪文化中的追求、向往超越现实的宗教精神和体现在近代文化中的探求自然之理、改造自然世界以满足人的生存需求的科学精神。前者是“在求超越现实,以上达于普遍者之认识,而成就纯理科学、哲学、文艺,与依理性、依人性、依人心深处之上帝与爱,而生活之人格”[9],是向上“而求着实际存在,即成为——绝对精神实在之认取,此即西方中古精神”[10]。后者是“下达而求实际存在,即求知自然之理,并依之以改造自然世界,或制造出理想中之事物,以符人之情意上的各种特殊要求”[11]。这两种精神分别代表了西方文化传统中宗教的传统和科学的传统。不难看出,唐君毅在着重宏观地考察了中西文化精神基础上,中心思想是要肯定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价值,并且又能以正确的思维方式,正视中国传统文化的不足及西方文化的优点。
通过对中西文化的疏释,唐氏更进一步指出了中西文化的差别。他认为中国文化是“自觉地求实现的,而非自觉地求表现的”。与此相反,西方文化则是“自觉地求表现的,而未能真正成为自觉地求实现的。”在此,“自觉地求实现”和“自觉地求表现”被唐君毅看成是中西文化差别的集中表现。他认为,所谓“自觉地求实现”其内在含义是指“精神理想,完全自觉为内在,而自觉的依精神之主宰自然生命力,以实现之于现实生活各方面,以成文化,并转而直接以文化滋养吾人之精神生命、自然生命”[12]。这就是中国文化之精神。另一方面,“自觉地求表现”指的则是“精神先冒出一种超越的理想,以为精神之表现,再另表现一种企慕追求理想,求有所贡献于理想之精神活动,以将自己之自然生命力,耗竭于此精神理想前,以成就一精神之光荣,与客观人之世界之展开,而不直接以文化滋养吾人之精神生命、自然生命”。[13]这就是西方文化精神。这样,中西文化的两种形态则被唐氏分别看作是理想精神的主观进路和客观进路。所谓理想精神,就是超越的本心。因而主观进路和客观进路,即是本心的两种“势用”。中西文化都是根植于人超越的本心。通过比照,唐氏认为中国文化之缺乏就在于未能由主观进路中开出客观进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科学与民主精神之缺少,实因未能由主观进路中开出客观进路所致,即中国文化作为内在的主观进路尚未能充分地在客观层面上表现自己。这里可以见出,唐君毅一方面用抽象的方法即从哲学的角度揭示了中西文化的差异,也从另一方面深刻展露了唐氏试图倡导让中国文化精神去融摄西方文化精华的一种思想意向。
二
既然新儒家们认为中国近代的民族危机,本质上是一场文化危机。因而关键的问题是解决中国文化的出路问题,即如何重建中国的文化。基于对中、西文化的体认,唐君毅阐明了他关于如何重建我们民族文化,吸收西方文化的实践理路的思想观点。
通过对历史文化的反省,唐君毅无所讳言地指出了中国文化的缺失。他认为中国文化的缺失在于仅只弘扬了内在的主观进路,而未能充分地在客观层面上加以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科学与民主精神的缺乏实即由此而致。他以为重构民族文化就是要纳入西方文化的客观化进路,“保持客观超越理性之精神”。如果说在中国是否需要引进科学与民主这一西方文化的精神的问题上,作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唐君毅和西化论者都持有肯定的态度,那么在如何吸收西方文化的问题上,则表现出他和西化论者大相径庭的思想理路。他反对西化论者在吸收西方文化之时,对中国传统文化持全盘否定的态度。他认为西化论者的“以打倒中国文化之传统,作为接受西方文化之代价”的作法,是不能真正吸收西方文化精神,反而会将中国精神丧失殆尽。他认为这样的态度是对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的态度,是以功利的动机来鼓吹西方的科学与民主自由,这完全忽视或否定了中国文化的道德形上智慧所具有的精神价值。
在唐君毅看来,对西方文化的接受和中国未来文化的建设必须以中国文化精神为根基。也就是在肯定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的前提下,主张吸纳西方文化的长处,来丰富补充中国文化缺失的文化重建方式。他主张采取“依于肯定客观超越理想之精神,伸引吾固有文化中相同之绪,以全套而取之”的文化重建方式[14]。而如此的引进、吸收西方文化的文化重建方式,在实质上是要“完成中国文化自身常有之发展,实现中国文化之理念之所涵之事”[15]。可见,唐君毅所述的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并不是要以“自觉地求表现”的西方文化精神来取代“自觉地求实现”的中国文化精神,同时也不是利用西方文化来对中国文化修修补补。他认为中国文化精神虽然表现一种主观的进路和客观性的匮乏,但中国文化精神就其大本大源而言,并没有什么不足,而是圆满自足的。出现中国文化的弱点,是出自历史的原因,是由于其所蕴含的内在精神没有得以充分展现为具体,或者说是其所涵盖的内在精神发育缓慢而没到位。诚然,唐君毅实际上是认为中国文化精神在本源上并不拒斥西方文化之客观精神的,甚至内含着西方文化精神,而西方文化的精神之价值则只不过表现为对中国文化具有一定的刺激而已。通过这一刺激,中国文化将自己所内在蕴含的以往没有展现的精神逐一地展现出来,从而使中国文化发展步入新的阶段。唐君毅把这样一种对西方文化的接受方式称之为“纳方于圆”。也就是说要以中国文化的“圆而神”精神来融摄西方文化中的“方以智”精神。“圆而神”和“方以智”是唐君毅用以表述中国文化精神与西方文化精神的两个概念,“圆而神”代表中国文化精神,是不偏执任何文化理想,而能会通其理想,即无执的精神。“方以智”,则代表西方文化的精神,即执著于理想和理智的精神。唐君毅的“纳方于圆”的文化接受方式,其实质表现了唐氏面对西方文化,既想采取接纳西方科学与民主的文化精神,又试图避免由于西方的客观精神的影响而产生对物化的执著和心灵的异化之弊。可谓这种文化接受方式是唐氏作为新儒家的特有文化心态使然。这样的文化心态驱使他既要接受西方文化,又不能不超越特有的限阈,而这一局限性的超越则又要本着中国文化的“圆而神”的精神,才能得以圆满完成。这就初步形成了他的文化建构理路,这一文化建构的理路,就是唐君毅的“返本开新”的文化建构方式,它表明了“返本开新”的深层本质是“由中国文化精神之圆中,化出方来”。“纳方于圆”实际就是“返本开新”,即反求超越的本心以开出新文化的格局。
唐君毅还主张通过“返本开新”,未来中国的文化方可获得其新的面貌。他认为中国未来文化将呈现出作为人性人道的“人极”、作为天道的“天极”、作为多方面表现客观精神之人文世界的“皇极”并立发展,无一偏废的局面。在这个“人极”、“天极”、“皇极”并立的文化中,“圆而神”的精神完整地融摄了“方以智”精神,从而建立一个全面展开的“人文中国”。“人文中国”的建立,“就在我自己当前地位里,把天下国家的责任承担起来”。这就是唐氏所要展示的文化践履导向,他认为这样一来,他的文化理想就会得以实现,中国人文精神才得以重建和发展。
上述可见,唐君毅为使中国传统文化继续扎根立足和发扬光大,的确煞费苦心、精思睿识,也显示了唐君毅在当时处理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之关系问题的可贵之处。也反映出他的思维方式是从实际出发的,是具有辩证法的“扬弃”思想的。使以往儒家的中西文化观与科学的中西文化观的距离缩短了。然而,当我们再联系本文的第一部分内容,将不难窥探出唐君毅的中国文化的人文根本精神是他重构和振兴中国文化的大前提,他所谓的返本实质是回归到儒家道统的地位上,以大一统为常道,这是起支配决定作用的方面。以“道统”、“政统”为前提的开新,势必很难开出科学与民主,而又开出科学与民主之新,又不得不否定返本的必要性,这种开新却又是建筑在违背开新的标准的基础上的。返本与开新之间的矛盾使唐氏真是进退维谷,左右为难!因而,无论是他的“纳方于圆”之法也好,还是“返本开新”之理路也好,由于他存在着理性上向往未来、情感上却眷恋过去的矛盾情结,都脱离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根本精神这一“积淀”的干系,更冲不出他思想中固有的国粹主义倾向的樊篱。他的这些具有创建性的思想火花都受制于这个大前提,均不能不落中国的“道统”、“政统”之窠臼,束手服从于中国的“道统”、“政统”的文化精神。依照这种受根本制约而改造的中国文化显然不是根本改造的中国文化,没有受到根本改造和并非是真正重建的文化自然摆脱不了文化危机并依然是处于危机中的文化。可见,唐君毅所倡导的按照中国本根人文精神所重创的中国文化仍然只能是具有浓重国粹主义倾向的文化。显然,本此重构的文化仍然不是也不可能是中国文化的出路,中国文化的危机问题在唐氏那里势必未能得到消解。可以说,中国文化的出路只能是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扬弃中国古今文化之糟粕和外国古今文化之糟粕,吸纳中国古今文化精华与外国古今文化之精华,将中国古今文化之精华与外国古今文化的精华有机结合起来,不断整合与重创新文化,舍此,恐怕别无它路。
三
作为新儒家的宗师之一,唐君毅为民族文化的复兴作出了可贵的理论贡献,这是应当予以肯定的。然而,另一方面他又是文化保守主义的主要代表,他的文化观又难免存在着归约主义倾向。所以应当对唐君毅的文化观进行公允地评价。
从积极的意义上看,唐君毅极力地反对“五四”以后西化派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和价值虚无论;也不同于国粹派,他并不完全否认中国文化有其自身的弱点,也不同于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论者,他认为中国文化的复兴和建设,不能仅仅利用西方文化来对中国文化加以修补,而应该是体用并重,道器共举。唐君毅作为文化保守主义者,却能对西方的民主与科学加以认肯,这不能不说他的思想是积极的,也表现了一个真正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的求实精神和科学态度,其所为是难能可贵的。他的保守主义是同自由主义、激进主义“在许多共词概念的同一架构里运作”[16]。其理论实质是文化决定论,即主张民族的危机本质上是文化的危机。不同于西化论者为引进西方科学与民主而对整个传统文化采取虚无论的态度。唐君毅对民族文化有一种执著之情,他认为唤醒人们的道德意识,重建儒家的“伦理精神系统”是摆脱近代以来的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的关键。他认为对中国传统文化应持有“同情”和“敬意”。“敬意向前伸展增加一分,智慧之运用亦随之增加一分,了解亦随之增加一分”[17]。我之主观思想,了解他人之主观思想,己为而易,而若他人之思想,乃远较我之思想,为高远博大者,则我以凡俗卑近之心,更绝不能有相应而深入了解”[18]。欲真正把握和体察中国文化之生命精神,必须首先对中国文化进行同情和敬意的了解,因为中国文化乃中国圣贤之仁心的真诚流露。他认为“先存敬意之心,并不意味自己立场的放弃,而是开拓和扩大自己的心胸和度量”。以西方文化来套用附会中国文化,就势必把中国文化放在西方文化之下,或者放在和西方文化并列的地位,忽视了中国文化独特长处,就不能真正体察和证会中国文化先贤之真诚恻怛之仁心。
另外,唐君毅对中、西文化的认识,表明了他对近世之文化危机的抉择。在近世中,价值的虚无论和人的“物化”,使人处于“存在”的迷宫之中。为抗衡于价值虚无的世界,唐君毅为此而呕心沥血,苦心探究。从积极的层面而言,如果说西化派看到了传统文化的负面作用,并以其彻底否定传统文化的方式而进行思想解放,那么唐君毅所做的一切则是要表明,若想使科学与民主成为中国文化之有机组成因素,不能仅仅使其在“价值虚无”的世界中存在,而必须使其与中国文化内在本原上接榫。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唐君毅力图弘扬中华文化,确立人的道德主体,重建“人道尊严”,在形上终极关怀的意义上克服“人的存在迷失”,其内在动机和选择的虔诚都是无可厚非的,并且不乏一定的现实意义。
然而,如果我们把唐君毅的文化观,即其“返本开新”由“内圣”而“外王”的理论,放回处于文化危机的现实中国的社会脉络中去,以批判的态度来看待他的理论,便会发现其理论的内在困境。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唐君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无批判接受的态度,使他对传统文化认识很难展示传统文化的真正面貌。由于他在前瞻式的吸纳中具有浓厚的恋旧心理和所持的保守态度,故传统文化的负面因素他那里基本是被忽视或对其认识不深。于是人们很难理解被唐君毅描写得生机盎然,并将成为拯救中国与世界文化之命运的传统文化,何以连中国自己之现实也解救不了,并在近代以来遭受一系列严重的挫折?诚如林毓生所指出:“我们从唐先生的书中,很难找出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严格批判,因为他在心情上不愿意那么做。”[19]
第二,唐君毅文化观的最大困境在于中国传统儒学和近代以来许多文化思潮普遍存在的归约主义倾向。即是说唐君毅仍然以“内圣外王”之道来解决内在心灵修养和外在事物的关系。他的文化观中的文化重建方式是“返本开新”。对西方文化精神及文化的客观层面,他没有给予独立的地位。正是在他看来,“人的一切活动,都可以说是精神”,一切皆依道德自我而建立,从而也均归约为道德生活的内容,显然客观精神就被归约为主观精神。这样,客观精神就没有其自身之价值和独立存在的地位,反过来只是用来供养主观精神,成为主观精神展现自己的外在形式。因而,所谓对西方文化客观精神的接纳,则不过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观精神辖持下伸展自己从而展现自己的“空壳”而已。这就是其“内圣外王”、“返本开新”的实质。
第三,唐君毅之所以在文化观上存有归约主义倾向,就在于他对人的存在和人性的内在结构缺乏深刻的理解。人的存在是一个双层面的存在,是经验存在和超验存在的统一体。经验与超验是人性结构的真实的二元存在。这样的二元结构表明,人一方面是有限的非自足的存在,因为人在精神层面是生成的;另一方面人又具有对现象界的超越以作为一趋向无限的存在。这样的二元结构显示了人处于自由与压抑、超验与经验的张力的限阈之中,这二者是人性之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如果说近代以来的危机是文化危机,那么由于文化是人性在现实中的创化产物,因而文化危机也必然是深层的人性危机的体现。即是说传统文化的危机所体现的是人性的超验层面和经验层面的双重危机,因而文化传统的再造也只能从这两个层面入手,而不能对任何一方有所偏废。因为人性这个二元结构尽管可以沟通,但却不能将一方归结为另一方。唐君毅的文化归约主义存在根源就在于将人性的经验层面归结为超验层面。因而在他的视野里中国文化的缺失只是经验层面的,而儒家的心性之学——道德形上学,却是圆满自足的,并可以由这一形上层面推出形下层面;唐氏所谓的学习西方,也只是经验层面之事。民主与科学都被他划为经验层面上的操作方式,并没有被理解为西方文化精神之超验与经验的二元存在。从深层面看,唐氏的文化观实质也是一种“中体西用”论,只不过较之于洋务派则层次更深罢了,存在一些康德的味道罢了。
总之,唐君毅的文化观的中心思想是要肯定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价值,表现了维护民族利益的爱国主义情操,在当今高科技发展的世界,人文理想尤其重要可贵,他毕竟指出中西古今人文精神之融通即是中国文化返本开新之路,表现了一定程度的开放意识,在重新审视传统文化,寻找传统和现代化的接榫,防治民族文化虚无,克服人的文化存在迷失及解决传统与现代、中学与西学、形上与形下等方面都给我们提供了深刻的启迪和借鉴,而且具有时代意义。然而由于他缺乏人性的经验与超验的二元统一的认识,缺乏对实践内涵的本质认识,在理论上必然无法真正解决中华民族的终极关怀问题,必然无法真正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再造提供一条切实可行的光明之路。
注释:
[1][3][5][7][9][10][11][12][13][14][15]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台北正中书局,1987年版,第476页、478页、218~221页、60页、505页、506页、506页、496~497页、498~499页、501页、8页。
[2][8]唐君毅:《人文精神之重建》,台北学生书局,1980年版,第53页、129页。
[4]钱穆:《中国文化的危机与展望——当代研究与趋向》,台湾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1年版。
[6]唐君毅:《中国文化与世界》,刊于香港《民主与评论》1958年第1期。
[16]史华慈:《论保守主义》、《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保守主义》1980年台湾时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版,第20页。
[17]唐君毅主笔:《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刊于台湾《再生》杂志,1958年第1期。
[18]唐君毅:《中华人文与当代世界》第385页。
[19]《中国论坛》第15卷、第1期,第22页。
标签:唐君毅论文; 儒家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中国精神论文; 理性选择理论论文; 人性本质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人文精神论文; 中国传统文化论文; 人性论文; 科学论文; 天人合一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