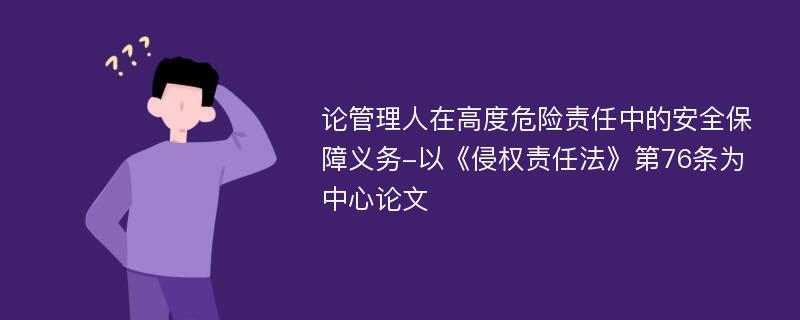
部门法研究
论管理人在高度危险责任中的安全 保障义务
——以 《侵权责任法 》第 76条为中心
王道发
(中央财经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081)
摘 要 :虽然《侵权责任法》第76条规定了管理人的安全保障义务,但是管理人承担的责任仍然属于无过错责任,而不是过错推定责任。法律规定安全保障义务旨在限制管理人减轻或者免除责任的效力,而且此种限制作用主要体现在因果关系方面。在具体适用中,通过对管理人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考量,证成受害人的损失与其自身原因的关联程度,再依据高度危险区域的危险程度和一般社会公众对危险的认识程度来最终决定免除或者减轻管理人的责任。厘清《侵权责任法》第76条规定的“安全保障义务”,对于该条的定位和适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高度危险活动区域;安全保障义务;无过错责任;责任的免除与减轻
引言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76条规定了管理人的安全保障义务,其法律意义在理论上一直存在争议。对于安全保障义务的不同认识,也引出了对《侵权责任法》第76条归责原则的不同认识。在司法实践中,法官也普遍通过考察管理人是否履行安全保障义务来判断管理人是否存在过错,从而最终决定管理人是否承担责任和具体的责任份额。此操作实际上就是将第76条按过错责任进行适用,这与将第76条规定于高度危险责任体系中的定位存在一定的矛盾。但是,即使将第76条定位于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管理人在第76条中负有的安全保障义务具体承担何种角色也存在较大的争议。
本文试图围绕《侵权责任法》第76条规定的管理人安全保障义务进行探讨,结合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具体问题,明确管理人安全保障义务的具体性质,从而厘清《侵权责任法》第76条的法律意义,为《侵权责任法》第76条的科学适用在解释论上提供可行的方案。
一 、问题的提出
《侵权责任法》第76条规定:“未经许可进入高度危险活动区域或者高度危险物存放区域受到损害,管理人已经采取安全措施并尽到警示义务的,可以减轻或者不承担责任。”在该条文中,管理人已经采取安全措施并尽到警示义务的,属于履行了安全保障义务。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如果社会交往中的危险超出了普通程度构成一种特别程度的危险,那么就属于危险责任的调整范畴而不能适用安全保障义务[1]。实际上,安全保障义务作为一种法定义务与高度危险责任是存在关联性的。因为,在属于不作为责任原始形态的对他人侵权行为之责任领域内,监督者控制潜在危险的义务通常来源于他对危险源的控制能力[2]。这同样适用于高度危险区域的管理人。
由于管理人负有的安全保障义务规定于高度危险责任之中,因此,学界和实务界对该安全保障义务的法律性质存在重大分歧,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在高危区域的管理人与作业人非为同一主体时,应将第76条定位为高危区域管理人责任的规范基础,适用过错推定责任原则[注] 参见:曹险峰.独立责任类型抑或减责事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76条的定位[J].法商研究,2018(1):137-148. 。依据此观点,管理人负有的安全保障义务,实际上就是判断管理人是否存在过错的规范标准。如果管理人证明自己已经尽了安全保障义务,则不存在过错,依据过错推定责任原则,不须承担责任。
综上,在《侵权责任法》第76条中,管理人负有的安全保障义务具有一定的边界,该义务设置的意义不在于考量管理人是否存在过错,因此该条款不适用过错推定责任。反之,将管理人负有的安全保障义务用于判断受害人过错是否存在,在逻辑上也难以自圆其说。既然《侵权责任法》第76条不属于过错推定责任,而且第76条又规定于高度危险责任章节,由于高度危险责任是危险责任的一个类型[注] 参见:张新宝.侵权责任法[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281. ,因此第76条属于严格责任的范畴。高度危险责任作为最典型的严格责任,毫无疑问其免责事由应当有严格的限制。《欧洲侵权法原则》在设计严格责任的免责事由时,遵循了这样一个原则:危险程度越高,免责的可能性越低[注] 参见:European GrouponTort Law, Principles of European Tort Law:Text and Commentary, Springer, 2005,pp.128. 。据此,管理人负有的安全保障义务实际上是严格责任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管理人责任免除的限制条件。
硬膜外血肿预后的关键是早期发现并迅速果断处理,避免脊髓不可逆性损害,即越早手术治疗效果越好,椎管内麻醉后出现肢体功能障碍症状至手术椎板切开减压的时间小于12h可实现肢体功能完全恢复[4]。对于本病例的处理自始至终贯彻该原则,从患者发现肢体功能发生障碍到再次进入手术室开始手术,麻醉和手术医生都在争分夺秒,7h内进行了有效椎管内减压,为患者后期肢体活动功能恢复较快奠定坚实的基础。
第三种观点认为,只有在管理人已经采取安全措施并尽到警示义务的前提下,受害人仍然进入高度危险活动区域或者高度危险物品存放区域,才能认定受害人具有重大过失[注] 参见:张新宝.侵权责任法[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285. 。依据此观点,管理人负有的安全保障义务是对受害人重大过失认定的限制条件。质言之,受害人是否构成重大过失,以管理人是否尽了安全保障义务作为必要条件。如果管理人没有尽到或者不能证明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就不能认定受害人构成重大过失,就不能发生管理人责任免除或者减轻的效力。
以上三种观点在规制路径上存在本质的区分。对于管理人负有的安全保障义务的不同理解,也会对《侵权责任法》第76条的定位认识产生本质的区别。如果将安全保障义务作为判断管理人过错的规范基础,第76条则是以过错责任为归责原则的独立责任类型。如果将安全保障义务作为判断或者限制认定受害人重大过失的基本条件,第76条则属于典型的法定免责或者减责条款,其以无过错责任作为归责原则。
《侵权责任法》第76条规定的高度危险区域责任以管理人承担责任为前提,只是其以责任减轻或者免除对管理人的责任方式作了反向规定。虽然在责任构成中不需要对管理人的过错进行考量,但是不意味着管理人不承担一定的义务。这也是《侵权责任法》第76条规定管理人安全保障义务的实质理由。
综上,由于学界和实务界对于管理人在高度危险责任中负有的安全保障义务的认识存在分歧,导致了规制路径也存在差异。不同的规制路径对行为人和受害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质不同的影响,最终决定了《侵权责任法》第76条的规范目的能否实现。因此,不厘清管理人在高度危险责任中负有的安全保障义务的法律性质,将会在具体适用中引起若干困境。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以往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改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适应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要求作出的创新和发展,表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必将对全面深化改革产生深远影响[7]。以往我国水资源利用和配置是以政府为主导,尽量发挥市场在配置中的作用,而这次全会上提出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为水资源产权明晰和界定、交易提供了指导原则。特别是在节约农业水资源方面,为真正实行农民用水权明晰和交易、补偿等提供了政策保障。
二 、可能引起的困境
(一)事实层面:规制对象的不确定性
依据《侵权责任法》第76条的规定,管理人负有的安全保障义务既可以得出管理人的过错,也可以判断出受害人的过错。在整个《侵权责任法》规范体系中,行为人负有的安全保障义务一般用于推断行为人在主观上是否具有过错。例如,《侵权责任法》第37条、第46条和第91条等具有安全保障义务性质的条款都被用于认定行为人的过错。而第76条规定,也可依据该内容来判断管理人的过错。
[12]Still,Pakistani economists disagree as to whether their country can fully take advantage of the opportunity.Some note that it is unclear whether the agreement will help Pakistan overcome a 50 percent trade imbalance with China.
值得注意的是,有学者认为在事实层面上也可以依据管理人负有的安全保障义务来推断受害人的过错[注] 参见:薛军.“高度危险责任”的法律适用探析[J].政治与法律,2010(5):37-44. 。此观点将管理人的安全保障义务和受害人的过错联系在一起。在管理人采取了合理的安全措施并尽到警示义务的前提下,可以推定受害人存在过失。此种观点固然有理。但事实上,如果管理人没有尽到合理的安全措施和警示义务,也可以推定受害人过失。在司法实践中,有法院就认为由于管理人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而直接引起了受害人的过失[注] 如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与姚云莉、吴延令、吴某某、吕造香、刘庆祥、国网白山市江源区供电公司、万志贵侵权责任纠纷二审案。可参见:白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吉06民终356号民事判决书。 。
基于上述分析,由于管理人的安全保障义务对管理人和受害人而言都存有判断其过错的可能性,因此,《侵权责任法》第76条规定管理人负有的安全保障义务仅从文义上看,无法辨识出其究竟适用于判断管理人的过错还是受害人的过错。质言之,管理人负有的安全保障义务规制的对象具有模糊性。
(二)规范层面:归责原则的双向性
如果从构成要件和法效力上看,《侵权责任法》第76条在形式上与过错推定责任没有明显的区分。管理人负有的安全保障义务也可以是过错推定责任的重要标志。在这点上,《侵权责任法》第76条与第91条具有相似性,第91条就是典型的过错推定责任。
但是,《侵权责任法》第76条的归责原则认定在学理上存在一些论争。一种观点认为应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3];另一种观点认为应适用过错(推定)责任原则[4]。依据第一种观点,第76条属于无过错责任,管理人负有的安全保障义务仅在责任承担阶段发生作用,而不影响责任构成。因为在无过错责任中,并不考虑行为人是否存在过错。依据第二种观点,第76条属于过错推定责任。在此情形下,管理人负有的安全保障义务则是判断管理人存在过错的直接依据,并决定最终的责任构成。无论是将第76条定位为无过错责任还是过错推定责任,管理人负有的安全保障义务在规范层面都会对管理人承担的责任产生影响。正如有学者所言,在无过错责任中,仍可以适用过失相抵规则[5]。因此,即使在无过错责任中,也能基于过失相抵规则,发生第76条所规定的“可以减轻或者不承担责任”之效果。
实际上,单行法对于一般社会主体要求的规定与《侵权责任法》第76条所规定的“未经许可进入高度危险活动区域或者高度危险物存放区域”是对应的。例如,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的内容就体现了这一点[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规定:“行人非法进入高速公路造成自身损害的,当事人请求高速公路经营者承担赔偿责任的,适用《侵权责任法》第76条规定。” 。另外,《侵权责任法》第76条和《道路交通安全法》之间也表现出了有机联系。《侵权责任法》第76条规定的适用条件所要求的“未经许可进入高度危险活动区域或者高度危险物存放区域”和“管理人负有的安全保障义务”与《道路交通安全法》对受害人的禁止规定和道路管理人的安全保障义务是相互对应的。
(三)利益层面:保护中心的模糊性
可见,虽然安全保障义务具有作为认定过错的规范基础之功能,但是不能由此得出,只要存在安全保障义务的规定,就可以认定为过错责任。更为重要的是,除了认定过错外,也应当正视民法上的安全保障义务在因果关系的判断中所具有的特定法律意义。当然,对于安全保障义务在因果关系的解释上应当有所区分。在侵权责任法上,责任构成都以特定归责原则作为基础,而归责原则实际上就是责任承担的价值判断。具体而言,过错责任是以行为人的过错作为价值判断标准,而无过错责任则是以损害结果作为价值判断基础,因果关系的判断对于无过错责任的构成具有根本的影响。因此,笔者认为,安全保障义务对于因果关系的认定意义主要体现于无过错责任之中。毕竟,在过错责任中,如果行为人履行了安全保障义务,就可以直接判断行为人不具有过错,从而认定责任不构成,无须再就因果关系是否成立进行考量。而在无过错责任之中,由于责任构成不需考虑行为人是否存在过错,因此,安全保障义务对于责任构成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因果关系的认定方面。
当然,管理人采取安全保障措施对于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具有重要意义,虽然采取措施需要付出一定成本,但受害人在管理人的安全保障措施之下较之于没有安全保障措施,遭受损害的可能性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在此情形下,也可以认为,管理人的安全保障义务是为受害人的利益保护而设计的。
但是,从文义解释上看,管理人负有的安全保障义务仍然具有进一步解释的空间。例如,虽然管理人应采取安全措施,但是该安全措施是该达到“合理”还是“充分”的程度?对于管理人的警示义务,也存在尽到的警示义务是否明显的问题。这些都直接关系到管理人是否充分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如果在尽职状态上存在瑕疵,无论依据何种观点来解释安全保障义务产生的法律后果,都会对管理人和受害人的利益产生实质影响。
由于管理人的安全保障义务既有保护管理人的一面,也有保护受害人的一面,因此,很难确定管理人的安全保障义务在适用过程中,到底是以保护何者利益为中心。在形式上,管理人的安全保障义务以避免受害人遭受损失为直接目的,且是管理人承担保护受害人利益责任的具体体现。而在实质上,管理人同样可以依托于安全保障义务的考量达到减轻或者免除责任的效力,从而保护自身的行为自由。但如果不明确管理人安全保障义务所指向的利益保护中心,就无法协调好其中蕴含的利益冲突,这也是厘清管理人在高度危险责任中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的法律意义之所在。
三 、《侵权责任法 》第 76条规定 “安全保障义务 ”的正当性
(一)“安全保障义务”的法定性
《侵权责任法》第76条规定的管理人安全保障义务内容主要来自于相关单行法的规定。例如,《铁路法》对铁路管理部门的安全保障义务进行了规定[注] 《铁路法》第47条第2款规定:“平交道口和人行过道必须按照规定设置必要的标志和防护设施。” ,《电力法》对电力管理部门的安全保障予以了明确规定[注] 《电力法》第53条第1款规定:“电力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国务院有关电力设施保护的规定,对电力设施保护区设立标志。” 。这些规定内容都属于高度危险区域相关管理者的安全保障义务,与《侵权责任法》第76条的“安全保障义务”形成呼应。质言之,《侵权责任法》第76条的“安全保障义务”都由具体法律规范予以特别规定。
管理人依照法律规定履行安全保障义务,既有维持公共安全的积极意义,也有保护高度危险区域内危险活动和危险物的作用。毕竟,高度危险区域内的危险活动或者危险物对社会生活也有极大的正面价值和利益。所以,为了能利用其带来的好处,法律仍然要允许一定程度上此种可能发生损害的危险[7]。因此,对于管理人安全保障义务的理解,不能单纯从保护受害人的利益进行考量,同时也应当考虑其对于维持高度危险区域管理秩序的重要价值。
因此,法律在规定管理人安全保障义务的同时,也会规定社会主体不得扰乱高度危险区域的正常管理秩序。例如,《铁路法》第51条规定:“禁止在铁路线路上行走、坐卧。对在铁路线路上行走、坐卧的,铁路职工有权制止。”可见,相关法律也对禁止或者限制一般社会主体在高度危险区域的活动进行了规定。而对于一般社会主体而言,遵守法律规定既是不损害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的体现,也是谨慎注意自己人身和财产利益的基本要求。
由于管理人负有的安全保障义务在无过错责任和过错推定责任的适用中,都能产生“可以减轻或者不承担责任”的效力,因此仅从管理人的安全保障义务很难判断出第76条的归责原则。在这个意义上,仅就第76条而言,如果将管理人负有的安全保障义务作为过错推定责任的标志,也无法完全排除第76条属于无过错责任的可能性。而且,从体系解释上看,第76条规定于整个高度危险责任章节之中,也为将第76条解释为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提供了正当性依据。在侵权责任法规范体系之中,其他行为人负有的安全保障义务一般可以作为过错推定责任的标志,但在第76条的适用过程中,该安全保障义务对于归责原则的指示作用具有两面性,为责任类型的确定制造了一定的困难。
值得注意的是,“行人不得非法进入高速公路”不等于“高速公路经营者有义务确保无任何行人非法进入”[8]。这就意味着管理人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的功能期待并不是以成功防止受害人非法进入高度危险区域作为权衡标准,而应当以法律规定的具体要求为准。只要管理人依据单行法律规定的要求履行了安全保障义务,就可以同时认为其符合《侵权责任法》第76条规定的“管理人已经采取安全措施并尽到警示义务”的要求。另外,由于管理人的安全保障义务是法律明确规定的,而法律是确定、可知的,在这个意义上,管理人是没有任何理由推卸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因此,管理人安全保障义务的法定性是具体的,这也为判断管理人是否履行了安全保障义务提供了可靠的标准。
(二)“安全保障义务”的边界:无法防止受害人“故意”和“自甘风险”的损害
《侵权责任法》第76条规定的管理人安全保障义务主要来源于单行法律。法律规定安全保障义务既有维持管理秩序的考量,也有预防和避免普通大众非法进入高度危险区域遭受损害的功能。但是,应当理性对待管理人的安全保障义务,并不是说法律规定了管理人的安全保障义务,就绝对能避免受害人进入高度危险区域。在原因力上,受害人的损失可能主要是自甘风险的后果,而不是管理人疏于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直接结果。因此,《侵权责任法》第76条规定的管理人安全保障义务有一定边界。
具体而言,管理人负有的安全保障义务不能防止受害人“故意”和“自甘风险”的损害。在受害人对非法进入高度危险区域遭受损害存在故意的情形下,无论管理人采取多么充分的安全措施和警示措施,都难以阻止受害人对于损害的追求。质言之,在受害人故意的情形下,法律规定的安全保障义务与受害人的损害发生没有实质意义上的联系。而且,《侵权责任法》第27条规定,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造成的,行为人不承担责任。因此,如果管理人能证明受害人存在故意,那么就应免除责任。
无论管理人是否尽到法定的安全保障义务,受害人未经许可进入高度危险区域,本身就属于自甘风险的行为。在法国和比利时等国的法律中,当受害人自甘冒险时,通常依过失相抵制度对加害人的赔偿责任进行相应地减轻[6]162。在过失相抵的适用中,也存在过错比较的重要过程,以避免发生行为人因为受害人的轻微过错而免除责任的不公结果。可见,基于受害人自身的重大过失,管理人也可以产生减轻或者免除责任的效果,而这与管理人的安全保障义务在一定意义上不存在必然的逻辑联系。
尽管如此,不可忽视的问题是,在管理人已采取合理的安全措施并尽到警示义务的前提下,受害人自甘风险进入高度危险区域遭受损害的,该如何解释管理人的安全保障义务与受害人损害之间的关系?有学者主张,在管理人已采取合理的安全措施并尽到警示义务的前提下,可以推定受害人存在过失,因此可以主张减轻其责任[注] 参见:薛军.“高度危险责任”的法律适用探析[J].政治与法律,2010(5):37-44. 。这种观点值得商榷。一方面,管理人的安全保障义务和受害人的过失属于相互独立的对象,在逻辑上管理人是否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与受害人是否存在过失不具有直接相关性。即使管理人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受害人也可以基于自身过失而发生损害。另一方面,管理人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受害人基于重大过失而发生损害,不仅可以发生减轻管理人责任的效力,还有可能发生免除管理人责任的结果。当受害人的重大过失是损害发生的全部原因时,可以免除管理人的责任。
大学英语教学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并无捷径可走。没有一种完美的理论或模式能在短期内解决教学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随着科技的发展,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单一教学模式将逐步被以学生为中心的多元教学模式所替代。认真学习建构主义理论的精髓,深化我校非英语专业大学英语教学模式改革,教学相长,定会形成师生双赢的局面。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法律对受害人进入高度危险区域行为进行了禁止或者限制规定,因此,受害人未经许可进入高度危险区域本身就属于违法行为。如果没有受害人实施该违法行为,《侵权责任法》第76条就没有考量“管理人安全保障义务”的必要性。在《侵权责任法》第76条中,管理人安全保障义务的适用是以受害人非法进入高度危险区域行为作为前提条件的。在因果关系上,受害人的违法行为才是受害人损害发生的直接原因。
第二种观点认为,在管理人已采取了合理的安全措施并尽到警示义务的前提下,可以推定受害人存在过失,因此可以减轻管理人责任[注] 参见:薛军.“高度危险责任”的法律适用探析[J].政治与法律,2010(5):37-44. 。依据此观点,管理人负有的安全保障义务是推定受害人存在过失的规范基础。即,只要管理人尽了安全保障义务,就可以直接推定受害人对损害存在过失。最终,依据过失相抵规则,减轻管理人的侵权责任。
(三)“安全保障义务”的功能价值:因果关系上的价值考量
在司法实践中,不同法院对于管理人负有的安全保障义务的法律性质也存在分歧。在有些案件中,法院以管理人负有的安全保障义务作为认定管理人过错的基本依据[注] 如辽宁省高速公路管理局与吴金宏等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二审案。可参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沈中民一终字第02468号民事判决书。 ,这是以过错责任为归责原则。而在南京南站旅客抢越铁轨致死案中,法院依据《侵权责任法》第76条的规定,认为管理人已经采取安全措施并尽到警示义务,最终判定管理人不承担责任。在此案件中,法院严格依据法定的免责事由进行判断,并没有对管理人是否存在过错的事实进行判定,更没有以管理人是否存在过错来认定责任,而是以受害人的重大过失作为免除管理人责任的法理依据。
虽然对于过失相抵规则的适用是否包括不承担责任的情形还存在争论,但大多学者认为,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扩大具有过错时,可以减轻或免除赔偿义务人的损害赔偿责任[注] 参见:梅仲协.民法要义[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221; 史尚宽.债法总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303; 王利明.侵权行为法研究(上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611; 张新宝.侵权责任法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137-138. 。但是,《侵权责任法》第76条作出了更为严格的限制规定,只有“管理人尽了安全保障义务”,才能减轻或者免除管理人的责任。这说明将第76条的规定直接界定为过失相抵制度还为时尚早,需作出进一步的解释。笔者认为,此处管理人负有的“安全保障义务”实际上是对过失相抵制度适用效力的限制。在《侵权责任法》第76条的适用中,管理人尽了安全保障义务,才能在价值判断上将受害人的重大过失界定为“造成损害”的主要原因,从而才能依据过失相抵制度减轻或者免除管理人的责任。
实际上,“安全保障义务”不仅具有考量过错的规范作用,而且在因果关系的认定上承担一定的价值判断功能。管理人负有的安全保障义务在因果关系的判断中具有重要作用。因为在侵权法中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认定包含事实判断和法律价值判断两个层面,前者判断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事实上的因果联系,后者进一步在法律价值上对前者予以修正和补充,并最终确定因果关系[9]。管理人承担的高度危险责任在本质上就是不作为侵权行为的后果。安全保障义务的作用就在于以法律规范的价值判断功能弥补不作为侵权中因果关系在事实性和相当性方面的不足[1]。因此,管理人的安全保障义务也承担着判断因果联系的功能。
《侵权责任法》第76条规定的“安全保障义务”和第37条规定的“安全保障义务”具有相似之处。有学者指出,在第37条中,如果经营者实施了其应当实施的作为行为,损害后果不会发生或者可以减轻,则认为存在因果关系;否则,不认为存在因果关系[10]。除此之外,关于《侵权责任法》第37条,也有学者进一步认为,在商场、车站、学校、幼儿园等场所,第三人实施侵权行为造成损害,商场、学校等安全保障义务人尽到安保义务的,对损害发生没有原因力,因而是第三人侵权行为[11]。此类观点认可了安全保障义务在认定因果关系上的法律意义,这同样适用于管理人的不作为行为与受害人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如果以管理人尽到了法律规定的安全保障义务可以避免或者减轻损害,来解释安全保障义务与受害人的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那么也可以证成减轻或者免除管理人责任的正当性。这实际上也是以因果关系的价值判断来解释“管理人是否应当承担责任”的问题。
自平王东迁以后,北方的经济中心之一关中经济区被秦接管,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废除落后的生产关系,建立起与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并以先进的政治制度作为保障,以严刑峻法作为依据,全面、快速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自孝公以后,农本商末的思想成为秦王朝经济政策的中心,并兴修水利,保证农业的灌溉需求。秦昭襄王命蜀郡太守李冰主持修建都江堰、秦王嬴政命郑国主持修建郑国渠,战国末期出现的两个闻名天下的宏大水利工程,说明秦国已经占据关中、蜀中两大经济区,更说明秦王朝已经成为当时经济最发达的国家。
在高度危险责任中,立法蕴含着两种利益的激烈冲突,一方面既要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另一方面也要保护高度危险活动对于社会进步的价值。“法律上要求高度危险作业人承担责任,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利益衡量的结果。虽然有可能造成严重的损害后果,但其本身仍然是有益于社会的活动,在认定高度危险作业时,同样要考虑作业的社会价值。”[6]《侵权责任法》第76条关于管理人安全保障义务的规定,不单是要求管理人采取安全措施保护一般社会主体的利益,更为重要的是,它涉及保护管理人的行为自由。通过对安全保障义务的强调,有利于平衡相关当事人的利益,防止不当加重行为人的责任[1]75。因此,第76条规定的管理人安全保障义务并不能说完全是对管理人行为自由的限制,它对管理人而言也有正面保护的价值。
随机响应动力学分析以电机与车轴的垂向相对动态位移为输出结果,并取统计学中的3倍标准差,即3 σ作为边界值,各工况计算结果汇总如表3~4所示。
在此逻辑之下,依据管理人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具体情况来判断受害人损失和管理人行为之间因果关系的紧密性,从而决定管理人是否予以免除责任或减轻责任,是符合价值判断的基本规律的。正如有学者所言在要求行为人采取积极作为措施阻碍损害发生时,涉及避害措施的充分性问题[12]。笔者认为,在避害措施的充分性判断上,应当以法律规定为主,以法官的司法裁量权为辅。如果法规已经对管理人在高度危险区域的安全和警示措施作出了具体规定,而且管理人已经按照法律的规定采取了相应措施,就应当认为管理人的安全保障措施是符合充分性要求的。但是,在法律没有规定具体的措施时,如果管理人仅是依据主观判断采取措施,此时就存在解释安全保障措施是否充分的问题。在这种情形下,应当由法官依据个案的实际情况来判断管理人的安全保障措施是否具有充分性,从而决定最终的适用效力。
这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从上层建筑层面看,既可上升到宣传中国、弘扬中国文化、讲好中国故事加以认识;从经济基础而言,它又是一项文化创意产业,值得推进。因此,其直接或间接的政治、社会、外交、文化、经济等意义及效益不可小觑。
四 、“安全保障义务 ”和 《侵权责任法 》第 76条的定位
(一)《侵权责任法》第76条属于无过错责任
《侵权责任法》第76条主要解决受害人未经许可进入高度危险区域造成损害的问题,在归责原则上应当置于高度危险责任体系中进行统一考虑,适用无过错责任。有学者主张,高度危险区域管理人对防止潜在受害人进入高危区域具有注意义务,但对高度危险源却无相应的防范能力,由其承担无过错责任原则,没有坚实的法理基础[注] 参见:曹险峰.独立责任类型抑或减责事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76条的定位[J].法商研究,2018(1):137-148. 。实际上,这就涉及管理人的法律地位问题。无论管理人是否属于高度危险源的直接开启者或者制造者,都不能忽视管理人作为“保有者”仍然属于高度危险源控制者的法律地位。即,作为高度危险区域的管理者,在现实中也具备一定的专业技术去管理高度危险源,而且特定的法律法规也会要求高度危险区域的管理者具备相应的资格和技术。基于此可以认为,高度危险区域的管理人具有控制高度危险的能力。这与作为无过错责任依据之一的“控制危险的能力”是一致的。
由此可见,无论管理人和作业人是否存在区分的情形,《侵权责任法》第76条都属于无过错责任。在司法实践中,不能认为管理人负有一定的安全保障义务就否定《侵权责任法》第76条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同样,在管理人的责任构成中,对于“安全保障义务”进行审查的意义也不在于确认管理人是否构成过错以及对责任构成的实质影响,即不能认为管理人主观不存在过错而认定管理人不承担责任。由于过错推定责任在本质上仍然属于过错责任的范畴,只是在举证责任上存在一定的特殊性,如果将第76条定位为过错推定责任,管理人不构成过错,自不需要承担责任,在逻辑上可能无法出现第76条所规定的“减轻责任”情形。在这个意义上,《侵权责任法》第76条也应当认为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
(二)《侵权责任法》第76条属于过失相抵制度
尽管在比较法上对于无过错责任是否适用过失相抵制度存在争议,但是我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都认可在无过错责任中适用过失相抵规则。主流观点认为,《侵权责任法》第3章的“不承担责任和减轻责任的情形”,对过失相抵制度作出了规定[13]。另外,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也明确规定了,在受害人具有重大过失的情形下,无过错责任可以适用过失相抵制度[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第2款规定:“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三款规定确定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时,受害人有重大过失的,可以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 。
在《侵权责任法》第76条中,受害人行为本身属于自甘风险的行为,原则上也可以认定为具有重大过失。首先,仅从文义规定,无法判断出受害人未经许可进入高度危险区域的行为是否具有主观追求损害的目的,但可以合理推断的是,在很多情形下,受害人自己是不希望或者不应当希望发生损害结果的,因此不能将受害人的行为直接界定为故意。其次,从行为的外观进行分析,受害人的行为构成重大过失更为恰当。事实上,无论法律是否规定了管理人的安全保障义务,受害人如果基于一般的社会常识可以认识到进入高度危险区域的危险性以及造成损害的可能性,依然进入高度危险区域,可以认为其存在重大过失。依据《侵权责任法》第76条的规定,如推断出受害人具有重大过失的,可以减轻甚至免除管理人的责任。这与过失相抵制度的运行逻辑基本一致。
在高度危险责任中,由于不需要考虑行为人的过错,因此规定管理人安全保障义务不是考量管理人过错的规范基础。但是,不能忽略的是,高度危险责任作为严格责任以保护受害人的利益为中心。而受害人的过错本身就是责任免除或者减轻事由,在这个意义上,管理人负有的安全保障义务也可以认为是对管理人责任减免效力的限制,此结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完全以管理人的安全保障义务来限制受害人的重大过失产生的减免效力,无法充分揭示管理人安全保障义务与管理人获得责任免除或者减轻效力之间的本质联系。
法律规定管理人在高度危险区域中的安全保障义务是价值选择的结果,旨在限制管理人的责任免除效力,以达到对受害人利益的强化保护。法律规定管理人的安全保障义务,一方面是为了避免发生受害人不知道其进入的区域属于高度危险区域而遭受损失的情形,旨在最大限度排除受害人不应当知道其进入的区域属于高度危险区域的可能;另一方面,也应当正视,即使受害人事先基于管理人的安全保障义务而知悉高度危险区域的危险性,也不能排除受害人对造成自身损害存在重大过失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管理人的安全保障义务与受害人的重大过失之间只是存在某种可能的联系,如果将两者作直接的关联显然不恰当。因此,《侵权责任法》第76条属于过失相抵制度,如果受害人的损害结果是受害人的自身原因造成的,从理论上而言可以减轻或者免除管理人的责任。
6、向外撬动阀体,同时迅速的将钢板插入阀体与油箱侧安装法兰之间,确认抽力吸住钢板后,松动预留螺栓,拆除开裂阀门。此时,应注意使钢板均匀受力,避免破坏真空而漏油。(如图)
(三)《侵权责任法》第76条属于独立的规范基础
在高度危险责任中,《侵权责任法》第76条虽然在适用上与单行法存在诸多关联,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第76条不构成独立的规范基础。笔者认为,《侵权责任法》第76条在性质上属于完全性法条,理由在于第76条具有独立的适用条件和法律效果。在司法实践中,法院的具体操作大多也是将第76条作为独立的规范来对待。例如,在南京南站旅客抢越铁轨致死案中,法院依据《侵权责任法》第76条的规定,认为管理人已经采取安全措施并尽到警示义务,最终判定管理人不承担责任。
通货膨胀对钱多的人有害,还是对钱少的人有害?我的答案是对钱少的人有害。因为钱多的人,一般都把钱变成了资产,资产保值,抵御了通胀。而钱少的人,一般是存款或持有现金。
当然,在体系解释上,《侵权责任法》第76条虽具有特定的适用范围,与高度危险责任的其他条款也可能会发生竞合关系。学界一般认为,第76条不能适用于第70条和第71条的规定[注] 参见:张新宝.侵权责任法[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285; 曹险峰.独立责任类型抑或减责事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76条的定位[J].法商研究,2018(1):137-148. 。因为在核设施致人损害责任、民用航空器致人损害责任中没有规定受害人故意之外的过失可以带来管理人免责或者减轻责任,而第76条实际上是针对受害人重大过失而产生的免责或者减责的情形。那么,规定受害人过失可以减轻责任的高空、高压等高度危险作业、危险物质致人损害条款[注] 参见:《侵权责任法》第73条。 ,是不是就必然意味着与第76条在性质上属于特殊与一般的关系?笔者认为,《侵权责任法》第73条与第76条不属于特殊与一般的关系。主要理由在于:第73条和第76条的适用要件存在重大的差异,第73条主要是关于高空、高压等高度危险作业的规定,而第76条是关于高度危险区域的规定。而且,第73条的损害是由高度危险作业活动直接引起的,而第76条的损害则是主要由受害人自己过失引起的。因此,如果受害人自己未经许可进入高度危险区域造成损害的,原则上可以独立适用《侵权责任法》第76条的规定。
需要指出的是,《侵权责任法》第76条规定的责任类型是一种高度危险区域责任,在本质上属于高度危险责任的范畴。高度危险责任除了包括对周围环境实施积极、主动危险活动引发的责任形态外(第70条至第75条),还有因其管理控制的场所、区域具有高度危险性承担的责任形态。后者是一种静态的消极的高度危险责任形态[注] 参见:王胜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条文解释与立法背景[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295; 程啸.侵权责任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594. 。这也反向指明了在第76条的适用过程中是以受害人自身原因主动造成损害作为逻辑前提的,而管理人承担的侵权责任则与管理人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存在实质的相关性。
《侵权责任法》第76条作为完全性的法条,在独立适用过程中蕴含着受害人和管理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受害人作为损害发生的起因,与管理人所负有的安全保障义务之于避免损害的作用之间本来就是不对称的。《侵权责任法》对于“高度危险”的内部考量中本身就包含了一个客观事实:即使采取安全措施并尽到了相当的警示义务也无法避免损害[14]。但是,这不意味着管理人负有安全保障义务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对于高度危险行为,尽管不能完全将其消除,也不能在所有情况下避免其转化为实际损害,但是通过相应的技术手段和管理措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其予以消减,也可以在一些情况下避免其转化为实际损害[7]98。这也说明了在《侵权责任法》第76条中,高度危险和受害人的实际损害之间存在一个演进的过程。管理人所管理的区域固然基于高度危险作业或者高度危险物本身具有高度危险性,但是对于“受害人未经许可擅自进入高度危险区域”的行为,并不具有绝对的控制能力,加之高度危险区域的高度危险属于“被允许的危险”这一价值考量,因此,法官在适用《侵权责任法》第76条的规定时,只要管理人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除高度危险区域的危险程度和一般社会公众对危险的认识程度具有特殊性外,原则上应当免除管理人的责任。对于同一适用对象,如果其他法律规定与第76条的规定存在矛盾之处,那么应当以第76条为依据,因为第76条作为独立的规范基础以管理人负有的“安全保障义务”作为价值考量基础来决定管理人责任之承担,更能体现第76条作为严格责任对受害人利益的强化保护。
五 、“安全保障义务 ”与减责效力
(一)“安全保障义务”的履行判断
《侵权责任法》第76条并未对安全保障义务的要求作出具体的规定,且单行法也没有相关规定。在这种情形下,管理人对于安全保障义务是否达到充分履行的程度可能就会存在争议。由于管理人负有的安全保障义务在第76条的适用过程中充当价值判断的角色,因此,法律对于管理人履行安全保障义务只存在行为意义上的要求,而不对结果作要求。质言之,法律不要求管理人履行的安全保障义务必须具有阻却损害发生的效果。在管理人履行了法定安全保障义务的情形下,受害人仍然进入高度危险区域而发生损害的,不能由此就认定管理人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管理人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认定也存在以实际安全措施是否最终阻止了损害发生作为判断标准。例如,在陆生度等与江苏广靖锡澄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高度危险活动损害责任纠纷上诉案中,法院认定高速公路管理者采取了必要的安全防范和警示措施。但是,高速公路入口的起落杆客观上没有完全封闭通道,陆锡兴从间隙处驶入,值班人员亦未引起注意,应认定相应安全措施的阻却效果没有实现[注] 参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锡民终字第1484号民事判决书。 ,法院因此认定管理人没有充分履行安全保障义务。
毫无疑问,管理人负有的安全保障义务对于损害发生具有重要的预防作用。正如有学者所言,对高度危险进行预防,最普遍的方法就是对涉及高度危险的物品或活动进行管理时确定量化指标及操作规程,符合该指标的可以适用,并严格按照规程从事相关事项,否则即予以禁止[7]98。这些可量化的指标为管理人充分履行安全保障义务提供了较为确定的标准,一般是由法律或者相应的行政法规等规范性文件予以规定。
人大代表退出机制的建立,打破了代表身份终届制,体现了“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民”的宗旨,辞退代表不来虚的来实的,更加激发了代表履职的责任感。本届以来,已对15名履职不认真、选民评价不高的市、镇人大代表进行约谈,其中已有9名主动辞去代表职务,劝辞2人,并将代表辞职情况及时向社会公开。
在《侵权责任法》第76条的适用过程中,受害人受到损害是因为自身的重大过失和高度危险区域内的危险源相结合引起的。而在一般的高度危险责任中,受害人受到损失是由于高度危险物品或活动本身的危险特性引起的。在这个意义上,《侵权责任法》第76条规定管理人安全保障义务的目的并不是彻底消除危险源的危险性,而是最大限度地避免受害人未经许可进入高度危险区域,在此基础上,尽力去避免实际损害的发生。
具言之,对于管理人是否充分履行安全保障义务,存在形式和实质两种不同的判断标准。形式判断标准要求管理人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行为符合法律或者其他规范性文件所要求的基本标准即可,不对管理人的个体差异或者高度危险区域的个别化情形作出区别对待。而实质判断标准要求在符合法定的情形下,还要结合管理人和高度危险区域的实际情况,作出差异化的对待。笔者认为在《侵权责任法》第76条的适用过程中,对于管理人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程度的判断标准采取形式判断标准即可,即只要管理人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行为符合法律的形式要求,就可以认定管理人已经充分履行了安全保障义务。
(二)“安全保障义务”与减责效力之间的关系
从文义上看,依据《侵权责任法》第76条的规定,只要管理人已经采取安全措施并尽到警示义务的,就可以减轻或者不承担责任。质言之,管理人尽了安全保障义务,会存在减轻责任和免除责任两种效力。在司法实践中,一般就以是否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直接决定是免除责任还是减轻责任。具体而言:(1)如果管理人尽了安全保障义务,管理人就不承担责任。例如,在白桂英、白华财、白芳琴、白桂芳、殷元福与陕西省高速公路建设集团公司汉宁分公司高度危险责任纠纷案中,法院依据《侵权责任法》第76条的规定,认定管理人已经采取安全措施并尽到警示义务,并最终判决管理人不承担责任[注] 参见:宁强县人民法院(2016)陕0726民初297号民事判决书。 。(2)如果管理人未尽到或者未充分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管理人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即产生减轻责任的效力。例如,在程某某、马某某等与国网山东兰陵县供电公司等触电人身损害责任纠纷案中,二审法院判决:“上诉人供电公司作为涉案高压电线的产权人未采取相关的安全措施,违反了《侵权责任法》第76条的规定,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注] 参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临民一终字第2303号民事判决书。
正如上文论述,在司法实践中,如果管理人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可以免除责任,这是符合《侵权责任法》76条的文义的。但是,管理人在未尽安全保障义务的情形下,依据《侵权责任法》第76条依然可以产生减轻责任的效力,承担部分的侵权责任,这似乎与《侵权责任法》的文义存在一定的出入。笔者认为,之所以产生这样的适用疑惑,一方面是由于理论界将第76条的归责原则定位为过错责任原则,将“管理人未尽安全保障义务”作为其过错与受害人的重大过失进行比较带来的;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理论上没有界定清楚到底何种情形下适用“免除责任”,何种情形下适用“减轻责任”。
其次,2017年10月22日林雪川对黎永兰施暴之后,无论是对医院的护士、黎永兰的工作单位广安区政府、黎永兰的家属,都谎称是黎永兰喝醉酒之后自己滑倒摔伤的,根本没有告知实情。直到10月25日,黎永兰的家属发现情况有异常之后报警,警方将林雪川挡获之后,他才说出了施暴的详情。
《侵权责任法》第76条在适用上属于无过错责任,管理人负有安全保障义务与过错责任或者过错推定责任没有关系,这在上文中已经论及。关键在于,管理人负有的安全保障义务与免除责任或者减轻责任到底存在何种关系?笔者认为,如果管理人尽了安全保障义务,在第76条的适用过程中,原则上应当免除管理人的责任,在例外情形下才产生减轻管理人责任的效果。这主要取决于高度危险区域内的危险活动或者危险物的危险程度和一般社会公众对该项危险的认知程度[注] 参见:张新宝.侵权责任法[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285. 。如果高度危险区域的危险活动或者危险物的危险程度较高,则管理人即使尽了安全保障义务,也不能完全免除责任,只应当减轻责任;如果因管理人的原因导致一般社会公众对该项危险的认知程度较低,也不能完全免除管理人的责任,而只能产生减轻其责任的效力。
据悉,此次规划招标的预算金额为3 500万元,包括广州市轨道交通一体化规划研究和广州东站综合交通枢纽规划两大部分。其中,广州市轨道交通一体化规划研究分为8个专题:广州市轨道交通网络发展现状及规划评估;广州市轨道交通一体化规划研究客流调查与预测;粤港澳大湾区广州铁路通道方案及广州市内布局方案;广州铁路枢纽客站分工优化调整及新客站选址研究;越珠江通道规划布局研究;三眼桥至新塘通道扩能方案研究;广深港高铁引入广州中心城区方案研究;广州市轨道交通四网融合规划方案研究。
至于管理人未尽到或者未充分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情形下,在价值判断上若能证成受害人的重大过失是造成损失的部分原因,依据过失相抵制度可以减轻管理人的侵权责任。反之,如果从逻辑上认定管理人未尽安全保障义务是导致受害人进入高度危险区域并发生损害的唯一原因,该结论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不周延的,因为受害人也可以出于自己疏忽或者盲目自信的理由进入高度危险区域从而遭受损害。但在价值判断上倒是可以认定,由于管理人未尽安全保障义务,受害人的重大过失只是造成损害的部分原因。基于此判断,从原因力标准上看,管理人才应当对受害人的损害承担部分责任。不过,此种情形下的部分责任与《侵权责任法》第76条规定的尽了安全保障义务情况下承担的部分责任具有本质的区分。管理人在未尽安全保障义务下的部分责任是由于受害人的重大过失是损害发生的部分原因带来的,而《侵权责任法》第76条规定的尽了安全保障义务情况下承担的部分责任是由高度危险区域内的危险活动或者危险物的危险程度以及一般社会公众对特定危险的认识程度决定的。从根本上说,《侵权责任法》第76条下的“减轻责任”是无过错责任在责任严格方面的强化版。
综上,《侵权责任法》第76条所规定的管理人负有的安全保障义务是对因受害人重大过失适用过失相抵制度的限制,且此种限制主要表现在原因力的解释上。如果管理人尽了安全保障义务,而受害人在此种情形下仍然未经许可进入高度危险区域,则可以认定受害人的重大过失是造成损害的全部或部分原因,从而依据过失相抵制度产生减轻或者免除管理人责任的效力。如果管理人未尽安全保障义务,即使受害人可能在事实上是出于重大过失而遭受损失,但是在价值判断上亦应认为管理人未尽安全保障义务之行为是造成损害的部分原因,管理人应当承担部分的侵权责任。
六 、结语
《侵权责任法》第76条规定管理人的安全保障义务具有特殊的法律意义,不仅提供了明确的适用要件,也为管理人的减责效力进行了必要的限制。法律规定管理人的安全保障义务,不是对管理人的过错进行规范,这意味着《侵权责任法》第76条不适用过错推定责任原则,而且由于管理人的安全保障义务在侵权责任法规范体系内被规定于高度危险责任章节之中,据此,《侵权责任法》第76条在归责原则上仍然是无过错责任原则。
管理人在《侵权责任法》第76条中承担的仍是严格责任,法律通过安全保障义务的设定对管理人减责效力的限制主要体现在因果关系方面。如果管理人履行了安全保障义务,那么受害人未经许可进入高度危险区域则是造成损害的全部原因。在此种情形下,管理人获得责任免除就具有充分的正当性。但是如果高度危险区域的危险性超出合理程度和公众的一般认识,为了突出对受害人的特殊保护,例外情形下只应当减轻管理人责任。至于管理人未尽安全保障义务的,则在价值判断上证成受害人的重大过失是损害发生的部分原因,依据过失相抵制度,应当减轻管理人的侵权责任,即管理人承担部分侵权责任。这与《侵权责任法》第76条对管理人“减轻责任”的法律规定在规制路径上存在本质的区分。ML
压痕法是将维氏或洛氏压头以一定的载荷压入涂层,然后根据载荷与裂纹曲线的斜率来判断结合强度。王海斗等[31]研究了等离子喷涂层应力水平对声发射幅值的影响,结果表明,声发射幅值与接触应力的大小无明显的关系。马增胜等[32]采用纳米压痕法研究了拉伸应变对镍薄膜力学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弹性模量和硬化指数与材料的变形程度无关,屈服强度和变形阶段有关。图1为德国评价结合强度的标准,此方法采用洛氏硬度计加载,在与压痕边缘相邻的膜层破坏后卸载用光学显微镜观察以评定其试验结果。图中HF-1~HF-4(HF是德语中结合强度的缩写)表示有足够的结合强度,而HF-5~HF-6表示结合强度不够[33]。
参考文献 :
[1]刘召成.安全保障义务的扩展适用与违法性判断标准的发展[J].法学,2014(5):72.
[2]冯·巴尔.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下卷)[M].焦美华,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269.
[3]王胜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条文解释与立法背景[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295.
[4]王成.侵权责任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218.
[5]程啸.过失相抵与无过错责任[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4(1):137.
[6]王利明.论高度危险责任一般条款的适用[J].中国法学,2010(6):160.
[7]窦海阳.《侵权责任法》中“高度危险”的判断[J].法学家,2015(2):96.
[8]陈广华,顾敏康.“行人非法进入高速公路”视域下经营者民事责任研究[J].法学家,2017(6):88.
[9]张新宝.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404-406.
[10]张新宝,唐青林.经营者对服务场所的安全保障义务[J].法学研究,2003(3):88.
[11]张力,郑志峰.侵权责任法中的第三人侵权行为——与杨立新教授商榷[J].现代法学,2015(1):42.
[12]冯珏.安全保障义务与不作为侵权[J].法学研究,2009(4):73.
[13]梁慧星.中国民事立法评说:民法典、物权法、侵权责任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344.
[14]王胜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解读[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347-348.
On the Safety Guarantee Obligation of Managers in Highly Dangerous Responsibilities :Centered on the Article 76of the Tort Liability Law
WANG Dao -fa
(Law School,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Although Article 76 of the Tort Liability Law stipulates the administrator’s security obligations, the administrator’s liability is still non-fault liability, not fault presumption liability. The law stipulates that the duty of security is designed to limit the administrator’s effectiveness of mitigating or exempting liability, and this restriction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legal causality. In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it is proved that the loss of the victim is caused by its own reasons through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administrator’s fulfillment of the security obligations, and then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administrator is exempted or mitigated according to the degree of danger in the highly dangerous areas and the general public’s awareness of the danger.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orient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Article 76 of the Tort Liability Law to clarify the “security obligations” stipulated in Article 76 of the Tort Liability Law.
Key Words : storage area for highly dangerous materials; obligation of safety guarantee; no fault liability; exemption and mitigation of responsibility
中图分类号 :DF522
文献标志码: A DOI:10.3969/j.issn.1001-2397.2019.02.08
文章编号: 1001-2397(2019)02-0104-15
收稿日期 :2018-10-22
作者简介 :王道发(1988),男,浙江苍南人,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本文责任编辑 :黄 汇
标签:高度危险活动区域论文; 安全保障义务论文; 无过错责任论文; 责任的免除与减轻论文;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