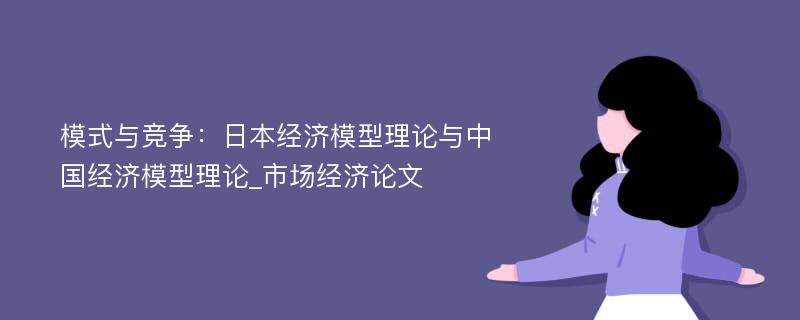
样板和对手:日本经济模式论之于中国经济模式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模式论文,中国经济论文,样板论文,之于论文,日本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模式论的兴起,是近年来中国最为重要的思想事件之一。因为持续的经济发展是中国模式论得以出现的基础,所以中国经济模式论在中国模式论之中自然占有关键位置。但是,中国经济模式论远未完成。本文试图通过与日本经济模式论的比较,确认推进中国经济模式研究的途径。
一、中国经济模式论:未完成的理论
学术意义上的中国经济模式论最初由政治学者提出①,其后主要由政治经济学家推进。截至目前,围绕中国经济模式论展开的研究在总体上并不尽如人意:支持者们的研究基本上以现象描述为主,反对者们的批评则有简单化之嫌。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模式存在与否成为争论的主题,相关研究则缺乏实质内容,处于停滞的状态。在导致上述现象的诸多原因之中,以下两点的影响最为明显。
首先,附着在中国经济模式论上的非学术因素阻碍了正反双方客观地面对这一议题。一方面,经济意识形态因素让中国经济模式论者急于概括中国经济的经验,无暇或无意进行细致而扎实的基础性研究;另一方面,一些经济学家彻底将中国的发展归结为引进市场机制的结果,对于并不完全符合经济自由主义原则的制度安排的经济价值兴趣阙如。其次,关键词的歧义让双方的研究都停留在比较初级的阶段。比如,中国经济模式论的反对者认为,一般意义上的“模式”指已经成熟、可以输出的经验,而中国的实践远未成熟,因此中国经济模式论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类似地,很多中国经济模式论者混淆了“经济模式”与“经济模式论”。实际上,经济模式指特定经济体的结构性特征,而经济模式论则是对于这些结构性特征背后的逻辑以及这些特征之间的关系的经济学解读。②
因此,对于中国经济模式论者,以下提醒或许不是没有意义的:尽管任何经济学研究都难以完全避免经济意识形态的影响,但是以经济意识形态代替经济学研究会影响本领域的研究进展。对于中国经济模式论的反对者,类似的批评也不容回避: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确实处于形成的初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经验不能在将来进入成熟的阶段,而且关于中国经济中的典型现象的经济意义以及这些典型现象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将有助于推动中国经验上升为社会科学理论——毕竟大国的经济发展历程往往蕴含着推动社会科学发展的契机,英、美、德、日等国的早期发展和经济学与管理学的进步之间的关系已经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在不将中国的实践视为已经定型、可以向国外输出的成熟体系的前提下,以开放的态度,在社会科学的意义上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机制进行研究当然具有重要意义。这种研究就是笔者所理解的中国的经济模式论,而如何从不同于上文提及的正反两方的角度有效地推进这种研究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二、作为市场经济多样性理论关键部分的日本经济模式论:被忽视的参照系
从学科类别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模式论是市场经济多样性理论的一个分支。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在学术背景等方面具有明显的差别,上文提及的正反双方却都排斥市场经济多样性理论的影响,这一态度导致中国经济模式论相关研究脱离了国际学术界的主流,处于独立发展的状态。
市场经济多样性理论发轫于20世纪60年代③,侧重于论证不同类型市场经济的内在逻辑,并致力于在动态的视角下对不同类型市场经济的竞争力进行比较。④在今天,该理论已经在国际学术界“获得了市民权”。但是,在笔者的阅读范围之内,中国经济模式论之争的正反两方都没有援引这一理论。
或许在中国经济模式论的支持者看来,有效的宏观调控和强大的国有企业意味着中国经济和一般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具有明显的区别,因此市场经济多样性理论在中国经济研究中没有用武之地。考虑到这些学者大多具有政治经济学背景,重温政治经济学界前辈在改革初期对相关问题的论述具有特殊的意义。⑤
在此仅举两例。蒋一苇认为,在经济运行机制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没有根本区别,所以是否存在宏观调控可能无法成为区分不同类型市场经济的核心标准。⑥类似地,林子力指出,与财产的所有权相比,财产的使用方式,即生产活动的组织方式是更为关键的问题。也就是说,企业的所有权同样未必是一个决定性的变量。⑦依据两位学者的分析,即使在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之下,以宏观调控和国有企业为依据,将中国经济模式论和市场经济多样性理论对立起来也未必可取。
相形之下,中国经济模式论的反对者们没有援引市场经济多样性理论的原因则非常直观:他们实际上将美国型市场经济视为市场经济的最优形态⑧,因此没有给予市场经济多样性理论应有的重视。
全面地排斥市场经济多样性理论所产生的影响是重大的:(1)这种排斥导致相关研究缺乏理论工具,而理论工具的匮乏意味着中国经济模式论的倡导者们的研究只能停留在现象层面;(2)这种排斥意味着相关研究失去了明确的参照系,而参照系的缺失不但阻碍了研究的发展,而且导致中国经济模式论的反对者们的批评无法切中要害。如果说上文提及的经济意识形态因素和关键词的歧义是阻碍中国经济模式论持续发展的观念层面的原因的话,那么,对于市场经济多样性理论的排斥则是阻碍中国经济模式论持续发展的分析技术层面的原因。由于观念层面的对立在短期内难以化解,优先解决分析技术层面的问题就成为深化中国经济模式论的一个现实选择。
将中国经济模式论纳入市场经济多样性理论之后可以发现,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在后者的各分支之中,日本经济模式论的借鉴意义最为明显。首先,日本经济模式论的形成极大地提高了市场经济多样性理论的科学性,加速了后者的理论化进程。⑨其次,日本经济是市场经济多样性理论所重视的主要经济体中唯一一个亚洲的、非基督教的经济体。因此,日本经济模式论在市场经济多样性理论中占有关键位置。基于上述事实,笔者拟以日本经济模式论为参照系,思考中国经济模式论的发展方向。⑩
总的来说,中国经济模式论处于发展初期,分析框架尚未确立,若干关键议题有待处理。在这种情况下,将日本经济模式论作为参照系引入相关研究,有助于提升中国经济模式论的学术水准。本文的分析表明,日本经济模式论对于中国经济模式论具有双重意义:在发生学方面,尽管日本经济模式论经历了发展历程和研究重点的转变,但是保持了内在逻辑的连续性,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是可供中国经济模式论参考的样板;在关键议题的处理方面,日本经济模式论则是中国经济模式论必须面对的对手。因此,能否在借鉴日本经济模式论在发生学方面的经验的基础上,在关键议题的处理上实现对日本经济模式论的“赶超”,将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中国经济模式论的前途。
三、作为样板的日本经济模式论:基于发生学的分析
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在发展阶段的完整性和研究重点的转变过程两方面,日本经济模式论堪称中国经济模式论的样板。
(一)日本经济模式论的发展阶段和研究重点的转变
就发展阶段而言,日本经济模式论经历了出现、精致化和完善化三个阶段,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从研究重点来说,与上述演变基本同步,日本经济模式论的研究重心经历了从政企关系、企业层面的组织形态到竞争力的技术基础的逐渐转变,呈现出不断深化的局面。
日本经济模式论有两大渊源:一个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密切相关,另一个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没有直接的关系。日本经济模式论的最早版本,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30年代围绕日本社会的特殊性而展开的“日本资本主义论争”以及在战后继承了这场论争的主角之一“劳农派”的问题意识的“宇野经济学”的若干内容。这一高度政治经济学化的版本,间接地影响了比较制度分析学派——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模式论的主流——的研究。(11)日本经济模式论的另一个版本出现于日本经济开始展现出国际竞争力的20世纪60年代之后。在这一时期,以政企关系为中心,国际学术界开始关注日本经济的特殊性,日本经济模式论出现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2)与当下的中国经济模式论类似,在日本经济模式论的出现阶段,政治学家发挥了重要影响,政企关系也是最为重要的主题。
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在比较制度分析学派的推动下,日本经济模式论开始进入精致化阶段。(13)在这一过程中,企业层面的组织形态成为研究的中心,演化博弈论被引入,日本经济模式论的基本框架得以确立。(14)90年代后期,随着竞争力相对衰退,日本经济模式论受到挑战。(15)面对这种挑战,日本学界开始重新审视相关领域的研究积累。在这样的过程中,日本经济模式论进入完善化阶段,研究重点开始转向竞争力的技术基础问题。
在这一时期,日本经济模式论的主要推动者由经济学家转变为管理学者,其代表人物是藤本隆宏。在日本经济处于全盛期的20世纪80年代,日本制造业企业在几乎所有产业都具有竞争优势。当时的日本经济模式论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这一现象,在论证日本企业组织形态的经济价值时没有充分重视产业变量的影响。换言之,在不同产业的日本企业组织形态基本相同且都表现出强劲竞争力的背景下,这一时期的日本经济模式论没有充分注意到这样的组织形态在不同产业具有的经济价值有所不同。(16)但是,90年代中期之后,日本电子企业的竞争力出现明显下滑。这种变化自然让日本经济模式论的说服力大打折扣。在这样的背景下,藤本隆宏从产品建构理论——企业战略领域的最新进展——出发,对日本经济模式论进行了完善。(17)
在产品建构理论的框架下,依据产品的技术逻辑,制造业的产品可以区分为封闭集成型、开放模块型和封闭模块型三类,汽车、电子和机床分别是这三类产品的代表。藤本领导的研究团队指出,日本企业竞争力的相对衰退并不是全局性的:在电子企业竞争力下降的同时,汽车企业竞争力在持续上升。这一现象表明,日本企业的组织形态至少在部分产业仍然具有明显的经济价值。(18)而且,藤本的研究没有停留在现象描述的阶段。在将产品的建构特征数量化的基础上,藤本在统计学或一般理论的意义上确认了产品的建构特征和日本企业出口竞争力之间具有的明确的相关关系,即日本企业的组织形态在汽车等集成型产品的设计和生产过程中仍然具有明显的经济价值。(19)
从本文的视角来看,藤本等人上述工作的意义在于对日本经济模式论进行了收缩与完善:一方面,将日本经济模式论的解释范围从所有产业缩小到具有集成型产品建构特征的产业群;另一方面,为日本经济模式论提供了坚实的、产品技术意义上的依据。换言之,藤本等人的工作尽管在形式上限制了日本经济模式论的解释范围,但是在本质上深化了日本经济模式论的理论基础。
(二)对于中国经济模式论的意义
日本学界的经验表明,国别经济模式论的发展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研究重点。参照日本经济模式论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目前中国经济模式论明显处于形成的初期,中国经济模式论者在现阶段的任务在于:通过以经济学研究为中心的学术积累将其精致化,并将中国经济正在经历的产业结构和发展模式调整纳入分析视野。
首先,有志于中国经济模式论的学者应该积极地引入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推动研究重点的转变。现阶段,中国经济模式论的研究重点在于政企关系和所有制形态。特殊的政企关系和所有制形态当然是中国经济的宏观特征,但是问题的关键应该在于论证这样的政企关系和所有制形态如何影响中国企业的行为特征。毕竟企业才是经济活动的微观主体,只有从企业行为的角度才能够真正把握政企关系和所有制的影响。遗憾的是,中国经济模式论者没有注意到这一问题。如上文所述,中国经济模式论者将政企关系和所有制形态视为中国经济的本质特征。(20)很明显,对于中国经济的这种把握方式缺乏明确的“微观基础”。实际上,在市场经济多样性理论和日本经济模式论的早期版本中确实存在以政府的作用为中心来区分市场经济类型的思路,但在后续发展中这些理论都在将政企关系和企业活动联系起来的方向上实现了转化。(21)
其次,正如日本经济和日本经济模式论的发展历程所反映的那样,高速增长不可能永远持续,只重视高速增长期的经济模式论迟早会受到挑战。中国经济正处于产业结构和发展模式的调整期,而现阶段的中国经济模式论却完全没有体现这一问题。因此,如何在具有内在一致性的逻辑之下,运用统一的分析框架同时对调整期前后的中国经济发展进行分析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四、作为对手的日本经济模式论:基于关键议题的分析
在关键议题——论证本国经济的本质特征的经济价值、确立本国经济在多样的市场经济中的相对地位——的处理方面,日本经济模式论是中国经济模式论无法回避的竞争对手。
(一)日本经济模式论中的关键议题及其处理方式
日本学界通过将两个关键议题视为一体两面的方式来同时对它们进行处理。他们提炼出“交易惯例”——日本企业活动的“典型事实”——这一分析视角,通过与美国企业的交易惯例进行比较的方式来确认日本经济的特殊性,并借助这种比较来分析这些“典型事实”的经济价值。由于日本的交易惯例从一开始就被置于和美国的对应物完全相对的位置上,所以对于这样两组交易惯例的经济价值的确认实际上就是对日本经济模式与美国经济模式的相对位置的确认。
战后,关于日本经济特殊性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这些研究存在两个问题:(1)研究尽管涉及了雇佣制度、工资体系、技能形成、工会形态、竞争形态、银企关系和政企关系等日本经济的几乎所有侧面,(22)但是缺乏清晰的主线。其结果是,这一时期的日本经济模式论处于比较松散的状态。(2)一些研究具有“单线的进步史观”的痕迹,有将日本的实践视为对欧美模式的全面否定的倾向。(23)但是,在80年代中期之后,上述现象逐渐得到改观,日本经济模式研究中出现了清晰的主线,诸如“日本第一”或“日本企业代表了未来的发展方向”之类的简单观念也被更为客观的评价所代替。
在这一时期,相关研究开始向日本企业在金融、制品和劳动力市场——市场经济中的三种主要市场类型——的交易惯例集中。(24)与这些高质量的研究相关联,青木昌彦将理念型(ideal type)意义上的日、美企业在交易惯例上的差别抽象为企业的信息结构(information structure)的不同,将两者分别归纳为相对水平的信息结构和相对垂直的信息结构,并运用主流经济学的手法论证了两者之间不存在绝对的优劣之分。(25)由于信息的传递或处理方式反映了不同类型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而相对水平和相对垂直的信息结构分处信息结构的两个端点,所以青木昌彦的研究不但论证了日本企业的交易惯例的经济价值,而且表明日、美经济分属市场经济光谱的两端。在青木昌彦之后,一批学者开始自觉地对日、美企业的交易惯例的形态及其思想基础进行对比,进一步推动了日本经济模式论的发展。(26)
需要注意的是,日本学界对上述两个关键议题的处理符合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的要求。换言之,日本学界的问题意识或许是特殊的,但是其分析方法却是普遍的。因此,在进行“竞争性解释”的过程中,中国学界也只能采取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科学方法。
(二)对于中国经济模式论的挑战
和日本经济模式论一样,中国经济模式论也必须论证中国经济的本质特征的经济价值并确立中国经济模式在多样的市场经济中的相对地位。但是,在将日本学界对于同一议题的处理方式纳入视野之后,中国经济模式论者在这两个关键议题的处理上将处于两难的状态:一方面,开发出可以处理上述问题的原创性方式的难度很大;另一方面,如果采用日本学界的处理方式,中国经济模式论很可能成为对日本经济模式论的简单复制。
首先,对于上述关键议题的处理方式不但必须符合社会科学的一般原则,而且需要在方法论上有所突破。比较制度分析和产品建构理论的日本学派不但促进了日本经济模式论的持续发展,而且推动了经济学和管理学的进步。但是,从现有的分析框架和主体内容来看,对于中国经济模式论者而言,形成在学术水准和原创性上可以与日本学派比肩的处理方式的难度很高。
其次,如果采用日本学界的处理方式,即依据比较制度分析和产品建构理论的日本学派的框架,从交易惯例或信息流动方式的角度来把握中国经济的本质特征,那么在日本学者已经论证了美、日经济处于多样的市场经济的两端的情况下,中国经济模式论者将很难为中国型市场经济找到他们所期望的位置。中国经济模式论者志向高远,试图论证中国经济模式是对美国经济模式——他们唯一重视的市场经济模式——的超越,或至少将中国经济模式论证为足以与美国经济模式对置的经济模式。但是,如果采用日本学界的处理方式,在美、日经济是市场经济的两个极端类型的认识已经成为市场经济多样性理论的基础观念之一的情况下,中国经济模式将只能被处理为美、日市场经济的某种混合或变形,其理论价值将大打折扣。这种前景显然不符合中国经济模式论者的期待。换言之,面对日本学界在国别经济模式论的关键议题的处理方式上所取得的突破性进展,中国经济模式论者似乎进退维谷。正是在上述意义上,我们认为日本经济模式论是中国经济模式论的竞争对手。
五、超越日本经济模式论的途径:生产组织方式的多样性与可变性
如上文所述,日本经济模式论在发生学和关键议题的处理方面是中国经济模式论的样板和对手。在以样板的姿态存在时,日本经济模式论当然是中国经济模式论的助力,但是在以对手的形式出现时,日本经济模式论则似乎是中国经济模式论的阻力。作为样板的日本经济模式论提醒中国学界必须进行多学科的、基础性的学术积累,并将中国经济可能经历的调整纳入视野;作为对手的日本经济模式论则暗示,只有在原创性分析方法之下,中国经济的本质特征才有可能被揭示出来。很明显,对于中国经济模式论的发展来说,后者的意义可能更为重大:如果中国学界不能以不同于日本学界的方式来论证中国经济的制度安排或中国企业的组织形态的经济价值,那么不管中国经济以何种速度扩张,这种扩张的学术价值都难以被真正挖掘出来。但是,强调日本经济模式论在关键议题的处理方面是中国经济模式论的对手,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模式论只能在日本经济模式论的发展轨迹上亦步亦趋。进行这种强调的目的在于指出,只有在建立原创性的、可以反映中国经济本质特征的分析框架之后,中国经济模式论才有可能获得真正的发展。笔者认为,引入生产组织方式的视角,有助于我们理解日本经济模式论的局限并确认构筑中国经济模式论的新途径。
生产方式或者说生产组织方式指生产活动的组织方式,不但是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范畴(27),而且是市场经济多样性理论的关键内容。日本经济模式论所重视的交易惯例,实际上就是日本的生产组织方式的核心内容。这一范畴所包含的理论空间,为中国学界在吸收日本学界的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完成对关键议题的论证、实现对于作为对手的日本经济模式论的超越提供了具体的研究路径。在这种研究路径之下,中国经济模式论者可以在市场经济多样性理论的框架之下,为中国型市场经济找到至少和美、日型市场经济鼎足而三的定位。
在市场经济多样性论者看来,市场经济时代的生产组织方式具有空间上的多样性和时间上的可变性。(28)换言之,不同国家的市场经济体系具有差异,而各国市场经济体系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为其形成期的时代背景所规定。(29)在这样的视角之下,作为战后最成功的两大赶超型经济体,日本和中国的生产组织方式不但具有本国特征,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20世纪90年代前后世界范围内主流生产组织方式的演变及其特征。进而言之,由于形成的时期不同,两国的生产组织方式必然存在本质的不同。如果中国学术界能够准确地把握中国的生产组织方式的国别和时代特征,那么中国经济模式论的前景也将豁然开朗。
长期以来,生产方式或者说生产组织方式问题一直被处理成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相关研究主要以争论的形式围绕定义展开,而没有和中国经济研究联系起来。近年来,学界从多样性和可变性两个角度对于当代中国的生产组织方式的本质特征进行过初步的讨论,这些讨论或许可以为深化中国经济模式论提供思考方向。
首先,生产组织方式的多样性是市场经济多样性理论的核心命题,但是在先行研究中,所谓多样性大多只是强调国别经济体系之间的区别。但是,在将市场经济多样性理论导入中国经济研究之后出现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中国经济内部也存在明显的多样性。这一点不但是中、日两国经济的关键区别,而且是中国经济的本质特征。实际上,当代中国存在三种典型的生产组织方式:一种由富士康等跨国企业主导,另一种为本土民营企业主导,第三种被大型国企主导。(30)更为重要的是,上述三种生产组织方式的存在空间也是不同的:富士康等跨国企业主导的生产组织方式典型地存在于广东,本土民营企业主导的生产组织方式典型地存在于江浙,大型国企主导的生产组织方式典型地存在于内陆。
众所周知,日本社会具有明显的均一性,日本学界在分析日本经济的特征时,实际上也假设不同地区的生产组织方式之间不存在本质的差异。因此,如果中国学界从国家内部的生产组织方式的多样性入手,那么不但可以在国别经济模式论的关键议题的处理上获得一个具有理论高度的、与日本经济模式论不同的方式,而且中国经济的本质特征也将清晰地呈现出来。
其次,中国经济内部复数的生产组织方式的出现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技术变化密切相关。如果说日本高速增长期的生产组织方式与集成型技术关系密切的话,那么中国经济内部复数的生产组织方式的出现则与模块化的不同形态紧密相关。(31)用政治经济学的术语来表达的话,这里所说的模块化属于生产力领域的变化,而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力与生产组织方式之间的动态关系的丰富积累为我们深入地刻画这些生产组织方式的形成机制并把握中国经济的本质提供了条件。(32)
上文中曾经提及日本学界成功地论证了日、美经济分处于市场经济多样性光谱的两端。需要指出的是,日本学界是基于交易惯例这一高度学术化并具有坚实的经济学基础的视角得出上述结论的。但是,在这样的视角之下,中国经济可能存在的本质特征无法得到充分的揭示。本文引入生产组织方式这一范畴的目的,即在于提供一个重新把握市场经济多样性光谱的新视角,为揭示中国经济的本质特征提供一个出发点。在这个视角之下,中国型市场经济可以在多样的市场经济之中获得崭新的定位。从交易惯例的角度来看,日、美经济确实处于市场经济多样性光谱的两端。但是,在生产组织方式的视角下,市场经济多样性光谱将呈现不同的形态:在这种光谱之中,经济内部的生产组织方式的多样性意味着中国经济处于光谱的一端,而美、日经济将处于光谱的另一端,尽管美、日经济之间仍然存在明显的差异。
①中国模式论的首倡者雷默提及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些特征,但是他的观察是随意而零散的。随后中国的政治学者对这一主题进行了阐发。参见:Ramo J.C.,The Beijing Consensus,the Foreign Policy Centre,2004;黄平、崔之元编著:《中国与全球化: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潘维编著:《中国模式:解读人民共和国的60年》,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
②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学者倾向于将经济模式等同于政治经济体系。但是,正如本文的主体部分所展示的那样,20世纪90年代之后,在国际学术界,经济模式研究的中心已经转向企业层面的制度安排。关于这个问题,参考以下文献。Aoki M.,Towards a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MIT Press,1988.Hall P.and Soskice D.,Varieties of Capitalism: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Amable B.,The Diversity of Modern Capitalism,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Aoki M.,Kim H.-K.and Okuno-Fujiwara M.eds.,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ast Asian Economic Development: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World Bank,1996.Okimoto D.,Between MITI and the Market:Japanese Industrial Policy for High Technology,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
③Shonfield A.,Modem Capitalism:The Changing Balance of Public and Private Power,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
④Aoki M.,Towards a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MIT Press,1988.Hall P.and Soskice D.,Varieties of Capitalism: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Amable B.,The Diversity of Modem Capit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
⑤政治经济学有两种含义:一是作为理论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二是更为关注政企关系的政治经济学。本文在第一种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至于第二种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参见朱天飚:《比较政治经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⑥参见蒋一苇:《论经济民主》,《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第9页。
⑦参见林子力:《计划与市场:在一个新的层次上的探讨》,《改革》1991年第1期,第39页。
⑧宋磊、孙晓冬:《经济民主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基于生产方式视角的分析》,《经济学家》2011年第11期,第10页。
⑨著名学者理查德·弗里曼(Richard Freeman)指出,日本经济研究是20世纪80年代国际经济学中进展最为明显的领域之一。参见:青木昌彦、口ナルド·ド-ア编著『ツステムとしての日本企業』、NTT出版、1995年、ix頁。市场经济多样性理论的第二代领军学者布鲁诺·阿玛布尔(Bruno Amable)也承认,青木昌彦关于制度互补性的研究对于他的分析框架具有重要影响。参见:ブル一ノ·アマーブル『五つの資本主義』、山田銳夫ほか訳、藤原書店、2005年、1頁。
⑩中国的日本经济研究者在中国经济模式研究中集体缺席。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是,这些研究者倾向于自我定位为区域经济或国别经济研究者,较少关注中国经济研究中的理论问题。
(11)关于宇野经济学和比较制度分析之间的学术联系,参见:Song L.and Zhang Y.B.,Beyond Ideological and Empirical Descriptions:Theorizing Japanese and Chinese Development Experiences,in Xiaoming Huang ed.,Modem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Japan and China:Developmentalism,Capitalism and the World Economic System,Palgrave,2013。上述研究比较详细地讨论了日本经济模式论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的发展。因此,本文的重点在于总结90年代中期之后的日本经济模式论的特征。
(12)Johnson C.,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Policy:1925-1975,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
(13)除比较制度分析学派之外,调节学派等流派的学者也推动了日本经济模式论的发展。参见:Boyer B.and Yamada T.eds.,Japanese Capitalism in Crisis:A Regulationist Interpretation,Routledge,1999。
(14)Aoki M.,“Horizontal vs.Vertical Information Structures of the Firm”,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76,No.5,1986,pp.971-983.
(15)Richard Katz,Japan:The System that Soured,New York:M.E.Sharpe,1998.
(16)青木昌彦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但是没有展开分析。参见:青木昌彦『日本経済の制度分析:情報、インセンテイブ、交涉ゲーム』、永易浩一訳、筑摩書店、1988年、第50~55頁。另外,他的分析大量地援引了关于日本汽车企业的研究。换言之,藤本所代表的关于日本汽车企业的研究在日本经济模式论的精致化阶段已经占有重要位置,而这种位置在日本经济模式论的完善化阶段表现得更为突出。就上述意义来说,处于精致化和完善化阶段的日本经济模式论具有内在的连续性。
(17)关于产品建构理论以及基于产品建构理论的日本经济研究,参见:Baldwin C.and Clark K,Design Rules:The Power of Modularity,Cambridge:MIT Press,2000;宋磊:《战略的组织、技术基础与日本企业的兴衰》,《现代日本经济》2006年第5期。
(18)藤本隆宏『日本のものづくり哲学』、日本経済新聞社、2004年;『ものづくりからの復活』、日本経済新聞社、2012年。
(19)Fujimoto T,“Architecture-based Comparative Advantage:A Design Information View of Manufacturing”,Evolutional and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Review,Vol.4,No.1,2007,pp.55-112.
(20)儒家传统的经济效果在当下的中国经济模式论中潜在地占据关键位置。因此,论证儒家传统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是中国经济模式论者必须完成的工作。但是,先行研究没有关注这一重大问题。在本文的语境下,重要的是,尽管中、日两国的儒家传统存在差异,但是也具有共性。因此,如果像部分中国模式论者主张的那样,儒家传统对于经济活动具有重要影响,那么中国的交易惯例与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的日本的交易惯例的共性必将越来越明显。这种局面的出现意味着当下的中国经济模式论只能向日本经济模式论趋同,其理论价值将大打折扣。参见:宋磊「中国経済モデル論の起源、構成、問題点:代替案のための考察」、植村博恭ほか編著『アヅア资本主義の多樣性』、藤原書店、2013年。
(21)Hall P.and Soskice D.,Varieties of Capitalism: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Aoki M.,Kim H.-K.and Okuno-Fujiwara M.eds.,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ast Asian Economic Development: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World Bank,1996.Okimoto D.,Between MITI and the Market:Japanese Industrial Policy for High Technology,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
(22)有学者在日本人论的脉络下对于这一时期的日本经济模式论或者说日本经营论进行过比较全面的介绍。参见南博:《日本人论:从明治维新到现代》,邱淑雯译,台北:立绪文化,2003年,第384~393页。
(23)Dore R.,Japanese Factory,British Factory:The Origins of National Diversity in Industrial Relation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2.
(24)伊丹敬之ほか編著『日本の企業システム』1~4巻、有斐閣、1992年。
(25)需要注意的是,青木昌彦和藤本隆宏都将信息的流动方式或企业对信息的处理方式视为企业组织形态的本质特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两个时期的日本经济模式论保持了内在逻辑的一致性。这一点是理解日本经济模式论的关键所在。
(26)相关研究参考下述文献。Itami H.,Mobilizing Invisible Asse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今井賢一『資本主義のシステム問兢争』、筑摩書房、1992年。小池和男『日本の雇用システム:その普遍性と强み』、東洋経済新報社、1994年。Nonaka I.and Tacheuchi H.,The Knowledge-creating Company:How Japanese Companies Create the Dynamics of Innova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浅沼万里『日本の企業组織:革新的適応のメカニズム』、東洋経済新報社、1997年。武田晴人『日本人の経済思想』、岩波書店、1999年。
(27)关于生产方式的内涵,学界有长期的争论。本文在生产组织方式的意义上使用这一范畴,即将生产方式基本等同于生产组织方式。关于对生产方式的这种理解,参见吴易风:《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第56~58页;高峰:《论生产方式》,《政治经济学评论》2012年第2期。
(28)山田銳夫『きまざまな資本主義』、藤原書店、2012年。
(29)有学者提及了这一问题,但是没有意识到这一问题的本质涉及生产方式,也没有触及当代中国的生产方式的本质特征。参见高柏:《新发展主义与古典发展主义:中国模式与日本模式的比较》,《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1期。
(30)参见宋磊、孟捷:《富士康现象的起源、类型与演进:基于生产方式视角的分析》,《开放时代》2013年第3期;宋磊「中国経済モデル論の起源、構成、問題点:代替案のための考察」、植村博恭ほか編著『アジア資本主義の多樣性』、藤原書店、2013年。在与企业理论专家宫本光晴的交流中,他认为,以工序间分工为特征的中国江浙地区的生产组织方式在日本企业的发展中基本没有出现过。
(31)参见宋磊、孙晓冬:《发展型国家自主创新战略的起源与形态》,《现代日本经济》2012年第3期;宋磊:《创新活动的中国悖论:成因与启示》,《新视野》2013年第2期。
(32)在生产方式原理的视角之下,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上述三种生产组织方式的局限,从而为分析中国经济中所发生的政策转换和结构调整做理论准备。参见宋磊:《中国版模块化陷阱的起源、形态与企业能力的持续提升》,《学术月刊》2008年第2期;孙晓冬、宋磊、张衔:《模块化的发生机制与外来劳动者——社会关系的两种形态》,《教学与研究》2013年第3期。
标签:市场经济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经济研究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 市场经济地位论文; 相关性分析论文; 日本中国论文; 企业特征论文; 经济学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形态理论论文; 关系处理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