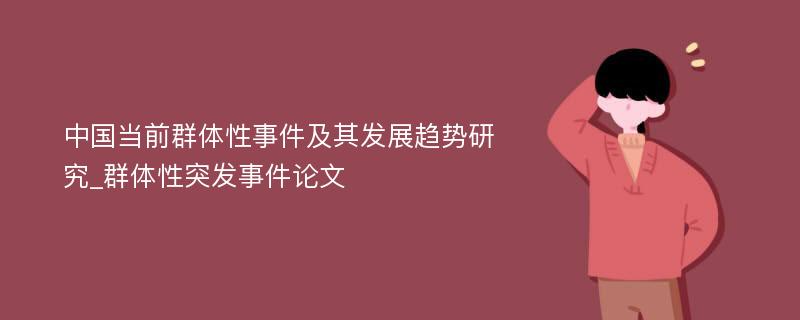
当前国内群体性事件及其发展趋势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趋势论文,群体性事件论文,国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3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1026(2008)03-0006-05
本文把国内群体性事件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立足于对群体性事件的定义、类型和特征作理论上的梳理,对已提出来的阶段性特征及其发展趋势等作一概括和分析并结合学科理论建构对此作初步探讨。
一、“群体性事件”的概念
尽管国内学界有关群体性事件研究成果丰硕,但对“群体性事件”概念和类型本身还存在不同的认识,因此,有必要厘清“群体性事件”的概念。学术界、新闻界和政府有关部门对群体性事件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贬义词演变为中性词的过程。2004年11月8日中办、国办转发的《关于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理群体性事件的工作意见》使用了“群体性事件”;2005年,第一次亮相国务院新闻发布会的中组部发言人坦言,“当前中国改革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关键时期,有些矛盾集中显现,并因此发生了一些‘群体性事件’”。[1] 自此,在主流媒体和官方话语体系中“群体性事件”逐渐被当作一个中性词而使用,这意味着它已不再是一种事实上的禁忌,反映了我国政府对此类现象基本态度的改变,使人们对此有了新的认识。
国内学者对群体性事件的理解是多义的。如,“所谓群体性事件是指突然发生的规模较大,参与人员较多,以扩大事态、加剧冲突甚至实施暴力为手段,以满足需要为目的,扰乱、影响、破坏社会治安秩序,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2];“群体性事件是指因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由一定数量人参与并形成一定组织和目的的集体上访、集会、阻塞交通、围堵党政机关、静坐请愿、聚众闹事等,并对政府管理和社会造成影响的群体行为”[3];“群体性事件是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由利益要求、观念主张相同或相近的群众形成群体,聚众以非法的形式或手段来主张合法权益表达意愿的,有较大社会危害性应依法妥善处置的事件”。[4] 早期“群体性事件”的研究中对其本质的认识是共同的:“由特定或不特定的多数人参与;参与人具有较为一致的动机、目的;活动过程中出现严重违法行为,破坏社会治安秩序,危害他人或公共安全;处置过程中警方与当事人易形成对立”。[5] 这些定义突出和强调了它的破坏性,隐含了对群体性事件的不安。
“群体性事件”就词语结构而言由三部分组成:一是“群体”,指众多人群,表明事件的主体是群体而不是个体。二是“事件”,正如阿伦特所说,指那些打乱常规过程和常规程序的事情。当然,除了指“意外发生的事”外,还有另一层含义,这些事件如果没有引起公众的注意就可以或可能不算事件。三是“性”,这里的“性”更多地是指事件本身特有的性质。群体性事件构成要件有三:其一,进行抗议活动的人群;其二,为表达严重不满而采取的集体行动;其三,有重大社会影响。三者结合构成了群体性事件特定的内涵,即特指那些突然发生、带有异常性质、涉及到众多人的公共事件。据此,我们认为,所谓的群体性事件指在特定情景下,人数众多群众聚集在一起,因某一种大致相同要求或愿望结成短时期的共同体,为了共同利益或公开表达诉求,或直接争取维护自身利益,或发泄不满、制造影响,而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集群行为。
群体性事件并非中国社会所特有。一般而言,西方国家将我们所说的危及公共安全的社会突发事件称之为骚乱(Disturbance)。骚乱是指群众由于长期压抑而形成的对某种制度或某一人群的不满,由于一具体事件的发生而集中宣泄行为。“群体性事件”在西方国家被认为是正常的游行示威。在特定的时空中,符合当时法律和政府认可的称为游行;未遵守当时法律和得到政府认可的称为“非法聚会”;发生激烈对抗的冲突则被称之为“骚乱”或者说“暴乱”;引发大规模的群众行为则被称之为“社会运动”。
除此之外,“颜色革命”是在这里有必要论及的另一个概念。这里的“颜色革命”(或者称之为“街头政治”)特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利用目标国家的社会矛盾和困难,制造政治危机,发动社会抗议、街头抗争,推翻合法政权的颠覆运动。“颜色革命”与国内研究者所指的群体性突发事件在表现形式上有极其类似之处,但本质并不一样。在西方和其他国家,群体性突发事件往往会演变为“颜色革命”。如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2003)、乌克兰的“橙色革命”(2004)、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2005),几乎都是由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引发,冲突进一步扩大,进而出现围困政府机构等行为、最后导致重大政治危机,迫使领导人下台,颠覆现有政权。
二、当前国内群体性事件值得特别重视的发展趋势
与改革开放初期的群体性事件相比较,当前的群体性事件表现出以下值得特别重视的趋势。
(一)更多的“非直接利益者”参与,其中“行动群众”的成分增多
一般说来,群体性事件现场聚集人员可分三种,即事件的“参与者”、“反对者”和“旁观者”。参与者显然是为了争取自身的利益,而更多的社会成员只是事件的旁观者(也就是“非直接利益者”),他们没有任何利益动机来参与事件。时至今日,有更多的“非直接利益者”卷入群体性事件中,构成了群体性事件的基本群众。初期群体性事件参与者在人员组成上具有很强的同质性,大多是转型期利益相对受损的弱势群体。而在今天有大量人群卷入的案例中,有很多参与者自身利益并没有受到直接的侵害,而只是普通的旁观者。在多起群体性事件中,事件的发展只要有人带头闹事就可能一呼百应,旁观者很容易变成行动群众。当前重特大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引爆过程一般表现为现场各方面人员迅速集结、数量激增、很快形成一定规模且彼此呼应。同时由于群体情绪受到交叉感染,就会促成过激群体行为,过激行为又促成狂热状态,造成群体情感发泄,难于控制。从参与者的行为特征来看,现在的参与者与初期的参与者有较大差异。目前群体性事件中参与者情绪愈来愈带有对抗性,在群众共同的心理情绪基础上,现场“行动群众”增多,过激行为突出,甚至会出现非法占据公共场所,包围冲击重要机关部门和要害单位、引发打砸抢等极端行为。当前群体性事件的暴力对抗明显加剧了矛盾性质转化的可能性,即由经济问题或者是非问题转化为敌我问题、从非对抗性演化为对抗性的可能性增大。
至于旁观者为什么更多演变为参与者的原因,有的研究者认为,“这种冲突是由人们对一些公共权力掌握者的不满累积而成”[6];还有的研究者认为,“人们越无法用言论进行抗争,也就越有可能转向暴力,即使不直接参与暴力的人也可能因此越加同情那些有暴力抗争行为的群体性事件”。[7] “非直接利益者”置社会风险不顾而成为事件的直接参与者,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事件的性质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可能预示着国内群体性事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二)组织化倾向日益明显,向有组织的策划型发展
初期的群体性事件组织形式大都属于自发松散型。群体性事件主体是由一部分因某种利益关系相一致的人构成的。在这个特殊群体中,可能有组织者和策划者,也有普通的参与者,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群体的某种特殊的利益,因而他们的行为具有一致性和功利性,一旦某种利益得到满足,这一群体也就不存在了。因此这类“群体性事件”大都没有组织的外形,或者说没有操纵整个事件的主谋者和核心组织,他们的群体行动可能会表现出有一定组织化的痕迹,且抗争有一定章法、一定的声势,但参与者多为临时纠合的群众,通常只是由一部分人怀着各自目的聚集起来,现场动议、临时策划,进而提出涉及参与者共同关心且极易被社会所接受的各种要求。
目前国内群体性事件表现出日益突出的组织化倾向。一是现在规模较大的群体性事件组织严密,重特大群体性事件基本上都有人策动、准备充分,有为首者或骨干从中进行串联、指挥和操纵。有相当数量的群体性事件酝酿之初就成立了组织(或者自发的组织)。某些事件中不难发现有“能人”或“高参”的影子。二是在联络上,采用各种方式,如口头通知、电话通知甚至张贴书面通知等形式促成群众聚集,利用多种手段推动群体互动。三是在策略选择上,一般不涉及社会核心理念,而是从传统政治话语和法律框架内寻找行动依据,为自己行动赋予符合支配价值的意义,行为力求做到合理合法,尽可能去政治化,注意避免可能被解释为“与党和政府作对”,被贴上对抗政府的标签。如多起事件始终以下岗工人、弱势群体的“生存需要”为道义支持,打着“要饭吃”、“要工作”的旗号,争取群众的同情与认可。又如郑州升达学院学生因文凭“变脸”,身穿印有“诚信”文化衫,喊出“还我学历证;退我父母血汗钱”的口号,其意不言自明。[8] 四是选择敏感日子制造事端。在行动中统一口号和着装,打出横幅、标语、散发传单,想方设法向政府施加压力。五是在行为方式上,有的案例表现出一定的克制性,如咸阳“10·24事件”(2004),“深圳特区民工填堵路陈情讨公道事件”(2006)。在群体性事件组织化水平提高的前提下,反而会出现另一种可能性,群体性事件的表达方式更多地限制在理性化范畴;有的群体性事件为通过谈判、讨价还价、让步、妥协方式解决问题,为冲突的平息留有余地。
(三)社会心态极度脆弱,“怨恨变量”增长
当前国内某些地区公众社会心态环境脆弱,甚至于畸形,有几点发人深思。社会心态失衡是造成群体事件的重要诱发因素。安徽池州事件本来只是一起普通交通事故,事情并不大但却演变成为上万群众聚集的重大群体性事件。哈尔滨“宝马车撞人事件”中,一辆普通的宝马车却成为权力和金钱的符号,引发了公众对“有钱人的横行”的极大痛恶。万州“10·18事件”中仅仅就是一句“公务员传言”就构成了万人聚集的缘由。围观群众阻挡民警执行公务说明群众对当地政府行政行为的公正性有所怀疑。万州事件“这中间起决定作用的催化剂,是一句诈言,以及它的讹传:出手一方谎称自己是国家公务员,出了什么事都可以摆平。仅此一端,足以使围观群众被激怒,再通过放大走形,一个群体性事件就此酿成”。[9] 为什么一句谎言能够引起公众这么大的情绪反应呢?对此的后续研究发现事件的诱因看似简单,有一定的偶然性,然而事发万州却有其内在的必然性,是前期三峡移民工作中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凸显的结果。一件普通交通事故,一起简单刑事案件,甚至于一句为壮胆而胡编乱造的谎言都可能酿成一场群体集体无意识的非理性发泄,这种对社会、政府和现实不满的心态可能比群体性事件本身更可怕。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群众对地方政府的极端不信任和公众社会心态极度脆弱则是社会稳定最大的危险。
(四)境外政治力量试图涉足国内群体事件,推动利益诉求的转化
近期国内群体性事件在冲突的起点和“诉讼主题”语言上发生了一些微妙变化,从土地问题到环境污染,到旨在宣示和确立农民这一社会群体抽象的“合法权益”,抗争的内容越来越广泛和深刻。在这一背景下,群体性事件的状态、形式更加错综复杂,一些境外政治力量利用群体性事件和某些社会敏感问题,造谣污蔑,恶意炒作,攻击中国的政治制度,丑化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形象。一些群体性事件本来是由追求经济利益所引发,仅限于特定的利益诉求,但在某些境外非政府组织或“民间维权人士”介入下,经济问题就出现政治化的迹象,甚至于在个别地区呈现出“寻求体制外解决问题”的倾向。有些一般群体性事件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染指,激化为严重的群体性突发事件。在有些行为方式诡秘多变,呈明显政治化倾向事件的背后不排除有一定政治目的或寻求某一社会利益的极端个体及集团插手的可能性。必须高度注意和重视矛盾性质的变异性,防止重特大群体性事件因处置不当演变为群体性突发事件,演变为骚乱、暴乱和社会动乱。
三、国内群体性事件发展变化的分析与预测
预测群体性事件,尤其是群体性突发事件,在什么时候发生和目前的地震预报一样可能是一个“世界难题”。但从操作层面,大致判断其发展变化趋势还是有可能的,也是必要的。今后若干年内在中国发生大规模,特别是特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综合多方面研究成果,有关观点大致有三种:第一,发生特大的社会冲突的规模比较小。第二,“中国农民闹不起大事,农村不可能出大事,所以农村稳定问题并不可怕”[10],由于缺乏知识分子的“加盟”,农民在近一个时期内是难以闹起大事的”。[11] 第三,在今后一段不太长的时间内,我国极有可能会发生大的社会危机。笔者认为,未来一个时期是国内群体性事件的多发期,在理论上我们应该正视目前国内已经存在爆发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甚至由大规模群体性突发事件引发局部的社会动乱的可能性。
(一)群体性事件对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构成持续威胁
经验告诉我们,此起彼伏、连绵不断的群体性事件可能动摇公众对政府的信心,消耗政权的合法性,对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构成持续威胁。影响和决定我国未来群体性事件发展变化趋势的因素有很多,但最为关键和最为重要的变量有两个:一是国内就业形势的变化;二是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中失地农民生计解决方式及其最终效果。而最不利的因素则是近年来弱势群体贫困加剧且增加速度变快。国内有的学者用弹性法和趋势外推法模拟,至少在15年内国内的失业难以缓解。[12] 这是支持我们认为今后10-20年是国内群体性事件高发期的一个有力依据。
国内学者应用一些简单可行的预测方法,“具体地讲,就是对一定区域内曾经发生过的群体性事件的因果关系进行综合分析,找出其中相对应的诱发因素,然后通过模拟方法,结合当前的现实,对照历史与现实,辅之以量化归纳法,将这些诱发因子与事件参与者的关系程度依次排队,将各种诱发因子进行量化归纳,找出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预测何种情况最容易引发群体性突发事件。[13] 对中国未来5年形势的专家预测中,接受调查的98位专家中有51位,占66.26%的认为会发生重大危机;而在危机发生种类中,经济和社会危机均排名第一。[14] 据此香港《凤凰周刊》主笔杨锦麟认为:“将2010年设为中国可能危机和前景的时间拐点”。[15] 对此不同的认识并不影响对群体性事件发展变化趋势的判断。我们面临着许多内忧外患,而对政策不满的群体性事件急剧上升直接影响政治局面的安定团结和国家政权的稳定。正视社会心态的现状,防止发生大规模群体性突发事件,避免引发剧烈的社会动荡,以至于引发全面的危机已成为当务之急。
(二)防止农村群体性事件将是今后很长一个时期维护社会稳定工作的难点
尽管早在几年前农村群体性事件就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重视,但农村问题却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在一定情况下还存在着部分地区局势变得严峻的趋势。目前的城乡统筹改革试验中,有一点应该引起高度警惕:一些近郊农村的村社纷纷挂牌变为了城市社区,“村民”摇身一变,成为了“居民”,却失去土地。现实的结果,可能目前在统筹城乡发展中对农村土地的调整较易,有的农民甚至还拿到了“下岗证”,但是暂时妥协只是掩盖了根本的矛盾。其实随着交通条件急速改善,部分地区土地不断升值,与土地联系在一起的某些特定农业人口的实际“含金量”已超过非农业人口(这一结论可从若干大城市近郊“非转农”① 几乎不可能就可以得出)。目前沉浸在新市民身份喜悦的大部分农民对此认识是不够的,但是认识不够并不等于这一事实就不存在。在某些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率先突破和大胆创新”探索中,某些不当的方式,为地方政府特别是受利益驱使的基层政府,强制征用农民土地创造了条件,引发了新的一轮土地流失。作为丧失世代赖以生存土地的代价,农民所得到的土地补偿费是不足的。土地的失去将造成农民的生存危机,尤其是通过单一的货币补偿方式安置的农民将留下若干后遗症。那些“无地、无业、无保障”的新“三无”农民在难以生存下去的情况下最终还是要找政府。
(三)防范高校群体性突发事件始终是维护社会稳定工作的重点
警惕高校成为未来国内群体性事件的集中爆发点。高校群体性突发事件,是指受国际形势、国内局势、高校管理等因素的影响,以高校学生为主体,在较短时期内骤然发生的、有悖于法律法规的群体性行为。高校群体性突发事件除了突发性和群体性外,采取外部冲突形式,是高校群体性突发事件的表现特征。“其发展的过程为:激情的言语倾诉——激动的行为干涉——激烈的纠缠取闹——激化的亚暴力事态”。[16] 事实证明,思想活跃、年轻气盛的青年学子始终是社会运动的先锋。任何时候,高校始终是维稳工作的重中之重,千万不要因“前方无战事”而忽略了对高校群体性事件的关注。
(四)“下层知识分子”的出现是一个值得警惕的信号
大学毕业生的社会地位分化、经济地位下降和精神层面混乱,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随着高校招生规模不断扩大,失业或未就业大学生数量逐年上升,当今中国开始自然形成了一个被我们在这一特定研究领域中称之为“下层知识分子”的阶层或者说利益群体(目前究竟称之为“阶层”,还是“利益群体”,判断其发展到哪一个阶段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充分理解其存在的现实和分析其可能的后果)。这里的“下层知识分子”(或者说“失意知识分子”)是一个与知识精英(主要指中高级知识分子)相对应的概念,主要指以失业、待业甚至于长期无业(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并持续一个特定时期)的大学毕业生为主构成的一个新群体。尽管“下层知识分子”目前还不被看作是一个完全独立的社会阶层,但它确实代表着某种群体或某部分人。
解决高校大学生就业难已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从个体心理发展来看,大学生毕业后最初10年的不稳定极有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职业生涯初期的经历和体验对大学生思想定型具有重要的作用。大学毕业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找不到合适工作,长期游走于职业生涯边缘,与主流社会分离,可能会造成他们对社会主流价值与现存秩序认同感的缺失;长期挫折和底层情结使他们对社会不公、下层民众面临的困难有更多的体验,从根本上影响或改变其基本的政治观点。随着长期无业大学生人数的增多,这些有相同经历、相近兴趣和一致利益的“精力过盛”者,很容易因某些问题而形成群体行动。曾经的“天之骄子”成为“贩夫走卒”,要适应中国的传统文化恐怕绝非一日之功,长期挫折和无奈可能会促使他们产生以自己的理念来改造社会的冲动,一旦这种冲动转换为争取意识形态上话语权的努力和尝试,具有政治抱负的“领袖”就自然而生了,“下层知识分子”中的精英极有可能演变成为有组织性的社会运动的组织者。而群体性事件,一旦发展到这一阶段就会形成巨大根本性的变化,未能进入体制内的“下层知识分子”很易被一些境外政治力量利用,充当政治运动的发动机。“下层知识分子”成为极端群体性事件的催化剂,群体性事件就有可能引发政治动荡,演变成为大规模的运动。
(五)国内某些地区多种不稳定因素汇聚,西部地区有可能成为爆发重大群体性突发事件的重灾区
随着社会转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群体性事件由于具有“突发性”而演变为“群体性突发事件”。当前国内若干地区催生群体性事件的各种消极因素正在积蓄,在偶然事件引发下突然释放可能具有较大的破坏性。如三峡库区在进入后移民期以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库区产业空虚影响就业和社会稳定,构成了一种被称之为“产业空虚化综合症”的现象。库区社会心态环境脆弱,移民心理交织着各种复杂的思想和感情,汇聚了各种不稳定因素,思想不稳定现象十分明显;当前部分移民就情绪而言处于失控前的“临界点”,有脱离理性、脱离法制渠道“解决问题”的迹象。这些不稳定因素如果在同一方向上的聚集和释放,可能产生较大的破坏性,以致引发烈度较大的政治事件。
收稿日期:2007-06-22
注释:
① 指非农业人口转为农业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