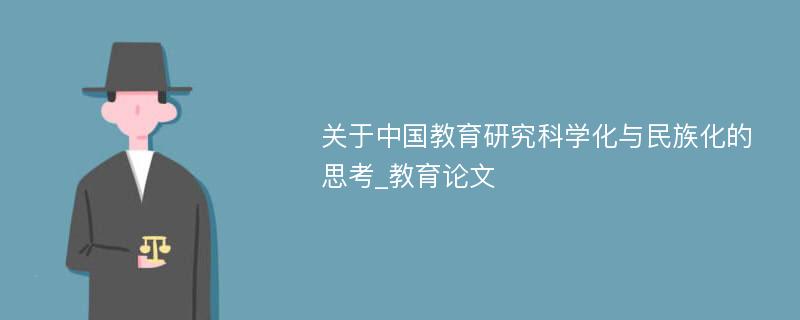
中国教育研究的科学化与民族性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性论文,中国教育论文,化与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33X(2004)04-0010-05
自从人类产生了教育,就有人对教育现象进行自觉或不自觉的研究。当然,早期教育研究还谈不上是科学研究。与西方相比,中国教育研究的科学化乃是近百年来,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的事。一些先进的中国教育家接受了西方科学精神,力求对教育现象进行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研究,他们提倡科学实验,注重科学方法,大力推广教育测验、教育调查、教育统计等教育科研方法,促进了中国教育研究的科学化进程。但另一方面,许多有识之士也明确指出,科学绝非是万能的,科学方法也不能包治百病,科学只能解决事实问题,而难于处理价值问题。因此,除热情礼赞近代西方科学精神及科学方法外,他们十分关注中国的国情民性,努力阐发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致力于教育研究的本土化与民族性探索。近十年来,教育研究中的历史研究部分也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如何认识教育历史研究的当代价值,如何更好地开掘民族教育智慧,如何把民族教育智慧有效地吸收并转化到教育学的理论建构之中,如何突出教育研究的民族特色,仍然是中国教育研究亟待改善的重要问题。没有民族性就没有世界性,中国教育学术要走向世界,就不能不致力于中国教育研究的民族性问题,努力做到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辩证统一。
一、教育研究的科学化探索与反思
所谓“教育研究的科学化”,即指对人类教育现象进行科学实证意义上的研究。很显然,这种研究只能是人类社会和理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依据法国社会科学家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关于人类理智的三个阶段理论,即所谓“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阶段”,西方社会从16世纪初就开始突破“形而上学”范域而迈向科学“实证阶段”,并于19世纪末最终完成了“现代科学知识”的结构转型。
在西方,教育的科学研究可溯源至17世纪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Johann Amos Comenius,1592-1670),而18-19世纪的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Johann Friedich Herbart,1776-1841)更是自觉地把教育研究建立在科学的心理学知识基础之上,开启了后世教育研究的科学化探索。随着赫尔巴特教育思想的全球传播,教育研究的科学化倾向得到了较普遍的认同。其后,像杜威这样的大教育家已明确指出要“谨慎地使用‘科学’这个词”,强调“没有什么自称是严格符合科学的学科,会比教育更可能遭到假冒科学的损害”[1];但在日新月异的科学革命和经济现代化激发下,教育研究的科学化无疑是近代西方教育研究的主流思潮。
与西方教育研究相比,中国教育研究的科学化起步较晚,它是伴随着对西学认识的不断深化而确立的。从1866年京师同文馆建立“天文算学馆”开始,教育领域每一项带有“科学”意味的改革,由于不可避免地牵动着传统价值观的变化,总是遭到保守势力的顽固抵抗,甚至1904年中国第一个正式实行的近代学制,也没有逾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念樊篱。直至1915年,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新文化”领袖们以哪怕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的勇气,大力引入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中国人的现代科学知识观才得以逐步形成。与之相应,中国教育家也逐渐摆脱传统的“形而上学”思维方法,在引进赫尔巴特教育理论的基础上又引进了杜威教育理论。1919年“五四”前夕,杜威来华讲学,其后实用主义与科学主义教育思想更是广为流传,注重教育的科学研究很快成为当时教育界的共识。陶行知、陈鹤琴、舒新城、廖世承、俞子夷等一大批教育家都先后投身于中国教育的科学化运动,大力提倡教育测验、教育统计、教育调查、教育实验等教育科学研究,尝试用科学方法研究教育,力图建立科学的教育学。
应该肯定,教育的科学化探索相对于中国传统以直觉思维和抽象思辨为特征的“形而上学”方法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符合人类理性精神和知识转型的客观需要。1949年11月,李建勋曾对中国教育的科学研究进行理论总结。他说:“近三十余年来,教育受自然科学之影响,对于以往之传统观念,权威意见,开始怀疑,遇有教育上之各种问题或主张,均用眼见及观察之原则(Priciple of"Look and See")处理之,以求其真实性,如形式陶冶(Formal discipline)及互补理论(Theory of Complement)之被否定,可为明证,近三十年来,教育在科学研究上之长足进步,即为以事实更换传统观念及意见,以精确测验代替粗略估计之有以致也。”[2]数量化、精确度、客观性等观念,受到了教育科学研究的特别推崇。
但必须指出,想通过观察、测验、量表、统计、调查等科学方法去研究人类动态变化的复杂教育现象,并期望达到“自然科学所用度量衡之客观而精确”的程度[2],则是十分困难的。因为科学本身就不是万能的,它只能解决事实问题,难于处理价值问题。科学的发明,并不能代替宗教、道德等人文价值存在。杜威曾敏锐地指出:“即使在数理科学里,量的观念和接近质的秩序的观念比较起来,只占第二位。无论如何,对于教师来说,活动和结果的质比任何量的因素更为重要。”[1]英国哲学家波珀(又译波普尔)进而认为:“假如没有纯思辨的有时甚至相当规模的思想信仰,科学发现是不可能的。”[3]中国近代教育家马相伯则明确指出:“凡言形下之科学愈发明,形上的真道德、真宗教愈无用者,皆呓言也、梦话也。”[4]就教育而言,它当然具有神圣的价值导向功能。在中国古代,这种教育价值导向主要表现为伦理上的“义利之辨”和人格上的“内圣外王”。近代以后,由于中西文化的激烈冲突,传统的道德价值观念固然受到了冲击,但并不等于要全盘否定传统文化;而只是对传统价值观、人生观进行必要的批判、调整与改造。一部分头脑清醒的教育家在热情讴歌和引进西方科学知识的同时,并没有忽视中国的国情民性及其深厚的民族文化精神,而是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开始了教育研究的本土化和民族性探索。
以陶行知为例,他赞赏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的反传统价值,借以对中国封建专制主义教育传统进行批判,但他并没有照搬杜威教育学说,而是根据中国国情民性和长期的教育实践,把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改造成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并把其思维术“五步法”置换成具有辩证唯物主义精神的“五路探讨”——行动、观察、看书、谈论、思考,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活教育理论,满足了中华民族解放与复兴的时代需要。又如陈鹤琴,他认同近代西方科学民主精神以及杜威教育理论的合理内核,但强调中国教育研究一定要结合国情进行再创造,称“那些具有世界性的西方先进教材和教法可以采用,但必须以不违反国情为唯一的条件。”[5]从鼓楼实验幼稚园,到上海、江西等地开展的各种形式教育实验,陈鹤琴以实际行动走出了一条新教育中国化之路,创造了与杜威生活教育理论齐名的“活教育”理论。依据庄泽宣的理解,“新教育中国化”至少必须符合四个条件:“1.合于中国的国民经济力;2.合于中国的社会状况;3.能发扬中国民族的优点;4.能改良中国人的恶根性。”[6]而要符合这些条件,则离不开专家学者的长期研究与实验。这一点,在上述陶行知、陈鹤琴的例子中得到了充分证明。他们之所以能在教育研究领域做出自己创造性的独特贡献,正是得益于其孜孜不倦的长期研究与实验。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教育研究的本土化和民族性探索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总体而言,仍然十分薄弱。据学者调查,从1917年到1948年,中国学者自编了78种教育学著作(含中国人编写的教育学教材),开始了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教育探索,但这些教育研究,“在总体上表现为模仿(西方)有余而创新不足。这种模仿是全方位的,包括教育科学的价值观、研究方式、研究内容等各方面。”[7]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全盘“苏化”,中国教育研究的本土化和民族性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合理解决,只是由模仿西方转向模仿前苏联。“改革开放”以后,这种状况有所改善。但直至20世纪90年代初,著名学者陈元晖先生仍以学术界缺乏“中国教育学”为憾事,称当代“所有已出版的《教育学》教科书,几乎一致地没有对中国的教育经验进行总结,包括古代的,近代的,现代的,当代的”;强调“把‘中国教育学,编出来,才能使‘进口教育学’变为‘出口教育学’。”[8]这个批评虽然过于严厉,但确实指出了中国教育研究的痼疾。
二、民族教育智慧的开掘与转化
百年来,中国教育研究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取得的成绩还是主要的,教育研究的科学化已习以为常,当代教育研究正呈现出多学科交叉研究态势。教育学也由单数变成复数,大一统的教育学已成昨日黄花,每一个教育学的分支学科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重要成果,这或许可以理解为当代教育研究的繁荣。但另一方面,我们确实较少见到陈元晖先生所期望的能够出口的“中国教育学”。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尚缺乏对民族教育智慧进行更有效的开掘,研究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同时,也未能将民族教育智慧更自觉地转化并融入现代教育学的理论建构之中,史论脱节仍然存在。
近代以来,许多著名教育家都对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做过深刻批判,但他们在激烈批判的同时并没有给予全盘否定,而总是坚信五千年中华民族的伟大教育智慧,坚信它是人类精神文明的一部分,需要给予理性的分析与总结。毫无疑问,这一艰巨任务不是一代人也不是某一个学科所能解决,它需要包括教育史学科在内的各类社会科学研究者来共同承担。近十年来,教育史学科与其他学科一样也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从总体上说水平仍不够高。教育史研究在不断吸收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进一步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更新研究方法及思路等方面,尚有很多工作要做。”[9]就研究方法而言,笔者认为,作为历史学与教育学交叉学科的教育史研究,应该兼取二者之长,并借鉴哲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多学科成果,对教育史问题进行全方位多维度研究,其研究的终极目的当然是指向“中国教育学”,是为了建设中国特色的教育学理论,是为了更好地培养有世界眼光的“中国现代人”,是为了给当代中国教育改革实践提供必要的历史借鉴。
教育史研究不是发思古之幽情,民族教育智慧是真实存在的,她不在遥远的过去,就在我们身旁,甚至已化作血液流淌在我们心中。关键是我们是否善于发现。意大利历史学家贝奈戴托·克罗齐说,历史与生活总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当代性“是一切历史的内在特性”。[10]凡是历史上的事物无不内在地散发出当代意义,而当代事物无一不是历史的延续以及延续基础上的再生。从这个意义上说,继承民族优秀文化,开掘民族教育智慧,并把民族教育智慧转化为有血有肉的当代教育理论建设,同样需要付出创造性的艰苦努力。也许历史并没有为我们提供现成的答案,但整理国故正是要“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11]依胡适之见,“整理国故”之后的重要工作,便是“再造文明”。开掘民族教育智慧,在很大程度上即是要对现代教育学的理论建构做出应有的回应。
1991年,陈元晖先生曾明确指出:“对中国古代的教育学理论遗产的继承,不是引用古人的片言只语为标志,应该是一种系统的总结。当我看到某一本教科书中引用了几句中国古人的名言,来证实外国某一种理论时常有喧宾夺主之感。”[8]陈先生之所以会产生“喧宾夺主”的感觉,就是因为我们缺少对本民族教育智慧的有效开掘和转化。他进一步指出:“所有已出版的《教育学》教科书,几乎一致的没有对中国的教育经验进行总结。……如《学记》上所说的‘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这12个字,但只是像蜻蜓点水一样,一忽而过,这不是‘总结’,而是一种‘点缀’。”[8]其实,除《学记》外,《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老子》、《师说》等许多传统教育宝藏都亟待我们去开采,传统教育中“有教无类”的全民观念、“智仁双修”的人格理想、“义利统一”的价值导向、“天人合一”的博大情怀、“整体辩证”的思维方式都蕴藏着无限的教育智慧,需要我们进行创造性的现代转化。[12]
为了突出教育研究的民族性,有必要对中外教育学术概念进行理性整合,将具有民族特色的学术概念吸收到“中国教育学”的理论建构中来。这一点,前人已做出了榜样,可惜未能引起后人足够的重视。以宋明理学为例,当时也受到外来佛教文化的强烈冲击,但理学家却能本之于原始儒学精神,立足宋代社会现实和教育实践,将外来佛教文化与本国儒学文化结合起来,创立了一系列具有民族特色的理学教育概念及其理论体系,实现了中国教育自先秦以来的第二次理论创新。
同理,20世纪初年,当外来西方文化强力东渐之际,国人中的有识之士也曾起而回应,对中外学术概念进行理论会通。近代教育家马相伯就十分注意对外来思想学术概念的本土化探索,以“Philosophia”为例,马相伯主张将其译为“致知”,他解释说:“《大学》朱注:‘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殆即西庠所谓Philosophia(非牢骚非阿),译言爱智学欤!……和译‘哲学’,似泛。况且致知章既亡,则礼失而求诸野,正可取西庠之说以补之。”[4]然而,马相伯这一极具本土化的译法未能被当时学术界所采纳,社会上通行的仍然是日本人借助汉语而创造的译法——哲学。又如,西文“Pedagogy”或“Education”,日本人译之为“教育”,此二字虽然源于中国古籍,却不是中国人首先这样翻译的,而是日本人“创造了汉语‘教育’的近现代用法”。[13]
毫无疑问,如何使外来文化与本国文化相融共进,如何在学术互译沟通中体现中华民族特色,无疑是转型期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的重要问题。由于译词不一,人言人殊,必然影响学术理论的正常发展。马相伯当年曾主张建立“函夏考文苑”,设想其中一个重要工作就是校订旧译,编纂新译,厘正新词,以建立中国自己的学术理论体系。但遗憾的是,马相伯在民国初年的这一伟大设想,在当时政局动荡的年代里不可能化为现实。
今天,中国文化学术和教育交流由于“全球化”浪潮而变得更为频繁,外来思想学术的本土化以及中国教育学术的民族性问题无疑变得更为突出。如何在吸收外来思想学术的同时,融入民族教育智慧?“怎样从深层次上把民族文化传统、教育遗产与当代教育思想之间断了的‘线’重新联系起来,使之有机结合?”[14]不能不说是未来“中国教育学”建设的努力方向。
三、中国教育学术的民族性和世界性
注目于民族教育智慧,并不意味着放弃教育学术的国际化追求。近代东西方文化交通以来,国人已无法抗拒外来学术文化的全方位渗透和影响,“求新知识于世界”越来越成为中国知识人士的自觉行为。诚如梁启超所说:“我青年诸君,今后不能不广求新知识于世界,非游学欧洲,殆不能占优胜也。”[15]不过,留学海外,求新知识于世界的目的无非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各项学术文化建设事业,使之能够更好地走向世界。其实,越具有民族性的东西就越具有世界性,越具有世界性的东西也就越具有民族性,二者总是辩证地交集在一起。
一方面,民族性离不开世界性,中国教育学术发展需要充分吸收世界先进教育理论,并进行本土化再创造。近代中国教育历史发展规律已经证明,凡是在教育学术上有所作为的教育家无不重视学习外来文化教育理论,潜心研究并努力汲取其中的合理成分,那种深藏“夷夏之辨”的华夏中心主义早已随着闭关政治的终结而终结。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和教育经验,已成为当代中国教育创新的一个理论基点。当然,再先进的外来文化教育理论都不可能直接拿来套用,而需要结合中国的社会历史背景、现实文化条件、民众接受能力等因素,进行实践再探讨和理论再创造。
另一方面,世界性也离不开民族性,世界教育理论的繁荣也需要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教育学术的积极参与,使之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从这个意义上说,建立有民族特色的“中国教育学”无疑显得十分迫切。马相伯曾语重心长地说:“一国有一国的文化精神,一国有一国的语言文字。尤其是我国自有数千年的历史,当自家知道爱护它!……如果一律要数典忘祖,老夫认为很可痛哭!”[4]在他看来,伴随着军事经济上的侵略,西方列强必然继之以文化精神上的控制和奴化。他敏锐指出:“今之欧人,皆欲以文化化吾,甚欲以彼文彼语,以化吾文吾语。”[4]在当代,某些西方国家正挟其军事经济实力,大肆宣扬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殖民主义之际,重温马老的教诲,不能不令我们肃然起敬。诚然,我们不能无原则地歌颂传统,也不能随便拿未经研究的“古董”参与世界,而应该对民族文化教育传统展开深层次的研究,真正做到融会贯通、“古为今用”;同时,我们也不能将刚刚从人家那里学来的东西,未经完全消化又简单地还给人家,而是要把既具有世界新知又不乏民族智慧的全新的“中国教育学”贡献于世界。
作为学科意义上的教育学研究,西方固然要领先于中国。但博大精深的中国教育文化传统确实为我们留下了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亟待我们在实践的基础上结合世界先进教育理论进行有效开掘,并给予创造性转化。令人鼓舞的是,已有学者注意到要“从传统教育理论中继承和改造一些有生命力的教育话语”。[16]更有学者期待以“研究的方式”介入到当代中国教育改革的“伟大的历史实践中去”。[17]相信通过学界同仁们的共同努力,建立可以出口的“中国教育学”的崇高学术理想一定能够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