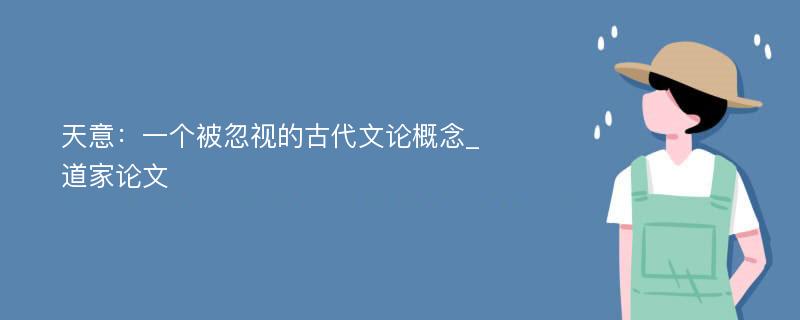
天机:一个被忽视的古文论概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论论文,天机论文,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徐中玉先生撰写的“灵感”条在解释西方灵感论之后说:“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著作中经常提到的‘天机’、‘兴会’、‘神来’、‘顿悟’等,指的也是类似的思维现象。”(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434页。)在他列举的四个概念中,“兴会”、“神来”因与盛唐诗的紧密关连而受到研究者垂青;“顿悟”因与严羽“妙悟”说相近而不断有人论及;唯有“天机”一说,迄今尚未见全面论及者。这似乎表明,研究者尚未把它视为一个古代文论的概念。本文拟就其原委略作陈说。
一
在《庄子》一书中,反复出现的“天”字代表崇尚自然、反对人为的思想,“天机”与“天籁”、“天倪”、“天钧”、“天府”、“寥天一”等词语一样,是这种思想的具体表现。由《秋水》篇所讲述的一个寓言,可以推知“天机”的含义:
夔谓蚿曰:“吾以一足趻踔而行,予无如矣。今子之使万足,独奈何?”蚿曰:“不然。子不见夫唾者乎?喷则大者如珠,小者如雾,杂而下者不可胜数也。今予动吾天机,而不知其所以然。”蚿谓蛇曰:“吾以众足行,而不及子之无足,何也?”蛇曰:“夫天机之所动,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注: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国书店影印扫叶山房本,卷六。)
在这个寓言里,庄子以蚿、蛇为代言者,强调自然生命所本有的、非人力所能认识与控制的神妙难言的机能。西晋郭象注这段文字,发挥庄子之意,将其与“逍遥”之旨联系起来,说:
物之生也非知生而生也,则生之行也岂知行而行哉!故足不知所以行,目不知所以见,心不知所以知,俛然而自得矣。迟速之节,聪明之鉴,或能或否,皆非我也。而惑者欲有其身,而矜其能,所以逆其天机,而伤其神器也。至人知天机之不可易也,故捐聪明,弃知虑,魄然忘其所为,而任其自动,故万物无动而不逍遥也。(注: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国书店影印扫叶山房本,卷六。)
“有其身”是以身为己之所有,也就是自以为是,以心智活动违背自然之道。郭象认为生命源于自然,故应一切顺应自然,否则就“逆其天机,而伤其神器”。所谓“神器”,亦即“天机”,郭象把它理解为自然之神在生命体内设置的一个机关(器)。唐人成玄英则直接把“天机”解释为“天然机关”,并指出其运行与心智活动无关,说:
今蚿之众足,乃是天然机关运动而行,未知所以,无心自张。(注: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国书店影印扫叶山房本,卷六。)
所谓“无心”,便是完全摆脱心智活动的干预,全任其自然而然地运行。
按照我们的认识,任何行为皆由思维决定,主张任“天机”之自动,反对主张意念,就是崇尚自然而然的思维活动,或者说,是反对知性,崇尚直觉思维。
庄子哲学以“心斋”、“坐忘”为指归,主张把心灵引入“虚”、“无”之境,使之与冥冥之中的天道合一。《人间世》中说:“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答。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所谓“听”是比喻,喻指如何认识世间万物。“听之以心”是以有见之心审视万物,“听之以耳”是用感觉官能观照万物,均不能摆脱主观心智之干预、影响和约束,把一个凸现出来的“我”横亘于认识的视野中,未能与自然大道合一。“听之以气”则是以虚空之心接受世间万物,在认识的视界里无我无物,故能与万物冥会,与天道合一。由此可见,庄子所宣扬的是一种听凭直觉、反对知性的思维方式。天机自动,正是这种思维方式的形象体现。
在庄子看来,心智活动与人的社会生活相关联,只有完全超越社会活动,“归精神乎无始,而甘冥乎无何有之乡”,才能杜绝思虑,纯任天机。因而,那些靠着自己的聪明才智日夜奔波于名利场上的人就与“天机”无缘了。《大宗师》篇说:
其耆(嗜)欲深者,其天机浅。
在这里,嗜欲深和天机深是截然相反的人性品格,天机深者为真人、至人,嗜欲深者为凡人、俗人。
《大宗师》篇曾描述庄子理想中的至人说:“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就是率性而行,没有执著,没有心灵的挂碍,来去自由,“相与交食乎地,而交乐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撄,不相与为怪,不相与为谋,不相与为事,翛然而往,侗然而来。”(注: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国书店影印扫叶山房本,卷八《庚桑楚》。)这种理想人格于追名逐利者是不相容的,因而庄子把惠施相梁比为枭嗜腐鼠,把曹商使秦得车百乘比为舐痔之所为,而他自己则甘心于“困窘织屦,槁项黄馘”,过贫穷困顿却富于心灵自由的生活。由此可见,“天机”说还体现了庄子反对世俗欲望,主张放任自然、复归本真的人生态度。
“总之,“天机”说具体表现了《庄子》所宣扬的思维方式和人生态度。道家其他经典也有言及“天机”者,所表露出来的思想与《庄子》无异。如《淮南子·原道训》认为,圣人处于穷乡僻壤,“蓬户瓮牖”,但能“不为愁悴怨怼,而不失其所以自乐也”,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在于:
则内有以通于天机,而不以贵贱、贫富、劳役失其志德者也。(注:《淮南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卷一。)
所谓“圣人”,相当于庄子所说的“真人”,“内通于天机”,指与天道冥合,任自然、无嗜欲、无挂碍的人格精神。另《列子·说符》篇借伯乐之口论九方皋相马,说:
若皋之所见,天机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视其所视,而遗其所不视。(注:杨伯峻:《列子集解》,中华书局1979年版,卷八。)
晋人张湛注:“天机,形骨之表所以使蹄足者。”这与郭象所谓“神器”、成玄英所谓“天然机关”意思相同;张湛又说:“得之于心,不显其见。”这则与郭象所谓“捐聪明、弃智虑”,成玄英所谓“无心自张”意思相同。观“天机”,相当于庄子说的“听之以气”的思维活动,九方皋相马是在认识事物的思维活动中纯任直觉,不介入任何知性见解,故不区别其牝牡玄黄。
二
最早将道家的“天机”说引入文论的,是陆机的《文赋》。陆机描述创作中经常出现的一种微妙现象,说:
若夫感应之会,通塞之际,来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灭,行犹响起。方天机之骏利,夫何纷而不理。思风发于胸臆,言泉流与唇齿。纷葳蕤以馺遝,唯豪素之所拟。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及其六情底滞,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揽营魂以探颐,顿精爽以自求。理翳翳而愈伏,思乙乙其若抽。是以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虽兹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勠。故时抚空怀而自惋,而未识夫开塞之所由。(注:陆机:《陆机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卷一。)
他认识到创作中有时文思流利,有时思维滞涩,文思流利时写出的文章神采飞扬,音节浏亮,思维滞涩时则欲求其一字而不得。他认识到,在创作中有一种非主观意愿所能控制的力量,就像《庄子》里说的蚿、蛇之能够行走一样,似乎被一种神秘而玄妙的机关控制着。于是,他将“天机”一词引入了进来。天机到来是可以感知的,故说“在我”;但如何开之启之,则不由自己,所以又说“非余力之所勠”。
人们一般把陆机此处说的“感应之会”(按:《文选》本作“应感之会”)与“天机骏利”均解释为文学创作中的灵感现象,这当然是不错的。但需要指出,正如上文引徐中玉先生所言中国古代文论中的灵感论表现为几个不尽相同的范畴,几个范畴所指各有侧重,且源于不同的思想系统:“兴会”说强调勃发于中的情绪体验,“神来”说强调妙手偶得,二者分别与儒家、道家思想有一定渊源,“顿悟”说更强调认识活动中的感悟,源于禅宗学说。由陆机引入的“天机”说,虽属于中国文艺学灵感论之系统,但并不能含盖整个灵感论。我认为,不宜直接把陆机说的“天机”诠释为“灵感”,不如将其解释为“敏妙通灵的艺术思维”。
陆机之后,“天机”便成了人们论文谈艺的一个习语。如沈约《答陆厥书》说:以“《洛神》比陈思他赋,有似异手之作,故知天机启则律吕自调,六情滞则音律顿舛也。”(注:萧子显:《南齐书》,中华书局排印本,卷五十二《文学传·陆厥传》。)基本沿袭陆机之意。之后,随着创作经验积累和认识的逐步深化,人们看到,“天机”可以在中情酣畅时驳发,可以靠心物相触感发,也可以靠调养神气获致。
所谓中情酣畅,是以饱满的激情投入创作,不苦思、不雕琢,任想象飞翔,任语言流淌。李白在《秋夜于安府送孟赞府兄还都序》中盛赞对方说:
……虽长不过七尺,而心雄万夫,至于酒情中酣,天机俊发,则谈笑满席,风云动天。(注:李白:《李太白文集》,四库全书本,卷二十六。)
这虽不是写创作时的状态,却与李白本人激情饱满、酣畅自足的创作状态相通。李白诗歌的特点,是乘兴而起、发想无端、转折无痕,黄庭坚称之曰:“余评李白诗如黄帝张乐于洞庭之野,无首无尾,不主故常,非墨工椠人所可拟议。”(注:黄庭坚:《山谷题跋》,丛书集成初编本,卷二《题李白诗草后》。)此评化用《庄子·天运》篇的典故,显然是将李白之诗比喻为“天机不张而五官皆备”的“天乐”。以“天机俊发”称李白的诗歌创作,是十分恰当的。书法创作也有类似的状态,如窦冀赞怀素书云:
狂僧挥翰狂且逸,独任天机摧格律。龙虎惭因点画生,雷霆却避锋芒疾。鱼笺绢素岂不贵,只嫌局促儿童戏。粉壁长廊数十间,兴来小豁胸襟气。长幼集,贤豪至,枕糟藉麴犹半醉。忽然绝叫三五声,满璧纵横千万字。(注:《全唐诗》,上海古籍出版社缩影印扬州书局本,第483页《怀素上人草书歌》。)
兴到之时,以酣畅饱满的激情纵横挥洒,是为“独任天机摧格律”。画家也有类此者,符载《江陵陆侍御宅燕集观张员外画松石序》记张璪作画时的状态:
员外居中,箕坐鼓气,神机始发。其骇人也,若流电激空,惊飙戾天,摧挫斡掣,撝豁瞥列,离合惝恍,忽生怪状。(注:姚铉:《唐文粹》,四库全书本,卷九十七。)
“神机”即“天机”,张璪作画“箕坐鼓气”而天机发动,也是激情饱满、酣畅淋漓的。
谈及中情酣畅,就涉及到了兴会、酒与天机的关系。先说兴会。简单地说,“兴会”就是审美情绪的发动,审美情绪由发动而入于酣畅,往往产生灵妙之作,“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注:《全唐诗》,上海古籍出版社缩影印扬州书局本,第391页李白《江上吟》。),与“天机俊发”是一致的。再说酒。艺术家与酒有不解之缘,“李白斗酒诗百篇”、“张旭三杯草圣传”(注:《全唐诗》,上海古籍出版社缩影印扬州书局本,第511页杜甫《饮中八仙歌》。),陶潜、苏轼等任自然的诗人也多好酒。酒与创作的一个重要的关系,即在于能够引发“天机”。刘熙载论诗文之别时也说:“醉中语亦有醒时道不到者,盖天机之发,不可思议也。”(注:刘熙载:《艺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诗概》。)
所谓心物相触,是在无意于创作之时,诗人主体情性与对象客体偶然默契,不劳拟议而自然触发。署名司空图的《诗品·实境》说:“取语甚直,计思匪深。忽逢幽人,如见道心。清涧之曲,碧松之阴,一客荷樵,一客听琴。情性所至,妙不自寻。遇之自天,泠然希音。”(注:孙联奎、杨廷芝:《司空图〈诗品〉解说二种》,齐鲁书社1980年版,第113页。)妙不自寻而遇之自天,说的正是心物相触而启动了灵妙思维,杨廷芝在此品目下即批注曰:“此以天机为实境也”。苏洵在一篇文章中以风与水相遭为比喻说:“然此二物者,岂有求乎文哉!无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物之相使,而文出于其间,是天下之至文也。”(注:苏洵:《嘉祐集》,四库全书本,卷十五《仲兄字文甫说》。)此论受道家自然思想之启发,并影响到了苏轼的自然天机说。苏轼在《南行前集叙》中说:“己亥之岁,侍行适楚,舟中无事,博奕饮酒,非所以为闺门之欢。山川之秀美,风俗之朴陋,贤人君子之遗迹,与凡耳目之所接者,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注:苏轼:《苏东坡全集》,中国书店影印世界书局1936年本,前集卷二十四。)外境与心灵的触发,相当于苏洵所说的风水相遭。其文出于自然,非人力之所强,所以,苏轼又说自己的文章“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注:苏轼:《东坡题跋》,丛书集成初编本,卷一《自评文》。)以自然而然、不可知论创作,显然受了道家“天机”说之影响。与苏轼一脉相承,袁宏道《行素园存稿引》论创作说:
博学而详说,吾已大其蓄矣,然犹未能会诸心也。久而胸中涣然,若有所释焉,如醉之忽醒,而涨水之思决也。虽然,试诸手,尤若掣也。一变而去辞,再变而去理,三变而吾为文之意忽尽,如水之极于淡,而芭蕉之极于空,机境偶触,文忽生焉。风高响作,月动影随,天下翕然而文之,而古之人不自以为文也,曰是质之至焉者矣。(注:钱伯城:《袁宏道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卷五十四。)
所谓“机境偶触”,就是内在的“天机”与外在的物境相触,翕然引发自然之妙文。
由饱满的激情引发的“天机”不假外求而酣畅自足,创作出的作品也鼓荡着饱满的激情,如李白之诗,张旭、怀素之书,皆是生命颠峰状态的宣泄,弥漫着振奋开张、奇幻浪漫的精神。由心物相触引发的“天机”,因强调心境平和而减少了充溢于中的酣畅之情,但由于心物相融而对物理、事理有更为深刻的把握,用丰富的形象表现出天人相合的情味,并未降格为知性思维。两者代表了不同的创作心态、思维机制和文化审美取向,但都没有给规矩、法式或格调留下馀地,因而,都表现了道家尚自然的思想对文艺创作论的深刻影响。
人们还认识到,“天机”可以靠调和神气而获致。陆机将“天机之骏利”和“六情之底滞”相对,“六情”指喜、怒、哀、乐、好、恶,“六情底滞”就是感情处于不活跃的状态,实际也就是精神状态不佳,这说明他已经模糊地认识到“天机”到来与人的精神状态有关。但在“天机”面前,他毕竟束手无策,“未识夫开塞之所由”,只好投笔作罢。后来刘勰著《文心雕龙》,设《养气》一篇专论调养,主张“清和其心,调畅其气,烦而即舍,勿使壅滞”,对后世的涵养天机说有启发作用。李渔《闲情偶寄》论戏曲创作说:
有养机使动之法在。如入手艰涩,始置勿填,以避烦苦之势。自寻乐境,养动生机,俟襟怀略展之后,仍复拈毫,有兴即填,否则又置。如是者数四,未有不忽撞天机者。(注:李渔:《李渔全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闲情偶寄·词曲部》。)
李渔已认识到,“天机”之到来是可以靠调养精神寻求的。沈宗骞论画也说:
或难之曰:“机神之妙既尽出子天而非人为之所得几固已,今者吾欲为之心,独非属人乎?”曰:“盖有道焉,所谓天者人之天也,人能不去乎天,则天亦岂常去乎人?当夫运思落笔,时觉心手间有勃勃欲发之势,便是机神初到之候,更能迎机而导,愈引而愈长,心花怒放,笔态横生,出我腕下,恍若天工,触我毫端,无非妙绪。”(注:俞剑华:《中国画论类编》,人民美术出版社1986年版,第六编山水下《芥舟学画编》卷一《取势》。)
他也认识到,天机之到来是可以把握的,如及时抓住,把直觉思维引入巅峰状态,就会进入创作的自由境界。在这里,作为敏妙艺术思维的“天机”已不再像道家哲学里所讲的“天机”那样玄妙难测,而是可以凭着自己的感觉把握、凭着调整自己的精神状态获致的了。而强调“心怀怡悦,神气冲融”,强调“人能不去乎天”,仍体现了道家致虚守静思想的深刻影响。从陆机、沈约到李渔、沈宗骞,人们对文艺创作中“天机”——敏妙通灵的艺术思维——的认识和把握逐步深化了。
以上所论,是古代文艺学天机说的第一层含义。它虽不能含盖整个中国古代文艺学的灵感论,却以创作灵感为追求。因为天机说本是道家哲学用语,被文艺学借用又体现了道家思想的深刻影响,故可以称之为源于道家的灵感论。
三
古代诗人画家运用“天机”一语,还有一项不能为灵感论所统摄的含义,如王维《山中与裴迪秀才书》写道:
当待春中,草木蔓发,春山可望,青鯈出水,白鸥矫翼,露湿青皋,麦陇朝雊,斯之不远,倘能从我游乎?非子天机清妙者,岂能以此不急之务相邀。然是中有深趣矣!(注: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四库全书本,卷十八。)
此处诗人所说的“天机清妙”,是取义于道家天机说所蕴涵的崇尚自然的人生态度,是指摆脱世俗功利羁绊的超凡脱俗人格与人生境界。当然,艺术家要求生活中有必要的物质条件,要求必要的亲情慰藉,在此基础之上,才能优游自适,在审美观照中获得心灵的怡悦。以审美观照和心灵愉悦为目的,和主张与道冥一的先秦道家是有差别的,与其称之为自然人格,毋宁称之为“艺术人格”更为确切。王维用“天机清妙”以称裴迪,实亦自我精神之写照。另如皇甫冉《杂言月洲歌送赵冽还襄阳》写道:
家住洲头定近远,朝泛轻桡暮当返。不能随尔卧芳洲,自念天机一何浅。(注:《全唐诗》,上海古籍出版社缩影印扬州书局本,第629页。)
自念“天机”之浅,是因为不能甘心于淡泊名利之境,不能怡然于自然山水之乐。所言“天机”,与王维所言者意同,指淡泊名利而亲近自然的艺术人格。
宋初的黄休复认识到,这种艺术人格对文艺创作具有积极意义,他在《益州名画录》中说:
大凡画艺,应物象形,其天机迥高,思与神合,创意立体,妙合化权,非谓开橱已走,拔壁而飞,故目之曰神格耳。(注:黄休复:《益州名画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品目》。)
所谓“思与神合”,是指艺术家能够妙观万物,使自己的创作构思与自然万物之神理相合,要做到这一点,条件是“天机迥高”,“天机”可以理解为天赋,联系其本意来看,应理解为超凡脱俗的艺术人格,相当于王维说的“天机清妙”。苏轼说得更明白:
或曰:龙眠居士作《山庄图》,使后来入山者,信足而行,自得道路,如见所梦,如悟前世,见山中泉石草木,不问而知其名,遇山中渔樵隐逸,不名而识其人。此岂强记不忘者乎?曰:非也。……天机之所合,不强记而自记也。居士之在山也,不留于一物,故其神与万物交,其智与百工通。(注:苏轼:《东坡题跋》,丛书集成初编本,卷五《书李伯时山庄图后》。)
“不留于一物”,就是心中无世俗之念,无所执著,无所挂碍,只有这样,才能以其心神与自然万物相融会,是为“天机之所合”,也就是艺术人格与自然万物之间达成默契。
强调倾心于审美愉悦的超凡脱俗的艺术人格,是古代文艺学天机说的第二层含义。这层含义是不能被灵感论所统摄的。但是,并不能说这层含义与灵感论无关。在许多古人看来,敏妙通灵的艺术思维闪现,使艺术家在一闪念间迅速创作出机趣无限的佳作(天机自动),与艺术家超凡脱俗的艺术人格(天机清妙)是有着内在联系的。这种联系就是,艺术家必须摆脱世俗之念的羁绊才能发动创作中的灵妙思维。换言之,只有天机清妙,才能天机自动。北宋末年张怀在《山水纯全集后序》中说:
造乎理者能画物之妙,昧乎理则失物之真。何哉?盖天性之机也。性者,天所赋之体;机者,人神之用。机之发,万变生焉,惟画造其理者,能因性之自然,究物之微妙,心会神融,默契动静,于一毫投乎万象,则形质动荡,气韵飘然矣。故昧于理者,心为绪使,性为物迁,汩于尘坌,扰于利役,徒为笔墨之所使耳,安足以语天地之真哉!是以山水之妙多专于才艺隐遁之流,名卿高蹈之士……岂庸鲁贱隶、贪懦鄙夫,至于粗俗者之所为也?(注:俞剑华:《中国画论类编》,人民美术出版社1986年版,第六编山水下韩拙《山水纯全集》卷尾附。)
所谓“天性之机”就是前面说的天机,“造于理”者“因性之自然”,是天机清妙,天机清妙才能“究物之微妙”,依自然万物的本来面目(神理)认识观照之,心与神会,动合神理,挥洒万变而入于自然,启动敏妙通灵的艺术思维,作到天机自动。这实际就是认为,只有以直觉思维观物写生,才能出神入化;而只有品格高逸之人,才能排除知见,纯任直觉思维。这种认识在古代是有代表性的,上引沈宗骞《芥舟学画编·取势》还谈到:
机神所到,无事迟回顾虑,以其出于天也。其不可遏也,如弩剑之离弦;其不可测也,如震雷之出地。前乎此者杳不知其所自起,后乎此者杳不知其所由终。不前不后,恰值其时,兴与机会,则可遇而不可求之杰作成焉。……惟天怀浩落者,值此妙候恒多。……夫非天资高朗,淘汰功深者,不能不迟回顾虑,于是,毕其生无天机偶触之时……始因不能速以至不得势,继且因不得势而愈不能速。囿于法中,动辄为规矩所缚,拘于象内,触处为形似所牵。(注:俞剑华:《中国画论类编》,人民美术出版社1986年版,第六编山水下。)
“天怀浩落”和“天资高朗”,说的就是摆脱了世俗牵掣的艺术人格,如无此种人格为底蕴,必然被矩矱所束缚,迟回顾虑,不能在创作冲动到来时开启敏妙通灵的艺术思维。
由此看来,古代文艺学天机说的第二层含义,即强调摆脱世俗羁绊的超凡脱俗的艺术人格,并不独立于灵感论之外,而是与灵感论紧密相关的。由于这层含义的存在,源于道家的灵感论具备了不同于“兴会”、“神来”、“顿悟”诸说的独特之点:它把灵感论由单纯的思维论升华为人生哲学和人生态度。与强调灵感思维的突发性和短暂性的西方文论相比,这一意义上的天机说强调了灵感思维的必然性,拓宽了追索灵感的维度,体现了以天人合一、自然为追求的道家思想对古代文艺学更深一层的影响。
晋人司马彪把庄子说的“天机”解释为“自然”,更能从理论的角度切近庄子本意。道家崇尚的“自然”本有两重含义,一层含义是“自然而然”,既不以人力干预外物,也不以理性节制自我,漫然所之,率性而行。另一层含义是“回归自然”,即去伪存真,超尘脱俗。“自然而然”是“率”,“回归自然”是“真”。率与真又是二而一的:唯真者能率,唯率才能体现真,故道家常言“率真”。庄子“天机”一语,正蕴涵着道家任自然思想的两重含义:“今予动吾天机”,强调的是“率”;“其嗜欲深者其天机浅”,强调的是“真”。被文艺学借用后的“天机”指敏妙通灵的艺术思维,更多继承了“自然而然”的含义,而且由一种源于生命的自然本能,变成了突发性的、短暂的、来去无踪的思维活跃状态,只有在中情酣畅、心物相触或调养神气之后才能偶然“撞”见,对于那些醉心于道家思想的人而言,这是难以接受的,于是他们强调艺术人格对启动天机的作用,一方面补足了文艺学天机说复归自然的义项,另一方面又揭去了它来去无踪、难于把握的神秘面纱。这样一来,道家的天机说和文艺学的天机说便具有了一脉相传的关系:敏妙通灵的艺术思维强调的是“率”,超凡脱俗的艺术人格强调的是“真”,唯超凡脱俗者能启动敏妙通灵的艺术思维,从容率意,不被法度所拘束,唯启动敏妙通灵的艺术思维者才能天马行空,超越凡俗而入于自由之真境。
四
道家任自然的思想对古代文艺学的影响又不是单线而下的,而是较为复杂。其中固然有像苏轼一样在行文用笔方面追求自然而然、在审美趣味方面追求潇洒冲淡的,但更多则是从文艺自身的角度认识到灵感现象的存在,借用道家天机说来表达“自然而然”之义,但在审美趣味方面并不受道家影响,如上文所举的陆机喜用华辞丽藻,就是有悖于朴素自然之文风的。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人在文艺论著中谈到“天机”,不仅表现了道家旧思想的影响,而且还表现了其他思想的影响。换言之,道家思想是和其他思想搅在一起影响到这些人的文艺思想的。如包恢《答曾子华论诗书》说:
盖古人于诗不苟作,不多作,而或一诗之出,必极天下之至精。状理则理趣浑然,状事则事情昭然,状物则物态宛然,有穷智极力之所不能到者,犹造化自然之声也。盖天机自动,天籁自鸣,鼓以雷霆,豫顺以动,发自中节,声自成文,此诗之至也。(注:包恢:《敝帚稿略》,四库全书本,卷二。)
“发自中节”,是理学对感情的要求,“天机自动、天籁自鸣”是道家的任自然主张,二者被统一在一起了。另如徐渭《奉师季先生书》论乐府兴体起句时说:
乐府盖取民俗之谣,正与古国风一类。今之南北东西虽殊方,而妇女儿童、耕夫舟子、塞曲征吟、市歌巷引,若所谓《竹枝词》,无不皆然。此真天机自动,触物发声,以启其下段欲写之情,默会亦自有妙处,决不可以意义说者。(注:徐渭:《徐渭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卷十六。)
这里与天机说所表现的任自然思想相统一的,则是这位晚明思潮先驱的市民情调。他们所谓“天机自动”,主要是指自然而然,或说创作中的敏妙通灵的艺术思维,在情感基调、审美趣味方面并无道家倾向。应该说,在这一意义上的天机说与西方的灵感论更具可比性。
借用道家“天机”说的还有一些重苦思、重格调的文论家。他们所谓“天机”的含义,虽然还有受道家思想启发的一面,但在总的思想倾向上已发生了变化。皎然《诗式》卷五有云:“夫诗人造极之旨,必在神诣,得之者妙无二门,失之者邈若千里。”将诗歌创作归结为妙无二门的“神诣”,看似受庄禅思想之影响。他又说:“后辈若乏天机,强效复古,反令思扰神沮。”与道家思想也还是一致的。但接下去却说:“何则?夫不工剑术,而欲弹抚干将、大(太)阿之铗,必有伤手之患。”(注:皎然:《诗式》,丛书集成初编本,卷五“复古通变体”。)这里强调的是“术”,即靠后天学习所掌握的技能,这就与道家任自然的思想背离了。该书开卷表明其写作意图说:
洎西汉以来,文体四变,将恐风雅寝泯,辄欲商较以正其源,今从两汉己(以)降,至于我唐,名篇丽句,凡若干人,命曰《诗式》,使无天机者坐致天机,若君子见之,庶有益于诗教矣。(注:皎然:《诗式》,丛书集成初编本,卷一“总序”。)
他认为“天机”是可以靠学习获得的,他选择的名篇丽句,就是为后学者提供法式,让他们用来获取“天机”的。这样,源于道家的“天机”说,就失去了崇尚自然的双重本义。明代论诗开复古派先声的李东阳在《怀麓堂诗话》中提到,他曾觉得诗有五声之分,但不敢确认,后来听到先辈类似的话,始敢信其有,于是不厌其烦地宣扬其说,其门人有闻之者,便告诫他“莫太泄漏天机”。所谓“泄露天机”,就是把他所悟到的诗歌创作规律表达出来,让别人轻易地领会到真谛,而所谓“天机”,也就是靠后天学习、领悟所能掌握的诗歌创作规律,与法度、格调有密切关系。后来谢榛在《四溟诗话》中也提到,他与朋友谈诗法心得,李攀龙在场,诫之曰:“子何太泄天机!”也是同样的意思。至此,“天机”已变成重格调者所认识到的艺术规律或秘密心得了。这是文艺学天机说的第三层含义。
这一意义上的天机说虽背离了道家崇尚自然的旨趣。但在强调认识或心得的神秘性这一点上,还可以看到与道家思想的一点渊源。个人领悟到的艺术规律或秘密心得,不在灵感论的范围之内。但在功夫和积累的基础上有所感悟,显然是自以为跨入或瞻望到了创作自由境界的神秘之门,与灵感论还是有一定关系,不妨视为古人追索创作灵感的另一维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