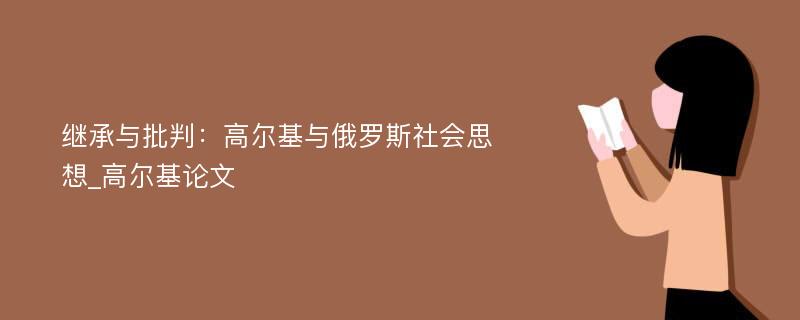
继承与批判:高尔基与俄罗斯社会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尔基论文,俄罗斯论文,思想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俄罗斯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及文学评论家瓦·罗赞诺夫说过,对于西方人来说俄罗斯文学开辟了道德世界观的新纪元,西方读者为俄国作家所倾倒,但其崇尚的绝不是俄罗斯作家创作的高超艺术性,而是其中展示的崭新而又独特的道德世界观,这种道德观通过作品中俄国生活的丰富画面和俄国人特别的性格特点表现出来。(注:瓦·罗赞诺夫:《围绕俄罗斯思想》,载《罗赞诺夫文集》,莫斯科1990年版,第317 页。)同样作为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的尼·别尔嘉耶夫也指出,(注:尼·别尔嘉耶夫:《俄罗斯精神》,莫斯科1990年版。)俄罗斯文学并非因充溢着创作喜悦才产生,而是由于个人和人民的苦难及痛苦的命运、由于探索全人类得救的真理才产生的,因此恰恰是俄国的作家极其尖锐地提出了关于人类创作和文化意义的问题,并对文化存在的意义表示怀疑,与不可避免地对生活本身进行改造、不可避免地在生活中实现真理相比,俄罗斯的作家们强烈地感受到艺术创作的悲剧意味。在这一点上体现了俄国人灵魂中强烈的禁欲成分以及探索解脱、期待另一种更高尚生活的渴望,此即俄罗斯文学的道德性往往高于其艺术性的根源所在。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高尔基表露了同样的艺术道德价值观念。在回答作家费定提出的“如何写作”这个问题时,高尔基说,人的可贵之处在于其对生活的意志力,在于其顽固地要超越自我,挣脱锁链,摆脱由理智设下的狡猾阴谋,这理智似乎在追求完全的和谐,而实际上却是在给人营造安静的兽笼。他认为,艺术家的责任就是表现这样的人,并且天才的作家往往是不大好的修辞家(1920年12月20日。本文所列举的信件皆出自《高尔基与苏联作家通信集》莫斯科1964年版,以下只在括弧中注明信件日期)。由此可以看出,与其他多数的俄罗斯文学艺术家一样,对于高尔基来说,文学创作过程中道德标准高于艺术标准。
俄国学者符拉德金娜在《20世纪俄罗斯文学是一个统一的美学体系》一文中对20世纪俄罗斯文学作了全面而又系统的阐述。(注:柳·弗拉德金娜:《20世纪俄罗斯文学是统一的美学体系》,载俄罗斯《文学问题》杂志1993年第2期。)她指出, 与俄罗斯古典文学传统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是构成该体系的主要因素之一,这其中包括对传统的遵循、对传统的重新思考、与传统的论争及至对传统的否定。从总的文学进程来说,俄罗斯古典文学的独特传统意识在于把对道德核心的有目的的探索看成是人类存在的基础,看成是与之相关的对作家崇高使命的认识,作家的崇高使命即在于他必然承担的社会使命,艺术必须为社会目的服务。把20世纪俄罗斯文学确定为一个统一的美学体系,其主要的统一点是对那些俄罗斯文学曾关注并且目前仍旧关注的俄罗斯文化生活中诸多特有问题的反映和描述,这些问题包括:一、人民与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二、俄罗斯国家发展道路问题;三、“小人物”及其与之对立的国家的关系问题;四、俄国乡村问题。
在研读高尔基的过程当中,我们确认,上述每一个问题都或轻或重、无一例外地贯穿于他的艺术创作与评论之中,故此不妨照此模式对高尔基的美学思想体系进行分析和评判。
一、人民与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
在对俄罗斯文化进行深入思考之后,别尔嘉耶夫指出,“革命前的俄罗斯似乎形成了两个种族,那个时代的俄罗斯人生活在不同的层次之中,甚至是生活在不同的时代”,而这“一种文化之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文化”是世纪之交俄罗斯文化的矛盾所在,是俄罗斯文化艰难命运的原因所在。(注:尼·别尔嘉耶夫:《自我认识》,莫斯科1990年版,第138—141页。)无疑,作为对俄罗斯文化命运极其关注的人,高尔基不会反对别尔嘉耶夫的论断,因为他同样深切地感到,“知识分子在精神上与人民的生活环境隔绝这样一种不安感始终在不同程度上固执地纠缠着我,——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生活的创造力像在我们——俄罗斯这样遥遥相隔。”(《守夜人》)在高尔基看来,“那些优秀的、聪明的知识分子的生活似乎太平淡了,他们好像置身于半理性的、愚昧的无谓忙碌之外”(《守夜人》),因而自以为是“平民中的精华”(萨姆金语)的知识分子其实并没有承担起教育民众、使民众摆脱无知和愚昧状态的任务,他们只会夸夸其谈,说一些尽管“富有见地、发自肺腑”但却对生活来说“毫无裨益”的话(《旧事》)。如果事实如此,那么知识分子自诩的崇高使命究竟是什么?如何体现?或许,正是由于“知识分子”这种无意义的存在,高尔基才痛感其《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是为俄国知识分子唱出的一首挽歌(1927年10月2日致格拉特科夫)。
在进一步阐述高尔基对人民与知识分子关系问题所作的评论和认识之前,我们首先对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概念及其内涵和外延作一个确定和解释。
别尔嘉耶夫对俄罗斯“知识分子”有其充分的了解和深刻的研究。他认为,(注:尼·别尔嘉耶夫:《俄罗斯精神》,《俄罗斯共产主义的起源及其意义》,莫斯科1990年版。)俄罗斯的“知识分子”是一种俄罗斯文化背景下的独特现象,其概念绝不等同于西方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它所指的并不单单是从事脑力劳动、脑力创作的人,如学者、作家、艺术家、教授等。在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形成是与西方不一样的,属于“知识分子”之列的完全可能是不从事脑力劳动的人,而与之相反,不少俄国学者和作家不能算作这种特殊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俄罗斯“知识分子”更象是僧团或是宗教派别,有其特别的极其偏执、不容异己的道德规范,有其独特的世界观、特别的风尚和习俗,甚而有其独特的、与众不同的面孔,依据以上种种特点很容易就能够把他们与其它社会团体区别开来。“知识分子”在俄罗斯是思想意义上的而非职业意义上的划分。它由各种阶级成分组成,首先主要是贵族中最有修养的一部分人,其次是一些牧师和祭司的子女,其中还有小官吏和城市居民,1861年解放农奴之后从农民中产生了一部分。他们被各种思想——尤其是社会思想——联合起来,并且毫无例外地把一切思想意识活动都变成社会政治活动,包括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西方思想在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心灵中首先被折射成怜悯心和爱人思想,而出于怜悯和爱,他们只看到现实中存在的种种不公正现象和阴暗面,并且在这样的现实中找不到自己的精神家园;他们生活在与周围现实的分裂之中,认为自己是“我们”,国家和政权是“他们”,在这种现实中养成一种富于幻想的,分裂教派式的道德习惯。“知识分子”表现出典型的俄罗斯民族性,他们被陀思妥耶夫斯基称作“俄罗斯大地上伟大的流浪者”。他们是永远的流浪者,在俄罗斯大地漫游流浪,在各种思想中徘徊探索,寻找精神家园,寻找真理和正义,寻找未来之城。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高尔基诸多作品中的主人公就表现为这种意义的“知识分子”,他们如三部曲中的阿列克塞、《忏悔》中的马特维,《在人间》、在《我的大学》中飘泊流浪、探索学习、寻求生活的真理和意义的“我”等。其探索的结果是——真理在人民中间。高尔基借《忏悔》中约纳神甫之口宣称:“民众是不朽的,我相信他们的精神,我相信他们的力量,他们是唯一不容置疑的生活基础,他们是过去和未来的一切上帝之父,他们是造神者,是永生的,正在暗地创造一个你所想象的上帝,一个美与理智、爱与正义兼备的上帝。”
应该说,约纳神甫,“一个给我指出通向上帝的康庄大道,给我的灵魂以终生的鼓舞和希望的人”,对人的分类与别尔嘉耶夫对宗教的分类,其内在意义是一致的。约纳神甫认为人分两类:一类是永恒的造神者,是人民,一类是追求权欲的奴隶,他们歪曲耶稣的精神实质,崇尚人对人的统治;别尔嘉耶夫说:宗教分为“预言的、神启的宗教”和“祭司的、神甫的宗教”,前者追求永恒性,永不满足,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和未来之城,而后者却满足已有的,维持旧秩序,反对人的精神自由。(注:参阅拙文《白银时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载《国外文学》1996年第3期。)
普里什文是高尔基推崇的几个老作家当中的一个,从他与高尔基的关系中亦可窥见后者对俄罗斯人民与知识分子关系问题所作的思考。普里什文早期日记中出现、而后转入其文艺作品中的主题是知识分子的“寻找上帝”问题。在小说《在隐没城邦的城垣旁》中,作家对知识分子与人民的关系及其历史命运作了深入思考。他认为,探寻隐没城邦的旅行不只是作家个人生命中的一桩大事,而且是20世界俄罗斯文化的大事件。(注:“隐没城邦”是俄罗斯宗教信仰和精神家园的象征。传说在彼得大帝改革以后,一些虔信的教徒逃遁到北方森林里,与他们心目中的“反基督者”彼得誓死为敌。他们隐没到“光明湖”下建立圣城吉杰什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寻神运动”中许多人到过这里。)普里什文试图通过知识分子与人民的关系,通过俄罗斯文化的命运及其精神分裂(他认为知识分子与人民是俄罗斯精神的两大极端)来理解20世纪初俄国知识分子的“寻神”活动。结论是:知识分子探索与人民探索的交合点是“没有精神家园,寻找未来城堡”的世界观。我们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在俄罗斯人的生活当中,“寻找上帝”不只是单纯宗教意义上的探索,它更多地是指精神探索,是寻找生活中的真理并探索在生活中实现真理的道路。
普里什文在写给高尔基的信中说:“虽然我们的信仰不尽相同,但至少我们的感受和精神支柱是相近的”(1926年10月3日), 即对“爱”的理解是一致的。这是一种“将生活的目的和意义、生活的全部美好之处乃至整个世界都寓于自我的爱”,是“蕴含着探知所有人生奥秘的钥匙和所有艰深复杂的人情世态的谜底”的爱,它是“无限的、永不枯竭的”(《隐士》)。普里什文正是对此表示认同,感到在自己苦苦的探索中终于找到了坚实的基础。而这也是高尔基孜孜不倦在人世间流浪寻索的结果。这种爱是欢乐,它不是“知识分子”所固有的不容异己的偏执,它能够创造出人世间的一切美丽。难怪高尔基说《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是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挽歌,因为在作家看来,俄国的知识分子并没有寻找到生活的真正意义。“为什么活着?”——这是小说的主题之一,俄国的知识分子一直在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但真正的答案却始终没找到。作家指出,“由于外来的、使人难堪的推动而感到精疲力竭的人们应该而且被迫审视自己的内心世界,再一次深入思考存在的目的和意义”(1926年3月15日致作家格里高里耶夫)。 “外来的推动”所指的是俄罗斯知识分子对外来思想、尤其是西方思想无休止的追逐。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一方面,高尔基对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偏执和不容异己持否定态度,另一方面,对他们空洞地醉心于思想、特别是西方思想的作法予以坚决排斥。存在的目的和意义在于“爱”,爱的真理只能在人民之中才能找到,人民出色的代表就是作品中的约纳神甫、拉里翁神甫、小偷和流浪人萨韦尔卡以及隐士等。与他们相比,“知识分子”的毛病就在于自视清高、逃避人民、逃避生活、囿于自我,“这种人对生活冷漠,盲目,沉默。”可以说《忏悔》中米哈伊洛的评价从根本上解释了“知识分子”的悲剧所在。如同别尔嘉耶夫的分析一样,他们与现实不妥协,在现实中只看到罪恶因而分裂出来,以教条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态度维护其信念,由此导致不容异己的极端偏执,尽管他们能够无私地、义无反顾地奉献于精神追求和对真理的探索,但这种行为是另一种样式的自私,这是一种为保全“自我”而与现实、与民众分裂的自私。因此高尔基宣称,只有与在劳动和永不停息的探索中用自己精神的美创造上帝的民众融为一体时,知识分子才能找到唯一正确的途径,正像米哈伊洛所言,“一个人只有在整体中才能找到永生”。
二、俄罗斯社会发展道路问题
俄罗斯社会发展道路问题是西方派与斯拉夫派、民主派与自由派斗争的焦点,就文学而言,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在不同时代、不同文学体裁中都有所涉及。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问题是上一个问题的继续和延伸。
在该问题的探讨中离不开国家政权和人民这两个概念,而在俄罗斯,国家与人民的关系从未真正地协调过,一直被明确地区分为“他们”和“我们”。17世纪分裂教派就是对政教合一国家的抗议,因为彼得大帝的改革一方面推进了俄罗斯的文明进程,在上层(文化层)与西方文明进程接轨,但另一方面又以暴力手段强奸了民意,干涉人民信仰,导致了人民与政权的决裂。这一时期的基本冲突是帝国思想、强大的军事警察国家思想与分裂教派中、人民中及知识分子中的宗教救世思想之间的冲突,国家政权越来越使知识分子及有教养的人们感到格格不入。符谢·伊万诺夫之子维亚·伊万诺夫在论及高尔基的一篇文章中这样提问:“为什么恰恰是富人(包括高尔基)支持革命?为什么最为极端的反政府思想在公爵身上,比如克鲁泡特金和伯爵身上,譬如托尔斯泰,得到最充分的体现?”(注:维亚·伊万诺夫:《斯大林为什么杀害了高尔基?》,载俄罗斯《文学问题》1993年第1 期。)萨姆金同样感到疑惑,“为什么柳托夫捐钱给社会革命党呢?专制政体对他的生活有什么妨碍呢?”原因就在于,寻求力量的俄罗斯帝国与寻求社会真理和正义的“神圣罗斯”之间的冲突和碰撞越来越激烈,前者要求绝对服从,一切为了帝国利益,而后者追求自由和个性独立。
俄罗斯知识分子及其有教养的人都感到,人民是有待破解的谜,他们深信,在沉默无言的人民中间隐藏着生活的伟大真理,终有一天人民会开口说话,只不过现在他们是受奴役的、愚昧无知的。换一个角度说,俄罗斯知识分子从两个方面受到压迫:自上是沙皇专制政府的压制和迫害,自下是愚昧无知民众的沉默和冷漠。高尔基对俄罗斯发展道路的思索同样离不开对政权、人民和知识分子的关系进行解剖。作家对专制政体和独裁统治深恶痛绝,对沙皇极尽讽刺和嘲笑;对知识分子表现出一种爱恨交加的感情,爱其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和永不妥协的精神实质,恨其夸夸其谈、自我封闭的孤芳自赏;对于俄罗斯人民的命运作家时刻关注,深信人民一定会有所作为,一定会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占据其应有的地位。为此就要解放人民,用文化知识教育他们,使他们获得个性自由。神学院学生弗拉德金说出了作家本人的心里话,“在这样忙忙碌碌、艰难肮脏的生活里,在人们还象一盘散沙的情况下,已经能够创造出这么伟大的奇迹,那么一旦人们在精神上得到解放,整个世界都用赞美诗和音乐来抒发自己那伟大心灵中燃起的热情时,大地上将会出现什么奇迹呢?”(《忏悔》)
在俄罗斯发展道路的探索中,高尔基强调,既要克服盲目的个性自由,又要反对对个性的践踏;既要反对东方式的愚昧,又要反对西方式的小市民习气。终极目标是要促成人类的复兴,把整个人类联合到统一的世界大家庭之中,使人感觉到自己不再是科学的、阶级的、教会的人,而是人类之人。(注:高尔基:《列昂诺夫的长篇小说〈獾〉序言》,载《高尔基与苏联作家通信集》,第262页。) 这种思想可以说是俄罗斯社会思想的一脉相承。高尔基认为,在俄罗斯发展道路的选择上人是最为重要的因素,“一切在于人,一切为了人”。这应该是什么样的人呢?这不是萨姆金之类夸夸其谈、耽于幻想、惰于行动的人;这不是巴热诺夫(《守夜人》)之类意志坚强、头脑清醒、愤世嫉俗可却因对现实绝望而自杀的人;这不是高尔基给女作家福尔什的信中提到的那些所谓俄罗斯的“强人”(注:高尔基:《谢拉皮翁兄弟》,载《高尔基与苏联作家通信集》,莫斯科1964年版,第172页。)。
“不能这样生活下去!”——这是高尔基的呼唤。应当行动起来,“不逃避,作一个行动的人”(1927年4月17日致格拉特科夫)。 高尔基认为,旧文学没有在人民中培养英雄主义精神和积极向上的态度,其主要精力集中在阐述社会存在诸问题上,对人本身的关注太少;新文学的任务就是要培养积极向上、崇尚英雄主义的真正的“强人”。如米哈伊洛所言,在新的社会里面,“孩子们应该自由成长,不能把他们变成只会干活的牲口,他们应该是自由的,朝气蓬勃的人,应该用发自内心的勇敢而美好的青春之火,用不断创造出来的伟大的美来照亮人的内心世界和整个生活。”
三、“小人物”问题
与大多数俄罗斯作家不同,高尔基反对怜悯,他认为,“艺术家是拥有让他人激动起来的才能的人,是使他人放弃喜悦、同情、怜悯等种种情感的人,因为这种种融入思想和语言的情感常常变成锁链,桎梏人的精神自由。”(1925年1月18 日致费定)高尔基批评费定“怜悯的人道主义”,他说:“屠格涅夫的《木木》、果戈理的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以及其它等等‘无用的老马’都已经不再有用处了。”他认为对“无用的老马”的怜惜是“某种古老的、基督教的东西”,而作为一个真正的“自由艺术家”应该抛却一切怜悯心,俄罗斯文学中的怜悯已经够多了(1926年1月28日致费定)。 在《致莫纳尔希斯特的信》中作家写道:“过去和现在我都在写同一个问题,即对生活持消极态度是多么有害,我们多么需要有一种积极奋发的生活态度。”而积极奋发的生活态度不是通过怜悯和同情获得的,也不是“小人物”身上可能具备的。高尔基欣赏吉洪诺夫,因为其作品充满了英雄主义精神和积极奋发的生活态度;赞赏格拉特科夫,因为其小说《水泥》一定会培养教育许多人,它抓住了生活的主旋律,表现了生活中高昂的革命热情,催人向上;认为《母亲》从艺术价值上说不算是一部好书,但是它达到了教育目的,塑造了坚强的人和英雄人物(1927年4月17日致格拉特科夫)。
在小说《一个没用人的一生》中,高尔基确乎不是怀着厌恶和敌视去描写受国家、受人压制的“小人物”主人公一生的,而且我们相信,每一个读到叶夫塞试图改变生活却横遭污辱的人都会与他一起痛哭,一起呐喊:“为什么欺负我!为什么取笑我!为什么不接受我!”在呐喊声里主人公彻底失去了自童年起就朦胧存在于内心深处的“我的花园,我的绿色的花园”,失去了“生活会慢慢好起来的”(在小说中重复了七次)这样一个美好的信念。在自杀之前叶夫塞仍旧不甘心地尖声嘶叫:“我要,我要,我要……”这里隐藏着多么深刻的痛苦,而从作家字里行间的描述中我们知道,对这痛彻心扉的绝望他并非无动于衷。作家不由自主流露出同情和怜悯,可与此同时我们不能忘记,小说的题目是《一个没用人的一生》。
高尔基反对木木、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及其一切“无用的老马”身上体现的忍耐和沉默,反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忍耐吧,高傲的人!”以及托尔斯泰的“自我完善吧,勿以暴力抗恶!”他反对对痛苦的膜拜,因为盲目崇拜痛苦只会消磨人的意志,使人变得更为消极,因此他说“有一种生物力使我敌视一切痛苦”(1926年3月27日致费定)。 高尔基认为对痛苦的反应不是忍耐和沉默,而是斗争,“斗争是生活的好法则”(《守夜人》),“革命消灭了消极等待幸福的人,逐渐代之以试图用自己个人的意志努力获得幸福生活的人。”(注:高尔基:《谢拉皮翁兄弟》,载《高尔基与苏联作家通信集》,莫斯科1964年版,第172页。)我们知道,虽然高尔基对罗赞诺夫持否定态度, 但后者对他的评价却是正确的,即“从本性上说高尔基是一个斗士”。(注:瓦·罗赞诺夫:《离群索居》,载《罗赞诺夫文集》,莫斯科1990年版,第83页。)所以,不仅是在《母亲》这部直接宣传革命斗争的小说里,即使在《忏悔》这样主要描写“寻神运动”的作品中,高尔基仍旧在工人的革命斗争中看到了希望和俄罗斯的前途。
或许,尼采对怜悯的观念从某种意义上高度概括了高尔基“敌视痛苦”的态度。尼采认为,“怜悯背离了让人生机勃勃的情绪,它使人抑郁”,“怜悯阻碍了发展律,也就是阻碍了淘汰律,它保存行将毁灭的东西;它为那些被剥夺了继续生存权以及为生活所淘汰的人作辩护;而由于它使各种失败的人继续存在,因而赋予生命本身以黯淡和可疑的一面。”(注:尼采:《反基督者》,载《尼采文集·权力意志卷》,青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5页。)所以我们说, 面对“为生活所淘汰的人”、“失败的人”,如叶夫塞·克林科夫,高尔基怀着的更多的不是怜悯和同情,而是可怜和悲哀,只能说他是一个“没用的人”。
四、俄罗斯农民与农村问题
在俄罗斯文学中表现的农村问题与其说是社会经济问题,不如说是道德伦理问题。高尔基在其文学作品中极少对农村生活进行描述,而且完整的农民形象也不多。但是这并不是说作家不关心这个问题,对于农村及农民问题的思考和态度散见于作家的作品、评论和书信中。
总的来说,高尔基对农民的评价是否定的,认为农民是俄罗斯一切历史灾难的根源。在寄给吉洪诺夫的一份附录中高尔基写道:“大量的小私有者在文化发展的过程中每时每刻起着并继续起着极端的、特别有害的作用,恰恰是小私有者(从农村出来的人)过去是现在还是无产阶级思想意识的毒害者,他们同时以农民的古老迷信和从中产阶级中吸收的个人主义弱肉强食心理毒害无产阶级。”(注:高尔基:《附录》,载《高尔基与苏联作家通信集》,第305页。 当时在吉洪诺夫的组织下计划出版一套有关俄罗斯生活方式、风土人情的图书。)虽然这里批判的是小私有者,但根源却在农村。在高尔基眼里,俄国农民“懦弱无能、丧魂落魄”,他们具有“猥琐的狂怒,胆怯而贪婪的习性,被屈辱和劳务压弯了的腰身,由于愁苦变得暗淡无光的眼神,精神上的迟钝和思想上的愚昧,以及各种迷信心理。”(《忏悔》)“他们对国家的命运漠不关心,他们对农村、土地的依附性和那种对待有教养的人根深蒂固的、兽性的仇恨,简直达到了可怕的程度。”(《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这就是高尔基对农民的态度。如果说这还不够直接,是出自作品人物之口,那么,在给费定的信中作家直接宣称:“我对农民常常与历史不可抗拒的要求相对立从本能上感到仇恨”(1925年9月17日)。 正因为高尔基对农民怀有的否定评价,维亚·伊万诺夫才说:“就其历史观念而言在俄罗斯文学中没有一个人与当代农村题材小说更对立:一切把农村看成失去的天堂的人……都使高尔基感到厌恶和仇恨。”(注:维亚·伊万诺夫:《斯大林为什么杀害了高尔基?》, 载俄罗斯《文学问题》1993年第1期。)1926 年在写给格拉特科夫的信中作家确切指出:“我总是对‘微小数量’的城市无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抱以好感,对‘百万之众’的农民阶级持否定态度”。
在与费定的辩论中表现了高尔基在农民问题上的鲜明立场。可以说,在费定与高尔基的讨论和争辩中体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也是俄罗斯文学对农民与农村问题态度的缩影。费定认为,未来的文化恰恰要依靠农民而非硬驱赶他向前走的人。庄稼人固执地抓住旧的东西不放并非出于恶习,他们感到从这些“赶车人”身上什么也抓不住,而因此指责农民“愚昧无知”、“因循守旧”是没有道理的。“赶车人”根本就不理解农民,不理解他们的文化与心理基础,若要农民跟自己一起走,就必须理解他们,了解他们的文化,而不能一味强拉硬拽(1925年11月)。对于费定的观点高尔基反驳道,“赶车人”恰恰把活生生的、崭新的真理带入生活之中,他们是文化的创作者。农民与“赶车人”总是处于对立之中,是因为他们希望安静、安稳,而只有打破对安静与平稳的欲望社会才会进步,人类才会向前发展。这种希望就寄托在“赶车人”身上,他们就是知识分子和城市无产阶级(1925年9月17日)。
从以上对各个问题所作的阐释和分析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即在高尔基的观念中一切问题的提出和解决皆围绕一点:在怎样的程度上对社会进步有利,可以多大程度地解放人,使之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体现人的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在人民与知识分子、俄罗斯社会发展道路、“小人物”问题及农村与农民问题的探讨中,高尔基表现了其积极向上、不断进取的道德观念,在许多方面迥异于古典俄罗斯文学传统,展示了新颖的文化层面。
标签:高尔基论文; 知识分子论文; 俄罗斯文学论文; 文学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忏悔论文; 守夜人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