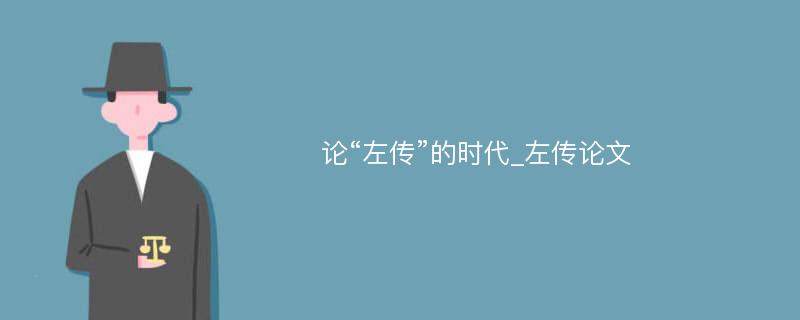
论《左传》的成书年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左传论文,成书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现在大多数学者认为《左传》成书于公元前四世纪,但有前四世纪初、中、晚期多种不同主张。本文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辨析分歧的焦点、是非,力图做出更为近实的结论。
杨伯峻先生定《左传》成书于前403至前386年间,是目前最有影响的一说。本文通过分析书中陈氏代齐的预言和充分列举有关旁证,证明《左传》作者知晓前四世纪七十、六十年代的历史事件,判定《左传》成书于前四世纪七十、六十年代,认为杨先生所定时代偏早。
胡念贻认为《左传》作于春秋末年,左氏对战国历史“全然不知”。本文通过辨析胡氏思想方法之误和对于史实的失考,证实其论断有失客观,并对本文第一部分论点作了进一步申述和补充。
关键词焦点 陈氏代齐 郑先卫亡 预言 从后傅合 写作期 抄撮 客观
自从唐人打破左丘明作《左传》的成说之后,虽经历代学者探讨,对《左传》的作者始终得不出可信的结论,在目前条件下只好存疑。但对于《左传》成书的年代,大多数学者有了比较接近的看法,认为它是公元前四世纪的产物①,即战国时期的著作。至于在前四世纪什么年代,则仍然存在分歧。本文的写作目的,是想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分析现存分歧的焦点、是非,获得更多共识,把问题的研究向前推进一步。下面分两个问题谈。
一、《左传》成书年代述论
我们首先列举具有代表性的、定出具体成书年代的十家意见,以作为进一步探讨的出发点:
1.梁启超:在田氏代齐、三家分晋、韩氏灭郑以后②。
2.新城新藏:在前四世纪五、六十年代③。
3.刘汝霖:在前375——前340年间④。
4.蒋伯潜:同梁启超说⑤。
5.陈梦家:在前329——前320年间⑥。
6.朱东润:在前四世纪初期⑦。
7.徐中舒:在前375——前352年间⑧。
8.童书业:成书下限为前329年⑨。
9.杨伯峻:在前403——前386年间⑩。
10.赵光贤:在前375——前351年间(11)。上列十家有八家认为《左传》成书于前386年陈氏代齐和前375年韩国灭郑以后,6、9两家持有异议。而第9家是目前影响最大的一家。杨伯峻先生认为:“当时人多看到陈氏有代齐的苗头,是否果真代齐为侯为王,谁都未敢作此预言”,陈氏为侯是“《左传》作者所未及知道的”,因而断定《左传》成书不晚于前386年(12)。朱东润先生说:“《左传》的成书在魏的开始强大”,他引人注目地不提陈氏代齐、韩国灭郑(13),后来终于说《左传》是“战国初期(前五世纪)”(14)的作品,采纳了刘逢禄“书终三家分晋”(15)的主张,比杨说更提前了。梁启超曾经“颇信”《左传》成书“上距孔子卒百年前后”(16),可是后来又说“左氏这书是当三家将分晋、田氏将篡齐而未成功时的产品”(17)。胡念贻也以为:“这个‘莫之与京’,《左传》本文的解释是指‘成子得政’……还不是指陈氏代齐。”(18)可见6、9两家的意见有一定的代表性。
可是早在宋代,朱熹就痛快淋漓地说:“《左传》是后来人做。为见陈氏有齐,所以言‘八世之后,莫之与京’;见三家分晋,所以言‘公侯子孙,必复其始’。”(19)现代多数学者都与朱熹看法相同,他们依据“书中屡见”三家分晋、陈氏代齐的预言,常常不加论证就认为《左传》“必定”作于前386年陈氏为侯之后。杨伯峻先生也认为“《左传》作者一定看到魏斯为侯”(20)。
现在问题已很清楚,症结所在,就是《左传》作者究竟有没有看到陈氏代齐。
杨先生阐发说,庄公二十二年传文所说“成子得政”,意即筮者所说“代陈有国”;晏婴说“吾弗知齐其为陈氏矣”(昭公三年),所以卜辞也只说“八世之后,莫之与京”,不言“十世之后,为侯代姜”;史赵也只是说“继守将在齐,其兆既存矣”(昭公八年);仲由更说“(陈氏)既斫丧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终飨之,亦不可知也”(哀公十五年)。所以他认为《左传》作者未及见陈氏篡齐。对于这个论断,我们还可以引《史记》为其佐证。《田齐世家》载,陈完八传至成子,成子弑简公立平公(前481),为相五年,“齐国之政皆归田常,田常于是尽诛鲍、晏、监止及公族之强者,而割齐自安平以东至琅邪自为封邑。封邑大于平公之所食。”弑君专政,封邑大于君,是可以称做“莫之与京”的,而这时下距陈和为侯还有九十年。齐康公十四年(前391),陈和“迁康公于海上,食一城”,更可以说“莫之与京”,这时陈氏仍然没有封侯。
但是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认为《左传》成书在前386年之后。先说内证。首先,如何理解“八世之后,莫之与京”。成子于陈完既然为八世,又正好专齐姜之政,传文为什么还要说八世“之后”?如果“莫之与京”仅指“成子得政”,彼此岂不相左?其实,“之后”二字是把十世、十二世都包括在内的。有人指出:“‘八世之后,莫之与京’,非特指‘八世’,而包括‘之后’,也即包括成子得政至田和篡齐这段时间的事。因此不能说田和代姜是作者未及知道的。”(21)这个批评很中肯。有齐国,做诸侯,才是真正的“莫之与京”。其次,如何理解“代陈有国”?陈为诸侯。陈完子孙不做诸侯,就谈不上“代陈有国”。有国,可以释为专擅国政,也可以指做诸侯。《尚书·吕刑》“有邦有土”(《墨子》引“有邦”为“有国”),蔡沈集传:“有邦,诸侯也。”“有天下”是做天子,“有国”就是做诸侯。“有国”与“代陈”相连,只能是指陈亡之后,陈完子孙代齐为侯。卦“遇《观》之《否》”,《观》、《否》下位经卦都是坤,坤为土,“于是乎居土上”,“著于土”,这不是着意影射“有士”为君的意思吗?至于左氏只说“成子得政”,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左氏好奇,他对于“物莫能两大,陈衰,此其昌乎”,亦即对“及陈之初亡也,陈桓子始大于齐;其后亡也,成子得政”这样的巧合很感兴趣,所以特意点出,以昭示卜筮的灵验,至于“得政”以后,因为已有“八世”二句,也就不言自明了;二是,左氏虽然好作预言,未尝不通过卜筮、书中人物或“君子曰”说出,成子得政尚在春秋末年,他可以说明,至于陈氏为侯,已入战国九十年,如果通过他的口直接说出“十二世有齐国,为侯代姜”,那就违背了他的常例,而且立刻暴露了他所处的时代,使一大批预言都失掉了神秘性。我们不应当对左氏抱有这样的期望,也不应当因为他没有点明陈氏为侯而产生误解。第三,哀公十五年仲由对陈瓘讲的话,宜分两点看:(一)那不过是仲由为鲁国游说的一段辞令,意在劝说陈成子“善鲁以待时”,注意力向内而不要对外,不能由此论定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二)不能认为左氏为作预言而改动了相关的所有史料,仲由不知道身后的事,他不敢肯定陈氏一定代齐,很符合他的实际。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说齐国:“表东海者其太公乎!国未可量也。”昭公六年叔向对子产说:“终子之世,郑其败乎!”这些话都与其他预言和后来的事实相抵触或有出入,我们不应当因为这些原始史料而错认了左氏的预言。
下面列举外证,看看《左传》作者究竟有没有看到和看到多少前386年以后的历史事件。首先证明《左传》成书不能必保在前386年之前。其一,定公九年,阳虎奔晋,适赵氏。仲尼曰:“赵氏其世有乱乎!”《四库全书总目》说:“后竟不然,是(左氏)未见后事之证也。”其实这是十分灵验的预言,只要一翻《史记·赵世家》就可以知道:简子之世,有赵稷之乱,范氏、中行氏围简子于晋阳;襄子之世,知、韩、魏再围襄子于晋阳;献侯之世,桓子逐献侯自立,桓子死,国人复立献侯;烈侯之世,有武公之乱(22);敬侯之世,有武公子朝之乱;成侯之世,有公子胜之乱,又有公子緤之乱;肃侯之世,公子范袭邯郸;武灵王、惠文王之世,有公子章之乱,公子成、李兑饿杀主父(武灵王)。自前497至前295二百年间,赵氏传九世乱九次,真正是“世有乱”。《左传》成书诚然不会晚到前295年,可是有谁能肯定,作者说这话时必定在前386年(赵敬侯元年)之前而不会在其后呢?其二,文公六年秦穆公卒,以活人殉葬,传文说:“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秦穆公死后,仅据《左传》记载,秦伐晋即不下八、九次,左氏为什么却要说秦“不复东征”呢?这大概只能有一个解释:人们亲眼看到的东西永远比听到、读到的东西印象深刻。左氏这样说和他所看到的秦、魏形势有关。秦自躁公至出子二年(前442——前385),有一段衰落时期,外有义渠、蜀、魏的威逼,内有频繁的篡弑易君之乱。试看:躁公二年,南郑反。十三年,义渠来伐,至渭阳。十四年,躁公卒,立弟怀公。怀公四年,庶长晁杀怀公。简公七年,魏尽取河西地。惠公十三年,蜀取南郑。出子二年,庶长菌改迎立灵公子献公于河西而立之,杀出子及其母(23)。所以秦孝公说:“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24)献公虽然安定了君位,立志图强,但“不复东征”的局面一直持续到他的晚年(前四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而与秦成为鲜明对照的是,秦的东邻魏国这时正是长足发展的时期。前419年,秦、魏开始争夺土地,前408年魏完全占有秦河西地,前406年魏灭中山。魏文侯敬礼贤能,变法图强,任用李悝、吴起、西门豹、乐羊等,魏国大治,成为战国前期第一强国。姚鼐说《左传》作者“于魏氏事造饰尤甚(25),肯定就是因为他亲眼看到了魏国的发展和强大,又目睹了秦国的君臣乖乱和自顾不暇。既然自前五世纪后期至前四世纪六十年代中叶秦都处于不东征的时期,有谁能肯定,左氏说秦“不复东征”,必定在前386年之前而不会在其后呢?
下面证明《左传》成书必定在前386年之后。襄公二十九年、昭公四年两次预言“是其(郑)先亡乎”,“郑先卫亡”。至周烈王元年(前375),郑国果然先于卫等很多诸侯国而灭亡。试想,如果不是作者看到郑国灭于韩,襄、昭之际的人怎能预知一、二百年以后的事?又为什么预断得这样灵验?《左传》中的预言几乎无不“其应也如响”,连主张左丘明作《左传》的《四库全书总目》的作者也掌握了它的秘密:“预断祸福无不征验,盖不免从后傅合之。”这是理解《左传》的一个诀窍。上述十家中之所以有五家把《左传》成书年代的上限定于前375年,原因即在于此。这是证据之一。
卫国直至秦二世时才灭亡,而《左传》僖公三十一年说:“卫迁于帝丘,卜曰三百年。”昭公四年又说:“郑先卫亡”,预断卫国继郑之后在前330年前后灭亡,这是不是作者“信口开河”呢?不是,这是因为严重的外患内忧,使卫处于危亡关头。赵成侯三年(前372),赵攻取卫之乡邑七十三。十年(前365),又攻取卫的甄(26)。赵在卫西北,甄在卫都濮阳之东,赵攻取这样大片的土地,就在西、北、东三面包围了卫国。(前354年,赵攻取卫的漆、富丘,又在南面截断了卫与魏的通路,迫使卫朝赵,导致魏救卫,次年齐又救赵。这时的情况,估计左氏未及见之。)这时在卫国内部,子南氏专权,卫君处境岌岌可危。《竹书纪年》说,子南劲朝魏,后梁惠王“命子南为侯”,《韩非子》更说子南劲“弑其君”而“取卫”。子南劲就是取代卫成侯(前361——前333)的卫平侯,所以《荀子》称成侯为亡国之君(27)。左氏并没有看到前333年子南劲取卫(说详下文),但他因为看到前365年前后卫国内外所呈现的危势,才敢于断言“卫亡”的。当时因为郑亡不久,所以就说“郑先卫亡”了。这个“卫”不是指亡于秦二世时的子南氏的卫,而是以卫康叔为始封君的卫。由此可见,传文的预言在当时确有征象为据,事后的发展也果不出其所料。而这一切都发生在前386年之后,足证《左传》成书不可能早于陈氏代齐。这是证据之二。
《左传》在襄、昭时期多次使用岁星纪事,两次说到星宿分野,都是用以预断吉凶,异常灵验。如昭公十年,岁在玄枵而出现了妖星,裨谌说玄枵是齐国分野,而晋国始封君唐叔是齐女所生,灾祸将降临到晋君。本年果然晋平公卒。本世纪初,日本学者新城新藏对岁星纪事、星宿分野等做了专门研究,他的结论是:“凡《左传》及《国语》中之岁星经事,乃依据西元前365年所观测之天象,以此年为标准的元始年,而按推步所作者也。故作此等纪事之时代,当在此年后者,是不待言。然自此标准的元始年经十数年后,观测与推步之间,自有若干参差,而当时人亦自然注意及之(28)。爰著此纪事之年代,恐在此标准的元始年以后数年之内也。”(29)星宿分野的制定,宋代郑樵和新城新藏都认为在三家分晋以后,新城氏并认为在韩灭郑和魏迁大梁以后。岁星十二次和星宿分野,是为占星术而作。战国甘德的《天文星占》和石申的《天文》,当作于前四世纪六十年代前后(30),《左传》中的占星术可能就出于魏国人石申。对岁星纪年法的起源时代,有人提出不同看法,也有人进一步推算证实,认为新城氏的论断“精当”、“可取”(31)。岁星纪年法行用于战国,十二个岁名如摄提格等至《离骚》才开始使用,这都是事实。当今天文学界,也认为《天文星占》、《天文》“都属于占星术的东西”,书中记载的“一部分恒星的坐标值(如二十八宿距度等)则确与公元前四世纪,即石申的时代相合”(32)。二十八宿的距度是建立分野的基础,上面这一论述,等于在星宿分野和占星术方面进一步确认了新城氏的论断。由此可以判定,《左传》的成书不可能早于前四世纪六十年代。这是证据之三。
宣公三年传文说:“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对于这条预言,应当说明下列几点。第一,所卜年、世,应当从文王、武王算起,还是从成王定鼎算起,通观上下文意,我同意杨伯峻先生的意见,应当从武王算起。第二,关于西周的年数,究竟《竹书纪年》说可靠,还是《史记·匈奴列传》、《汉书·律历志》、《通鉴外纪》可靠,恐怕只能说《纪年》更可靠,所以郭沫若、翦伯赞等都依《纪年》把武王灭纣定于前1027年。近世出现了前1066年说(新城新藏、范文澜)、前1057年说(张钰哲、张培瑜),现在更受史学界重视的则是倪德韦、周法高、赵光贤所持的前1045年说。依《纪年》和后一说,自武王灭纣至前386年(周安王十六年),“世”恰为“三十”,“年”仅为六百四十二或六百六十,怎么能肯定《左传》成书“很难到周安王时代”(33)?第三,左氏这个预言,必定有所见而云然,不会是无的放矢。(一)据《史记·周本纪》、《秦本纪》载,烈王二年,即秦献公十一年(前374),“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周与秦国合而别,别五百载复合,合十七岁而霸王者出焉。”这话又见于《封禅书》、《老子列传》,文字有小异。引人注意的是,此借周太史之口,作了周、秦“复合”亦即秦吞并周的预断。秦献公是一位励精图治的君主,即位后,他就立即采取措施作夺回河西失地、向东方发展的准备,到他晚年就大举向东方用兵了。上述预言,或许出于秦人造作,但可以说是无风不起浪。(二)周考王为续周公的官职,封其弟于河南(今洛阳王城),即周桓公,至显王二年(前367)臣下杀周威公(桓公子),而韩、赵出于本国利益需要,插手周室内乱,帮助威公少子根在巩建立了一个小国,把周王室分裂成东、西周(34)。王畿仅存的七个邑,至此又分属东、西周两个小国,“周天子”只居洛阳依东周以存身,是十足的徒有其名了。(显王十六年即前353年,韩攻东周,取陵观、邢丘,东周割高都、利给韩,估计左氏未及见之。《韩非子·说疑》说:“周单荼……援外以挠内,亲下以谋上”,“单氏取周……臣之弑其君者也。”春秋、战国之交,刘氏、单氏为周室卿士,而刘氏亡于定王(前468-前411)时,此后单氏执周政。单荼弑君取周,有人以为周政权“曾一度落入单氏手中”,有人以为即指弑周威公(35),不可详考。总之,极端微弱的周王室,既有内乱,又有外患,左氏必定以为它很快就会灭亡,所以作了“三十、七百”的预断。至于显王在位长达四十八年,慎靓王之后的周王赧又苟延五十九年,这是左氏始料不及的。这条预言同样证明,《左传》成书必在前386年之后。这是证据之四。
基于以上诸证,我们可以看出:《左传》作者对前375年的韩灭郑,前372和前365年的赵攻卫与当时子南氏的专卫政,前367年周室的分裂削弱,前四世纪六十年代所观测的天象和兴起的占星术,战国前期赵氏的世世有乱,前五世纪晚期至前四世纪六十年代魏的强大和秦的衰落,一句话,他对于战国初至前四世纪六十年代的历史事件都是知情的。
综合内、外证,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左传》作者不仅知晓三家分晋,而且看到了陈氏代齐。杨伯峻先生定《左传》成书于前403-前386年间,时间偏早了。第二,前四世纪七十、六十年代可能正是《左传》的写作期。一些学者定《左传》成书年代的上限为前375年,是适宜的。
探讨《左传》成书年代的下限,至少要考虑以下几点:一是秦国的“东征”,二是“卫亡”,三是滕的复国,四是铎椒著《抄撮》的时间。
秦献公经过近二十年的准备,便于前366、364、363、362年连续用兵,并且接连取得胜利。特别是前364年秦魏石门(今山西运城西南)之战,地近魏都安邑,斩首六万,可能是战国以来规模最大的战争,当时引起很大震动,周显王贺秦,秦献公称伯。前362年之战,魏再次损地折将(36)。值得注意的是,魏在前364或前361年便由安邑迁都大梁(37)。魏迁都有向中原发展的意图,但从迁都的时机看,必定与秦的进攻有关。与此同时,自前361至前358年,魏在秦魏边境“自郑(今陕西华县)滨洛(洛水)”,修筑了一条数百里的长城(38),对秦采取了防守的态势。秦孝公元年(前361),秦出兵东围陕城(今河南三门峡市),二年,周王致文武胙于秦,四年,败韩于西山,七年,孝公、梁惠王会于杜平(今陕西澄城东),八年(前354),与魏战元里,斩首七千,攻取少梁(39)。同年,“秦公孙壮率师伐郑(韩),围焦城(今河南尉氏西北),不克。”“公孙壮率师城上枳、安陵(今河南鄢陵北)、山氏(在焦城西南)。”(40)这时不仅改变了“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41)的局面,而且秦师攻入中原腹地,插进韩、魏界中来了。这是前所未有的。关注各国时事的左氏,即使尊魏,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还不修正秦“不复东征”的说法,就是咄咄怪事了。赵光贤先生把《左传》成书年代下限定于前352年秦攻取魏的安邑,其实秦攻入并且筑城于韩、魏腹心地带,其严重性未必在魏失安邑之下。如果左氏对前364、362年的秦胜魏还不肯放在心上,这时无论如何也应当改变他的观点了。
上列十家中有两家把前329年定为《左传》成书年代的上限或下限,新城氏也说过《左传》成书于前365-前329年,这都是依据僖公三十一年(前629)所说:“卫迁于帝丘,卜曰三百年”。童书业考定卫于前333年亡于子南氏。我们认为左氏并没有实际看到前333年的卫亡,他只是依据前372、365年的赵攻卫和子南氏专卫权而言中的。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有以下两条理由。
昭公四年传文说:“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曹灭于春秋末,蔡灭于战国初(前447),滕于前414年亡于越(42)。越于前379年由琅邪迁都于吴,滕可能在越国南迁后恢复,具体时间虽不可考,照理不应当晚于前355年前后。左氏断言滕在姬姓中为先亡国家之一,意味着他不知道滕的复国。前330年前后正是滕定公在位时期(43),可证左氏生活年代决不会晚到此时。这是理由之后。
司马迁说:“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44)孔颖达引刘向《别录》说:“铎椒作《抄撮》八卷。”(45)前人已经考定,司马迁这里所说《春秋》就是《左传》,而《抄撮》就是抄撮《左传》而成的《铎氏微》(46)。楚威王在位在前339-前329年,那么《左传》成书就必不晚于这个时期。况且,铎椒得做威王师,资望必定不低,而他习学《左传》也不应少于四、五年,自习学至成名、为师,总要用十五、二十年时间。又,是不是《左传》一成书铎椒就立即读到或马上得到了传授呢?所以这样算来,《左传》成书最晚不应晚于公元前360至前355年间。这是理由之二。
我们可以举出确凿证据证明《左传》作者了解前四世纪七十、六十年代的情况,但他对五十年代的情况便或明或暗,存在彼此参差的情形,就像《史记》记事的下限一样,并不是一刀切。所以我们可以把《左传》成书年代的下限定于前360至前355年间,亦即秦孝公初年(47)。
沈玉成同志说:“写定的时间应当在三家分晋即公元前403年以后的三、四十年间。”(48)虽然没有举证,但他的判断是相当准确的。
陆德明、孔颖达引《别录》说:“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吴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铎椒,铎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49)自赵匡以来很多人指斥这个传授系统虚妄,恐怕不会是全妄,至少铎、虞习《左传》是事实,依当时情势推测,铎椒也必定有师承。如果一定要在这个传授系统中拉出一个年代相当的人做作者,按上面论定的年代,就不可能是死于前381年的吴起(50),而应当是另一个左丘人——吴期。(51)
二、能否通过预言考证《左传》成书的年代
和很多学者的做法一样,本文主要是通过《左传》中涉及战国时代的预言、史实,考订《左传》成书年代的。有人对这种方法持否定的态度,认为《左传》中这类预言只是“片言只语”,通过预言推断成书年代“是不科学的”(52)。胡念贻分析了九条预言,认为七条不应验,一条在“疑似之间”(陈氏代齐),一条是“战国时人窜入”(三家分晋),他于是得出了如下结论:
可以证明作者对于战国时的历史全然不知,说明他不是生活在战国时代。他把一些信口开河的预言写进他的书里了(53)。
由此他仍认定《左传》“作于春秋末年”,“作者是左丘明”。在我们看来,胡氏所说九条预言(上文都已说到)可以分为三类:(一)是验辞,共六条,即三家分晋、陈氏代齐、郑先亡、滕先亡、赵氏世有乱和卫国三百年,都是很灵验的预言。胡氏为什么以为后四条都“不验”呢?因为“郑至三家分晋之后始灭韩”,他便认为这一条不验了。这显然不是预言本身不验,而是先入之见(成书于春秋末)作怪,主观地认为“不验”。他的目的是“考察”《左传》是否“为战国时作”,明明在战国应验了却嫌其时代太晚而不认为应验,自己陷入了一个怪圈之中,这样的考察还有什么意义?胡氏附和顾炎武《日知录》的说法以为滕亡于宋王偃,于姬氏为最后亡,却不知道滕先亡于越,这是失考。胡氏又说,赵“世代相传,没有常发生变乱”,用语甚含混,不“世代相传”怎么能说“世有乱”?传九世而乱九次,算不上“常变乱”,算不算“世有乱”?左氏未及见子南氏篡卫,但他据情势所作的推断十分准确,胡氏认定卫亡于秦二世,自然也属于失考。(二)依据当时的征兆作预断,而后来事情发展出乎意料的有二条,即“不复东征”和“卜世三十,卜年七百”。结果虽然没有言中,但是探寻左氏作预料的背景,仍然可以作为考证成书年代的参照。胡氏承认《左传》作预言的目的是要把事情写得“更加神乎其神”,却又认为关于战国时代的预言是作者出于“全然不知”的“信口开河”,这是不是自相矛盾?左氏这位史学、文学的天才,如果不是确有所见,他为什么无端地去做与他的目的背道而驰的愚蠢之举?(三)是作者未加改动的真实史料,即“国未可量”一条。这是季札观察当时的形势,加上他的主观情感对齐国所作的判断,因而与书中反复预言的陈氏代齐发生的抵触。这提出了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左传》一书细针密缕,极少有漏洞,与《史记》的“甚多疏略,或有抵梧”情况不同。但这不等于说就没有“抵梧”(54)。季札说这话在齐景公四年(前544),当时的晋国政出多门,逐渐失去霸主的权威,于是齐景公有小霸之志,图谋“代兴”。当吴国北上之前,齐景几乎称霸,他的与国有郑、卫、鲁、宋等,而且屡次攻打晋国。所以公孙丑说:“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显。”(55)可是,“一般史家多因左氏他处‘浮夸’之记载,误信陈氏早已得势,一若‘小霸’之齐景公时陈氏已成代齐之局者,实非事实。”(56)昭公三年晏子说:“公弃其民,而归于陈氏。”“姜其危哉!”昭公二十六年晏子又说:“陈氏厚施焉,民归之矣!……则国其国也矣。”这类记载,“皆是预言,决不足信。”(57)《左传编撰考》也指出,昭公三年、二十六年的记载:“与时代不合,……带着晚出的烙印”,“乃误取《晏子春秋》文。”我们对此有三点说明。其一,据《史记·田齐世家》,开始使用大斗、小斗的不是田桓子无宇,而是田僖子乞,司马迁的记载应当别有所据,它和上述童、赵的论断正可相互印证。对此,前人总以为《左传》是而《史记》非,现在看来《史记》是而《左传》非才合乎情理。其二,《晏子春秋》和《左传》昭公三年相应的记载是《问下》第十七篇,两书语句相同,而《晏子》在“或燠休之”与“其爱之如父母”之间独多一段:“昔者殷人诛杀不当,僇民无时,文王慈惠殷众,收恤无主,是故天下归之,无私与,维德之授。今公室骄暴,而田氏慈惠。”以齐君暗比殷纣,把田氏比做文王,不用说这样的话只能出于陈氏或拥陈者之口,绝不可能出于晏子之口。《左传》少了这段语,必是左氏觉得不妥而删削。可是“田氏慈惠”与下句“其爱之……”联系非常紧密,左氏删除以后,使“其”、“之”远承上文的“民”和“田氏”,文字便不联贯。这是《左传》抄《晏子》的铁证(58)《晏子》与《左传》昭公二十六年相应的记载有《谏下》第十九、《问上》第八、《外上》第十和十五。《谏下》的一篇只字没有提到田氏,只是说:“欲知把齐国者,则其利之者邪?”后三篇则明确说:“田无宇之后为几”,“齐国,田氏之国也。”文章的先后演进之迹,昭然可见。引人注意的是,《左传》不同于《谏下》的含糊其词,却同于另三篇明点田氏。其三,齐景公在《晏子》中三番五次地问:“后世孰将把齐国?”“美哉其室,将谁有此乎?”“后世孰将践有齐国乎?”一个图谋称霸的国君而有这样的精神状态,是有背常情的,这只能理解为陈氏及其徒党的造作。可是,《左传》却把这样的话明白地写进去了。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一是季札的话是当时真实情况的反映,不出于后人造作,因此不应拿它来考察《左传》作者的时代;二是,这种真实史料的存在,正可拿来鉴定一些预言的晚出,而不应当用它去抵消那些预言的灵验。
《左传》中涉及战国的预言是不是只有上述八、九条呢?不是。左氏了解战国中期以前的历史是一个不容置辩的事实,并不是出于谁的附会和想象,我们还可以举出很有说服力的例证。如闵公二年说:“季氏亡,则鲁不昌。”季氏亡于鲁在鲁元公(前436-前416)之世,所以到鲁缪公(前415-前383)(59)时便不由季氏执政,而任用公仪休。淳于髡说:“鲁缪公之时,公仪子为政,子柳、子思为臣,鲁之削也滋甚。”(60)据《史亡·六国年表》,前412年,齐伐鲁。前411年,齐取鲁之都。前408年,齐取鲁郕。前394年,齐限鲁最。前385年,齐伐鲁,破之。这都发生在鲁缪公之世。假如左氏对战国历史“全然不知”,他的预言怎么会和后来淳于髡的话、《史记》的记载若合符契?假如他是“信口开河”,他的预断为什么能够如此灵验?
再如襄公二十七年传文:“其余皆数世之主也,子展(罕氏)其后亡者也”,二十九年传文:“郑之罕,宋之乐,其后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国乎!……乐氏……其以宋升降乎!”也都是涉及战国的预言。襄公末年至春秋末不过七十年,可传三、四世,恰抵“数世”之数,罕氏既不同于郑“其余”诸卿而“后亡”,则必至战国无疑。襄公二十九年罕虎继父位为上卿,次年为郑相(旋即“授子产政”,但罕虎及其子之位次仍在子产之上),那么这里所说的“得国”就不应当是指执郑政,而是指得君位。自此终春秋之世,郑无篡弑的记载,直至郑哀公八年(前455)始见“郑人弑哀公”,郑幽公元年(前423)韩攻郑,杀幽公,郑繻公二十七年(前396)子阳之党弑繻公(61),《韩非子·说疑》说:“郑太宰欣……上逼君,下乱治,援外以挠内,亲下以谋上”,“太宰欣取郑……臣之弑其君者也。”太宰欣弑君取郑已无从详考,但与上述郑君被弑必定有关。“太宰”是相、执政的通称。左氏在襄公二十九特意说:“故罕氏常掌国政,以为上卿。”综合来看,这个取郑的太宰欣,就必定是罕氏的后人。前已证左氏知道郑的灭亡,他对郑亡前的废兴更替怎么会不了解?宋国乐氏的得国,见于记载的是哀公二十六年(前469)乐卿为上卿执宋政,至于乐氏“以宋升降”,又必定包括此后的一段时间,也表明左氏对此有进一步的了解。有人以为在戴氏篡宋时(在前356年以后),乐氏与宋同亡,故称“以宋升降”(62)。
综合上述十一条预言,八条应验,三条不验。应验的预言,从事件说,涉及蔡、滕、晋、魏、赵、韩、齐、郑、卫、宋各国的兴衰变化;从时代说,属于战国初年至战国中期即前四世纪七十年代,其中有关魏、赵、卫、宋的论断包括了前四世纪六十年代乃至以后的情势。三条不验的预言,无例外都有当时的征象为依据,涉及周、秦、齐(季札的话)的史实,其时代晚的在前四世纪六十年代,如周的分裂削弱,秦“不东征”。
一部春秋时代的史书,写及战国时代各国这么多历史事件,还不足以引起注意,从而断定作者和它的成书时代在战国吗?不作细致的分析,把它们说成“个别的例子”、“不验”、“窜入”,简单化地予以否定,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当然分析预言不是探索《左传》成书的唯一方法,可以而且应当通过其他途径进行探索(63),但是对《左传》这部书而言,客观分析书中预言所得出的结论无疑是有说服力的。
注释:
①⑨(27)(56)(57)(62)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335页、261页、336-337页、90-102页、103页、263-264页。(27)复参陈奇猷《韩非子集释·说疑》。
②⑥《要籍解题及其读法·左传》。
③(29)《东洋天文学史研究》561页、418页。
④⑥转引自蒋善国《尚书综述》232页。(5)《十三经概论》440页。
⑦(13)朱东润《左传选·前言》。
⑧徐中舒《左传选·后序》。
⑩(12)(20)(23)(46)《春秋左传注·前言》。⑩初版作“周安王十三年三八六年”,新版改作“周安王十三年(公元前三八九年)”,均有误,应当作“周安王十六年(公元前三八六年)”。
(11)《古史考辨·左传编撰考》。
(14)《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编一册57页。
(15)《左氏春秋考证》卷上。
(17)《古书真伪及其年代》第五章。
(18)(53)《左传的真伪和写作时代问题考辨》,载《中国古代文学论稿》。
(19)《朱子语类》卷八十三。
(21)(52)陈茂同《左传的作者及其成书的年代问题》,《厦门大学学报》84年1期。
(21)复参《史记·田齐世家论赞》。
(22)《史记·赵世家》载,烈侯在位九年卒,弟武公立,武公十三年卒”,其说不可信。《竹书纪年》有“赵烈侯十四年”,杨宽《战国大事年表》定烈侯在位二十二年是对的。《史记》多出武公一世而《世本》无其事,表明武公乃作乱自立,敬侯元年“武公子朝作乱”,也透露了此中消息。此事史家乃未发。
(23)(24)(36)(39)(41)《史记·秦本记》、《六国年表》。(23)简公七年事复参《战国史》270页。
(25)《左传补注·序》。
(26)《史记·赵世家》。
(28)此指《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述及岁星赵次事,即“岁在星纪,而淫于玄枵”。
(30)新城氏以为在前四世纪五、六十年代,杨宽《战国史》453页说在“前360年左右”。
(31)王胜利《岁星纪年管见》,载《中国天文学史论文集》第五集,又见注(18)胡念贻文、杨宽《战国史》452-453页。
(32)《中国大百科全书·天文学》“中国天文学史”条。
(34)杨宽《战国史》275页有详考。
(35)参《春秋左传研究》263页、周勋初《韩非子札记》283-284页。
(37)后人引《竹书纪年》,或说此事在梁惠王六年(前364),或说在九年(前361),今人多以为在九年。
(38)魏“西边”长城之筑,史籍记载颇多纷错,此据张维华《中国长城建置考》上编《魏长城考》,惟其所说梁惠王十二年当秦孝公三年尚非是,实当孝公四年(参杨宽《战国大事年表》中有关年代的考订)。
(40)(42)《水经·渠水注》引《竹书纪年》、《史记·越世家》索隐引《竹书纪年》。
(43)(59)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423页、《先秦诸子系年通表二》。
(44)《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
(45)(49)《春秋经传集解序》疏、《经典释文序录》。
(47)日人狩野直喜说:“左氏预断秦孝公以前事皆有验,孝公后概无征。”(《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六十七节引)可与此相印证。
(48)《左传选译·前言》。
(50)姚鼐《左传补注·序》、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吴起传〈左氏春秋〉考》、郭沫若《表铜时代·述吴起》与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春秋左传作者推测》等均以为吴起为《左传》作者或主要作者。
(51)铎椒为楚人,又仕楚于楚,似可证《左传》最初在楚国传布。吴起仕楚被杀,其子吴期盖家于楚。郑樵、朱熹都以为《左传》载楚事详,作者为楚人。此说或可追索。
(54)董增龄《国语正义·序》、皮锡瑞《经学通论·春秋》、顾颉刚《春秋三传及国语之综合研究》都述及《左传》的自相矛盾和不可信据处。(55)(60)《孟子·公孙丑上》、《告天下》。
(58)《晏子》之文有的抄自《左传》,而《左传》亦抄《晏子》。对照二书均有明证。(59)《史记·郑世家》。(61)胡念贻以《论语》多用介词“於”而《左传》多用“于”,《论语》多用疑问语尾词“与”而《左传》不用,认为“《左传》产生的时代略早于《论语》”,可惜其说不能成立。对于以“于”、“於”判定古籍成书时代,何乐士《左传虚词研究》115至116页作了透彻说明和批驳。左丘明与孔子既为同时之鲁国人,孔门弟子又忠实记录孔子的神情语气,而一用“与”一不用“与”,即应另寻原因(如语言习惯不同等),无法说明《左传》成书早于《论语》。胡念贻又以左氏每言鲁则称“我”,使臣聘鲁均言“来”等,断言《左传》必作于春秋末年之鲁国人,亦未必然。《史记》之各篇“世家”均言“我”、“来”,作者乃同一司马迁。多方面进行探索无疑是正确的,只是应当作客观全面的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