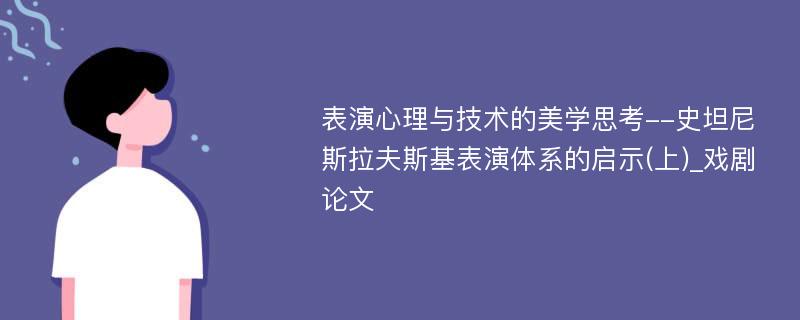
关于表演心理技术的美学思考——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的启示(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斯拉夫论文,斯基论文,美学论文,启示论文,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戏剧与音乐之间有着很多区别,但就二者都具有二度创作的性质来说,它们之间也有相通之处。在音乐表演艺术中,如能吸收戏剧表演——特别是心理技术方面的成果,应该是有益的。尽管精通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的人未必就是一个音乐表演家,而一个音乐表演专业工作者,如果能从戏剧表演理论方面丰富自己的修养,将会对音乐表演大有帮助。
一、表现派与体验派
表现派与体验派的争鸣,在推动表演美学的发展方面曾起了巨大的作用。 19 世纪表现派的代表是法国演员科克兰(Constant Coquelin1841—1916),他坚持演员主要依靠理智进行艺术创造的观点,他曾断言:在“最真实有力地表现感情的时候,他(按指演员)连这些感情的影子都不应当去感受”。他是以善于表演莫里哀、博马舍等人的喜剧而闻名的,他的理论看来也是建立在表演喜剧的经验基础之上的。德国史诗戏剧流派的创始人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 1898—1956)是表现派观点延续到20世纪的代表。他的《戏剧小工具篇》被称为《新诗学》,他称自己的史诗戏剧为“非亚里斯多德式戏剧”。布莱希特提倡“间离技术”,要求演员与角色保持一定心理距离,随时提醒观众:这是演戏。“间离的反映是这样一种反映:对象是人所周知的,但同时又把它表现为陌生的”。正如历史学家看待历史事件时保持着距离一样,“间离就是强调事件的历史性,就是把事件和个人表现为历史的、暂时的”。布莱希特并不绝对排除演员可能产生的感情体验,不过,在他看来,这属于“间离技术”所派生的现象。凡此种种表明,表现派强调的是表演艺术的假定性。值得注意的是:科克兰在《演员的双重人格》一书中就提出了第二自我必须始终处于“第一自我的监督之下,控制在事先考虑好并事先设计好的轨道之中”的看法,在这一方面来说,作为表现派的代表,科克兰也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先驱之一。
体验派以意大利演员萨尔维尼(Tommaso Salvini 1829—1916)为代表,他认为:演员在创造人物时,演员自己的感情与剧中人物的感情应该基本“合一”。“演员不仅要在研究角色的时候再一次体验自己的激动心情,而且在他每一次演出这个角色的时候,无论是第一次或第一千次,他都应该或多或少地去体验这种激动的心情”。这表明,体验派强调的是表演艺术的真实性。他是以表演莎士比亚的戏剧而闻名的,他的理论也是建立在表演莎士比亚的作品的经验基础之上的。他认为第一自我和第二自我并不是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而是一种“生活与表演的平衡”,他认为演员过着“双重生活”,也就有着双重的自我,生活中的我即第一自我,表演中的我即第二自我,与角色基本“合一”的“自我”属于第二自我,第二自我要进入“忘我”的感情境界,体现艺术的真实性;演员自己那个“自我”属于第一自我,第一自我要保持“有我”的理智状态,知道自己在表演,也就是说,体现艺术的假定性。“生活与表演的平衡”也就是第一自我与第二自我的平衡。实质上,这已经承认了戏剧艺术中真实性与假定性的两重性。斯坦尼斯拉夫斯基(Stanislavsky 1863—1938)是20世纪体验派的代表, 他对这种“平衡”曾有过一个理解过程,在《戏剧》(斯坦尼斯拉夫斯全集,以下简称“全集”卷五548—549页)中他写道:“这就象站在刀尖上一样,很不容易,……当你做戏的时候,就不可能体验。……你身上的观众将战胜创造者”。后来,在写《演员自我修养》时,就改变了看法:“演员用心灵的一半完全进入最高任务,贯串动作、潜台词、视象、自我感觉诸元素线,而另一半,他又以……心理技术来过着生活……演员在创作时是过着双重生活的……双重性并不妨碍灵感。恰恰相反!它们是相辅相成的”。他说的这个“另一半”即演员的心理技术,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重要贡献。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晚期正是集中了表现派与体验派各自所积累的合理经验才最终建立起自己的表演体系的。本文主要就是探讨斯氏心理技术的研究成果对音乐表演美学所具有的借鉴意义。
空白、程式化、静止
无论是表现派与体验派,都反对表演艺术中的“空白”、“程式化”和“静止”。
所谓音乐中的“空白”,就是音乐徒具形式而没有表达什么意义内涵的那种状态,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没有音乐的‘音乐’”。艺术家其实都忌讳这类“空白”,音乐表演者的二度创作也不例外。“如果演员不创造角色, 剧中会出现令人扫兴的脱离生活的空白点”(《1904 —1905年导演日记》全集卷五260页)。有些学生,只知照谱演奏, 至于作品什么含义,他根本不予考虑,这样的演奏,能够将大师的作品,也变得苍白而不知所云。学生限于修养,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样下去是不可能培养出真正的演奏家来的。
程式,它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在艺术实践中积累和凝定下来,成为比较规范化的、为观众欣赏习惯所理解的、能够表达一定意义的、具有“艺术语言”的约定俗成性质的东西。各种艺术都有自己的程式,这并不是什么坏东西。每种艺术都有人所共知的东西,否则,它就不能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又都要表现为“陌生化”,即创造成为新鲜的东西,否则,它就没有艺术价值。程式也需要具有人所共知与陌生化的双重性质,一旦缺少了创造性,成了纯粹的“程式化”,各种面孔都用刻板公式套来套去,就成了一种“俗套”。“要避免俗套(它会赶走生活),同时又要保留舞台程式”(全集卷五,《艺术手记》19页)。“‘程式化的’演出的经验……会破坏演员艺术中最重要的和最本质的东西,因为它们……以简单化的公式和假面来替换人的性格的多面性和复杂性”(同上,24页)。一个表演艺术家,不但不应该把贝多芬的作品演奏成柴可夫斯基式的,也不应该用一个模子去套贝多芬的不同作品。
如果,表演家认真地研究了作品,也有所发现,而又停止于第一次的发现,他也就停止了发展,“静止”于一定的点上了。同一位表演者的每次演奏又不可能是完全同样的反复,当一个人停止了创造性劳动的时候,他的表演将陷入一种“以重复和强化体操代替气质”(《1904—1905年导演日记》)的境地,而表演艺术的生命力,则正须要体现出活泼泼的创造精神。
二、从形式到内容
“即使是一个内行也很难在舞台上划清演员同作者在创作上的界限,很难判断诗人的创作于何处结束,演员的创造由何处开始”(《关于戏剧评论的札记》全集卷五505页)。一个尊重作者的表演者, 总是首先就要寻找作者创作的思维轨迹,甚至要追寻到作者思维的开始阶段,并且要以投入到这个轨迹中去,作为表演者“走进”作品的“入口”。
从形式上看,二度创作开始于对作品的阅读。在阅读过程中,作为读者的演奏者,接触的是具有物质属性的作品形式,作为读者的思维活动,发生的是从形式到内容、从外部语言到内部心灵、从体现(结果)来领悟体验(原因)的运动。当然,作为精神性质的内容,就寓于这个形式之中,但是,要想真正掌握作品内容,确实并非一件容易的事。
对同一首作品的不同演奏,可以相差很远,这个分歧是从阅读作品就开始了的。表演者首先是作品的接受者,对于即使是普通读者来说,接受也不纯粹是被动和消极的。“接受过程不是对作品的简单复制和还原,而是一种积极的、创造性的反作用”([德]姚斯《文学史作为文学科学的挑战》据瓦尔宁编《接受美学》143页)。
向作者靠拢
“梅特林克在写剧本前做过的一切,你们都要做到。唯有通过这条途径才能使你们接近作者”(《读《青鸟》后对剧团的讲话》全集卷五415页)。这不仅指要研究作者创作的历史背景等等,同时, 研究角色,向角色靠拢,也是向作者靠拢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演员不仅能创造他所创造的人物生活中已被作者提供并将在舞台上表演的那个片断,还能创造仅仅为角色个别台词隐约提过的被描绘人物从前的全部幕外生活。……整个一生”(《关于排戏和创造角色的札记》全集卷五593 页)。听老师们讲,上海越剧院的刘如曾先生五十年代在我院讲课,在谈到越剧院的艺术家们钻研剧本是何等认真的时候,就曾说过,仅是从他们为《梁山伯与祝英台》等剧本写出的一本一本的“角色自传”,就可以看出他们在艺术创造上下了多大的功夫!他们的演出所以使人百看不厌,和这种刻苦努力是分不开的。
隐在的读者
作者,不管是个人,还是集体(就如民间音乐的作者那样),不管本人是否意识到这一点,都是为一定的读者而创作的,就是说,都含有与读者对话、交流的性质,有时,这读者就是作者自己,这其实也就是以那些与作者自己类似的人作为读者。“在文学作品本文的写作过程中,作者的头脑里始终有一个隐在的读者,而写作过程便是向这个隐在的读者叙述故事并进行对话的过程,因此,读者的作用已经蕴含在本文的结构之中”([德]沃·伊瑟尔《隐在的读者》57页)。这意味着,读者在心理上愈接近作者心目中这个隐在的读者,也就愈能向作者靠拢。
文本与作品
在伊瑟尔的学说中,有两种区别特别值得注意。其一是:伊瑟尔认为“文本”的概念不等于“作品”的概念。当作品完成而尚未与读者(观众、听众)接触之前,它仅只作为“文本”而存在着,它尚未进入消费过程——观众(读者)的实际审美过程,尚未实现自己的意义。当审美主体将自己的审美经验注入文本之中时,它才成为审美对象,才作为真正实现了意义(进入消费了)的“作品”而存在。
含义与意义
其二是:“含义”不同于“意义”。“含义是示意的整体,它是由文本所包含的各个方面所暗示的,它必须在阅读过程中被集中。意义是读者对含义的消化,把它化为他自身的存在”([德]伊瑟尔《阅读活动》151页)。就是说,含义属于作者所创造的文本客体, 意义属于读者主体与文本客体相结合的产物。伊瑟尔就将文本看作“结构指示器”(同上9页)或“战略格局”(21页), 在阅读活动中发生着从含义到意义的转化运动。同一个文本客体,被不同的读者所阅读,其结果将建构出不同的“意义”。
限定与自由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曾经阐述过“生产决定消费”的观点,生产不仅生产出消费的一定内容和方式,也生产出一定的消费者,就像古典音乐、民间音乐、流行音乐、先锋派音乐都各自生产出自己的观众一样。那末,就应该是作品决定阅读,而不是阅读决定作品。表演者处理作品的自由,应该说,一方面是相对的、有限的——“读者只能在接受前提(作品)规定的范围内将作品现实化,读者的自由只能在作品的对象性范围之内活动,对作品的任何解释都只能是实现建立在作品的内容和结构之上的意义潜能”([德]瑙曼《社会——文学——阅读》)。因此,我们不应该给作品提出不根据作品本身的意义潜能的任意性解释。另一方面,这个自由又可能是巨大的,创造性的。“由于新的艺术技巧的运用,作品本文中包含的不确定性与空白逐渐增多,本文的意向也变得越来越含蓄、模糊,具有多义性,作品的现实化需要读者愈来愈深入的介入”。(伊瑟尔《隐在的读者》283页)。 于是才可能做到如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所说的:“往往作者写的是一回事,而演员所创造的要精彩得多,完全是另一回事,是作者所不敢奢望的。 (《1904 —1905年导演日记》)。这样的创造性发挥,不但不应受到责难,而且是应该加以提倡的。
视点与视境
凡是需要在时间中展开的艺术,接受者在刹那间,都只能接触到一定的共时性的局部——伊瑟尔就叫它“视点”,在历时性的过程中才能在头脑中积累起作品的其他部分——伊瑟尔就叫它“视境”。其中随时发生着“视点”向“视境”的转化。此时此刻是视点的东西,在下一瞬间就会转入视境。如果再次阅读或者作品本身就有“再现部”性质的段落,那么,曾经是“视境”的东西就会再转化为“视点”。在整个欣赏过程中存在着“视点”与“视境”的相互转化。
元素与贯串动作
历时性的东西是由共时性的东西的延续所构成的,另一方面,共时性的东西,又是由历时性的某些暂时的因素所集合而成的,二者本来互相渗透,只是为了讨论问题的方便,我们才把它们分别加以考察。
如果我们把视境看作一个母系统,那么,视点就是组成这一母系统的许多子系统,同时,视点这一子系统,又是由许多亚子系统(它们正是历时性的某些暂时的因素)组成的。这些亚子系统,斯氏就称之为“元素”。而历时性的“视境”,就被斯氏称为“种子”发展而成的“贯串动作”。不过,斯氏的“元素”概念,不仅用于分析剧中的角色,也用于分析演技训练,后者如:斯氏也把“想象”、“情绪记忆”、“肌肉松驰”、“注意”、“假设”、“信念”、“交流”、“适应”等等,称为“元素”,属于应该分别进行训练的演技。而前者则用于分析角色。因为无论是从共时性还是从历时性的角度来看,角色的相对整体都是由许多不同的元素构成的。
斯氏所说的形象思维中的基本“单位”,也就是一定的完形即“格什塔”,在多数情况下,“单位”即完形都是由若干元素构成的(虽然也不排除是由单一的元素构成的可能性),这些“单位”,正像系统论所阐述的一样,任何“完形”系统都具有如下的特点——整体决定局部,局部也决定整体。“在正确地造成了内部舞台自我感觉中,只要有一个元素不正确,它马上便会牵连到其余元素,使这些元素跟它一样不正确,从而破坏创作时必须具备的内心状态”(《演员自我修养》475页)。
研究一下斯氏关于排演卡·哥尔多尼的《女店主》所写的札记,是富有启示意义的。斯氏认为,正是在这个剧本中,他能最鲜明最令人信服地检阅“体系”的成果。
哥尔多尼的《女店主》,主要的戏剧发展线索是:聪明、美丽、乐观、善良而贫穷的女店主米兰多林娜周围有许多求爱者,一个是破落封建贵族第·福里波波里侯爵,一个是用金钱买得爵位的商人第·阿尔巴里奥里特伯爵,一个是骑士里巴夫拉达。女店主巧妙地戏弄了这些追求者,最后却选择了勤劳、诚实的仆人范布里奇奥作为她的终身伴侣。斯氏就扮演骑士的角色。
在1913年9月的排练后, 他的札记中写道:他“在角色中没有发现自我,反而丧失了自我”。晚些时候,他的手稿中又写道:在我们演员这里,几乎每一个角色都是从“最根深蒂固、陈腐不堪、渗入我们心中的刻板”开始的(全集第四卷531页)。
在1908年12月斯氏写给亚·阿·布洛克的信中,曾说到:艺术剧院创作史第二个十年(即1908年)的开始,标志着它的“新时期的开始”,“基于人的心理和生理本质的单纯而自然的基础的开始”。这一时期正是斯氏表演理论进入建立体系的重要时刻。按斯氏的看法,演员既要从作品中找到角色的元素,还要在自己身上找到角色的元素,才能顺利地进入创作过程。不过,斯氏所说的“在角色中感觉到自我,按其本来面目感觉到自己的天性”并不意味着角色身上的一切素质,演员都必须具有,事实上,这也是不可能的,而是说,角色的素质如与演员的个人素质和他积累的生活印象相适应,演员才能够实现具有真实感的体验,在这基础上,才谈得到:爱之愈切者,感情愈真,恨之愈透者,揭露愈深。对于反面的角色,就要如华·托波尔科夫所说的那样:给予“最有力的嘲笑和否定”。而简单的用刻板的公式往角色上一套,正是演员所要突破的“第一条死胡同”(斯氏语),这根本“套”不住角色,恰恰是套住了演员自己,因为这一公式仅仅是把活生生的经验抽象为类型的东西。人们可以轻易地列出一些“千人一面”的简单公式,诸如:某种人说话是“甜密密”的,另一种人说话是“冷冰冰”的,如此等等,它似乎是可以“对号入座”的“法宝”,其实,正由于它缺乏个性,也就到处就不适用。
之后不久,他写道:“为角色找到了两个元素。厚道和对婆娘的厌恶感(《关于排戏和创造角色的札记》全集卷五590页)。
1914年3月7日以后的札记,写于该剧已经正式上演第十五场之后:“例如骑士一角。我进入的是严肃的总督的形象(这一点角色身上是有的)[按:圆括号中的话是斯氏写的,下同]。符拉基米尔·伊凡诺维奇发现的是快乐的骑兵少尉(有)。贝奴阿坚持仁慈宽厚(有)。也有人倾向于塑造个钟情的中学生(有一点儿)……”
斯氏创造的骑士角色究竟形成了怎样一种由种子发展而成的贯串动作,可以由诸多评论中看出:“骑士常常被演成吵吵嚷嚷的大老粗……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则塑造了一个高尚、头脑简单但可爱的人物——从他对女店主的钟情上说是个大孩子——的有趣形象”(1914年第2807期《演剧季新闻》雅·利沃夫的文章);“骑士从一个外表虽然严肃但心肠慈善、无畏、安静的人渐渐变成热烈得如痴如醉。整个内在风貌的这一转变,这一渐变,我们是目睹了的,同时几乎觉察不出这种变化,因为这个转变几乎就象生活本身。不存在表演,只有实实在在的体验,实实在在的在激情影响下的内心变化。而且很难说骑士在转变的当儿是在哪种场合更好一些,是在他傲慢而不可接近的场合,还是在他享受到他同米兰多林娜之间突然产生的亲密关系时,他跟她一起嘲笑侯爵的场合,还是在继续回味米兰多林娜的温馨,因而对其他女人的纠缠感到屈辱的场合,或者最后当他的爱情已不能自制的场合。很难说这是‘完美地扮演角色’,因为每时每刻这都不象是角色。”(1914年2月4日《俄罗斯通报》伊·伊格纳托夫的文章)。
斯氏要求演员必须具有美学分析的能力和了解写作技巧,我认为这是很有见地的,这决不是对于表演者的苛求。“演员应当善于掌握角色,利用它达到自己的创造目的,犹如机械师使用机器一样。为此不仅要十分熟悉剧本的构造,而且要了解写作技巧。机械师学习操纵机器时,为了研究它的各个部件及其性能,他要拆卸机器,然后再把它的各个组成部分装配起来,对每个部件既能分别地又能整体地来进行研究”(《关于演剧艺术的札记》全集518页)。 关于“机器”的说法只是个比喻,其精神实质是可以理解的,就是要求对于作品的局部和整体都要达到比较透彻的了解。
以演奏贝多芬《热情奏鸣曲》第一乐章为例,演员不仅要确切地掌握乐曲的结构,而且要能理解和感觉到局部的“格式塔”的含义。在主部主题中,我们遇到了至少四个元素:首先是低音区、弱奏的分解小三和弦的旋律线,属于低沉的悲怆性元素;立即转入带颤音的同音反复加级进的朗诵性音调,是一个内心倾诉式的元素;前两个元素都是抒情性的,第三个元素则发生了性质上的跳跃,它是一个:三个音的同音反复加一个下行三度的所谓“命运”动机,是一个搏斗性质的元素;而后面紧跟又是新的元素出现:它是一个渐强式的快速上下翻滚的分解小和弦式的“走句”式音调,所谓“热情”倾泻式的元素。这四个元素构成的视点,包含着多少对于令人压抑的现实生活的复杂的感触!这就是演员开始进入艺术创造的客观起点。
连接部除再次肯定主部出现的元素之外,增加了呼喊性的战斗性质的元素。副部主题,更具声乐性质,明朗的歌唱性中隐约包含了《马赛曲》的音调(正如罗曼罗兰所发现的),暗示着作者的理想、期望与法国革命的联系。但是在第二次陈述时,旋律“化开”了,不清晰了,逐渐转向半音阶式的连接部分,逐步失去了明确的性质,趋向于“犹豫”不定的求索中的彷徨。结束部又趋向于激动、坚决、恢复信念和愤怒敲击式的元素的复合性质。
发展部分四步依次展开:主部第一动机的元素;加上激动的震音元素;连接部的呼喊性音调;副部主题的强有力的展开,掀起战斗的高潮。经过统一调性的再现部,结尾部又重新掀起一个短暂的高潮,却又以主部主题第一元素的渐弱、消失而暂停于一个战斗的间隙。
以上只是给第一乐章这棵“大树”的“树干”顶多也包括到“树枝”,作了简单的描述。这种音乐中的以“元素”构成共时性的集合,通过历时性的发展而构成“贯串动作”的发展过程,难道不是与戏剧中的元素与贯串动作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相似性或者称为逻辑关联吗?(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