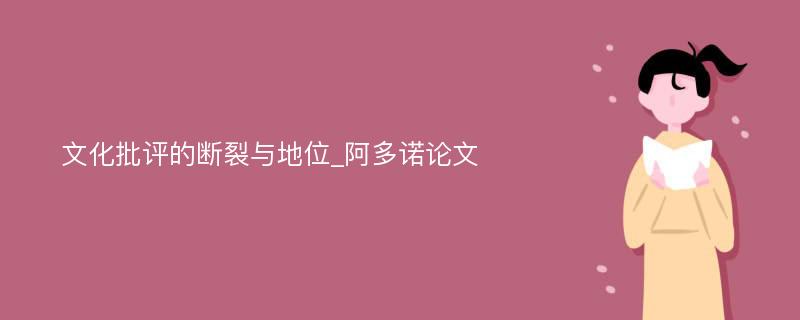
文化批评的破与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批评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16)01-0075-09 阿多诺(Theodor W.Adorno)的《文化批评与社会》(“Cultural Criticism and Society”)写于1949年,首次发表于1951年①,后被作者收入《棱镜集》(Prisms,1955)一书中,置于全书之首。1981年,美国西北大学的韦伯夫妇(Samuel and Shierry Weber)把该书译成英文,遂在英语世界产生了较大反响。但时至今日,此文或此书还没有中译本。 《文化批评与社会》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此文写于阿多诺由美返德的一个转折点上,其中携带着他对纳粹德国的诸多思考,而文化、文化批评则是他进入德国问题的突破口。更重要的是,此文在结尾部分写出了那句此后引起诸多误解和广泛争议的名言——“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Nach Auschwitz ein Gedicht zu schreiben,ist barbarisch/To write poetry after Auschwitz is barbaric),此谓“奥斯威辛之后”命题,从而也把阿多诺推到了文化/文学论争的风口浪尖上。那么,究竟该如何理解这篇文章?又该如何把这句名言还原到此文的具体语境和写作此文的历史语境之中,对其进行贴近阿多诺原意的解读?所有这些,将是笔者写作本文的主要意图。 1949年年底,阿多诺结束了在美国的流亡生涯,返回联邦德国。还在战争刚结束时,流亡美国的文坛领袖托马斯·曼(Thomas Mann)便在德国的《巴伐利亚州报》上发表了一篇《谈德国责任问题》的文章。此文因为其中的一个观点——德国人对纳粹暴行负有一定的集体责任——而引发了一场论战,史称“托马斯·曼风波”。反对托马斯·曼的人主要有莫洛(Walter von Molo)和蒂斯(Frank Thiess)等作家,他们为自己在纳粹统治期间的默默抵抗而辩护,蒂斯更是把他们这些人的所作所为视为一种“内心流亡”(inner emigration)②,进而指责那些真正的流亡者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这种回应激起了托马斯·曼的愤怒,他不无偏激地还击道:“凡从1933年至1945年能在德国出版的书籍,比毫无价值还无价值,总之不堪沾手。它们散发着血腥味,寡廉鲜耻,应当统统地销毁,捣烂,打成纸浆。”③显然,这场风波并非一般的意气之争,而是隐含着两类德国知识分子(“滞留国内”与“流亡国外”)互不信任的敌对情绪,呈现着两种流亡方式(“真正的流亡”和“内心流亡”)孰是孰非的重大分歧。正是出于这一原因,托马斯·曼最终并未返回西德或东德,而是选择了在瑞士定居(1952年)。但他的忘年交阿多诺却在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的召唤下返回了当时的西德。 因此,联邦德国并没有敞开怀抱热情欢迎这些流亡知识分子的归来,恰恰相反,冷淡、疏远、心存芥蒂甚至隐隐的敌意才是知识界对待他们的基本表情。回到德国的阿多诺自然也遭到了这种冷遇,与此同时,他又意识到一种极不正常的氛围弥漫在整个社会之中——各阶层的人们都讳言罪责。于是,在给托马斯·曼的一封信中,他如此描述了自己当时的感受:纽伦堡审判(Nuremberg Trials)之后,德国人的“难以启齿之罪”(unspeakable guilt)似乎也随之“蒸发”了。在战败的德国,很难发现有任何纳粹。不仅没有人坦白承认他是纳粹,而且德国人相信“没有一个人曾经是过……我注意到所有认同希特勒主义或新近具有国家主义色彩的那些人都坚定地宣称,他们对整个战争期间所发生的最坏的事情一无所知——然而,那些有意反对的人却证实了最平庸的智力所告诉我们的东西:那就是自1943年以来,所有的事情都是常识。”④阿多诺的这种感受是非常准确的,因为斯坦纳(George Steiner)在写于1959年的一篇文章(《空洞的奇迹》)中也特别指出了这一事实。在他看来,战争结束后的最初三年里,许多德国人还能以现实主义的眼光客观审视希特勒时代的屠杀与肆虐。然而,从1948年开始,却出现了一个新的神话:“上百万的德国人开始对自己和容易轻信别人的外国人说,过去那段历史其实根本就没有发生,那些恐惧是被同盟国的宣传和喜欢编造轰动事件的记者恶意夸大。不错,确实存在些集中营,据说是有许多犹太人和其他一些不幸儿被灭绝。‘但不是六百万,亲爱的朋友们,根本没有死那么多人。你知道,那都是传媒的宣传。’”于是,“各行各业的德国人开始宣称,他们对纳粹政权的暴行一无所知”,而“‘让我们遗忘’成了德国新时代的祈祷文。即便有些人无法遗忘,他们也力劝他人遗忘。”因为只有遗忘、忽略或佯装对那段历史概不知情,人们才能继续生活⑤。由此看来,阿多诺所返回的德国并不是一个牢记着自己罪与耻的国度,那时的德国人已开始习惯否认和遗忘,并试图与那段历史划清界线。 与此同时,战后的重建工作也在德国紧锣密鼓地进行着。然而,在阿多诺看来,其他方面的重建相对容易,文化的重建却难乎其难。因为早在1944年,他就对所谓的文化重建深表怀疑:“这场战争之后生活将‘正常’继续,甚而至于文化也能被‘重建’(rebuilt)——好像文化重建已不是对它加以否定——这种想法是愚蠢的。数百万犹太人已被谋杀,而这却被看作一个插曲,且与大屠杀本身毫无关系。这种文化还有什么好等待的?即便无数的民众还有时间等待,难道可以想象发生在欧洲的这一切将没有任何结果,遇难者的数量也将难以转变成整体野蛮之社会的新质量(new quality)吗?”⑥而阿多诺之所以认为不经过否定的文化重建无法进行,关键在于在他看来,纳粹发动的这场战争以及他们灭绝犹太人的行动已充分证明了文化的失败。而文化一旦失败,它将变得理屈词穷,因为“迄今为止已然失败的文化并不能为它的继续失败提供正当理由,就像童话里的那个姑娘不能用储藏的精面粉撒在流满啤酒的地方。”⑦如此看来,文化重建对于阿多诺来说基本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因为道理很简单,文化不能像战后的建筑物一样可以推倒重来,它必须以先前的文化为基础。但先前的文化又问题重重,已成失败的赝品。如果重建是在已经失败的文化上展开,那无异于错上加错。 阿多诺正是带着这样一种对文化的“前理解”返回德国的,而德国人遗忘历史、否认屠杀的景象也让阿多诺感到极为震惊。在这种现实语境的逼迫下,阿多诺准备出手了。而对于他这次的出手,阿多诺的传记作者德特勒夫·克劳森(Detlev Claussen)是这样描述的:当时德国人在战后想回到正常状态的心情非常迫切,但因为太迫切了反而不能如愿以偿。面对这种局面,阿多诺则扮演着一个信使的角色,只不过他带来的并非好音信,而是不折不扣的坏消息。作于1949年的《文化批评与社会》便是阿多诺进入“后纳粹德国”(post-Nazi Germany)的入场券⑧。既然是入场券,便意味着这是阿多诺在阔别德国知识界多年之后的首次亮相,也意味着他带来的“坏消息”必须足够振聋发聩,这样才能引起德国知识界的高度重视。而从此文的效果史来看,阿多诺显然达到了这一目的。 那么,阿多诺带来的又是怎样的“坏消息”呢?当然首先是文化批评所存在的种种问题。但文化批评的问题仅仅是“果”,文化本身的问题才是“因”。而由于文化问题又是被这个社会整合之下与精神一道沉沦的产物,所以,文化又与社会、精神紧密地纠缠在一起,组成了一系列的问题链。于是,要想理解阿多诺所谓的文化批评,必须首先理解他对文化的批判。 在阿多诺的心目中,文化首先是一个很成问题的概念。而之所以成问题,一方面来自于它对既定传统的因袭,一方面也意味着它被管理起来之后早已变形走样。马丁·杰伊(Martin Jay)曾经指出:“在那篇置于文集之首的纲领性文章——《文化批评与社会》中,阿多诺延续了1930年代‘研究所’对‘肯定性文化’(affirmative culture)——此谓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的命名——的抨击。他坚决反对把高雅文化当作凌驾于物质利益之上的偶像加以崇拜。”⑨如此看来,阿多诺在这里虽然避开了“肯定性文化”和“高雅文化”等等表达,但他所谓的文化实际上又与“肯定性文化”或“高雅文化”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对于“肯定性文化”,马尔库塞早在1937年就做过界定。在他看来,文化这一概念除了狭义的用法外,还有一种广义的用法。后者把文化看作一种具有独立自足性的精神王国,这样它便与“文明”(物质再生产领域)区分了开来。而所谓的“肯定性文化”便是在这种用法的基础上所指认的一种文化形式,它是资产阶级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的产物。马尔库塞在分析这种文化所存在的问题时特别指出:“对孤立的个体的需求来说,它反映了普遍的人性;对肉体的痛苦来说,它反映着灵魂的美;对外在的束缚来说,它反映着内在的自由;对赤裸裸的利己主义(egoism)来说,它反映着美德王国的义务。在新社会蓬勃兴起的时代,所有这些观念因其指向对生存的既有组织的超越,它们具有了一种进步的特征;而一旦资产阶级统治开始稳固之后,它们就越来越效力于压制不满的大众,越来越效力于纯为自我满足的提升。它们隐藏着对个体的身心残害。”⑩由此看来,在马尔库塞的论证中,“肯定性文化”主要被分析出来的是一种负面的价值。 尽管传统意义上的“肯定性文化”并非阿多诺谈论的重点,但他的批判显然是从这一逻辑起点开始的。因为根据他的描述,我们看到“文化发端于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彻底分离。正是从这种分离(似乎也可以说是原罪)中文化才汲取了自己的力量”(11)。但是,在随后的发展中,它又经历了一个中立化和物化的过程。而按照阿多诺在《文化与管理》(“Cultrue and Administration”)一文中的说法:“中立化的过程——文化转变为某种独立的和外在的东西,脱离了与任何可能的实践的关系——使得文化有可能被整合进那个它从中不知疲倦地纯化自己的组织之中。”(12)由此看来,文化的中立化实际上就是文化远离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并把自己进一步打造得冰清玉洁的过程。而这种远离和打造,又让文化耗尽了自己的潜力,从而也让它与真正的艺术和哲学有了明显的区分。“因为值得信赖的艺术作品和真正的哲学,按照它们的实际含义,都不曾单独在自身内部、在其自在的存在(being-in-itself)中耗尽自己”,它们还能对自由的实现做出某种承诺。但文化却是另一番景象: 假如文化依靠着五迷三道的现实(bewitched reality)存在,并最终依靠控制他人的劳动成果存在,文化对自由的承诺就依然是含糊且可疑的。整个欧洲文化——抵达消费者那里的文化,如今已由管理者和心理技术员为全部人口量身定做的文化——退化为纯粹的意识形态,起因于文化的物质实践功能所发生的变化:它放弃了干预(interference)。(13) 退化为意识形态意味着文化已成“虚假意识”,放弃了干预又意味着文化可以自视清高,超然物外,可以对现实世界的杀戮与灾难不闻不问,三缄其口。在阿多诺看来,这样一种文化本来就存在着先天不足(阿多诺把它形容为“文化的阉割或去势”(the emasculation of culture(14))),而在一个越来越被管理起来的社会里,它又进一步被物化了。大体而言,这种物化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文化的商业化和文化的官方化。 文化的商业化显然更多延续了《启蒙辩证法》中的思路,这不仅是因为阿多诺在开篇不久便提到了他与霍克海默发明过的术语——文化工业(culture industry),而且也因为此文多处回响着《启蒙辩证法》的声音。区别只在于,如果说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谈到的文化工业更多面对的是美国的大众文化,那么他在《文化批评与社会》中却不得不直面德国乃至整个欧洲的文化问题了。阿多诺认为:“在整个自由主义时代,文化跌落到了流通领域之中。因此,这一领域的逐渐凋敝也击中了文化的要害。随着企业中精于计算的分配机器消除了交易与其不合逻辑的漏洞,文化的商业化也在荒诞中达到顶点。完全被征服被管理之后,在某种意义上彻底‘被养殖’(cultivated)之后,文化已经灭绝了。”(15)当然,灭绝的只是阿多诺心目中的那种具有否定性和干预性的文化,而兴盛起来的则是被“置于市场意志之下”的文化,把外来文化“作为稀有之物进行投资”的文化。当这种已被贬值为“文化商品”(cultural goods)的文化还要寻求所谓的“文化价值”(cultural values)时,它也就彻底断送了自己的声名(16)。 文化的官方化并非阿多诺的明确表达,但我以为这一思路贯穿在整篇文章的始终,其批判的力度甚至远远超过了他对文化商品化的抨击。阿多诺认为存在着“两种类型的极权主义政体(totalitarian regimes)”(17),其中的一种自然是指纳粹德国的法西斯主义,而另一种则应该指的是苏联的社会主义(18)。两种政体的共同特点,一是“军营式的严格管制(regimentation)”,二是“整体之网(the network of the whole)”拉得越来越紧(19)。而在严格管制中,在所有的一切都要归并到一个整体的过程中,个体意识被预先塑形而失去了逃避的空间,新闻自由变成了发布谎言和发作兽性的掩护,文化批评被整合掉“批评”,而只剩下了所谓的“文化”。在谈到这一现象时,阿多诺特别指出: 当德国法西斯分子诽谤批评这个词语并用空洞的“艺术欣赏”(art appreciation)概念取代它的时候,他们只是被这个专制国家的粗野利益引导着如此操作,而这个国家面对鲁莽的新闻记者依然惧怕波萨侯爵(Marquis Posa)的那种激情。但是,这种叫喊着要废除批评、追求自我满足的文化野蛮行为,这种野蛮部落入侵精神保护区的行为,并没有意识到回报它的是以牙还牙(repaid kind in kind)。……法西斯分子除了像批评家那样天真地信任文化本身并屈从于这种信任之外,他们还把文化简化为一种典礼般的盛大景象(pomp),并认可了精神这个庞然大物。他们把自己看作文化的医生,并认为自己能够从文化身上拔掉批评之刺。因此,他们不仅把文化降低到官方的层面上,而且除此之外,他们还无法认识到文化与批评无论好坏,二者都是相互缠绕在一起的。(20) 这里提到的波萨侯爵是席勒历史悲剧《唐·卡洛斯》(Don Carlos,1785)中的人物。面对专制国王菲利普二世,波萨侯爵曾把自由提到一种自然人性的高度,发出了“请您允许思想自由”的呼吁(21)。然而,现实世界的专制国家面对记者要求自由的呼声,却依然害怕得要命。于是那些文化官员一方面会用武力去围剿那种敢于犯上作乱、兴师问罪的文化(阿多诺曾引用希特勒帝国文化议院发言人的话说:“一听到‘文化’这个词,我就伸手抓起了自己的枪。”(22));另一方面,他们又通过对文化的无害化处理(拔掉批评之刺),把文化绑在“政治美学化”的战车上,让它去妆点官方的门面,让它为权力歌功颂德。只要想想里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所导演的纪录片《意志的胜利》(Triumpf des Willens,1935)和《奥林匹亚》(Olympia,1938)等文化产品,我们便会意识到这个时候的文化究竟扮演着什么角色了。 弄清楚阿多诺所谈的文化究竟是怎样一种文化之后,我们也就能理解为什么他要对文化批评痛下杀手了。如果在英国的批评传统中谈论文化批评,我们可能马上会想到阿诺德(Matthew Arnold)、利维斯(Frank R.Leavis),然后再想到伯明翰学派所开创的文化研究。想到前者,意味着文化批评是从精英主义立场出发而对文化(尤其是大众文化)进行的批判;想到后者,则意味着文化批评更是从平民主义视角出发而对文化进行的分析。而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文化批评都应该是对文化(甚至是对社会、政治等等)现象的批评。然而,被阿多诺押上审判台的文化批评却并非如此。《文化批评与社会》一开篇便这样写道:“对于任何一个习惯于用其耳朵思考的人来说,复合词‘文化批评’(Kulturkritik/cultural criticism)肯定是一种令人讨厌的铃声,不仅仅是因为像‘汽车’(automobile)那样,它是由拉丁语与希腊语拼凑而成的。这个复合词使人想到了一种明目张胆且声名狼藉的矛盾。”(23)为什么文化批评矛盾重重、名声不佳呢?理查德·沃林(Richard Wolin)对此曾有过如下解释: 阿多诺发现“文化批评”天生就是一个很成问题的术语。他的怀疑与德国语境的特殊性有关。Kulturkritik(文化批评)这个术语会让人想起学究们的价值观,也就是像托马斯·曼在1916年的小册子中描述的那种“不谙时政者”(unpolitical man)的价值观。正因为如此,它的言外之意主要涉及臭名昭著的“文化与文明”(Kultur/Zivilisation)的二分法:亦即涉及到德国把自己当作一个“文化民族”(Kulturnation)的自我理解,而这种理解又与英、法、美西方各国那种没有灵魂、利欲熏心的商业精神截然对立。这样,在德语的意义上,文化批评与那种从虚无缥缈的“文化”立场出发形成的批评(即对生活中一切庸俗与卑鄙之事、“文化之敌”的批评)相比,就较少具有“对文化的批评”(criticism of culture)的意味,由此也暴露出后者的缺陷和不足,等等。(24) 在这里,沃林对“文化与文明”二分法的解释与我在前面所引的马尔库塞的解释是基本一致的,即文化更多是德国人在精神层面对自己民族国家的一种想象,而文明则主要涉及物质生产和再生产,更多与西方其他国家的商业主义进程形成了一种关联。因而,在沃林的解释中,文化批评的矛盾首先体现在它所隐含的“文化”与“文明”的二元对立上。而按照阿多诺的思路,更重要的矛盾还在于:首先,虽然“文化批评最最崇拜的还是文化这一概念本身”,但这种文化恰恰又缺少文化(25)。其次,当文化变成一种意识形态(亦即虚假意识)时,文化批评也难逃其咎,因为正是它的参与,文化才成为一种被设计出来的谎言。在《文化批评与社会》中,阿多诺虽触及到了这一问题,但并未完全展开。倒是他写于1944年的《孩子与洗澡水》一节内容反而说得更加清楚:“在文化批评的种种主题中,确立时间最长和最重要的主题是这样一种谎言:文化制造了一种与不存在的人类相匹配的社会幻觉;它隐藏了产生出所有人类作品的物质条件;而且通过安慰和哄骗,它也足以使糟糕的经济决定的存在保持生机。这就是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概念,乍一看来,它似乎既与资产阶级的暴力学说相一致,又与其对手尼采与马克思的思想相吻合。但恰恰是这一概念像所有有关谎言的忠告那样,本身具有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可疑趋向。可以在私人层面看到这种趋向。金钱思维及其伴随的冲突已不屈不挠地发展到最温柔的性爱领域,延伸到最崇高的精神关系之中。”(26)在这段论述中,阿多诺再明白不过地指出了文化的谎言色彩:文化脱离了物质生产条件,最终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幻象。这应该看作文化批评的“功劳”之一。 再次,文化批评已经与文化形成了一种共谋关系,而这种共谋主要体现在,当文化商业化时,文化批评及文化批评家扮演着运输代理商(traffic agents)和估价信息收集者(appraising collector)的角色:“大体而言,文化批评会让人想起讨价还价的姿态,想起专家质疑一幅画的真实性或把它归到某大师次要作品一类中的情景。人们贬低一件东西是为了得到更多的东西。当文化批评家进行估价时,他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地卷入到一个被‘文化价值’玷污的领域,甚至当他对文化的抵押咆哮如雷时也是如此。他在文化面前做沉思状也必然包含着仔细观察、全面调查、权衡轻重、做出选择:这件东西适合他,那件东西他拒绝。”(27)另一方面,当文化官方化时,文化批评又成了体制的维护者,而这种维护又是通过已经变异的精神现象完成的。阿多诺指出,在一个全面管制的社会里,精神现象也会刻上社会秩序的标记:“它们可能会以娱乐或教化的面目出现,直接有助于那个体制的万古长存;同时恰恰由于其特性在社会上预先形成,它们也很乐意成为体制的鼓吹者。这就仿佛是被众所周知的《好管家》(Good Housekeeping,旧译为《家政》)‘批准’盖章后,它们巧妙地获得了一种退化的意识,然后再以‘自然而然的’(natural)样子出场,并允许自己认同于诸种权力。”而由于“文化批评依托经济体制而存在,无论其内容如何,它都卷入到了那种体制的命运之中”(28),所以,文化批评也就间接地成为了这种体制的吹鼓手。这里需要稍作解释的是,《好管家》是美国的一家老牌女性杂志(创办于1885年),而由于该杂志刊发有关产品测试的内容,所以它也以“好管家印章”(Good Housekeeping Seal)和“好管家批准印章”(Good Housekeeping Seal of Approval)而知名于世。这也意味着,只要是通过《好管家》测试认可的产品,它也就获得了“产品质量许可证”。通过这一类比,阿多诺强调了精神现象在其退化的过程如何获得了质量可靠的检测。换句话说,当文化批评面对这种盖过戳的精神现象时,它已可以大放其心,而不需要承担失察、失职等等风险了。 大体而言,这就是阿多诺所呈现出来的文化与文化批评的种种问题。而由于此文像他的其他著作文章一样,依然呈现的是一种齐头并进、密不透风、机锋暗藏、碎片写作(fragmentary writing)的话语风格,所以我的这种拆分、归类和解读已不可避免地简化了阿多诺的思想。如果再把这种思想通俗化地稍作总结,可以说阿多诺眼中的文化是旧罪(原罪)既未去,新罪又加身,它早已成为许多人(包括文化批评家在内)浑然不觉但实际上又非常可疑的东西。文化批评则守着问题多多的文化,扮演着美容师的角色——粉饰现实,美化社会。而精神(我并没有拿出更多的篇幅来探讨阿多诺的这个概念)一方面“在摆脱开封建神学监护的同时,它已在这个现状中分不清是谁的影响下日益陷落”(29);另一方面,当文化批评最终接管了精神之后,它又干起了倒卖精神的勾当。正是在这一语境中,阿多诺才指出了一个令人痛心的事实:“文化批评一旦越出它与物质生活状况的辩证逻辑而扭曲了精神,它就会毫不含糊和直截了当地抓住精神,把它当作宿命原则(the principle of fatality),并因此廉价出售精神自身的反抗。”(30)于是,像失败的文化那样,精神也彻底失败了。虽然精神还具有反思能力,但这种反思也依然于事无补。因为“甚至精神单靠自己的失败所进行的最彻底的反思也局限在这样一个事实里:它仅仅停留在反思层面,却没有改变证明其失败的存在。”(31)而最终的景象是,当生活、文化、精神和文化批评都被物化或成为一种“物化的意识形态”之后,这个世界已经变得相当恐怖了。因为物化的意识形态被阿多诺形容成了“一种死人的面模(death mask)”(32)。 那么,有什么办法能改变这种局面呢?阿多诺在指出了种种问题之后自然也亮出了他的拯救方案:让“对所有物化毫不妥协”的辩证法去穿透那个“凶险的、被整合成整体的社会”(33);让内在批评(immanent criticism)去“分析智识现象与艺术现象的形式和意义”,从而“努力抓住它们的客观理念与其借口之间的矛盾”(34);让文化的否定性(negativity of culture)去揭示“认识的真实或虚假,思想的重要或残缺,结构的紧凑或松散,修辞手法的结实与空洞”(35)。通过这番武装,阿多诺对批评家与文化批评就都提出了新的要求:“文化辩证批评家必须既参与到文化之中,又游离到文化之外。”(36)而“批评的任务绝不是去寻找被分配到特定利益集团那里的文化现象,而更是去破译那些体现在这些现象中的社会趋势……文化批评必须成为社会的观相术。”(37) 很显然,让文化批评成为社会的观相术意味着对现有文化批评的大力改造。而改造既是一种清理——清理文化批评与负罪的文化、假面的社会所形成的暧昧关系;也是要为它输入新鲜血液——让辩证法、否定性和内在批评成为文化批评的动力。如此这般之后,它才能戳穿社会之物化、文化之野蛮、意识形态之虚假的伪装,成为文化批评家手中批判的武器。在“这个世界正在变成一座露天监狱(open-air prison)”(38)的残酷现实中,阿多诺这种带有乌托邦色彩的拯救无疑显露出一种理想主义的微光,从而也接通了本雅明的那句名言:“只是因为有了那些不抱希望的人,我们才获得了希望。”(39) 较为详细地梳理与分析了《文化批评与社会》的基本思路之后,我们便可面对结尾部分的那句名言了。这句名言的上下文如下: 一个社会的极权程度越高,精神的物化程度就越严重,而精神单靠自己逃离其物化的尝试也就越自相矛盾。就连最极端的末日意识也有沦为茶余饭后之闲谈的危险。文化批评发现自己面临着文化与野蛮之辩证法的最后阶段。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甚至侵蚀到这样一种认识:为什么写诗在今天已变得不可能了。绝对的物化曾把智识进步预设为自己的要素之一,如今却有吸收整个精神的架势。如果批判精神(critical mind)将自己局限于自我满足的沉思之中,它就无法应对这种挑战。(40) 在这段文字中,“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是单独冒出来的一个句子,显得非常突兀,因为这段文字乃至整篇文章并未涉及任何诗歌写作的问题,也未提及奥斯威辛。但为什么阿多诺会让这个句子孤零零地出现在这里呢?而且,进一步追问,这个句子与其他句子是什么关系?为什么说社会的极权程度与精神物化呈正比?什么是文化与野蛮的辩证法?文化批评究竟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实际上,结合《文化批评与社会》全文的语境,这段文字以及这句名言并非很难理解,但由于许多反驳者并不面对此文的语境而只是就事论事,误解也就由此产生了。因此,我们也有必要在这里略作分析。 如前所述,阿多诺在此文中谈到了两种极权主义体制,而阿多诺从卢卡奇那里继承过来的物化(reification)也频频在这篇文章中亮相。根据杰姆逊(Fredric R.Jameson)的解释:“物化指的是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转化成为物或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即卡莱尔(Carlyle)所说的‘现金交易关系’,把社会现实转化成交换价值和商品。”(41)这种说法更适合解释一种普遍的社会状况与生活状况,而在精神层面,我们更应该把物化理解为一种人的心灵世界的简单化、粗鄙化、动物化和野蛮化,它接通的是马克思所谓的“异化”(alienation)。而一旦社会被极权主义接管,一方面意味着生活世界的全面物化,一方面又意味着精神世界的整体异化。在这样一个世界中,由于所有的东西都处在盘根错节的物化关系之中,所以精神单凭自己的一己之力是无法改变现状的,它想摆脱物化、洁身自好的努力也像抓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那样变得难乎其难。 那么,什么又是“文化与野蛮的辩证法”呢?这时候,我们不应该忘记阿多诺是一位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就是说,当阿多诺还没有大力修正黑格尔的“辩证法”时,他一般是在黑格尔所呈现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的,即对象自身具有一种矛盾性。于是,文化与野蛮的辩证法也就意味着文化与野蛮的相互缠绕和对立统一。通俗地说,也就是文化中包含着野蛮因素,野蛮中渗透着文化内涵,二者相互交融,彼此依靠,形成了一个奇怪的矛盾统一体。验之于阿多诺在整篇文章中所谴责的文化,文化确实已不成体统。而这里所谓的野蛮也绝不只是一种修辞手法,它更应该指的是一种非人性的状态。因为早在写作《启蒙辩证法》的时候,阿多诺与霍克海默研究的逻辑起点便是要探讨“为什么人类没有进入真正的合乎人性的状态,反而陷入到一种新的野蛮之中。”(42)从此往后,人性状态的对立面——野蛮或野蛮状态,就成为阿多诺的一个固定表达,并在其著作文章中频繁出现(例如,在《最低限度的道德》一书中,阿多诺使用“barbaric”与“barbarism”的地方约达35次之多)。当他在《文化批评与社会》的结尾处使用这一表达时,一方面接通了《启蒙辩证法》的思路,另一方面也已在此文中做了许多铺垫(据我统计,野蛮一词在文中出现过六次),所以无论从哪方面看,“文化与野蛮的辩证法”都并不显得突兀。而所谓的“最后阶段”,则是指出了这一形势的严峻。因为一旦在“合题”阶段生效之后,这种情景就成了生活的常态,也成了合理的存在。因此,文化批评面临着一个危急关头,或者面临着本雅明所谓的“紧急状态”(state of emergency)(43)。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阿多诺说出了那个著名的句子:“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阿多诺的学生蒂德曼(Rolf Tiedemann)曾解释说:“在阿多诺的这个句子中,‘写诗’是一种提喻法(synecdoche);它代表着艺术本身,并最终代表着整个文化。”(44)从阿多诺全文的逻辑走向上看,这种解释是可以成立的。也就是说,阿多诺通篇都在谈文化(偶尔涉及艺术问题),当谈到高潮部分时,他便以局部代整体,亮出了提喻这把杀手锏,从而进一步指出奥斯威辛之后艺术创作的不可能性与文化的非正义性。进一步思考,我们甚至可以把阿多诺的这句表达理解为一种话语策略,即为了呈现文化问题的严重性,他用一个提喻把这种严重性推向了极致:当文化已经充分野蛮化之后,以文化的名义所进行的艺术创作或艺术创作所呈现出来的文化内容也很难逃脱野蛮的魔掌。尤其是当艺术“为了美化这个社会”而“肯定着和谐原则(principle of harmony)的有效性”(45)时,它也就成了文化的同谋。这样一种艺术当然是野蛮的。 正是因为这一命题具有极大的挑战性和刺激性,才激起了诸多作家、诗人的不满。仅在德国境内,反对这一定论的作家便有一长串名单,其中的重量级人物有京特·安德斯(Günther Anders,哲学家汉娜·阿伦特的第一任丈夫)、安德施(Alfred Andersch)、恩岑斯伯格(Hans Magnus Enzensberger)、希尔德斯海默(Wolfgang Hildesheimer),以及2015年去世的格拉斯(Günter Grass)等。限于篇幅,我在这里已无法展开这些论争以及阿多诺的回应,而只是想指出一个事实:几乎所有的误解者和反对者都没有去认真追寻阿多诺的思路与理路,以致其反对的声音已大大简化了阿多诺的思想。而实际上,德国人后来之所以能逐渐直面自己的过去,并使自己的文学艺术变得冷峻起来,显然与阿多诺对文化重建问题的反复言说和“奥斯威辛之后”命题的不断呼吁不无关系。而在这些呼吁与言说中,《文化批评与社会》既非起点也非终点,但它是一个重要的节点,也是文化问题的聚焦点,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①See Stefan Müller-Doohm,Adorno:A Biography,trans.Rodney Livingstone,Cambridge:Polity Press,2005,p.564. ②研究纳粹德国文学的英国专家里奇(J.M.Ritchie)经过一番辨析后指出:“内心流亡”(该词在里奇著作汉译本中作“国内流亡”)一词原来既可指消极抵抗也可指积极抵抗,这场论战则进一步限定了这个词的含义。“1945年之后,这个词严格限制用在那些留在德国国内、运用文学手段消极抵抗的作家们身上。这个词也标示出非流亡作家和流亡作家之间的鸿沟。”[英]里奇:《纳粹德国文学史》,孟军译,上海:文汇出版社,2006年版,第129页。 ③参见李昌珂:《德国战后的“托马斯·曼风波”》,《译林》1997年第4期。Stefan Müller-Doohm,Adorno:A Biography,pp.330—331.[英]里奇:《纳粹德国文学史》,第128—133页。 ④Stefan Müller-Doohm,Adorno:A Biography,p.332. ⑤[美]乔治·斯坦纳:《语言与沉默:论语言、文学与非人道》,李小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21—123页。 ⑥Theodor Adorno,Minima Moralia:Reflections from Damaged Life,trans.E.F.N.Jephcott,London and New York:Verso,p.55. ⑦Theodor Adorno,Minima Moralia:Reflections from Damaged Life,44.阿多诺在此处所打的比方来自于格林童话中《弗里德尔和卡特丽丝》的故事。弗里德尔下地干活时嘱其妻子卡特丽丝守在家里,做好烤肉,备好饮料,等他收工。卡特丽丝煎着香肠时想起了要去地窖接啤酒,用酒壶接啤酒时又想到狗没拴好,会衔走锅里的香肠,于是接了半截便急忙上来查看。狗果然叼走了香肠,于是她又去追狗。等她回来后发现啤酒流满了地窖。她担心丈夫回来后生气,便把一袋精面粉撒在啤酒流过的地方。参见[德]雅各布·格林、威廉·格林:《格林童话全集》,杨武能、杨悦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3年版,第215—217页.。 One Last Genius,trans.Rodney Livingstone,Cambridge,MA: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8,p.261. ⑨Martin Jay,Adorno,London:Fontana Paperbacks,1984,p.48. ⑩[美]马尔库塞:《审美之维》,李小兵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0页。据英译文有改动。Herbert Marcuse,"The Affirmative Character of Culture," in Negations:Essays in Critical Theory,trans.Jeremy J.Shapiro,London:Allen Lane,the Penguin Press,1968,p.98. (11)Theodor W.Adorno,"Cultural Criticism and Society," in Prisms,trans.Samuel and Shierry Weber,Cambridge,Ma.:The MIT Press,1981,p.26. (12)Theodor W.Adorno,The Culture Industry:Selected Essays on Mass Culture,ed.J.M.Bernstein,London:Routledge,1991,p.101. (13)(14)(15)Theodor W.Adorno,"Cultural Criticism and Society," in Prisms,p.23、p.24、p.25. (16)(17)(19)(20)(22)(23)Theodor W.Adorno,"Cultural Criticism and Society," in Prisms,p.22、p.26、p.21、pp.22—23、p.26、p.19. (18)阿多诺在此文中有三次明确提及苏联或俄国人:第一次表达为“新俄罗斯暴君的恐怖”,第二次说苏联制造了“犬儒式恐怖”,第三次他说俄国人糟蹋了传统文化:“被俄国人假惺惺地回收利用的文化遗产已最大程度地变成了可消耗的、多余的垃圾。”Theodor W.Adorno,"Cultural Criticism and Society," in Prisms,pp.28,31,34. (21)参见《席勒文集》第三卷,张玉书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4页。 (24)Richard Wolin,The Terms of Cultural Criticism:The Frankfurt School,Existentialism,Poststructuralis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2,pp.xi-xii.中译文参见[美]理查德·沃林:《文化批评的观念》,张国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3页。 (25)(27)Theodor W.Adorno,"Cultural Criticism and Society," in Prisms,pp.23,19、pp.22—23. (26)Theodor Adorno,Minima Moralia:Reflections from Damaged Life,p.43. (28)(29)(30)(31)(32)(33)(33)(34)(35)(36)(37)(38)Theodor W.Adorno,"Cultural Criticism and Society," in Prisms,p.25、pp.20—21、p.24、pp.32—33、p.30、pp.31-34、p.32、p.32、p.33、p.30、p.34. (39)Walter Benjamin,"Goethe's Elective Affinities," in Selected Wrirings,Volume 1:1913-1926,eds.Marcus Bullock and Michael W.Jennings,Cambridge,Mass.,and London: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p.356. (40)Theodor W.Adorno,"Cultural Criticism and Society," in Prisms,p.34.需要说明的是,此译本“critical mind”处译作“critical intelligence”,这里采用的是其他译本的译法。See Theodor W.Adorno,Meta physics:Concept and problems,ed.Rolf Tiedemann,trans.Edmund Jephcott,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179. (41)[美]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68页。 (42)Theodor W.Adorno & Max Horkheimer,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trans.John Cumming,New York:Herder & Herder,Inc.,1972,p.xi. (43)Walter Benjamin,Illuminations,trans.Harry Zohn,London:Fontana Press,1992,p.248. (44)Rolf Tiedemann,"'Not the First Philosophy,but a Last One':Notes on Adorno's Thought," in Theodor W.Adorno,Can One Live after Auschwitz?:A Philosophical Reader,ed.Rolf Tiedemann,trans.Rodney Livingstone and Others,Stanford,Califo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xvi. (45)Theodor W.Adorno,"Cultural Criticism and Society," in Prisms,p.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