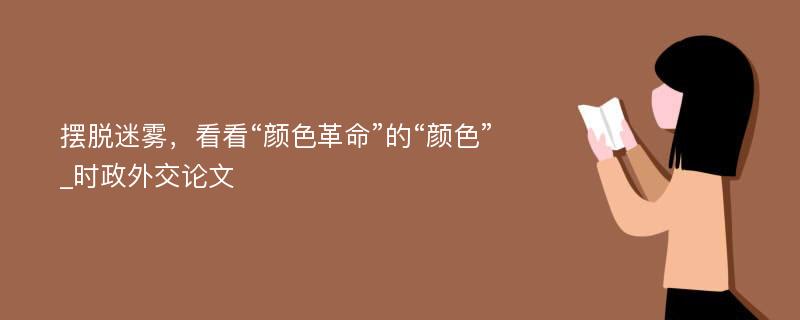
拨开迷雾看“颜色革命”之“颜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颜色论文,迷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颜色革命”一词是来源于西方的说法,是指独联体国家近两年来发生的政治变革。因为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的“革命”都是在某种颜色的标志下进行的。2003年11月22日下午,当格鲁吉亚前总统谢瓦尔德纳泽在新议会的成立大会上讲话时,反对派“逼宫”,28小时后,谢氏宣布辞职,萨卡什维利在随后的大选中当选为格新总统。由于萨氏冲入议会大厅时手举玫瑰,所以该事件又被称为“玫瑰革命”。在国内外的双重压力下,2004年12月26日乌克兰进行了第二次总统选举,尤先科顺利当选。尤先科的支持者都以橙色标识参加活动,所以该事件被称为“橙色革命”或“栗子花革命”。2005年3月24日, 阿卡耶夫总统被迫逃离祖国吉尔吉斯斯坦,同年3月28日,吉新议会举行会议选举巴吉耶夫为新总理。 因为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市花是黄色的迎春花,发生革命的时间正好是迎春花开的季节,所以吉的变革被称作“黄色革命”,也叫“柠檬色革命”。
“颜色革命”的国际国内背景错综复杂,相互交织
从国内因素来看:
这些国家都是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获得独立后都面临着两个主要的历史任务:一个是完成独立进程,一个是完成社会经济转型。要同时完成这两个任务,难度可想而知。苏联解体以后,国与国之间密切的经济联系中断了,给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很大的困难,还有的国家发生了内战,战争和动荡使本来就比较弱的经济遭受更大的打击。比如,格鲁吉亚曾经发生过内战和武装冲突,这使得国家本来比较困难的经济更加雪上加霜。吉尔吉斯斯坦长期依赖西方外债,外债规模已经相当于其国民生产总值的90%左右。
这些国家取得独立后,原苏联时期的国家机器和政治精英绝大部分都保留下来,原有的各种弊端也同样保持着自身的惯性,包括个人集权、权力寻租、法律虚设等现象都腐蚀着这些国家的肌体。比如,在乌克兰“橙色革命”中起到很大作用的国家安全局的一些官员,指责亚努科维奇犯有盗窃和袭击罪,并与攫取了乌克兰许多国有财产的腐败商人有密切联系,他们不想为这样一个人服务,暗中给反对派提供支持。
中亚国家大多社会贫富悬殊,在涌现出大批富翁的同时,失业成为普遍现象。中亚国家的人均月工资只有几十美元。以吉尔吉斯斯坦为例,贫富差距大,是其政局动荡的一个重要原因。目前吉贫困人口约占总人口的38%,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月平均工资仅为30—40美元。吉许多最盈利的大企业和行业被阿卡耶夫家族和亲信控制。“黄色革命”参与游行的大都是失业人群以及农民群体,有媒体报道说,参与活动的很多人承认自己受到食物和资金的诱惑,只有少部分人是出于政治目的才上街游行。
独联体国家独立后的第一代领导人为国家的政治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但随着民主政治体制的逐步完善和外部民主压力的加大,面对国内错综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难题和社会思潮的快速变化,很多执政党和领导人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不适应社会发展变化的现象。与此同时,独立后出现的新生政治力量发展、整合加快,形成了强大的反对派。他们大都推崇西方民主体制,反对个人集权和一党长期执政。这些人深谙选举政治的运作程序,善于利用经济政治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发难,有相当的社会号召力。
独联体国家在独立之初,均照搬美国模式,立宪规定总统只能连任两届。但以中亚国家为例,除了吉尔吉斯斯坦,虽然迄今四国总统都已连任两届,但均未有离职卸任的表示。哈萨克斯坦的反对派就此攻击说,一个民主国家的法律无论怎样修改也不会允许一个总统在位超过20年。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三国的政局动荡,都是由选举引发。选举中的操纵和不公正,如贿选、来自官方的种种限制以及官方对媒体进行控制等都引起群众不满,是政局突变的直接导火索。
从国外因素来看:
从这几次“颜色革命”的具体过程看,俄罗斯为了保住自己的“后院”和维持自己的战略生存空间,一方面不断批评、警告美国、欧盟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等国际组织要“谨言慎行”,另一方面,主要是利用历史形成的纽带联系和政治支持施加影响。但是由于各种历史的、现实的限制,俄罗斯的具体作为很少,也无法给亲俄的政治势力提供现实的帮助,效果非常不好,在争夺中明显处于下风,给人以力不从心之感。反观美国,抓住有利时机,政府支持和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双管齐下,始终掌握着竞争的主导权,取得了有利的战略态势。从已经发生“颜色革命”和目前正在受到“颜色革命”威胁的国家来看,它们几乎都处于关键的地缘战略区域,对美国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
据国际战略观察家分析,北约东扩和欧盟扩大后,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成为俄罗斯西部边界唯一的“缓冲区”和战略屏障,美欧通过支持在乌建立亲西方的政权,意在挖俄罗斯的墙脚,削弱这个战略对手在这一地区的影响。中亚地处欧亚大陆腹地,既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又处于俄罗斯、中国、印度和伊斯兰世界的中间,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意义。苏联解体后,美国就抓住各种机会进行渗透。美国一直希望将吉尔吉斯斯坦改造成为中亚的“民主样板”,并希望以此带动整个中亚地区接受西方式民主政治。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后,更是实现了其在中亚的军事存在。格鲁吉亚地处中东地区与俄罗斯的中间地带,是里海油气资源输往西方的重要通道,又是斯大林的故乡,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在“颜色革命”中,美国政府一是制造有利于反对派的国际舆论环境,比如不承认选举的合法性,向当权者施加压力,向反对派提供信息和策略咨询,组织对选民的投票问询调查,间接支持反对派的游行示威等等;二是提供实实在在的技术和资金支持。乌克兰选举危机爆发以后,俄罗斯一直指责美国幕后插手这一事件。美联社提供资料称,美国政府过去两年间在乌克兰投入超过6500万美元。事实上,美国国务院每年用在所谓“推动全球民主”方面的总支出高达10亿美元,而对乌克兰的投入就是其中一部分。
在“颜色革命”的准备和进行过程中,大量的支持、帮助反对派的工作是由非政府组织具体实施的。美国官员承认,美国资金虽然从没直接提供给乌克兰政党,但大多数情况下,资金都是通过欧亚基金会这种非官方组织、选举培训组织或人权论坛送出,其中部分资金间接用于帮助培训乌克兰反对派组织和个人。非政府组织包括索罗斯基金会、国际因特信息、自由之家、欧亚基金会等。今年5月12日,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帕特鲁舍夫表示,在过去的两年里,美国等西方国家通过其资助的非政府组织,帮助俄罗斯等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反对派们走上街头,对抗政府。他还对这种行为进行了强烈谴责,称其险恶用心是削弱俄罗斯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
客观把握“颜色革命”,需正确认识三种关系
“颜色革命”的背景和原因就像它的颜色一样错综复杂,国际国内因素相互交织,要拨开迷雾客观准确地把握“颜色革命”之“颜色”,必须建立在正确认识三种关系的基础上。
“颜色革命”与苏东剧变的关系: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颜色革命”是第二波苏东剧变,但有所不同。
“颜色革命”与上世纪苏联东欧剧变时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鹅绒革命”一脉相承,意思是通过非暴力的柔性政变夺取政权,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次从2003年起开始的“颜色革命”浪潮实际上是苏东剧变历史进程的延续,但内涵有所不同:
1989年的苏东剧变,先是东欧国家纷纷脱离了苏联的控制,全面倒向西方,最后苏联这个庞然大物于1991年底轰然倒塌,15个加盟共和国各自独立,除了波罗的海三国外,12个加盟共和国建立了独联体。在这次剧变中,所有的东欧国家和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都制定了自己的宪法,在法律层面上建立起西方式的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这被视为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巨大成功。因为国体和政体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所以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颜色革命”。苏东剧变的关键内涵有两点:一是苏联的解体,二是所有苏东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上向西方的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制度全面转轨。此次亲美的(吉尔吉斯斯坦例外)反对派利用国内的社会、经济、政治矛盾和选举中的舞弊问题向政府发难,在美国的民主化战略的外部支持下,以基本上不流血的“街头政治”方式发动了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最后夺取了政权。这些“颜色革命”普遍带有反腐败、反独裁的性质,实际上是一种政治势力代替了另外一种政治势力,但是并没有改变原来的社会政治制度。既然建立了民主制度,实行选举政治,那么执政党的改变就是很正常的现象。只不过因为这些转轨国家所处的特殊的历史阶段和国际国内环境,在政权转移的过程中出现了不正常的现象引发了政治危机,造成了政局的动荡。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次变革谈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颜色革命”。
内因与外因的关系:国内各种矛盾的激化构成这次“颜色革命”的内因,西方的民主扩展战略则是外因。
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第一位原因,外因通过对事物内部矛盾的影响而促进和阻碍事物的发展。从这三个国家发生政治危机的原因来看,国内因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也就是说这些国家的前政府在解决国家自身问题的时候,出现和积累了很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和矛盾,造成许多人对当权者不满,给反对派提供了发展壮大的社会土壤以及向当权派挑战的借口。外部势力利用了国内的这种矛盾激化的状态,导致了这些危机的出现。也就是说,不能认为“颜色革命”完全是美国一手制造出来的,并不是美国想在哪个国家搞“颜色革命”,哪个国家就发生政治危机,说到底危机还是由这些国家内部问题引起的。只有当国内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当社会上不满情绪不断高涨时,外部因素才可能产生作用。不管是在格鲁吉亚、乌克兰还是吉尔吉斯斯坦,若不是社会自身渴望变革,若不是社会的忍耐已超出极限,美国和欧洲都无法将事态引向自己期望的轨道。当然,这么讲并不是要否认美国在“颜色革命”中的重要作用,而是为了澄清一些认识上的误区。
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从“颜色革命”的进程和实质来看,美俄战略争夺与这些国家内部政治派别斗争的关系交织在一起,其中国内政治派别的斗争构成这次变革的主要矛盾,而美俄的战略争夺是次要矛盾。
唯物辩证法认为,主要矛盾对事物的发展起决定性作用,但是非主要矛盾也并不是消极被动的因素,可以影响和制约主要矛盾的发展。对这次“颜色革命”起决定作用的是这些国家的内部政治斗争,其中的反对派成了主要矛盾中的主要方面,所以决定了这场斗争的最后结果。在整个过程中,俄罗斯和美国都在力图影响事件的进程和发展方向,但是从结局来看,还是这些国家的人民自己决定了自己的命运。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美俄的战略争夺,特别是美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积极推动,不仅仅是构成了这场斗争的国际环境,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卷入了这场斗争,对政局的发展方向和进程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颜色革命”的结果对美国也是有利的。
从这些国家未来的对外政策走向来说,也不能简单地说都对美国有利,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根本上说,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是由它的国家利益决定的,弱小的国家要在大国的夹缝中求得生存,必须要保持对外政策的平衡。从目前来看,格鲁吉亚和乌克兰走的是亲美路线,但同时仍然要顾及俄罗斯的利益需求。
从“颜色革命”浪潮的发展态势和美国“民主扩展”战略来看,最有可能受到冲击的是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它们都具有与吉尔吉斯斯坦相似的国内条件和国际环境。当然还有被称为欧洲“最后一个独裁堡垒”的白俄罗斯,美国领导人已经多次表示希望其发生民主变革,对其反对派提供公开的支持。另外,“颜色革命”之风还有可能刮到独联体之外的国家,比如黎巴嫩和埃及,其实这也是美国“大中东计划”的题中之义。
总体来讲,“颜色革命”浪潮的发生和发展,对国际关系和国际战略格局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在意识形态和地缘战略上对俄罗斯和中国形成了很大的结构性压力。对此我们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进行深入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