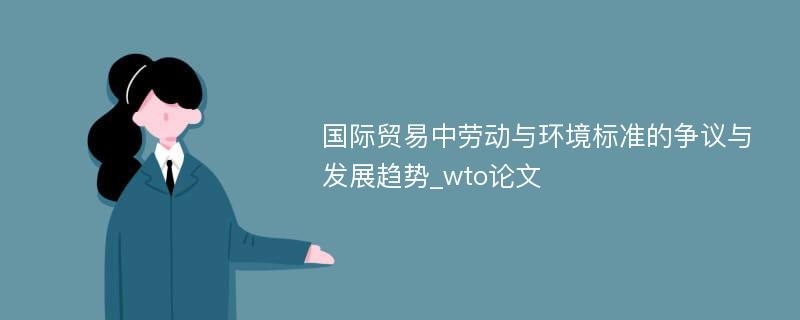
国际贸易中的劳工、环境标准之争及发展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环境标准论文,劳工论文,发展趋势论文,之争论文,国际贸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4)01-0077-04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是否应将劳工、环境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的问题上一直争辩着。虽然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坚决反对,1986年开始的世界贸易组织乌拉圭回合谈判未将劳工、环境标准列入谈判议题,1999年12月的世界贸易组织西雅图会议也因劳工、环境标准协议问题而失败,2001年11月的多哈会议虽将贸易与环境问题列入谈判议题,但劳工标准问题仍被搁浅。无论如何,发达国家对这些“社会条款”的重视不会削减,发展中国家也会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尽量找出种种理由予以反驳。本文旨在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就这个问题的争论进行评述,并对其发展趋势做初步判断。
一、劳工、环境标准的“公平贸易”之争
“公平贸易论”的主要倡导者是美国。其最初的思想主要包含两方面:一是主张对等的市场开放。不管经济发展程度如何,不对等的市场开放被认为是不公平贸易;二是主张公平竞争。凡是由政府通过某些政策直接或间接地帮助企业在国外市场上竞争,并造成对国外同类企业的伤害,即被看成是不公平竞争[1]。近年来,“公平”的内涵也因决策者、学者们各自利益的需要而有所延伸[2]。
首先,劳工、环境标准的支持者认为发展中国家低的劳工、环境标准不管对发展中国家的员工,还是发达国家的员工都是一种“不公平”。
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员工来说,低工资将会引起与贫穷有关的不充足食物供应、不充分医疗保障以及子女失学等问题,低标准的工作环境将会使员工的身心健康、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童工的使用将剥夺儿童的受教育权利,低环保标准地区的民众也将遭受环境恶化的苦果;对于发达国家的员工来说,来自低工资标准发展中国家货物的竞争将可能使其所在的企业经营困难,甚至倒闭。这些员工因而收入下降,甚至失去收入。另外,由于一些环境影响的过境性,低环境标准国家恶化的环境可能使发达国家受到影响,如酸雨、臭氧层削减的全球影响效应等;对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员工所受不公平待遇的抱怨还来自于其“受剥削”的境地。跨国公司赚取了无数利润,而为其服务的发展中国家员工所挣工资却不能满足基本的生存条件;发达国家的消费者享受了廉价的进口货物,而生产这些货物的低工资标准、低工作环境标准的发展中国家员工则仅得到少量工资,并留下了许多安全、健康问题;为了躲避发达国家高劳工、环境标准的监管,许多发达国家的企业将其工厂转移至低标准的发展中地区,这可能造成许多发达国家员工的失业。
针对上述观点,劳工、环境标准的反对者一方面通过实证分析说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其产业,并不是因为发展中地区低劳工、环境标准的驱动。这些成本仅占产品成本的很小部分,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地区转移产业有其他原因。对发展中国家劳工、环境标准的高要求,并不能阻止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这样由低劳工、环境标准引起的发达国家产业转移,进而其员工失业的理由也不能成立。另一方面反对者认为,如果有最低工资标准要求,发展中国家的失业程度可能会加重,许多进城务工的农民可能被迫返回收入微薄的农村,甚至沿街乞讨;如果禁止使用童工,儿童的处境也可能会更差,一些女童可能沦为妓女;如果实施高的环境标准,可能使依靠资源型产业发展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放慢,进而减少对清洁技术的投资,致使高标准的环境影响走向环境标准支持者的反面。所有这些对发展中国家的员工来说是更加的“不公平”。
其次,劳工、环境标准的支持者认为发展中国家低的劳工、环境标准使高标准发达国家的生产成本相对偏高,削弱了发达国家的竞争优势,这对发达国家来说是“生态倾销”和“社会倾销”,是一种“不公平”贸易行为。允许发展中国家低标准产品的贸易自由化,将导致“低标准驱逐高标准”的柠檬问题和低层次竞争(race to the bottom)现象的产生。
发展中国家认为由于不同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在对待增长与环境问题、增长与劳工问题的平衡协调上,必然有不同的侧重点。由于各国劳动市场条件、税收水平等差异很大,因而不同国家的劳工、环境标准不可能完全相同。不承认发展中国家在资源密集型产业和劳动成本方面的比较优势,对发展中国家是不公平的。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生态倾销”和“社会倾销”责任,是发达国家在降低纺织、服装和农产品壁垒后的一种新的、更加隐蔽的贸易保护壁垒[3]。
再次,劳工、环境标准“公平性”的争论来自于对主权独立性的不同考虑。劳工、环境标准的反对者认为,劳工、环境标准的制订属于一国主权的范畴。应由本国政府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自主决定。最低工资标准应充分考虑本国的劳动市场条件;童工年龄上限应根据本国习俗、文化等因素确定;环境标准的制订应充分考虑本国经济发展的阶段,重在处理好环境管制和经济增长的协调关系。对于一个贫穷的国家来说,宽松的环境标准可能增强国内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有利于国民经济增长。由发达国家或国际组织为发展中国家制定劳工、环境标准是对发展中国家主权的侵犯,对发展中国家非常的不公平。
有趣的是,发达国家也认为,劳工、环境标准的制订属于一国主权的范畴。他们有权利独立自主地根据本国实际情况制定高的劳工、环境标准,并有权阻止不达标准的外国产品的进入。他们认为,允许不达其标准的发展中国家产品进入,也是对发达国家主权的一种侵犯,也是对发达国家的不公平。环境保护主义者认为,在1991年的美国与墨西哥金枪鱼—海豚之争中,原GATT裁决美国基于生产过程和方法的标准不合理一案以及1996年的美国与委内瑞拉、巴西成品油环境标准争端案件中,WTO冲突解决委员会裁决美国败诉等案例都是对美国独立环境管制权的一种侵犯。
二、WTO引入劳工、环境标准“合理性”之争
对于WTO中是否应附有专门的劳工、环境标准协议,也有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
首先,将劳工、环境标准纳入WTO规范的支持者认为,贸易自由化是环境恶化和童工市场发展的主要原因。在不能保证自由贸易将导致良性效应时,不应笼统地实施贸易自由化;贸易报复是最理想的劳工、环境标准实施机制。如果WTO中附有专门的劳工、环境标准协议,WTO冲突解决委员会将会依此对违反协议的成员国作出裁决,要求该国调整相应的国内政策。不能按要求作出调整的,其他成员国有权在WTO框架下对其实施报复性的贸易制裁行动。劳工、环境标准协议的支持者认为,这种有WTO约束的贸易制裁是最直接、最有力的劳工、环境标准实施保障,也是一种负互惠性的体现。
同时,劳工、环境标准协议的支持者认为,虽然许多国家接受了国际劳工组织发布的《国际劳工协议》和国际环境组织发布的《国际环境协议》,但迄今为止仍然没有一个有效的实施机制。如果WTO中有专门解决国际贸易中劳工、环境标准的规则,则遵守者将获得相应的利益,而违反者将受到贸易伙伴国对等程度的报复制裁。这不仅是对《国际劳工协议》和《国际环境协议》的必要补充,也充分体现了权利义务对等的公平原则。
与此相对应,将劳工、环境标准纳入WTO规范的反对者认为,劳工协议已经由国际劳工组织制订,环境协议已经由国际环境组织制订,这些协议的基本原则与WTO宗旨并不矛盾。WTO仅仅是一个贸易组织,不应该涉及像劳工、环境标准这样的国内政策问题,WTO无权阻止成员国不参与有关国际劳工、环境标准的双边、诸边及多边协议的行为[4]。
同时,劳工、环境标准协议的反对者认为,贸易能创造用于环境治理的资本从而有助于环境问题和劳工问题的解决。劳工、环境标准问题不应运用贸易制裁工具,而应该通过自愿行动途径解决[5]。如果某种产品是在血汗工厂或污染环境下生产的,消费者将不会购买该产品。市场机制会使生产者自愿地改善劳工的工作环境和工资待遇,并尽量采取“绿色”方法生产。与此相适应,劳工、环境标准协议的反对者还建议,建立产品“社会标签”和“绿色标签”制度,使消费者清晰地识别这种产品。他们用理论证明,这比贸易制裁更有助于社会福利的增进[6]。
WTO引入劳工、环境标准协议的第二个争论来自于WTO对相关问题的平等待遇问题。劳工、环境标准协议的支持者指出:WTO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保护公司和知识产权所有者的利益;为了保护公司及其股东利益的反倾销和抵消性关税行动也得到WTO的认可。那么,基于非歧视原则,意在保护劳工及其他公民利益的劳工、环境标准协议也应成为WTO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此相对应,基于同样的逻辑,劳工、环境标准协议的反对者指出,像健康和福利政策、教育政策、税收政策等国内政策必然导致一些国家产品的成本优势和另一些国家的成本劣势。既然这些政策没有纳入WTO规范的范畴,劳工、环境标准政策也应由各国根据本国实际自主决定,WTO不应对单独劳工、环境标准问题采取歧视待遇而规范之。
另外,发展中国家还指出,不管什么原因引起的不公平竞争问题导致了一国产业受到实质性损害,WTO已经提供了可利用的保障机制,没必要再设立新的劳工、环境标准制约机制。
三、劳工、环境标准问题发展趋势
国际贸易中劳工、环境标准问题的发展趋势一方面取决于支持者与反对者谁将在最终的争执结果中占上风,另一方面则取决于国际贸易中劳工、环境标准问题发展的实践态势。
首先,就劳工标准问题来说。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一方面发达国家在国际大分工中主要生产和出口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的产品,其劳动密集型产品将大量转移至发展中国家,这使发达国家的劳工处境更加艰难;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的首要条件是资本的全球化扩张,而资本扩张的直接结果是资本地位的不断上升和劳工地位的不断下降。要求提高劳工工作和生活条件的呼声越来越高。因而在国际贸易活动中,必然涉及劳工标准问题。经济发展应与社会发展同步,这是一个客观要求[7]。
就环境标准问题来说,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发展中国家国民对环境质量的要求也将越来越高,可持续发展问题也将越来越受到发展中国家政府的高度重视。来自发展中国家对环境标准与国际贸易联系起来的抵触和反对也将越来越弱。国际贸易中环境标准的实施也是迟早的事。
其次,WTO多边贸易规则的制定,目前还主要由发达国家所影响或左右,而这些国家的政府及工会等相关组织是劳工、环境标准的积极推动者,且这个意见已经被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国际环境组织等国际组织所认可。所以在WTO框架下将劳工、环境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将是一个必然趋势。
事实上,WTO已经承认了环境、健康与安全目标的合理性,并在实践中尽力对贸易自由化与这些社会发展目标以同等程度的重视。有资料表明,截止2002年3月,WTO共受理了21个有关环境、健康与安全的贸易争端案件,其中6个案件已经被做出裁决(注:这6个案件是:委内瑞拉和巴西诉美国汽油冶炼的歧视性标准;印度、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和泰国诉美国对没有使用海龟避免设备捕捞小虾国家的小虾进口的禁止;美国、加拿大与欧盟的牛肉—荷尔蒙争端;加拿大诉澳大利亚对冷冻鲑进口的禁止;美国与日本的农产品贸易争端;加拿大与欧盟诉法国对石棉进口的禁止。其详细的内容请参阅Kelly,T,2003。)。除了法国的石棉进口禁止举措得到了WTO的肯定外,其他5个案件的被告方都被认定为在实施贸易保护。WTO认为:法国的石棉进口禁止符合WTO有关健康与安全保护条款的要求;美国对成品油和小虾进口禁止的理由虽符合WTO的环境例外规则,但在实施中表现出对外国生产者明显的歧视性;欧盟对牛肉进口的禁止确实有防止荷尔蒙导致人体生长风险的考虑,但没有科学的根据;澳大利亚禁止加拿大冷冻鲑进口和日本对美国农产品进口限制的理由也都没有科学的根据[8]。从这些案例可看出,只要有科学依据,并且没有构成对外国生产和产品的歧视性待遇,WTO对成员国追求环境、健康、安全等社会目标是肯定的。
最后,发达国家的政府和民间组织已经将国际贸易与劳工、环境标准联系起来。虽然目前只是单边行为,但已经对国际贸易活动产生了重大影响。比如,美国贸易法规定,在确定普遍优惠制度的受益国时,应考虑该国是否已经采取或正在采取措施,向其本国的劳工提供国际公认的劳工权利。对于那些不符合国际公认劳工标准要求的国家,美国可以考虑撤消、中止或限制向该国提供普遍优惠(注:参见韩立余译,《美国贸易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1版,P164-165。)。同时,美国关税法也规定,在外国全部或部分由劳改犯人开采、生产的货物,不得在美国的任何口岸入境。
另外,目前全球已有30多个国家推出了环境标志制度[9],而且许多国家构建了共同的环境标志制度,如北欧国家实行的“白天鹅制度”等。更重要的是,不仅WTO允许的针对产品本身的绿色标准,而且WTO目前不允许的针对加工和生产过程(PPM)的环境标准也有许多国家在实施。不管PPM标准最终是否会成为多边规则,其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却是实实在在存在的。
从民间层面来看,国际标准组织针对环境管理的ISO14000认证体系已被各国企业普遍接受。得不到这张“绿色通行证”,其产品的出口将会遭到拒绝。美国经济优先准入权认证机构理事会(The Council on Economic Priorities Accreditation Agency)于1997年参照ISO9000的原理制定了一套《社会责任标准8000》,并配备有认证证书和监督机制。用以向各国消费者表明通过SA8000认证的产品符合国际公认的最低劳工权利标准,符合有关社会责任的要求[10]。SA8000虽然是民间劳工标准,但必将对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产生重大影响。
四、结论
发达国家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低劳工标准、低环境标准是社会倾销、生态倾销,这将会导致低标准驱逐高标准的“柠檬问题”产生。发展中国家认为发达国家的高劳工、环境标准要求是一种新的、更加隐蔽的贸易保护工具。其对劳工、环境标准的“公平贸易”之争、WTO引入劳工、环境标准协议的“合理性”之争等也都各执一词。这场争论仍会继续,但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同步性,伴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而对劳工权利、环境质量要求的逐步提升,以及发达国家在WTO中的绝对地位等因素决定了劳工、环境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是迟早的事。事实上,作为单边、双边行动,劳工、环境标准问题已经对区域贸易、国际贸易产生了重大影响。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一方面需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贸易伙伴国出于贸易保护需要对劳工、环境标准的滥用;同时应积极主动地运用国际公认的劳工、环境标准,以提升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收稿日期:2003-09-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