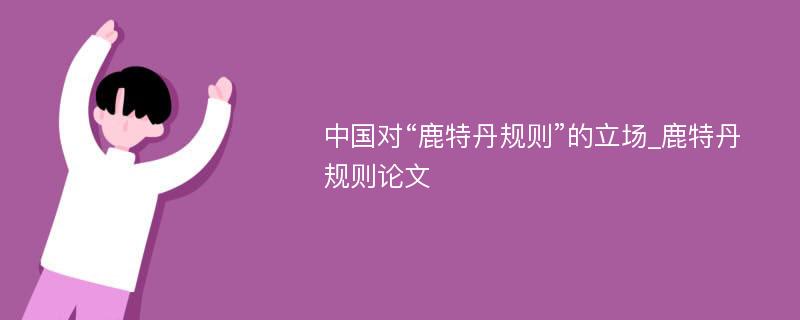
《鹿特丹规则》的中国立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鹿特丹论文,中国论文,立场论文,规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何志鹏.《鹿特丹规则》的中国立场[J].中国海商法年刊,2011,22(2):25-37.
中图分类号:DF96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7659-(2011)02-0025-13
一、引言
2008年12月11日在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全程或部分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公约》(简称《鹿特丹规则》)在以前数年初步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广泛注意,并称为近来中国国际法学界,特别是海商法学界密切关注的问题之一。
一些学者在这一公约起草的阶段就予以关注①,介绍该规范的主要内容、基本进展,对关键领域进行了评述,并提出了一些建议,相关论文如陈琳撰写的《论国际运输法统一下的海商法“上岸”——以〈UNCITRAL运输法草案〉为起点》,载《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陈鉴、陈峥峥撰写的《运输法草案适用范围的评介》,载《沈阳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司玉琢撰写的《UNCITRAL运输法(草案)难点问题研究》,载《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司玉琢撰写的《论喜马拉雅条款的沿革及理论基础——兼评UNCITRAL〈运输法草案〉下的海上履约方》,载《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刘昕撰写的《海运货物控制权问题研究——兼评UNCITRAL运输法草案第11章的规定》,载《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屈广清、王淑敏、杜萱撰写的《UNCITRAL〈运输法草案〉对提单持有人诉权的保护及其借鉴》,载《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孙朋撰写的《简论UNCITRAL运输法草案中的权利转让》,载《商场现代化》2006年第9期;宣行撰写的《新运输法草案第13条的借鉴意义》,载《中国船检》2006年第4期;余妙宏撰写的《UNCITRAL运输法公约(草案)托运人制度之变革及对策》,载《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杨明芳撰写的《浅议运输法草案扩大适用于航次租船合同》,载《理论界》2005年第9期;赵月林撰写的《对〈运输法草案〉“运费”一章的评述》,载《中国海商法年刊》2002年第1期;司玉琢、蒋跃川撰写的《关于无单放货的立法尝试——评〈UNCITRAL运输法草案〉有关无单放货的规定》,载《中国海商法年刊》2003年第1期;蒋跃川撰写的《论权利转让——评〈UNCITRAL运输法草案〉关于权利转让的规定》,载《中国海商法年刊》2003年第1期;朱作贤、王晓凌、李东撰写的《对提单“提货凭证”功能重大变革反思——评〈UNCITRAL运输法草案〉的相关规定》,载《中国海商法年刊》2005年第1期;向力撰写的《论海运条约冲突的解决模式——以联合国货物运输法草案为中心》,载《中国海商法年刊》2008年第1期。
在公约通过之后,更是引起了很多学者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据笔者统计,自《鹿特丹规则》通过后至2011年5月底,在国内的学术杂志上发表的直接关于《鹿特丹规则》的论文有100余篇,来自大连海事大学、上海海事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华东政法大学等的专家对《鹿特丹规则》所进行的国际航运制度变革进行了探索。考虑到海商法这一学科在中国法学界的“小众研究”位置,不能不说已经引起了相当广泛的关注②。其中,对于承运人的责任③、港口责任④、法院或仲裁庭选择⑤、法律选择⑥等问题,国内外学者已经有了较多的分析。关于这一规则对于中国相关方面的影响,也有学者进行了调研⑦,或者基于自身视野和经验的分析⑧。而对于中国是否应当签署和批准《鹿特丹规则》,则大略可以分为四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鹿特丹规则》凝聚了智慧,代表了先进的立法方向,即将开启一个新的时代,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都应当加入。2011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王祖温建议中国尽早加入这一国际法律规范体系(参见《全国人大代表、大连海事大学校长王祖温:我国应早日加入〈鹿特丹规则〉》,载《现代物流报》2011年3月15日第A8版);李海教授认为,《鹿特丹规则》是“一个经历十多年智慧与心血的结晶、一套极具综合性的法律规则、一个平衡船方与货方利益的新成果”参见李海撰写的《〈鹿特丹规则〉:一个值得珍惜的统一法律的机会》,载《中国海商法年刊》2010年第1期)。第二种观点认为,《鹿特丹规则》取得了成绩,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但中国作为海运大国应当加入,以保护本国利益。司玉琢教授认为,《鹿特丹规则》的先进性表现为平衡利益、寻求统一、顺应时代、促进发展;其不足则表现为规则内容庞大、条款交织复杂,创新制度有不完善之处,有些制度的可操作性有待实践检验(参见司玉琢撰写的《〈鹿特丹规则〉的评价与展望》,载《中国海商法年刊》2009年第1期第3-8页)。第三种观点则认为,《鹿特丹规则》内容过于复杂,规范内容的各项创新有待检验,所以应当谨慎(参见朱曾杰撰写的《初评〈鹿特丹规则〉》,载《中国海商法年刊》2009年第1期;张永坚撰写的《如何评价〈鹿特丹规则〉》,载《中国海商法年刊》2009年第1期)。承担商务部调研项目的主要承担人张丽英教授认为,《鹿特丹规则》的新变化对货方来说,应该说是有利有弊的,多数货主从整体上对新规则持积极的态度。应全面考查《鹿特丹规则》给船方、货方、保险、银行等各个方面可能带来的影响,以积极的态度对待《鹿特丹规则》,关注其在多式联运、控制权、电子运输单证等诸多方面的积极尝试,并以审慎的态度对待《鹿特丹规则》,认识到其对国际贸易举足轻重的影响,并持续关注中国主要贸易伙伴对新规则的态度,在此基础上就是否签署《鹿特丹规则》做出慎重决策(参见张丽英撰写的《〈鹿特丹规则〉对中国进出口贸易影响的调研》,载《中国海商法年刊》2010年第4期)。类似的视角,也可参见邹盈颖撰写的《中国法视角下对〈鹿特丹规则〉评估的认识》,载《法学》2010年第11期。第四种观点认为,《鹿特丹规则》作为各国观点妥协的产物,近期很难生效,中国可以考虑借鉴其合理的方面,修订国内立法。“《鹿特丹规则》对单证托运人、持有人以及控制权相关制度的设计,是我国海上货物运输立法所不具有的或不完善的,因此,我们应当对此予理性地加以吸收和借鉴。”(参见费宏达撰写的《〈鹿特丹规则〉视野下FOB条件下卖方之货物控制权》,载《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另参见郭萍、张文广撰写的《〈鹿特丹规则〉述评》,载《环球法律评论》2009年第3期)
鉴于中国对于《鹿特丹规则》的立场与态度尚在争论之中⑨,所以本文拟从宏观的角度,从现实出发,根据国际社会与国际立法发展的基本脉络,分析以下几个问题:应当如何认识《鹿特丹规则》所设定的目标?为达到这一目标,《鹿特丹规则》所采取的手段是否适当?具有何种意义?存在哪些问题?中国在《鹿特丹规则》所设计的航运领域处于何种地位?应当采取什么样的立场?
二、《鹿特丹规则》所设定的目标分析
《鹿特丹规则》的出现,是在国际海事立法领域的一次积极的尝试,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长期的舆论准备和宏大的实践目标。其具体目标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
(一)确立一套统一的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法
自1924年《统一提单的若干法律规定的国际公约》(《海牙规则》)以来,多边的海上货物运输规范已经出现了数种,其适用事项范围、权利义务配置、参加国、实际效果均存在较大差异。[1]如果说,《维斯比规则》仅仅是对《海牙规则》零敲碎打式的补充完善的话,《汉堡规则》则是对海牙-维斯比体系的革命式修正。但是,实践有其内在的规律,在机会不成熟的时候试图新创一套海运规范体系,其实很难成功。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自由主义者更赞赏渐进的改革,而不主张突进式的变迁。1978年在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UNCITRAL)的推动下出现的《汉堡规则》,在14年之后才生效,至今也没有获得广泛的承认和施行。由于海上货物运输具有高度的跨国性,所以这种规范割裂的状况始终为一些航运界和法律界人士所忧虑。从另一个角度讲,建立一套全新的、超越以往的海上货物运输规范,是一代海商法专家心中的梦想。
UNCITRAL为这一梦想的实现提供了一个起航的空间。由于《汉堡规则》迟迟未能生效,20世纪90年代早期,国际海事委员会(CMI)⑩开始研讨海上运输法的整体改革。数年后,UNCITRAL作为《汉堡规则》的倡导者,也开始考虑海上货物运输立法的重订问题。1998年,UNCITRAL与CMI议定合作起草新规则。这一新规则承载着海商法专家将海上货物运输规范统一化的长期希望和美好愿景。草案在专家小组努力下于2002年问世并转移给UNCITRAL,数经讨论,终于在2008年通过,并定名为《鹿特丹规则》。从这一过程很容易理解,《鹿特丹规则》意在提供包括海运区段的整体、统一国际货物运输法律规范,进化、发展国际海事立法,试图结束以往海上货物运输多种规则分据的不成体系局面,借鉴以往国际规范的经验,结合现代科学技术以及商事关系,特别是保险业的发展所建立的新体系,并期待着国际海上货物运输能最终统一于鹿特丹体系(11)。
(二)以海上货物运输为轴心的多式联运规则体系
与以往单纯针对海运的国际条约不同,《鹿特丹规则》采用的是“海运+其他”(maritime plus others)的方式(《鹿特丹规则》第1条)。这让人清晰地感觉到,《鹿特丹规则》试图做到的不仅是纵向的统一,即统一历史上的几大海上货运规则,而且还是横向的统一,即以海上运输为轴心,兼顾涉及海运的多式联运。这也就让我们回忆起联合国的另一个机构——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的一项未能成功的努力,即《联合国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公约》(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Multimodal Transport of Goods,1980)。该公约旨在对多式联运经营人和托运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进行规定,解决因国际货物多式联运的发展而带来的一系列法律问题,规定了国际货物多式联运中的管理、经营人的赔偿责任及期间、法律管辖等各个方面(12)。《鹿特丹规则》在很多方面接手了《联合国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公约》的初衷,虽然在规则原则上可能不尽一致,但是采用最小网状责任制,肯定有《联合国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公约》的启迪(《联合国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公约》第18条和第19条)。从这个意义上讲,《鹿特丹规则》给自己设定了更多的任务,试图在集装箱运输迅猛发展的时代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也显现出对电子商务的进一步整合。[2]
(三)试图建立一个托运人与承运人之间更加均衡的权利义务体系
很多学者认为,主流的国际货物运输体系(即“海牙-维斯比体系”)更倾向于照顾承运人,而没有完全接受民法中普遍采用的过失责任制度。根据国际政治经济学者苏珊·斯特兰奇的观点,任何一个秩序都是多种结构性权力和联系性权力促成的结果,[3]所以,国际航运秩序当然是有其国家与市场的原因的。(1)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都会鼓励运输业发展。因为运输业不仅意味着商业利益,而且意味着国防利益。通过运输服务可以获得收入,在战争和武装冲突时,运输力量就会变成战斗力(13)。(2)运输业自身所面临的商业风险是巨大的,这种风险不仅来自于船舶造价高昂、海运市场的情势难于预测,而且来自于海上自然风险和技术风险众多,船舶事故屡屡出现。(3)承运人在航运市场上具有技术和信息上的自身优势。船方在签订运输合同、履行运输合同方面占据着市场的优势地位,而且承运人之间虽然存在竞争,但仍由于行业的一致性,有可能成为一个团体。(4)与承运人相比,货方分散,无法形成专业性团体,缺乏讨价还价能力。也正是由于船货双方信息、能力的对比,美国在1893年才以国家立法的方式限制承运人的免责,也正是这种限制,奠定了《海牙规则》的基础。[4]《汉堡规则》试图忽略这种力量与信息的不对称,构建一种完全的过失责任制度,但显然没有成功(14)。
《鹿特丹规则》在这一点上采取了进化而非革命(evolution instead of revolution)的方式,即试图改变以往的不够公平和均衡的状况,建立新的体系,又考虑在当前的技术水平之下的可能性,从而形成了一个比海牙—维斯比体系要求严格,而比《汉堡规则》要求略宽松的承运人责任体系。但与此同时,也进行了很多创造性的制度设计,例如,创设了货物控制权的制度(15),确立了履约方这一概念(16),不再采用提单的概念,而采用了“运输单证”的概念,这拓展了海运单证的范围,有利于电子化,并直接导致在该公约框架下提单性质的变化(17),并且通过凭指示放货的货物交付规范,试图解决以往“无单放货”的问题(18),对于法院选择也制定了一些值得研究的规范。[5]当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是承运人责任的变化,这是该规则得以独树一帜于既有的海运规则体系的重要方面(19)。
(四)《鹿特丹规则》设定目标实现的可能性
如果人类的历史发展有什么规律可循的话,大概可以论断:循序渐进的小规模改良更容易成功,大刀阔斧的大规模革命更容易陷入困境。目标设计得过于庞大或者复杂,在采取行动的时候本身就容易陷入混乱之中(20),或者改革过去之后还会被颠覆(21)。这或许可以从一个侧面证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在量变没有积累到相当程度的时候,试图推进质变是不符合客观规律的,无论愿望多么美好,最终都无法取得成功。中国古人所说的欲进反退、欲速则不达,就是这个道理。国际海运立法的发展也应当充分考虑这一规律。数年前,我国已有学者认为,国际海事立法在承运人责任基础方面最终应归入到过失责任,但必须考虑原有的法律文化基础。[6]《鹿特丹规则》的尝试考虑集装箱运输的广泛使用、考虑电子商务的迅速推开、考虑运输速度的加快,凭单提货并不总是具备可行性这些因素是值得肯定的,因为它符合了近30年来海运和多式联运的发展。[7]但是,从另一个方面看,将一份国际法律文件界定为既处理海上运输又着眼于与海运相连接的多式联运,采用履约方、控制权等新的国际制度,就很可能是步子迈得过大(22),关于海运单证的规定也容易使实践者陷入迷茫(23),而其中最为引人注意的承运人义务与责任的问题,更是值得关注。[8]《鹿特丹规则》现在做出的这些改良和革新,是否能够创设妥当可实施的制度,是否真正实现了公平合理,理论研究者提出了不同的分析和意见(24),实际的情况、最终的结果,显然还有待于实践的检验(25)。
三、《鹿特丹规则》所采取的规范形式分析
《鹿特丹规则》究竟是否可行,不仅是一个实体规范的问题,还涉及形式的问题。由前文阐述可知,《鹿特丹规则》是针对不成体系的国际海上运输法律规范而进行的一种尝试(26)。在形式上,《鹿特丹规则》属于条约,即以国际法的形式体现,而在处理的事项上,其着眼于商事问题,即属于跨国商事交往的以海运为基础的货物运输关系。
(一)以国际条约作为表现形式的跨国商事法律规范
尽管《鹿特丹规则》是国际条约,但处理的仍然是私人之间的关系,而非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一类型的条约与纯公法性质的国际协定不同,例如核不扩散条约、领土条约处理的是国家之间的权利义务,国家直接在条约下为一定的行为,或者不为一定的行为。与具有混合法效果的投资条约也不同,混合条约的典型代表是双边投资保护协定(BITs),它们表面是国家之间的约定,实际则是国家许诺予以投资者的待遇,是将国家与私人之间的义务转化为国家之间的权利义务,国家之间通过条约的方式为私人的权利提供“保护伞”。《鹿特丹规则》处理的是位于不特定国家范围之内的货方和承运人由于跨国运输而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鹿特丹规则》第5条)。
20世纪以后,国际法出现了新的发展方向,具体表现为范围进一步拓展,处理的事项范围从传统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发展到国家与国际组织、国际组织之间、国家与私人、私人与私人。也就是说,国际法在框架和名义上仍然主要是“国家之间的法”,但在内容和实体上已经渗透到个人的生活,不仅表现为国际人权法的大幅度发展,而且表现为以国家的名义确认私人的权利和义务分配。国际商事条约就是在这一背景下的产物(27)。这一类型的条约是对传统的合同法规范进行的矫正。契约自由、意思自治是传统民法的基本理念,但这种自由带来的问题是效率不高、权利义务设定可能不完善,甚至由于交易地位的差异,权利义务设定不公平。在海商法领域,私人力量不均衡的问题非常明显,所以国家力量介入交易之中,营造新的平衡。这种介入源自美国的《哈特法案》,由《海牙规则》国际化,经修订后为《维斯比规则》,另立之《汉堡规则》,则试图在货方保护方面提供新的规范。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本身并不承担条约所规定的实体权利义务,而主要是提供一种地理意义上的法律环境。也就意味着,这一国家属于这一法律规范的领域。
(二)国际商事法律统一化的基本模式
根据国际社会的经验,跨国商事法律规则的统一化有以下几种途径。
一是制定统一的国际公约。一般有国际组织邀请专家对某一问题进行研讨,起草文本,而后召开国际会议,对草案文本进行谈判,谈判议定后作为多边条约通过,开放由各国签署、批准。批准或加入的各国承诺:条约生效以后,在本国领域内施行这一规范,或者在彼此之间的交往中采用这一规范。这一路径的优点是:作为硬法,其实施的范围明确,国家以政府为代表直接参与,增加了相关规则的庄严程度。其缺点则在于:因为条约的参加者是国家,国家所包容的私人种类繁多、利益要求各自不同,条约的内容又是确定私人的权利和义务,所以国家的利益界定难度要比单纯的私人界定大得多,同时,国家的行动成本相比私人也要大得多。这就很容易出现一些条约生效以后,由于各国法律文化的传统差异,或者国内现有规则的兼容性问题,而得不到足够的响应,因而无法生效,或者即使生效,其范围也非常狭窄的情况(28)。
二是制定区域统一实体规范。这是欧洲共同体(前身为欧洲共同体,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之后称为欧盟)成立之后在自由市场的框架下逐渐形成的实践方式。欧洲共同体为了形成一个内部通畅的市场,在立法层面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在共同体的宪法性文件的基础上(29),通过条例(regulations)、指令(directive)、决定(decision)等立法方式,确立了一系列欧盟内部的民商事交往统一法律规范。这些立法由于欧共体法律的优先适用和直接适用原则(30)而直接成为共同体内各成员国的法律规范,并且由欧共体法院保障实施。这种路径的优点是统一性高,确保所有成员国内都自动实施和遵行此种规范;其缺点是需要非常成熟的法律统一化社会环境,成员国范围相对狭窄。所以,欧盟的经验很难复制,无法推广成为国际共同体普遍效仿的对象。
三是编纂国际商事习惯、示范法或者示范合同。鉴于很多国际民商事条约的成本巨大、收效甚微的不成功教训,一些国际组织机构转而采取了放弃硬法努力而尝试采取软法方式确立跨国民商事秩序的实践手段。[9]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包括国际商会(ICC)拟定的《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Incoterms)、《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UCP600),UNIDROIT拟定的《国际商事合同通则》(PICC),国际咨询工程师联合会(FIDIC)拟定的合同条款(31)等。以PICC为例,该通则广泛吸取各法域的成功经验,总结国际合同实践中的共性规范,提出一套具有广泛指导性的规范体系,但并不以公约的形式要求国家参加,而是以推荐参考的模式供各国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国际商事交往的当事人参照采纳。这种相对柔性的方式,反倒使这一规范被更为广泛地接受(32)。ICC拟定的各项国际商事惯例也被广泛采用,具有普遍的适用性。这一方式的优点是节省了国家谈判、签署条约的交易成本(33),而且由于国际私法普遍认可的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34),只要当事人明示或者默示地进行了选择,特别是通过格式合同的方式进行选择(35),这些习惯与国家立法、国际公约具有同等的法律约束力。这种路径的缺点则是很难统计和认定某一软法的实际适用范围及效果。相比这种缺点而言,其优点仍然是明显的。[10]所以,不仅在国际商事领域这种做法方兴未艾,而且在一些与国家之间、国家与私人之间的经济关系领域,这种规范也起着越来越显著的作用(36)。
根据全球治理的理论,多元主体、多重渠道的社会秩序形成方式是当代世界的主要特征(37)。国家与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关系中各自以不同的行为模式发挥自身的作用(38)。这种多元治理模式是我们分析包括海运在内的运输法律规范的发展方向应当考虑的宏观语境之一。
(三)《鹿特丹规则》采取方式的效果探讨
分析《鹿特丹规则》的采取的方式的预期效果,就需要进一步思考:其所设定的宏大目标能否实现?采用国际公约的方式是否明智?应当如何适用?回答这一问题,应当结合国际社会相关领域的实践。包括海运在内的运输属于服务贸易的一种,显然具有民商事法律关系的性质,但是这一法律关系又与每一个国家的主要经济力量在国际经贸关系链条中所处的不同位置直接相关。所以,各国的权利义务配置的侧重点、价值取向殊难一致。这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从《海牙规则》《维斯比规则》直到《汉堡规则》(39),虽然都是国际公约,参加国的数量和国家的发达程度差别很大。如果一项法律规范明显地有利于承运人,则一般地说,只有承运人在本国经济力量中占据明显的优势地位的国家,才有内在的推动力去参与该国际立法;那些托运人、收货人与承运人力量相近或者承运人远不占优势的国家对此则很难赞同。反之,如果一项法律规范倾向于保护货方的利益,或者改变了以往较为偏向于保护承运人利益的传统,则由于承运人是一个相对集中的团体,他们会促动本国政府不去参加此类国际立法。所以,航运大国很少对这样的国际公约表示接受(40)。
就包括海运在内的运输领域而言,UNCITRAL显然采取了第一种方式。1978年的《汉堡规则》在其大力推动之下通过,并于1992年生效,但实际上真正的适用范围并不广泛。美国虽然在条约上签字,却并没有批准(41)。制定《鹿特丹规则》显然抱着比《汉堡规则》更宏伟的目标,不仅处理海运的问题,而且处理包括海运的多式联运(maritime plus),实际上包含、变通地整合了UNCTAD 1980年通过但未能生效的《联合国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公约》的规范。虽然其中的内容具有很大的合理性,不仅符合现代交通、通讯发展所带来的运输技术的新水平(《鹿特丹规则》序言第4段),而且也反映了运输保险发展给运输法律关系带来的新特质(42)。但是,这种以国际公约的方式确立新规则、希求各国参与的方式,可能显得成本过大、预期过高,如果采用示范法的模式,肯定会降低成本,而取得的效果则可能相似。从这个意义上看,考虑多样化的海运立法模式,可能有更好的效果。UNCITRAL之所以坚持采用硬法的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于建构理性的路径依赖。也就是,从《海牙规则》以来,国际社会一直试图统一海运规范,一直采用国际条约的方式,而没有充分考虑其他替代方式的现实可行性。
当然,也可以预期,经过一段时间的尝试、探索、试错与磨合之后,各国逐渐认可了《鹿特丹规则》,使其接受的范围更加广泛,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的国际运输法。
莫世健教授认为,《鹿特丹规则》的通过开启了一个新海运时代,即“鹿特丹时代”。《鹿特丹规则》内容本身的相对科学性和合理性以及多个贸易和航运大国对该规则所采取的积极态度,都预示着“鹿特丹时代”到来的不可避免性。[11]
有些观点则认为,《鹿特丹规则》的抱负难于在近期实现。因为公约“在一些规定上过于理想化,或者说学理化。比如说解决无单放货问题的规定现在看没有实践基础,完全是凭空制定出来的,究竟效果如何,需要实践检验。还有承运人识别问题,实际上是没有考虑公约适用范围扩大的情况,而是套搬了各国在解决海上运输承运人识别的规定。公约试图作出各方面的全面规定,结果导致公约结构和内容都很复杂,在实践中需要一个很长的熟悉过程”。[12]
笔者认为,也许用更长的时间尺度来衡量,采纳《鹿特丹规则》、迎接“鹿特丹时代”的观点有其道理,但就目前而言,这种趋势还不算不太明朗,尚有待于进一步观察。
四、中国对待《鹿特丹规则》应考量的因素
前文已述,关于中国对《鹿特丹规则》的立场或者态度,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在笔者看来,这些观点,除了各自背景与视野的差异,本质上并无明显的冲突,只是有一些更强调理想和应然,有一些则强调现实。笔者认为,站在认清现实,并对现实进行引领和批判的角度,首先应当确定《鹿特丹规则》中国立场时应当考量的因素。其中,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值得留意。
(一)中国在《鹿特丹规则》所涉领域的利益取向
根据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国家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单纯的、如个人一样有着明确的利益取向、意志倾向的行为体。国家更适合于被理解成为有诸多利益取向不同的、意志与愿望存在很大差异的行为体构成的组合。如果说在纯粹的国际公法问题上,这种利益差异都可以表现出来的话(43),那么,在国际商事条约的语境下,这种多元利益诉求的情况就更为明显了。
正如在1980年CISG的体系下,没有任何参加国是纯粹的买方,也没有任何参加国是纯粹的卖方一样,在《鹿特丹规则》的框架下,也不会有一个国家纯粹是承运人,或者纯粹是货方。
莫世健教授认为,拥有贸易大国和航运大国的双重利益身份,应对《鹿特丹规则》采取积极研究和推动的态度,争取建立中国在“鹿特丹时代”国际海运秩序构建中的主导地位,以确保其最大利益。[11]笔者认为,这诚然是非常良好的愿望,也可能符合中国政府和学者的期待,但是,这似乎并不符合国际社会格局与中国发展的客观现实与近期趋势。
从中国的运输企业利益定位看,中国是一个海运大国,但并不能算是一个海运强国。具有高水平航海服务能力的中国香港地区,在遵循的法律规则上并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简称《海商法》)(《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三),也不会在不经征询其意见的情况下,适用中国所参加的国际条约(《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153条)。中国内地的船舶总吨位比较高,但从总体上看,技术和管理并不算太先进(44),而且还有很多吨位仅限于内河和沿海运输,也就是不适用《海商法》(45)。也就是说,虽然具有很大的容量,但并不够发达。这样一来,航运领域虽然有较为明显的利益团体,但这些团体之间的观点可能是不一致的。因而就不能说,中国政府的利益界定应当与航运界的取向相一致。
与此同时,从中国的进出口企业利益定位看,中国又是一个贸易大国,不仅是世界重要的货物生产加工国,也是巨大的市场。这就意味着需要大量的货物进出口。无论是中国制造的商品的出口,还是中国加工所需的原材料以及设备、消费品的进口,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包括海运在内的运输服务。但是,从利益代表和表达上看,托运人和收货人(货方)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缺乏统一性,不像承运人那样相对集中、专业化、经常化,而是表现为较为分散和非专业,因此,难于形成一个统一的声音(46),由此也无法判定货方的利益取向就是中国的利益界定基础。
《鹿特丹规则》的核心就在于承运人一方与货方之间的权利义务配置,从前述分析可知,对于《鹿特丹规则》所涉及的两个主要方面,中国都有重大的关切,所以,很难以抽象的概念来看待《鹿特丹规则》语境下的中国利益,而必须进行具体、深入的分析,并给出建立在比较基础上的结论。既然中国在船货双方均有利益需求,那么,在两者自身利益界定尚未明确,两者之间的关系也难于衡量轻重的前提下,更为妥当的结论是,当前中国不存在明显地促动或者疏离《鹿特丹规则》的利益导向。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不足是现实,中国对于国际产品定价的决定权不足也是现实。在认定这一前提的基础上,有必要进一步考量积极加入《鹿特丹规则》是否足以改良中国在国际社会所处的不利位置。这也就意味着,如果对规范没有全面深入的审视,在没有对中国的利益进行清晰界定之时,就加入这一规则,很可能像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接受特别保障措施的状况一样,损害国家利益(47)。
当然,从国际法的角度看,包括《鹿特丹规则》在内的国际条约分为签署和批准(接受、加入)等不同环节,签署条约本身并不带来相关权利和义务的落实,而仅仅意味着对国际社会推动海运立法发展所持的肯定态度,表明中国在国际立法的引领地位。
(二)采纳《鹿特丹规则》并不导致中国相关领域的“帕累托改进”
正由于在《鹿特丹规则》所涉及的领域,中国的船方和货方两个方面都有着相当大的分量,所以《鹿特丹规则》对于既有海运承运人责任区间、归责原则所进行的改变,对于中国相关利益方的影响就会是复杂的,而无法单一化、简单化认识。
中国现有的国际海运法律规范在承运人责任方面的基本实体规范以《海牙-维斯比规则》为蓝本,在部分问题和形式要件上参照了《汉堡规则》。这一制度设计在以往近20年的实践中并没有遇到明显的困难、阻碍,或者批评,反倒是受到了广泛的好评,甚至得到有关国家的效仿。就此可以认为,这些规则的设计时比较合理和成功的。
如果改用实施《鹿特丹规则》,则虽然名义上有利于货方,表面上建构了一个更为公平合理的船货双方权利义务体系,但事实上,根据海运服务的一般实践,这种改革更多只是程序意义上的,而非实体意义上的;或者把原有的义务安排从这一当事人转移到另一当事人,或者交易的其他参与方(48)。这种为一方创设权利,为另一方增加义务的制度安排,并没有增加所有参与人的福利,所以这种公平合理很难在短期内做出有效的评估。而理想的、具有实际意义的制度改进则应当通过“帕累托改进”,也就是增进所有当事人的福利,或者在不减少既有当事人福利的情况下增加部分当事人的福利,由此实现“帕累托最优”。从中国《海商法》现有的规则、《海牙-维斯比规则》现有的规则到《鹿特丹规则》设计的规则,对于具有广泛的船货双方利益的中国而言,并不是帕累托改进。
(三)暂不加入《鹿特丹规则》并不意味着中国被拒于该体系之外
《鹿特丹规则》第5条规定:
“1.除第6条另有规定外,本公约适用于收货地和交货地位于不同国家,且海上运输装货港和同一海上运输卸货港位于不同国家的运输合同,条件是运输合同约定以下地点之一位于一缔约国:
(a)收货地;
(b)装货港;
(c)交货地;或者
(d)卸货港。
2.本公约的适用不考虑船舶、承运人、履约方、托运人、收货人或者其他任何利益方的国籍。”
《鹿特丹规则》第66条规定:
“除非运输合同载有一项符合第67条或者第72条的排他性法院选择协议,否则原告有权根据本公约在下列管辖法院之一对承运人提起司法程序:
(a)对下列地点之一拥有管辖权的一管辖法院:
(ⅰ)承运人的住所;
(ⅱ)运输合同约定的收货地;
(ⅲ)运输合同约定的交货地;或者
(ⅳ)货物的最初装船港或者货物的最终卸船港;或者
(b)为裁定本公约下可能产生的向承运人索赔事项,托运人与承运人在协议中指定的一个或者数个管辖法院。”
根据如上两条规定,从国际私法的运行过程的角度可以得出下面的结论:在《鹿特丹规则》生效之后,在如下情况下该规则可能与我国的有关方面产生联系:(1)如果中国货方作为托运人或收货人与外国船方签订或者履行合同或者部分合同,而合同的履约地点位于《鹿特丹规则》的参加国之内;(2)中国船方作为承运人与外国货方作为托运人、收货人签订或者履行合同或部分合同,而合同的履约地点位于《鹿特丹规则》的参加国之内;(3)中国货方作为托运人或收货人与中国船方作为承运人,签订或履行合同或者部分合同,而合同的履约地点位于《鹿特丹规则》的参加国之内;(4)外国货方作为托运人或收货人与外国船方作为承运人,签订或履行合同或者部分合同,而合同的履约地点位于《鹿特丹规则》的参加国之内,在中国法院提起诉讼或者到中国仲裁机构提起仲裁。
当然,这种适用仅仅是可能性,而非必然性。因为这还进一步取决于运输合同争端解决所在国是否具有强行法(强制适用的法);在没有强行法的情况下,当事人所进行的法律选择(如果存在),或者在没有法律选择的时候,法院、仲裁庭认定的准据法(例如根据最密切联系原则)。也就是说,中国的货方、船方、法院、仲裁机构均可以通过合同选择或者法律选择、争端解决的方式接触并适用《鹿特丹规则》,而不至于完全隔绝于该规则之外。这与美国相关法律的适用颇有相似之处(49)。此种法律适用的情况意味着,即使不加入《鹿特丹规则》,在该规则生效后有关方面也可以通过实践的方式评估这一规则适用的效果,可以从容地实验和观察,分析适用的利弊。
五、中国对《鹿特丹规则》立场的确立
《鹿特丹规则》以良好的愿望、多方的努力为统一海上货物运输甚至是与海运相联系的多式联运法律规范进行了尝试。不过,由于其涉及的范围过于广泛,试图创设和建构的制度过于繁杂,又采取了以国家签署为入门基础的条约的模式,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生效进程。
中国在《鹿特丹规则》上的立场是由自身的经济状况与中国的利益取向决定的。从过程上看,中国代表全面参加了《鹿特丹规则》的谈判,并提出了一系列的提案,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有的提案没有被采纳,但是这一过程有益于专家对该规则有较为深入的认识。在《鹿特丹规则》通过以后,有些部门进行了相关调查,但结果还不算明朗,对于相关决策的影响尚不直接。在调查不全面深入、结果不清晰的情况,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些学者倾向与积极加入《鹿特丹规则》,另一些学者提倡谨慎了。
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在国外,学界和各利益团体对于《鹿特丹规则》的立场和认识仍有些不统一。欧洲议会关于《2018年前欧盟海运政策战略目标及建议》的2010年5月5日决议[2009/2095(INl)]明确建议欧盟成员国应当推动《鹿特丹规则》的尽快签署、批准和执行,以构建崭新的海事责任体系。[13]美国海商法协会(Maritime Law Associ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侵权审理和保险实务部(Tort Trial and Insurance Practice Section)、国际法部(International Law Section)在2010年2月向美国议会提交的报告中,请求美国众议院敦促参议院批准这一公约(50),很多美国学者也主张尽快根据《鹿特丹规则》推动美国海上货物运输法的现代化。[14]FIATA海上运输工作组建议各成员建议本国政府不接受《鹿特丹规则》(51);欧洲物流协会则认为,比起以往的规范,《鹿特丹规则》没有提供什么利益,它已经发展为一个极为复杂的法律文件,而没有达到法律规范应有的清晰和明确(52)。
立场形成与作用的过程是一个以经济利益为基础来确定政治立场,进而确立法律决策和做出秩序选择的复杂过程。从中国政府的角度,还有必要收集更加充分的信息,进行更为翔实的效果预测。在没有足够的理由认为新的制度从实施效果上有利于中国的整体利益之时,不贸然加入规则更有利于秩序的维护。所以,中国对于《鹿特丹规则》应采取审慎的态度,保留着参与的可能性(53)。同时应当铭记的是,重要的不在于结果,而在于是否能以公开、透明的方式,确定选择结果。
当然,法律不仅仅是对现实的描述,也包括对未来的期许。法律在很多时候都应当被理解为是一个价值排序表,即法律保护什么、鼓励什么、容忍什么、打击什么。也就是说,法律还有指引的功能。如果从这个角度来分析的话,中国政府还有必要进一步考虑,我们试图实现一个什么样的运输体系?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可能比前一问题更为复杂,需要的信息数据、分析更加全面。在这个阶段,值得考虑的是,利用既有国际立法的一些尝试以及其他国家立法的一些经验来修订《海商法》(54),在国内创制一个相对公平、妥当的国际体系(55)。
从中国的国家立场上看,中国更适合表达这样的观点:首先应当肯定国际社会为航运服务法律发展做出的积极努力,也应当指出,很多制度设计本身还存在着缺陷,国际海事立法的统一化需要在实践中探索和逐渐成熟。中国期待着在实践中渐进地检验和改良相关的规范,在积极参与这一规范体系形成的基础上,进一步与该规范体系保持密切的联系,并在该规则相对成熟的时候加入这一规范体系。在《鹿特丹规则》发展的过程中,中国作为全面参与《鹿特丹规则》确立的国家,可以通过签署的方式表达中国对于国际货运规范制定的决定意义。
注释:
①例如,一些当时出版的教材就介绍了这一立法的进展。参见司玉琢主编《海商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64-167页。
②参见姚新超撰写的《简评〈鹿特丹规则〉》,载《对外经贸实务》2009年第12期;孙勇志撰写的《“鹿特丹规则”新变化与影响力》,载《中国远洋航务》2010年第8期;蒋正雄撰写的《〈鹿特丹规则〉:海商法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
③除了后文涉及的文献,参阅王欣撰写的《简评〈鹿特丹规则〉对中国外贸的影响》,载《中国海商法年刊》2010年第3期。
④“公约较好地维护和平衡了港口经营人、货主和船公司的利益,特别是从根本上解决了港口经营人的民事法律地位问题,使港口经营人的利益获得了最大限度的保护。有利我国航运经济关系的稳定,有助于海事司法实践的统一,对保障港口经营活动的良好秩序,促进贸易和航运的进一步发展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参见黄应军撰写的《〈鹿特丹规则〉港口经营人责任制度的分析比较》,载《中国港口》2010年第8期第56页。其他相关论文还有王威撰写的《我国航运业引入〈鹿特丹规则〉的障碍及其解决路径选择——以港口履约方无单放货为例》,载《社会科学家》2010年第10期;韩立新撰写的《〈鹿特丹规则〉对港口经营人的影响》,载《中国海商法年刊》2010年第1期;侯佳洁撰写的《〈鹿特丹规则〉对我国港口经营人责任限制问题的启示》,载《中国水运(下半月刊)》2010年第8期;易传剑撰写的《〈鹿特丹规则〉对我国港口经营人民事责任限制的影响及其发展》,载《法制与社会》2010年第5期。
⑤相关论文如刘兴莉撰写的《海事货物索赔管辖权的国际统一——评〈2008年鹿特丹规则〉第14章管辖权规则》,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刘兴莉撰写的《国际公约下扣船法院实体管辖权行使的限制——评〈鹿特丹规则〉第70条》,载《中国海商法年刊》2010年第2期;吴蕾撰写的《鹿特丹规则管辖权规定及对我国的借鉴》,载《企业导报》2011年第3期;蒋俊鸿撰写的《鹿特丹规则管辖权规定评述——兼谈对我国海事司法的影响》,载《商业文化(学术版)》2009年第12期;徐艳如撰写的《浅析〈鹿特丹规则〉中的仲裁问题》,载《中国海商法年刊》2009年第4期。
⑥相关论文如陈琦撰写的《〈鹿特丹规则〉下非海运区段不优先适用国内法之利弊分析》,载《中国海商法年刊》2009年第3期。
⑦商务部委托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海商法研究中心,针对《鹿特丹规则》对我国外贸的影响进行研究和评估,并提出应对《鹿特丹规则》适用的政策、措施和建议。研究结果表明,《鹿特丹规则》对货方来说有利有弊,多数货主从整体上持积极态度,中国政府应以客观全面、积极、审慎的态度对待《鹿特丹规则》。在审议通过课题报告的基础上,相关专家提出,有必要进一步明确中国政府对待《鹿特丹规则》的态度。参见《条法司组织专家对“〈鹿特丹规则〉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课题进行终期评审》一文,载http://tfs.mofcom.gov.cn/aarticle/bc/201103/20110307442103.html。
⑧“如果中国加入《鹿特丹规则》,对我国国内航运业、物流业等将会产生不同作用与影响;将对中国的司法实践造成困惑;也将使中国国际航运、物流业面临因适用《鹿特丹规则》与运输路经国的国内法冲突而带来的难以预期的风险。”参见孙勇志、郭春风撰写的《〈鹿特丹规则〉“适用范围”的比较研究》,载《青岛远洋船员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第1-6页。其他相关论文如郭萍撰写的《从货方的视角看〈鹿特丹规则〉》,载《中国海商法年刊》2010年第2期;夏庆生撰写的《〈鹿特丹规则〉对卖方(货主)的影响》,载《中国海商法年刊》2010年第2期;汪忠华撰写的《〈鹿特丹规则〉下托运人义务变化的初探》,载《对外经贸实务》2010年第2期;李凌撰写的《从承运人视角看〈鹿特丹规则〉》,载《水运管理》2010年第5期。
⑨参见邹盈颖撰写的《中国法视角下对〈鹿特丹规则〉评估的认识》,载《法学》2010年第11期;姜绍甜撰写的《中国是否应该加入鹿特丹规则?——运用利益分析法分析》,载《中国商界(下半月)》2010年第9期。
⑩CMI于1897年成立于安特卫普,是海商法领域影响广泛的非政府、非营利组织,目标是采取各种措施促进海事法的统一化。其草拟和制订的《约克一安特卫普规则》、1987年《里斯本规则》以及《电子提单规则》《海运单规则》等,对航运界的意义非常巨大。与UNCTAD、国际海事组织(IMO)有着长期的合作,《关于海上旅客及其行李运输的雅典公约》《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公约》《海难救助公约》《船舶优先权、抵押权公约》《扣船公约》均有其贡献。
(11)相关阐释,请参见《开启鹿特丹时代——司玉琢解读〈鹿特丹规则〉》,载《中国远洋航务》2009年第5期。
(12)该公约于1980年5月24日在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全权代表会上通过,但至今未能生效。签署国有智利、墨西哥、摩洛哥、挪威、塞内加尔、委内瑞拉6国,批准国有布隆迪、智利、格鲁吉亚、黎巴嫩、利比里亚、马拉维、墨西哥、摩洛哥、卢旺达、塞内加尔、赞比亚11国。按公约规定,30个国家接受该公约后12个月生效。2005年之后,该公约就不再有新的国家考虑,所以看来生效的机会已经不存在了。参见http://r0.unctad.org/ttl/docs-legal/unc-cml/status/UNConventionMTofGoods,1980.pdf。
(13)英国在二战中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就体现了民间海上运输能力在武装冲突中的重要作用。
(14)对于海上货物运输法律规范发展的分析,可参见马得懿撰写的《海上货物运输法理论流变的哲学回应》,载《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9年第2-3期。
(15)相关论文如Gertjan Van Der Ziel撰写的Chapter 10 of the Rotterdam Rules:Control of Goods in Transit,载Texas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2009年第375页;向力撰写的《论货物控制权——以〈鹿特丹规则〉货物控制权规定为中心展开》,载《武大国际法评论》第12卷(2010年);许硕撰写的《鹿特丹规则下货物控制权的性质辨析》,载《中州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吴煦、司玉琢撰写的《〈鹿特丹规则〉中货物控制权之法律性质》,载《中国海商法年刊》2011年第1期;费宏达撰写的《〈鹿特丹规则〉视野下FOB条件下卖方之货物控制权》,载《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费宏达撰写的《国际海运法之新发展——兼评〈鹿特丹规则〉之货物控制权制度》,载《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赵亮撰写的《〈鹿特丹规则〉之控制权的中国司法实践和立法反思》,载《中国海商法年刊》2009年第1期。
(16)相关论文如王秋雯撰写的《区别而论的责任体系:〈鹿特丹规则〉履约方制度的引入——兼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的选择》,载《中国海商法年刊》2010年第4期;王威撰写的《〈鹿特丹规则〉中海运履约方赔偿责任的理论探讨》,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陈玉梅撰写的《论〈鹿特丹规则〉对履约方的规制——对我国多式联运中运输责任主体的反思》,载《法学杂志》2010年第8期。
(17)相关论文如韩立新撰写的《〈鹿特丹规则〉下可流通提单“物权凭证”功能沦丧抑或传承?》,载《中国海商法年刊》2010年第3期;韩立新撰写的《〈鹿特丹规则〉下记名提单“物权凭证”功能考探》,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李小年撰写的《〈鹿特丹规则〉对不可流通运输单证的法律协调》,载《中国海商法年刊》2010年第1期;张敏、王亚男撰写的《〈鹿特丹规则〉对提单制度的影响》,载《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傅廷中撰写的《〈鹿特丹规则〉视角内提单的物权凭证功能之解析》,载《中国海商法年刊》2010年第2期;吕鸣撰写的《〈鹿特丹规则〉下提单功能的缺失与重塑》,载《国际商务研究》2010年第4期。
(18)相关论文如张湘兰、向力撰写的《〈鹿特丹规则〉货物交付制度探析》,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李笑黎撰写的《〈鹿特丹规则〉下无单放货解决机制:从凭保函放货到凭指示放货》,载《中国海商法年刊》2011年第1期;李伯轩撰写的《论〈鹿特丹规则〉中的无单放货问题》,载《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卢小青撰写的《〈鹿特丹规则〉规制无单放货之新动向》,载《世界海运》2010年第10期;王堉苓撰写的《简评〈鹿特丹规则〉对无单放货之规定》,载《中国海商法年刊》2009年第3期;祁欢撰写的《〈鹿特丹规则〉对无单放货承运人责任制度的影响》,载《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陆玉撰写的《浅析〈鹿特丹规则〉中的无单放货》,载《知识经济》2010年第6期。
(19)相关论文如司玉琢撰写的《承运人责任基础的新构建——评〈鹿特丹规则〉下承运人责任基础条款》,载《中国海商法年刊》2009年第3期;李伯轩撰写的《论〈鹿特丹规则〉对承运人的影响——以承运人的义务与责任为视角》,载《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孙勇志撰写的《试论〈鹿特丹规则〉的新变化及国际影响力》,载《交通企业管理》2010年第8期;向力撰写的《国际海运业承运人责任体制的传承与发展——〈鹿特丹规则〉承运人责任规定介评》,载《中国海商法年刊》2009年第4期;赵春燕撰写的《〈鹿特丹规则〉对承运人责任变化的分析》,载《对外经贸实务》2011年第3期;王建伟撰写的《〈鹿特丹规则〉取消航海过失免责对船货双方的影响及其应对措施》,载《集装箱化》2010年第11期;孙勇志撰写的《应关注“鹿特丹规则”对承运人法律责任的修改》,载《中国远洋航务》2009年第3期。
(20)例如,法国大革命就是在美好的梦想中陷入混乱和恐慌之中,最后非但没有使法国真正进入民主社会,反倒引致拿破仑称帝。
(21)例如,中国古代的王莽改制、王安石变法,都是因为不能很好地考虑当时的社会现状,步子迈得过大,而没有取得成功,迅速地被推翻。
(22)有学者认为,面对FOB条件下卖方法律地位的问题,《鹿特丹规则》引入的“单证托运人”这一概念,虽然立法思想可取,制度设计存在若干不合理之处,因而不仅不能给FOB贸易下的卖方提供充分的保护,还可能使其面临更大的法律风险。关于可转让运输单证下的无单放货问题所设计的机制不仅可能不实用,而且还会产生相当多的法律问题,因而是不成功的。参见蒋跃川、朱作贤撰写的《〈鹿特丹规则〉的立法特点及对其中涉及重大利益的几个问题的分析》,载《中国海商法年刊》2010年第1期第26-34页。
(23)例如,李小年认为,考虑到各国迥异的国内法,《鹿特丹规则》有关海运单和记名提单的规定要求航运与贸易界对各国不同的法律规定比较熟悉,因此给业界的非法律专业人士带来了很多困难,在现实中仍有不确定性。(参见李小年撰写的《〈鹿特丹规则〉对不可流通运输单证的法律协调》,载《中国海商法年刊》2010年第1期第41-48页。姚莹提出,《鹿特丹规则》对承运人“凭单放货”义务进行了重大变革,但相关制度设计并未实现便利交易的目标,同时削弱了交易的安全性。参见姚莹撰写的《〈鹿特丹规则〉对承运人“凭单放货”义务重大变革之反思——交易便利与交易安全的对弈》,载《当代法学》2009年第6期第120页。
(24)参见陈敬根、关正义撰写的《〈鹿特丹规则〉下混合原因致货物毁损时赔偿责任的分担》,载《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袁发强、马之遥撰写的《平衡抑或完善——评〈鹿特丹规则〉对海运双方当事人权利与义务的规制》,载《中国海商法年刊》2009年第4期;杨晶撰写的《试论〈鹿特丹规则〉下托运人义务之强化》,载《中国海商法年刊》2009年第1期;姚新超、冷柏军撰写的《〈鹿特丹规则〉下贸易商权利与义务的变化》,载《国际贸易问题》2009年第11期;许俊强撰写的《收货人提取货物的义务——兼评〈鹿特丹规则〉第43条收货人接受交货义务》,载《中国海商法年刊》2009年第3期;朱作贤撰写的《论2008年〈鹿特丹规则〉对限制“合同自由”的突破》,载《理论界》2009年第12期;张丽英、景晴撰写的《〈鹿特丹规则〉下批量合同相关法律问题探析》,载《中国海商法年刊》2010年第3期;胡长胜撰写的《论〈鹿特丹规则〉批量合同下的货方利益保护》,载《武大国际法评论》第12卷(2010年)。
(25)於世成教授认为,“鹿特丹规则的前景并不明朗,对船、货双方的利弊还需要进一步分析;制度创新尚需要实践检验;国际接受程度还不明朗。就我国而言,鹿特丹规则可能加重航运业的负担,如‘管货义务’的转移,可能增加货主的谈判成本。《鹿特丹规则》适用于多式联运合同之后,可能很难在短时间内被我国各地法律所接受。”参见於世成撰写的《鹿特丹规则前景并不明朗》,载http://www.cnss.com.cn/article/32130.html。
(26)关于《鹿特丹规则》起草与发展的过程,参见凯特·兰纳撰写的《〈鹿特丹规则〉的构建》,载《中国海商法年刊》2009年第4期第3-4页。
(27)此种条约自知识产权领域开始,主要体现在国际货物买卖领域,例如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
(28)例如,国际私法会议通过的很多公约都缺乏广泛的约束力。1978年海牙《代理法律适用公约》虽然生效,但只有4个成员国;1985年通过的《关于信托的法律适用及其承认的公约》情况略好,有9个国家接受该公约;1989年通过的《死者遗产继承法律适用公约》、2000年通过的《关于成年人国际保护公约》至今尚未生效。参见李双元主编的《国际私法(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29页、第247页、第457页。
(29)欧共体基础条约包括《罗马公约》《欧洲单一法令》《马斯特里赫特条约》《阿姆斯特丹公约》《里斯本条约》。
(30)关于欧盟法的优先适用、直接适用,参见Paul Craig and Gráinne de Búrca,EU Law:text,Cases,and Materials,5th e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pp.178-229
(31)1957年,国际咨询工程师联合会首次出版了标准的土木工程施工合同条件,在此之前还没有专门编制的适用于国际工程的合同条件。第1版以当时正在英国使用的土木工程师学会的《土木建筑工程一般合同条件》为蓝本。由于该标准合同的封面为红色,故很快以“红皮书”而闻名世界。第2版于1963年发行,只是在第1版的基础上增加了用于疏浚和填筑合同的第三部分,并没有改变第1版中所包含的条件。第3版于1977年出版,对第2版作了全面修改,得到欧洲建筑业国际联合会、亚洲及西太平洋承包商协会国际联合会、美洲国家建筑业联合会、美国普通承包商联合会、国际疏浚公司协会的共同认可,并经世界银行推荐,将FIDIC条件第3版纳入了世界银行与美洲开发银行共同编制的《工程采购招标文件样本》。可见,FIDIC条件第3版已获得国际上的广泛认可和推荐。第4版于1987年出版,1988年做了订正。此次修订FIDIC比以往修订时更多地与世界银行进行了协商。同时,还与在监督第3版的使用方面颇有经验的阿拉伯联合基金会的代表们进行广泛的接触。第4版在第3版的基础上经协商作了较多的修改。在第4版修订中,还同意承包商代表在起草过程中的咨询地位,最后定稿由FIDIC全权负责。FIDIC条款虽然不是法律,但却为全世界公认的一种国际惯例。
(32)关于PICC的意义,参见左海聪撰写的《试析〈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的性质和功能》,载《现代法学》2005年第5期。
(33)科斯定理认为,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时候,初始权力配置并不重要。但实际上,交易成本从不为零。
(34)关于意思自治,参见徐冬根主编的《国际私法》,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03-104页。
(35)格式合同在国际商事交往中普遍应用。
(36)例如,美国、德国的双边投资协定范本,联合国、OECD推出的税收协定范本等。
(37)关于全球治理的特征,参见俞可平著《全球化:全球治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版第1-22页。
(38)非政府组织在国际治理中起的作用越来越大。有关讨论参见黄志雄撰写的《非政府组织:国际法律秩序中的第三种力量》,载《法学研究》2003年第4期。
(39)关于《汉堡规则》的基本背景、过程与文本,参见Final Act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he Carriage of Goods by Sea,Document A/CONF.89/13。
(40)至2011年6月初,《汉堡规则》共有34个参加国,而曾经签署过该公约的一些国家,如巴西、丹麦、芬兰、法国、德国、瑞典、葡萄牙、新加坡、瑞典、美国,都没有批准这一公约。具体情况参见http://www.uncitral.org/uncitral/en/uncitral_texts/transport_goods/Hamburg-status.html。
(41)由于美国的三权分立传统,国家代表签订的条约需要国会通过才能批准,而国会很可能否决加入该条约的议案。所以,在历史上,美国经常出现签订条约却不批准的情况,无论是《国际联盟盟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约》,还是建立国际贸易组织的《哈瓦那宪章》,美国都没有批准。
(42)参见《鹿特丹规则》序言第4段。有关分析参见凯特·兰纳撰写的《〈鹿特丹规则〉的构建》,载《中国海商法年刊》2009年第4期第2页该文特别提到“现行制度忽视了对于现代运输业来说极为重要的两个方面:一是在过去的五十多年里,集装箱运输的发展十分迅速,已经极大地改变了海上货物运输业的面貌……二是现代贸易越来越多地使用无纸化交易。”
(43)例如,国际贸易法中的反倾销、反补贴规范对于进口国而言,主要对同一行业的生产者有利,而对消费者不利。WTO将这些规则确立为国际规范,显然意味着国家背后生产者的力量具有更大的压力。
(44)目前中国的海上商船队中,杂货船数量最多,其次为散货船、油船、客货船、客船等,船队船龄较老。近年新添了滚装船、集装箱船和多用途船。
(45)我国船舶运输的法律现状是,远洋运输适用《海商法》第四章的规定,承运人享有航海过失免责权,并享有责任限额。内河及沿海运输适用《合同法》及交通运输部的《国内水路货物运输规则》等关行政规章,实行严格责任制度,承运人的航海过失不能免责;承运人在运输过程中造成货损货差,承运人按受损货物的实际价格进行赔偿,没有最高赔偿限额。有关讨论参见倪学伟撰写的《航海过失免责存废论》,载《海商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46)根据张丽英教授的调查,“很多企业认为有关运输的国际立法与他们没有太大的关系,认为把货物交给物流公司就算了,不用货主公司太操心”。对于《鹿特丹规则》的各项改革,很多货主认为存在缺陷,增加了货方负担,或者难于实现。参见张丽英撰写的《〈鹿特丹规则〉对中国进出口贸易影响的调研》,载《中国海商法年刊》2010年第4期。
(47)相关论文参见何志鹏撰写的《WTO法治的中国立场》,载《国际经济法学刊》第17卷第4期(2000年)。
(48)例如,承运人免责的时候,货方向其保险人请求理赔;而承运人不能免责时,则由承运人向其保险人追偿。
(49)一般提单中会规定“地区条款”,即运往或来自美国的货物,应受《1936年海上货物运输法》的约束。参见司玉琢主编的《海商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41页。
(50)"As sea carriage is predominantly an international activity,uniformity and predictability are much desired.In practice,the existing conventions remain subject to each nation's interpretation,resulting in further complication."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Maritime Law Associ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Tort Trial and Insurance Practice Section,Sec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Report to the House of Delegates.
(51)FIATA Position on the UN Convention on Contrac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Carriage of Goods wholly or partly by Sea(the "Rotterdam Rules").Doc.MTI/507,Annex II.
(52)The European Voice of Freight Logistics and Customs Representatives,CLECAT,aisbl (n° 0408301209),Brussels,11th of May 2009.
(53)在这个意义上,於世成教授的观点值得肯定:应从定性研究转到定量研究,如对承运人责任加重,对其管理成本的增加到底会有多大,是否能被我国航运企业所接受。让行业各企业积极参与调研;对《鹿特丹规则》的评估不能局限于某一个行业,同时应该兼顾不同发展层次的企业,另外,还应该考察其是否有利于增强我国航运业的国际竞争力。参见於世成撰写的《鹿特丹规则前景并不明朗》,载www.cnss.com.cn。
(54)参见梁慧星撰写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的建议》,载http://www.iolaw.org.cn/showNews.asp?id=21329。
(55)很多海商法学者持续关注《海商法》的修改,并提出了很多内容充实、论证扎实的建议。参见司玉琢、胡正良撰写的《谈我国〈海商法〉修改的必要性》,载《中国海商法年刊》2003年第1期;司玉琢、胡正良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修改建议稿条文参考立法例说明》,大连海事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司玉琢、李志文主编《中国海商法基本理论专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张永坚撰写的《中国〈海商法〉修改之泛论》,载《海商法研究》(总第3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张永坚撰写的《究其细微,考其全貌——再议中国〈海商法〉之修改》,载《海商法研究》(总第4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标签:鹿特丹规则论文; 海牙规则论文; 国际多式联运论文; 法律规则论文; 立法原则论文; 商事主体论文; 海运论文; 法律论文; 航运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