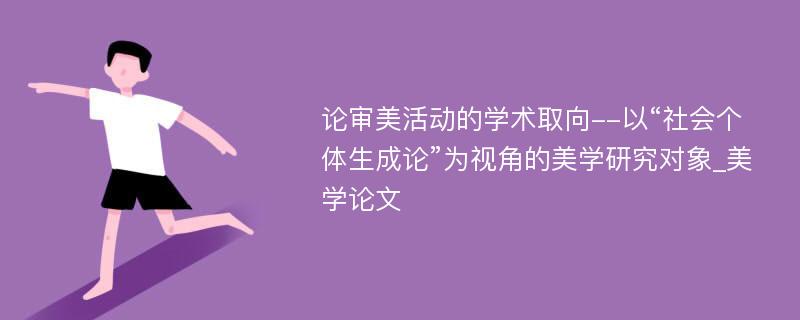
论审美活动的学术定位——从“社会个体生成论”看美学的研究对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学论文,研究对象论文,个体论文,学术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于任何一位秉承严格的学术批判研究精神而从事美学研究的学者来说,“究竟应当如何研究美学”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根本性问题——如果说两个世纪之前的美学研究者,还可以由于现代艺术没有崛起、人们的日常生活尚未走向符号消费,而仍然以传统认识论的研究方式不断追问“美是什么”、因而根本不用认真考虑这个问题的话,那么,当今的美学研究者则再也没有这样的“福气”了。因为无论通过概略回顾美学研究的历史、了解两千多年来的美学家都一直没有为“美是什么”找到任何可靠答案,还是着眼于20世纪以来的美学研究现状,目睹当今既无法弥合传统美学观与现代艺术观之间的断裂、又对目前的“审美泛化”(aestheticization)束手无策(注:当然,这里所谓“束手无策”,只是就严格意义上的美学研究而言,而不是指通过引入其他非哲学学科的研究视域而继续进行的探讨和研究;毋庸赘言,即使这样的“引入”也没有从根本上为美学研究开辟新的天地,反倒是因为绝大多数研究者失去了继续在哲学层次上进行探讨的兴趣,而使这样的美学研究止步不前了。)的现实,我们都不能不切实面对这个实际存在的重要问题。那么,究竟应当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在我看来,正像一个军事指挥员在久攻一座堡垒而不克时,就需要及时考虑调整攻击的角度和方式那样,在面对美学研究有史以来已经出现的所有这些尴尬处境时,我们显然也有必要认真考虑一下以往的美学大家们用于进行各自研究的角度和方式,而不应当仅仅着眼于他们所得出的结论是什么。
因此,“究竟应当如何研究美学”并不是一个“耸人听闻”抑或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伪问题,而是我们今天的美学研究必须充分重视、认真对待的关键性问题。
为什么强调“学术定位”——解开常识和西方研究模式形成的“死结”
这里所谓“学术定位”之中的“学术”,强调的既不是“闭门造车”的“纯学术”,也不单纯是已经作为研究结果而存在的各种研究结论;它更多的是强调研究者必须从审美活动的现实环境出发,认真批判反思被其用来得出各自研究结论的基本立场、思维框架和方法论视角,找到美学进一步健康发展的道路——毋庸赘言,综观国内近代以来出现的各种美学研究所采用的具体方式,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绝大多数研究者基本上只停留在学术研究的“常识”(common sense)(注:毋庸赘言,研究者所具有的“常识”不同于、甚至可以说“高于”普通人的常识,不过,在我看来,这两者之间充其量只是程度上的差异、而不是本质方面的不同,因为从根本上说,它们都流于“熟知”、都是未加严格的、哲学层次上的批判反思的思维水平;尽管这种水平或者状态实际上构成了更高层次的认识、实践和伦理评价乃至审美活动的基础和母体,但纯粹处于这种状态显然是不可能得到“真知”的。)层次上,亦即只关注前人和同时代人所得出的研究结论是什么,而很少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究使这些研究结论得以产生出来的,研究者所运用的基本立场、思维框架和方法论视角:无论出自某一“门派”的研究者对其特定的美学研究“学统”的恪守和承续,还是更一般的研究者所谓“引经据典”之举及其崇敬心态,都比较鲜明地表现了这一点。
实际上,这样的研究方式并不是没有问题的——一方面,就这种从“常识”出发进行美学研究而言,这种做法不仅从表面上说只见“鱼”而忽视“渔”,往往只注重具体的研究结论而忽视其特定的研究方式和方法,而且,从更加严格的学术性批判反思的角度来看,这种做法实际上仅是从特定的“常识”出发,着眼于这些已有的研究结论本身的优长劣短,并没有清楚地认识、准确地把握这些研究结论究竟是如何得出的,以及它们究竟为什么具有如此的优长劣短,因而实际上只是着眼于当下的现实需要或者学术问题、单纯运用自己的“常识”来判断这些结论究竟是“合适”还是“必须推翻”,而没有、也不可能着眼于实际上必须超越常识层次的、更加深刻的,具体体现为研究者所依据的基本立场、思维框架和方法论视角的哲学研究的学理层次。因此,这些做法虽然貌似在进行具有哲学高度和深度的美学研究,实质上却因为没有真正进行这种研究所必需的彻底的批判反思,往往流于这样的常识层次而不自觉。
这样一来,研究者所做的工作实际上便往往体现为两种基本情况:要么由于恪守已有的基本立场和方法论视角,只能通过对研究对象的不断细化、对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展,而对已有的特定研究结论加以“修补”;要么在进行如此这般的“修补”、“扩展”而无功的情况下,把已有的研究思路和结果完全抛在一旁而“另辟蹊径”,实际上却因为没有进行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的根本突破,而仍旧处于彷徨不前的学术研究困境之中——毋庸赘言,无论许多美学研究者从“美是难的”出发、把“美”当作美学的研究对象而进行的各种各样摸索,还是自20世纪初以来的艺术哲学家们“另辟蹊径”而通过界定和研究“艺术”、用“艺术哲学”研究来代替“美学研究”而进行的许许多多探求,其结果都已经表明了这一点。
不过,如果我们不满足于这种具有“事实描述”色彩的考察,而是进一步深入探讨隐含在这种“常识”性研究方式背后的思维模式,那么,一个具有关键性重要意义的根本问题就会浮现出来:迄今为止的美学研究者所采用的、脱胎于研究自然界客观物质对象的自然科学研究模式的、西方唯理智主义传统哲学认识论的思维模式,究竟是不是适合于研究具有浓厚的主观情感体验色彩的美学研究对象?(注:无论把美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美”,还是把艺术哲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艺术”,它们的研究对象都具有浓厚的主观情感体验色彩,因而都与纯粹客观的自然科学研究对象、与传统的哲学认识论所涉及的对象具有本质的不同。)毋庸赘言,只要我们承认这两种研究对象有本质的区别——前者是纯粹客观的、没有生命欲求和情感意志的,后者则是活生生的、饱含主观情感体验的,那么,这个问题就既不是一个“伪问题”,也不是一个无关紧要、可以随意忽略的枝节问题,而是直接关系到“究竟应当如何进行美学研究”的关键性问题。
在已经发表的有关文化哲学(注:我们之所以把文化哲学研究与这里的美学研究相提并论,主要是因为在我看来,分别作为这两者的研究对象而存在的“文化活动”和“审美活动”在本质特征方面的区别,远远小于它们与传统的哲学认识论所探讨的纯粹的客观物质对象之间的区别——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两种研究对象由于同样涉及主体的情感体验而只具有纯粹程度方面的差异、并没有实质内容方面的不同。)研究方式的文章中,我曾经把迄今为止的绝大多数研究者所沿用的这种思维方式,称之为“传统哲学思维方式”,并且对其根本不适合于研究文化的本质特征进行了归纳和批判(注:参见霍桂桓《试论文化哲学研究的基本前提和可能性》,《求是学刊》2003年第6期。),这里囿于篇幅不再对其加以复述。实际上,既然这种为了追求绝对客观和普遍有效的研究结论而竭力摒弃所有各种主观因素的唯理智主义思维方式,根本不适合于研究文化活动和文化现象,而文化活动和文化现象作为饱含主观情感体验的研究对象又与审美活动和审美现象基本相同,因此我们显然可以顺理成章地说,这样的基本思维方式也同样不适合于探讨和研究各种审美现象——实际上,无论从所谓“美是难的”而得出的“美无法定义”,还是研究者通过“另辟蹊径”而出现的“艺术无法定义”,所表明的都不过是这种基本思维方式、研究方式、定义方式对于美学研究来说的根本“不适当性”而已。可以说,美学研究者如此沿用下来的这种思维方式、研究方式和上述出于“常识”而对美学进行的各种各样研究,实际上互为表里,共同构成了迄今为止的美学研究无法突破的困境、难以解开的“死结”!既然“美无法定义”、“艺术无法定义”,那么,在连自己特有的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都无法确定的情况下,今天的“美学”研究也好、“艺术哲学”研究也罢,不是都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吗?
这样一来,难道今天的美学研究、艺术哲学研究真的无路可走了吗?否!这并不仅仅是因为就当代中国国内的美学研究而言,绝大多数研究者即使在“美学热”过去之后,实际上也仍然在殚精竭虑地继续进行这些方面的探讨和研究;而且,从我们实际上完全有可能转变思维方式、变革研究模式的意义上说,得出这样的悲观结论也是没有任何根据的——这里的关键性问题并不单纯是“今天的美学研究究竟有没有出路”,而且是“究竟应当以何种方式继续进行美学研究”,亦即“究竟应当如何研究美学”。在我看来,既然以追求绝对客观和普遍有效的真理为根本取向的、西方唯理智主义思维方式,既不适合于探讨美学的研究对象、因而也不适合于进行美学研究,所谓“美无法定义”、“艺术无法定义”显然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因为试图进行这样的定义的基本意向和因此而采取的具体步骤,实质上恰恰就是有意无意地继续恪守这种唯理智主义思维方式的产物!
我认为,这里的关键在于,研究者究竟是不是明确意识到进行学术研究必须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即“任何一位研究者的基本立场、思维框架和方法论视角,都是由其特定研究对象的本性决定的”——概而言之,这条基本原则既是包括美学研究者在内的任何一个学科的研究者,在进行严肃的学术研究、通过努力保持价值中立立场而追求其研究结论具有客观有效性的过程中难以忽略的基本前提,也是实事求是的基本精神在学术研究领域之中的具体体现。就严格的哲学意义上的美学研究而言,只要充分认识到遵循这种基本原则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我们就有可能不再出于未加任何严格批判反思的“常识”习惯、盲目照搬上述并不适合于探讨美学的特定研究对象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而是通过认真贯彻这种基本原则,看一看作为美学的研究对象而存在的审美活动和审美现象,在现实生活之中究竟处于什么地位、发挥什么作用,从而通过确定它与其他学科的研究对象的本质区别,实现对它的严格学术定位。在我看来,只有这样做,我们才有可能真正通过突破上述西方传统的唯理智主义思维方式,彻底破除迄今为止一直存在于美学研究领域之中的“死结”。
为什么突出强调“审美活动”——走出当今美学研究困境的必要举措
有必要强调指出的是,这里充分强调必须对作为美学的研究对象的审美活动进行严格的学术定位,并不意味着完全撇开以往的学术前贤的所有各种努力而“别出心裁”、“标新立异”,而是恰恰相反——只有从几乎所有这些学术前辈已经进行的各种不可多得的研究以及所得出的结论、经验和教训出发,我们才有可能比较清楚地意识到迄今为止美学研究领域一直实际存在的困境和“死结”。因此,在我看来,仅仅指出迄今为止美学研究领域之中存在这种困境和“死结”是不够的,因为这样做至少仍然有我们上面已经批判过的只重视“鱼”而忽视“渔”的做法之嫌。为了真正通过“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实现对这种思维方式的突破、从而破除这样的“死结”,我们可以非常概略地考察一下以往美学研究者们进行其美学研究的主要方式及其基本特征,看一看究竟是不是必须把审美活动视为美学的研究对象吧。
如果着眼于学理性思路演变的历程,那么,概而言之,美学家们迄今为止通过界定其研究对象而体现出来的研究方式,主要经历了从单纯地探讨和研究所谓“美的对象”、“审美心理”,逐渐发展到探讨和研究“审美关系”,再逐步走向探讨和研究“审美活动”这样一种由抽象走向具体的过程:
首先,就单纯探讨和研究所谓“美的对象”的做法而言,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无论所谓对“美”、“崇高”、“悲剧”、“喜剧”乃至对“丑”进行的界定和研究,对各种艺术门类及其在某个历史时期的基本特征的界定和研究,还是相应地(或者“另辟蹊径”地)对各种“审美心理”现象的探讨,其思维方式都具有一个共同的关键性特征,即都是不加任何批判反思地搬用上述西方传统唯理智主义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为了使其研究结论具有绝对客观性和普遍有效性,把被研究对象彻底地从其现实存在的有机联系之网中抽取出来、孤立起来,进而试图单纯立足于被研究对象的共时性维度、仅仅通过条分缕析式的研究,便得出同时具有历时性维度的“普遍有效”的“规律”。因此,一言以蔽之,这种美学研究方式的基本特征是“单向”的“静态”研究——所谓“单向”即只关注孤立的被研究对象,并没有把现实的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真正实事求是地有机结合起来;所谓“静态”则是指这种研究所具有的共时性、平面化研究视角,基本上消除了其被研究对象的历时性动态生成维度。因此,研究者所关注的只是其对象的当下之“然”,而没有、也不可能进一步通过探讨其“所以然”而得出更加全面和恰当的研究结果。
这样一来,实际上,所有这些被研究对象不仅都失去了使其得以产生和发挥作用的社会现实环境、特别是现实审美主体的各种主观成分,也因为这种研究方式所具有的抽象化、形式化、平面化倾向,彻底丧失了原有的立体生命感和不可或缺的情感体验特征,因而变得与自然科学所探讨的、没有生命和情感的自然物质对象毫无二致了。显然,这样一种基本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所能够得出的结论,充其量只能是一些类似“生产操作规程”的“规则”,甚至因为缺乏必要的清晰性和可操作性,还不如这样的“生产操作规则”更有实际意义——只要看一看在人们的审美活动、艺术创作活动中,这样的“美学研究”的“结论”基本上都没有什么“指导意义”的实际情况,我们就可以比较清楚地理解这一点。
其次,就各种所谓将“审美关系”视为美学研究对象的研究方式而言,无论所谓“美在关系”之中的“关系”究竟是“主体—客体统—关系”,抑或是“实践关系”、“价值关系”,就其实际研究过程所包含的基本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而言,这种研究方式都确实已经超越了上述“单向”“静态”的研究方式——不再以“攻其一点、不计其余”的方式,要么“客观”地单纯探讨“美的对象”、要么“主观”地专门研究“审美心理”现象,而是试图通过引进“审美关系”,开始着手把这两个方面联系起来进行探讨和研究,因而具有重视“双向性”的基本特征。显然,无论就这种研究方式所涵盖的学术研究广度来看,还是就其因此而具有的更加充分的理论解释力而言,它都比上述“单向”“静态”的美学研究方式前进了一大步。可以说,这种努力及其相应的具体研究进展,实际上是从上述“单向”“静态”的美学研究方式,走向既关注审美客体、也同时关注审美主体的“双向”研究方式,从而为更加全面地看待、探讨和研究美学的研究对象,奠定了必要的基础、开辟了有可能使美学研究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
不过,概览一下国内外研究“审美关系”的主要观点可以看到,其所包含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虽然有了上述进步,但却不仅没有对“审美关系”做出足够明确的界定(注:有必要指出的是,虽然国内外有不少研究者不再满足于从“艺术反映现实”的角度出发,继续把审美关系当作认识关系来研究,而是进一步将其界定为“价值关系”,但由于此举并没有对已有的基本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进行必要的反思和突破,因而实际上不仅置审美关系所包含的认识成分于不顾,也不可能真正阐明审美关系与直接基于利害关系的价值评价关系究竟具有哪些本质区别和有机联系。这样一来,这种做法显然是貌似有所进展,实际上仍然“止步不前”、没有真正实现对审美关系之本质特征的明确界定。),而且也仍然是“静态”的、缺乏现实维度和历史维度的——其“静态”性比较突出地表现在,客体与主体之间的审美关系仍然是孤立的,它究竟具有哪些不同于主体与客体的其他关系(诸如认识关系、实践关系、经济关系、政治关系、伦理关系、乃至宗教关系)的本质内容和基本特征?它与这些其他关系究竟具有哪些联系和本质区别?诸如此类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清晰和系统全面的研究和论述(注:尤其是考虑到曾经一度占据主导地位的所谓“艺术反映现实”的观点的时候,情况更是这样;显然,在这种情况下,美学不仅因为根本不可能与认识论、真理观真正区别开来而导致对审美对象的研究方式的扭曲,而且更加重要的是,这种观点和做法实际上也掩盖了美学研究者直接照搬上述西方传统唯理智主义思维方式的非法性。);而其缺乏现实和历史维度则具体表现为,几乎所有关于“审美关系”的论述和观点,都仍然具有形式化、平面化、抽象化的基本特征:不仅几乎所有研究者都仍然把这种关系当作具有不依赖于具体时代的、普遍适用的研究对象来加以探讨和论述,因而仍然不可能具体深入地探讨和研究审美关系的实质内容和本质特征,也不可能明确研究和论述“现实主体究竟具备了什么条件和素质才能成为审美主体”,特别是不可能具体阐明审美关系在不同的文化传统之中、在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实际体现出来的不同特色。
那么,究竟应当如何通过界定美学的研究对象来进行恰当的美学研究?在我看来,从根本上说,美学研究和其他任何一个学科的研究一样,首先必须结合现实对其研究对象进行恰当的学术定位。于是,这里的问题就“转化”为“究竟应当如何对美学的研究对象进行恰当的学术定位”?我认为,只要我们不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批判的那样,继续采用拘泥于“观念的王国”的、“从观念到观念”的抽象研究方法,亦即不再一厢情愿地把审美关系抽象化、形式化、观念化,使之变成没有现实审美主体的抽象关系,而是实事求是地将其视为由活生生的现实主体参与其中、与相应的审美对象共同构成的,既具有历史性、又具有现实性的审美活动,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彻底克服审美关系这种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抽象“静态”特征,将其真正置于不断发展变迁的现实社会生活之流中来进行考察、进而加以相应的学术定位。显然,这样一来,研究者所涉及的美学研究对象,就不再是抽象化、形式化和观念化的“审美关系”,而必然是活生生的、在现实生活之中实际存在的、不断发展变化的“双向”“动态”的审美活动。
所谓“审美活动是一种‘双向’‘动态’的活动”,是指就其实际存在形态而言,它不仅包含了作为审美对象的、以饱含情感的感性符号的形式具体存在的外在对象,包含了作为审美主体的、具备了审美需求和审美潜质的现实主体,而且更加重要的是,它本身是由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通过各种富有情感体验色彩的感性互动过程(aesthetic interactions)共同构成的、具有动态性的现实活动过程。因此,它不仅把上述“单向”“静态”和“双向”“静态”的美学研究方式所涉及的研究对象维度都包括在其中,而且作为一种现实存在的、活生生的活动,以主体通过各种感性符号构建精神家园、追求和享受自由的基本特征,既区别于人们在日常生活之中进行的其他活动,同时也为研究者实事求是地、而不是抽象地探讨和研究它与这些其他活动的有机联系,真正打开了方便之门。
那么,应当如何探讨和研究审美活动?毋庸赘言,作为一种“活动”,它显然不再是经过抽象化、平面化、形式化、观念化的“观念”及其“关系”,而是现实存在的、动态的、活生生的、具有自己独特的本质特征的“过程”。这里必须强调指出的是,虽然我们行文至此已经看到,无论“美的对象”、还是由之进一步发展而来的“审美关系”,实际上都是由于上述(没有进行深刻哲学批判反思的)“常识”性研究、因为对西方传统唯理智主义思维方式的直接照搬,而无法清晰地确定自己的研究对象(具体表现为这种“从观念到观念”的研究模式所面临的上述困境和“死结”),但是,研究者在因此而走向探讨和研究审美活动的过程中所面临的、“究竟应当如何探讨和研究审美活动”这样一个问题,却根本不像表面上看来的那样,可以轻而易举地加以解决和回答。
之所以这样说,既是因为这种走势实质上是由于上述困境和“死结”的逼迫、因而本身就隐含着进行基本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之突破的要求,也是因为无论美学研究还是艺术哲学研究,迄今为止实际上都是按照“概念→判断(定义)→推理→理论”的传统研究模式和论述方式进行的,其基本要求是概念必须清晰确定、判断必须具有“真值”、推理必须系统严密,然后才谈得上因此而建立的理论具有有效性和解释力。显然,研究者通过达到这种要求取得的直接结果,是主要立足于被研究对象的共时性维度而对其进行的抽象化、形式化、平面化和观念化,从而相应地形成概念、判断、推理和理论体系。毋庸赘言,这样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主要适合于探讨和研究孤立和静止的物质对象,而不适合于研究包括审美活动和艺术欣赏在内的、具有动态性和过程性的对象。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今天的美学研究者试图通过把审美活动看作是自己的研究对象而走出上述困境、破除上述“死结”,而所面对的实际情况却是不仅美“不可定义”、艺术也同样“不可定义”,那么,究竟应当如何“对审美活动进行严格的学术定位”呢?
如何对“审美活动”进行学术定位——“社会个体生成论”(注:囿于篇幅,我们在这里不打算叙述这种理论,只能运用它的基本方法论视角进行必要的论述;感兴趣的读者请参见霍桂桓《文化哲学论要》第一章第三节,北京出版社2007年版。)提供的现实可能性
毋庸赘言,假如美“不可定义”、艺术也同样“不可定义”,那么,究竟应当如何对作为美学研究对象的审美活动进行严格的学术定位?因为按照目前不少研究者所采用的、实质上是作为沿用迄今为止的西方唯理智主义思维方式的结果而存在的观点来看,既然作为美学和艺术哲学研究之必要起点的、对其研究对象的明确界定都不可能,所谓“严格的学术定位”岂不更是无稽之谈?
在我看来,这里的关键性问题是,我们究竟能不能通过对上述西方传统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的彻底批判反思和扬弃,真正突破这种“从观念到观念”的“观念的王国”,从而实现基本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的根本转变!尽管这样说似乎具有抽象的色彩,难以在实际研究过程中落到实处,不过,只要具体看一看上述困境和“死结”的具体表现之一(注:即“美不可定义、艺术也同样不可定义”。)并略加分析,我们就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并理解实现这种转变的重要意义。
实际上,“美”和“艺术”之所以“不可定义”,一方面固然是由其独特的本质特征决定的,因为它们那因人而异的情感体验特征、瞬息万变的动态属性,都使它们与性质和存在形态相对稳定的自然科学研究对象截然不同;但是,在我看来,因此而出现的学术研究困境却根本不是由这种不同造成的,而是由研究者没有通过充分重视和研究这种不同而探讨和采用新的研究方式和方法、仍然自觉不自觉地沿用根本不合适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的倾向和做法所造成的。因此,这里存在的根本问题是,研究者究竟是根据新的对象探索并运用适合于这种对象之本质内容和基本特征的研究方式和方法,还是把已有的、并不一定合适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当作必须恪守的“金科玉律”,以之衡量甚至“剪裁”新的研究对象?
另一方面,研究者之所以不断地寻求对“美”和“艺术”进行“定义”,不外乎希望此举能够使自己的研究结论像自然科学的研究结论那样严密、精确和普遍有效。不过,这种愿望实际上却只能是“一厢情愿”,这样的做法也只能是“劳而无功”——且不说迄今为止的美学家和艺术家所进行的殚精竭虑的不断探索,所得出的结果都不过是“美”和“艺术”都“不可定义”;而且,自然科学的绝大多数研究结论,实际上也不像许多人所想象的那样“严密、精确和普遍有效”,毋宁说,它们都是需要一些具体条件、在特定的范围之内才能成立的:即使诸如“1+1=2”这样似乎千真万确的等式都取决于现实对象的特殊属性(注:比如说,具体到两团柔软的泥巴,这个等式就未必成立了,因为它们结合在一起会变成一团更大的泥巴,即实际上是“1+1=1”。),更不用说那些更加复杂的结论了。此外,一种研究结论究竟是不是具有解释力,也并不主要取决于其具体表述方式是否规范严密,而是主要取决于它究竟是不是通过恰当的表述方式,比较全面地表达了其对象的具体内容和本质特征——从这种意义上说,无论逻辑严密的规范性“定义”,还是“微言大义”的描述性“叙事”,实际上都具有由其特定对象的本性决定的、具体的合法性(注:有必要指出的是,一个研究结论究竟是不是具有足够的理论解释力,实际上还取决于接受者的基本素质、取决于接受者能不能与被接受对象形成当代哲学解释学所谓的“视域融合”;囿于篇幅,这里无法详细论述这一点。)。所以,从这里的“不可定义”出发,并不能得出“对审美活动进行严格的学术定位是无稽之谈”的结论。
既然如此,那么,究竟如何进行这样的学术定位?这样做能够通过严格确定美学的研究对象,解决“究竟应当如何研究美学”的问题吗?
就前一个问题而言,在我看来,只要研究者真正意识到上述困境和“死结”,都是由于沿用并不适合于美学研究的西方传统唯理智主义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才出现的,并且因此而认真坚持和贯彻“任何一位研究者的基本立场、思维框架和方法论视角,都是由其特定研究对象的本性决定的”基本原则,突破迄今为止一直存在于美学研究领域之中的“观念的王国”,进行这样的学术定位就是完全可能的。具体说来,“对审美活动的学术定位”取决于“对审美活动的现实定位”——也就是说,取决于我们究竟能不能实事求是地确定现实的审美活动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所具有的地位,亦即取决于真正弄清楚人们在什么基础上、在什么条件下、为了什么而进行审美活动。必须强调指出的是,探讨和研究“审美活动的现实定位”,不仅需要彻底突破西方传统的唯理智主义思维方式所具有的抽象化、形式化和平面化的研究模式,而且,也需要突破其主要关注被研究对象的共时性层面的研究视角,从“社会个体生成论”的基本立场出发,引进把被研究对象之间的有机联系包含在其中的历时性“生成”视角(growing-up perspective),从而使所谓“有机联系”由抽象走向具体、由平面走向立体。
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人们在现实生活之中进行的审美活动,不是没有任何基础和条件的,而是恰恰相反,更加重要的是,审美活动与这些基础和条件根本不是抽象的并列存在关系,而是动态的逐级扬弃生成关系。因为,如果同意中外许多研究者已经指出的“审美活动是对自由的享受”的观点(注:虽然国内外已经有不少研究者以各种形式提出了这种观点,但我们在这里却囿于篇幅而显然不可能一一列举出来。),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这里的“自由”绝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通过人们实际进行的社会实践活动过程产生出来的,是通过他们在这样的实践过程之中,依次经历与(包括自身和他人在内的)客观对象的认识关系、实践性物质改造关系和精神性有机统一关系而逐渐表现出来的。
概略说来,作为现实社会个体而存在的主体,为了生存、发展和享受自由,首先必须对其周围的现实环境、特别是对与之直接相关的对象进行认识,从而既消除因为自身的蒙昧无知而出现的主客体截然对立状态,又为进一步改造这样的对象准备必要的基础和条件,其结果即是形成主体—客体的认识性统一关系。在此基础上,主体为了使其物质性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不断得到实际满足,便通过各种社会互动过程(social interactions)具体实施对这些物质对象的改造,从而既由于获得了可供消费的物质、精神产品而与对象达成物质性统一关系,使自己的生理和心理需要得到相对满足,也因为特定的社会实践所包含的各种社会规范、制度的陶冶,使自身的动物性需要逐步生成为人的需要(管仲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所指的就是这种情况)。这既激发了主体通过构建精神家园享受更高层次的自由的愿望,也为这种追求和享受奠定了基础,准备了各种条件(墨子所谓“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所指的就是这种情况);因此,主体才会通过创造和运用各种饱含情感的感性符号,进行追求和享受更高层次的自由的文化活动和审美活动。
可见,就其现实地位而言,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之中,审美活动实际上是处于认识活动和物质性实践活动这两种“过程”之“后”的,亦即是“后实践”(post-practice)的——也就是说,包括认识活动在内的广义的社会实践活动,既是它的前提和基础,又是使它得以产生、存在并发挥作用的母体;审美活动既来源于这种实践、以这种实践为基础,同时也由于主体为了追求和享受更高层次的自由,通过其构建的、各具特色的精神家园而超越和扬弃了这种实践。这就是它在现实生活之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样,从前面已经提出的“任何一位研究者的基本立场、思维框架和方法论视角,都是由其特定研究对象的本性决定的”这样一种基本原则出发,我们就可以根据审美活动所具有的这种地位,来探讨和研究它的学术定位了。
实际上,所谓“审美活动的学术定位”,只能是根据它在现实生活之中的地位和作用,来探讨、确定和研究它作为美学的研究对象所具有的、由这样的地位和作用决定的、在以美学为其分支学科之一的哲学研究领域之中所具有的地位。因此,如果说作为一个完整学科的哲学,既包含探讨和研究认识活动的认识论,包含由分别探讨和研究现实生活的经济活动、政治活动、司法活动、伦理评价活动、宗教活动的经济哲学、政治哲学、法哲学、道德哲学、宗教哲学构成的社会哲学,也包含探讨和研究文化活动的文化哲学、探讨和研究审美活动的美学的话,那么,在这样的总体性研究领域之中,审美活动以及对其进行研究的美学,就显然处于认识论和分别由经济哲学、政治哲学、法哲学、道德哲学、宗教哲学所构成的社会哲学,以及研究文化活动的文化哲学之“后”,即处于具有“立体”色彩的哲学体系的“顶端”——也就是说,在具有逐级扬弃生成的立体色彩的哲学研究领域之中,作为美学的研究对象的审美活动,由于本身即是超越和扬弃认识活动、经济活动、政治活动、司法活动、伦理评价活动、宗教活动等方面的结果,所以,它那具体表现主体自由度的内容和境界比所有这些活动的相应内容和境界都高、都丰富,因而实际上是由所有这些活动共同构成的“金字塔”的“塔尖”。
这里需要强调以下三点:
第一,我们之所以立足于“社会个体生成论”的基本立场而进行这样的探讨和研究,首先是因为作为美学研究对象的任何一种具体的审美活动,本身无一不是实际存在于“社会”之中的——也就是说,它既是融历史文化传统、现实社会环境和具体主体对自由的追求于一炉的“社会”的产物,同时也在这样的“社会”之中发挥其特定的作用。因此,迄今为止的所有各种忽视“社会”维度的“纯”美学研究,无论为我们准备了多么坚实的“巨人的肩膀”,本身都是没有出路的。
第二,我们之所以立足于“社会个体生成论”的基本立场而进行这样的探讨和研究,也是因为审美活动本身具有极其鲜明的“个体性”——也就是说,它本身是现实存在的社会个体,通过具有动态生成和逐级扬弃色彩的社会实践过程、通过自身人生境界的不断提升过程而追求和享受自由的具体表现和结果。因此,只有充分重视和认真研究现实社会个体的人生境界的不断提升过程及其具体表现,而不是像以往那样进行“没有审美主体的美学研究”、探讨“没有审美主体的审美活动”,我们才有可能真正实事求是地研究包括“趣味无争辩”在内的所有各种审美现象,从而使美学研究真正走上健康发展之途。
最后,我们之所以立足于“社会个体生成论”的基本立场而进行这样的探讨和研究,更是为了突出强调必须彻底突破美学研究迄今为止所采取的、主要关注被研究对象的共时性维度的西方传统唯理智主义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引进能够把被研究对象的静态共时性维度和动态历时性维度有机结合起来的“生成视角”——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真正恰当地既把审美活动与人们进行的其他活动明确区别开来、又有机结合起来,从而通过清晰地确定它的现实地位和学术地位,通过勘定它的作用范围和疆界而对它进行的全面探讨和研究,使美学真正能够走上健康发展之路。
标签:美学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本质与现象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传统观念论文; 艺术哲学论文; 常识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