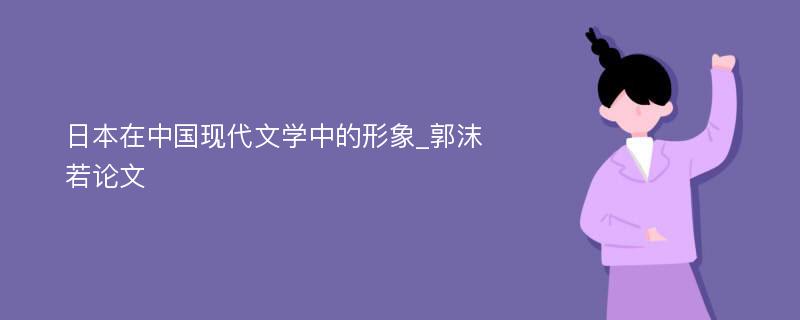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日本形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中国论文,形象论文,文学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919(2000)06-0103-06
纵观中国现代文学史,至少有三方面的作品比较多地涉及到日本题材,也程度不同地塑造了一些给读者以深刻印象的日本人形象。一是20年代的留日作家,如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成仿吾等人的小说、散文、诗歌作品。二是30年代东北沦陷区作家,如萧红、穆时英等人的小说。三是三四十年代抗日时期所涌现出的大批抗日战争题材的小说、诗歌、戏剧作品。三类不同类型的文学作品,向中国读者提供了影响至深、特点各异的跨文化信息。第一类作家的作品,由于出自一些在日本生活多年的作家之手,对日本社会的政治结构、风土人情、教育体制、自然景观等各方面的内容均有比较详细的描述。这类作品中频繁出现的日本女子形象系列,可以讲,已经成为众多中国人心目中的一种理想的女性形象原型。直至今日,我们仍然可以在一般民众有关女性的价值取向上看到这方面的痕迹。本文集中考察第一类作家的作品。其余几类作家的作品以后另行论述。
一、樱花情结
作为日本国花的樱花,如同处女红的颜色一样,在20年代的中国,让许多有志青年,陷入一种虚幻的遐想。在这股浩浩荡荡的留日大潮中,人们不难发现日后成为中国新文学巨匠的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人的身影。细心的的读者也不难发现,这些作家,尤其是郭沫若、郁达夫的众多诗歌、小说创作中最成功的作品,恰恰是那些描写留日生活的文字。郭沫若的诗集《女神》、小说《残春》,郁达夫的小说《沉沦》、《银灰色的死》、《南迁》、《风铃》,以及张资平的《一班冗员的生活》等等,都是以这个樱花之国为背景的感人力作。
黄叶初的短篇小说《恋爱初期的失败者》,形象地说出了作品中主人公那时的心境。
无独有偶,张定璜的小说《路上》也描述了作品中主人公类似的梦想,只不过,这样的梦想在主人公再回首的追忆里渗透了无限苍凉的气息:
八年了,差不多同样的船八年前曾经装载一个天真的纯洁的少女在这个烟波浩荡的海上,遥望着无限的幸福,向东方驶去[1]。
然而,现实毕竟与梦幻有非常大的距离。留日之前想象中的扶桑之国,多了一层玫瑰般的色彩,风景无限美好。留日之后,亲自观察到、体验到,并饱尝其酸甜苦辣的日本,在这时的众多作家的作品里,却变成了一个轻视中国、人欲横飞、等级森严、贫富悬殊的社会。风花雪月、山川草木,以樱花为其象征的日本自然风光,这时又成了中国留学生逃避冷酷的现实社会,寻求一丝生命慰藉的避难所。我们的诗人、作家,经常徜徉其中,并把这种没有国籍意识,没有种族歧视,对谁都一视同仁的自然之母尊为生命的神龛、灵感的源泉。同时,自然与社会的这种差异,也使得留学生们被侮辱、被损害的心灵世界能寻找到一个平衡的支点。否则,很难想象这些留学生能完成他们的学业。也很难想象像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这样极度敏感、脆弱的作家,能存活其自然和艺术的生命。
郭沫若是这样来描述樱花的:
我们在春季的晴天试走到郊野外来,氤氲的晴霭在空中晕着粉红的颜色,就好像新入浴后的处女的肌肤,上天下地一切存在都好像中了酒一般,一切都在爱欲中燃烧,一切都在喘息。宇宙就是一幅最大的画。青春的血液还在血管中鼎沸的人,怕不会以我这句话为过分罢。况且在日本的春天,樱花正是浓开的时候,最是使人销魂,而我又独在这时候遇着了她。[2](p215)
从作者的作品里不难看出,自然的描摹与社会的写真,使用的是完全不同的笔触,流露的是完全不同的情绪。我们的诗人诅咒日本社会,但他深爱着这里的大自然。
在个人气质上与上述感伤型作家迥然不同的鲁迅,在有名的短篇小说《藤野先生》一文里,描写日本的标志性国花樱花时,却少了一份烂漫,多了一份无奈:
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上野的樱花烂漫的时节,望去却也像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3]。
这里,我们不能忘记同时期的另一位重要作家——郁达夫。正如作家本人的个性是那样伤感、变幻无常一样,遇着痛心之事的时候,他笔下的岛国风景浓重地涂上了苍凉、悲观的色调:
雪瑚的东京,比平时更添了几分生气。从富士山顶上吹下来的微风,总凉不了满都男女的白热的心肠。一千九百二十年前,在伯利恒的天空游动的那颗明星出现的日期又快到了。街街巷巷的店铺,都装饰得同新郎新妇一样,竭力的想多吸收几个顾客,好添这些年中的利泽,这正是贫儿富主,一样多忙的时候。这也是逐客离人,无穷伤感的时候。[4](P1)
郭沫若以其历史学者的知识储备,从当时的博多湾去探寻其独有的历史事变,反映了作家在感知樱花之国的壮丽山河时具有的浓重的历史沧桑感。在《今津纪游》中,作者这样写道:
邮片已写满了,在那平如明镜的海上,元舰四千艘,元军十万余人,竟会于一夜之间,突然为暴风所淹没,不可抗的终是自然之伟力了。[5]
总而言之,樱花也好,富士山也好,博多湾也好,所有这些天籁的成分,已经不是一处处纯粹客观的自然存在,而是这些作家主观移情之后,洋溢着他们自己人格精神的大自然形态。在这里,自然界的一山一水,都成了作家心境的写照和象征。换句话说,是一种符号意义上的自然环境。上述作家在描述同一自然风景时传达出的不同情绪,给读者留下的不同感受,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二、民族与国家
留日生活,备尝艰辛。20世纪20年代日本资本主义的高速发展,很快将这样一个历史简短、传统上十分落后的岛国推向世界五大强国之列。中日经济发展水平的极大差距,给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们以极大的震撼。同时,日本自身经济的成功也在这个岛国培植了一股轻视中国、憎恶华人的社会风气。
从这一时期的诸多作品看来,在受尽歧视和侮辱之后引起的那种诅咒日本社会的强烈情绪,几乎渗透在所有作品的字里行间。民族与国家的意识,是通过中日对比、切肤经验之后自然产生的。
郁达夫在他的代表作《沉沦》里,通过主人公的呐喊,传达了这样的观点:
他们都是日本人,他们都是我的仇敌。我总有一天来复仇,我总要复他们的仇。[4](P20)
他们都是日本人,他们对你当然没有同情的,因为你想得他们的同情,所以你怨他们,这岂不是你自家的错误么?[4](P21)
只有置身于外国的土地,人们才会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外来者。不,不仅仅是一个外来者,而是一个天生就肩负着耻辱的国籍十字架的赤贫的异邦人。作家这时所受的侮辱,已经不仅仅是个人恩怨意义上的坎坷和挫折。在他身后,遭受凌辱的是整个中华民族。一个哀其不幸,怒气不振的民族。作家郁达夫在他的作品里,将这种情绪升华后这样写道:
我何苦要到日本来,我何苦要求学问。既然到了日本,那自然不得不被他们日本人轻侮的。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富强起来。我不能再隐忍过去了。[4](P22)
日本社会,或者换句话说,日本的帝国意识,像一堵无法逾越的铁壁,阻隔开了这样两个一衣带水的邻邦。它们之间绵绵一个世纪之久的鸿沟,在今天,仍然无法填平。日本社会对待华人的极度歧视,使得我们的作家时时要发出这样那样的诅咒。
我们曾经指出过,不同的作家,由于个人经历的差异,对待同一件事或同一个人,认识的角度和深度大相径庭,因而在作品中反映出来的效果是很不一样的。诗人徐志摩作客日本,而非留学,因此从他的诗里,我们更多地感到作者对这个扶桑之国的顶礼膜拜之情,以及在高度的现代物质文明挤压下所萌生出的对于中华文明的挽歌式的悲叹。这种悲叹在他的“留别日本”里不难看出。
与上述两类作家明显不同,作家张资平,虽然也留学日本,却少了份怨天尤人、痛骂一切的情绪。在他的作品里,我们可以看到,面对日本社会普遍存在的歧视中国人的状况,作者更多采取一种中立、客观的态度。他认识到,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很大程度上也在于他们留学生自己低劣的素质。这样的自我批判精神,又与郭沫若、郁达夫的作品里所流露出来的情绪化的自责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说在郭沫若、郁达夫的作品里,我们经常能看到一些怀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并用自己柔弱的身躯去抗争东洋帝国的留学生形象,那么,在张资平的作品里,我们更多地看到那种令人失望的《一班冗员的生活》。日本帝国的经济成就和由此滋生出的自大、排外风潮,已经将许多中国留学生从骨髓里同化了。甚至有一些不惜脱胎换骨、邯郸学步的留学生,自愿归附到日本帝国的脚下。张资平的小说《一班冗员的生活》,就勾画了这样一种假洋鬼子形象。
三、都市感觉
它无情地击碎了所有贫穷者的自信和自尊。面对这样一个高速运行的庞然怪物,中国留学生们,只有凄凉的哀叹和厌世的无奈。他们既是一群异邦人,又是一群多余者。作家郭沫若、郁达夫在他们的小说里多次写到这样的心境。在都市纷繁的人流的挤压下,一部分留学生将他们的视线聚焦到那包容一切的大自然,以及国籍意识淡薄,以善良、温柔著称的日本女子身上。这两种麻醉剂,抚慰着受凌辱者的灵魂,也形成了这段时期中国文学的两股原动力。作家成仿吾写道:
市内的空气,浓的差不多连呼吸都很困难。他只任那人的潮流把他流去。那一家一家的装饰,和那陈列台上的物品,对他好像没有什么引力的一般。这不是因为他的感受欠灵敏,他觉得去年的冬天,好像就是昨天的事情一样,他们也曾把这些市街,红红绿绿装饰了一遍,没有几天,又把它都撤了。[6]
这是一个徘徊于日本社会边缘的孤独者的真实写照。
这也是一个极端憎恶都市喧哗,而以一种“破帽遮颜过闹市”的心态,在这个世界上踽踽独行的多余人的写照。从郁达夫的作品里,我们也能看到这样的文字:与郁达夫和成仿吾纯粹袒露个人心态不同,郭沫若的描述则带有较强的政治色彩:
木屐的交响曲!这要算是日本停车场下车时特有的现象了。坚硬的木屐踏在水门汀的月台上,汇成一片杂乱的噪音,就好像有许多马蹄的声响。八年前我初到日本的时候,每到一处停车场都要听得这种声响,我当时以为日本帝国真不愧是军国主义的楷模,各地停车场竟都有若干马队驻扎。[5](P26)
四、女子系列
上文曾经指出过,大自然与女人,很大程度上成为中国青年留学生抚慰其精神创伤的麻醉剂。在郭沫若、郁达夫等人的作品里,我们可以看到,有泛着一抹处女红的纯情女子,也有“雪一样的乳峰”、“肥白的大腿”这种纯粹引起主人公情欲的女人。从这些女子的社会属性看,有房东的女儿,有日本女同学,有病院的看护妇,有社会底层的贫民姑娘,有已成为他人妻子的美妇人,也有风俗场所的风尘女子,可以说,这些女性构成了留日作家笔下最感人至深的人物系列。然而,悲剧往往都是从难以实现的事情开始。在作品中的男主人公们看来,这些女性尽管是他们朝思暮想,寄托苦闷之情的鲜活载体,但情欲的达成往往只能在梦中才有可能。这样的玫瑰般的幻觉更加重了作品中的主人公群像——中国留学生们的悲剧色彩。郁达夫的小说《沉沦》里的主人公“他”,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窥视房东之女,日本女子的性感胴体,使之发出近乎赤裸裸的喟叹:那一双雪一样的乳峰!/那一双肥白的大腿!/这全身的曲线
在另一些作品里,作家郁达夫却让我们看到了男女主人公之间那几乎纯洁无瑕的诗意般的感觉。在无限美化女子的同时,作家郁达夫在写到日本男人时,仿佛带着一种情欲的复仇倾向。房东的日本男主人是丑恶、狰狞的;学校里的日本男学生是粗鲁、愚蠢的。惟有日本女人是天使的化身。
郭沫若也是一个多情作家。在他的作品里,我们虽然看不到郁达夫对于女性所怀有的那种近乎病态的爱慕情结,但所表现出来的时如牧歌般的缠绵悱恻,时如暴风骤雨式的热烈奔放情绪,也给当时的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残春》中对于生活不幸的S姑娘流露出一种惜香怜玉之情。
“残春”是这样来描写天使般的S姑娘的:
她(s姑娘)说话的时候,爱把她的头偏在一边,又时时爱把她的眉皱成“八”字。她的眼睛很灵活,晕着粉红的两颊,表示出一段处子的夸耀。[2](P28)
……“啊啦,你不要客气了!”说着便缓缓地袒出她的上半身来,走到我的身畔。她的肉体就好像大理石的雕像,她亸着的两肩,就好像一颗剥了壳的荔枝,胸上的两个乳房微微向上,就好像两朵未开苞的蔷薇花蕾。我忙立起身来让她坐,她坐下把她一对双子星,圆睁者望我。[2](P31)
与郭沫若、郁达夫过多地着墨于女子的美丽外貌不同,张资平的作品则注重从人物的品德和秉性的角度去刻画日本女子的内心情操。从他的作品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个出生卑微,却忍辱负重,专心于相夫教子,且无怨无悔的日本女子形象,《一班冗员的生活》,低低吟唱了一首日本姑娘绫英对中国留学生程君的那种超越一切物质条件的爱情悲歌。
程君住在吉江家里拿不出钱来,吉江夫妇渐讨厌他起来了。绫英说程君的落第是她害了他,她便在A区的贫民窟里找了一间三张席的房子,把程君的行李搬过去,一同住下。绫英每天到一间烟草制造局里去当女工,每天可以赚四五角的工钱,买米回来煮稀饭分着吃。程君没有尝过这种贫苦家庭的滋味的,每晚上对着象鬼火一样的洋灯垂泪,可怜他们一个月六角钱的五烛电灯都点不起[7]。
滕固的小说《石象的复活》,告诉我们的,则是一个因爱情而走火入魔的老留学生的故事。
他又买一束美好的信封,把一页页的情书封好,上面写着“中村苔子亲展”,只写这六个字,投到邮筒里,隔了几天,又模拟她的口吻,回信,也封好,写着自己的地址,自己的名字,投到邮筒里。邮差送来后,他拆开来轮流地朗诵[8]。
五、先生与学生
很多人知道鲁迅笔下正直、敬业的藤野先生,却很少有人知道日本教育界对积弱积贫的旧中国所持有的那种歧视,乃至蔑视的态度。我们在东山的《最初之课》里发现了这种强烈的反差色彩。
讲堂前面,正对着大面,有一座小土堆,栽有几棵低矮的花树,四面围着铁链子。路是用打碎了的石块铺成的,靴子啦,木屐啦,在上面走过,沙沙的响声,非常好听[9]。
“喂,你是什么人?”“哼是呀,你的名字这簿上没有。你不是日本人。你是朝鲜人吗?清国人吗?”“我是中华民国人”,他冷静地答了。“什么,中华民国,我怎么不晓得?支那吧。”
那先生答了,向屏周投了一瞥轻蔑的目光,全堂的人都哗……地笑了。此时他早起那些愉快的感情,被几次不快之波荡尽了[9]。
张资平在他的小说《一班冗员的生活》里也有类似的描述,与东山的叙述只有程度上的差异,并无实质上的不同:
W那班的主人教授是Y博士……对着中国人便拿着高帽子出来,背过睑去便把中国人说的卑鄙狗贱的Y博士[7]。
郁达夫在他的作品里虽然没有直接地写任何日本先生,但对一帮日本学生的刻薄描写,也足以让自恃甚高的日本教授们倒抽一口凉气:
那一位近视眼,突然说出了几句日本式的英语话来,伊人看看他那忽尖忽圆的嘴唇的变化,听听她那舌根底下好像含一块石子的发音,就想笑出来。[4](P62)
陶晶孙的“木犀”描述的是一个千年难遇的故事。中国留学生与日本女先生共浴爱河,生离死别。虽然作品脱不出一般爱情故事的模式,但赋予男女双方这样的特殊身份,并把故事的叙事背景放在这个特殊的时代,似乎源自一种非国籍化的恋母情结。
六、劳动者悲歌
日本是一个等级观念很强的国家。张资平在他的小说《他怅望着祖国的田野》里对此作了详细的介绍:日本国民阶级,可分六等;一、皇族,二、贵族,三、华族,四、士族,五、平民,六、新平民。新平民是朝鲜或台湾人,改用日本式姓名,与日本内地平民混居,数代之后,得有做日本平民资格。中国留学生,正如上文所指出的,充其量是日本社会的一群多余者或平民。新平民的形象在作家们的作品里时有出现,如郁达夫的小说《十三夜》就是以台湾学生陈君作为作品主人公的。
郁达夫作品的人民性,可以从他对日本劳动者饱含同情的描述中看出来。作家在目睹日本普通劳动者单调、无聊的生活时,激起了对自己祖国的人民所遭受的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类似命运的痛苦反思。郭沫若对于一位日本平民女子则表达了这样揪心撕肺的痛惜之情:
不平等的社会吆,万恶的社会吆,假如她不住在这样的贫民窟里,她怎么能得肺痨?假如她不生在这贫民家里,她纵得肺痨也可以得相当的营养了。啊,残酷的社会!铿铿的铁锁锁着贫民,听猛烈的病菌前来蹂躏!我要替她报仇,我要替她报仇……[2](P227)
在另一部短篇小说《万引》里,作者干脆将一位可怜的日本小知识分子所遭受的悲惨命运作为文章的主题。这不能不使人联想起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形象。在竭力想逾越日本社会吃人的等级制度的时候,主人公松野很难拔起自己的头发,去过一种超脱、浪漫的文人生活。每天等待着他的是嗷嗷待哺的妻子、儿女,是失业和贫困。“偷书不算偷”,松野的悲剧人生,让人再一次认识到,中日虽是不同的国家,但生活在这两块土地上的人都不得不面对同一位上帝。
至此,我们已经对以创造社为核心的中国现代作家的作品,从人物形象与社会环境的关联等方面作了一个简略的巡礼。比较文学,或者说比较文化,涉及的问题很多,但只有从不同的角度去研究各种文化之间的渗透和传承,才有可能揭示其间的深层次关系。中日关系的研究也不例外。
收稿日期:2000-08-02
标签:郭沫若论文; 郁达夫论文; 文学论文; 中国现代文学论文; 日本作家论文; 中国形象论文; 沉沦论文; 张资平论文; 作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