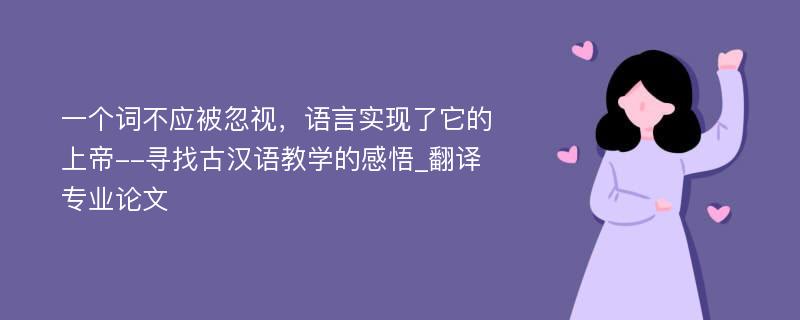
一字未宜忽,语语悟其神——找寻文言文教学的情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言文论文,一字论文,情味论文,语语悟论文,未宜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字未宜忽,语语悟其神,惟文通彼此,譬如梁与津。
——叶圣陶《语文教学二十韵》
诗人流沙河曾在诗中写道:“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心态,中国人有中国人的耳朵。”其意谓: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特殊的文化心态、审美趣味,中国人也有其特有的文化心态和审美情趣。有人说,掌握祖国的语言就好比得到了一把打开本国文化的钥匙。那么,在中学教学文言文,就好像在孩子们面前打开了一扇窗户,铺开了一条通道,让他们能穿越时空,去阅读,去思考,去吸取,与两千年前的大师直接对话,了解并深刻地认识我们的祖先,懂得我们的历史,从而继承和发扬我们的文化。
然而,我们文言文教学的现状并不好:教师片面注重文言文的表象教学,只顾着抓字、词、句的直接对照翻译,又一味单纯地强调语言基础,单纯以讲、记、背、默、译为线,强迫学生记忆、练习,缺乏对古代文学作品潜藏魅力的开发研究,一篇篇文质兼美的古文被分解得支离破碎,魅力全无;文言文教学的情味尽失;学生的兴致永远无法高涨,学生对文言文的厌烦程度日益加重,甚至到了痛恨的程度。这显然与《语文课程标准》中的“感受、鉴赏、思考、领悟”的目标相去甚远。在这样的现实面前,“找寻文言文教学的情味”理所应当成为我们每一位语文老师关注并努力的对象。
叶圣陶先生强调:“阅读方法不仅是机械地解释字义,记诵文句,研究文法修辞的法则,最紧要的还在多比较,多归纳,多揣摩,多体会,一字一语都不轻易放过,务必发现他的特性。”[1]这也就是要求教师引导学生将含蓄在话语中的意思、情趣以及作者运用语言的精妙之处,都把它体会出来,和作者的心情相契合,从而使学生的语感更丰富、更敏锐。
所以,在笔者看来,文言文翻译的确是文言教学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但是,翻译的理想境界应融字句意思的理解和思想、情感、风格等的体味为一体。“一字未宜忽,语语悟其神”,要帮助、促使学生悟出文章中传神的字字语语,让学生忘记是在翻译,而觉得是在体验,通过文章独特的语言形式、音韵节奏和旋律跌宕,走进作者所描写的情境中,与作者对话,去感受作者,体会作者,爱着作者的爱,恨着作者的恨,最后真正内化吸收,从而增添文化内蕴,丰富情感知觉。因为,语言和思想本来就是统一的,有人说,语言最重要最深刻的作用就在于能由美归真(艺术的真实),深入生命节奏的核心,表达瞬息万变的动静状态和生命节奏的韵律。很多经验也都告诉我们,一旦言语形式稍有变化,譬如增加、删减或改变一个词、一个标点,或者调整几个字的顺序,言语的内容将随之发生变化。比如,贾岛诗中的“推敲”二字,“问题并不在‘推’字和‘敲’字哪一个比较恰当,而在哪一种境界是他当时所要说的而且与全诗调和的。在文字上推敲,骨子里实在是在思想情感上‘推敲’”[2]。所以,引导学生翻译的同时,重视一些富有情味的实词、虚词和句式,悉心研究一番,潜心思虑一通,不仅能大大减少翻译的“无趣”之嫌,使对作品的感受、鉴赏、思考、领悟落到实处,而且也能促使学生从中发现古文字的情趣,感受作品的韵味,领略古典文学的魅力,从而愿读、喜读、多读。
对于此,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我进行了一些尝试,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重锤敲打富含情态的实词。
黑格尔说过:“艺术家要善于驾驭形式,音乐家应很快把感情变成曲调,画家应把感情变成线条和色彩,文学家应把感情变成语言和文字,把思想感情通过专业技巧表现出来”[3]。思想,意即语言和文字再现了活泼泼的生活场景,凝练了深刻内蕴的哲理情思,实现了作家的思想情感。古汉语中的实词与现代汉语中的实词一样,除了抽象地反映事物对象之外,还带有不同的感情色彩、形象性等情态特征,担负起表情达意的功能。因此,对于富含情态,看似平常实不寻常的字词(尤其是动词),不能轻易放过。
比如,《触龙说赵太后》中有这样一句:“左师触龙言愿见太后。太后盛气而揖之。入而徐趋,至而自谢……”其中,“徐”的意思很清楚,即“慢慢”之意;“趋”呢?查《古汉语字典》或《新华大字典》等辞书都能弄清,如《新华大字典》中说:“趋的本义指跑,又特指古书上一种为了表示恭敬的礼仪性的小步快走,引申为奔向,趋向。”那此处,“趋”应取“一种为了表示恭敬的礼仪性的小步快走”之意。翻译“人而徐趋”一句时,学生一般都翻作“触龙进宫后慢慢走上前去”或“触龙进宫后,就慢慢地小步快跑上前”,就此作罢。然而我提醒他们好好想想翻出的句子,就发现了矛盾之处:又是“慢慢”,又是“快跑”,真令人费解。是不是真的是文字表达的错误呢?于是,我就引导学生从上下文语境出发找出答案。经过讨论达成共识:一般情况下,臣见君,应“疾趋”,触龙见赵太后当然应“疾趋”,但因为他脚有毛病,只能以“徐趋”的步子走,用前倾快步走的姿势,一步一步向前慢走。“徐”与“趋”两个互相矛盾的词放在一起,活画出一位老者想表示恭敬小步快走却走不动的老态,以动作示其足痛,这是一种有意识的苍老,他的机智,他的从容不迫为下文闲谈乃至提出为子谋职做了铺垫。这一句也可以翻译作:触龙做出快步走的姿势,慢慢地挪动着脚步。
在此过程中,学生饶有兴致地阅读上下文,比较“疾趋”与“徐趋”的不同之处,同桌或前后桌进行热烈的讨论,组织语言,形成答案。当达成共识后,学生欣悦之情溢于言表,而这样的良好情绪又很好地激发了之后的学习热情,也使触龙的“可爱”形象在学生脑中清晰了一些。
又如,在翻译《促织》中的句子时,有个别学生突然发现似乎有些不对,“循陵而走,见蹲石鳞鳞,俨然类画”一句,其中的“走”是古今异义,应解释为“跑”,但是前文却有“旬余,杖至百,两股间脓血流离,并虫亦不能行捉矣”,且“循陵而走”之前就有“乃强起扶杖”的记叙描写,扶着拐杖才能勉强行走,此处如何能“跑”呢?细究之下,体味不少:杖打之后,伤痛是真实的,几日后,扶着拐杖才能勉强行走,正可以看出成名被打得不轻;然而,在不能捉到好的蟋蟀,全家就不能过上平安的日子的事实面前,捉到善斗的蟋蟀已经是成名心中唯一的念想了,可以让他忘记伤痛,不顾一切地奔跑、寻求。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孱弱的成名拖着伤腿,忍着剧痛奔跑寻找的惨样,颇感心酸。联系后文,也更使我们体悟到了蒲松龄所要揭露的“官贪吏虐”之毒和所表达的“故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不可忽也”的深刻主旨。
第二,悉心揣摩表示语气的虚词。
讲虚词,一般只讲它的语法作用,例如“也”是个语气词,用在句末表示解释或判断,有时也表示感叹、祈使、疑问和反诘等语气;用在句中则表示提示。但古人写文章用虚词,却更加看重它表情达意的作用,因为虚词用得好,确实有“含不尽之意于言外”的效果。如清末古文家林纾所说:“须知有用一语助之辞,足使全神灵活者,消息极微,读者隅反可也。”
欧阳修在《醉翁亭记》里连用21个“也”字煞句,就是创造性地使用虚词的一个范例,读来只觉得神采飞扬,摇曳生姿,而绝无单调重复之感。大约有两个原因:第一,文章采用了直接诉诸读者形象思维的写法,总是先将实际的景物描绘出来,而后加以解说,如此层层展开,有如画卷平舒,每一层又都用一个“也”字结住,使人感到不疾不徐,自然合拍,使文章形成一种富有韵律的吟咏句调,具有舒缓圆畅的散文节奏。第二,作者的纵情山水,其实是在与老百姓一同享受无忧无虑的生活。这种感情既渗透在景物描写之中,与之互为表里,又表现在某些内心独白式的话语里,这就使全文洋溢着一种平和、愉悦的情调,而“也”字的连用则恰好成为这一情调的最合适的表现形式。所以,宋人罗大经《鹤林玉露》有评:欧阳修“唯用平常轻虚字,而妙丽古雅,自不可及”[4]。
由此可见,对虚词不能只是立足于把它放在句子范围内来进行研究,了解其语法作用,还应着眼于全篇,领会其在表情达意上的作用,体察其情味。
比如“乎”,可表示揣度语气,相当于“吧”;也可表示感叹语气,相当于“啊”“呀”。《触龙说赵太后》中“日食饮得无衰乎”一句中,“得无”与语气词“乎”组成“得无……乎”的句式,是古汉语中的固定句式。此句式表示对某种情况的推测,“得无”可译为“该不会”或“恐怕是”,显然“乎”应译为“吧”,整个句子应译为:您每天的饮食该不会减少吧?这一点不难明确;但如果我们可以好好揣摩体味一下这“乎”(即“吧”)中的情感内蕴,便可体会到:“日食饮得无衰乎”的询问中充满了一个老臣对主子的真切关注,从而营造出一种和谐的交流氛围,这氛围氤氲着温情,于是,一番叙寒暖、拉家常,便从精神上解除了太后戒备之心,作用着实不小。
再如,韩愈《祭十二郎文》第五自然段中,从“呜呼!其信然邪?其梦邪?其传之非其真邪”以下,先是连用三个“邪”字,紧接着又接连不断地连用三个“乎”字,五个“矣”字。在进行此段翻译时,“邪”应作“呢”讲,这一点学生很快就达成了共识,但是,对“乎”和“矣”的翻译却多有分歧,并且也牵涉到对整个句子翻译应采用什么句式的问题。如,“少者强者而夭殁,长者衰者而全存乎”一句中,“乎”在此处是表示疑问还是表示反问?是翻译成“呢”好还是翻译成“吗”好?那整个的句式是用一般疑问句式好还是用反问句式好?而“矣”可作“了”,也可表示感叹,翻译成“啊”,还可翻译成“了啊”,哪一种更好?显然,这已经不仅仅是翻译的问题,只有从情感表达的角度来定夺哪一种翻译更加符合韩愈初闻噩耗时将信将疑,不愿相信又不得不信的心理,更能实现韩愈处于极度悲痛之中极端复杂和矛盾的心态。虽然在课堂讨论中,关于这几句的翻译到最后也没能完全趋于一致,且花了不少的时间,但学生的翻译向古文翻译“信、达、雅”之“雅”的要求迈进了一大步,并且对韩愈之于十二郎的满腔真情的体悟真正做到了深入肺腑。在集体诵读时,真情投入,沉浸其中,感人至深,实现了情感的升华,对《古文观止》中“情之至者,自然流为至文。读此等文,须想其一面哭,一面写,字字是血,字字是泪。未尝有意为文,而文无不工”[5]的评论体察颇深。
第三,仔细推敲深蕴情感的句式。
常见的句式有:(1)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和感叹句;(2)肯定句和否定句;(3)主动句和被动句;(4)长句和短句;(5)整句和散句;(6)常式句和变式句。这些句式恰到好处地运用,对于表情达意大有好处。有时不同的句式可以表达基本相同的内容,但就语势强弱、感情色彩、节奏韵律等方面来说,肯定是有不同的,甚至可以说,只有这一种句式最适合表达这一种意图或这一种情感。在翻译过程中,有意识地引导学生推敲作品所选用的句式,不仅可以使翻译的落实更为细致,而且可以使学生更深入地领略文章内容和思想,同时,这种推敲也能反过来促进学生在行文说话时对句式的选择能力。
在《邹忌讽齐王纳谏》一文中,邹忌向他的妻、妾与客分别提出自己与徐公谁美的问题。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其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这三句回答所表达的意思一样,都是“徐公没有您漂亮”。但妻与妾的回答采用了疑问(反问)句式,而客的回答所运用的只是一般句式,而且妻的回答的前半部分可以视作采用了一个感叹句式。这三句话在翻译上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难度,可是,其句式上的差别正是我们应仔细比较辨别的。
我们可以发现,这三个句子的感情色彩不同:妻是由衷的赞美,口气亦毋庸置疑;妾的话有讨好的意味,口气有点勉强;客呢,其中礼貌、尊重的成分占多,口气有点客气,而这样的不同正是由于感情的不同及身份地位的差异。邹忌正是因为敏感地察觉到了这种细微的差别,才进而“推自己及齐王”,发现“王之蔽甚矣”,其自知之明可见一斑,其善于劝谏可见一斑!
再如,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一诗,句式特点及其对表达情感所起的作用也可以在诗句翻译时多加体会。这首诗的句法的变化极富于创造性,虽然以七言为基调,但是还交错地运用了四言、五言、六言和九言的句子,浑然一体,非常协调。诗句有长有短,节拍有急有缓,诗体流畅自然,完美地表现了李白感情的起落及其豪迈奔放的个性特征。如“云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烟。……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一段中,节奏变化极快,先作六字句,忽改作四字句,忽又作七字句,其间又杂以九字句。六字句写诗人惊定时所见,采用了楚辞的句法,舒缓浪漫;四字句写诗人惊奇于自然界之神力,急促跳跃,于毛骨悚然动人心魄之中又柳暗花明;七字句写仙境初开,金碧辉煌,令人目眩,仙女聚会,盛况空前,明艳之中不失轻快,气象非凡。再如诗末两句“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前五拍,后四拍,顿挫有力,表现出了诗人不可一世的豪迈气概和蔑视“权贵”的傲岸襟怀。这些,如在翻译讲解的过程中加以指点体会,定能使学生在了解大意的基础上,更快更好地深入审美鉴赏的层面。
第四,激情诵读,实现内化。
这是基于文言文学习特性而言的,不管你的翻译有多完美,体悟有多深刻,你学习的都并不是现代语言组织而成的现代文章,“文言翻译”所能成就的是扫清理解的障碍,完成局部的审美,你应回过头“直接”面对文言文章,进一步进行整体把握、审美评价和内化吸收。此时,“诵读”应不失为一种最佳的方法。
叶圣陶先生一向重视语文课中的美读。他指出:“所谓美读,就是把作者的情感在读的时候传达出来。这无非如孟子所说的以意逆志,设身处地,激昂处还他个激昂,委婉处还他个委婉——美读得其法,不但了解作者说些什么,而且与作者心灵相通了,无论兴味方面或受用方面都有莫大的收获。”[6]诵读把躺着的书面文字,用声音立起来,出口时的声音负载着思想感情,增强了语言文字的可感性。学生通过反复多遍的诵读与课文的语言文字反复接触,才能更深刻地领会作者在字里行间的语言节律,受到更直接、更强烈的感染,才能真正体会到古典文学的独特魅力,感受到文言教学的情味,进而喜欢我们的古代文化,传承并发扬我们古代文化的精髓,这也才实现了完整的真正意义上的文言文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