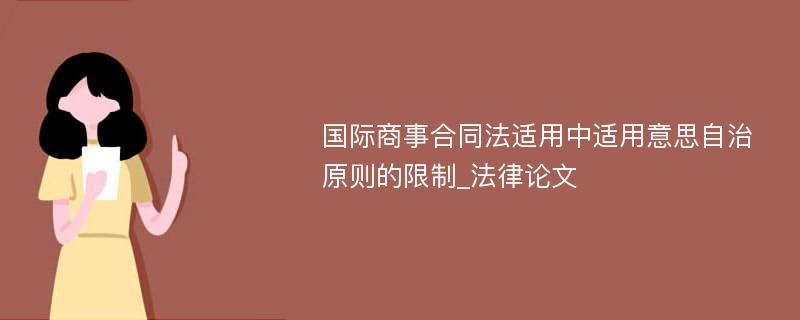
“意思自治”原则在国际商事合同法律适用中的适用限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商事论文,则在论文,合同论文,法律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认为:“意思自治”原则已经成为国际商事合同法律适用的首要原则,各国对合同当事人选择法律的方式、选择法律的时间和选择的法律等均有不同程度的限制;我国宜有限度地承认涉外合同的当事人默示选择法律的方式;不宜禁止当事人在合同订立后争议发生前这段时间选择适用法律,也不宜禁止当事人在合同订立后协议变更原选择适用的法律;而对合同当事人选择的法律所涉及的问题则应作出相应的限制性规定。
一
在国际私法上,国际商事合同领域里的“意思自治”原则是指合同当事人有权在协议一致的基础上,选择某一国家或地区的法律来支配其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一旦当事人之间产生争议,受案法院或仲裁机构应以当事人选择的法律作为合同的准据法,以确定其间的权利义务〔1 〕。
“意思自治说”作为合同法律适用的一种理论, 其萌芽可追溯至15世纪后期注释法学派的代表者诺忽斯·柯迪乌斯(Rochus Curtius)的观点。巴托鲁斯(Bartolus)在“法则区别说”中认为,有关合同的形式及效力应适用合同缔结地法。柯迪乌斯则认为,之所以要适用合同缔结地法,是因为当事人已默示地同意适用该法〔2〕。此后, 杜摩林(Dumoulin)在柯氏观点的基础上,在《巴黎习惯法评述》一书中,系统地阐述了自己正面的结论:合同当事人的意志可以决定适用于合同的法律。在当事人无明确表示时,应根据各种事实所确定的默示的意思决定适用于合同的法律。由于杜氏的学说与资产阶级所倡导的“契约自由”思想相吻合,因而其学说受到了胡伯(Huber)、萨维尼(Savigny)、孟西尼(Mancini)和斯托雷(Story)等一大批法学家的赞同,并先后传入英美及欧洲大陆各国。
然而,当资本主义步入垄断阶段后,随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出现,“意思自治”理论同“契约自由”哲学一样受到了相同的“礼遇”,许多人对此提出了自己反对的观点。其中最主要的反对意见为:其一,承认当事人意思自治可能会为当事人规避法律提供方便〔3〕;其二, “意思自治”理论给予了个人一种通常只能由立法者才能行使的权利。
但是,由于“意思自治”的实质即是“契约自由”论在合同领域的具体体现,因而,它符合国际民商事流转活动对自由的需求;而且,将此理论上升为一项法律适用原则,符合法律规范必须是一般正义、效率及安全等价值承载者的要求。因为,这一原则首先有利于合同法律适用结果的可预见性,即所谓在谈判进行时,就使合同受到一种法律的完全支配,从而有利于国际商事合同关系的安全;其次,“涉外合同适用当事人选择的法律”这一冲突规范简洁而明确的系属,有助于提高解决合同争议案件的效率;再则,这样一种不确定性规范在通常情况下的适用,自然可以展示法律富于人情的一面,它可以通过对国际民商事合同不同情况各得其所的处理,而得到人们对法律的敬服,这无疑是有助于体现出法律的一般正义性要求的。正因为此,“意思自治”理论不仅获得了国际私法理论界的广泛支持,而且,现代国际私法的实践也表明,“意思自治”原则已是确定国际商事合同准据法的首要原则。
我国1985年《涉外经济合同法》规定:“合同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1986年《民法通则》第145条和1992 年《海商法》第269条也有与之相似的规定, 这表明我国在立法上已经确立了“意思自治”原则在涉外合同法律适用中的首要的原则性地位。关于该原则的司法实践方面的规定主要体现在198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外经济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答》(以下简称《解答》)中〔4〕。 对于包括这一原则在内的我国涉外合同法律适用的制度,有学者指出它反映了当今国际社会关于合同法律适用的最进步的理论和实践〔5〕。
那么,在“意思自治”原则已成为国际商事合同法律适用的首要原则的今天,是否意味着当事人可依此原则而享有绝对的或完全的选择法律的自由呢?从实践上看,大多数国家一方面在赋予这一原则以首要的法律选择的地位时,又在相关条件下和相应方面对该原则的适用规定了不同程度的限制。其具体表现主要为对当事人选择法律的方式、选择法律的时间及选择的法律本身规定相应的限制。
二
(一)关于合同当事人选择法律方式的限制
合同当事人选择法律的方式是指当事人表达自己选择合同准据法的意向(Intention)形式。其包括明示和默示两种方式, 所谓明示法律选择(Express Selection )是指当事人在合同的法律选择条款或合同外的法律选择协议中,对自己选择有关法律为合同准据法之意向的明确表达;所谓默示选择(Implied Selection )则是指当事人在合同中或其它与合同有关的行为中对自己选择有关法律为合同准据法之意向的暗示。
通常,各国对合同当事人选择法律方式的限制,主要是对当事人默示选择方式的限制。其作法主要有以下三种:
其一是只承认明示的法律选择,不承认任何默示选择。如土耳其、秘鲁和我国即是如此〔6〕。 我国在立法上未明确规定合同当事人选择法律应采用何种方式,但1987年《解答》则规定:“当事人的法律选择必须是明示的。”
其二是有限度地承认默示的选择。法国法院据以确认当事人默示选择法律的主要标志有:当事人在合同中就某一特定问题援引了某国法律的规定,对争议解决地点的选择、对特定国家格式合同的采用;其它标志为:合同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的态度,合同使用的文字、付款地点及货币种类的选择等〔7〕。可见, 法国法院的有限承认方式即是以与合同当事人主观意志有关的行为因素,作为确定当事人默示选择法律意图的主要依据。
1955 年《海牙公约》(全称为《国际有体动产买卖法律适用公约》)规定,当事人的选择“必须在明示的条款中规定,或者是根据合同的条款必然得出的结论”〔8〕,据公约报告人的解释, 这里所考虑的因素仅限于合同包含了某国法律条款或某国格式合同的情况〔9〕。1978年《海牙公约》(全称为《代理法律适用公约》)规定合同当事人的法律选择“必须是明示的,或者是从当事人之间的协议以及案件的事实中合理而必然地可以确定的”〔10〕,该公约与前者相比,显然放宽了对确定当事人默示选择法律意图的限制。1986年《海牙公约》(全称为《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法律适用公约》)规定当事人选择法律的协议“必须是明示的或从合同的规定或当事人的行为整体看可以明显地证明出来(Clearly Demonstrated)”〔11〕,这里合同“当事人的行为整体”作为确定其默示选择法律的依据之一,显然不同于1978年公约所称的“案件的事实”。笔者认为“当事人的行为整体”应主要是指案件中与当事人的主观意志有关的因素。
其三是依据案件的各种情况推定(Presume )合同当事人默示选择法律的意图。这是以英国为代表的作法:若合同当事人对解决其间争议的地点已选择在英国的,即可迳直认为当事人已默示选择了英国法为合同准据法;其他可作为推定的依据为:当事人对合同格式、用语及合同中特有法律术语的选择,合同当事人的住所、国籍、合同标的特点及位置等〔12〕。但在作推定时,是以以上其中之一为准、抑或将其中一部分或全部与案情结合起来考虑,英国并无一固定的规章。
我国及部分国家在实践中对默示选择法律方式持否定态度的主要理由为:其一,由法院或仲裁机构根据种种因素推定合同当事人默示同意适用的法律,往往并不能真正代表当事人的意图,事实上易导致法院地法适用范围的扩大;其二,这种作法在许多情况下不利于保证法律适用结果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
尽管如此,笔者认为,我国应当在国际商事合同领域里有限度地承认当事人默示选择法律的方式。
首先,前述反对理由中第一点固然有其合理性,但在一定程度上却未认识到默示选择与“推定默示意图”的本质区别。〔13〕因为默示选择之实质为合同当事人选择某国法律的一种暗示,它在法院或仲裁机构确定当事人选择法律的意图之前就已客观存在;而据后者,法院或仲裁机构在作推定时,并不以合同当事人是否既存默示选择法律的意向为必要前提。因而,从本质上讲,承认默示选择方式意味着对“意思自治”本意的遵守,而承认推定选择,则往往会与“意思自治”的本意相违背。
其次,承认这一选择法律的方式,诚然会导致法律适用结果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见性,但在国际私法领域所有的法律适用原则中,此缺陷并不为默示选择法律方式所独有。况且目前各国在这方面都有一定的限制,即要求必须在十分明显或确定的条件下才得认定合同当事人的默示表示,这无疑可以尽量保证法律适用结果的公正性与合理性。
第三,前述海牙三公约的规定只是表明公约对合同当事人默示选择法律方式的限制,而不是对这一方式的否定;而在对确定合同当事人默示选择法律的结果的要求方面,海牙公约的规定已出现了一种越来越要求最准确、最完整地反映当事人选择法律真实意愿的趋势。因此,我们现在所要解决的不是应否承认默示选择法律方式的问题,而应该是在承认这一方式的基础上,如何尽量避免和减少法律适用结果的公正合理性要求与法律适用结果的不确定性、不可预见性这一对矛盾所产生的问题。
再则,这时里所说的“有限度”即是,我们不妨借鉴法国的作法,以与当事人的主观意志有关的行为因素作为确定其默示选择法律意图的标志。这类行为往往是当事人选择法律心理活动的表现,因而只有这类行为才可以被认为符合严格意义上的“意思自治”;若象英国那样,以合同当事人的住所、国籍、合同标的的特点及位置等客观因素作为确定依据,就很难明确区分“意思自治”原则和“最密切联系”原则在合同法律适用中的作用;而且,这种有限承认的作法也比较符合我国的现实。
我国司法实践只承认明示法律选择方式,而在合同当事人无明示法律选择的情况下,则是以“最密切联系”原则作为确定合同准据法的依据,而此原则又主要是借助“特征性给付原则”实施的。依这两项原则确定合同准据法时,一般是以一些与合同有关的客观因素,如当事人的营业所所在地、住所地、行为地、财产所在地等作为特征性给付地的界定依据。这样产生的问题是,在某一涉外合同中,若从与当事人的主观意志有关的行为因素可以明显地看出当事人已存在默示选择法律的意图时,而又不考虑此,直接依这两项原则确定合同的准据法,则有可能违背当事人的初衷,从而不利于合同争议公正、合理地解决。
(二)关于合同当事人选择法律的时间限制
任何一项国际商事合同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处于法律支配的“真空”状态,基于此,涉及当事人选择法律的时间问题是:(1 )当事人在合同订立后能否选择支配合同的法律?(这里有两种情况:其一是合同订立后争议发生前,其二是争议发生后)(2 )当事人能否通过协议变更原选择的法律?
有些学者对以上问题是持否定态度的。如莫里斯认为,当事人选择法律的意图只能以订约时为准,在确定合同准据法时,对当事人在订约后实施的行为不应予以考虑〔14〕。但在实践中,这类观点未被大多数国家采纳。
1987年《瑞士联邦国际私法法规》规定:“对法律的选择可在任何时候作出或修改。如果作出或修改是在合同订立之后,其效力溯及合同订立之时。”1980年《罗马公约》(全称为《欧共体合同义务法律适用公约》)和1986年《海牙公约》也规定,当事人可以在任何时候协议变更其合同所适用的法律〔15〕。
我国立法上对此无明文规定,但从1987年《解答》的规定看,我国司法实践只承认两种时间的选择为有效,即合同订立时、或争议发生后至开庭审理前。
笔者认为,我国法律不宜限制合同当事人选择法律的时间。首先,当事人在合同订立后协议选择法律的行为或变更原选择法律的行为,与原订立合同的行为相比,属从行为。但从其本身来看,属独立的契约行为,而且其目的在于为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的确定寻求法律依据。因此,承认当事人在合同订立后的所有时间内选择或变更法律的有效性,符合我国法律已经确立的“意思自治”原则的本意;其次,前述“意思自治”原则已成为国际商事合同领域各国普遍采用的一项原则,从各国对当事人选择法律的时间规定看,通常作法是不作限制。因此,借助法律解释中的“比较法解释方法”,即通过“引用外国立法体例及判例学说,作为一项解释因素,用以阐述本国法律内容”〔16〕,我们不妨可这样认为:既然我们采用了这一各国普遍采用的原则,也就接受了大多数国家在当事人选择法律的时间限制上的作法。
当然,如同1980年《罗马公约》和1986年《海牙公约》那样,各国在允许当事人在合同订立后选择或变更原选择的法律时,又对当事人的行为规定有两方面的限制:第一,不应对第三人的权利造成影响;第二,不得有损合同在形式上的效力〔17〕。这样作显然是旨在保护善意的第三者,以防止当事人通过变更准据法造成对第三者不公平的结果产生。这种作法,我国立法者不妨可资借鉴。
(三)关于合同当事人法律选择的限制
这一限制主要涉及的问题为:当事人选择的法律能否排除与合同有关的国家关于合同的强制性规则?当事人能否选择与合同无客观联系的国家的法律?
从各国的实践看,如果说各国在国际商事合同领域对适用“意思自治”原则的某些方面(如当事人选择法律的方式、选择法律的时间)的限制有减弱趋势的话,那么各国对当事人法律选择的限制却有加强的趋势。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对当事人法律选择所涉及的上述问题,各国都有较为详尽的规定。如关于前述第一个问题,英国的判例规则为,当事人的选择不能排除特定英国制定法(如1977年《不公平合同条件法》)的适用;瑞士国际私法及1986年《海牙公约》对此也有明确规定,且规定当事人不得通过法律选择排除适用法院地和法院地之外的国家适用于国际合同的强制性规定〔18〕。而对前述第二个问题,英国法院早在1939年的维他食品案(Vita Food Product Inc V.Vnus Shipping Co Ltd)中和1949年的波塞文案(Beisserain V.Well)中, 就确立了所谓主观善意标准和客观善意标准,这两种标准分别在不同情况下被采用。各国在这些问题上的详尽的规定,无疑有利于国际商事合同的当事人签约时有章可循,有利于国际商事合同案件的处理有法可依。但与此同时,由于各国内法对当事人选择法律所涉及问题的限制性规定存在歧异,这些歧异又通过何种方式来解决,则又为国际私法的理论与实践提出了必须解决的新问题。
第二,重视法律选择的政策导向,以致对某些特殊类型的合同排除了“意思自治”原则的适用。
前述各国对当事人通过法律选择,排除适用一与合同有联系的国家的必须适用于国际合同的强制性规则(有人称之为“直接适用的法律”)的行为,都规定为无效。这一作法正是现代国际私法重视政策导向,从而导致“直接适用的法律”的地位进一步提高的结果。
所谓“直接适用的法律”是指一国为维护其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而制定的专门适用于某类涉外民事关系的强制性规范。由于它不是笼统的法律制度而是一项项具体的法律规范或文件,这些规范往往都是按自我设定的“适用范围”而迳直适用于相应的涉外民事关系的,因此,在国际商事合同领域“直接适用的法律”的效力范围内,是绝对排除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另外,由于这类法规一般体现在各国具有公法性质的经济立法中,如外汇管制法、技术转让法等。这样,各国有关“直接适用的法律”的适用范围的规定,就反映出了当今国际私法另一值得注意的动向,即适用外国法时,其公法同样可以适用〔19〕。
重视政策导向,限制合同当事人选择法律的另一方面表现为保护弱方当事人的利益。如在消费者契约方面,欧洲国家一般把消费者视为弱方,在解决法律冲突时,只适用消费者的惯常居所地国家的法律,而不允许当事人选择适用其他的法律(如1987年瑞士国际私法第120条); 在劳务雇佣合同方面,新近立法也对当事人选择法律作了一定的限制,规定原则上适用劳务履行地法,同时还注重法律适用的灵活性与合理性,对不同的情况分别规定不同的连结因素,以示不同案件应分别适用不同的法律(如1978年《奥地利联邦国际私法法规》第44条)。
从我国的立法及实践看,我国对当事人选择法律的限制主要有:通过公共秩序保留制来限制当事人选择法律的适用,而这在立法技术上采取的是合并规定的方式,即并用“消极的排斥条款”和“积极的保留条款”。据此,涉外合同的当事人选择的法律不得违背我国的公共秩序;在我国境内履行的中外合资、中外合作企业合同,中外合作勘探开发自然资源合同适用我国的法律。在选择法律的范围方面,1987年《解答》规定,当事人选择的法律可以是中国法,也可以是港澳地区的法律或是外国法律。但所选择的法律是否必须与合同存在联系,我国立法及实践未作规定。
据此,笔者认为,我国对合同当事人的法律选择,除现有规定的限制外,还应借鉴其他国家和1986年《海牙公约》的作法。而对某些特殊合同,如涉外消费者合同和雇佣合同当事人的法律选择,也可象前述各国那样作出相应的限制性规定,同时,还应加强和进一步完善我国在消费者保护法和劳动法方面的立法。
注释:
〔1〕〔13〕《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9月第一版,第464页。
〔2〕〔7〕享利·巴迪福著:《国际私法各论》(曾陈明汝译),台湾正中书局1979年10月第二版,第277页、319—322页。
〔3〕Von Bar.Theorie und Praxis Internationals Privaterecht.1989.Vol—2.PP.5.
〔4〕《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87年第4期。
〔5〕李双元主编:《中国与国际私法的统一化进程》, 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5月第一版,第93页。
〔6〕〔10〕〔11〕〔15〕〔17〕〔18〕韩德培、 李双元主编:《国际私法教学参考资料选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7月第一版, 第207页、306页、479页、504—505页、492页。
〔8〕卢峻主编《国际私法公约集》,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10月第一版,第303页。
〔9〕Document Relating to the 8th Session of the HagueConference o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PP.236—237.
〔12〕Morris and North. case and materials on PrivateInternational Law.1984.PP.454.
〔14〕Dicey and Morris.the Conflict of laws.1980.10thed.PP.753.
〔16〕梁慧星:《论法律解释方法》,载《比较法研究》1993年第1期,第57页。
〔19〕韩德培:《国际私法的晚近发展趋势》,载《中国国际法年刊》(1988年),第14—1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