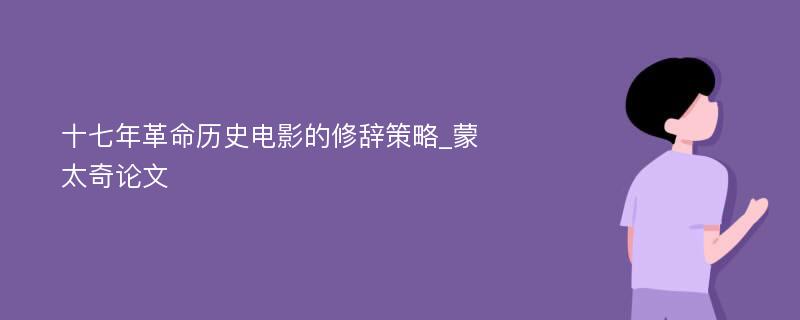
“十七年”时期革命历史题材电影中的修辞策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修辞论文,题材论文,时期论文,策略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9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302(2011)01-0005-05
电影是运用视听语言建立起来的叙事连续体,本文表述的电影修辞是指由视听语言构成的各种规则和惯例,如果从这个维度考察“十七年”时期革命历史题材电影,会发觉这一时期的电影创作者大多能够熟练运用视听语言表现空间、时间和叙事关系,而且在利用修辞策略配合意识形态需要方面做了大量的实验。
一 电影修辞和叙事内容的顺畅结合
这一时期的创作者运用视听语言的原则是建立在“三个服务”上,即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为叙事服务和为意识形态服务。为了使修辞手段更好地贯彻落实到“三个服务”中,创作者首先要做的就是消除视听造型上的陌生化。当时电影事业的领导者夏衍明确告诫创作者,技术是为主题服务的,为作者所要表述的思想服务的,离开了主题耍技巧,这是本末倒置,片面强调技术,甚至为技术而技术,这就会陷入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的泥沼,而实际上,政治和艺术分不开,主题思想和运用的技术也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①夏衍强调的主题、政治,实际上就是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为了使他的观点更有说服力,能够最大范围地被创作者接受,夏衍经常以自己的创作经历来现身说法,他说自己以前脑子里有洋教条,片面追求简练,结果是拍出来的片子群众看不懂,也就达不到目的,说明自己脑子里群众观点还不明显,因此他得出电影的手法一定要大众化的经验,否则就会犯主观主义的毛病。鉴于这样的认识,于是就有一系列对应的要求:“必须时刻记住电影是最富群众性的艺术,写一句话,拍一个场景,都要考虑到群众的喜闻乐见,都要考虑到千千万万观众的接受程度,都要考虑到影片的社会效果”。②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夏衍的要求是十分细致和明确的:凡是关键性的情节、语言、性格上的反映等等,一定要交代清楚,可以用特写来突出表现。他认为在中国的戏曲里常常反复地重复主要的东西,不失为一种有效的传统,适合于电影这种“一次过”的艺术。有了这样的指导原则,从当时电影的画面构成来看,在取景构图、视角选择、明暗色彩和光学技巧等视觉元素的使用上均强调保守的现实性以接近观众的视觉经验和思想逻辑为标准,就不足为奇了。比如张客在分析《青春之歌》的艺术特色时,指出导演在镜头的分切、衔接和镜头内部的场面调度上,“都不离开主题,不离开人物,每一个镜头都有来龙去脉,不孤立,有前呼,有后应。”③这不光是对一部影片修辞内容的总结,也是当时绝大部分影片共同遵守的艺术规条,我们可以对当时影片中的修辞策略作一个大致的梳理:
(一)避免造型的陌生化
尽管当时的理论工作者也在提醒创作者注意电影的“特性”,但在实际创作中还是更多地依赖其他姊妹艺术,尤其是戏剧和文学这两根“拐杖”。虽然有的创作者并不忽视摄影造型、美术造型与音响等元素的作用,比如在拍摄影片《南征北战》时,为了得到新颖的角度,摄影师想出了许多土方法,在陡峭的山崖上用木板搭出一条数十米的长条,将摄影机和机器伸出去,以便能够拍摄到敌我双方争夺凤凰岭的大全景场面。④但在多数情况下,“特性”意识主要体现在形象本性上面,他们不在电影“本性”(美学原则)层次上进行突破和创新,更不愿意追求影像的独立审美价值,创作者排斥对客观事物作主观性、假定性的处理。在“普及为主”的原则下,各种艺术技巧的使用被认为会妨碍观众对影片的接受,影片《桥》摄制组在总结拍摄经验时就写道:“导演在过去的拍摄过程中,有两条顾虑,怕观众看不懂,又怕手法太洋气,因此‘推拉摇移’都没敢用”,⑤在这样的自我约束下,许多影片就大量铺陈纪录片式的生活场景,一切都交代得详详细细,按部就班,造型处理上崇尚自然、写实。
(二)组接上的自然顺畅
通俗性、人民性要求在节奏上体现为晓畅明白,这一时期革命历史题材电影的镜头组接遵循的是清楚流畅的剪辑风格,创作者成功地隐藏摄影机,以让人察觉不到剪辑的存在为最高原则。大部分导演遵循“跟着角色走”的思路,似乎电影就是主人公言行的记录。在具体的技法上,遵循视点原则、轴线原则和动作匹配原则;剪辑讲究逻辑关系,体现因果关联性。在场景转换时,创作者尽量做到自然、顺畅,前后有照应。如在影片《逆风千里》中,第1个镜头先是指导员的中景,他对老纪交代道:“你命令一班、二班,立即行动,在七点钟以前做好战斗准备。”然后镜头摇到马蹄表(闹钟),变成特写,指针指向6点40分,第2个镜头是从表的特写开始,指针指向6点40分,和前一个镜头一样都是钟表的镜头,用对时间的重视把两个场景联系在一起,然后摇到国民党军孙师长的脸部特写,慢慢拉开成双人镜头,他身边的副师长叹息道:“队伍怎么还没来”,镜头摇成战士搬箱子的全景,不知不觉中已经完成了场景的转换,而且节奏明快。
由于当时影片的结构受到戏剧式分幕、分场的影响,淡出淡入、划出划入等传统组接手法运用得较多,同时为了适应审美经验不多、但民族审美趣味相延成习的农村观众的需求,在剪辑时很少运用可以省略时空过程、但能突出必要内容的“跳接”,这样的结果是镜头组接比较平稳,但难免也会导致影片的节奏拖沓、沉闷。
(三)对蒙太奇属性的重视
由于倡导对生活进行加工改造的文艺主张,自然就派生出来对蒙太奇的情有独钟,而不是长镜头、景深镜头,因为蒙太奇“不仅仅是将各个拍摄下来的片段加以连接而使观众对连续发生的动作获得完整印象的表现手段,而是将各种现象的隐蔽的内在联系变成明显可见、不言自明的最重要的艺术方法”,⑥这种艺术方法便于表达创作者的主观意念,展示强烈的戏剧冲突,因而十分符合服务意识以及民族审美习惯。“十七年”时期的创作者能够熟练运用多种蒙太奇手法,除了对比蒙太奇、平行蒙太奇、交叉蒙太奇、呼应式蒙太奇、心理蒙太奇、隐喻蒙太奇、错觉蒙太奇等常规蒙太奇处理手法,还有少量的镜头内部蒙太奇处理手法,通过演员调度、镜头运动、镜头焦点的变化等手段来完成情节的交代。《南征北战》中在解放军抢先登上摩天岭制高点后,采用了一个跟移拍摄的长镜头,将镜头移到拼命往上冲的国民党军队那里,完整地表现了两军短兵相接的紧张场面。这个运动镜头跟着人物的运动而自然而然地运动,不给人突兀、生硬的感觉。
(四)音响和音乐的渲染功能
这一时期的编导在对白以外的音响使用上,除了用来渲染环境气氛,更重要的是增强戏剧效果,衬托人物的情绪和性格。《野火春风斗古城》中,银环去监狱探望大娘,进了牢房后她大吃一惊:原来被关押的是杨晓冬的母亲!此时,窗外一道闪电和一声炸雷。临别前杨母摘下戒指交给银环,银环以为杨母知道了自己爱慕杨晓冬的心思,此刻,又是一声响雷。这两处音响处理,既贴切,又细腻,既是自然音响,又代表着银环的心身。在这段例子中,音响已经不是一种游移的元素,它的作用就像黑泽明说的那样,不是简单地增加影像的效果,有时候是其两倍乃至三倍的乘积。
“音乐好”同“故事好、演员好、摄影好”一起成为“十七年”期间评价好电影的一个标准,在音乐的运用上,它也成为表达影片内涵、强化人物情绪的手段,甚至成为影片的“点睛之笔”。名曲《流亡三部曲》与《五月的鲜花》不仅作为《青春之歌》中重要场面的插曲,而且成为影片音乐基调的有机组成部分,每当它出现时,或沉痛或激愤,无疑强化了作品的情感力量。而在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当卡拉为了护送古兰丹姆去找解放军,在路上被阿曼巴依暗枪打死时,女声合唱的高亢旋律回荡在冰山上:“光荣啊,祖国的好儿女。光荣啊,萨米尔的雄鹰!”以及影片《农奴》中表达对解放军的歌颂和农奴的觉醒的歌声,这些都体现出创作者对电影配乐形式和功能的进一步探索。
二 电影修辞与意识形态的有意缝合
由于“十七年”时期的创作者长期受主流意识形态的熏陶,加上他们精于民间修辞法则,在表现现实的同时适时地加入创作者自己的倾向性,使得文本的政治意指性大大加强,在处理光线、色彩、位置、角度、组接等诸多元素时,都表现出强烈的指向性和倾向性。
光线的倾向性。虽然在不同光源的设置、光的不同强度、明暗对比与光影变化上并没有多少突破,但摄影师在光源倾向上的实践是持续的,在用光线表现人物性格和精神面貌时也颇有收获。除了遵循影调为剧情服务的大原则,这一时期的光线处理也积累了一些程式化的经验,总体的格调是正面人物、英雄人物在明亮的光区,而可以忽略光源依据,让英雄人物的形象始终出现在亮部,避免有阴影和暗部出现,有道是革命者的浩然正气直接转化成布光依据。在《红旗谱》中我们可以发现,创作者对朱老忠常采用明快的光线,突出慷慨、豪壮的精神风貌。创作者有意识地让反面人物在暗部和阴影处活动,同样没有光源依据,在任何时间段,任何环境下,作为敌对势力的代表人物(如《烈火中永生》中徐鹏飞,《红旗谱》中的冯兰池)始终处在一种半明半暗的光影包围之中,让他在精神上处于劣势。
色彩的倾向性。这一时期的创作者并没有将色彩纳入到影片的总体造型基调设计中,换言之,并没有成为意义场域的支撑点,但某些带有象征意义的色彩,尤其是红色已经成为这一时期革命历史题材电影中不可缺失的符号,《青春之歌》中,林红的红梳子和红毛衣演化成林道静的红色旗袍和红色党旗;《烈火中永生》中的红色党旗;《红色娘子军》中的红色军旗,红色以及和它辉映的五星、镰刀、铁锤作为特定时期的“文化图腾”被一再渲染,红色被认为是凝结着烈士鲜血的颜色,是革命的颜色,是共产党的生命底色,当它在革命最艰难的时候出现,会给人带来信心和勇气,是曙光在前的预示,当它在胜利时出现,又作为指引人们迈向新征程的鲜明路标。
位置的倾向性。如果按照成规和惯例,导演只是在故事情节先在的、约定俗成的前提下,处理摄影机和演员的位置,多半是隐藏起摄影机的存在,但在“十七年”时期的革命历史题材电影中,剧中人物的位置安排带有很多刻意的成分,能够感受到强烈的爱憎壁垒,导演总是使主人公(正面人物)处于构图中的主要位置。而体现导演态度最明显的一场戏,是《林海雪原》中杨子荣献“进见礼”一场,威虎厅里,八大金刚和众山匪分立两旁,正中央是高高在上的座山雕的虎皮宝座,画面是典型的三角形构图,画面的核心显然在塔尖位置,座山雕从他的座椅上走下来,宣布对杨子荣的嘉奖令:“封你为威虎山的老九,咱们是国军,总得有个官衔,上校团副,祝胡参谋荣升,举杯”,作为一个正式的仪式应该相对严肃和庄重,但导演让座山雕在行走中说完台词,而且说完后并没有坐回他的椅子,这一看上去并不严谨的场面调度,其实是导演苦心经营的,目的就是为了突出主人公杨子荣的高大形象,他让杨子荣处在画面顶部,而主人座山雕却在他左下方,明显处于从属位置,杨子荣右手举碗,右腿更是夸张地踩在石阶上,摆出姿势潇洒的弓马步,作俯视众人状,这一撇开主人座山雕,烘托杨子荣形象的构图,尽管违背生活常理,但却达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规范要求。
角度的倾向性。因为要突出最能体现主流意识形态的正面人物和英雄人物,在角度方面,拍摄正面人物时采用仰摄镜头较多,这样的画面效果造型感较强,能够强化被摄体的力量和主导性倾向。《洪湖赤卫队》中赤卫队员出场时,伴随着歌声,分别是行进中的、绑担架的、擦标枪的赤卫队员的镜头,13个镜头中就有四个是仰拍的镜头。而在“韩英被捕”一场中,正当团长因为找不到赤卫队恼羞成怒,准备对群众大开杀戒时,韩英从芦苇荡中冲了出来,在接下来拍摄韩英的三个镜头时,导演全部采用了仰拍方式,突出韩英的高大形象。这种处理方式在拍摄正面人物时被普遍采用,特别是表现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对立时,倾向性就越加明显、直露。
组接的倾向性。在导演将片断化的空间重新编排、组合成一个完整空间时,会及时嵌入具有明显意识形态“提示”的镜头,来达到引导、教化目的。如喜儿被黄世仁强暴后,镜头切换成写有“大慈大悲”的匾额与“积善堂”的木牌,没有对话和旁白,一个镜头就作了无言的控诉,这被认为是带有“嘲讽意味的表意性镜语与陈述动作事实的叙事性镜语融合为一”。《农奴》中,当强巴醒来望见军医的帽徽时,即出现“五角星”的特写,这个特写镜头又被叠印在强巴为土登活佛收留后,他在白度母神像前冥想时的画面上,随之又叠印出解放军军官扶他上马的镜头,如此重复前面展现过的画面,用叠印镜头来揭示强巴当时若有所悟的思想状况,使得画面的倾向性更加明确。
景别的倾向性。特写镜头能够突出主要事物,将主体从周边环境中独立出来,可以清晰地看出人物的面部表情、目光,神态特点,很容易吸引观众的注意力。这一时期革命历史题材电影中近景和特写镜头的比例很高,《赵一曼》全片共704个镜头,其中近景177个,特写92个;《上甘岭》镜头总数和《赵一曼》差不多,近景202个,特写48个;《钢铁战士》全片620个镜头中,特写和近景镜头就用了90多个,比重相当大;影片《董存瑞》的导演有意识地使用较多的中近景与特写镜头,使影片形成一种明快简洁的节奏,体现了主人公火爆刚烈的性格,以及紧张激烈的战斗气氛。特写镜头较多,这表面上看起来和好莱坞电影影响有关,但好莱坞电影中大量使用特写近景镜头是缘于他们的“明星制”,而在“十七年”时期,并没有十分推崇个体明星的意识,这里面有一个原因,按照夏衍在《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中的要求,鉴于特定的民族欣赏习惯,重要的内容是要交代清楚,甚至具体要求重要的地方“一定要拍近景,并咬字清楚”。⑦特写镜头又被看作是心灵景观,易于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红色娘子军》“洪常青牺牲”一场的景别处理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导演用大量的特写镜头构成了这个长达3分30秒的段落,饱满、有力的特写镜头汇成了一股波涛汹涌的视觉冲击力,把影片的情绪推向了高潮,既表现了革命者不怕牺牲、英勇无畏的精神,又衬托出烈士的鲜血和遗物对吴琼花的灵魂冲击,更加坚定了她的革命信念。
形象选择的倾向性。身体和心灵、行为的直接相关性在中国通俗文化中,是一个明显的文化记号。男性英雄人物的形象通常是身材魁梧、高大,脸型方正,眉宇中透着英气,目光炯炯有神;而女性英雄人物形象则身材精干,脸型端庄,目光坚定,动作利落,步伐稳重有力,外形有意掩饰女性生理特征,向男性化靠拢。总的来说,好人的好不仅体现在他的内心,也体现在他的外表,坏人的坏不仅体现在他的行动和灵魂,而且体现在他的外形上,有意加以丑化,既然是纯粹恶的代表,对于恶是不需要理解的。人物从出场时就被归类和划分,分别贴上了两个阵营的标签,政治身份已经决定了身体的外形和姿势,对演员的选择也相对变得简单,但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深究,在这一时期革命历史题材电影中,身体更像是一个抽象的符号,变成创作者用来承载意义的隐喻,借已形成“符号”的身体而注入了意义与价值。
三 民族风格的探寻与修辞实践的局限
从“十七年”时期的作品看,艺术家图新的愿望并没有泯灭,这里面既有对民族风格的探寻,也尝试过突破主题和技巧的边界。
在修辞风格上自觉从民族文化中汲取营养,试图从中国传统艺术形式中找到电影艺术表现的灵感、原则、方法或者相似点,赋予电影的叙事、语言、节奏、氛围以民族气质,许多艺术家对电影民族化的探索是自觉的,郑君里早年翻译研究外国电影理论,就主张要苏联也要美国,要卢米埃尔、格里菲斯,也要爱森斯坦,在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发展中国自己的蒙太奇。在具体实践中,包括意境的营造、情感的放大、插曲的运用等,对意境的追求又是下功夫最深的地方,意境在电影中可以理解“为主客观结合、虚实结合的一种诗化的艺术形象及其触发的艺术联想”⑧,这是艺术家一直以来寻求的民族化道路的一个突破口。考察《青春之歌》、《柳堡的故事》等影片,就会发觉这些影片中的环境、造型、静与动、虚与实的关系显示出浓郁的时代和民族特色。在环境选择上,导演有意识地选择和创造具有民族特色的环境,《红旗谱》、《小兵张嘎》是辽阔的冀中平原;风车、水稻田是苏北水乡常见的景象(《柳堡的故事》);《农奴》是巍峨的布达拉宫。银幕上对社会景象的选择和提炼,作为烘托和解释主人公内心世界的艺术手段,是有着不容替代的艺术价值。在史东山导演的杰出影片《新儿女英雄传》中,白洋淀地区的自然景观成为影片中一个重要的叙事元素,导演深情地描绘了这片风貌独特的自然环境,使这部写实的影片注入了诗性的成分,这样做即契合中国文化中人与自然的亲近和谐,又表达了美丽家园决不允许入侵者践踏的潜在含义。
尽管当时的探索只是一个局部、一个方面,不足以说明电影艺术民族化的全部,但它毕竟与民族化有关,电影的民族化之路是一条艰难的道路,中国传统艺术是写意的,它和电影这个“舶来品”包含着的逼真和写实的原始风貌是有矛盾的,并不容易发生“化学反应”,但“十七年”时期电影艺术家的努力,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启示是,我们可以使中国的叙事作品增加抒情性,不局限于对生活形态的描摹,而是添加对生活的一种富有诗意的抒写,这也是这一时期电影修辞特点之一。
建国初期,在延安记录电影学派朴素影像的强烈冲击,以及苏联电影的造型和蒙太奇思维的双重合力下,也构成了一些新影像系统的创作,《新儿女英雄传》、《中华儿女》、《白毛女》、《我这一辈子》、《关连长》等影片都不同程度地吸收了纪录片的拍摄手法,《关连长》中大量运用自然光效也与旧“影戏”的室内布光风格不同。影片《农奴》粗犷浓郁、洗练简洁的影像产生了强大的视觉冲击力。在长镜头的实践中,由于技术上的限制,数量并不多,但也有运用出色的例子,例如那个被多次提及的。影片《小兵张嘎》中罗金保带着嘎子穿过院子、翻墙进入队部的长镜头,充分展现了崔嵬导演娴熟的场面调度能力和摄影师聂晶出色的运用摄影机的能力,表现了人民战争的伟力存在于人民群众之中的思想。影片《董存瑞》中,在董存瑞的参军努力失败后,导演用了一个出色的长镜头,镜头从姑娘们送队伍唱着歌走回家,到董存瑞和郅振标两人靠在墙头上讲王平的怪话,又恰好被王平走来听见,像一个优美充实的句子。还有在场景转换时采用的急甩手法,《逆风千里》中,镜头从一个敌军官急甩到另一个敌军官身上,把几个心怀鬼胎的人物一下子勾连在一起。再比如在构图上大胆地破除平衡,正常情况下,水平线歪斜,镜头摇摇晃晃是不允许的,但《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李侠被捕前,摄影师有意拍摄了四个地平线倾斜的画面,表现全副武装的敌人驾驶着吉普车迎面开来,水平线左右歪斜的画面交替出现,增强了紧张、杀气腾腾的气氛,更引起观众对李侠命运的关注。和常规中国电影相比,这些手法都是在视听修辞上的创新之处,但遗憾的是,仅仅是几个导演有创新的要求,形不成大的气候,或者他们也意识到了要和传统拉开距离,但在实际行动中,又因为这样那样的牵制,以及各种各样的顾虑,就进行得不那么彻底了,这一时期的艺术家基本上属于改良主义艺术家,他们的沉思更多的还是“体制内的沉思”。尽管有些艺术家也不屑于重复自己的创作,不停地提供新的想象力和新的艺术形象,但从完成的作品看,变化还是局部的,小范围的,这种突破和创新是有限度的,没有出现具有颠覆性的作品。
从整体上考察,这一时期的电影修辞手段并不丰富,可能的原因有这样几种:首先,创作者对电影修辞的认识还沿袭传统的思维,比较保守,在它和内容的关系上分出“主次”,修辞是为内容服务的,它扮演的是一种辅助的角色,因此,艺术家更多的是把精力放在内容编织和主题的提炼上,修辞就停留在“交代清楚”的层面上,评论家罗艺军有类似的看法,他说当时电影面临的主要课题是如何表现新内容,对艺术形式的问题来不及更多考虑。⑨这样,传统的表现手法就能够完成任务,不需要刻意求新,况且,按照大众审美习惯,一些新的表现手法反而会受到排斥,不如用习以为常的手法来得保险。其次,迫于当时的文艺观的压力,认为过分强调修辞的话,会被扣上“形式主义”的帽子。因此,对影像的自主性,也就是影像本身的表现力上探索不够。尽管同一时期在西方电影中,随着新现实主义、新浪潮、真实电影等流派的出现,作为表现手段的长镜头、景深镜头、跳接、色彩处理、高速摄影、越轴等手法已经在国外电影中大量应用,但因为技术条件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这些手法并没有得到重视,这一时期中国电影在形式上明显属于传统电影。再次,当时的艺术家在修辞和传统文化的结合上,还处于摸索阶段,尽管郑君里等导演因为多次借用戏曲的表现形式被一再称道,但实际的效果仍带有明显的舞台痕迹,效果并没有舞台上那么光彩夺目,戏曲舞台具有假定性、虚拟性的特点,观众也带着先在的认同进行观看,观众虽然也认同电影的假定性,并不会把电影当真,说到底它就是一束光投射到白银幕上产生的幻影,但观众又要求影像如生活本身一样真实,因为电影的照相本性使得电影比其他任何艺术更接近真实。因此,如何处理假定性和照相本性(具象)之间的矛盾是个大问题,这一时期的艺术家还没完全处理好“虚”与“实”的问题,这也不是短时间内可以解决的问题。
另外,这一时期的影像体系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倾向性,形成了某些成规化的处理方式,比如为了有意突出“正面人物”而采取的一系列修辞手法,这也为“文革”电影的极端视听风格埋下了伏笔,为“三突出”口号的提出提供了影像表达的雏形,因为排斥了其他的可能性,使艺术之路变得狭窄,这是这一时期电影修辞手段留下的“不良资产”。
注释:
①⑦夏衍:《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页,第53页。
②《“中国电影回顾”随感》一文收入林缦、李子云编选的《夏衍谈电影》,中国电影出版社,1993年版,第60页。
③张客:《余音绕梁——试论影片〈青春之歌〉导演艺术创作上的特色》,载《崔嵬的艺术世界》,中国电影出版社,1982年版,第236页。
④舒晓鸣:《从〈南征北战〉、〈西安事变〉到〈大决战〉》,载《再现革命历史的艺术》,中国电影出版社,1993年版,第157页。
⑤《〈桥〉摄制组接受经验教训,决定修改剧本继续拍摄》,载《东影通讯》第21期。
⑥许南明主编:《电影艺术词典》,中国电影出版社,1986年版,第62页。
⑧罗艺军:《电影的民族风格初探》,《电影艺术》,1981年第11期。
⑨罗艺军:《风雨银幕》,中国电影出版社,1983年版,第2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