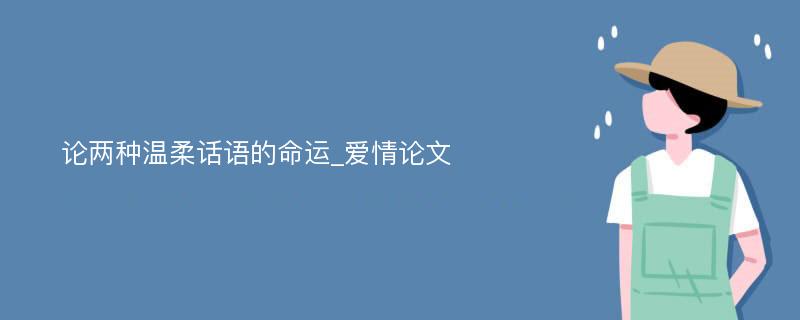
论柔情词的两种命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种论文,柔情论文,命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柔情词从它成熟以后,就一直面临着两种命运:一方面为人所爱,文章从古代的婚姻制度、文学分工及词的功能的演变等几方面揭示了其中的原因。另一方面又为人所轻,文章在揭示了柔情词为人不尊的原因之后,着重论述了宋人和清人对柔情词的推尊。
文学表现情感莫善于用词;而在言情的各类词中,其数量之丰,名作之多,以柔情词为最。词以柔情为主题的创作情况,在我国各体文学的发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但这是否能够说明,柔情词在人们心中有较高的地位呢?恰恰相反,柔情词从它成熟直至最后衰亡,一直被看作末道小技而为人所轻,这一现象也是各体文学发展史上罕见的。本文试图对这一现象作一宏观审视,以求教于方家。
一
词一方面为人所爱,另一方面又为人所轻,这一现象不是存在于历史进程的某一阶段,而是贯穿于词成熟以后的全过程,从晚唐五代到清末都是如此。
晚唐五代时期,花间词的产生标志着词的成熟。花间词的内容,以咏女子生活和男女相思为主。温庭筠因为艳词写得精妙,故被花间词人尊为鼻祖。但温庭筠在世期间,因为能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为京师人士所不齿。《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下本传云:“初至京师,人士翕然推重。然士行尘杂,不修边幅,能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公卿家无赖子弟裴诚、令狐滈之徒,相与蒱饮,酣醉终日,由是累年不第”。温氏荣枯,可谓皆因侧艳之词而致。
宋初,承花间而来的柔情词的创作方兴未艾。晏欧、张、柳的柔情词誉满当时。尤其是柳永的相思离别之体,声传一时,天下咏之。但正因为柳永一生从事这种壮夫不为的侧艳之词,落得功名不扬的结局。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有云:“仁宗留意儒雅,务本理道,深斥浮艳虚美之文。初,进士柳三变,好为淫冶讴歌之曲,传播四方。尝有《鹤冲天》词云:‘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及临轩放榜,特落之,曰:‘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当柳永再次参加进士考试时,因《鹤冲天》一词的缘故,又一次落榜。这件事,体现了宋仁宗对柔情词的卑视。
卑视柔情词的人是否就不爱柔情词呢?不一定。就拿那位“留意儒雅,务本理道”的宋仁宗来说,他是一个深于儿女之情的人。他曾因宋祁的一首柔情词写得好,给了宋祁一个意外的收获。宋祁的那首柔情词为《鹧鸪天》,词曰:
画毂雕鞍狭路逢,一声断断绣帘中。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金作屋,玉为笼,车如流水马如龙。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 这首词写的是词人的一次艳遇,所遇者是一位宫廷内人。这首词后来传唱到宫中,宋仁宗听到后,不仅没有给宋祁降罪,却把这位宫廷内人赠与他。对宋祁来说,真可谓词通蓬山。若究其原因,不就是宋仁宗爱宋祁的这首柔情词才如此开恩的吗?
柔情词被爱又被轻,不仅从宋仁宗那里体现出来,整个宋代就是如此。胡寅在《题酒边词》中论及宋人对词的两重态度时说,词“方之曲艺,犹不逮焉;其去《曲礼》则益远矣。然文章豪放之士,鲜不寄意于此者。”在观念上对词卑视,但在创作上又深为爱之,这种矛盾现象在柔情词中体现得最突出。
元代,词进入衰世。在这种总趋势下,也还是有些文人热心词的创作,并且产生了象张翥这样少数的优秀词人。过去的词话评论元词时,几乎都提张翥。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云:“元词之不亡者,赖有仲举耳。”先著《词洁》云:“元词以张仲举为工。”但张翥对词并不看重,他看重的是文章。象张翥这样有成就的词人对词尚不看重,其它人对词的轻视就勿庸赘言了。
明代,词由衰而亡。卓人月对此揭示道:“我大明诗不如唐,词不如宋,曲不如元。”(见《寒夜录引言》)尽管如此,明人在词的创作数量上却多于金元。金元词共七千多首,明词总计有一万首。这说明明代词人队伍虽不及小说和戏曲,但染指于词者也还是不乏其人。明人在柔情词的创作中,敞开了感情的世界,故纵情欲,淫哇之词盛行于世。这类词受到人们的卑视是应该的。刘熙载《艺概·词曲概》云:“流俗误以欲为情,欲长情消,患在世道。倚声一事,其小焉者也。”刘永济《词论》卷下亦云:“若徒作侧艳之体,淫哇之音,则谓之小也亦宜。”
清代,词学复兴。浙、常二派为推尊词体做了不懈的努力,但他们中很多人是在词为小道末技的观念下推尊词体的。朱彝尊、张惠言都是持这种观点的尊体论者。朱彝尊在《陈纬云红盐词序》中说,“词虽小技”,但可将不遇之感寄托于此。张琦在《重刻词选序》中谈到《词选》的编辑目的时说,“先兄(指张惠言)以为词虽小道”,但为了便于金生学词,于是和我编辑了《词选》一书。朱、张二人视词为小道,主要着眼于柔情词是词之主体这一事实。
从以上的回顾中可知,在柔情词的发展史上,不论在盛时还是在衰时,不论是柔情词的卑视者还是推尊者,都存在着在创作行为和意识观念上的巨大反差。这一唯词才有的文学现象确实发人深思:柔情词为什么会有这两种命运呢?
二
人类是最富于感情的,而在感情的世界里,最普遍、最天然的感情就是爱情。这是一种异性之间的相悦之情。这种感情说它普遍,是因为它不分区域,不分时代,不分贵贱。只要一个人到了一定的年龄,总会产生一种对异性的爱的追求。这种感情说它天然,是说它不是经过后天教育才会产生,它是人的生理和心理的一种本能。它就象大自然中的刮风下雨一样,永不休歇。但是,人类对爱情的这种需要,在古代社会长期得不到满足。这是什么原因呢?让我们重温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及国家的起源》中对古代婚姻制度的阐述。他在谈到古代的婚姻特征时说:“在整个古代,婚姻的缔结都是由父母包办,当事人则安心顺从。”(以下引文未注明出处者,皆引自恩格斯此文)还说:“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不是个人的意愿。”在这种情况下结成的夫妇,他们之间有没有爱情呢?恩格斯说:“古代所仅有的那一点夫妇之爱,并不是主观的爱好,而是客观的义务;不是婚姻的基础,而是婚姻的附加物。”这就深刻说明了古代夫妇之爱不是真诚相爱,只是因为结为婚姻而尽义务,所以这种夫妇之爱只是婚姻的附加物,这就是古代夫妇之爱的实质。在古代社会,有没有胜于上述那种“夫妇之爱”的男女之爱呢?也就是如恩格斯所说的以“体态的美丽,亲密的交往,融洽的旨趣”等为条件而产生的男女之爱呢?恩格斯认为,这种真正的爱情在官方社会是不存在的,因为古代的婚姻制度扼杀了真正爱情的产生。那么,这种真正的爱情在哪里呢?古代的女子被剥夺了参与社会活动的权利,只能被限制在家庭这个狭小的圈子里,对自己的丈夫不管爱还是不爱,只能听从命运的安排;而男子有权利和机会接触那些官方社会以外的女子,如沦入乐籍的歌妓舞女。他们在交往的过程中,那些落魄文人、失意官吏和风尘女子之间,其身份和地位尽管不同,但命运则往往相近。这正如罗隐赠与老妓云英的一首诗中所说:“我未成名卿未嫁,可怜惧是不如人”。艺妓的色艺之美,文人的才情气韵,都会构成男女相悦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之间极易滋生发自内心的对对方的爱。所以,恩格斯说:“现代意义上的爱情关系,在古代只是在官方社会以外才有。”恩格斯肯定官方社会以外的爱情的正当要求,其前提是官方社会没有真正的爱情。我国封建社会的情况,与恩格斯所说的古代欧洲社会的婚恋状况同然。我国古代的柔情词,绝大多数写的是官方社会以外的爱情,写官方社会认可的夫妇真诚相爱的那种柔情词并不多见。这一情况说明,在我国封建社会人们对真正爱情的渴望。但若用封建的伦理道德来衡量,这种婚外的恋情是一种不正当的爱情;若从爱情的本质观察这一现象,则是古人对爱情的一种正当要求。这种爱情对邪?错邪?通过上面的辨析可明也。
那么,这种男女柔情为什么不放到诗文中去表现呢?这是因为诗文是文学中神圣的殿堂,它不允许男女柔情闯进去。查礼《铜鼓书堂词话》中云:男女柔情“文不能达,诗不能道”。这是因为在封建社会,诗用来言志,文用来载道,言志载道是我国诗文在内容上一个很悠久的传统。在这一观念的支配下,诗文创作被看作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见曹丕《典论·论文》柔情哪有资格跻身诗文之中呢?
既然诗文对柔情加以排斥,那么柔情到哪里去表现呢?在词产生以前,只能在里巷歌谣中去反映;词出现以后,柔情找到了它最适合的表现形式。早在词的萌芽时期(即民间词的阶段),柔情的内容就已经很突出了。由民间词转入文人之手以后,柔情内容高度集中,迅速成了词表现的主题。这种情况,后人不管是批评,是肯定,是保留,柔情作为词的主题一直伴随了词的整个兴衰过程。
下面我们从柔情词的功能入手,对词的柔情主题加以考察。唐五代北宋时,词的用途是应歌。当时词所配的音乐是燕乐,燕乐是一种宴饮娱乐之乐,它主要用于公私宴饮的娱乐场合。当时词的演唱者多为女子,男性歌手是少数,这就是“独重女音”的演唱风俗。在燕乐曲情和女性歌手的双重制约下,加强了词的娱乐性功能。而在娱乐的内容中,男女柔情和世俗最接近。南宋时,随着音乐中心的转移和词人队伍北大后随之而来的词人音乐素质的下降,词与燕乐的关系渐渐疏远,词的用途,由北宋以前的侧重应歌逐渐转向侧重应社。文人社集是一种带有娱乐性的文学活动,这类活动中的诗词唱和的内容虽然比单纯应哥宽了一些,但儿女柔情的抒发依然是重心。一些应社的咏物词虽不属赋情之作,但在咏物时往往插入闺房之意,这是词以柔情为主题在咏物词中的折光。经过元明至清,词的用途由应歌、应社转而强调应时。但这时词的应时和诗不同,它是借柔情以寄托。文人用世的各种感慨通过闺房儿女之言传达出来,这又是词以柔情的主题在言志抒怀时的体现。通过上面的论述可知,在创作中词始终显示出它永不衰竭的活力,确实有着历史的和文学自身的原因。
三
柔情词为社会所轻,首先在于我国封建社会在文学职能认识上的传统观念。我国古代的诗论、文论中,十分重视文学的社会职能,十分重视诗文的教化传道的作用,而诗文为此而创作,故诗文就成了我国古代文学中的尊体。男女柔情和社会政治生活比较间接,没有诗教、文道的传统,这是柔情词为人所轻的一个主要因素。文学的职能是多方面的,诗可以侧重言志,文可以侧重传道,词为什么就不可以侧重言情呢?若承认文学分工的相对合理性,词以柔情为主题是无可厚非的。
柔情词为社会所轻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柔情词冲击了封建理学。宋明理学主张“存天理,灭人欲”,认为抒情诗都是些玩物丧志的东西,所以理学家程颐干脆就不写诗。他说:“某素不作诗,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欲为此闲言语”。(见《二程遗书》卷十八)这就是理学家对诗歌言情的态度。邵雍则认为,诗歌中的情可溺死人。他说:“近世诗人,…殊不以天下大义为言者,故其诗大率溺于情好也。噫,情之溺人也甚于水”。词比诗歌的情感性更强,尤其是柔情词,它深刻展示了人类在爱情上的真诚愿望,这自然就更使得理学家们不可睁目而视了。在理学盛行的封建社会,柔情词受卑视是很自然的。那么,封建统治者为什么不禁止柔情词的创作呢?这是因为若要禁止,这不仅限制了普通人对爱情的心理追求,同时对他们自己在爱情上的心理需要也是一种限制,所以他们对柔情词就自然采取宽容的态度了。
柔情词为社会所轻,也有它自身的原因。有的柔情词,多用华艳的词藻描摹女子的体态风姿,把词中的女子看作欣赏的对象,男女之间的爱恋之情不够真挚深沉,感受不到词人肺腑的倾诉,刻骨铭心的东西少,带有较多宫体诗的趣味。虽然说不上是淫词,但也谈不上是雅词。自然,柔情词中的淫冶之作也有,但这类词泛滥成灾的时候毕竟不多,多数是属于上面所说的情况。再者,很多柔情词把个人的感情生活单纯化。词中所写的柔情和外面的世界及自己的功业了无相干。这种情况,有的是在文学分工论的观念的支配下所作的选择,而有的则是因为词人远离社会,局限书斋生活的缘故。但无论原因如何,和大千世界没有任何联系的柔情,毕竟不能说其品格是高尚的。
历史上词人们对柔情词不尊的原因,未必从理性上都能看透,但有远见卓识者还是不乏其人。正是由这些人倡导,谱写了无数推尊柔情词的好篇章。
推尊柔情词,宋人开其端,清人畅其绪。宋人推尊柔情词的主要途径是除俗倡雅,实现柔情词的雅化。在创作上经历了北宋的倡雅和南宋的复雅两个阶段。倡雅者以秦、贺、周、李为代表,复雅者以姜、吴为代表。而对两宋柔情雅词的创作进行理论总结的,是沈义文的《乐府指迷》和张炎的《词源》。两书虽然在雅词的审美追求上不同,但除欲倡雅的主张却是共同的。概括地说,《乐府指迷》主柔婉深隐之雅,以周清真的雅词为冠;《词源》主清空醇正之雅,以姜夔为宗。那么,柔情雅词有什么共同的要求呢?沈义文在《乐府指迷》中说:“为情赋曲者,尤宜宛转回互。”“宛转”讲的是言情要委婉含蓄;“回互”讲的是用笔要曲折隐讳。对此主张,张炎在《词源》中有一段话比沈氏讲得更具体。他说:“簸弄风月,陶写性情,词婉于诗;盖声出莺吭燕舌间,稍近乎情可也。若邻乎郑卫,与缠令何异也。”郑卫之音是民间俗乐,多淫哇之声,孔子主张对这类音乐必须禁绝,否则它会乱雅乐。缠令是北宋时期市井中流行的俗乐,多鄙陋之语,张炎认为柔情词必须和缠令划清界限才能称雅。除俗才能得雅,但如何才能脱俗呢?张炎《词源》说:儿女离情“全在情景交炼,得言外意”。这是讲写柔情必须借景物以映托,方能防止浅俗。而沈义文在《乐府指迷》中则提出了在用语上的要求:“下字欲其雅”,“用字不可太露”。雅语要求用语要文而不野,隐而不露,这就必须力避词中出现陋语、秽语、土语、谐语,即未经提炼的俚俗的市井之语。《乐府指迷》和《词源》对柔情词创作的理论总结,推进了柔情雅词的创作,进一步把为世所轻的侧艳小词推上雅途。
宋人以后对柔情词的推尊,用力最大的是清人。他们推尊的途径,除了净化柔情词的言和意之外,就是借柔情以寄托。前者是对宋人倡雅的继承,后者是对宋人引志入词的发展。对于引志入词,张炎在《词源》中有云:“词欲雅而正,志之所之,一为情所役,则失其雅正之音。”《诗序》有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张炎在这里接过《诗序》的说法加以推衍发挥,认为词的雅正也是由志所生出,词若一味言情而无暇顾及志,就会有失雅正。这实际上是用“诗言志”的传统去要求词,是将诗教移植于词的一种信息。至于在柔情词中如何将志引进来,张炎并未在理论上提出来。到清代,才提出用比兴寄托的方法引志入词。清初,浙西词派为挽救明词淫哇颓风,以白石词为榜样,论词专主醇雅,终于将词推上雅途,出现南宋雅词在清初的复兴。朱彝尊在《红盐词序》中说:“盖善言词者,假闺房儿女之言,通之于《离骚》变雅之意,此尤不得志于时者所宜寄情焉耳。”这里的《离骚》变雅之意,就是指不遇文人的忧急之情。后来的常州词派,从重意格出发,比浙西词派更加强调寄托。张惠言在《词选序》中主张,词应该借“里巷男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周济论词主寄托不遗余力,他在《宋四家词选》中评淮海词云:“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又是一法。”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卷一中,主张词要能够通过“写怨夫思妇之怀,寓孽子孤臣之感。”借柔情寄托,柔情本身会不会受到侵害呢?前面谈到,柔情是为封建正统观念所轻的,而志则历来为正统观念所重。把志通过寄托引进柔情词,柔情就会因志的尊崇地位而提高自己的价值。柔情词为言志提供了阵地,同时它也就因被用为言志而带上了一个体面的花环。人类的感情世界是丰富多样的,各类感情之间既相异又相通。男女柔情,通过联想,可以很自然地通向其它各类感情。而实现这种通感,柔情本身并不需要“输出”,因而也就不会被削弱。柔情为什么具有这种功能呢?叶嘉莹先生有一段话说得很在理,他在《常州词派比兴寄托的新检讨》一文中说:“人世间所谓爱,当然有多种之不同。然而无论其为君臣、父子、夫妇、朋友之间的伦理的爱,或者是对学说、理想、宗教、信仰等的精神的爱,其对象与关系虽有种种之不同,可是当我们欲将之表现于诗歌,而想在其中寻求一个最热情、最深挚、最具体、而且最容易使人接受和感动的爱的意象,则当然莫过于男女之间的情爱。所以歌筵酒席间的男女欢爱之辞,一变而为君国盛衰的忠爱之感,便也是一件极自然的事,因为其感情所倾注之对象虽有不同,然而当其表现于诗歌时,在意象上二者可以有相同之共感。所以越是香艳的体式,乃越有被用为托喻的可能。”寄托莫善于用柔情,柔情靠寄托被推尊,这就是寓意和柔情的关系。它们之间相溶而不相违,各自都没有排它性。如果说宋人将柔情词雅化的着眼点是提高其情感素质,那么清人借柔情以寄托的着眼点是增加其情感内涵。途径有别,但都提高了柔情词的品格。
柔情词的推尊者为改变其词不尊的命运作了不懈的努力,自然功不可没,但是因为柔情词不尊的最主要的原因并不在其本身,所以柔情词的品格无论怎样提高,最终也没有改变末道小枝的卑微地位而成为文学中的尊体,这就是柔情词的历史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