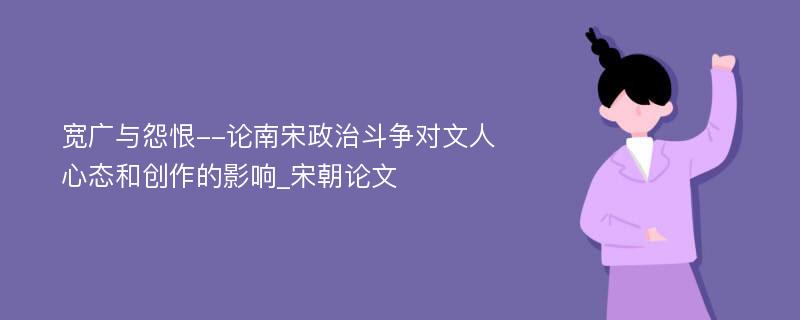
旷达与怨怒——论南北宋政治斗争对文人心态及创作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旷达论文,怨怒论文,文人论文,心态论文,宋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就整个宋代看,一方面“重文轻武”的政治模式给文人们提供了更多的参政入仕的机会,而积贫积弱的现状,外族的威胁侵凌,更使这些以“兼济”为心的文人士大夫无法坐视,他们纷纷上书论政,表现出关心时政、追求理想的空前热情。但从另一方面看,宋王朝的政治机制以专制保守、因循苟且为特点,它已丧失了发愤图强、雪耻复仇的自信和勇气,北宋时两次政治改革均以失败而告终,南宋则主和路线始终占据上风。文人士大夫的奋斗追求最终碰壁,又使他们饱尝了仕途坎坷和世道的艰难。面对打击磨难,北宋文人取旷达之心,自我排遣,主动解脱痛苦,表现出一种超然物外的理性精神和洒脱豁达的心胸;而南宋文人则绝无半点退让之心,他们以其特有的坚定执着,表现为一种入而不返,愤激热烈的精神。北宋文人与南宋文人的不同心态与特定的历史状况、特定的政治斗争密切相关,而它们又必然影响到文人们的创作,使两宋文学呈现出旷达与怨怒的不同风貌。那么,两宋的政治斗争是怎样对文人的心态及创作发生影响的呢?这正是本文试图讨论解决的问题。
一
宋代以靖康之难为界,前期虽国力不振,但尚能维持江山的一统,政治家们也有幸获得施展抱负的机会。尽管“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的结局都是失败,但它们本身毕竟激发了广大士人的忧患意识,他们别宗立派,各抒己见,表现出积极干预政治的高度热情。但是,随着变法的失败,改革的实质日渐蜕变,党争纷起,意气用事,政治上的打击迫害接踵而至,新旧党之间相互倾轧,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蔡京)内结中宦,外连朝士,一不附己,则诬以党元祐,非先帝法,必挤之而后已,今在朝之臣,京党过半。”(《宋史·常安民传》)面对风波叠起,前途莫测的险恶前路,一方面,文人们坚守住自己的信念主张,绝不屈从苟合,俯仰随人,表现出“屈于身而不屈于道,虽百谪而何亏”(王禹偁《三黜赋》)的刚直之性。如范仲淹“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宋史·范仲淹传》);尹洙“会范仲淹贬,敕榜朝堂,戒百官为朋党。洙上奏曰:‘仲淹忠亮有素,臣与之义兼师友,则是仲淹党也。今仲淹以朋党被罪,臣不可苟免。’宰相怒,落校勘”(《宋史·尹洙传》);欧阳修“论事切直,人视之如仇”,当时“范仲淹以言事贬,在廷多论救,司谏高若讷独以为当黜。修贻书责之,谓其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若讷上其书,坐贬夷陵令”。(《宋史·欧阳修传》);王安石“性强忮,遇事无可否,自信所见,执意不回。至议变法,而在廷交执不可,安石傅经义,出己意,辩论辄数百言,众不能诎。甚者谓‘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宋史·王安石传》)。他认为“孔孟之所以为孔孟者,为其善自守不惑于众人也。如惑于众人,亦众人耳,乌在其为孔孟也”(《答段缝书》),在《众人》诗中,他更写道:“众人纷纷何足竞,是非吾喜非吾病。颂声交作莽岂贤,四国流言旦犹圣。……乃知轻重不在彼,要之美恶由吾身,”表现了坚定的意志和高度的自信。苏轼身历新旧党争,“其于人见善称之如恐不及,见不善斥之如恐不尽”(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绝不肯随波逐流。新党掌权时,他敢于提出异议,“时安石创行新法,轼上书论其不便,安石滋怒”;旧党执政时,他又敢于说出自己的不同意见,以致“积以论事,为当轴者所恨”(《宋史·苏轼传》)。在《与杨元素》中,他曾诗人自道:“昔之君子,惟荆是师;今之君子,惟温是随。所随不同,其为随一也。老弟与温相知至深,始终无间,然多不随耳。致此烦言,盖始于此。然进退得丧,齐之久矣,皆不足道。”另一方面,北宋的文人士大夫在仕宦失意时,又大多能以佛老的虚静明达和因任自然的态度排遣痛苦,解脱矛盾,以淡泊之心面对悲凉的境遇。正如洪迈《容斋随笔》(卷十四)所说:“士之处世,视富贵利禄当如优伶之为参军,方其据几正坐,噫呜诃箠,群优拱而听命,戏罢则亦已矣。见纷华盛丽当如老人之抚节物,以上元、清明言之,方少年壮盛,昼夜出游,若恐不暇,灯收花暮,辄怅然移日不能忘;老人则不然,未尝置欣戚于胸中也。睹金珠珍玩当如小儿之弄戏剧,方杂然前陈,疑若可悦,即委之以去,了无恋想。遭横逆机阱当如醉人之受骂辱,耳无所闻,目无所见,酒醒之后,所以为我者自若也,何所加损哉?”这种超脱、冷静、恬淡正是北宋文人独特的个性所在。一般说来,北宋文人都很重视操守品节,他们的进退出处总是以保持人格的尊严为大前提,这就决定了他们对用舍行藏本身并不执着:“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苏轼《泌园春·孤馆灯青》),“仕路崎岖,群言摧沮,虽死生不变乎己,况用舍岂累其怀”(苏轼《登州谢宣诏赴阕表》)。这种洒脱的态度来源于北宋文人对人生悲欢、生死祸福的透彻了悟,以及静、达、和、安的处世准则。“(富)弼恭俭孝敬,好善疾恶,常言‘君子与小人并处,其势必不胜。君子不胜,则奉身而退,乐道无闷’”(《宋史纪事本末》卷三十七)“尹师鲁自直龙图阁谪官,过梁下,与一佛者谈。师鲁自言以静退为乐,其人曰:‘此犹有所系,不若进退两忘。’师鲁若有所得,自为文以记其说”(《梦溪笔谈》卷十八)。苏轼认为“君子学以辨道,道以求性。正则静,静则定,定则虚,虚则明。物之来也,吾无所增;物之去也,吾无所亏。岂复为之欣喜爱恶而累其真欤?”“所谓静以存性,不可不念也。能得吾性,不失其在己,则何往而不适哉?”(《江子静字序》)“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超然台记》)。正是这种哲人般的了悟与高度的理性精神,使他们不必象陶渊明那样着意地寻求世外桃源:“桃花流水在人世,武陵岂必皆神仙”(苏轼《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他们认为“世间即出世间,等无有二”(苏轼《南华长老题名记》);“朝市山林俱有景,不居京洛不江湖”(黄庭坚《追和东坡题李亮功归来图》)。这种人生态度既是对前世隐居避世以求洁身自好的一个发展,也是北宋文人超尘脱俗品格的外现。北宋文人的独特之处正是将坚定的信念、独立的人格与旷达的襟怀结合起来。他们从容地面对人生路途上的种种打击与挫折:“横祸所加,随处安受,不悔不折”(包恢(《跋山谷书范孟博传》);“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苏轼《定风波·莫听穿林》),“此心安处是吾乡”(苏轼《定风波·常羡人间》),从而形成了北宋文人特有的外圆内方、外和内刚的心态,正如欧阳修所说:“是以君子轻去就,随卷舒,富贵不可诱,故其气浩然,勇过于贲育,毁誉不以屑,其量恬然,不见于喜愠。能及是者,达人之节而大方之家乎?”(《送方杀则序》)
苏轼曰:“人瘦尚可肥,俗士不可医。”(《于潜僧绿筠轩》)黄庭坚曰:“余尝为诸子弟言,士生于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书稽叔夜诗与侄榎》)脱俗,是宋代文人追求的理想境界,而北宋文人的超尘脱俗又表现为彼此相连的两极,一是参与政治时,临大节而大辱,毫不畏惧地捍卫自己的理想,坚持自己的主张,从而彻底否认了媚俗阿谀的趋附心态;二是受打击遭迫害时,处危变而不惊,以旷达平和之心泰然处之,绝无悲戚哀怨之态,表现出一种磊落高洁的情怀。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就可以理解,北宋文人既有《朋党论》(欧阳修)、《与高司谏书》(欧阳修)、《答司马谏议书》(王安石)、《山村五绝》(苏轼)等言辞激烈,态度鲜明的作品,又有超越于悲愤之上的宁静平和之作:“行见江山且吟咏,不因迁谪岂能来”(欧阳修《黄溪夜泊》)、“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苏轼《初到黄州》)、“日啖荔枝三百颗,不妨长作岭南人”(苏轼《食荔枝》)、“鬼门关外莫言远,四海一家皆弟兄”(黄庭坚《竹枝词》)。
苏轼在《自评文》中说:“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可以说,这种“随物赋形”的水的精神品格也就是北宋文人的理想人格,它既包含了顽强的毅力和坚定的意志,也包含了明达理智,旷放超脱的襟怀。这种坚贞自守、进退自如的精神与心态对北宋文学发生了深刻而直接的影响,它造就了北宋文学的典型风貌,即从容自然,淡朴高雅。欧阳修提出“除去文饰,归彼淳朴”(《斫雕为朴赋》),其文从容闲雅,“纡徐委蹦,往复澳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苏洵《上欧阳内翰节一书》);苏轼“经幽初有适,挥洒不应难”(苏轼《宋复古画潇湘晚景图三首》),他的滓品“大缕缺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苏轼《答谢民师书》);黄庭坚诗文“超轶绝尘,独立万物之表”(见《宋史·黄庭坚传》引苏轼评论),同时又推崇“句法简易而大巧出焉,平淡而山高水深”,“文章成就更无斧凿痕,乃为佳作耳”(黄庭坚《寄王观复书》)。可以说,北宋文学从一开始起,便烙上了文人们坚毅而又洒脱、执着而又超脱的个性。
二
宋室南迁,山河破碎,故国中分。面对严峻的现实,爱国志士大声疾呼,抗敌复国成为时代的声音。在这一关系到祖国的统一与分裂、民族的尊严与耻辱的大是大非面前,南宋士大夫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隆兴再讲和,失定受书之礼,上尝悔之,迁(范)成大起居郎假资政殿大学士,充金祈请国信使,国书专求陵寝,盖泛使也。上面谕受书事,成大乞并载书中,不从。……至燕山,密草奏,具言受书式,怀之入。初进国书,词气慷慨,金君臣方倾听,成大忽奏曰:‘两朝既为叔侄,而受事礼未称:臣有疏!’搢笏出之,金主大骇曰:‘此岂献书处耶?’左右以笏标起之,成大屹不动,必欲书达。既而归馆所,金主遣伴使宣旨取奏。成大之未起也,金庭纷然,太子欲杀成大,越王止之,竟得全节而归。”(《宋史·范成大传》)陆游之时,正逢“朝廷之上,无不以画疆守盟、息事宁人为上策,而放翁独以复仇雪耻,长篇短咏,寓其悲愤”(赵翼《瓯北诗话》卷六)。辛弃疾在山东沦陷区曾多次“登高望远,指画山河,思投衅而起,以纾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愤”(辛弃疾《美芹十论·序》)。后逢“金主亮死,中原豪杰并起,耿京聚兵山东,……辛弃疾为掌书记,即劝京决策南向”。“绍兴三十二年,京令弃疾奉表归宋,高宗劳师建康,召见,嘉纳之,授承务郎、天平节度掌书记,并以节使印告召京。会张安国、邵进已杀京降金,弃疾还至海州,……乃约统制王世隆及忠义人马全福等径趋金营。安国方与金将酣饮,即众中缚之以归,金将追之不及。献俘行在,斩安国于市”(《宋史·辛弃疾传》)。陈亮当“隆兴初,与金人约和,天下欣然幸得苏息,独亮持不可”,“高宗崩,金遣使来吊,简慢。……亮感孝宗之知,至金陵视形势,复上疏,……大略欲激孝宗恢复”(《宋史·陈亮传》)。
正是这一份深沉的爱国之情与忠义之心使他们执着于恢复故土,一统江山的神圣事业:“整顿乾坤,廓清宇宙,男儿此志会须伸”(张元干《陇头泉·少年时》);“平生铁石心,忘家思报国”(陆游《太息》)、“丈夫不虚生世间,本意灭虏救河山”(陆游《楼上醉书》);“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辛弃疾《水调歌头·千里渥洼种》)、“袖里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补天西北”(辛弃疾《满江红·鹏翼垂空》)……。他们认为“恢复之事,为祖宗、为社稷、为生民而已,此亦明主所与天下智勇之士所共也,顾岂吾君吾相之私哉?”(辛弃疾《九议·其一》)为了这个事业,他们甘愿驰骋沙场、奉献生命:“我欲乘风去,击楫誓中流”(张孝祥《水调歌头·雪洗虏尘静》)、“事有可为,杀身不顾”(辛弃疾《淳熙己亥论盗贼札子》)“平生万里心,执戈王前驱。战死士所有,耻复守妻孥”(陆游《夜读兵书》)、“马革裹尸当自誓,蛾眉伐性休重说”(辛弃疾《满江红·汉水东流》)……。
从南宋社会的状况看,一方面是爱国志士“忠愤所激,不能自巳”(辛弃疾《美芹十论》),他们一腔热血,壮怀激烈,念念不忘“南共北,正分裂”(辛弃疾《贺新郎·细把君诗说》),“其欲扫开河洛之氛祲,荡洙泗之膻腥者,未尚一日而忘胸中”(谢尧仁《于湖词序》)。正是基于这一点,他们把建功扬名与收复故土结合起来:“千古风流今在此,万里功名莫放休。君王三百州”(辛弃疾《破阵子·掷地刘郎玉斗》)、“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辛弃疾《破阵子·醉里挑灯》),因此,从维护民族的尊严和祖国的完整统一出发,他们不可能取北宋文人那种进退自如,行藏用舍不挂于怀的洒脱态度,而是入而不返,执意不回,一往情深,甚至至死不休:“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陆游《示儿》)。但另一方面,爱国志士的理想壮志又与现实构成了尖锐的矛盾。南宋一代,基本上坚守主和之策,虽然孝宗即位之初,亦曾锐意恢复,然而自符离一败,宋金议和,偏安遂成定局,中原恢复之事也就遥遥无期。在这种形势下,主战派屡屡受到打击排挤,他们以一腔报国热情却落得“心在天山,身老沧洲”(陆游《诉衷情·当年万里》)的境地,心中自然会积淀起强烈的愤恨之情,从而化作对投降派、对误国小人的严厉批判:“诸公尚守和亲策,志士虚捐少壮年”(陆游《感愤》);“公卿有党排宗泽,帷幄无人用岳飞”(陆游《夜读范至能揽辔录,……》);“渡江天马南来,几人真是经纶手?长安父老,新亭风景,可怜依旧。夷甫诸人,神州沉陆,几曾回首”(辛弃疾《水龙吟·渡江天马》)、“事无两样人心别。问渠侬:神州毕竟,几番离合?汗血盐车无人顾,千里空收骏骨”(辛弃疾《贺新郎·老大那堪说》)……。
英雄无路请缨,壮士报国无门,骐骥终伏枥下,这就是南宋那个特定的时代造成的爱国志士的悲剧,正所谓“旧恨春江流不断,新恨云山千叠”(辛弃疾《念奴娇·野棠花落》),“叹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辛弃疾《贺新郎·肘后俄生柳》)。这一悲剧决定了此期文人悲愤抑郁的心态:“念腰间箭,匣中剑,空埃蠹,竟何成!时易失,心徒壮,岁将零,渺神京。干羽方怀远,静烽燧,且休兵。冠盖使,纷驰鹜,若为情?闻道中原遗老,常南望,翠葆霓旌。使行人到此,忠愤气填膺,有泪如倾”(张孝祥《六州歌头·长淮望断》);“生逢和亲最可伤,岁辇金絮输胡羌。夜视太白收光芒,报国欲死无战场”(陆游《陇头水》);“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辛弃疾《水龙吟·楚天千里》)。然而,可贵的是,他们并没有被打击挫折压垮,而是始终保持着不屈的精神。他们的品格节操就表现在愈是受到排挤迫害,愈是饱尝痛苦磨难,他们对理想的追求就愈是坚定。在逆境中,他们没有沉沦,而是顽强的求奋进;在痛苦中,他们不求超脱,而是坚定的抗争。陆游是“蓬窗老抱横行略,未敢随人说弭兵”(《书愤》),“平生铁石心,忘家思报国”(《太息》),“逆胡未灭心未平,孤剑床头铿有声”(《三月十七日夜醉书》);辛弃疾则“休说鲈鱼堪鱠,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水龙吟·楚天千里》),“我最怜君中宵舞,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贺新郎·老大那堪说》)。他们坚信:“胡运何须问,赫日自当中”(陈亮《水调歌头·不见南师久》),“男儿事业,看一日、须有致君时”(辛弃疾《婆罗门引·龙泉佳处》)。但是,在那个令人窒息的现实中,他们的理想信念愈是坚定,他们所感受到的悲愤也就愈是强烈,而当他们把满腔的悲愤渲泄在作品中时,便形成了巨大而凶猛的感情波澜,从而造就了一种奔放激越的气势和至大至刚的壮美,它别具一种崇高壮烈的人格美。执着、坚毅、永不屈服的奋争精神就是这一时期文人及其作品的共同特色。他们的作品给予读者的是一种强烈而又深沉的感奋,它们展示给读者的是失路英雄激烈而又苦闷的灵魂。
总起来说,北宋文人表现出的是一种平和宁静、澄澈恬淡的心态,这是北宋文人的品格节操的折光;而处在尖锐的民族矛盾中的南宋文人则表现为一种激烈难平、执着进取的精神,这是由特定的历史时代和爱国志士的忠义灵魂所决定的。两宋文学表现出的这种差异,恰好是文人词与英雄词的最好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