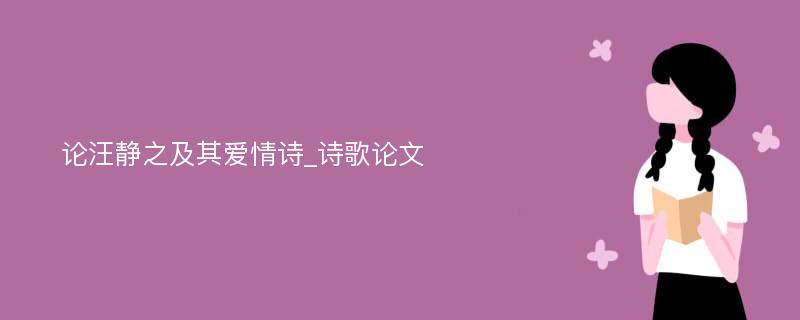
纸上谈爱 满纸悲辛——论汪静之和他的爱情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悲辛论文,之和论文,纸上论文,爱情诗论文,汪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34(2002)05-0007-07
曹雪芹曾深有感触地把《红楼梦》说成:“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 谁解其中味”。
事隔刚好一个世纪的今天,当我重新翻开“湖畔诗人”汪静之(1902-1996)在1922年出 版的诗集《蕙的风》这本中国新诗史上第7本诗集[1]的时候,我也有曹雪芹当年内心所 拥有的那种悲凉、愤怒、惊奇、颤栗的强烈感受。它就是我在本文标题中所说的:“纸 上谈爱,满纸悲辛”。
一、暮气沉沉中的少年气象
出版《蕙的风》时,汪静之才20岁,而且是个中学生。诗集一出版,就在诗坛闹得沸 沸扬扬。不过,汪静之还是幸运的。当时他就读的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是名扬全国的东南 新文化堡垒[2]。而且新诗刚刚才起步两三年,适逢百废待兴的大好时机。还有此时他 与曹佩声[3]、丁德贞、傅慧贞[4]、符竹因[5]4位新女性之间的爱情瓜葛使他拥有了相 当丰富的写爱情诗的题材。这是他的“诗库”[6]P234。最后重要的一条是他有象胡适 这样的中国新文化运动先驱的同乡(他们俩同为安徽绩溪县上庄余村人)。所以,他就能 够拥有象应修人、冯雪峰和潘漠华这样的至交同仁并与他们一起创办了中国新文学史上 第一个新诗社团——湖畔诗社;他就能够写出大批的现代爱情诗;他就能够让自己的处 女诗集在当时影响甚巨的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他就能够使自己的诗集在出版的时候请 到当时就已名震四方的鲁迅审读,胡适[7]、朱自清和刘延陵3人作序和周作人题签,而 且当胡梦华等几个旧派文人频频发表文章攻击《蕙的风》存在严重的道德问题的时候[8 ],甚至连新文学阵营内部也有象当时远在美国读书的闻一多大骂它“只可以挂在‘一 师校第二厕所’底墙上给没带草纸的人救急”[9]P19的时候,周作人、宗白华、鲁迅等 人毅然地站了出来,替他说话、维护它的价值,从而在这场不期而遇的关于文学和道德 的论争中使得汪静之和《蕙的风》声名大震而成为中国新诗史上一部重要的诗集。
我以这样的方式来开始进入《蕙的风》,不是贬低它,更不是诋毁它;而是表明我对 汪静之和《蕙的风》的价值取向,那就是它的思想价值大于它的艺术价值。但我也不是 要说汪静之是位思想家和精神战士,而恰恰相反,汪静之是位浪漫派诗人、唯美主义者 、享乐至上主义者和“准隐士”。只不过,他和他的爱情诗恰好切合那个时代的审美趣 味。
在考察了上世纪初的新诗后,1935年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里说 :“中国缺少情诗,有的只是‘忆内’、‘寄内’,或曲喻隐指之作,坦率告白恋爱者 绝少,为爱情而歌咏爱情的更是没有”。而当时还是少年诗人的汪静之却只顾“自己发 现自己”而且又自己专写自己的爱情。这就是他在《蕙的风》出版时自己说的而让他当 时正在热恋着的符竹因书写卷首题词的那句话“放情地唱呵!”所包涵的精神状态。后 来,在《我怎能不歌唱》里,汪静之还坦陈了他写诗的内驱力:
我们住的地狱不能变为天堂,
我们的狂欢不能久长,
我们的青春如流水:
我怎能不歌唱?
这表明,汪静之是遵循“心的命令”来写诗的。他说过:“心的命令是不可违的”[10 ]P431。他还说:“我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完全是盲目的,不自觉的”[11]。在1957 年版的《蕙的风·自序》里,汪静之进一步阐释说:“‘蕙的风’是我十七岁到未满二 十岁时写的。我那时是一个不识人情世故的青年,完全蒙昧懵懂。因为无知无识,没有 顾忌,有话就瞎说,就有人以为真实;因为不懂诗的艺术,随意乱写,就有人以为自然 ;因为孩子气重,没有做作,说些蠢话,就有人以为天真;因为对古典诗歌学习得少, 再加上有意摆脱旧诗的影响,故意破坏旧诗的传统,标新立异,就有人以为清新。”。 这是在特定的政治环境下说的特定的话,真真假假,躲躲闪闪,若隐若现,给人“一半 清醒一半醉”的感觉,而诗人的矛盾心态可以从其“文本的分裂”中窥见出来。
《蕙的风》收诗160多首,其中爱情诗占四分之一。有位研究湖畔诗派的专家,做了一 项十分能说明问题的细致工作——他把此前已经出版的6本新诗集从爱情诗的角度进行 了统计,结果发现它们里面的爱情诗的总和还不及《蕙的风》一本里的数量;而当时在 写爱情诗方面、在数量上能与汪静之相匹敌的只有刘大白,但因为刘大白的爱情诗如他 自评的“用笔太重,爱说尽,少含蓄”[12]和没有完全挣脱掉旧体诗词的陈腐气味而难 以给人新印象而成为可有可无的“旧梦”了[13]P27-33。所以,人们习惯上把汪静之称 为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第一位爱情诗人。
虽然,汪静之自小就有“梦中题诗”[14]P266的记录,而且在15岁那年因爱上了已病 故的未婚妻的小姑母而作了一首七言绝句向她表白自己萌动的爱情。但是此前他还从未 写过新诗。他几乎是在新诗荒原上来开笔写新诗的。虽然他受到了《新青年》上白话新 诗的直接诱发,但是当时可资借鉴的中外新诗少得可怜。何况他认为中国现代的书不必 去读[15]P124。他只推崇周作人[16]P401和冰心[17]P252/253/269/272。而外国诗人他 喜欢海涅[18]P2和泰戈尔[19]P125/307。他是凭借着天资和才情“自动”写情诗的。所 以,他的诗就能给人“纯洁天真,活泼乐生”[20]的美好印象。不管熟悉还是不熟悉他 本人的,不管是在国内的还是在国外的中国诗人,只要是持首肯姿态的,都一致赞扬《 蕙的风》有可爱的“稚气”而无垂死的“暮气”(胡适语)。这种“少年气象”(宗白华 语)令人兴奋、给人鼓舞的是:它不但给新诗带来了光明,而且给当时死气沉沉的社会 添了些微的亮色。因而它的意义由诗之内向诗之外弥散开来;它的作用也就被意外地放 大了。
二、欲望化的诗歌文本
浪漫主义的基本品格是激情的表现。而汪静之的爱情诗是浪漫主义诗篇。在上世纪20 年代旧礼教旧道德的全面禁锢下,同时,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前提下,自我解放的 总体目标是个体欲望的解放。而无限要求的个体欲望与现实满足感的有限性之间势必会 产生冲突。质言之,现实生活中对爱情的追求、失落、痛苦、挣扎通过爱情诗渲泄出来 ;这就使得现实的苦痛和压力在欲望化的爱情诗写作中得到了稀释和缓解,但从来没有 根除过。汪静之在爱情诗里说“我心里筑了一座悲苦的城”(《心上的城》),“心上有 了一座悲痛的岛”(《海水与虹霓》)。尽管如此,它们还是给人“不忍不读”而又使人 微笑[21]的审美感受。
汪静之现实欲望文本化过程中的几块界碑是:从1922年的《蕙的风》到1927年的《寂 寞的国》,再到写于1922年至1933年10多年的情书集《汪静之情书:漪漪讯》(它是中 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情书集,中间时间跨度有11年,有约150封信,长达32 万字。这是广为人知的徐志摩的《爱眉小札》无法比拟的),最后到1996年之前写的关 于他与6位青年女性之间恋爱的“情场痛史”的古体诗文集《六美缘》。而我们在这里 只谈新诗,故把后两者就悬置不论了。
先谈诗集《蕙的风》的欲望化表现。《蕙的风》抒写的是“我”与4个恋人之间的患得 患失的情事。这4个女子除了与他白头偕老的符竹因(绿漪、录漪)外,其他3个分别是曹 诚英(诗中用B代称)、丁德贞(诗中用D代称)和傅慧贞(诗中用H和蕙代称)。我们可以戏 拟《六美缘》而称《蕙的风》为“四美缘”。汪静之主张少交友[22]P301,保持精神的 清洁。他持有现代意义上的婚恋观(比如,他坚持用“伊”而不用“她”,除非用“男 也”作为一个汉字来替代“他”[23]P161),提倡精神之恋[24]P230/284/307,而非“ 金莲”、“楚腰”之类。因此,他写爱情诗也就不是狎客听艳曲,遗老作艳诗,而是一 种“纯洁的尝试”[25]P113。
首先,汪静之涉猎到当时一些极敏感的婚恋话题。他认为:“道德是依时代精神而转 移……。破坏旧道德的人不是无道德,却是最有道德的人,因为旧道德已经变成不道德 了”[26]P271。而“这旧道德上的不道德,正是情诗的精神”[27]。在封建礼教蒙昧愚 民的欺骗下,中国婚恋里出现了心态畸形的男女。为此,汪静之在《贞节坊》里为“贞 女”、“节妇”和“烈妇”而扼腕落泪,在《不曾用过》里辛辣地讽刺了愚人又愚己的“贞男”。因为,汪静之是极力反对“自己镣铐自己”[28]P299的。诗人含泪地笑着写 道:“他独身到七十岁时死了,/他的魂就进了天堂。/他把心呈上上帝查验,——/是 一颗枯死的心脏。//上帝悲悯地发怒说:/‘你不知已犯了罪恶?/愚人呵!我给你的爱情 ,/你一点也不曾用过!”。这些有力的诗句说明了“贞女”、“节妇”、“烈妇”、“ 贞男”等这类在现实中自戕而把希望寄托在未来世界的愚男昧女们就连他们痴信的上帝 也不会宽宥他们的。如果说,这里的贞男贞女是一些典型的“旧人”,那么,在《小和 尚》和《灵隐寺》里诗人写了另一个极端的“新人”形象。前者写了人性未泯的“小和 尚”对前来朝拜的妇女流露出“希求的眼色羡慕的神情”。后者写了灵隐寺的和尚久已 压抑的爱情在春天莅临的时候要沸腾了。“旧人”和“新人”是两个极端的代表。而在 《被摧残的萌芽》里,从私生子被抛弃在荒郊野外来警示那些为数不少的半旧半新的“ 过渡人”。
在思想上汪静之就没有这种过渡性的时代特征,而只有“新人”的战斗风采。他当年 备受胡适和宗白华等人推崇的小诗《一步一回头》:“我冒犯了人们的指摘,/一步一 回头地瞟我意中人,/我怎样欣慰而胆寒呵”。着一“瞟”字,尽得风流。它展示出诗 人对自己“意中人”的那种极其矛盾而又复杂的心态:既想看,又怕看;既倍感欣慰, 又深觉胆寒。最后,爱情的力量占胜了一切。所以,诗人才敢于“冒犯”世俗的偏见, 恋恋不舍地不断地瞟他的意中人。但它也从侧面突出了封建势力的顽固和巨大。它既写 了封建礼教严密的捆绑,又写了自由爱情的不羁。它确实达到了“趣味在文字的缴绕上 ”[29]和拥有“曲折的心理情境”[30]这类新文学先驱们对新诗在美学追求上所预设的 目标。汪静之的这首诗和分别受到赵景深、宗白华称赞的《祷告》[31]、《谢绝》[32] 3首诗都摆脱了草创期新诗普遍存在的说理太多的弊病,达到了深入浅出的佳境。
再来看看第二个诗歌欲望文本《寂寞的国》。在这里,诗人进一步以自我的爱情波折 为叙说的中心,好像只顾自个儿说自个儿的,在寂寞的、一个人的天地里倾诉。而且此 时他假想的读者、听众由《蕙的风》时期的4个女性剧减到只有符竹因一个。这不能不 说也是诗人此时寂寞的一层意思。比如,写单恋的有《不曾知道》、《她心里有一座花 园》、《秋风歌》和《野草全枯黄》等。而《漂流到西湖》里的:“我单思苦恋的爱情 ,/已经绿遍了西湖水”道出了单恋苦涩而又不肯罢休的滋味。又如,写失恋的《独游 》、《很好过了》、《笛声》等。这类诗尽管表现出了失望的惆怅,但是更让人体味到 诗人在失望的尴尬情境下令人心颤的悲苦——明知希望的不可得、“希望太虚幻”(《 希望》),还要苦苦地追求。这种执著不但不使人感觉到诗人是在非理性地胡闹,反而 使我们要为诗人锲而不舍的爱情至上的爱情追求而击掌!他说,尽管“我自己的心中/也 有了沉重的塔儿镇压”(《雷峰塔》),但是“我为你的美而生”(《赠录漪》),“我为 你到世界上来”(《玫瑰》),“我没有信仰”,“我把你当做上帝”,而“你若要命令 我不再爱你,/我绝对不能从命”(《不能从命》),“你的心是我的故乡,/你的心是我 的祖国。/我生长在你的心里,/我最爱住在你心窝”(《挖窖》)。这些诗践诺了他曾经 告诉内人的写诗秘诀:抒情 + 大胆[33]P407。
从《蕙的风》到《寂寞的国》,诗人生活的圈子进一步缩小,他被时代、生活和情爱 ,也被自己逼到了一个狭窄的甬道。这再一次体现了诗人一贯的诗歌主张“我在做诗便 是在生活”[34],“我的诗就是我的代表”[35]P57。而不少的论者认为它表明汪静之 在走下坡路,进一步颓废和黯淡[36]。我就不懂这些人为什么一定要诗歌紧跟时代?难 道“风派写作”就一定比沉稳的写作好些吗?既然我们都知道爱情不会总是一帆风顺的 这样的常识,那么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胡闹着去要求汪静之的《寂寞的国》该比《蕙的 风》光明些、上进些呢?汪静之本人生前也曾为《寂寞的国》的倍受冷落而焦心![37]。
而从艺术上讲,汪静之自认为《寂寞的国》比《蕙的风》自觉些。此时他已经得出了 一个诗歌公式:“情感 + 想象 + 事实 = 诗”。在写作《蕙的风》时,他是从他非常 推崇的《诗经》[38]P54/64/90/92/155那里借用了赋比兴的手法,所以在诗集里,大自 然的一切都被人格化、对象化,都成双成对地“谈”起了恋爱。而在《寂寞的国》里, 在更多的时候,诗人干脆直接使用“你是……”“我是……”的二元矛盾对立统一的隐 喻性抒情结构,象《太阳和月亮的情爱》、《河水》、《湖水和小鱼》和《我是死寂的 海水》等就是。同时他还常常运用到后来为朱湘所不齿的失败的排比[39]P20。而我认 为,在一无所鉴、一无“师承”的情况下,排比的反复运用,有利于避免诗歌结构的板 结,有利于使诗歌张开想象的翅膀,从而有可能产生一种“交叉文化蒙太奇”的审美效 果。此外,《寂寞的国》多采用西方诗歌的高低格的结构体式,使诗歌呈现出比《蕙的 风》更自觉的格律化的倾向。它要比新月派的现代格律诗美追求要早得多!而这也是人 们常常在研究新诗的格律化、规范化时所容易轻易地忽视的!
三、艺术至上、享乐至上
汪静之自幼生活优裕,在其父的引领下,遍游了徽州一带名山大川[40]P24;从小到16 岁一直和姆妈或阿姐同睡[41]P169。15岁前就有了指腹为婚的未婚妻,同她和比她大1 岁的小姑妈3人常常在一起玩耍,可谓有了自己的青梅竹马了。所以,汪静之说:“进 了中学,仍旧像个小孩,不懂人情世故,受不了一点委屈”[42]P169。童年和少年的这 些经验,使他长大后难免不形成远离社会、倾心山林、爱好美女和崇尚艺术的品性。
汪静之把艺术和享乐看得很重要。尤其是1923年过后,他从诗集《蕙的风》写作的自 发时期进入到诗集《寂寞的国》写作的自觉时期,而湖畔诗社同仁应修人、冯雪峰和潘 漠华纷纷改弦更张地写革命诗并投入现实革命斗争的激流中去了,他不但没有跟上他们 、跟随“大流”去投身革命,反而越来越清醒地、强烈地意识到及时行乐的重要。在19 22年7月19日写给符竹因的情书中,他劝慰道:“记得你前信说‘生活又很枯燥’,我 以为总有法子改造的;不然,这种没趣的生活,岂不大有损于精神么?丰润精神,培养 心情,最好莫过于艺术——文学、音乐、画图。”[43]P21。而在汪静之看来,诗和诗 人又在其他艺术和艺术家之上。他说:“一切艺术,最高超的、最美妙的总莫过于诗, 而最多情的大都是诗人”[44]P330,“诗真是一件最可享乐的东西”[45]P309。
正是因为汪静之持诗歌至上观念,所以他不会是个现实主义者,而只能成为浪漫主义 者。而且他宣称自己是个唯美主义者、享乐主义者[46]P262。在现实生活方式上,汪静 之和“五卅”运动前的应修人、郭沫若等人都有西方唯美主义诗人式的“生活美学化” 或说“美学生活化”的倾向。汪静之曾先后在上海和武昌写给符竹因的两封情书里交代 了他与应修人和郭沫若之间的难免使人有“同性恋”之感的一些隐秘的生活细节。
汪静之的唯美主义、享乐主义不仅从现实行动上表现出来,而且还从他的情书这种欲 望的旗帜和他的诗歌这种欲望文本里表现出来。
在情书里,他多次大张旗鼓地宣扬他的享乐主义的观点。1923年6月22日在写给符竹因 的祝贺生日的长信中有这样一段话:“人生最大最终之目的为何?求乐耳!流年如水去, 青春不再来,极可悲也,于乐何有?……。生到世上来为了求乐而有意义,不然等于不 生,故须及时行乐也(但是真正高尚的求乐,非俗流之求乐)”。同年11月9日,他又在 写给符竹因的信里说:“青春不再来,确是极可哀极可痛的无可奈何的事。但不可因此 便灰心一切,专事纵乐怠堕,我们应当更要努力上进,著书立说,做一点好成绩留在世 上,于是我们的精神永远不会再死了”。可见,汪静之之享乐,不是纵乐、挥霍、颓废 ;而是要认真地过好每一天。
而在诗歌里,他也是这样写的:比如《柳儿娇》:“尽力地舞蹈,/表出本来的美妙” ,“失去了青春何处找?/快把碧波儿搂抱。/只管今朝拼命地欢爱去,/听他是凋零呀枯 槁”;又如《我是天空的晚霞》:“但在我被毁灭的刹那,/让我再醉舞一番”,“但 在我快憔悴的末日,/让我再鲜红一次”;再如《我若是一片火石》:“我为了仅仅一 秒钟的欢舞,/愿把我的生命作牺牲”等等。而且,他还把这种思想传染给他的爱人。 比如,在《莫停下你的金樽》的末节所言:“这是甜美的葡萄酒呀,/玫瑰一般的清芬 ,/录漪呀,莫停下你的金樽,/莫干了你的芳唇”。
四、“做个纯粹的诗人”
汪静之诗文里有着对时间的强烈的自觉意识。这是他思想现代化的表征。传统文化的 本质主义和整体性构成、内在意义的确定和生存空间的统一,决定了它所建立的是一个 超越时间的所谓永恒的世界;因此,时间,就不构成传统文化的基本因素。而在新文化 运动的思想启蒙下,新诗人们对传统提出了质疑和挑战。这样,原来的本质主义遭到了 否弃,传统的意义受到了嘲讽,而文化空间的整体性被强行瓦解。现代人好像自己被自 己突然推置到无家可归的漂泊境地(汪静之写过《漂泊》和《漂泊者》,可惜后者失传 了)。当文化发生断裂后,现代人在时间的巨大压力下,重新上路,去寻求人的根本性 存在;这样,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先锋行动。
而汪静之把他的先锋行动仅仅局限在个体欲望的寻求上,而努力不与世界发生关系。 他走的是一条在自己发现自己之后又要自己独自去实现自己的个体的孤独的奋斗之路。 当然,他的奋斗又不是急风暴雨式的,而是和风细雨式的。他是隐士式的奋斗、是唯美主义者式的奋斗,快乐式奋斗方式。这几乎是一贯的。只有在极“左”的环境下,它才 受到过一些干扰。解放后,他也不得不写了一些表态性的政治诗,在1957年重版《蕙的 风》时对原来的《蕙的风》和《寂寞的国》作了不少政治性的拔高式的增删[47]P79。 在90年代,他曾说这样一番总结性的话:“解放前我胆子小,不敢革命;解放后仍旧不 敢革命。因为怕组织性、纪律性。从20年代到现在,我都靠不谈政治,明哲保身、苟全 性命。否则,我不是当烈士,就是当右派,就不能自由自在地游山玩水,自由自在地谈 情说爱,自由自在地写爱情诗,我又要命做什么呢?”[48]。他一生都在有意回避政治 ,而值得庆幸的是几乎历次政治运动也都把他给“漏网”了。只有50年代中期,他因受 冯雪峰问题的牵连而被人民文学出版社停职回家过一次,文革时期更是相安无事。从政 治的、社会的意义上来说,他真正算得上一个现代的“隐士诗人”了。他兑现了1924年 初他在武昌一所中学教书时给符竹因写的信里的愿望:
我不愿入世,这个黑暗的社会非诗人所居之地,我见着普通一班“社会人”就头痛!(我只好把他们取“社会人”这个名字,因他们是溺在社会里的俗人,诗人却是脱离社会 的高人)。我只愿做隐士,我只愿“三间无佛寺,一个有妻僧”!我将来定要和你隐于山 水之中,做个纯粹的诗人,做个多情的诗人,做个真诗人!这个臭社会绝对不要管他, 改造社会是革命家的职务。诗人只管唱他的诗,音乐家只管奏他的乐[49]P376。
所以,对于这个庸俗的人间,汪静之有的只是憎恨。而这种多少有些厌世(他相信自己 和爱情)的情绪在《我只有憎恶》一诗里有集中的体现。
但是,诗人又不可能不食人间烟火。这种社会意识淡漠的情绪,使他在现实生活里不 断地吃亏碰壁。尤其是在婚后,在民不聊生的兵荒马乱的岁月里,为了养家糊口,他四 处奔波,不断地求职,随后因不善人事,又不断地遭遇解聘……。他坚持的“半隐士” 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方式给他带来的也是无尽的悲辛。我们也可以从《汪静之五十年前的 一封信》[50]里见出他在1946年前后的一段心迹:
盖有感于抗战八年之后,大学尽为各学阀各党派所占,已非纯粹的讲学之地。弟既不 属于任何学阀,又不属于任何党派,故毫无门路。……仍为一超然的无党无派的自由主 义者。……。弟素不喜欢加入团体,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文艺协会亦从未加入,虽因 此而陷入孤独无援,因此而绝少朋友之交游,亦无悔意也。……。六口之家,生活威胁 严重,请多方设法为荷。
开一代爱情诗风的汪静之,是个浪漫主义者、是个现代“准隐士诗人”,是个半调子 的厌世主义者,还是个百分之百的唯美主义者和享乐主义者。他的爱情诗如“柔和的笛 箫”,具有“田园的情调”(参见海涅的诗歌《倾向》)。
在欧洲爆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前一年,也是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在与沙俄哥萨克 的战争中壮烈牺牲的前两年,即裴多菲与森德莱·尤丽亚结婚的当年(1847年),裴多菲 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篇《自由与爱情》:“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 /两者皆可抛!”(殷夫译)。在这里,裴多菲假定了两层递级选择关系——生命、爱情和 自由;而选择的结果是“为了爱情,/我牺牲了我的生命;/为了自由,/我将爱情牺牲 ”。爱情比生命重要,而自由又比爱情和生命重要。这大概就是人们对爱情认识的最高 境界。比照一下,显然,汪静之只进入到了第一层,而对自由在生命和爱情中的认识则 是晦暗不明的。至少在写《蕙的风》时是这样。在1957年版的《蕙的风·自序》里,汪 静之自己就说了这样一番话:“我写‘蕙的风’时,看了‘新青年’上的政论,也不懂 。……直到‘五卅’运动那一年的秋天,应修人拿了‘共产党宣言’等三本书给我看, 我才好象瞎子睁开了眼一样,不象过去那样完全盲目糊涂了。……但我并没有真正认识 真理,只是在感情上欢迎革命,没有在理论上理解革命”。虽然,他也曾经写过《自由 》一诗并喊出了这样有力的口号:“我要怎样想就怎样想,/谁要范围我,断不成!”; 但是他在这里所作的精神上的自画像也仅是局限于为爱而爱的,断不是要去争取什么社 会性的自由。它表现出来的个体性追求是很明显的。因此,那种说汪静之曾投奔革命或 说有革命倾向是站不住脚的[51]。
总之,不象朱湘一生追求有“朋友、性和文章”[52]三样东西,汪静之一生只看重女 性和诗歌两样;他的一生,充分地实现了“半隐士”的生活目标和唯美的艺术追求。
汪静之(1902-1996),安徽绩溪人,20年代在杭州、上海两地读书,湖畔诗社的代表诗 人之一,高中学历,30、40年代在安徽大学、复旦大学等学校教书。建国后,在人民文 学出版社当编辑,晚年在杭州居住。出版过诗集《湖畔》(合集)、《蕙的风》、《寂寞 的国》、《诗二十一首》,诗论集《诗歌原理》,诗文集《六美缘》和情书集《汪静之 情书;漪漪讯》(由他的儿子飞白编辑)等。
收稿日期:2002-09-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