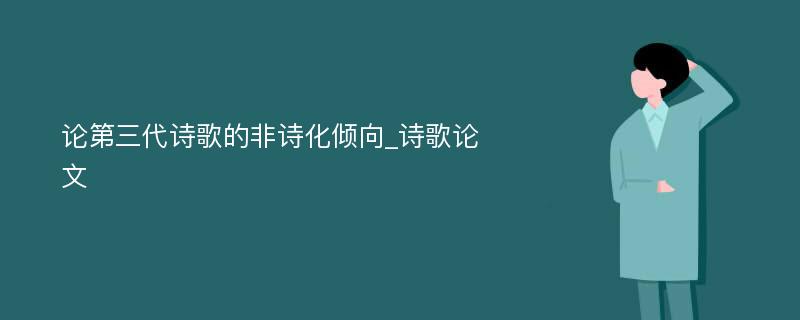
论第三代诗的非诗化倾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倾向论文,非诗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 要】 第三代诗在诗歌观念、语言形式和表现手法等方面对以朦胧诗为代表的现代新诗进行反叛并重建了一套自己的诗歌范式,在整体上表现出一种非诗化倾向。本文从反诗、泛诗、生命体验的角度来分析其诗歌审美观念的变化,从口语、前文化语言、返古语言的角度把握其对现代诗歌语言的自觉探索,从反讽、变形的角度研究它对诗歌表现手法的革新运用;“非诗”是诗歌创新的一种手段,也是诗歌发展演变的一条艺术规律。
【关键词】 第三代诗 非诗
继朦胧诗之后,当代诗坛出现了一股更具反叛精神的第三代诗潮,它们以一九八六年的中国诗坛现代诗群体大展为突破口,以集团冲锋的方式,打着“反对现代派”的旗号,喊着“打倒朦胧诗”的口号,铺天盖地,汹涌而来,它们无论是在诗歌观念上,还是在诗的语言形式、艺术风格、表达方式上,都表现出对以往诗歌的极大反叛,很难把它们纳入传统诗歌的范式和框架,表现出一种鲜明而又强烈的“非诗化”倾向。
第三代诗的产生,有着深厚的社会历史背景。文革结束后,随着偶像崇拜的消解,随着伟人们走下圣坛,人们惊异地发现:上帝原来只是人自己造出来的神,伟人也只是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的凡夫俗子。在神像倒塌的废墟上,他们发现了人,发现了自我。这时,他们原来的信仰产生了危机,价值观念发生了倾斜,他们不再崇拜,不再迷信,对现存的现实(包括已存的诗歌)的合理性产生了怀疑,并进而对传统的道德教义和艺术规范进行反叛。第三代诗人大部分出生在六十年代,他们受文革的毒害较浅,内心崇拜偶像的板结层较薄,具有较强的主体性,因此他们能够在朦胧诗人提倡表现自我的基础上,大胆地提出崇拜自己的主张,他们认为,对“过往年代的大师”,在内心深处“我们对他感激不尽,并充满了无限的敬仰,但重复和仿制他们,整天在他们的光芒阴影下疲于奔命,这对他们正是最大的不恭,对自己则是一种衰退和堕落。对一个伟大天才的回敬,最好的办法只能是,使自己也成为伟大”〔1〕,他们不甘于在前人的阴影下亦步亦趋, 不满于现实生活中大小诗人的论资排辈,他们要求艺术上的平等竞争,要求在诗坛上充分表现自我、崇拜自我的权利。
第三代诗作为一种新生诗体,在整体上表现出极大的随意性、无序性、驳杂性,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鱼龙相混、良莠掺杂,加上他们那种标新立异、目空一切的宣言,就更易引起人们的争议和不满,这就对“非诗”的生存带来了危机。固然,不加分辨地一味地肯定这些作品,认为它们是十全十美的,承认“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未免过于乐观和简单化;但无视这种客观现实的存在,不加分析地予以全面否定,则未免过于虚无和武断。对这种“非诗”,我们应采取客观的、事实求是的态度,对其加以辩证、全面的分析,才能明确其优劣,然后才能确定其应有的社会价值和艺术地位,并进而从中窥测、把握当代新诗发展的艺术规律。
诗歌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它要在无情的时间长河里生存下来,就必须不断地加以更新、发展,实现文体递变、新陈代谢,只有这样,它才能保持鲜活、旺盛的生命力。反观几千年的诗歌发展史,五四新诗之对于古典诗词、元曲之对于宋词、宋词之对于古诗与近体诗、乐府之对于三百篇——都是以前者对后者的改造、创新为前提,都是以一种“非诗”的形式存在着。就拿现在已广为承认的新诗来说,在五四时期,在满脑子格律、声韵、骈偶、典故的正统诗人眼里,新诗无疑是个怪胎,因此拥护它的人寥寥无几。在当时提倡白话已是非圣非法,何况提倡白话诗,然而新诗并不以某些人的意志为转移,它抵住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攻击,顽强地生存下来。因此,从这个角度讲,中国诗歌史又是一部“非诗”的历史,在每一次文艺繁荣时期,都留下了“非诗”的印迹。可以说,“非诗”是诗歌实现发展、嬗变的一种手段,是催动诗歌发展的一种内在动力。
新诗已走过了将近一个世纪的艰难历程,其间产生了许多优秀的诗篇,也产生了象郭沫若、艾青、闻一多、戴望舒、穆旦等许多著名诗人,但这并不意味着新诗已达到了至善至美的程度。作为一种新生的艺术形式,它仍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弊端,有待于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这一重任无疑便落到了当代诗人身上。当代新诗已极大可能地继承了现代新诗的“自由体裁”、“白话语言”及“现代人格”等优良传统,但与此同时,它又采取了一些“非诗化”手段来促进新诗的发展和演变。如果说五四新诗是对传统诗词的一次较彻底的“非诗”革命,朦胧诗潮通过对政治口号诗的“非诗”使新时期的诗歌创作恢复了五四新诗的优良传统并使之与二、三十年代的现代派诗歌接轨,那么第三代诗则是对现代新诗(朦胧诗)在某些领域进行了“非诗”的改革和创新。第三代诗的这种改革和创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反诗、泛诗、生命——“非诗”的诗歌观念
“诗言志”、“诗缘情”、“含蓄为美”、“诗是现实生活的反映”等诗歌观念,已作为一种文化心理积淀,深深地植根于我们的大脑里,并成了我们写诗、读诗、评诗的行为准则和价值尺度。可以说,它们最集中地体现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审美观念。然而,这些传家宝到了第三代诗人手里,却被无情地拒绝了,他们就象扔掉一张废纸一样把它们随手抛弃了,而将哪些过去被视为精神垃圾、严禁进入诗国的“破烂”加上诗的冠冕,堂而皇之地拥戴它们登入诗的殿堂,试看下面的宣言:
你们说,诗要美;我们说,诗要丑;你们说,诗要抒情;我们说,诗无情可抒;你们说诗要丰满,我们说诗要干瘪;你们说诗要写星星和花朵,我们说可以写撒尿和臭水沟;你们说诗要真实,我们说全世界都在撒谎。
——《大学生诗派宣言》〔2〕
什么都可能是诗,日常琐事,虚幻怪诞的胡思乱想,门外一个人的叹息,明天蚂蚁搬家等等。
——《新口语诗派》〔3〕
诗从属于生命过程,是对生命内涵的体验和深刻内省,只有潜入内在的心灵世界与人生对话的灵魂,才能获得诗美的升华。
——《关于诗的表白》〔4〕
这三段文字是众多的诗派宣言中主张“非诗”论的代表。它们好象是有志青年思考、探索、追求的箴言,又好象是玩世不恭的西皮士们闲聊、乱侃、不负责任的胡说八道。然而无论如何,这就是他们头脑中的诗的标准、诗的观念。他们从“反诗”、“泛诗”的角度来否定以往的诗歌,并进而构筑自己的诗歌王国,于是成批成批的“非诗”便应运而生。
“反诗”论者站在一个完全对立的角度来与传统诗歌进行分庭抗礼,他们提倡“反艺术”、“反文化”、“反崇高”、“反优美”、“反传统”、“反理性”的“非诗”主张,带有一种强烈的创造欲和近乎变态的破坏欲。这种审丑的诗歌观念,反映了在当前改革开放的大潮中部分青年诗人在人生观、价值观、艺术观上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它的目的,就是“捣碎!打破!砸乱!”覆盖中国当代诗坛的朦胧诗,它“所有的魅力就在于它的粗暴、肤浅和胡说八道”,它反对贵族式的高深和博学,而将“那些流落街头、卖苦力、被勒令退学、无所作为的小人物一股脑儿地抓住,狠狠地抹在纸上,唱他们的赞歌或打击他们”〔5〕, 尚仲敏的《关于大学生诗报的出版及其它》表现了一群没有成名的小人物对诗歌艺术的执着追求及其所遭遇的磨难,他们天真幼稚,感情激烈,可爱而又可恨,整首诗格调明快,幽默诙谐,这首诗本身就是对“反诗论”的标本注解。“反诗”理论的这种不负责任的狂轰乱炸,在文化理论上起到了解构的作用,但从其创作成果来看,有能力足以与传统诗歌(包括朦胧诗)相抗衡的诗歌作品至今尚不多见。
“泛诗”论认为一切都可能是诗,认为一切人都可能是诗人,这无疑取消了诗的圣洁、神秘色彩,取消了诗的深度模式,在诗歌与生活现象之间划等号,将诗歌推进到一个广泛的、普遍的“非诗”领域。但与此同时,它也给人们带来了一种新的困惑,它似乎蕴含了这样一个背反命题:什么都可能是诗,什么又都可能不是诗。这种观念虽然拓宽了诗的表现领域,但它混淆了生活与诗及好诗与坏诗的界线,给诗坛带来了部分庸俗、无聊、失败的赝品,同时它又重复了五四时期对这一问题的争论。
“生命论”一反生活反映论,将诗与生命联系在一起。诗人们不再满足于对外界生活的熟悉和体验,而将诗的触角从外在客观世界收缩进自己的内在宇宙,体验、倾听内在生命的孤独和节律。生命作为一种生存状态,与世界万物保持着一种非常微妙的关系,同时它也与外在宇宙一样伟大、博深,充满神秘感和诱惑力。诗人们象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发现了它,他们或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沉迷于生与死的玄思冥想(如欧阳江河的《悬棺》);或乐道于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注与思考,追求宇宙、人、艺术三者在整体上的同构与认同(如刘太亨的《生物》);或内视原始生命的骚动与喧哗,将生理快感与艺术陶醉融为一体(如唐亚平的《黑色沙漠》)。从目前来看,以生命为突破口来对新诗进行切入和创新,确实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但同时它也带来了一种满足于纯粹生理快感的性诗和一种狭窄的、封闭的“自我”的小诗,缺乏哲理内涵和艺术价值。可见,如何使内在生命处于一种开放的、流动的、与外在世界密切相连的状态并使之能转化成艺术作品,仍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反观历史,以往的诗界革命大都是诗人经过长期的实践探索,渐渐悟出其中的道理并进而概括成艺术理论,从而引起某一时期的诗歌观念及审美趣味的变化。然而,第三代诗人正好走了一条与此相反的道路,他们大多是先有自己的理论宣言,然后再按照这些理论框架去写诗,其结果便常常是理论与实践相脱节,形成了雷声大雨点小的尴尬局面。因为读者看重的是诗而非理论,理论与诗之间终究隔着一层;对于诗人来讲,眼高手低也毕竟是一种缺憾。况且,在这些理论宣言中,也并非所有的理论都有价值、都有指导意义,有许多理论本身就似是而非,缺乏系统性、完整性与开创性。这种现象如果继续下去,就又会产生另一种形式的口号诗或宣言诗。
二、口语、非诗、返古——“非诗”的语言
贝森特认为,“一首诗的时代特征不应去诗人那里寻找,而应去诗的语言中去寻找。我相信,真正的诗歌史是语言的变化史,诗歌正是从这种不断变化的语言中产生的,而语言的变化是社会和文化的各种倾向产生的压力造成的”〔6〕。由此可见, 语言不仅是一种诗歌媒介和载体,而且也是诗歌的一种内在本质。一方面没有语言就不可能有诗歌存在;另一方面有了什么样的语言也便有了什么样的诗歌。新诗与旧诗的根本区别之一,就在于“白话”与“文言”的区别;诗与散文(广义上的散文)的区别之一,便是诗的语言与散文语言的区别。在第三代诗中,诗人们对于语言的追求已由自发阶段上升到自觉阶段。这种语言的自觉,具体地表现为对几种“非诗”语言的试验与确认:
1.对“口语”的重新认同
口语,即日常生活的口头语言,它轻松、自然、清新、透明,有别于精炼、华丽、雕琢的诗的语言。它根本上是一种“杂乱无章的胚胎元素,低于一切字辞和文句,隐于所有诗歌后的,确是一种四季长生的繁枝茂叶,是语言之中的新枝成分”〔7〕,当代的部分年轻诗人, 正是在这个层面上选择认同了口语的这种衍生性和“非诗”性,以此来反对朦胧、雕琢、博深、虚伪、造作的语言风格,他们主张“诗应该象呼吸一样自然,象流水一样轻松,有则有,无则无”,诗应该脱去富丽堂皇、涂脂抹粉的贵族气,还它一个清秀质朴的自然味;诗应该走出贵族的沙龙,步入民间的庭院,因为“语言不是博学之士或字典编者的抽象构造,而是起源于工作、需要、关系、欢乐、深情、趣味,历经世世代代的人类,它具有宽而低的基础,靠近地面。它的最后决定者是大众,是接近具体生活,和真正的陆地和海洋关系最密切的人们”〔8〕。
主张以“口语”入诗,这在中国诗歌史上并不是开天辟地的第一次,也不可能是轰然作响的最后一次。第三代诗对“口语”的主张和见解,基本上继承了“五四”时期“口语”诗的优良传统,并在原来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和发展。不可否认,“口语”诗固然产生了部分优良作品,但也确实存在着一些无法卒读的次品,这就提醒人们要注意吸收历史的经验教训,在实现“口语化”的过程中,不要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完全追求“话怎么说,就怎么写”的白话原则。因为这样会使诗歌语言失去弹性和美感,并且令人产生怀疑,即白话语言不经选择、提练、加工,是否都能成为诗歌?如果这种怀疑能够成立,那么我们的诗人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而五十年代后期“全民皆诗人”的无稽荒唐就又成了艺术真理。
2.“前文化语言”的还原
对于我们来说,翻开字典查阅某个字的各种定义注释,是阅读写作的必要手段,一旦离开了这些定义和注释,我们便会觉得茫然无措,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文化语言”。然而“非非”主义正是在这一点上拿“文化语言”开刀,力图捣毁“文化语言”再重建他们的“前文化语言”体系。他们认为“文化语言都有僵死的语义,只适合文化性的确定运算,它无力承担前文化经验之表现。我们要捣碎语言的板结层,在非运算地使用语言时,废除它们的确定性;在非文化地使用语言时,最大限度地解放语言”〔9〕,这种还原“前文化语言”的主张, 无疑与有着几千年优良传统的诗歌语言有着本质的区别,与那种“无一字无来历”的刻意追求更是相去甚远。它旨在消除诗歌语言的板结层,在能指与所指的动态转换中最大限度地创造语言的张力。
“非非”就是要超越“是”与“非”的二元对立价值判断,非确定化、非抽象化地处置语言,这种语言方式对新的思维方式的产生、对摆脱诗歌的单一化倾向及拓宽诗歌新的表现领域,都有一定的催生作用。从他们的部分作品来看,有的作品(如杨黎的《冷风景》)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消除了僵硬的语义板结层,使诗歌语言富有弹性和活力。但大部分作品仍显得粗糙、僵硬,缺乏活性,与理论主张相去甚远。
还原“前文化语言”的主张从理论上看似乎是能够站住脚的,但实际上这种理论却面临着这样一种困境,即前文化语言是一种先于人类而存在的自然语言(如光、色、形、质及其运动)和人类自身的神秘的人体语言(如内在的神经过程和激素过程),而这种语言与文化语言分属于两个不同的语言体系。现在诗人所面临的问题是能否在文化语言之外新创一种前文化语言,能否脱离现有的文化语言来进行诗歌创作,很明显这条道路是走不通的,因为他们仍是用具有几千年心理积淀的文化语言来进行创作,这样他们就只能深陷于如何把前文化语言转化成文化语言、或者说如何用文化语言来表现那种神秘的前文化体验的语言怪圈之中。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了,那么这种语言自身也就汲汲可危了。
3.“返古”语言现象
众所周知,新诗以“自由白话”为基本语言特征,以“时代精神”为其根本的内在特质,如果一种诗歌不具备这两个特征,那么它相对于新诗来说就是一种“非诗”了。部分第三代诗人正是从这一角度切入,力图通过语言的“返古”来创造出一种别具一格的诗歌作品。他们与文坛上的“寻根派”一起,将触角伸进东方古老文化的故纸堆里,用新的感觉和顿悟咀嚼、阐释着易经、八卦和古老的神话故事,于是“太极诗”、“求道诗”、“卦诗”便应运而生;在语言上他们也一反白话而趋文言,抛弃通俗易懂的口语而选择佶屈聱牙的僻字古语,诸如岛子的《极地》、渠炜的《大曰是》,它们或是引经据典,或是用半文言、半白话的句子来表现那种神秘、怪异的感觉和氛围,使人产生一种远离现实、扑朔迷离的感觉。更有甚者,直接以八卦符号入诗,如黎阳的《现状》,这首诗将八卦符号、象形符号和语言符号排列组合在一起,表明我们的生存现状是一个有山、有水、有天、有岸、有白昼、有黑夜、有土地的有机整体。然而这种表达方式本身却类似于一种语言游戏,具有不可重复性,缺乏可操作性,与凝炼、传神的诗歌语言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这样的诗歌恐怕很难被视为诗的同类,与好诗之间的距离就更大了。
对于诗人来说语言是一个怪圈,一方面诗人可以随心所欲地驾驭它、运用它;另一方面诗人又必须老老实实地服从它、听从它。可以说,诗人的生命就在与语言这头怪兽的搏斗中度过,它既可以使诗人一举成名、光辉灿烂,也可以使诗人默默无闻、暗淡无光。以上三种“非诗”语言现象,表明了第三代诗歌语言的自觉,表明了诗人们对语言的探索与追求的新趋向。
三、反讽,变形——“非诗”的表现手段
诗歌作为一种艺术形式,自有其相应的、独特的表现方式。这种方式对于诗歌来讲,既是一种手段,又是一种目的。不难理解,古典诗歌与赋、比、兴,现代诗歌(包括朦胧诗)与象征、通感、移情、蒙太奇等,二者之间都表现出一种手段与目的的自然协调。而到了第三代诗人手里,以往的表现方式都不足以表现他们在当代社会氛围中的所感、所思、所悟,也就是说以往的目的与手段之间产生了不相融的矛盾。为表现新的内在感受,反讽、变形等新的表现手段就应运而生了。这些新的表现方式的运用,又带来了诗歌观念、语言及风格上的变化,“非诗化”的倾向也就愈加鲜明。
反讽作为一种现代的艺术表现方式,与传统的表现方式“讽刺”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反讽是对讽刺的讽刺,是对“讽刺”的更高层次的超越;传统的讽刺主要是客观性的(即某些社会现象本身具有讽刺效应),而现代的反讽主要是主观性的(即作家主体所创造出来的讽刺效应);传统的讽刺表现出对社会的强烈关注和浓郁的忧患意识和参与意识,而现代的反讽则表现出对社会的极端冷漠和浓重的无可奈何感;前者是庄重的、严肃的,后者则是谐虐的、讥嘲的;前者是一种正常的倒错,后者则是一种理智的反常;前者主要通过“冷嘲热讽”的途径来实现自己的艺术功能,后者主要通过“自我亵渎”的途径来达到自己的艺术目的。因此反讽是现代意识的载体,是现代艺术的表现方式。
第三代诗人在运用反讽这种表达方式时,对现实持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他们对现实的不满不再表现为激昂慷慨的愤世态度,而是表现为放荡不羁的傲世态度;他们放弃了朦胧诗人苦心孤诣追求的意象艺术而采用无逻辑、非理性的具有黑色幽默意味的艺术形式——反讽,来对抗当代诗坛中那种谦虚得有点虚伪、朦胧得有点神秘、高贵得有点可怕的艺术形式。李亚伟在《硬汉们》一诗中写到:
我们走过忆秦娥娄山关/走出了中文系,用头/用牙齿走进生活,用武断/用气功顶撞爱情之门/用不明飞行物进攻/朝她们的头上砸下一两个校长,主任/砸下陌生的嘴脸/逼迫她们交出怀抱得死死的爱情//我们骄傲地辍学/把爸爸妈妈朝该死的课本砸去/和贫穷约会,把手表徘徊进当铺/让大街莫名其妙地看我//用厮混超越厮混/用悲愤消灭悲愤/然后骄傲地做人
诗中描写了当代一些大学生荒唐的生活方式,诗人根据生活的现实创造出一个可恶而又可笑的艺术世界,呈现出反常、辛辣、玩世不恭的情调。在他的笔下,“忆秦娥”、“娄山关”、“爱情”、“爸爸”、“妈妈”等含有崇高、优美、神圣之意的意象被消解而成为滑稽、嘲笑的对象,而那些过去一直为社会所不容的行为(诸如辍学、厮混)则成为引以为骄傲的生活准则。诗人把幽默的风格建立在冷漠的、无可奈何的基础之上,用超越常情、不合常理的细节,用逗笑的嘲讽和自我嘲讽来渲染主题,他们通过一种过激的行为方式,通过对自我的残酷解剖,借以表现他们变形的心态,表现他们对现代生活规则的反叛之情,使“硬汉”沦落为流浪街头的嬉皮士,使昔日带着神圣光圈的诗人成为今天“腰间挂着诗篇的豪猪”。
变形作为一种表现手段,与传统的夸张手法是根本不同的。夸张是经由创作主体想象的渠道而将数量加大,只是外形的变异,其本质没有发生变化,如“白发三千丈”、“燕山雪花大如席”就是夸张的产物。而变形则是由于诗人内在主体的变异而产生一种强大的张力,并进而导致与之相对应的客观外形发生变异,这时诗人的内在主体与客观物象之间达到本质上的同构,二者融为一体,组合成一个新的意象。如廖亦武的长诗《黄城》创造了一种隐喻式的整体氛围,表现了诗人对社会与人生的深沉思考。然而经过艰苦的上下求索,他痛苦地发现:“我注定是一条虫子”,“你们注定是一条虫子”,“我”、“你们”与“虫子”之间的这种对等变形,表明了在现实社会状态下社会对人的异化及人对自身的异化;吕德安的《蟋蟀之王》、孟浪的《时间就只是解放我的那个人》等也都成功地运用了变形手法。变形手法的运用往往产生一种怪诞离奇的艺术氛围,并带有一种荒诞、悖谬的哲理倾向。
第三代诗人打着“反诗”、“非诗”的旗号,是否表明他们已步出了诗国的领地踏上了漫漫不归路?非也。不管他们多么富于反叛精神,不管他们流浪多远,他们最终仍要回归诗国,尽管这显得有点荒谬。就目前来说,不管第三代诗人对于诗的理解有多大差别,也不管读者对于“非诗”的看法有多大分歧和争议,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诗人们在写这些东西时是把它们当“诗”来写的,读者在阅读它们时是把它们当“诗”来读的。如此看来“非诗”与诗之间尽管有那么多的差别,但它们之间还是有一种内在的联系。那么这种内在的联系是什么呢?也就是我们把“非诗”看做诗的根据是什么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来研究一下文体演变的内在规律。
一种文体作为一个有机系统,它总是由各种因素(语言、形式、技巧、内容等)组合而成的,但这些要素在一种文体中并不是平等地起作用,而是其中的某一种要素起主要作用(即支配性要素),一部作品正是依靠这个要素被归入某一特定的文体。因此“我们不是根据诗歌作品的所有特点,而只是根据作品的一些特点而把它归于诗的范畴而不是归于散文的范畴”〔10〕。那么第三代诗人在解构了诗的观念、语言及表现形式后,还有什么没被解构呢?通过分析他们的理论宣言及其作品我们可以发现两点,一是作为诗的内核的主体的“情”依然存在,第三代诗人毁灭性的利刃在它面前变得愚钝了,对它无可奈何,尽管有的诗人公开宣布拒绝“抒情”。这种“情”的延续与存在是第三代诗之所以为诗的主要原因之所在;此正所谓“诗情诗体,本非一事”,“盖吟体百变,而吟情一贯”〔11〕。当然我们也应看到,第三代诗人所表现的主观感情与以前诗人的主观感情之间有着非常大的差别,它不再是优美的、神圣的、崇高的、含蓄的,而是非美的、卑贱的、宣泄的。如果把情感看做一个整体世界,那么前人只发现、表现了它的一半面目,而第三代诗人则发现、完形了它的另一半,从而完善、恢复了情感世界的本真面目;其次,诗的一些外在特征(如分行、分节、篇幅短小等)也被继承、保留下来,正是这两个传统色彩较浓的要素,将第三代诗归入了诗的范畴。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非诗”并不是诗歌之外的其它什么东西,而只是诗歌的一种新的存在形式,是此前诗歌的一种变体,只是逻辑意义上的否定之否定。“非诗”本身既是一种手段,又是一种目的,因此诗人在进行“非诗化”的同时,一种新的“诗化”建构也随之开始,“非诗化”与“诗化”处于一种双向的、互相转化的状态之中。对于诗人来说,要突破超越已有的“旧我”,使自己以后的每首诗都成为一个“新我”,就必须采用这种“非诗化”的手段。“少陵知诗之为诗,未知不诗之为诗,及昌黎以古文浑灏,溢而为诗,而古今之变尽”〔12〕,这句话说明了“以文为诗”给诗歌发展所带来的巨大变化,同时也使我们参悟到了诗体变革的一个内在艺术规律,即不但要“知诗之为诗”,而且要“知不诗之为诗”。
作为人类最古老的艺术形式,诗之河要想奔流不息,永不枯竭,它就必须象大海一样敞开宽广的胸膛,容纳百川,“向所谓不入文之事物,今则取为文料;向所谓不雅之字句,今则组织而斐然成章。谓为诗文境域之扩充,可也;谓为不入诗文名物之侵入,亦可也”〔13〕,这段话给我们提供了认识“非诗”的更高远、更广阔的视野,也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诗歌演变发展的必然途径。
综上所述,第三代诗在诗歌观念、语言形式及表现方式等方面都打破了传统的诗歌模式,并提出了自己富于创新意识的理论主张,实现了对朦胧诗的“非诗”化变革。尽管他们在创作上尚未拿出足以与自己的理论主张相媲美的杰作,但它在审美观念、语言表达方式等方面的实验探索,开启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向后现代主义文学转变的先河,也为九十年代先锋文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On a Non-Poem Tendancy on Third Generation Poems
Lu Zhouju
Adstract:From such sides as Poem idea,Language form andmeans of expression,third generation poems rebel against contemporary new poems which represents itself by "obscure" poems,at same time it is rebuilding own model style.In general,the third generation poems have shown a non- poem tendancy.The paper analyses change of its
idea
of appreciation of beauty from standpoint of anti-poem,Pan- poem and life experience; grasps its exploring language
of contemporary poem,based on oral ( spoken)
language, pre-cultrue lauguage and termed ancient lauguage;also studies its newly applying means of expression of poem from standpoint of satire characteristic and changing form. According to above analysis,the author come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non-poem is a way to create a new kind of style of poem, is a law of development of poem too.
Key Words:Third generation poems,non-poem.
注释:
〔1〕尚仲敏《反对现代派》,谢冕、 唐晓渡主编《磁场与魔方》,232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2〕〔3〕〔5〕转引自白行《有感于诗坛的“反理性”》, 《当代文坛》,1990(3)。
〔4〕《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见《深圳青年报》, 1986年10月24日。
〔6〕转引韦勒克、沃伦著《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186页,三联书店,1984。
〔7〕〔8〕[美]惠特曼《俚语在美国》。
〔9〕周伦右《非非主义宣言》, 见《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33~34页,同济大学出版社,1988。
〔10〕[俄]蒂尼亚诺夫《论文学的进化》,转引自陶东风《文体演变及其文化意味》,18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
〔11〕〔13〕钱钟书《谈艺录》,30页,中华书局,1984。
〔12〕赵闲闲《滏水集》卷十九,《与李孟英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