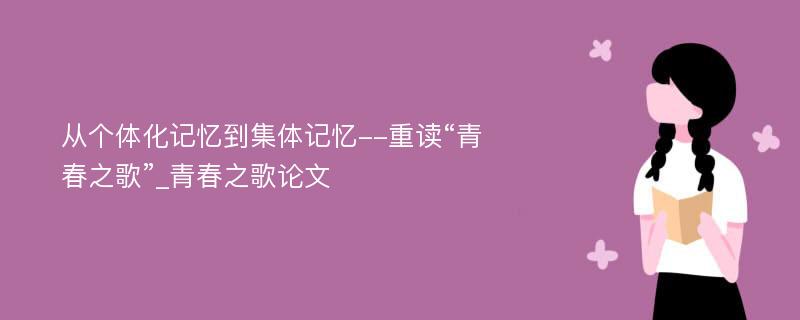
从个人化记忆到集体性记忆——重读《青春之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记忆论文,集体性论文,之歌论文,青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厚重的政治文化氛围笼罩下,“十七年”文学对“小资产阶级的创作倾向”和“知识分子的自我表现”异常敏感,于是便产生了这种现象:除了《青春之歌》之外,红色经典的主人公基本上都是工农兵,知识分子在革命历史的叙事中似乎成了边缘人。从这种角度讲,尽管杨沫当时屈从于粗暴的话语霸权,接受了争论者的意见,对《青春之歌》进行了修改,也尽管作品的文学史意义要大于文本自身所具有的思想意义,但这部多少承续着五四悲风余响的作品毕竟没有被打入冷宫,它给单色调的“十七年”文学带来了些许的异彩,也在一代人的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浪漫的理想主义记忆。
不过我们应该承认,《青春之歌》终于逸出强势意识形态话语的监控,并不是什么侥幸,它与二十年代自叙传体小说的差异是实质性的。作者为了将个人的生活经验缝合进宏大叙事中,不仅试图陈示个人主义皈依集体主义的思想逻辑,而且极力指证这种逻辑的惟一合理性,可以说主流话语统摄了作者个体的生命记忆。本文想要探讨的是,作者是怎样把破碎但令人激动的个体化记忆,包括独特的早期家庭生活体验和作为女性的社会生存体验,谨慎地编码成合符主流话语的。
一、细节虚构:事件历史——话语历史
《青春之歌》是一部自传色彩较浓的小说,从杨沫关于个人早期的生活经历和走上革命道路的自述中可以得知,林道静这个人物身上闪现着杨沫的影子。虽然《青春之歌》是小说而不是回忆录,林道静是小说人物而杨沫是隐含的作者,但从杨沫的自述和小说叙事的比较中,可以寻觅出从个体记忆转换成集体记忆的环节,从而厘清主流话语的叙事模式。
林道静的出走显然来自于杨沫“成人”的生命体验,是对杨沫独特的原生态生活经历的叙事。不过,这种关于个人体验与经历的叙事,都是在先在的观念统摄之下的精心编码。从杨沫的自传可以了解到,她对“罪恶”家庭的憎恨,直接源于父母的不和与家庭的无爱。她说,父亲是一个前清举人,靠办教育显赫起来,“花天酒地、嫖妓女、娶姨太太的腐朽生活,使他不顾家,使他堕落了。母亲开始还和他吵架,打跑了一个个姨太太。后来,她灰心了,不再管父亲,她自己也就成天和一些阔太太们打麻将、看戏、过起吃喝玩乐的寄生生活。由于对父亲的气愤,她也不再关心儿女”。(注:杨沫:《我的生平》,载《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杨沫专集》第3页,沈阳师范学院中文系编。 )这悲惨的缺乏抚爱和无人照顾的生活,她一生都挥之不去,像永远镂刻在心中的伤痕一样。杨沫16岁那年家中破产,其父逃之夭夭不知去向,为了抗婚她辍学离家。不久,杨母病故,这个家庭分崩瓦解,从此杨沫之于家庭犹如断了线的风筝。简言之,父亲的堕落与母亲的冷酷,构成了杨沫内隐的创伤性记忆,使她与家庭——最丰富的个人生活史的源泉之一分离开。
不难发现,杨沫在自传中讲述的原生态家庭故事,原本包含十分丰厚的悲剧涵意,是一个发人深省的能指结构,具有不断指涉、反复指涉和多重指涉的潜能。无论是杨父的堕落与破产、杨母的受害与冷酷,还是他们给子女带来的严重的消极影响,抑或是杨家子女对于家庭的不和与灾变所选择的种种态度,包括消极的厌倦、积极的反抗、无奈的出走等等,都可以生发出关于人性、命运,社会转型以及文化传统畸变的种种想像,由此获得对个人、家庭和民族文化的某种认识和把握,甚至能够揭示出投射在中国历史转型背景上的蕴含着社会深层问题的令人震惊的人性畸变,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讲述。
《青春之歌》从社会革命的角度出发重构作者早年的人生经验,所以把家庭作为社会权利结构和政治秩序的缩影。为了突出所指结构的意识形态性,作者还不得不对能指结构加以限定和规约,使它仅仅指涉所指结构。其最有效的编码方式,就是对自己原生态的事件历史进行细节的虚构,一个生动的例子就是把生母改写成继母,在小说形象林道静的血缘中注入佃农的血统。由继母承担加害者的角色,便将作者的个人体验提高到了“普遍性的高度”,因为林道静生母秀妮的悲惨命运,一方面揭示了林家的罪恶,隐寓了整个旧中国的黑暗,从而使林道静背叛家庭的个人选择具有了社会性意义;另一方面也为林道静最终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政治性的逻辑起点,自然朴素的阶级意识,对她最终成为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具有不言而喻的决定性作用。故此,从杨沫个人早期生活历史中的生母到林道静成长故事中的继母,看似不过是一个细节的虚构,然而在叙事上却是一个阿基米德点的移置。这种移置的结果是使小说的政治意义加强了,即宣谕家—国互义和阶级压迫:家长的权力是通过制度化的“家”这个装置,将阶级异己者置于死地,从而使个别的特殊世界向着阶级观念的普遍的地平线扩展开来。原本个人性的记忆转换成了集体的记忆,小说最终成了先在的意识形态的某种附属品。
二、话语与实践的分离:女性权利——社会解放
鲁迅先生20年代的一声“娜拉走后怎样”,给刚刚走出中世纪的知识女性一记当头棒喝,“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竟成为时代女性的精神徽标。(注:鲁迅:《娜拉走后怎样》,载《鲁迅全集》第1卷第159页。)
然而,这种精神徽标渐渐被视为奢侈的精神产物,不但被看作是多余的而且是有害的东西。汇集在集体主义大旗下的革命女性自豪地宣称,她们在娜拉“不是堕落,就是回来”的两条险峻的道路之外,寻找到了另一条女性解放的康庄大道,那就是妇女个人的解放必须随着社会革命的完成而实现,并以此号召妇女把个人的命运与某种社会变革的政治力量结合在一起,献身于政治的社会解放运动。林道静从孤独的社会异质者成为集体的同质者的人生轨迹,无疑就是为了指证这种具有“普遍性意义”的现代女性的“家庭——社会——国家”解放之路的。可是,这种解放之路愈来愈受到人们的质疑,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说,林道静的解放之路不过是别一种形式的“寻父”,她最终的归宿并不是其最初指望的独立女性的精神家园,而是一个丧失女性自我的集体意识形态。女性解放意识作为一种单独的社会意识,是阶级斗争与革命运动所不能完全包容或替代的。(注:陈顺馨:《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第7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4月出版。)那么, 林道静的女性意识是如何被逐渐消解与遮蔽的呢?
尽管杨沫为了迎合主流话语,把林道静最初的背叛家庭依附在浓厚的政治背景上,但是林道静的这一“成人仪式”的五四文化特质是不可能完全消抹的,三十年后杨沫也承认“我受了十八世纪欧洲文艺的个性解放的影响;也受了五四运动的影响,我要婚姻自主……”。(注:杨沫:《我的生平》,载《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杨沫专集》第7 页,沈阳师范学院中文系编。)体现在杨沫的影子林道静身上,其自我觉醒的标志就是鲜明的个体自主性:她不愿生活在无爱的空间,也不甘成为一个小官僚的附庸,所以把自己从家庭的网络中剥离出来,投身社会,自主地选择生活和把握命运。这种抉择显然是“依据某种描述去确知自身当下的行为及其原因”的,因而标志着她的“成人”。(注:[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第39页,三联书店1998年5 月出版。)
“成人”后的林道静,立即遭遇到话语意识与实践意识的冲突。她的关于自身选择的本质的解释,是源于西方启蒙思想的五四话语,而她置身于其中的现实生活却基本停留在传统的礼俗社会,话语意识与普遍沉滞的社会实践意识分离,因而她以一种与社会对立起来的方式来认同自我。林道静把自己不幸的社会境遇归罪于社会的黑暗,坚信自己无辜而且不愿意同流合污。然而,她毕竟生活在现实社会中,她的所有美好的理想在世俗世界里统统是空中楼阁。希望丧失了,生命孤单地留下,而且前面尚有漫长的人生道路要走。面对黑暗的生活世界和无望的未来,她缺乏勇气和耐心,只好投海自杀以死抗争。
林道静被余永泽救出后,生命出现了转机,她不仅有了生存的归属,而且获得了自由选择的爱情,在争取婚姻自主和个性解放的道路上迈出艰难的第一步,步入可能幸福的道路。然而,这种安定与幸福对于林道静来说,只是暂时和表面的。温馨的小家庭很快就使林道静感到沉闷、窒息:“她的生活整天是涮锅、洗碗、买菜、做饭、洗衣、缝补等琐细的家务,读书的时间少了;海阔天空遥想将来的梦想也渐渐衰退下去。”(注:杨沫:《青春之歌》第9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1 月出版。)作为第二代新女性的林道静,毕竟不同于她的前辈子君们,她从封建专制的家庭里走出的目的,并不仅仅只是为了寻找一个可靠的丈夫和编织自己的小家庭,然后终身依附着丈夫,厮守在精致的小天地里,她还有人格自由的向往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要独立生活,要到社会上去做一个自由的人。”(注:杨沫:《青春之歌》第8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1月出版。 )她不可能把人生的要义统统维系在狭窄的小家庭上。
尽管余永泽是位现代知识分子,也尽管他与林道静的自由结合具有反封建礼教性,但他深层的婚姻爱情观还是浸染着传统文化的价值观。他最初救出林道静,就未免不是“书生拯救风尘女子”;他之所以看重个人的功名事业,既是为了满足自我实现的需求,也自以为是为爱情作奉献——只有男人的成功,女人才有真正的安定和幸福可言,也就是说,他实质上是按传统社会的男子期望角色来进行自我定位的。同样,他也以传统文化对女子期望的定位去规范林道静,希望她成为一个美丽的贤内助。故此,他把林道静的美及对她的爱作为自己发奋的内驱力之一,而漠不关心林道静个人精神生活的追求,传统的“男才女貌”的情结潜沉于他的无意识。于是,在林道静眼中,“余永泽并不像她原来所想的那么美好,他那骑士兼诗人的超人的风度在时间面前已渐渐全部消失”。(注:杨沫:《青春之歌》第9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1 月出版。)林道静的女性解放意识与余永泽的传统男权意识,构成了林道静再次走出家门投身社会的主要原由。
一旦林道静的人生视野超越了小家庭而投向了广阔的社会,而且在卢嘉川的引导下认同了反叛社会的意识,那么她与余永泽的观念裂痕便由文化上的性别差异扩展到人生观,乃至以政治思想为核心的整个世界观,最终导致情感堤坝的溃决。但是小说极力掩饰林道静与余永泽最初的文化观的裂痕,化解现代女性意识与传统男权意识的对立,阻塞小说进一步朝着思考时代女性的生存和命运的方向发展。
作品忽略甚至隐匿林余之间的性别意识的差异,无非是为了挖掘历史故事的政治意义。但是从文化价值观到政治思想观并没有必然的逻辑桥梁,谁能肯定在婚姻爱情上认同传统道德观的人就一定不可能成为一个革命者呢?因此作品为了隐匿林余之间的性别观念的差异与突出政治观念差异,着重强调他们人生观的裂痕,以达到道德—政治的转义:余永泽对卢嘉川的嫉妒和对林道静的占有欲,表现了他道德人格上的卑琐和自私;余永泽对魏三大伯的吝啬,不但体现了他的虚伪冷酷,而且隐喻了他与林道静的潜在的阶级分歧,契合中国读者的传统伦理—政治的期待视界。小说对余永泽世俗的“资产阶级人生观”的批判,为林道静再一次出走提供了政治意义上的合理性,也延宕了林道静的青春认同期,从而有效地指证了青年知识分子步入集体主义的必然性和艰难性。
从杨沫原生态的家庭事件到林道静的故事,从女性意识到政治意识,我们可以得到三种启示:第一,历史题材小说的所谓真实性,首要的不在于小说中的故事是否完全由过去的实存事实构成,而在于叙事者对过去生活的意义把握。第二,一种原生态的历史事件原本潜藏着多重语义的可能性,具有多重的叙事发展的方向,每一种叙事都是多种选择中的一种,这就决定了历史叙事的文本特质。第三,历史叙事不单是将过去的体验组织成形,同时也是一种赋予形式的过程,而且叙事一旦成形便或多或少地具备意识形态的功能。
个人的生命具有独一无二性,如果生命的独特性变成历史法则的装饰,而且仅仅为惟一法则的表征,如《青春之歌》中知识分子改造的法则,那么个人原生态生活中的张力、神秘就统统被排斥为偶然,可能的深在意义也就无从发掘,其必然结果便是作为认识人类、社会和自我之手段的真正意义的故事难于自由生长,“十七年”的中国文学日渐枯萎直至荒芜的内在原由不就在于此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