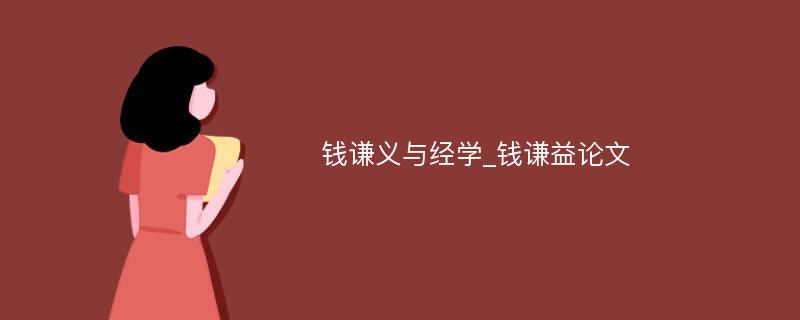
钱谦益和经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学论文,钱谦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本文认为钱谦益既是经学唱导者,又是异端思潮鼓吹者。他反对理学,为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批判理学思潮的发起开辟道路,显示出“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而以复古为其职志者也”的清学特征。
关键词 钱谦益 理学 经学 王学 异端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里说:“清学自当以经学为中坚。”它肇始于明代中叶,随着理学的衰微,面对心性空谈和八股文为害,首先有归有光倡导“通经汲古”。他说:“圣人之道,其迹载于六经”,“六经之言,何其简而易也。不能平心以求之,而别求讲说,别求功效,无怪乎言语之支而蹊径旁出也。”(《震川先生集·示徐生书》)对理学家的空言讲道,抛开儒学经典,主张以讲经取代,说:“汉儒谓之讲经,而今世谓之讲道,夫能明于圣人之经,斯道明矣。道亦何容讲哉!凡今世之人,多纷然异说者,皆起于讲道也。”(同上《送何氏二子序》)大倡“未有舍六艺而可以空言讲道者”(同上《送计博士序》)。接着,钱谦益继承归氏学说,以经学为实学,反对理学和八股,提出治经宗汉的明确主张,和清初批判理学的思潮相融合,汇为学以经世的宏大学术潮流衣被后世。追源溯流,清初经学的倡导,钱谦益也是开其端者。
明代理学泛滥,汉唐经学衰落。《明史·儒林传》说:“有明诸儒,衍伊洛之绪,采性命之奥旨,锱铢或爽,遂启歧途,袭缪成讹,指归弥远。至于专门经训,授受源流,则二百七十余年间,未闻以此名家者。”究其原因,明初提倡程朱理学,创立八股取土制度,颁朱注《四书》和宋元人注《五经》于天下,作为士子学习的规定内容和科举取士的依据,朱学取得独尊地位,“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明史·儒林传》)一般士子,为了利禄功名,争相奔趋,汉唐章句之学,逐渐无人问津,置之高阁。阳明心学兴起,欲通过“正心”挽救世道人心,给僵化的理学注入生气,吸引了社会信仰,一时取代朱子地位,“学其学者遍天下”,迅速风靡朝野,在嘉靖、隆庆以后的百余年间,“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黄宗羲《答恽仲升论子刘子节要书》)王阳明以“吾心”而不以孔子和经书为是非标准的主张,为某些进步思想家反对圣贤偶象和礼教束缚的“异端”提供思想资料。他极力宣扬精神理性的作用,补救朱学支离繁琐、寻章摘句之弊,把儒学推到一个新的阶段。在经历朱学的一段统治后,阳明心学的出现,确因其简易直接、开广活泼而使人们心目俱醒。但是,阳明心学否认客观世界的实在性和人类认识世界的必要性,认为只要“一觉”“一悟”,便可无所不知,成为圣人,为其后学的虚无主义和空谈之风的泛滥打开闸门,变成“开误后学,迄今祸尚未艾”的渊薮。心学日益走向空虚、贫乏、简陋的绝境。当内忧外患纷至沓来,社会危机日益加深,面对现实,总结过去,探索未来,使有识之士发现,心性之学的空谈并不能救世拯民,改变国弱民贫局面,必须返实去虚,以有用之“实”学取代无用之空谈,转移风气,挽救世道人心。实学的倡导者,从学术源流看,或宗法程朱,或师承陆王,都程度不同的否定自我,反戈一击,以实学之精神,或修正,或扬弃,虽然还未完全摆脱朱陆王的思想影响,但在本质上却是与其对立的新思潮,又因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要求相结合,还带有早期启蒙的思想成分。
钱谦益生当晚明清初,亲自编辑整理《震川先生文集》,他说:“往余笃好震川先生之文,与先生之孙昌世,访求遗集,参读是正,始有成编。”经过他的推崇表扬,“启、祯之交,海内望祀先生,如五纬在天,芒寒色正,其端亦自余发之。”(《有学集·新刻震川先生文集序》)是归有光学术主张和古文实践的后先呼应者。他上承归氏的倡导经学,提出“讲求实学,由经术以达于世务”,去虚就实,经世致用。始以穷经学古,终以通晓实用,针对明代学术之失,首先评击俗学弊病,转移明人的学术视野和社会风尚。什么是俗学?他说:
夫今世学者,师法之不古,盖已久矣。经义之弊,流而为帖恬;道学之弊;流而为语录。是二者,源流不同,皆所谓俗学也。俗学之弊,能使人穷经而不知经,学古而不知古,穷老尽气,盘旋于章句占毕之中,此南宋以来之通弊也。(《初学集·赠别方子玄进士序》)
他认为道学(按:指程朱理学)和八股文是俗学。道学流为语录,束书而事空谈;经义变为八股,成了利禄工具。清谈心性,酿成支配整个学术界的空疏虚妄之风;八股时文,造就一批除举业外百事不问的陋劣之士。故“自唐宋以来”,“为古学之蠹者有两端焉,曰制科之习比于俚,道学之习比于腐,斯二者皆俗学也。”(《初学集·答唐汝谔论文书》)俗学的“俚”和“腐”,自然是败坏学术风气的根源,导致社稷倾圯的祸首。他说:
经学之熄也,降而为经义;道学之偷也,流而为俗学。胥天下不知穷经学古,而冥行摘填,以狂瞽相师。驯至于今,辁才小儒,敢于嗤点六经,訾毁三传,非圣无法,先王所必诛不以听者,而流俗以为固然。生心而害政,作政而害事,学术蛊坏,世道偏颇,而夷狄寇盗之祸,亦相挺而起。(《初学集·新刻十三经注疏序》)
明确表示不承认理学为儒学正统,八股文也非文章正脉,举起反理学和八股的旗帜,与清初批判理学的思潮合流。他既认为“此南宋以来之通弊”,将矛头指向朱子为代的濂洛之学,指责程朱理学离经讲道,以抽象对话空谈哲学命题,渐至“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抛开读书明理,社会实践,开启虚无主义和不学无术的方便之门,“嗤点六经,訾毁三传”,世道败坏,风气沦丧,农民起义,边患频仍,朱明王朝穷途末路,走向灭亡的边缘。钱谦益确实看到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替修己治人之实学,给国家和社会带来的严重祸害,不提到亡国之罪高度,难于痛陈其弊,引起人们的警觉和高度重视。
振衰起弊,他认为只有“穷经学古”,以经学代替理学。“今诚欲回挽风气,甄别流品,孤撑独树,定千秋不朽之业,则唯有返经而已矣。”(《有学集·答徐巨源书》)“六经”既是文化的“原典”,又是传统政治合法性的依据,抛开儒学正统和孔孟经典,沉溺于理学家的语录,是学不知本,数典忘祖。唯有先河后海、正本清源,才能鄙弃俗学走上博稽经史的治学之路,故须求“六经”而务本原之学,在经学中谈义理,“以达于世务”的掌握。要学返其本,就必须“以汉人为宗主”,治经复汉,才是“正经学”的可靠途径:
六经之学,渊源于两汉,大备于唐宋元初。其固而失通,繁而寡要,诚亦有之,然其训诂皆原本先民,而微言大义,去圣贤之门犹未远也。学者之治经也,必以汉人为宗主,如杜预所谓原始要终。寻其枝叶,究其所穷,优而柔之,餍而饫之,涣然冰释,怡然理顺,然后抉摘异同,疏通凝滞。汉不足求之于唐,唐不足求之于宋,唐宋皆不足,然后求之近代。庶几圣贤之仞可窥,儒先之钤键可得也。(《初学集·与卓去病论经学书》)
汉儒学问“有物”“有脊”,内容充实,虽然章句琐碎,但依经典注疏,发挥圣人之言,未离圣贤之门,并重视社会人生,强调诗乐六艺的教化功能。而以思辨自诩的理学,空言说经,离开原著,随心所欲地解释发挥,变成高头讲章,势必导致汪洋恣肆,不可收束,到了明代,“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事游谈,更滋流弊。”(黄宗羲语,见《清代七百名人传》)甚至落入“不学不虑”、“不思不勉”的泥淖。所以钱谦益强调,“诚欲正人心,必自返经始;诚欲返经,必自正经始”,也就是以汉唐经学为源头,穷经考古,学有本源。这种复兴经学的主张,和经世思潮的时代呼声相结合,便开启实学思想中通经致用的新风气,是清初学术的基本特征之一。他对宋儒讲经的否定,视道学为俗学,标志着与理学的分道扬镳,毫无疑问,具有时代的进步意义。他不遗余力地复兴经学,肯定汉唐注疏,贯穿在自己的学术思想之中。如《初学集·苏州府重修学志序》:
古之学者,九经以为经,注疏以为纬,专门名家,各仞师说,必求其淹通服习而后已焉。经术既熟,然后从事子史典志之学,泛览博采,皆还而中其章程,隐其绳墨。于是儒者之道大备,而后胥出而为名卿材大夫,以效国家之用。并概括为“由经术以达于业务”的实学口号:
古之学者,必有师承,颛门服习,由经术以达于世务,画丘沟深,各有所指授而不乱。自汉唐以降,莫不皆然。胜国之季,浙河东有三大儒,曰黄文献洹、柳待制贯、吴山长莱,以其学授于金华宋文献公。以故金华之学,闳中肆外,独盛于国初。金华既没,胜国儒者之学,遂无传焉。嘉靖中,荆州唐先生起于毗陵,旁搜远绍,其书满家。自经史古今,以至于礼乐兵刑阳阳律历勾股测望,无所不贯穿。荆川之旨要,虽与金华稍异,其讲求实学,繇经术以达于世务则一也。(《初学集·常熟县教谕武进白君遗爱记》)
这种以倡导经学为中心的经世致用的思想,是清初学术的主干,它包括经、史、子、集,性理天道,天文历算,地理沿革和释道经籍在内的诸多学术领域,从钱谦益批判“陈腐于理学”、“肤陋于应举”开始,中经明清易代顾炎武、黄宗羲等人著述救世,期于“明学术,正人心”,到讲求“当世之务”的经世实学,去虚务实,归朴返真,划出一条明清之际学术发展的轨迹,为我国古代学术发展的重要阶段,也是近代之前古代学术发展的峰巅之一。虽然,实学以经学为主,内容和范围没有脱离儒家的经典和标准,重视儒家“经义”的书本知识,但它到后来衍化为清中叶乾嘉朴学的考据方法。在内容上,以“修己治人”或“有益于社会”的有用之学,批判理学和心学的“明心见性”、“致良知”的脱离实际之虚学,是传统学术思想的反思和总结,开辟了通向近代学术发展的桥梁。梁启超曾把它比作欧洲的“文艺复兴”。也就是说,“通经汲古”的学术潮流,将中国古代学术推向批判和清算理学的高度,应该是中世纪时期黑暗中的一线光辉。更不用说还有清初学术,是宋明理学向乾嘉汉学转换的一个不可缺少的中介,“于晚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力焉”(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话》)的意义了。清人江藩有《汉学师承记》,他说:“有明一代,囿有性理,汩于制义,无一人知读古经注疏者。自黎州起而振其颓波,亭林继之,于是承学之士知习古经义矣。”根据上面的分析,应当还有个钱谦益,他在顾、黄之前,继归氏而倡导经学的功劳是不应该埋没的。这也是钱谦益经学思想中极为精粹之处。
钱谦益的“通经汲古”也和东林学派的“尊经重道”一脉相承。清初的学术思想以晚明为先导,是由明末顾宪成、高攀龙为首的东林学人,试图重振没落的理学,成为“一时儒者之宗”开始的。钱谦益身为东林党人,从幼年起就师事顾宪成。他说:“余年十五,从先夫子以见于端文,端文命二子与停、与沐与之游。”(《初学集·顾端文公淑人朱氏墓志铭》)又说:“公初以吏部郎里居,余幼从先夫子省谒,凝尘蔽席,药囊书签,错互几案,秀羸善病人也。已而侍公于讲席,哀衣缓带,息深而视下,醇然有道者也。”(《初学集·顾端文公集序》)政治思想和学术观点自然要受到顾宪成的影响,带有东林学派的学术特征,并为钱谦益学术思想的渊源。
东林学人面对王学“谈良知者盈天下”,儒学经典和圣贤儒像的权威遭到破坏,以及心学本身陷入深刻的危机和困境,主张向笃守孔孟、具有儒学正统色彩的朱学回归,提出“学返其本”的问题,他们明确表示“学孔子而不宗程朱,是望海若而失司南也。”(《明史·高攀龙传》)毫不掩饰地声称“圣学正脉,只以穷理为先。”(《高子遗书·会语》)以读书、讲学、议政方式,参与救国活动,挽救纲纪凌夷,由此将“重经尊道”作为补时救世的良方。《东林会约》说:“尊经云何?经,常道也;孔子表彰六籍,程子表彰四书,凡以昭示往来,维世教,觉人心,为天下留此常道也。”高攀龙甚至认为“六经者,天下之法律也,顺之则生,逆之则死”(同上《程朱里阙亭》)。对儒家经典要奉循恪守,坚定不移,“读一字便体一字,读一句便体一句。心与之神明,身与之印证。”(《东林会约》)企图通过尊经重道,补偏救弊,振兴衰落的理学,在日趋加剧的社会危机里激荡起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潮。顾宪成说:“官辇毂,念头不在君父上;官封疆,念头不在百姓上;至于水间林下,三三两两,相与讲求性命,切磨德义,念头不在世道上,即有他美,君子不齿矣。”(《顾端文公集·小心斋札记》)高攀龙也说:“学者以天下为己任。”(《高子遗书·与李尚辅》)以“复兴正学”、“卫道救时”、提倡实际、反对空疏为主要内容的东林侑派,实际上给距离他们很近的清初启蒙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开了先河,所以黄宗羲修《明儒学案》时,高度赞扬他们“熹宗之时,龟鼎将移,其以血肉撑拒,没渊虞而取坠日者,东林也。”(《明儒学案·东林学案一》)
钱谦益经学思想,受东林学人顾、高的影响和沾沔,传其法嗣而扬其余波者,除东林党人的政治见解相同,在学术上仅限于尊经重学,以救世为己任。他入东林学派而又不为其所囿,受晚明思想解放潮流的薰染和浪漫洪流的洗礼,突破东林学派的樊篱,还有不同的一面。
王学的崛起,完成宋明理学的历史课题,但也“掀翻天地”,“非名教之所能羁络”,逐渐取代了步步推进、格物致知的程朱理学。东林学派深感王学百病交作,流荡不返,“自致良知之宗揭,学者遂认知为性,一切随知流转,张皇恍惚。其以恣情任欲,亦附于作用变化之妙,而迷复久矣。”(《高子遗书·尊闻录序》)“任心而废学”,与佛禅一致,“任空而废行”,则堕入虚学,因此王阳明学说既是禅学,又是虚学,应当否定。但也无法否认心学振聋发聩、震动人心的社会效果:“当士人桎梏于训诂词章之内,骤而闻良知之说,一时心目俱醒,恍若拨云雾而见白日,岂不大快!然而此窍一凿,混沌几亡,往往恁虚空而弄精魂,任自然而藐竞业。陵夷至今,议论益玄,习尚益下,高之放诞而不径,卑之顽钝而无耻。”(《顾端文公集·小心斋札记》)耽心封建文化体系的“混沌”灭亡,遂欲以尊朱抑王,否定王学,挽之使正:“以考亭(按:朱熹)为宗,其弊也拘;以姚江(按:王阳明)为宗,其弊也荡”,“昔孔子论礼之弊而曰与其奢也宁俭,然则论学之弊,亦应曰与其荡也宁拘”。所谓“荡”,指心学导致越出封建纲常规范的“开发有余,收束不足”,故明知“拘者人情所厌”,也要坚持“与其荡也宁拘”,回归朱学,视何心隐、李贽等人为名教罪人,守卫其儒学正统派的立场。
应当看到,王阳明的心学,视“心”为最高的哲学范畴和这个“心”所固有的“良知”,固然还是一个玄虚的精神实体,但它毕竟脱离了儒学正统,动摇孔朱的“圣人”标准,承认反传统的合理性,一新天下耳目。心学、禅宗和市民思潮的碰撞,是晚明社会出现异端思想的动力。这场狂飚式的思想解放对程朱理学和传统观念起了摧毁的作用,并在社会上扬起个性自由、感情解放的风帆。钱谦益顺应时代潮流,突破东林学派的范围,没有和顾宪成、高攀成一起尊朱抑王,反而对王阳明心学和异端人物采取肯定的态度。他说:
自正心诚意之学,陈陈相因,而姚江良知之宗始盛。儒者又或反唇而讥之。良知之言,因于孟子。孟子曰: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分而言之,曰仁义礼智,其实则良知而已矣。夫立乎人之本朝,蝇营狗苟,欺君而卖国者,谋人之军师国邑,偷生事贼,迎降而劝进者,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盖已澌然不可复识矣。其良知之未死者,如月之有魄也,如木之有枿也。质诸梦寐,告诸妻子,未有不淟然汗下,烦宪唏嘘者也。……诚使良知之学,讲之有素,知如是而为人,如是而非人也;知如是而为忠臣孝子,如是而乱臣贼子也;知如是而为圣贤,如是夷狄禽兽也。知汤之必灼也必不赴,知火之必焚也必不蹈,知涂炭之必焦烂也必不坐。如是而士气可立,国耻可振,猋庉脂夜之禅,其可以少解矣。(《初学集·重修维扬书院记》)
他认为王阳明“致良知”出于亚圣孟子“性善说”,和儒家心性学说同宗同源。只要在“一念发动之处”破除“邪念”,正心养性,就会使“孟子之言、药石也;姚江之言,救病之急剂也”,成为一副救世的良药。世人“用良知之学为急剂,号呼惕厉,庶几其有瘳乎?”社会和时代的危机就可解救。钱谦益站在维护封建统治者的立场夸大心学和良知的作用,实际上从中永远找不出解决社会矛盾的药方,但它对心学和良知的首肯,却呼应晚明思想解放的潮流,看到它背离理学、开启心智、激扬叛逆思想的功绩,也就是它构成批判理学的一支同盟军。从客观意义而言,自然不会附合“公之学,程朱之学也;其遇,亦程朱之遇也”的顾宪成,和“龙之学,以朱子为宗”的高攀龙,对阳明心学进行抨击。
特别对王学别传,有明一代怪杰李贽,别有会心,不像顾、高认为晚明出现礼崩乐坏局面,是与王学末流李贽、何心隐等推波助澜有关,顾宪成说:“李贽大抵是人之非,非人之是”,“何心隐辈坐在利欲胶漆盆中,所以能鼓动得人。”(《顾端文公集》卷五)故对他们毒害社会世道和人心,决不能等闲视之。李贽深受心学和禅宗影响,对程朱和一切伪道学猛烈攻击,他和紫柏禅师在当时称作“两大教主”。在他们异端思想带领下,社会发生巨大的动荡和变化,反抗传统观念,鼓吹个性自由,使一批士大夫解除内心桎梏,大胆追求尘世幸福和人间欢乐,对传统人生哲学和生活观念给予蔑视和挑战,晚明社会的叛逆思潮至李贽发展到顶峰。对这样一个著名的异端人物,钱谦益给于热烈赞扬,他说李卓吾“著书,于上下数千年间,别出手眼,而其掊击道学,抉摘情伪,与耿天台往腹,累累万言,胥天下之为伪者,莫不胆张心动,恶其害己,于是咸以为妖为幻,噪而逐之。”他则对其反道学勇敢行为同情赞佩,在《卓吾先生李贽》赞中说:“风骨棱棱,中燠外冷,参求理乘,剔肤见骨,迥绝理路,出语皆刀剑上事,狮子送吼,香象绝河,直可与紫柏老人相上下。”(《列朝诗集小传》闰集)还说:“余少喜读龙湖李秃翁书,以为乐可以歌,悲可以泣,欢可以笑,怒可以骂,非庄非老,不儒不禅,每为抚几击节,盱衡扼腕,思置其人于师友之向。”(《有学集补·松影和尚报恩草序》)怀着虔诚心情向李贽学习,“龙湖一瓣心香宛在,安得从作龄促席贽学而问之。”对统治阶级迫害致李贽冤死的悲剧,表示极大愤慨,他以同情笔墨写李贽“遂夺薙发刀刎颈,两日而死”的悲惨结局。
对顾、高等东林学人严加批评的王学左派代表人物,他也予以袒护,说:
稽良知之弊者,曰泰州之后流而为狂子,为戮民,所谓狂子戮民者,颜山农、何心隐、李卓吾之流也。彼其人皆脱屣身世,芥视权幸,其肯蝇营狗苟,欺君而卖国乎?其肯偷生事贼,迎降而劝进乎?讲良知之学者,沿而下之,则为狂子,为戮民,激而反之,则为忠臣,为义士。视世之公卿大夫,交臂相仍,违心而反面者,其不可同年而语,亦已明矣。(《初学集·重修维扬书院集》)
异端人物表面的越礼任诞,放荡纵欲,掩盖不住内里的愤世嫉俗,不甘颓废,“外表尽管装饰得如何轻视世事,洒脱不凡,内心却更强烈地执着人生,非常痛苦”,晚明狂士有着和魏晋名士同样的心态。钱谦益揭示他们的矛盾心理和内心实质,赞扬其本质是忠诚义士和轻视权幸的品格,实际上和他们后先呼应,支持异端人物的所作所为,站在晚明思想意识的前列,和正统派的东林学人划开了界限。
当然,他也深知王学末流的危害,在《李廷栋神道碑》里说:“世之衰也,世皆好圆而恶方,丰表而啬里,姚江之良知,佐以近世之禅学,往往决潘逾垣,不知顾恤,风俗日以偷,子弟日以坏。”对心学末流与禅学汇合带来世风日下,人欲横流,他的头脑是清醒的,尤其“良知”变成万灵妙药,“空”“无”思想泛滥,不读书,不探讨实际学问,不研究现状,只知清谈,诵语录,参话头,酿成空疏无学的祸害,他是极为痛恨的。但他仍然肯定心学,赞扬李贽等左派人物,看起来似乎相互矛盾,一方面恢复和阐扬六经,兴复古学,一方面又出朱入王,肯定良知和异端人物。其实,他也是想将新的作法与传统接轨,利用传统酿成革新的空气,如近代西方人重新发现古希腊而掀起“文艺复兴”运动一样,在既返本而又开新里,显示历史的自觉,阐扬六经,以传统作号召,纠正俗学的“腐”“俚”之弊,为后来的实学思潮披荆斩棘;崇仰异端,背离理学,跟上晚明浪漫洪流的步伐,亦可谓历史的光亮,它们都在反道学上交汇,成为清代学术的前导。
由上看,钱谦益既是经学倡导者,又是异端思潮鼓吹者,学术思想出入于东林学派,不为其牢笼,黄宗羲修《明儒学案·东林学案》未列其姓名,这是极为正确的。他反对理学,欲以经学代替理学,为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李颙等人批判理学思潮的兴起开辟道路,显示“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而以复古为其职志者也”(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的清学特征,逐步演变为有清一代学术思想而深深影响着文学的发展,虽然响应王学,赞扬异端,与顾炎武、王夫之异趋,而能与黄宗羲接轨,但因它带有晚明社会浪漫洪流和解放思潮的精神意向,又能与反程朱理学要求相呼应,是历史之光在钱谦益思想中的闪现,还是值得肯定和引起注意的问题。
标签:钱谦益论文; 心学论文; 儒家论文; 经学论文; 读书论文; 社会思潮论文; 国学论文; 黄宗羲论文; 李贽论文; 理学论文; 东林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