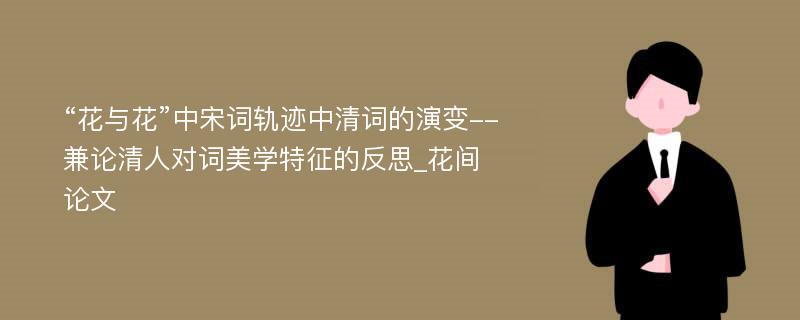
清词在《花间》两宋词之轨迹上的演化——兼论清人对于词之美感特质的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人论文,宋词论文,美感论文,特质论文,轨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清词是非常奇妙的。王国维曾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①唐代以后,宋朝、明、清等朝当然也有诗,可是我认为唐诗后面有宋诗、明诗、清诗的情况,与唐五代、两宋词之后之有清词,是截然不同的。唐诗和宋、明、清诗之间演化继承的关系有一个理性的认知和反思。宋朝的诗人要在唐诗的笼罩之下突破出去,形成一个自己的风格,所以有人说:“宋人不知诗而强作诗。”因为诗是重情的,可是宋人注重理性的思维,这是不同的。明朝的前后七子讲究复古。至于清诗中,则既有尊唐的一派,也有尊宋的一派。不管诗歌在文学史上经过了多么复杂而长久的演进,我以为其中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宋诗对唐诗有所转变,是有反省、有自觉的。宋代诗人对于唐诗的好处有清清楚楚的认知,他们有心要破除唐诗的约束,要从唐诗的成就之中突破出去,也就是西方说的“影响的焦虑”(the anxiety of influence)。而明朝人模仿唐诗,觉得唐诗很了不起,也是对唐诗的好处有清楚的认知。清朝的诗人不管是尊唐也好,尊宋也好,他们都是对于唐诗和宋诗的好处先有了清楚的认知,然后才发展下去的。而我觉得清词真的是非常奇妙,这是因为,词这种文学形式,虽然经历了晚唐五代、两宋的演进,可是由于这种文学体式的微妙,并不是那么轻易就能让大家认识和了解。晚唐和两宋词的演进是在自然之中,在模糊影响之中,在并没有更多反省之中,自然地演化过来的。而唐五代、两宋词在清代的演化,有着第二次的反省,或者说“第二次握手”,有一个重新认识的过程。清词的整个轨迹,并没有独出异军,另立旗帜,它的演化轨迹是和晚唐、两宋的演化轨迹相符合的,但不是重复,而是遵循着这个轨迹有了突破、有了变化。所以我认为清词的发展是在《花间》、两宋词的轨迹上的演化。
在这样的演化之中,清代词人才逐渐反省,思考词这种特殊的文学体式,真正的特殊之处是在哪里,为什么经过唐五代、两宋这么长久的自然演化,居然没有在理性的思考上清楚地认识到词的真正美感特质和意义?这是因为词的美感特质真是难以了解、难以认识,即使认识了也真是难以说明。那为什么中国的词会处于这么微妙的处境中?我以为这是与词起源的特殊环境分不开的。我们说诗是言志的,文是载道的,诗文体裁的形成和演进是在作者的主体意识清楚的认识之下发生和进行的。可是词在早期,它的兴起,不过是给歌女唱的歌词。说到词的演进,我特别提出来是《花间》、两宋词的轨迹上的演进,因为早期的敦煌曲子词只是民间流行的歌曲,就像任二北先生编辑的敦煌曲子词,内容是非常杂乱、非常众多的。只要当时会唱流行歌曲的人,任何行业都可以随时写一首曲子。而且那是在市井之间流行的曲子,文辞不够典雅。这也是为什么敦煌曲子词后代一直没有流行、没有刊印,一直到晚清的敦煌石窟里出现了,才被大家所认识的原因。而我们所说的词的演进,是以最早的一本编辑出来的集子《花间集》为开始的。值得注意的是,《花间集》编纂的是“诗客曲子词”。词是从《花间集》才开始流行的,而《花间集》是文人、诗客创作的。而且《花间集》的序文里面还特别提出编选这些诗客曲子词的理由:“庶使西园英哲,用资羽盖之欢;南国婵娟,休唱莲舟之引。”②编选的目的是为使得诗人文士、“西园英哲,用资羽盖之欢”的。而这些词是交给谁去唱的?是“南国婵娟,休唱莲舟之引”。所以小词的开始,一定要从《花间》讲起,文人开始为这新兴的歌曲填写歌词,当时就有一个成见:这些歌词是“用资羽盖之欢”的,是给歌女去唱的。为什么从晚唐五代到两宋一直对词的美感特质没有清楚的反省和认知,这就与最初的起源有密切的关系。当词产生以后,虽然有不少作者也插手写词,可是早期的词学没有真正认识到词的美感的真正意义和价值,这些词人处在困惑之中:到底是否应该为流行歌词写这种美女和爱情的小词呢?而我们中国一向就缺少理论的思辨,缺少理论化的论著,所以传统的文学批评,常常是散见于笔记、小说、序跋、诗话、词话中,都是很零散的。宋人最早的词学,就是从那非正式的笔记之中表现出来的,而表现的内容则完全是困惑。
宋人像王安石做了宰相,他见晏殊做宰相写了很多小词,就问:“为宰相而作小词,可乎?”③宋人笔记上还记载,黄山谷喜欢写小词,法云秀就说:“诗多作无害,艳歌小词可罢之。”④中国人从春秋战国的时代,从孔子的《论语》开始,就有了士当“以天下为己任”的观念。所以中国的士人,一直到晚清,读书人不读书则已,一读书就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观念存在心里了。可当这些士人要写听歌看舞的美女爱情的小词时,人们就感觉到困惑,所以法云秀劝黄山谷不要作小词,黄山谷也回答得很妙,他说:“空中语耳。”他认为,那是空中语,和诗文是不同的。诗文是言志载道的,那是我的主体意识(consciousness),是自己的意识活动,是写自己的情意,可是小词就是给歌女填的歌词,所以是空中语,这是莫须有的事情,与我作者是全不相干。蒲传正曾指出晏殊写的歌词:“年少抛人容易去”,是写美女和爱情。晏几道就替自己的父亲辩护,说“年少抛人容易去”,不是写的少年郎。“绿杨芳草长亭路,年少抛人容易去”,明明白白是男女爱情的赠别之词,可是晏小山要强辩,说“少年”是用白居易的诗,说的是“欲留年少待富贵,富贵不来年少去”,所以“年少”是少年的光阴。由此可见,宋人完全是在困惑之中的。一直到南宋的陆放翁还说,五代的战乱流离,而士大夫居然流连在歌酒之中。而且他说我少年时不懂事,偶然也写小词,“长而悔之”。但其实他很喜欢词,所以他又辩护:我既然也写了,姑且把它保存下来吧。
这一点也反映在李清照的《词论》中。李清照的《词论》当然并没有一本专著,也是保存于宋人的笔记《苕溪渔隐丛话》中。李清照首先提出李八郎擅歌,词是配合音乐来歌唱的曲子词,她的词论主要重在这一方面。当然李清照的成就不止于如此,李清照晚年经历了国破家亡的离乱之后,写出来不少好词。但是尽管如此,她却从来不把战乱明白地写到词里面去,她诗里面可以写“木兰横戈好女子,老矣不复志千里”⑤,“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⑥。她把激昂慷慨的破国亡家的悲慨只写在诗里面,不肯写在词里边。而且在《词论》中,她认为像苏东坡、欧阳修这些人写的词,根本不是词,只是句读不整齐的诗。所以她说“词别是一家”,认为词是配合乐曲来歌唱的歌词,她不以为破国亡家的悲慨可以写到词里边。他们有这样一种认知。
但苏东坡出现了,苏东坡曾经写过“老夫聊发少年狂”这样豪放的词,当时他给他的朋友鲜于子骏写了一封信说:“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⑦就指的是他《密州出猎》的这首小词。柳七郎指的是柳永,在一般的观念中认为他是淫靡的,“暖酥消,腻云嚲,终日厌厌倦梳裹。无那!恨薄情一去,音书无个。”⑧他的词都是写男女情爱,歌妓酒女的,而现在苏东坡不写柳永这样的内容,写出了像《密州出猎》这样慷慨激昂的作品。李清照那个时代已经是经历了北宋靖康之难到了南宋,她仍然不承认这样的词,她说那是“句读不葺之诗”。而且后来宋人的笔记也记载了,像苏东坡的“大江东去”只能是关西大汉拿着铁绰板来唱,而小词是应该十七八岁的妙龄少女,拿着红牙板,去唱“晓风残月”的。
词人对词的美感究竟如何认识,我认为他们的困惑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当歌词之词出现时他们就困惑了:我们要不要写这样的词;其后第二个时期,当诗化之词的东坡词出现了,他们又困惑了:这个不是词,这是句读不葺之诗,词是不能够这样去写的。而且除了这个观念以外,在词的体裁方面,确实跟诗有所不同,诗当然也有不同的体式,但是一般说来,总是以五言七言为主,不管是五古、七古、五律、七律,它基本上是以五个字、七个字为主要句法的。我现在还要提到,我认为中国诗有一个非常奇妙的特色,那是与我们的语言分不开的。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文学的特殊美感特质一定是受了我们的语言的影响,我们的语言一个最大的特色:单音独体。“天”、“地”、“春”、“夏”,这是单音;每一个字占一个方块,这是独体。“花”的英文flower,它是拼音,有很多的变化。而这种单音独体的语言系统在文学上起了很大的影响和作用。不是有意,也没有理论,而是天生如此。英文flower,本身就有一个起伏的变化,而中国字“春”、“夏”、“花”、“草”,一个字就很单调,当然中国古代的《诗经》也都可以弦诵,可以配合音乐去歌唱,可是自从中国诗歌脱离了音乐,而变成了“徒诗”(徒诗就是不配合音乐的诗歌),我们就开始有了吟诵。吟诵的起源其实也非常早,《周礼·春官》曾记载说,卿士大夫贵族的子弟到了入学的年龄来学习,教他们“兴道讽诵言语”⑨。“兴道讽诵言语”在历来的注疏里面,有很复杂的解释,一直到朱自清先生讲的《诗言志辨》中还谈到:《周礼》上所说的“兴道讽诵言语”,这个教学法到底是如何?他还觉得弄不清楚。其实我以为,参考古人的注疏,“兴”(阴平)是动词,当它作为名词就读“兴”(去声)。所以国子入学第一就要学诗,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连《牡丹亭》的春香闹学,第一篇还背“关关雎鸠”。学诗首先要学诗里面的“兴”,就是诗歌是带着兴发感动的作用的。我一讲诗词,就先讲兴发感动的作用,这是无可奈何的,这是我这个浅薄的人的一点狭窄的体会,而且是经过我多年与西方比较之后的所得。西方诗歌的缘起,是史诗(epic),是戏剧(drama)。史诗戏剧是对于外在事象的叙写,它所注意的是叙写方式。所以西方的文学理论,对于诗歌表现的技巧和方式特别注意。因为对于史诗或者戏剧,表现的手法才是重要的。所以他们轻视我们,认为你们中国人总说,一个人品格伟大,诗就伟大,可是一个人伟大、忠君爱国,并不见得就能写出好诗来。当然杜甫的诗是好诗,所以我的两个朋友梅祖麟、高友工,因为看了我写的《秋兴八首集说》,他们就用语言学来分析,认为杜甫诗之所以好是他的语言好,不在他的忠君爱国。所以中国的诗之妙处,外国要从语言学,从外表,从技巧,从手法来分析;而中国是讲兴发感动的,只说这个人,如杜甫是“忠爱缠绵”。但是“忠爱缠绵”不代表他的诗就好,中国真正的好诗是要有“忠爱缠绵”的内涵,并能用语言把“忠爱缠绵”的内涵恰如其分地表现出来。所以中国诗一定注重的是兴发感动,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且不管是哪一派的诗家,不管是严沧浪的“兴趣”、王渔洋的“神韵”,主要重视的都是诗歌本身兴发感动的作用,所以诗人的本质是重要的,你有了好的东西如何表现。而词不是诗人言志的,不能够用读诗的方法来欣赏和评述词。所以当词一出现,这些诗人文士就感到困惑了,不知道什么样的作品才是好词。词之所以微妙,就因为它是无心的,就是给歌女填一首歌词。我们常常说:“观人于揖让,不若观人于游戏。”我们大庭广众之下总要端庄、有礼法,表现得很好。揖让进退是外表,是在大众面前有意识做的一种公开的展示。但是在游戏之间,跟人家赌钱一输钱就急了,就看到他的本性如何了。小词所以非常微妙,就在于不是言志载道,而是游戏笔墨,像黄山谷说的“空中语耳”,就是随便填写。可是我们为什么说“观人于揖让,不若观人于游戏”呢?因为揖让之间总有造作、虚伪、伪装的成分,是有心要去做的。但是小词却没有,就是游戏笔墨,这就能把一个人最深隐的、真正的本质在无心之中表现出来了。小词的妙处怎么样去衡量?小词的妙处就在于通过它难以批评、难以掌握的游戏笔墨去探索最深隐最微妙的本质是什么,而本质常常是超出于外表之外的,而且本质也果然有高下的不同,这是必然如此的。
小词更奇妙的一点就是在它无心表现本质的时候,有两个很微妙的因素结合进来了,这是我以前在探讨《花间》词的女性叙写的时候曾经谈到过的:一个是“双重性别”的特色。要知道小词“庶使西园英哲,用资羽盖之欢”,都是文人、诗人,都是供男子在歌舞宴乐的场合娱乐的。在传统社会中,没有一个良家女子敢公开参加歌筵酒席的聚会,所有作者都是男子。而男子给歌女填写歌词,要用歌女的口吻去填写,要用女性的语言,来描写女性的形象和情思,这样就形成了“双重性别”。他的显意识是给歌女填写歌词,是写女性的情思、女性的生活;可是他自己毕竟是男子,所以就在无心之中把男子的隐意识(subconsciousness/unconsciousness)流露到里面去了,这是使小词微妙起来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双重的语境”。像韦庄所写的《菩萨蛮》:“红楼别夜堪惆怅,香灯半卷流苏帐。残月出门时,美人和泪辞。”⑩“洛阳城里春光好,洛阳才子他乡老。柳暗魏王堤,此时心转迷。桃花春水渌,水上鸳鸯浴。凝恨对残晖,忆君君不知。”(11)表面上是写他和所爱的女子离别了,他回不去了。而以韦庄的身世来讲,中年经历了黄巢之乱,后来唐朝被朱温篡夺了,他留在四川,四川前蜀的王建对他非常好,开国的制度都出自韦庄之手,“珍重主人心,酒深情亦深”,这个时候韦庄的词不是双重性别了,他是以男子的口吻写的。男子用女子的口吻写,是双重性别,韦庄是男子就用男子的口吻,不再是“双重性别”,而却有了一种“双重语境”的微妙作用。为什么说韦庄有双重的语言语境?因为他的小环境在前蜀,当时是偏安的。所以小环境还是填写歌词:“珍重主人心,酒深情亦深。须愁春漏短,莫诉金杯满。”“此度见花枝,白头誓不归。”(12)还是歌舞、宴乐、饮酒、花枝,可是他是身经了乱离的亡国之痛,而且北方逐渐强大,连南唐的中主、后主也包括在内,为什么王国维说南唐中主的《摊破浣溪沙》:“菡萏香销翠叶残”,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13)中主的这首词不过是写给一个乐人王感化去歌唱的歌词,写的就是闺中思妇的感情,有什么“众芳芜秽,美人迟暮”感?“众芳芜秽,美人迟暮”,是出自屈原的《离骚》,《离骚》是说当时楚国在秦国、齐国两大强国之间的一种忧虑。所以南唐的中主,尽管他在偏安的小国,作为一国的君主,也歌舞宴乐,但是他对那种倾危的形势、那种危险,不是完全没有感觉的,所以说是“双重语境”。眼前的语境,不管是在西蜀还是在南唐,都可以歌舞宴乐,可是身外的整个的中国大环境的战乱流离,那种危亡不能自保,在他的下意识无意识之间流露出来了。所以小词就很微妙,在你无心之中把你内心深处最幽微的、最隐约的,甚至于你自己都不知道的东西居然就表现出来了。
除却“双重性别”和“双重语境”,到北宋天下统一的时候,已经可以歌舞宴乐,而且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奖励做官的士大夫去歌舞宴乐。那时候身居高位的,不管是晏殊也好,欧阳修也好,他们所写的小词就更加微妙了,就像我说的,“观人于揖让,不若观人于游戏”,你不要板起面孔来言志载道,就在你无心之中写的那些歌舞宴乐的小词中,就把一个人最基本的心性表现出来了,所以晏殊说:“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14)欧阳修说:“直须看尽洛城花,始共东风容易别。”(15)都是写饮酒、伤春、看花,可是就是他们两个人的最深隐的心性,在游戏的笔墨之中就表现出来了。晏殊身为宰相,他有一种理性的持守和思考,“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在句语上也同样非常微妙,这是一个上下相对的联语,上联和下联之间有一种呼唤的照应,他在理性上说是“满目山河空念远”,一个“空”字,是很理性的认知,你“念远”远人就回来了吗?你“念远”就去到远方了吗?而“落花风雨更伤春”,这是两重的悲哀,我怀念远人,和远人不能相见,这是我第一层悲哀;落花风雨、春去难留,这是我的第二层悲哀,所以“落花风雨”就“更伤春”,可是他一个“空”字就有一种反省,“念远”是空的,“伤春”也是空的,所以他说“不如怜取眼前人”,你就掌握现在,今天能做什么,就尽量掌握今天就好了,所以晏殊有一种理性的反省和节制。而欧阳修沉着之中有豪放之致,是“直须看尽洛城花,始共东风容易别。”花是必然会谢的,人不管是生离也好,死别也好,总是会离开的。但是就在这一刻你把洛阳的花,真的都赏遍了,你既对得住洛阳花,你也对得起你自己了。他们本身的心性、做人的修养、态度都在无心之中流露出来了。当时的词人并没有真正反省认识到词这样微妙的好处,仍然把它看作是听歌看舞、伤春怨别的,所以李清照的时代还认为苏东坡、欧阳修所作的词都是“句读不葺”的小诗,她认为音乐的特性才是词里边重要的。这一种词的困惑一直到了豪放词出现。
豪放词的出现,这是第二次的转变,由歌辞之词到了诗化之词的东坡,再到豪放之词,而豪放之词就是从诗化之词发展出来的。有了苏东坡,所以才有了辛稼轩,可是豪放的结果有时候就变成叫嚣。陈同甫有一首很有名的词《水调歌头》:“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16)陈廷焯就批评说,这可以作为“中兴露布”(17),号召我们抗敌、恢复国土,但不是好词。这就是豪放的结果,流于叫嚣。柳永在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功绩,他把小词用长调拓展出来了。可是他的拓展的结果却有了流弊。温庭筠“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18),引起张惠言非常丰富的联想,到了柳永变成“暖酥消,腻云嚲,终日厌厌倦梳裹”(19),同样是“懒起画蛾眉”,却失去了那种丰富、深厚的联想,所以就变成浅俗、淫靡了。因为柳永的俗词和粗率叫嚣的豪放词,于是中国的词有了第三种困惑。一直到南宋末年,有了王沂孙、吴梦窗这些人的出现,而最早的发源的其实是周邦彦。因为写婉约的爱情词,小令含蓄蕴藉,但一铺陈,所写的婉约爱情词就变成淫靡了;一铺陈,所写的豪放词,慷慨的就又变成叫嚣了。为什么豪放的词激扬慷慨居然会变成叫嚣?这还要牵扯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小词的语言的性质。诗是五言七言,是齐言的形式,所以在《古今词论》中,王又华就引用毛先舒的话,认为长篇的歌行可以如同“骏马蓦坡”(20),“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21)管他说什么了,气势滔滔滚滚,就先给你一个美感。可是小词是长短句,而且常常有不合于诗的句法。诗的停顿都是二三或者二二三,这样的停顿,我们叫它单的格式的停顿;小词不但有四个字的、六个字的句子,而且即使是五个字的句子,有时也不是二三的停顿。周邦彦的《解连环》:“怨怀无托。嗟情人断绝,信音辽邈。纵妙手、能解连环,似风散雨收,雾轻云薄。”(22)它中间有很多五个字的句子,但不是二三的停顿,而是一四的停顿。这种句法,我们叫它双式的句法。双式的句法近于散文,如果你长篇地铺陈,都是双式的句法,有时就不免散文化,散文化的结果就变成了婉约词淫靡、豪放词叫嚣。怎么样来挽救这样的一个缺点呢?当然,东坡和稼轩的好词虽然是豪放,但是它有它的特色。稼轩尽管是豪放词,但是他的感情是沉郁顿挫的,他有多少的收复自己故乡的豪情壮志?“壮岁旌旗拥万夫”,他自己以为他渡江南来,几年之间就可以收复他的故乡,但是他没有,他在南宋的四十年,有二十年放废家居,有多少的抑郁痛苦?而他没有办法表现出来,所以稼轩的词,表面上写得非常豪放:“举头西北浮云,倚天万里须长剑。人言此地,夜深长见,斗牛光焰。”可是后面却说:“待燃犀下看”,又恐怕“风雷怒、鱼龙惨”。多少抑郁,多少低徊!“峡束沧江对起,过危楼,欲飞还敛。”(23)有多少豪情壮志,都压下去了,其中有多少低徊郁积?东坡的词:“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他写得多么样的豪放!可后面就说“正暮山好处,空翠烟霏。算诗人相得,如我与君稀。约他年、东还海道,愿谢公、雅志莫相违。西州路,不应回首,为我沾衣。”(24)又有多少婉转低徊!所以豪放的词真要写得好,像东坡的好词,稼轩的好词,是因为他的本质方面,有一种抑郁低徊的情感。可是所有《花间》、两宋词的好处,一直到南宋的末年,大家都没有清楚地认知,所以南宋末期关于词的著作,像《乐府指迷》,它注重的是什么?它注重的是说“桃”不可以直接说“桃”,要用代字。王国维就反对,认为真正有好的语言,“意足则不暇代,语妙则不必代”,为什么要用代字?为什么居然提出来用代字这么笨的方法?就是因为长调的婉约的词易流于淫靡,豪放的词易流于叫嚣,而在词而言一定是要有深沉、婉转低徊的意思,才是真正的好词。可是一直到南宋,他们都没有真正的反省思索和认知。
清代的词是继承着《花间》、两宋词轨迹上的演化。清词为什么有它的复兴或者说中兴,而不同于宋诗之对于唐诗?宋诗对于唐诗是清清楚楚知道唐诗的好处,不管明清是继承它也好,宋诗是反对它、破坏它也好,都有清楚的认知。可是五代两宋词发展下来,一直到最后,还没有真正掌握到那词的好处。所以“明人不知词而强作词”,因为明朝人对于词的幽约怨悱的深隐的好处,没有认知。所以他们只从表面上来看,表面上词也是配合音乐来歌唱的歌曲,就是写美女跟爱情,而且明朝受了元明以来的曲的影响,写得比较俗滥,所以大家就认为明词不好。一直到清朝初年,清初的作者,他们词集中都有许多写美女和爱情的词,其中有的是深刻的,有的也还是肤浅的,因为他们还没有清楚的认知。可是毕竟在明清之际,经过了一场国破家亡的乱离,所以叶恭绰在《广箧中词序》中就说:“丧乱之余,家国文物之感,蕴发无端。”(25)就以陈子龙等云间三子来说:陈子龙殉节死难了;李雯不得已而投降,李雯的心中有多少愧悔,多少惭愧?所以像李雯所写的《风流子》:“谁教春去也。人间恨、何处问斜阳。”(26)写得如此悲哀,而我们说“家国文物之感”,每个人遭遇不同,陈子龙是殉节死难的,李雯是屈辱的,吴伟业何尝不是后来也降清了?可是他自己觉得他是不得已而降清的,所以吴梅村终身在他的诗词里要表现一份不得已的悔恨,但是他跟李雯的悔恨不同。李雯是真正自己惭愧、懊悔,如此之悲屈,而吴伟业主要的是要表白他自己,“我本淮王旧鸡犬,不随仙去落人间”(27),他写的《贺新郎》说自己是“耿耿胸中热血”(28)。所以同样是遭遇了乱离,只是每个人的本性、遭遇、反应不同,所以从清朝初年一开始就表现出分途奔放,各尽所长,表现出了多彩多姿,这是明清易代之变造成的一个现象。
这种多彩多姿的现象,就使得词人对于词的美感有了深一步的反省,所以我的题目说,是在轨迹上的演化及对词之美感特质的反思。为什么说是在词的轨迹上的演化呢?因为对于《花间》、两宋没有清楚认知的人,走一遍路还不熟悉,再走一遍慢慢地就有了反省,第二遍又不是一步一步按照原来的足迹走过来的,是在那个轨迹之中有了演变,有了转化,而且明清的易代加强了他们这种反省思辨的意识。当然,我们说,就几个大家重要的词论来说,陈维崧所说“为经为史,曰诗曰词”,“穴幽出险以厉其思,海涵地负以博其气”(29),凡是诗文可以写的,我词里面有什么不可以写?所以陈维崧的词有两面:有的是未免豪放而浅薄,有的则也写了非常深沉的悲哀。可是那个时候一般人对于南宋的词不大理解,因为南宋词的叙写手法是受了周邦彦的影响,针对长调的柳词流于淫靡,长调的豪放词流于叫嚣,所以他有意用一种思索安排的手法使它委婉深曲。周邦彦的词也写爱情,他那种时空的错综,笔法的颠倒,是有心要增加词的委曲,而且不仅是在叙写之中增加他的委曲,还要在声音之中增加他的委曲,所以他用拗折,用平仄与诗不同的语法来拗折,这一切都是他有心去拗折,而这种写法的变化的深层特质,很多人都不认识,直到王国维也不喜欢,不知道怎样去欣赏南宋词。真正对南宋词的好处有了体会和认识,其实是清朝的朱彝尊。我以前写过一篇关于朱彝尊的词论的文章,在这些清代词人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朱彝尊对于南宋词有非常清楚地反省和认知。可是人是受命运跟时代左右的。本来,朱彝尊认识到南宋词的好处,而且《乐府补题》这本书也是他从江南的藏书人家发掘出来的。他知道这种南宋的词,这种咏物词可以写出来何等深厚婉转。因此他把《乐府补题》带到京师来,一下子就引起了轰动,而且被蒋景祁这些词人刻印成书了,很多人都唱和,为什么?因为他们那时候距离明清易代的时间不久,他们都知道这里面蕴含着难以言说的国破家亡的悲哀。可是《乐府补题》被带到京师来的时候是康熙十八年,那一年举行了博学鸿词科,朱彝尊以高等的成绩考中,做了高官。他认识了南宋词这种亡国之恨的那种低徊婉转的好处,可他失去了立场。孔孟早就说过:“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你“自反而不缩”呢?如果你自己不好,“虽褐宽博,吾不惴焉。”(30)你自反是正直的,你的内心是充实的,你自然就写出好词来。朱氏他认识了南宋咏物词的好处,但是他失去了写南宋的那种亡国的悲慨的立场,他写不出来了。所以在《茶烟阁体物集》中,朱彝尊写了多少无聊的词,咏美人的额头、美人的肩膀、美人的背、美人的胸、美人的手、美人的足,用了很多典故,用了很多非常精微美妙的句法和语法,用了很多美丽的语言,写的是什么?美人的身体的各部分。他失去了立场,也就写不出像《乐府补题》那样有深沉悲慨意蕴的词了。所以这个时候,受周邦彦之影响、由朱彝尊所提倡的雅词也走向没落了。
而后才有张惠言常州词派的兴起。张惠言说词是“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31),这真是说得啰嗦。其实假借闺房儿女的这段话,是朱彝尊给陈纬云写的《红盐词序》里面就曾经说过的,但是为什么朱彝尊当时说这样的话没有引起人的注意?其实我们中国很多人都体会到小词有一种微妙的作用,但都是在给朋友的词集的序跋里面说的,《姑溪文集》里边李之仪的《跋吴思道小词》,朱彝尊给陈纬云写的《红盐词序》,都是给朋友的序跋。序跋当然应该说好话,你的朋友总写美女跟爱情,而中国的传统认为写爱情、美女这个品格不高,所以你就说美女跟爱情里面有感慨,有寄托。但大家对你的这种说法不重视,认为你是给朋友写序跋,歌颂他,故意要这样说的。可是张惠言的《词选》就不一样了,张惠言《词选》是他选出来的,前面是总论的序言,他认为词是本来就应该有一种特殊的美感,他以为“里巷男女哀乐”可以写出来“贤人君子”,他说的非常妙,是写出“贤人君子幽约怨悱”还“不能自言之情”。还不止如此,更进一步说是要“低徊要眇以喻其致”,表现那么一种姿态,是让人去体会,而作者并没有直接说出来。这才是微妙的地方。可是张惠言有一个绝大的缺憾,这个缺憾是因为张惠言所生的那个时代的限制。为什么是时代的限制?因为中国的文学批评一向都是抽象的。像严沧浪的“兴趣”,王渔洋的“神韵”。我在国外讲课,“兴趣”是什么,你就很难翻译,是interesting吗?当然不是了,还要讲“气骨”,“气”是air,“骨”是bone,那是什么东西?他们都不知道。而中国传统就是如此的。你看西方的哲学书,那种条分缕析,那种思辨之细微。而中国不是,中国诸子的书,一个又一个的比喻,例如《庄子》,一个又一个的故事。中国人是让你直觉,让你妙悟,而不长于理性的思辨。所以中国的诗跟西方的诗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西方诗的起源是史诗和戏剧。中国就是诗歌,不但《诗经》是诗言志,你看《楚辞》的《离骚》,洋洋洒洒的一篇《离骚》,不都是屈原内心之中的感情志意的流露吗?所以中国的诗就是一种兴发感动,这是我们中国诗的基本的特质。只是这种兴发感动你缺少具体的理论说明,怎么办呢?中国古有比兴之说,“赋、比、兴”是按照诗的做法来说的,你要写恶事不能直接说,你要用比;美的事情不能直接说赞美,所以要有兴,这是比兴寄托。要不然就是《离骚》的美人香草的寓托。张惠言发现了小词之中有着一种微妙的东西,是“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那是什么?他找不到语言来表达,就说:“盖诗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则近之矣。”你要注意到他说的语气,他说“盖”,大概、或者,就是像。像什么?就是诗之比兴,就是变风之义、骚人之歌,“则近之”,大概就差不多了。他没有说就是,而说大概是,反正就是言外给你很多联想的一个东西。只是张惠言犯了另一个大错误,就是他要用比兴寄托指说每一句词。本来他的序言说的很婉转,他说“盖诗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则近之矣”,反正有那么一个东西,是言外有很多东西,让读者去联想。但他还想举点例证,他在例证中就指说,这个就是那个,那个就是这个,就把它都落实下来,落实下来就糟糕了,一落实,真是这牵强附会了。所以王国维就觉得他牵强附会,但是王国维也体会到小词里面有一种微妙的作用,所以他说词“以境界为最上”,但是“境界”是什么他也说不清楚,而且他把“境界”一词用的很混乱。“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是“境界有大小”,但那明明是诗的境界。他说“词以境界为最上”,却举了很多诗的境界,所以他也混乱,说不清楚那境界是什么?
清代的词是按照《花间》、两宋词的轨迹而演化的,清人也同时对于词的美感有一种反思的认知。我现在简单地念几句他们的词论,还是说得不够清楚。现在的这个时代是科学化的时代,是跟西方的理论有着密切交流的时代,是应该把小词这种难以言说而确实具有的美感特质加以清楚说明的时代。清朝人说不清楚,但是他们有认知,像丁绍仪《听秋声馆词话》说“语馨旨远”(32),语言写得很美丽,意旨非常遥远;江顺诒的《词品二十首》说“诗尚讽喻,词贵含蓄”(33);陈廷焯说“所谓沉郁者,意在笔先,神余言外”(34),里边要有一个东西让你去追寻,让你去想象。所以沈祥龙的《论词随笔》说:“词贵意藏于内,而迷离其言以出之。”(35)而一直到近代的况蕙风先生,其词话里面最有名的是“重、拙、大”之说。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针对很多人说我怎么老讲男性作者的词,作为一个女性怎么从来不讲女性词,所以我就开始谈女性词,从性别文化讲女性词的美感特质,讲了敦煌的曲子词、早期的那些不成家数的妇女哀歌,最后讲到两个有名的作者:足以成家的宋朝的李清照和朱淑真。我在写朱淑真的文稿里边引了况周颐先生的几段话,但是我认为他说的不完全对。况周颐先生提出词里面要“重、拙、大”,他也举了王鹏运一些说法,他说“重、拙、大”像五代的词中欧阳炯《浣溪纱》:“兰麝细香闻喘息,绮罗纤缕见肌肤”,“直是大且重。苟无《花间》词笔,孰敢为斯语者?”没有《花间集》写的爱情词,哪个中国传统文人敢这么大胆写出男女的爱情来?从来也没有。所以《花间》词其实有两种美感,一种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双重性别”、“双重语境”发展出来的小词的深蕴的内涵的一种美,我们要推尊词体,遵循中国传统的言志载道传统,所以特别重视这一类词。其实《花间》词就是写美女和爱情的词。那么像欧阳炯这样的词,能够把男女之爱这样庄严、正式地写出来的,而不流于轻薄,其实这才是《花间》词真正特有的一种特色。女性中间,不仅从来没有人敢写这么大胆的爱情,而且在文章中、诗词中写爱情就更要写得婉转、含蓄。这里我还要替一个人做辩解。南宋灭亡了,王清惠写道:“问嫦娥相顾肯从容?同圆缺。”被文天祥讥讽,说“夫人差矣”。他以为王清惠所写的是要跟嫦娥一样要圆就圆,缺就缺,这是不贞洁。我认为这是变天祥误解了王清惠。因为在中国的诗词里边向来有一个传统的句法,“肯”就是“不肯、岂肯”之意。韩退之所说的:“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就是我不肯,我岂肯。所以王清惠的意思是说,我王清惠怎么愿意像嫦娥一样随便的圆缺,她最后出家做了女道士。文天祥把“肯”看成正面的意思,这是文天祥对于王清惠的一个绝大的误会。中国所有的女性诗词,写爱情大多是正当的爱情,李清照写的是夫妻的爱情,徐灿写的也是夫妻的爱情。没有人大胆地敢写婚外的爱情,而就是朱淑真才写了婚外的爱情。还有,况蕙风先生以为朱淑真的风格比李清照更近于《花间》,所以朱淑真应该比李清照早,我认为那是不对的。我们根据朱淑真词句里面所引用的前人词句,她不但用过李清照,还用过张孝祥,所以朱淑真的时代绝对要比李清照晚。可是她的词风为什么反而更近于《花间》?那是因为朱淑真这个人,平生就以写爱情为主,而写爱情当然是《花间》传统。而且《花间》写的是大胆的爱情,所以朱淑真就大胆地写爱情,她是“不用《花间》词笔,哪个女性敢为此词者?”可是尽管有《花间》的词笔,一般女词人也不敢写婚外之情,而朱淑真写出来了。那么朱淑真的优劣何在?这一点我在论朱淑真的词里边谈到过,暂且不论。现在我要说的是况蕙风先生在“重拙大”之说以外有更好的讲词的特质的一段话,这是很长的一段话:“吾苍茫独立于寂寞无人之区,忽有匪夷所思之一念,自沉冥杳霭中来,吾于是乎有词。洎吾词成,则于顷者之一念若相属若不相属也。而此一念,方绵邈引演于吾词之外,而吾词不能殚陈,斯为不尽之妙。非有意为是不尽,如书家所云无垂不缩,无往不复也。”(36)
这才是小词的一种非常微妙的好处。所以我以为清词之所以有如此辉煌的成就,不仅因为宋人的词发挥有所未尽,而且因为小词的美感这么不容易被认识,宋人没有清楚的认知,而清朝的词人不但发现了词的这一种特美,而且对于词的特美开始有了一种美感特质的反省和认知。但是很可惜,我们传统的文学理论缺少一个恰当的分析语言,王国维尝试了,但是也还不够清楚,我认为我们的时代是应该对它有一个清楚的说明的时代。
注释:
①王国维:《宋元戏曲史·自序》,《宋元戏曲史疏证》,马美信疏证,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页。
②赵崇祚编:《花间集》,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页。
③魏泰:《东轩笔录》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2页。
④惠洪:《冷斋夜话》卷十,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76-77页。
⑤李清照:《打马赋》,黄墨谷辑:《重辑李清照集》,济南:齐鲁书社,1981年,第115页。
⑥李清照:《夏日绝句》,《重辑李清照集》,第91页。
⑦苏轼:《与鲜于子骏三首》之二,《苏轼文集》,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560页。
⑧柳永:《定风波》,《乐章集校注》,薛瑞生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119页。
⑨《周礼·春官宗伯下》,《周礼今注今译》,林尹注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第231页。
⑩韦庄:《菩萨蛮》,曾昭岷等编:《全唐五代词》,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52页。
(11)韦庄:《菩萨蛮》,《全唐五代词》,第154-155页。
(12)韦庄:《菩萨蛮》,《全唐五代词》,第154页。
(13)王国维:《人间词话》,唐圭璋编:《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4242页。
(14)晏殊:《浣溪沙》,唐圭璋编:《全宋词》,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90页。
(15)欧阳修:《玉楼春》,邱少华编:《欧阳修词新释辑评》,北京:中国书店,2001年,第108页。
(16)陈亮:《水调歌头·送章德茂大卿使虏》,《陈亮集》,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06页。
(17)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词话丛编》,第3794页。
(18)温庭筠:《菩萨蛮》,《全唐五代词》,第99页。
(19)柳永:《定风波》,《乐章集校注》,第119页。
(20)王又华:《古今词论》,《词话丛编》,第609页。
(21)李白:《将进酒》,《李太白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79页。
(22)周邦彦:《解连环》,《清真集校注》,孙虹校注、薛瑞生订补,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87页。
(23)辛弃疾:《水龙吟·过南剑双溪楼》,《稼轩词编年笺注》,邓广铭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82页。
(24)苏轼:《八声甘州·寄参寥子》,《苏轼词编年校注》,邹同庆、王宗堂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668页。
(25)叶恭绰撰、张璋辑:《遐庵词话》,张璋等编:《历代词话续编》,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第603页。
(26)李雯:《风流子·送春同芝麓》,叶恭绰编《全清词钞》,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41页。
(27)吴伟业:《过淮阴有感》其二,《吴梅村全集》,李学颖集评标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396页。
(28)吴伟业:《贺新郎·病中有感》,《全清词钞》,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5页。
(29)陈维崧:《词选序》,《陈迦陵文集》卷二,四部丛刊初编本:《陈迦陵诗文词全集》,第31页。
(30)《孟子·公孙丑章句上》,《孟子译注》,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61页。
(31)张惠言:《词选序》,《词话丛编》,第1617页。
(32)丁绍仪:《听秋声馆词话》卷十七,《词话丛编》,第2790页。
(33)江顺诒:《词学集成》卷八,《词话丛编》,第3300页。
(34)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一,《词话丛编》,第3777页。
(35)沈祥龙:《论词随笔》,《词话丛编》,第4048页。
(36)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一,《词话丛编》,第441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