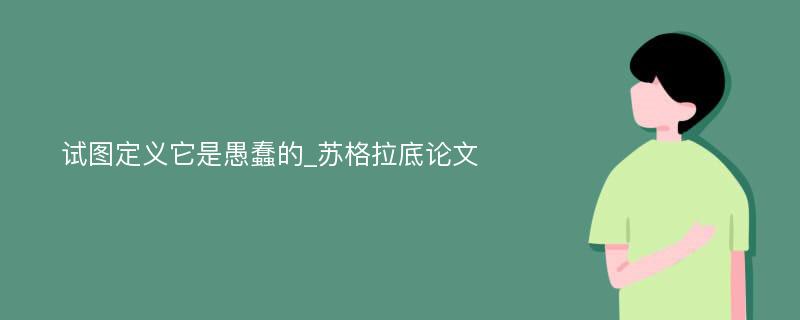
试图定义真乃是愚蠢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愚蠢论文,定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1-053文献标识码:A
在《欧绪弗洛篇》中,苏格拉底问神圣是什么,什么“使”神圣的东西神圣。显然,他在寻求一种定义,一种具有特殊性质的定义。他不屑于只是提供例子或罗列情况,因而他在每一事例问什么使例子成为例子,或者他给罗列的情况增加一项条款。他只是拒绝外延等同的概念(“某物是神圣的,当且仅当它对神是可贵的”):凡使某物对神可贵的东西就在于它是神圣的,但并非反过来也是如此。这篇对话的最后,苏格拉底请求欧绪弗洛用一个令人满意的回答来启迪他,而欧绪弗洛决定去赴另一个约会。
尝试定义,提供反例,改进定义,再提供反例,最终是失败的抱怨,这种模式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中期对话中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反复出现。美、勇敢、德行、友谊、爱、节制都被放在显微镜下,但是没有出现令人信服的定义。所有柏拉图似乎比较喜欢的定义只是对是一个智者是什么意思的倾向性说明。他也提供了几个平凡的正确定义样板:三角形的定义;泥(土和水)的定义。
在《泰阿泰德篇》中,柏拉图试图定义经验知识。如同自那以来的许多哲学家一样,他把知识看作是真信念加上一些东西——这样一种说明使信念成为有正当性的或有保证的。正是最后这种特征使他犯难了(再次预示了这个主题后来的历史)。看来,大多数哲学家都没有想到,柏拉图同样也没有想到,一定会进入有正当性的信念的分析的因果和理性要素的组合(一如它一定会进入对记忆、感知和意向行为的说明)就本性而言也许不会顺从于以更清晰更基本的词汇做出的鲜明表述。
然而,在当下语境中重要的是一个事实:在试图定义知识的时候,柏拉图只是在有保证性这一概念上承认失败。关于同样涉及带有真和信念的知识,他并不怎么担心。
而且,尽管如此,柏拉图不过是在开辟一条新路,千百年来其他哲学家一直跟随在这条路上。当真这个概念是你注意的焦点的时候,如果你担心它,你就会跟随柏拉图的指引;但是当你试图探讨知识(或信念、记忆、感知,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的时候,你就装作理解它。我们在休谟和其他人那里遇到过同样令人困惑的策略,他们在表述怀疑有关其他心灵的知识时,忘记了他们关于外在世界的怀疑论。当一个哲学家被一种意向活动的观念所困扰的时候,如果他能够以信念、欲望以及因果关系这些概念正确地分析它,他是会感到高兴的,而且这时他对这些(至少同样困难的)概念并不是特别担心。如果记忆受到审视,则与信念、真、因果关系,也许还有感知的联系就构成了这里的问题,但是只要可以把这些联系搞清楚,这些更进一步的概念暂时就被看作是清楚得足以用来澄清记忆。如果你的目标是意义,那么就完全可以假定你对意向和约定有一种充分的处理。我还可以很容易地继续往下说。
这些熟悉的、尽管奇特的困惑有时候表现在这一点上,有时候表现在那一点上,由此可以得到一个教训。我牢记的教训是,无论我们把这些各种不同的基本概念联系起来的企图多么脆弱或错误,这些企图还是比我们以更清楚、甚或更根本的概念得出正确的和富有揭示性的定义的努力表现得更好,而且告诉我们更多的东西。
这毕竟是我们应该期待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哲学家选择出来予以注意的概念,比如真、知识、信念、活动、原因、好的和对的,乃是我们拥有的最基本的概念。没有这些概念,(我倾向于说)我们就会根本没有概念。那么我们为什么应该期待能够以定义的方式把这些概念还原为其他一些更简单、更清晰和更基础的概念呢?我们应该接受一个事实:使这些概念如此重要的东西一定也排除了为它们发现一种更深层次的基础的可能性。
我们应该把这个明显的观察应用于真这个概念:我们不能希望以某种更透明或更容易把握的东西做它的基础。如同摩尔、罗素和弗雷格主张的,塔斯基证明的那样,真乃是一个不可定义的概念。这并不是说,关于它我们不能说出任何富有揭示性的东西,因为通过把它与其他诸如信念、欲望、原因和活动这样的概念联系起来,我们能够对它做一些揭示性的说明。真的不可定义性也不意味着这个概念是神秘的、歧义的或不值得信赖的。
即使我们被说得相信真这个概念是不能定义的,直觉或希望依然会存在,即我们能够用某种相当简单的表述来说明真之特征。当代真之哲学讨论的很大一部分特色在于,尽管市场上有许多这样的表述,但是似乎它们都没有摆脱相当明显的反例。一直有一种结果:主张极小的真之理论或真之紧缩论的人越来越多。这些理论认为,真是一个相对平凡的概念,不带有“与其他像意义和实在这样的概念的重要联系”①。
我赞同紧缩论者;试图把更多的内容注入真这个概念,大体上说是不吸引人的。但是我认为紧缩论者的结论是错误的,即使他们拒绝的东西多半是对的。我不会在这里逗留,说明我为什么拒绝接受符合论、融贯论、实用论等等,即这样一些理论,它们把真局限于在理想条件下可能会确定的东西或可能会被断定为有正当性的东西②。但是,既然我和紧缩论者一道不满意所有这样对真的特征说明,我就应该说明为什么紧缩论在我看来同样是不可接受的。
我们都知道,亚里士多德满足于
(1)说是者不是,或者说不是者是,就是假的,而说是者是,或者说不是者不是,就是真的。
当塔斯基③ 1944年提到这一表述的时候,他抱怨说,这是“不充分严格和清楚的”,尽管他喜欢这个表述而不喜欢另外两个表述:
(2)一个句子的真就在于它与实在相一致(或符合)。
(3)一个句子是真的,如果它表示一种现存的事物状态(同上,第343页)。
在1969年,塔斯基④ 又引用了(1),并且补充说:
从严格和形式正确的观点看,这个表述尚有许多改进之处。比如,它不够一般化;它只指一些“说明”某物“它是什么”或“它不是什么”的句子;在大多数情况下,几乎不太可能在这个模子里铸造一个句子而不偏向这个句子的涵义并附加该语言的精神(同上,第63页)。
他补充说,这也许是(2)和(3)这样的对亚里士多德表达方式的“现代替代”。
然而在《形式化语言中的真这个概念》中,塔斯基⑤ 更喜欢如下非形式陈述:
(4)一个真句子是这样一个句子,它说明事物状态是如此如此的,而且事物状态确实是如此如此的(同上,第155页)。
在我看来,亚里士多德的表达方式显然优于(2)、(3)和(4);它更符合塔斯基本人关于真的工作;而且塔斯基的评论,即(1)“不够一般化”,与他自己关于真之定义的精神很奇怪是不一致的。
(1)优于(2)(3)(4),有三个原因。首先,(3)和(4)提到事物状态,这样就使人以为,设定符合句子的实体可能会是一种说明真之特征的有用方式。(“一个真句子是一个符合事实的句子”,或“如果一个句子是真的,就有一种它所符合的事物状态”。)但是人们从未表明事实或事物状态在语义学中起一种有用的作用,而且支持塔斯基定义的最强有力的论证之一是说,在这些定义中,没有东西起事实或事物状态的作用。这是不奇怪的,因为有一个通常追溯到弗雷格(一种形式)或哥德尔(另一种形式)的令人信服的论证,其结果是至多只能有一个事实或事物状态。(这就是为什么弗雷格说所有真句子都命名真。)塔斯基的真之定义根本就没有利用一个句子符合任何“事物”这一思想。塔斯基⑥ 在一些说明中提到“事物状态”,比如:“语义概念表达了所讨论的语言中指称的对象(和事物状态)和指称这些对象的表达式之间的一定关系。”(同上,第403页)对这样提到“事物状态”,我们不应该当真。
更喜欢亚里士多德的真之特征说明的第二个原因在于,它避免了塔斯基的话语(4)中“如此如此”这些话所标示的笨拙的空白。弄懂如何填充这些空白,压力很大。而亚里士多德的表述听上去非常像是塔斯基T-约定的一种概括。
更喜欢亚里士多德的真之特征说明的第三个原因在于,它清楚地表明了其他表述方式所没有清楚表明的东西,即一个句子的真依赖于这个句子的内在结构,就是说,依赖于其诸部分的语义特征。在这一点上,它再一次更接近于塔斯基的真之概念途径。
塔斯基以可理解的方式用T-约定替代了我一直在讨论的那些粗糙表述。他的T-约定规定,对一种语言L中“是真的”这个真之谓词的一个令人满意的定义必须是这样的,最终隐含一切具有
s是L中真的当且仅当p
这种形式的句子作为定理,这里“s”被对一个句子的描述所替代,而“p”被那个句子或被该句子到元语言的一个翻译所替代。既然假定L中有无穷多句子,因此显然,如果真这个谓词的定义应该是有穷的(塔斯基坚持这一点),那么这个定义就必须利用一个事实:句子尽管是潜在无穷多的,却是从一个有穷的词汇表构造起来的。对于塔斯基所考虑的并且说明了如何定义其真的语言来说,所有句子都能够被赋予存在量化的形式、或存在量化的否定形式、或这样的句子的真之函数复合构成的形式。那么,从塔斯基的观点看,亚里士多德的表述方式(1)有多么“不完全”呢?它处理四种情况。有“说是者不是”这样的句子:用现在的话说,这是一个以“并非存在一个x,使得……”起始的假句子。一个例子可能是这样的:“不存在一个x,使得x=4”。然后有“说不是者是”这样的句子。比如,“存在一个x,使得x=4并且x=5”。还有“说是者是”这样的句子。例如,“存在一个x,使得x=4”。最后有“说不是者不是”这样的句子。例如,“并非存在一个x,使得x≠x”。根据经典的表述方式,头两种句子是假的,而后两种句子是真的。塔斯基至此是同意的。那么他要补充的会是什么呢?恰恰是已经提到的那类真之函数复合构成的句子(但在那些涉及否定的真之复合构成之外)。这些复合构成基于那种已证句子的真或假而是真的或假的。当然,塔斯基也详细表明,前四类句子的真或假反过来是如何依赖于它们的结构的。
这样,被看作非形式的特征说明的经典表述方式与塔斯基自己的工作相比仅在非常小的方面是“不完全的”,并且强于塔斯基陈述直观思想的非形式企图。无需说,有人可能会质疑在什么程度上能够充分地说明使用这样有限资源的自然语言的特征,但是这是一种同样适用于塔斯基的评论。
尽管塔斯基表示出一种符合论的方向,其中句子被说成符合事实,但是不应该认为他安慰了严肃而坚定支持符合论的人,对亚里士多德也不应该这样看。因为亚里士多德的表述和塔斯基的真之定义都没有引入像事实或事物状态这样的句子所符合的实体。塔斯基确实基于满足概念定义了真,而满足这一概念使表达式与对象联系起来。但是满足句子的序列决不是符合论者的“事实”或“事物状态”那样的东西,因为如果塔斯基的序列之一满足了一个封闭句,因而使它成为真的,那么这同样的序列也满足其他每一个真句子,因而也使它成为真的,而且,如果任何序列满足一个封闭句,那么每一个序列也满足它⑦。
如果塔斯基不是一个符合论者(而且他当然不主张一种融贯论或一种实用论或一种把真基于有保证的可断定性的理论),那么他是一个紧缩论者吗?这里的意见分歧很大。奎因认为他是,索玛斯也这样认为。艾奇曼蒂认为塔斯基关于作为语义概念的真根本就什么也没有说,而普特南同意这样的看法,尽管理由有些不同⑧。
如果如同里兹、霍维奇和索玛斯都坚决认为的那样,也如同奎因强烈暗示的那样,塔斯基说过与真相关“所有要说的东西”,那么一种紧缩论的态度就是有正当性的。这与“冗余论”观点并非完全相同,但是近似。紧缩论观点字面上看与去引号观点字面上看是一样的:我们总是能够用一个句子完满地替代那个引述的并且后跟“是真的”这话的句子。正像威廉姆斯和其他一些人指出的那样,塔斯基所补充的是一种断定整个句子类或我们不知道如何指称的句子类是真的的方式;你可能把这看作是冗余论的详细阐述,因为它允许当真这个谓词应用于一种它为之定义的语言的句子的时候,可以消除真这个谓词。
当我们相信是塔斯基表明了如何说明“约翰说出的这个有关修道院长的英语句子是真的”、“亚里士多德(用希腊语)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或“通常的条件式真值表使任何前件假的条件式是真的”这样的说法的意思的时候,我们同时必须认识到,伴随这一成就的是一个证明,即(给定了各种有道理的假定)真一般是不能定义的;无法有定义“对所有语言L和L中的所有句子s,s是L中真的当且仅当……s……L……”。换言之,塔斯基说明,只有通过限制真这个谓词对一种特定语言的句子的应用,真这个谓词用到这种特定语言的句子上才是有正当性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最近关于紧缩论的文献中,塔斯基被看作是为如下观点提供了支持:有一个单一的、简单的、甚至平凡的真之概念。)
因此,认真思考塔斯基的工作,不会鼓励人们对真这个概念采取一种紧缩论的态度。人们可以采纳普特南和艾奇曼蒂提出的思路,认为塔斯基甚至不是在研究语义学,尽管他坚持认为他在研究语义学;但是这种对塔斯基的解读并不支持紧缩论:它不过是否认塔斯基的结果与真这个普通的概念相关。而如果人们认为塔斯基的真之定义对特殊的语言与世界的关系做了一些说明,人们就不能同时声称他告诉了我们有关真这个概念所有要知道的,因为他还没有告诉我们他那些特定语言的真之定义所共同具备的那个概念是什么。
我认为,塔斯基并不是在试图定义真这个概念(这大体是显然的),而是在采用那个概念来说明特殊语言的语义结构的特征。但是塔斯基并没有表明我们一般怎样能够把真这个概念还原为其他更基础的概念,也没有表明如何从所有语境中——其中,“是真的”明白无误地用于句子——消除“是真的”这个英语谓词。T-约定并非是一种一般定义的粗略的替代物:它是一种成功努力的一部分,即试图说服我们,他的形式定义把我们的真这个单一的前理论概念应用于特定的语言。因此,紧缩论者不能仅仅因为塔斯基证明了如何处理个别语言的量化语义就诉诸他。里兹、霍维奇、威廉姆斯和其他一些人是错误的,因为他们坚决认为塔斯基所做的一切是揭示了一个概念的有用性,否则这个概念就是不必要的。他们对的地方是,为了他们与塔斯基一道提到的目的,我们需要真这个谓词;但是他们未能注意到一个明显的事实,这就是塔斯基解决了一个问题,同时也强调了另一个问题:给定了他所接受的制约,他并没有并且也不能定义真或完全说明真的特征。
多年以来,奎因关于真说了一些东西,但是从早期一直到最近,似乎一直包含了一种紧缩论的态度。例如,奎因一直重视真这个谓词的“去引号”方面,即如下事实:我们可以消除跟在一个英语句子引文后面的“是真的”这个谓词,方法是随着消去真这个谓词而简单地去掉引号。如同奎因在《从逻辑的观点看》⑨ 中说明的那样,我们有一个一般范式,即:
(T)“——”是L中真的当且仅当——。
这尽管不是关于真的一个定义,却可以使“L中真的”
在任何特殊应用中十分清晰,一如我们施用它的L的特殊表达式所具有的清晰。尤其是,认为“雪是白的”具有真的性质……就像认为雪具有白的性质一样十分清晰。(同上,第138页)
在《语词与对象》中,奎因⑩ 说:“说‘布鲁特杀死恺撒’这个陈述是真的,或‘钠的原子量是23’是真的,实际上不过是说布鲁特杀死恺撒或钠的原子量是23。”(同上,第24页)30年以后,《真之追求》重复了这个论题(11):
肯定没有人指责去引号的描述,没有人质疑“雪是白的”是真的当且仅当雪是白的。此外,这是一种完整的描述;它清晰明确地说明每一个清楚的句子的真或假。(同上,第93页)他总结说:“真就是去引号”(同上,第80页)。在这个问题上,奎因一直没有改变看法。
在奎因看来,正是真的去引号特征使真是一个比意义清楚得多的概念。奎因比较意义理论和所指理论说,它们构成“两个根本不同的领域,绝不应该得到一种共同的称呼”(12)。意义理论探讨诸如同义性、意义和分析性这样一些受到污染的论题。而所指理论所处理的概念,包括真,相比之下“不太模糊和神秘……”。这是因为,尽管“L中真的”对变元“L”不是可定义的,“我们确实所具有的东西足以赋予‘L中真的’(即使对变元L)以一种充分高度的可理解性,因此我们不太可能反对使用这个习惯用语”(同上,pp.137-138)。当然,“我们确实所具有的”是范式(T)和归功于塔斯基定义特定语言的“L中真的”的“便利的一般做法”。
真之去引号特征,再加上这个特征可以穷尽真这个概念的内容这样的看法,鼓励人们认为真与意义是可以完全分离的。但是它们一般能够分离吗?奎因著作中一些分散的论述说明不是这样。1936年,他发表了《约定的真》这篇出色而有先见之明的文章(13)。他在里面说:“就意义而言,……在任何确定一个词的上下文的真或假的程度上,都可以说这个词是确定的。”(同上,第89页)如果去引号的说明就是所有关于真要说的,那么很难看出真如何能够有这种确定意义的力量。奎因著作中其他一些段落使人联系到相同的思想:“总体上说,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我们学习如何分配真值。这里我同意戴维森;我们学习真之条件。”(14) 或者,“塔斯基的真之理论(就是)一种意义理论的结构”(15)。
至此可能看上去很容易把真之问题与意义问题分离开来。我们可以把真看作是去引号的(在引申的塔斯基意义上),因而是平凡的;这样,意义就是另一个问题,可以借助有保证的断定性、作用或翻译标准来处理。这就是比如霍维奇在他最近的著作《真》中遵循的思路,也是索玛斯(16) 和路易斯(17) 遵循的思路。它可能至少一度一直是奎因的观点。在《语词和对象》中,就在“布鲁特杀死恺撒”这个句子是真的不过是说布鲁特杀死恺撒这一说法之前的一段话中,奎因对一种实体性的真之概念失去信心,并得出结论说,我们只是“以一个给定的理论并且从这个理论的内部来看”(同上,第24页)而把真这个谓词用于一个句子的时候才懂它的意思。我认为,这就是奎因说真是“固有的”时所表示的东西。关键并非仅仅在于一个句子的真是相对于一种语言的;而在于没有一个可以被相对化的超验的单一概念(18)。
然而,奎因最近深思真“被感到含有某种崇高的东西。它的追求是一种高尚的追求,并且永无止境”;他似乎也认为:“科学被看作是追求和发现真,而不是对真做出判决。这是实在论的习惯说法,而且它是‘真的’这个谓词的语义的组成部分”(19)。
我现在转而考虑霍维奇的紧缩论说法,因为在我看来,他接受了其他紧缩论者所回避的挑战,即关于一个非相对化的真之概念要说出比我们能够从塔斯基的定义学会的更多的东西。霍维奇勇敢而令人瞩目的做法是使命题成为真的首要载体——严格说这本身并不是一个新思想,但是在捍卫紧缩论的严肃尝试的语境中却是新的。他很清楚他不能为适用于命题的真这个谓词提供一个明确的定义,但是他极力主张,如果我们把握如下事实,即
p这个命题是真的当且仅当p
这个模式“没有争议的个例情况”穷尽了它的内容,那么我们确实说了关于这样一个谓词(因而关于它所表达的谓词)所知道的一切。(“没有争议”的情况的限制就是排除任何导致悖论的东西。)这个模式被看作是一个公理模式:它的个例情况的整体构成了他的理论的公理。
当然,只有以不预设前提的方式明确说明了争议情况之后,这个理论才是完全的;而且由于公理集是无穷的,它就没有满足塔斯基对一种令人满意的真之理论的要求之一。但是也许第一个困难能够克服,而第二个困难可以被看作是拥有一个非相对化的真之概念的代价。此外,我们许多人关于命题的存在都有一些怀疑,或者至少关于使命题的个体化原则的存在是有怀疑的。
所有这些考虑使我踌躇,但是我打算在这里不考虑它们。我想给紧缩论充分的机会,因为在我看来它是一种更实体性的真之观点的惟一替代观点,而且在我看来,一如在霍维奇看来,最实体性的观点显然是不行的。但是尽管我热情地赞同霍维奇反对符合论、融贯论、实用论和认识论的论证,但是我却不能使自己接受他的“极小”理论。
关于霍维奇的理论我有两个根本性的问题,其中任何一个问题若是无法解决,本身都是拒绝他的理论的理由。而且我自己看不出如何解决它们。
第一个问题很容易陈述:我不理解这个基本公理模式或它的个例情况。把霍维奇的公理模式与塔斯基的非形式(并且最终被替代的)模式
“——”是真的当且仅当——
进行比较,将有助于我表述我的困难。塔斯基的反对意见(主要)在于,除非量化到引号内的位置,否则就不能把这个模式变成一个定义。这种抱怨最终是对引语的清晰性有疑问:它们所指称的东西如何依赖于它们的构成物的语义性质?有时候有人提议诉诸替代量化方式,而且人们可能奇怪为什么霍维奇不能通过采用替代量化方式来概括他的模式:
(p)(p这个命题是真的当且仅当p)。
但是在这里,霍维奇相当正确地说明他不能诉诸替代量化方式来解释真,因为替代量化方式必须由诉诸真来解释。
尽管如此,为什么霍维奇不尝试通过对命题进行量化来概括他的模式呢?回答应该是:因为如果这样,我们就会不得不把普通的句子看作是指称命题的单称词,而不是把它们看作表达命题。这将我带到了关键所在。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苏格拉底是聪明的这个命题”这样的短语呢?在对“苏格拉底是聪明的”这个句子的语义做出标准说明的过程中,我们利用了“苏格拉底”这个名字所命名的东西,还利用了“是聪明的”这个谓词所适合的(is true of)实体。但是我们如何能够利用“苏格拉底是聪明的”这个句子的语义特征来产生“苏格拉底是聪明的这个命题”的所指呢?这里,霍维奇没有给我们任何引导。我们可以说“苏格拉底是聪明的这个命题”这样的表达在语义上是非构造的吗?或者至少一个句子在(被看作一个函数表达式的)“……这个命题”这些词之前变成一个它所表达的语义上非构造的命题名字了吗?接受这一过程会使我们有一个无穷的初始词汇表,而“苏格拉底是聪明的”这句话在这个模式里两处的出现就不会有助于理解这个模式或它的个例情况。进一步的建议有可能是修正这个模式的个例情况,将它读作:
“苏格拉底是聪明的”这个句子所表达的这个命题是真的当且仅当如果苏格拉底是聪明的。
但是遵照这个思想就会要求使引用的句子相对于一种语言,而这是霍维奇一定要阻止发生的。
因此让我简要地如下提出我的反对意见:同一个句子在霍维奇模式的个例情况中出现两次,一次在“……这个命题”这些话之前,它的语境要求结果应该是一个单称词,即一个谓词的主语,还有一次作为一个普通的句子。我们无法消除这一个句子的这种重复而不破坏一个理论的整个面貌。但是,除非我们能够看到如何利用这个重复的句子在它两次出现时的相同语义特征,即利用它们来说明这种模式的个例情况的语义,否则我们就不能理解这种重复的结果。我看不到怎样能够做到这一点。
我在霍维奇的理论感到的第二个困难更依赖于我自己进一步的信念和承诺。霍维奇认识到,为了坚持认为如他所说真拥有“一种特定的纯粹性”,他必须说明,我们能够独立于其他观念而完全理解它,并且我们能够独立于它而理解其他观念。他并没有说真这个概念和其他概念之间没有关系。他只是说我们能够独立地理解这些概念。就我所关心的问题而言,这里有一些至关重要的情况,因为我不认为没有真这个概念我们能够理解意义或任何命题态度。让我们从这里挑出一个概念:意义。
既然霍维奇认为真是首先可以赋予命题的,他就必须说明我们如何也能够用它谓述句子和言语表达,而且他明白,为了说明这一点而又不损害真的独立性,我们必须在不直接诉诸真这个概念的条件下理解意义。在这个关键问题上,霍维奇说得简单,甚至简洁。他说,理解一个句子并不在于知道它的真之条件,尽管如果我们理解一个句子,我们通常知道它的真之条件。他坚持认为,理解一个句子就在于知道它的“可断定性条件”(或“恰当使用”)。他承认,这些条件可能包括句子(或言语表达)是真的。坦白地说,我看不出如果真乃是一种可断定性条件,而知道可断定性条件就是理解,那么我们如何能够在没有真这个概念的条件下理解一个句子。
然而我认识到,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领域,而且像达米特、普特南和索玛斯这样重量级的思想家遵循维特根斯坦和格莱斯提供的各种指引,相信可以使一种对意义的说明依赖于一种可断定性或使用的观念,而这一观念反过来并不诉诸真这个概念。
我的希望在相反的方向:我认为,这种与理解联系在一起的断定已经容纳了真这个概念——只要我们相信我们用来做出断定的句子是真的,我们在需要的意义上断定它就是有正当性的;而且语言之所以最终与世界联系在一起,就是因为那种典型地引起我们认为句子为真的条件构成了句子的真之条件,因此也构成了句子的意义。这里不是论证这个问题的地方。因为现在我必须简单地说明,如果我们不得不独立于一个说话者或一种语言的真之理论而发展一种这个说话者或这种语言的意义理论,这将会是不应该的,因为我们至少有某种如何表述一种真之理论的想法,但是关于如何表述一种以可断定性或使用这一概念为基础的意义理论,我们没有什么认真的想法。
我的结论是,真之紧缩论的前景是暗淡的。它的吸引力在我看来完全是消极的:它回避或至少试图回避一些明确标明的死胡同和可认识到的陷阱。
让我试着为我们关于真的疑难做一个诊断。我们仍然迷恋于苏格拉底的观念,即我们必须不断询问一个思想的本质,即以其他一些话做出一种有意义的分析,对什么使这成为一种神圣的行为,什么使这个或任何言语表达、句子、信念或命题为真的问题做出回答。我们仍然为一年级学生的谬误而着迷,这样的谬误要求我们首先要定义一些词,然后再以它们来进一步说任何事情或者关于它们再说些什么。
如果不清楚谁在试图定义真,那么如此重视定义真的动机可能就会是无意义的。试图定义真的不是塔斯基,他证明了真是不能定义的;不是霍维奇,他不承认这种企图。那么是谁承诺要定义真这个概念呢?好吧,这是对的。但是就是这种令人厌烦的强烈的定义要求却在一种伪装下表现出来,这种伪装即是试图提供一种简要的标准、模式、部分的却是导向性的暗示来取代严格的定义。自塔斯基以来,当我们思考不是相对于一种语言的真之概念的时候,我们对“定义”这个词非常当心,但是我们并没有放弃定义的强烈要求。这样,我认为霍维奇的模式在这一点上与达米特的有正当性的可断定性概念、普特南的理想的有正当性的可断定性和符合论和融贯论各种不同的表述方式是同等的。在我看来,所有这些如果不是试图做出严格意义的定义,也是试图形成定义的替代物。在真这种情况,没有简要的替代物。
现在我要描述我把什么样的理论看作可以相当彻底的替代那些我一直讨论并且(过分草率地)排斥的理论。我这里强调的是我认为需要有的方法论,而不是我在其他地方做出的更为详细的说明。人们可以说方法论不提供真这个概念的定义,也不提供任何准定义条款、公理模式或其他简明的定义替代物,这样人们就从否定的方面说明了方法论的特征。正面的建议是试图追溯真这个概念和给予它质体(body)的人的态度和行为之间的联系。
我的方法论感悟来自有关度量、或有关各种不同科学的有穷公理化理论。这些理论对一个或多个概念提出清楚的限定,然后证明这样一种理论的任何模型都有直观理想的性质,即该模型适合于它旨在的目的。由于在模型中有各种各样抽象实体的排列组合,还有无穷多不想要的经验事件和对象的模式,因此只有说明这个理论应该如何应用于适宜的对象或事件,才能把它应用于像质量或温度这样的特殊现象,或者针对这样的特殊现象来检验它。我们不能要求对如何这样做有精确的说明;发现一种有用的应用理论的方法是一件复杂的事情,其中包括摸索形式理论和检验它是不是像解释的那样正确。
我们对真这个概念感兴趣,只是因为世界有一些可以应用它的现实对象和状态:言语表达、信念状态、感悟。如果我们不理解这样一些实体是真的是什么意思,我们就不能说明这些状态、对象和事件的内容的特征。因此,除了真之形式理论外,我们必须说明真是如何表述这些经验现象的。
塔斯基的定义没有提到经验的事情,但是我们却可以毫无约束地问这样一个定义是不是适合某个说话者或某群说话者的具体实践——我们可以问他们是不是说那种定义了真的语言。关于塔斯基的定义,没有什么东西阻止我们以这种方式来看待它们,除非是有偏见地认为,如果把某种东西称为定义,它的“正确性”问题就是悬疑的。为了铲除这种偏见,我建议我们省略塔斯基定义的最后一步,即将他的公理化变为明确定义的那一步。这样我们就能充分有意识地称这个被阉割的定义为一种理论,并且接受真这个谓词为未定义的。这个未定义的谓词表达了一般的直观的适用于任何语言的概念,即表达了这样一个概念,我们总是针对它而偷偷摸摸地检验塔斯基的定义(当然,也是他招致我们这样做的)。
这个概念如何应用于人类的言语、信念和活动,我们知道得很多。我们用它解释人类的言语表达和信念,做法是给它们指派真之条件,而且我们通过评价这些活动和态度的真的相似性而对它们做出判断。经验的问题是如何通过观察和归纳来确定经验的真之载体的真之条件是什么。它强调的是:没有这种经验联系,真这个概念就无法应用于我们世俗的考虑或引起我们世俗的考虑的兴趣,而且,就我的理解,它根本就没有任何内容。
请考虑如下相似性:我如同拉姆塞考虑概率那样考虑真。他自己(并非没有理性地)坚信,概率这个概念首先应用于命题态度;它是信念度的尺度。他继续思考:我们如何能够说清楚信念度(主观概率)这个概念呢?主观概率是不可观察的,无论是对不太完全确信和更不完全相信地接受某个命题的人,还是对其他看见他并问他的人。因此拉姆塞把一种理想化的人的优选模式公理化,这种人或多或少与我们其他人一样,调整自己的对命题(或事物状态或事件)之真的优选,以符合自己的价值和信念。拉姆塞陈述了在什么条件下一个这样的优选模式会是“理性的”,并且实际上证明,如果满足了这些条件,就可以从这种人的优选重新建立起他的愿望和主观概率的相关力量。拉姆塞并没有假定每一个人在这种设定意义上都是完全理性的,但是他确实假定,从长远的观点看,由于有了他的理论,人们几乎足以完全理性地赋予主观概率这个概念以内容,或赋予如他思考的那种概率概念以内容。
不愧是一个杰出的策略!(无论它是否对概率做出了正确的分析)概率(或者至少信念度)这个概念,在拥有它的人那里是不可观察的,在观看他的人那里也是不可观察的。它与主要效用或主观评价这样一个等价理论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并且二者在公理结构上都与简单优选相联系。简单优选又通过在现实选择行为中的表现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经验基础。
我们应该以与我们考虑一个合理判定的理论同样的方式考虑一种一个说话者的真之理论。二者都描述我们可以在会说话的多少有些理性的动物的行为中发现的结构,并允许在一定程度上有出入的调整。在这种有出入的调整中,我们赋予我们简要地叫做主观概率和主观价值(信念和愿望)这样未定义的概念以内容;而且我们借助塔斯基那样的理论赋予真这个未定义的概念以内容。
最后说一点。我有意使赋予真这个概念以经验内容这个问题看上去比实际上更为简单一些。如果我们能够直接观察人们以他们说的话表示什么意义(把这作为基本证据),这个问题相对就会简单。但是意义不仅是一个比真这个概念更含糊的概念;它显然还牵涉到真这个概念:如果你知道一个言语表达有什么意义,你就知道它的真之条件。问题是应该给任何命题态度一种命题内容:信念、愿望、意向、意义。
因此我把真与可观察的人类行为联系起来的问题和把内容指派到所有态度上的问题看作是不可分割的,而且在我看来,这似乎要求有一种理论,它把一个真之理论嵌入一个包括判定理论本身的更大的理论。结果将容纳理性的主要范式,这些范式在一些人的思想和行为中的部分实现使这些人比其他人或多或少更可以理解。如果这种规范结构复杂得可怕,那么我们应该对一个事实感到安慰,这个事实是:在只是一些分散零碎的薄弱解释的证据的条件下,这种规范结构越是复杂,我们就越有机会对它表现的思想、有意义的言语和意向性活动做出解释。
(D.H.Davidson" The Folly of Trying to Define Truth" 原载The Nature of Truth,ed.by Michael Lynch 2001,译者单位: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注释:
①这些话引自达米特在霍维奇的《真》一书(Truth,Cambridge:MIT,1991)护封上的话。当然,这不是达米特的观点。
②我在《真之结构和内容》[“The Structrue and Content of Truth”,Journal of Philosophy,LXXXVII,6 ( June 1990) :279-328]一文中阐述了我拒绝这样的观点的理由。
③“The Semantic Conception of Truth”,Philos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IV,1944,pp.342-360.
④“Truth and Proof”,The Scientific American,ccxx( 1969) :63-77.
⑤“The Concept of Truth in Formalized Languages”,in Logic,Semantics,Metamathematics,New York:Oxford,1956,pp.152-278(最初于1936年以德文发表)。
⑥“The Establishment of Scientific Semantics”,in Logic,Semantics,Metamathematics,pp.401-408.
⑦由于序列在满足封闭句中的作用,我一度建议称塔斯基的真之概念为一种符合论,但是随后我撤消了这种建议,因为它引入误解。关于这个建议,参见“True to the Facts”,in Inquiries into Truth and Interpretation,New York:Oxford,1984。关于放弃这种建议,参见“Afterthoughts”,1987,in A.Malichowski,ed.,Reading Rorty,Cambridge:Blackwell,1990,pp.120-138。
⑧关于参考文献和进一步讨论,参见我的“The Structure and Content of truth”。
⑨Cambridge:Harvard,1961.
⑩Cambridge:MIT,1960.
(11)Cambridge:Harvard,1990.
(12)From a Logical Point of View,p.130.
(13)重印于The Ways of Paradox,Cambridge:Harvard,1976。
(14)The Roots of Reference,La Salle,IL:Open Court,1974,p.65.
(15)“On the Very Idea of a Third Dogma”,in Theories and Things,Cambridge:Harvard,1981,p.38.
(16)“What is a Theory of truth?” Journal of Philosophy,LXXXI,8,August 1984:411-429.
(17)“Languages and Language”,Minnesota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volume vii,Minnesota UP,1975.
(18)前面几段关于奎因的论述是改写的,其根据是以下一段更长更详细的关于奎因论真的研究。有一部分是引用,有一部分是改写:“Pursuit of the Concept of Truth”,in P.Leondardi and M.Santambrogio,eds.,On Quine:New Essays,New York:Cambridge:Harvard,1995,相关页码为:7-10。
(19)From Stimulus to Science,Cambridge:Harvard,1995,p.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