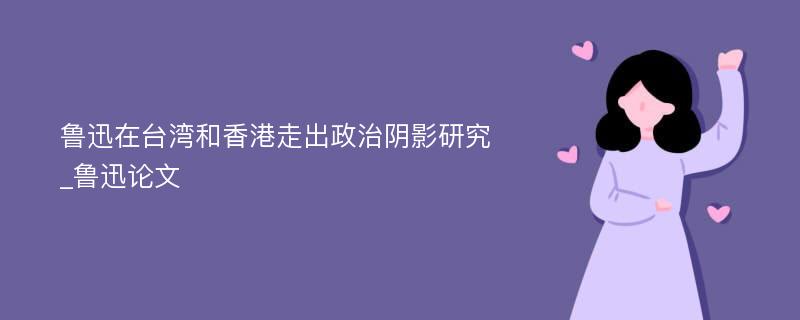
走出政治阴影的台港鲁迅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阴影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对1949年以来台港地区鲁迅研究状况的演进做了系统的述评。作者认为,1987年台湾“解严”之前的鲁迅研究,虽然不无具有学术价值与史料价值的评述,但总体上政治色彩过强,于鲁迅乃至历史多有悖误;“解严”之后,随着文化氛围的开放,鲁迅研究才有了符合鲁迅乃至历史本来面目的长足进展。作者得出结论说,走出政治实用主义阴影是台港鲁迅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的重要保证。
一
从1949年两岸对峙到1987年台湾解除戒严令,四十年间鲁迅及三十年代作家(甚至包括沈从文)的作品在台湾一律成了禁书,偷看鲁迅作品可构成杀头之罪。特别在五、六十年代,一切都要为所谓“戡乱救国”、“反攻大陆”服务,政治气压甚大。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不可能有正常的关于三十年代作家、作品特别是鲁迅的研究。当时的难得一见的关于鲁迅的文字,大概有这样几类:
一类可以郑学稼的《鲁迅正传》①和苏雪林的《我论鲁迅》②为代表,是专门“反鲁”的,以丑化、诋毁鲁迅为能事。早在鲁迅刚刚去世不久的1937年,郑氏便用小说形式写过《两个高尔基不愉快的会见》③,让鲁迅与高尔基互相谩骂、攻击一番。其《鲁迅正传》想用《阿Q正传》的笔调写鲁迅,阿Q就是鲁迅。作者说:“三十年代末和四十年代初,受中共指挥和影响的青年有‘鲁迅热’。我反抗这潮流,……决定在井潭的草舍菜油灯下写完两本书:《鲁迅正传》和《由文学革命到革文学的命》。”④到台后,这样的“反鲁”著作当然很切实用。
《鲁迅正传》采取了传记文学的形式,对鲁迅是一种“文学的丑化”,尚属比较间接。苏雪林的“反鲁”则采取了破口大骂的形式,火力远比郑氏为猛。《我论鲁迅》也不全是亡台后之作,三分之二的文章都写在大陆,基调早已形成。她的攻击集中在鲁迅的人格,说鲁迅是“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二十四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⑤,甚至“连起码的‘人’的资格还够不着”⑥。这样一些言辞曾惹起苏所尊敬的胡适先生的不满,说她态度未能“持平”,“未免太动火气,此是旧文字的恶腔调,我们应该深戒”⑦。十分遗憾的是,苏氏根本听不进胡适的良言规劝,到台后不仅没有“深戒”,在“戡乱救国”的政治气候下,反而变本加厉了。她不仅撰写了近三万言的全面清算鲁迅的《鲁迅传论》,而且写了《琵琶鲍鱼之成袖者——鲁迅》⑧等文,明确表示不同意胡当年对她的规劝与批评。而在《我论鲁迅·自序》中,辱骂鲁迅人格的措词更为激烈。可以说,苏、郑之作,是一种完完全全为政治斗争服务的“冷战文字”,缺乏丝毫的学术性。
另一类,可以林语堂的《记周氏兄弟》⑨、梁实秋的《关于鲁迅》⑩等为代表,是一种回忆性的评述,具有较强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林氏本是鲁迅《语丝》时代的好朋友,后因政见不合而反目。林先赴美后赴台,他虽然激烈“反共”也反对鲁迅的“左倾”,但他对鲁迅的人格、文品却始终是充满敬意的。他认为鲁迅的“文笔”很成功,“冷嘲热讽,一针见血,自为他人所不及。中国那种旧社会,北洋那些昏头昏脑武人,也应该有人,作消极毁灭酸辣讽刺的文章”。梁实秋是鲁迅生前的主要论敌之一,但他对鲁迅却充分表现了“绅士风度”或者说“大家风度”。他当然也不同意说鲁迅是什么“革命家”和“青年导师”,甚至也不同意说鲁迅是“伟大作家”,但他却“恶而知其善”,认为鲁迅是五四以来为数不多的“真有成就”的作家之一。《阿Q正传》“很有价值”,“在心理的描写上很是深刻而细腻”。其他的短篇小说也“有几篇在文字上和情操上是优美的”。“他的国文根柢在当时一般白话作家里当然是出类拔萃的,所以他的作品(尤其是所谓杂感)在当时确是难能可贵”。他所批评的鲁迅自身的缺点,一是嫌鲁迅没有一套“积极的思想”,“正面的主张”,而只是“消极”地指责,一味地“不满于现状”;二是批评鲁迅的“硬译”,特别是“以生硬粗陋的笔调来翻译俄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并“继而是奉行苏俄的文艺政策,终乃完全听从苏俄及共产党的操纵”;三是批评鲁迅杂文“个人攻讦的成分太多”,“多属片断性质”,“章法”也不太讲究;四是说鲁迅“没有文学家所应有的“胸襟与心理准备”,“态度不够冷静,他感情用事的时候多”。
还有一类是散见于文学史、文艺史之类著作中的鲁迅章节,如尹雪曼主编的《中华民国文艺史》(11)、周锦的《中国新文学史》(12)、刘心皇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话》(13)等。这些章节虽在某些具体问题上不无参差,但在总体倾向上可谓大同小异:肯定鲁迅的文学成就而反对他的政治态度,尤其认为毛泽东说鲁迅是三个“家”(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是一种“神话”,是为政治服务。
此外,也有少量的关于鲁迅的谈话或讲演,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胡适和徐复观。1958年“五四”,胡适在台北发表了题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著名讲演,其中,很自然地涉及了鲁迅。他根据鲁迅1935年9月12日写给胡风不让他加入“左联”的一封信,得出了鲁迅晚年已经反对“共党”了的结论。表面上看,这似乎有违国民党“戡乱救国”的宗旨,但实质上还是为了说明“共党”之非,连鲁迅也不能不反对了。胡先生失察之处即在于把鲁迅不同意胡风加入“左联”当成了不同意胡风加入“共党”,把二者混为一谈了。这个混淆也并不奇怪,因为他在私下谈话中一直把鲁迅看成一个“民主的个人主义者”,当成“自己的人”(14)。徐复观是台湾新儒学代表人物之一,由于他比较彻底地否定“五四”,因此和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学派发生了激烈冲突并对胡适攻讦甚力。由此可以想见,他对鲁迅也就不可能有什么客观公允的评价了。1953年,他应邀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发表了一个题为《漫谈鲁迅》的讲演,提出了一个相当耸人听闻的说法:鲁迅在世界文坛上“只能算三流作家”,因为鲁迅没有长篇小说,短篇小说也仅“有刺激力而没有感动力”;鲁迅的思维方式是直线型、简单化的,“缺乏反省能力”;他缺乏“人情味”,对原配朱安态度甚坏;他的阅读范围也很有限,他的阅读书单中,“找不出一两部真正有分量的中西著作”;他的阿Q丑化中国农民,很不“公平”,鲁迅不了解中国农民的“伟大品质”。不无自相矛盾的是,他又要大家学习鲁迅“写作的严肃态度及其写作的技巧,尤其可以学习他简炼的文笔”(15)。很显然徐氏的这个讲演,既充满了“冷战色彩”,也完全违背了他对弘扬民族文化的主张。试问,如果鲁迅在外国人面前都成了“三流作家”,那末,中国作家是否都成了天生的低能儿呢?
徐氏的讲演发表于香港,这也正好反映了香港学界从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对鲁迅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左”派的鲁迅论,和大陆毫无二致,指导思想同样是毛泽东的三个“家”。而“右”派笔下的鲁迅,则可说是台湾某些“反鲁”言论的翻版了。例如,著名报人胡菊人在他的长文《鲁迅在三○年代的一段生活》(16)中,便重复了苏雪林等认为鲁迅和日本帝国主义关系暖昧甚至不无汉奸嫌疑的错误论调。有些文章则沿袭了对鲁迅人身攻击的下流倾向。香港也有曹聚仁、司马长风、赵聪等那样比较严肃的学者,对鲁迅有比较严肃的分析评价,但鉴于我在《台港文学史家的鲁迅论》(17)一文中已做过详细评述,这里就不拟重复了。有必要稍加介绍的是一些海外华人学者(我们习惯把他们包括在台港学者之内)、特别是夏济安、夏志清兄弟的观点。
夏济安原为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曾与黎烈文等创办《文学杂志》,白先勇、陈若曦、李欧梵等皆为其高足。他1959年离台赴美,1965年在美逝世。他认为中国近代有三大小说家,第一位便是鲁迅。(18)而鲁迅之所以如此,他“厉害的地方就在于他强调一个‘恨’字”(19)。逝世前,他用英文写了《鲁迅作品的黑暗面》(20),为人们留下了一篇在海外罕有其匹的深刻独到的鲁迅研究论文。这里的“黑暗面”,讲的是鲁迅对中国宗教迷信、鬼魂、死亡等阴森恐怖事物的偏爱及其在文学创作中的表现。作者用鞭辟入里的分析,充分展示了鲁迅的心灵世界和创作世界,充分肯定了鲁迅的杰出才华及其出现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意义。他认为鲁迅的天才“很可能”比胡适、周作人都高,他是一个“病态的天才”,他也是“中国现代史上较有深度的人”。他虽然没有留下长篇小说,但他的那些“研究生活黑暗面的短篇小说也算得上是次一等的杰作(即仅次于长篇杰作的杰作——袁按)。夏氏还称鲁迅为“创造革新派散文的泰斗”,其“文体能自成一格”。他虽然不赞赏鲁迅杂文,认为那是一种“意见和情感”的“浪费”,但他并不否认那些文章“写得极为出色”。综上所述,夏济安的论文几乎可以说彻底摆脱了政治实用主义的干扰。
相形之下,夏济安乃弟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21)中对鲁迅的论述就有了较强的政治色彩。值得肯定的是,夏氏虽然视鲁迅的“殊荣”为“神话”,但他并未因此而象苏雪林女士那样大骂鲁迅的人格,更没有象徐复观那样把鲁迅贬为“三流作家”。相反,他以一个文学史家的眼光,客观公允地高度评价了鲁迅的历史价值和地位,认为他是中国“西式新体”小说的奠基人,是“最伟大的现代中国作家”,早就被人们所“推崇”。夏氏还具体分析了从《狂人日记》到《阿Q正传》、《在酒楼上》等鲁迅代表性的小说作品,认为它们不愧为中国现代小说的上乘之作。
政治阴影既有直白的表露,也有曲折的投射。有些纯学术性论著,也自觉不自觉受到了政治斗争的干扰。比如,在一些高度评价胡适、徐志摩、梁实秋的论著中,往往顺便贬低一下鲁迅;在梁实秋逝世时,一些悼念文章有意无意攻击、影射鲁迅;某些论著在批评、否定鲁迅的“硬译”主张和文字时,往往缺乏节制,不恰当地扩大否定范围,甚至极度贬低几成定评的鲁迅的语言艺术成就。
二
随着台湾社会经济的转型和政治体制的变化,也随着大陆的改革开放,早在台湾“解严”之前,台湾意识形态上的各种控制已大为放松,鲁迅及三十年代文学作品象一股汹涌的潮流,一下子便冲进宝岛。“解严”之后,则继之以大规模地争相出版这些作品,评论、研讨也正式出现在报刊和文坛。“解严”令刚一颁布,《鲁迅全集》便“忽如一夜春风来”,一下子出版了四套,强烈要求将鲁迅作品纳入大、中、小学课本的呼声也得到了愈来愈多的有识之士的响应。应该说,鲁迅不声不响地进入了宝岛,而宝岛的鲁迅研究也自然而然地成了一个学术分支。谷风版《鲁迅全集》和风云时代版《鲁迅全集》的两篇《序言》,也许不妨视之为台湾鲁迅研究正式确立的标志。
题为《鲁迅的精神与文学业绩》的谷风版序,作者是著名散文家、台大教授张健,文章开宗明义便高度评价了鲁迅:
鲁迅(周树人)是中国有新小说以来第一位杰出的小说家,同时也是五四时期一位优秀、犀利的散文家与杂文家,……又是一位有分量的文学史家。……(鲁迅)无疑是二○年代小说界的翘楚。
而他的散文,爽朗隽永兼而有之;他的杂文,嬉笑怒骂,锋芒逼人。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一颗巨星。
《序言》把鲁迅的主要精神和文学业绩,归纳为如下六点:1、“爱国家爱民族”;2、“对人性的批判”;3、“对传统的批判”;4、“对政治、社会的批评”;5、“出色的文学技巧”;6、“对文坛的影响”。它高度评价《阿Q正传》和鲁迅其他的小说作品,认为《阿Q正传》“一方面固然是对中国民族性的局部呈示,一方面也是对普遍人性弱点的剖析;诸如懦怯、狡狯、阴险、迷信、残酷、愚昧、吹嘘、欺善怕恶、自我欺骗等,岂止是中国人的专利?……这些人性的弱点,不但‘放诸百世皆准’,而且更可说四海皆同。鲁迅针针见血的刻划这些,其实不外乎表白一颗爱人、关怀人类的心!”鲁迅小说的技巧,是“超时代的异数。他的三十多篇中短篇小说(包括《故事新编》在内),以现代小说的眼光而论,都不失为第一流的作品,不论人物塑造、情节结构、叙事观点、时空处理、气氛酝酿、对话、节奏,均颇讲究,而又极少斧凿痕。甚至到了八○年代,仍有不少篇是值得吾人当作短篇典范的”。对台港学人一向评价较低的鲁迅杂文,《序言》也力排众议,给予高度评价:在“以较直接、较犀利的方式正面承担”对政治、对社会进行批评的诸多杂文中,鲁迅“或一语中的,或百箭丛集,或以反为正,或声东击西,这样锋利的文笔,在中国文学史上实在是罕见的。”
《序言》最后呼吁大家“能以文学的眼光、历史的眼光、民族的眼光、世界的眼光来看鲁迅;如果仍然有人坚持以偏狭的政治眼光来端详鲁讯,那将是文学的罪人,时代的罪人”。
风云时代版《出版小引》作者陈晓林也是一位著名散文学,他的这篇题为《还原历史的真貌——让鲁迅作品自己说话》的序言,基本观点和张健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他这样写道:“中国自有新文学以来,鲁迅当然是引起最多争议和震撼的作家。但无论是拥护鲁迅的人士,或是反对鲁迅的人士,至少有一项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受到双方公认的:鲁迅是现代中国最伟大的作家。”陈氏虽然也并不首肯大陆鲁研界举扬鲁迅的某些提法和做法,但他尤其尖锐批评了台湾多年来“查禁”鲁迅的做法:
台湾多年以来视鲁迅为“洪水猛兽”、“离经叛道”,不让鲁迅作品堂堂正正出现在读者眼前,也是割裂历史真相的笨拙行径。试想,谈现代中国文学,谈三十年代作品,而竟独漏了鲁迅这个人和他的著作,岂止是造成半世纪来文学史“断层”的主因?在明眼人看来,这根本是一个对文学毫无常识的、天大的笑话!
在尖锐批评了“海峡两岸基于各自的政治目的,对鲁迅作品作了各种各样的扭曲或割裂”之后,陈氏也概括了鲁迅及其作品的这样一些主要方面:1.“鲁迅是一个真诚的人道主义者,他的作品永远在关怀和呵护受侮辱、受伤害的苦难大众。”2.“鲁迅是一个文学才华远远超迈同时代水平的作家,就纯文学领域而言,他的《呐喊》、《彷徨》、《野草》、《朝花夕拾》,迄今仍是现代中国最够深度、结构也最为严谨的小说与散文;而他所首创的‘鲁迅体杂文’冷风热血,犀利真挚,抒情析理,兼而有之,亦迄今仍无人可以企及。”3.“鲁迅是最勇于面对时代黑暗与人性黑暗的作家,他对中国民族性的透视,以及对专制势力的抨击,沉痛真切,一针见血。”4.“鲁迅是涉及论战与争议最多的作家,他与胡适、徐志摩、梁实秋、陈西滢等人的笔战,迄今仍是现代文学史上一桩桩引人深思的公案。”5.“鲁迅是永不回避的历史见证者,他目击身历了清末乱局、辛亥革命、军阀混战、黄埔北伐,以及国共分裂、清党悲剧、日本侵华等一连串中国近代史上掀天揭地的巨变,秉笔直书,言其所信,孤怀独往,昂然屹立,他自言‘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可见他的坚毅与孤独。”
陈氏也同样呼吁:“现在,到了还原历史真貌的时候了。随着海峡两岸文化交流的展开,再没有理由让鲁迅作品长期被掩埋在谎言或禁忌之中了。……恩怨俱了,尘埃落定。毕竟,只有真正卓越的文学作品是指向永恒的。”
八十年代以来,先后论及鲁迅的台湾著名作家计有刘以鬯、曾敏之、余光中、聂华苓、於梨华、柏杨、白先勇、陈若曦、陈映真、水晶、刘大任、施叔青、杨牧、西西、梁锡华、梁秉钧、柯振中、王润华、罗智、阿盛等数十位之多,虽然见仁见智,评价并不尽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政治实用主义的阴影是愈来愈淡薄了。绝大多数作家几乎众口一词地肯定鲁迅的卓越贡献与技巧,不少作家还认为鲁迅是中国最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旅美小说家白先勇的下面一段论述也许最具理论色彩:
五四时代影响力最大的小说家当然首推鲁迅。鲁迅的重要影响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他对中国旧社会封建传统的黑暗面深刻尖锐的批判揭发,他这种道德的觉醒和道德的勇气,替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树立了一种典范。另一方面是他第一次将西方现代小说的技巧形式成功地引进他的创作中而开辟了中国小说,尤其是中国现代短篇小说的新风格……他在《呐喊》、《彷徨》两部小说创作中,……创造出一连串令人难忘的角色,从阿Q、祥林嫂、孔乙己到闰土。(22)
假如说现代派小说家白先勇充分肯定了鲁迅小说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那末,乡土派小说家陈映真着重阐发、高度重视的却是鲁迅小说的政治意义和社会影响。他说:“鲁迅给我的影响是命运性的”,这个“命运性”,指的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语言、文字乃至思考方式上,但更重要的一方面则是“对中国的认同”上。“从鲁迅的文字,我理解了现代的、苦难的中国。和我同辈的一小部分人现在有分离主义倾向,我得以自然地免于这个“疾病”,鲁迅是一个重要因素”(23)。这里所说的“分离主义倾向”,也就是现在愈演愈烈的“台独”倾向。而所谓鲁迅对他的“命运性”的、“对中国的认同”的影响,也就是反对和抵制“台独”的影响。而这种至关重要的影响,恰恰是他从《呐喊》中的那些小说作品(特别是《阿Q正传》)得来的。
随着鲁迅“堂堂正正”地走上文坛,鲁迅研究的专著也陆续出现了。一类是资料性专著,如刘心皇《鲁迅这个人》(24)、周行之《鲁迅和左联》(25)、王宏志《思想激流下的中国命运——鲁迅与“左联”》(26)等;一类是研究性专著,如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27)、王润华《鲁迅小说新论》(28)、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29)、张钊贻《尼采与鲁迅思想发展》(30)、林万菁《论鲁迅修辞:从技巧到规律》(31)等。这些专著的出现,为台港鲁迅研究的长足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部资料性专著可以说都是围绕三十年代文坛特别是“左联”展开考证和论述的,有许多问题,在大陆鲁研界看来,早已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学术价值。但是,在台港学者看来,这些问题却甚有意义,兴趣大得不得了,这正是四十年隔膜的结果,同时也的确存在着不同的视角和评价。比如鲁迅的加入“左联”及其与周扬等人乃至整个中国共产党人的关系,在三部书中都是重点章节。关于鲁迅加盟“左联”的动机,在鲁迅生前即流传着的“投降说”、“左派拉拢吹捧说”、“领袖欲说”,在台港也一直有很大的市场。但王宏志却逐一分析、否定了这些说法的片面和不实,从而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其实,简单来说,鲁迅之所以加入‘左联’,原因在于他(也许是天真地)真的相信这样的一个文学团体,会对中国的文坛,甚至中国的将来带来好处。”王氏的这个结论,和大陆很多学者的看法,可谓不谋而合,似乎并无新意。但是,由于这一看法完全由王氏自己通过考辨史实得来,而并非搬用大陆学者的现成结论,无论其功力还是观点,便都相当难得了。
刘心皇的《鲁迅这个人》顾名思义,考察的是鲁迅的为人行事。其中,并于鲁迅与共产党人的关系虽然有不少误解,但在鲁迅与所谓“右翼文人”的关系方面却有不少创见。比如他严厉批评曾今可、杨邨人、邵洵美、陈代等人以及《十日谈》、《社会新闻》等杂志,说他们用造谣、诬陷、告密等手段对付鲁迅和“左联”,怎么可能不一败涂地?刘氏甚至批评当时的政府“竟是以‘全武行’对付了文事。于是,又失去了社会的同情”。他对鲁迅的一些反击文字,以予以肯定,比如《伪自由书·后记》,“确实记录了当时文坛的动态,保存了一些真实的文艺史料”。三本资料性著作的这种客观公允的态度,不仅为台港学者,而且为大陆学者树立了楷模。
几本研究性专著,都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和创见。李著可视为一部鲁迅评传,它对鲁迅创作的分析最见独到,特别是他从中国文学发展的角度高度评价鲁迅杂文,实为卓有见地。王著虽说是一部论文合集,但它集中研究鲁迅小说,自成体统,首尾一贯,可以视之为一部鲁迅小说新论。集中的《鲁迅与象征主义》等文颇见功力。林万菁是王氏高足,他的专著乃其博士论文,蒐集材料至为丰富,就对鲁迅的修辞研究而言,可谓擅一时之盛。《中国意识的危机》是一部五四时期的思想史,所论自不限鲁迅,但鲁迅却占了相当大的篇幅。它认为鲁迅是一位“非凡而繁复的人物,具有一个机智、敏锐、精微而富于创造力的心灵”。“外观上他疏远,淡漠,内心则悲愤,沉郁;但他却有一种诚挚的关怀和道德的热情,这使他能以巨大的雄辩力表达他对中国文化危机的极度痛苦。”它一方面论证了鲁迅的“全盘性反传统”,但另方面则认为传统文化的许多方面对鲁迅却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从而形成了他“意识的复杂情”。张钊贻也是一名刚刚毕业的博士生,其专著也是他的毕业论文,也同样具有视野开阔、资料丰富,充满学术锐气的特点。可以说,在“尼采与鲁迅”这一课题上,它充分占有了有关资料,并做出了许多让人耳目一新的独特判断。值得一提的是,张氏富于思辨才能,这不仅在本书中有所体现,而且他还专门撰写了批评林毓生鲁迅论的文章:《既非“整体”,何须“受苦”——评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中所论鲁迅与中国文化》(32)不管论点的是非曲直,这种学术的锐气和勇气就首先值得赞赏。众所周知,学术论争的出现,往往推动着学术事业的发展。
台港鲁迅研究对台港学术界来说是一个新兴学科,前景大可乐观。走出政治实用主义阴影则是它长足发展的重要保证。由于这种阴影笼罩港台数十年,彻底摆脱自然也非一朝一夕之功。一些充满政治实用主义味道的言词还会不时冒出来。不久前,余英时先生在香港接受访谈时,大讲鲁迅“高度的非理性”、“没有正面的东西”、“乱骂人”、“流氓风格”等等,等等(33),几乎达到了兴之所至、信口开河的地步。在90年代的今天还出现这种一味诋毁性言论,实在与海峡两岸文化互补并进而推动中华民族文化振兴的大趋势背道而驰。与上引的那些严肃的学术论著相比,也显得十分滑稽可笑。
注释:
① 1943年1月重庆胜利出版社初版,到台后再版,1987年7月台北时报出版公司增订再版。
② 台北现代文化拓展社1976年初版。
③ 最初发表于三民主义青年团机关刊《青年向导》,收入《鲁迅正传》时易名为《高尔基鲁迅会见记》。
④ 《鲁迅正传》增订版《序言》。
⑤ 《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奔涛》半月刊第1卷第2期(1937年),收入《我论鲁迅》。
⑥ 《与胡适之先生论当前文化动态书》,《奔涛》创刊号(1937年),收入《我论鲁迅》。
⑦ 胡适:《答苏雪林女士》,《奔涛》创刊号,收入《胡适来往书信集》中册,中华书局香港分店1983年初版,亦收入《我论鲁迅》。
⑧ 原载台北1958年《军友报》,后收入《我论鲁迅》。
⑨ 收入《无所不谈合集》,台北开明书店1974年10月版。
⑩ 收入《关于鲁迅》,台北爱眉文艺出版社1970年版。
(11) 台北正中书局1975年版。
(12) 台北长歌出版社1976年版。
(13) 台北正中书局1971年版。
(14) 转引自周策纵的回忆。
(15) 收入徐著《中国文学论集》,台北学生书局1965年版。
(16) 连载于《明报》1972年12月至1973年1月,收入《文学的视野》,明窗出版社1975年初版,台北远景出版社1976年再版。
(17) 《文学评论》1991年第6期。
(18) 见庄信正《才情·见解·学问——敬悼夏济安先生》,收入《异乡人语》,台北洪范书店1986年初版。
(19) 见庄信正《追忆夏济安先生》,收入《异乡人语》。
(20) 原文为《Aspects of the Power of Darkness in Su Hsun》,刊美国《亚洲学会季刊》第23卷第2期(1964年2月号),收入《夏济安选集》,台北志文出版社1971年初版。
(21) 本书英文版于1961年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中译本于1979年由香港友联出版社出版,译者为刘绍铭等。
(22) 《社会意识与小说艺术——五四以来中国小说的几个问题》,收入《第六只手指》,香港华汉出版公司1988年版。
(23) 见韦名《陈映真的自白——文学思想及政治观》,收入《陈映真作品集》第6卷,台北人间出版社1988年4月版。
(24) 台北大东图书公司1986年6月出版。
(25) 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年8月出版。
(26) 台北风云时代出版社1991年9月出版。
(27) 英文原著出版于1987年,中译本出版于1991年3月,香港三联书店,译者尹慧珉。
(28) 上海学林出版社1993年7月出版。
(29)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出版社1986年4月出版。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出版大陆版。
(30) 香港青文书屋1987年出版。
(31) 新加坡万里书局1986年7月出版。
(32) 香港《八方》杂志第7辑,1988年5月号。
(33) 张伟国:《要有民主的人格,才会出民主的领袖——余英时访谈录之三》,香港《联合报》1994年9月8日。
标签:鲁迅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鲁迅全集论文; 文学论文; 周氏兄弟论文; 读书论文; 胡适论文; 呐喊论文; 作家论文; 阿q正传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