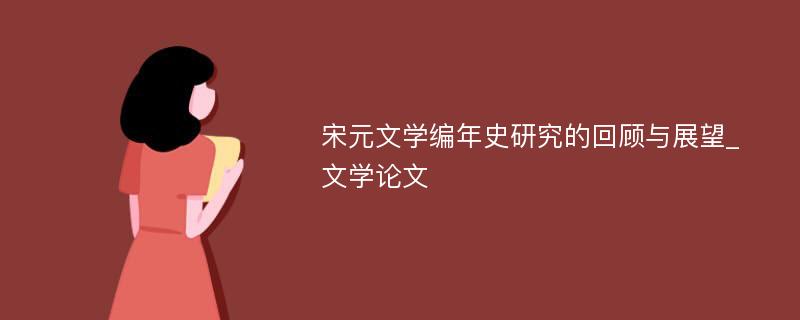
宋元文学编年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宋元论文,史研究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35(2009)04-0011-05
要进入“文学编年史研究述评”这一问题,首先要对“文学编年史”做一界定,顾名思义,就是文学的编年历史,它要展示不同时代立体交叉而又流动的文学图景。就“文学编年史”而言,既往的研究,经历了一个从“文学编年”到“文学编年史”发展过程。宋元文学编年史只是文学编年史研究的一个单元,回顾与总结其研究成果,须在综合考虑文学编年史整体成就的基础上进行。
一 文学年表
从学术发展的进程来讲,各种文学年表的制作为文学编年史的写作提供了扎实的资料基础,应当是学术递进中的重要一环。
最早以编年形式来研究中国文学的是敖士英,他的《中国文学年表》由北平立达书局1935年10月初版。该年表立足于中国文学之实际,注重其与相关学术的关联,如社会经济状况、文化政策、文学评论等等,又发扬实证精神,如作品的系年,一般都拿出证据来,目的是明晰中国文学的因革与流变。敖士英原计划要写六编,最终只完成第一编即自周至唐部分。一年之后,日本矢岛玄亮的《支那文学年表》问世——东京关书院于昭和十一年(1936)出版。该表编录自三代以降至清代几千年间中国文学的简况,表格分为五栏,依次是皇历、干支、帝王、年代、事项。“事项”一目,偏重于作家的生卒年、重大文学(文化)成果、朝廷文化政策及思想态势等,通过表格中所记叙的人物来看,矢岛玄亮的“文学”的概念比较宽泛,很多思想文化史上的人物,也大量入选,如陈瓘、刘安节、罗从彦、陈公辅等等。而且,文学家的层次(大、中、小)感不是很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固因年表的体例所限,无法给大作家太多的展示空间。另外,几乎所有文人进入到同一表格中,详列其生卒年(以熙宁、元丰间的条目为例,共约143条,其中属于生卒年的有80条),无疑会遮蔽了动态的文学流程。但作为早期一部相对完整的中国古代文学年表,它展示了文人生活的具体时段,并凸显了思想文化举措对文人写作生活可能产生的影响,其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谈文学编年史,不能不提陆侃如先生的《中古文学系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该书是陆先生研治中古文学史的初步准备工作,所以它的意义更在史实考订方面,但其体例及具体内容设置,都为后来文学编年提供很多经验,如在同一年内列举不同作家的年龄及创作活动等。80年代后期,产生了两部以编年为“骨干”的工具书:吴文治的《中国文学史大事年表》(上中下三册,上册黄山书社1987年12月第1版,中、下册1993年12月第1版)和刘德重的《中国文学编年录》(知识出版社1989年)。
以上文学年表或系年之作,或作为文学研究的工具书,或作为文学研究的基础资料整理,但其目的都是要弄清文学的基本史实。有些编撰者在编订编年史实资料时,已充分意识到这只是文学史(文学编年史)写作的初步工作,如陆侃如。有意识地为编年史做初步工作,当初步编年工作积累到一定程度时,进入文学编年史的写作,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从研究主体来讲,“意识”也会指引他转向可以操作的编年史写作上,并着手进行一些断代文学编年史的写作。此外,长期以来文学史过于单一的叙述模式(三部曲:背景、作家、作品),也促使研究者进行新的探索,并尝试别样的文学史写作。编年史作为古已有之的史学写作范式,加上前期文学编年资料的整理及基础研究的深入,文学编年史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便呼之欲出。
二 文学编年史
刘知渐的《建安文学编年史》,是国内第一部用编年的方法写作的文学史,对于更新文学史的编写工作进行了有意义的尝试。该书用编年形式总结出建安文学的发展不能归功于曹操一人,并揭示出文学发展的规律。这一创造性的尝试,获得熊笃先生的响应,写成了《天宝文学编年史》(1987年出版)。80年代后期的这两部文学编年史,虽然时间段很短(分别是25年、15年),但编者的思路非常明确,反映了初期文学编年史写作者已经具备相对成熟的理论素养。例如,他们都强调文学编年史是“编年”的“史”,不是系年录,更不是年谱汇合,而是既要“记述”又要“评述”的文学史,在作家作品的取舍方面,非常注重代表性,等等。但他们坚持的都是“纯文学”的观念,所以,许多文学性不强的作品(作家)被排除在外了。
《唐五代文学编年史》(1998年由辽海出版社出版)是第一部断代文学编年史,因此,它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史意义。该书的编写,体现了学界对于文学史的反思与探索,傅璇琮先生回顾这一过程时说:“研究文学确实应从文学艺术的整体出发,所谓整体,包括文学作为独立的实体的存在,还包括不同流派、不同地区可能互相排斥而实际又互相渗透的作家群,以及作家所受社会生活和时代思潮的影响。这样做,就会牵涉到总的研究观念的改变。但具体如何着手呢?我后来想到了编年史。我觉得文学编年史将对整体研究起一种流动关照和综合思考的作用。这也是对于长时期以来文学史著作体例所感到的一种不足。”[1]自序文学编年史有其他文学通史、断代史、文体史所不能代替的特点与优势。实际上,该书具体体例和内容,均符合傅先生的这一指导思想。仅以天宝十三载(754)为例,本年共列50条,其中涉及政治走向(安禄山入朝)、科举放榜、文人交游、礼乐制度(改诸乐名,立石刊于太常寺)、武功(哥舒翰收黄河九曲、封常清出师西征)等等,展现了安史之乱前夜社会文化的动态画卷,不仅编录了盛唐诗人群(高适、李白、杜甫、王维、岑参等)的活动,而且再现了大历诗人(如钱起、韩翃、萧颖士等)的生活。[1]899-917
《唐五代文学编年史》的学科史意义在于,突破了数十年来通行的文学史观念——纯文学观念,从傅先生的自序和该书的内容,可以看出,它背后的文学观,“是一种既具有现代科举气息而又更切合中国文学实际的大文学史观。”[2]这种“大文学史观”,用傅先生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从文学艺术的整体出发”(上文已引),希望打破文学史研究旧有的格局,把文化史甚至是社会史的研究成果引入文学史研究,从而开拓文学史的研究空间。该书突出材料性,强调实证性,不以铺叙描述或议论评析为长。作为知识体系,不直接提供结论式的断语,只从各个方面具体生动地展示有关的文学史细节、画面、素材,提供有关的原始资料。这一做法,要给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而不是让规律、结论先入为主。
其他几部断代文学编年史,如曹道衡、刘跃进的《南北朝文学编年史》,刘跃进的《秦汉文学编年史》,赵逵夫的《先秦文学编年史》等,都是在傅璇琮先生的倡导下完成的,体现了大体相同的文学观念,对相应时段的文学图景进行了有效的描绘。
陈文新主编的十八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9月出版),以编年形式演述中国文学发展的总历程,上自周秦,下迄当代,是第一部系统的文学编年通史。在体例的设计、史料的确认和选择方面,该书进行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尝试:
其一,关于时间段的设计,采取两个向下和向上两个时间序列。编年史通常以年为基本单位,年下辖月,月下辖日。这种向下的时间序列,可以有效发挥编年史的长处。另外设计了一个向上的时间序列,即:以年为基本单位,年上设阶段,阶段上设时代。这种向上的时间序列,旨在克服一般编年史的不足。具体做法是:阶段与章相对应,时代与卷相对应,分别设立引言和绪论,以重点揭示文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时代特征。
其二,对历史人物的活动,“言”和“行”并重,改变以往研究者只重视“行”(人物活动、生平)而忽略“言”(诗论、文论等)的偏向,具体到史料,包括序跋、信函、题记等等。
其三,较之政治、经济、军事史料,更加关注思想文化活动。所以,在资料的收录方面,有意加强了下述三方面材料:重要文化政策;对知识阶层有显著影响的文化活动(如结社、讲学、重大文化工程的进展、相关艺术事件等);思想文化经典的撰写、出版和评论。
三 宋元文学编年史
十八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将数千年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学以立体的方式呈现于一编之中,代表了这一领域中重要的建树,“标志着中国文学研究经由螺旋式上升的历程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3]其中的《宋辽金卷》由诸葛忆兵、张思齐、张玉璞三位先生主编,《元代卷》由余来明先生主编,他们以中国文学为本位,以史料为基础,以便于完整地呈现文学史迫近真实的面貌,二书均以资料见长,而且引用多为原始资料,每一时代之前《绪论》及每一阶段之前的《引言》,全是资料(前人对于该时代或阶段文学的看法),这些都是扎实的基本功,而且纲目细致,具体到日,条理清晰,便于查阅,为研究者提供了便利。
限于《中国文学编年史》整部书的体例所限,《宋辽金卷》及《元代卷》许多有待阐发的问题没有展开,使得一些关键的史料平铺在那里,鲜有史家大手笔给人带来的酣畅淋漓的感觉。仅以数例,试加说明:
以嘉祐二年(1057)为例,欧阳修知贡举,此事件在文学史甚至文化史都有重要的意义。王水照先生的《嘉祐二年贡举事件的文学史意义》[4]已做了精彩的评述,而《宋辽金卷》在本年正月六日条,单列一纲,在细目中引述欧阳修《礼部唱和诗序》、《归田录》,从欧阳修亲历者的角度谈礼部唱和;三月丁亥(十一日)条下,列举了一份进士及第名单。[5]上册,378事实上,该榜可谓名流辈出,不仅有文学卓异者,如二苏、曾巩等,还有以思想擅长者,如程颢、张载、朱光庭等,还有以政治出名者(虽然历史上对他们有相当的不满),如吕惠卿、章惇、曾布等,以上这些人员,大体上构成了此后五十年北宋政治文化格局的主体。另外,此次考试也是北宋诗文风气转变的一大契机,都应当点明。
再以嘉祐四年(1059)“本年重要作品”一目,共选了75首诗歌,其中欧阳修25首,苏轼父子42首。[5]上册,395与其罗列那么多,还不如选择一些重要作品,将其意义点破。此外,本年王安石作《明妃曲》二首,欧阳修、司马光、曾巩等人皆有唱和之作,在宋代诗歌史上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是宋诗风格趋向成熟的关键环节。即便不作阐述,也应该将这一事件单列出来。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宋辽金卷》在吸收最新学术成果方面,还有待加强,例如政和三年,吕本中写给其表弟赵承国一个论诗的帖子,记在《西塘集耆旧续闻》卷二中,该帖的重要意义,朱刚先生在《吕本中政和三年帖与宋代文学整体观》一文[6]中,已做了详尽地说明。该资料反而没有在《宋辽金卷》政和三年(1113)[5]中册,294-299中出现。
《元代卷》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如元仁宗皇庆元年(1312)“本年”下,列一纲“杨载以布衣召,授翰林国史院编修,与修《武宗实录》”,在细目部分,则引述了范梈《翰林杨仲弘诗集序》及黄溍《杨仲弘墓志铭》,并简述了杨载生平著述情况。[7]178如此读来,感觉很平淡,对比杨镰先生的《元代文学编年史》相应部分,发现该条却别有深意。本年,杨镰先生列了这样一条:“已在京师的虞集,与陆续来到的范梈、杨载、揭奚斯三人结识,并订交于大都”,紧接着分析了“元诗四大家”这一群体,在盛年(杨载42岁、范梈与虞集41岁、揭奚斯39岁)相聚并开始创作交流,使每个人受益匪浅,总之,这一事件对元诗整体面貌的形成起着关键作用。紧接着分析元仁宗即位之初京师文坛的状况以及四大家的诗歌交流。[8]156这些史实的评述与分析对于我们理解“元诗四大家”来说,应该有很大的帮助。
杨镰先生在文学编年史的写作中,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他的《元代文学编年史》集考证、论说于一体,是近年来文学编年史中有范式意义的论著之一。杨镰先生在《例言》开宗明义地谈到写作目的:“作为文学史著的一种,《元代文学编年史》通过对文学与历史结合部的研究,寻找文学发展的规律。”[8](凡例)编者抓住元代处于文学的转型期这一特点,在编年史中,传统的诗文与新兴的代言体小说戏曲并存,使元代文学不同体裁、流派、不同时期的作家、作品,在发展过程中有各自的位置。
在文学现象的纬度上,逐年编录文学现象,并揭示出现象背后的文学史规律或意义,如泰定元年(1324)五月,“龙仁夫为庐山东林寺僧道惠的诗集《庐山外集》作序”一条。杨先生用了两段文字来阐释该现象,第一段考证道惠其人及其《庐山诗集》;第二段论述道惠的诗风及其在元代诗学史的意义,“将江湖诗风引入僧诗的第一人……元诗史上不能没有他一席位置,不然元诗(特别是元僧诗)就失去了一部分内容。”[8]330值得说明的是,这样一条重要的文学编年史料,在《元代卷》竟被遗漏了。《元代文学编年史》的精彩之处:用文学史家的史识,对文学现象进行梳理、紬绎,从而将编年提升到“史”的高度,上举元仁宗皇庆元年(1312)“元诗四大家”的条目,便是很好的例证。
《元代文学编年史》断代编年的时间处理方法,也很有特点:以前编(中统元年以前四十年)、后录(明永乐之后)来延展元代文学的具体脉络;突破了以朝代为单元的编年史模式,前编、后录的采用,使一代文学有头有尾。若将这种处理方法应用于北宋、辽,南宋前期、金,南宋后期、元,或可弥补朝代叙事的单一与机械。例如,至元十三年(1276)正月一日,“伯颜部将阿里海涯攻陷潭州,南宋潭州守将、湖南镇抚大使李芾死之”条。[8]95杨先生的论述:“潭州之役,是元军南下最酷烈的战事。在阿里海涯麾下正面攻占潭州的将领崔斌,战后写诗凭吊李芾,其诗在宋元之际流传颇广。”紧接着,列举了李元美《长沙死事本末》等诗文及潭州陷落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这一事件同样没有选录在十八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的《宋辽金卷》及《元代卷》中。《宋辽金卷》没有编选此事件的原因,一方面因为在南宋灭亡的过程中,为朝廷死节的官员很多,失陷的城池也很多;另一方面,1278年之后的事情,已经不再是选著者关注的范围,他当然无法认识该事件在宋元之际的影响了。而《元代卷》的开始时间便是1279年,所以更不会引起编著者的关注。
《元代文学编年史》虽为编年体之作,该书却充分吸收纪传体、本末体等的优长,使事件、人物、文学间的关系清楚明白。仅以天历二年(1329)为例,略作说明:二月,陕西发生旱灾,张养浩受命前往陕西救灾。编者用互见的手法,先交待“此前张养浩凡七征而不起,一旦闻知灾情严重,夕闻命而朝就道”,在本年四月、六月、秋等条目中,两条线索同时展开:陕西灾情的始末;张养浩在灾区的情况及写作。张养浩积劳成疾去世后,又以同恕的《西亭记》对该事件进行补叙。张养浩在前往灾区途中及救灾过程中写的一系列“怀古”的《中吕·山坡羊》,[8]352-355产生于这样的历史场景,明白三者间的关联,对于理解张养浩及《山坡羊·潼关怀古》,必有启发。
《元代文学编年史》并非十全十美,有些方面还可以再增补,毕竟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如元成宗元贞二年(1296),《濂洛风雅》成书(以唐良瑞序为据)。《濂洛风雅》的意义,不仅在诗学史上确立了道学诗派,更重要的是对程朱一派理学思想以诗歌形式进行整理。可惜,这一史实并没有呈现在《元代文学编年史》中。
四 文学编年史反思录
上世纪90年代以前,学界的研究重心多放在“文学编年”上,研究成果多集中在文学年表的编订及断代文学编年资料的编撰上。但也有一些研究者不满足于文学编年资料的编订,意识到文学编年史乃文学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开始尝试以某一时段为题的文学编年工作。进入90年代后期,《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南北朝文学编年史》等断代文学编年史开始出现。新世纪以来,断代文学编年史的写作方兴未艾,如杨镰《元代文学编年史》、刘跃进《秦汉文学编年史》、赵逵夫《先秦文学编年史》等,而且,出现了大部头的编年文学通史——十八卷本的《中国文学编年史》。回顾文学编年之路,总结经验,必将对今后的文学编年史研究和写作提供鉴戒。
(一)从学科发展史来看,文学编年史是在对传统的文学史写作进行反思的基础上进行的。传统的文学史写作有自身的优势,有利于梳理重要作家的文学史意义,形成大体的判断,把握文学发展的总趋向;有利于教学,在向初学者普及文学知识时,以一流作家(作品)形成知识脉络,便于传授和掌握;但容易形成作家的“等级”制度,使文学史变成名家或名作的历史。文学编年史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弥补传统文学史带来的缺憾,在时空交汇点上,呈现出多姿多彩的文学图景,而且,伴随着立体交叉的排比、罗列,一些被隐藏的文学史实、现象得以显露,必将催生新的研究课题。文学编年史也有自身的弱点,在反映重要作家、作品尤其是对文学整体进行评判时,则显得不够明快。所以,两种不同路数、不同侧重的文学史写作模式完全可以和谐并存,这是基本的判断。厚此薄彼,轻易地抹杀传统文学史的意义,将不利于文学史学科的良性发展。毕竟,文学编年史只是文学史的一种形态而已。如果有可能,还可以摸索其他形态的文学史写作方式。
编年史作为著述体例,其长处便是能够最大限度地还原文学历史的场景。在此需要强调的另外一点:以编年史的眼光和方法来研究具体的问题,则是一种可以也值得推广的研究思路。例如我上面所举到的王水照、朱刚等先生的文章,都是以编年的思路切入文学研究,获得了与以往不同的见解。反思编年史研究,并不是所有的研究者都去写编年史,而是提醒大家注意“编年史”这样一种研究思路。
(二)文学编年史是编年的“文学史”还是文学(史)的“编年”,这是一个值得思索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和选择,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编年史写作样式,即便他们基于同样的文学史实。
认为文学编年史是编年的“文学史”,在写作时必然突出“史”的意义。具体的做法,就是在“编年”基础上作进一步的理论阐释,用“文学史”的观念统摄具体的编年史料,在看似不经意的材料之间,用“史”笔加以点拨,让前后左右的史实在文学史纲上波动。当然,这种史纲,不是拿别人的,而是通过文学编年和文学史的其他学习而感悟出来的。刘知渐的《建安文学编年史》、杨镰的《元代文学编年史》等就渗透着这种观念。
若认为文学编年史是文学(史)的编年,在编写时就会注重史料的考订和编年,也不能说他们没有“史”的概念,而是编著者不急于形成“史”的概念,或者不希望“史”评来影响甚至约束读者的思考空间。以《唐五代文学编年史》为代表的断代文学编年史以及十八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就属于此类著作。从内容的构成来看,完全是以丰富翔实的第一手资料按年月(日)编排而成。“干货”固然很好,但若没有“水”分的文学史,多少让人觉得有点涩。况且,“史”还绝非水分,而是“文学史”题中应有之义。但对于编者而言,似乎也意识到这一问题,用傅璇琮先生自己的话来讲:“严格说来,我们这样做还只是一种‘长编’,还未能如程千帆先生序言所倡导的《通鉴》淝水之战、淮西之战那样的笔法。”(《唐五代文学编年史·自序》)虽是自谦之辞,但却暗合实际。文学编年史毕竟不同于“文学史料长编”,编著者若在丰富的文学及文化史料的基础上,略加排比,使文学的“编年”上升到以“编年”为骨干的“文学史”,将是文学编年史的又一要务。
(三)在文学编年史中作家(作品)层次的呈现方式,还有待探索。在文学史的长河中,不同的作家(作品)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这是不证自明的命题。文学被历史化的过程中,作家的层次即其在文学史上的分量已被衡量、确定,其中必然有没“称”准的,但大多数还是符合文学发展实际的。文学编年史有意打破作家的“等级”层次,将所有的作家纳入同一时空坐标内,这是一种突破。但在编年的文学史中,如何凸显重要作家(作品),单靠多列举几篇作品或多系几个行实年月等细碎的条目,还不能明快地彰显其文学史意义,如何在诸条目之间建立可资考证的关联,在层次中凸显出“代表”,是今后需要进一步思索的问题。对于出色的文学编年史来说,不仅需要点拨,更需要“点睛之笔”,这也是对编著者文学史识与语言能力的综合考评。以重要作品而言,如绍兴三年二月吕本中作《夏均父集序》,九月作《谢幼槃文集序》,这两篇序是吕本中的“活法”理论的重要构成,反映了吕本中诗学思想的成熟:由强调“活”到“无法而有法”,标志着“活法”理论的升华。以重要人物为例,如吕祖谦——不以文学见长而与文学思想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与陆九韶、陆九渊兄弟有很深的交谊;鹅湖之会的促成者;陈亮的知己;曾几之外孙……对于这样的人物,如何在编年史中呈现?仅仅列举其生卒年与作品,恐怕不能显示出其代表性来。层次呈现的另一端,是文学代际之间的演进,有时呈现在同一文学时段,即上一代作家的谢幕期与新一代作家的开幕期重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将眼光局限于前一代的辉煌业绩,就会在重合的时段突出耆旧而忽视新秀。比如,宋徽宗朝初年(建中靖国至政和近十八年间),苏轼、陈师道、晏几道、黄庭坚、晁补之、苏辙、张耒等相继辞世,新一代作家开始步入文坛,如陈与义、李清照、韩驹、徐俯、吕本中等,在新、旧的衔接上,应当两条线路并进,并将其中的关联凸显出来。
综上所述,文学编年史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作为文学史的一种形式,应当充分发挥其优势,在现有成果的基础上,将文学编年史研究不断向前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