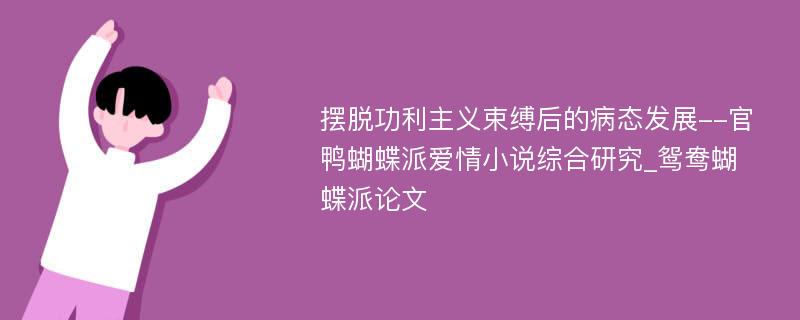
挣脱功利主义束缚之后的病态发展——鸳鸯蝴蝶派言情小说综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鸳鸯蝴蝶派论文,功利主义论文,病态论文,言情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207—4〔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1003—8353(1999)02—0132—06
一、鸳鸯蝴蝶派言情小说泛滥的成因
文学史的发展就是这样,那些不应被忘记的作家和作品,决不会因为人们的有意抹杀而销声匿迹;反之,那些不值得被人们记取的东西,不管你怎样去吹捧,它迟早都会在时间之河中沉没。鸳鸯蝴蝶派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巨大存在,经过时间的淘洗之后,仍然能够吸引人们的目光,就说明了这一点。鸳鸯蝴蝶派萌芽于清末民初,到袁世凯称帝时已初具规模,是一个跨越近现代文学两个时期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学流派。据有人统计:“由他们主办、编辑的杂志约113种, 小报和大报副刊不下50种;他们的作品,……仅长篇言情小说、社会小说就有1043部,如果把该派作者写的武侠、侦探、历史宫闱小说全部计算在内,则共有1980多部;短篇小说出版结集80多部,散见于各种杂志报刊的更难以胜数。”(注:向燕南、匡长福主编:《〈鸳鸯蝴蝶派言情小说集粹〉序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4月第1版,第1 页)对这一庞大而又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学流派,文学史不应该一笔带过。因为无论对其作品作怎样的评价,鸳鸯蝴蝶派都无可回避地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鸳鸯蝴蝶派小说创作题材广泛,后人将其分为言情小说、黑幕小说、侠义小说等,其中最具有代表性并且最能显示其创作成就和创作风格的是言情小说。鸳鸯蝴蝶派的大部分作家都致力于言情小说创作。鲁迅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对此作了概括性的论述:
那时的读书人,大概可以分他为两种,就是君子和才子。君子是只读四书五经,作八股,非常规矩的。而才子却此外还要看小说,例如《红楼梦》,……有了上海的租界,——那时叫做“洋场”,……有些才子们便跑到上海来,……
才子原是多愁多病,要闻鸡生气,见月伤心的。一到上海,就遇见了婊子。去嫖的时候,可以叫十个二十个的年轻姑娘聚集在一处,样子很有些像《红楼梦》,于是他就觉得自己好像贾宝玉;自己是才子,那么婊子当然是佳人,于是才子佳人的书就产生了。内容多半是,惟才子能怜这些风尘沦落的佳人,惟佳人能识坎轲不遇的才子,受尽千辛万苦之后,终于成为佳偶,或者是都成了神仙。
鲁迅在这段话中论述了言情小说的总体特点:(1 )言情小说产生的背景是上海的十里“洋场”,来自于资本主义世界的浮糜风气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淫风恶俗联姻,是滋生言情小说的“温床”;(2 )言情小说的作者主要是当时读书人中的“才子”。他们“是旷达的,哪里都去”。在他们身上既有封建文人放荡不羁的风流癖性,也有来自西方开放的性爱观念。正是这类人成为言情小说创作的主体;(3 )传统的“才子佳人”小说是这一流派的渊源;“才子”与娼妓们的鬼混是言情小说产生的生活基础。
言情小说在这一时期泛滥,除鲁迅所说的上述因素外,也体现了文学发展的内在要求。自梁启超提倡小说界革命以来,文学一直负担着救国保种的历史使命,这固然是崇高与神圣的,但对这一问题的过分强调,常常会冲击作品的艺术性,引起读者的逆反心理。大多数人读小说的目的是为了消遣而不是为了接受教育,可像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那种政治说教式的小说是无法满足普通读者这一阅读期待的,这就为言情小说留下了可乘之机;从社会形势来看,政治上“莫谈国事”的高压,社会的黑暗,把许多有历史责任感的知识分子赶进了文学这方“净土”,使他们把言情小说当做逃避现实的“世外桃源”。借“香草美人”以喻君子,本来就是中国文学的传统,那些踌躇满志而又报国无门的“才子”们,也就只好借“情天恨海”以浇胸中块垒了。
在本世纪初诞生的稿费制度也为言情小说的泛滥添加了催化剂。科举制被废除后,文人通过仕途获取生活资料的路已被堵死,许多文人被迫以卖文为生。为了应付“开门七件事”,追求小说创作的数量和迎和读者的口味就成为左右小说创作的外部力量。
在小说观念上,鸳鸯蝴蝶派是对自梁启超以来文学启蒙命题的背叛。它切断了文学与政治之间的连体关系,淡化了文学的历史使命感,若单从文学自身发展的要求来看,鸳鸯蝴蝶派对政治命题的逃避,有利于文学的自由发展。因为把小说当做娱乐与消闲的工具比把小说当做救国的手段更符合小说的本体特征。但这一回避历史使命的文学观念在重视文学社会功利性的人看来无疑是一种堕落,因此鸳鸯蝴蝶派自它产生的那天起就受到主流文化派的批评。不过鸳鸯蝴蝶派的言情小说也并非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污秽不堪,作为一个庞大的文学创作群体,它有着鲜明的流派特征和独特的文学追求,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他们有着明确的创作目的——娱乐与消闲。鸳鸯蝴蝶派刊物的编辑和作家们从不隐讳这一点,他们甚至还以此为骄傲。最具代表性的《礼拜六》杂志在《出版赘言》中宣称,他们的刊物之所以取名《礼拜六》,是因为从礼拜一到礼拜五人们忙于工作,礼拜日多停业交易,只有礼拜六下午是人们休闲的时间。休闲有多种方式,但读他们的小说是各种娱乐形式中的最佳方式:“买笑耗金钱,觅醉碍卫生,顾曲苦喧嚣,不若读小说之省俭而安乐也……以小银元一枚,换得新奇小说数十篇,游倦归斋,挑灯展卷,或与良友抵掌评论,或伴爱妻并肩互读,意兴稍阑,则以其余留于明日读之,晴曦照窗,花香入坐(原文如此——引者注),一编在手,万虑都忘,劳瘁一周,安闲此日,不以快哉!”(注:《〈礼拜六〉出版赘言》,《礼拜六》杂志第1 期)《游戏世界》上一则题为《玫瑰之路》的广告中说:“《游戏世界》是诸君排闷消愁一条玫瑰之路。其中有甜甜蜜蜜的小说、浓浓郁郁的谈话、奇奇怪怪的笔记、活活泼泼的游戏作品。”(注:《玫瑰之路》,《星期》杂志第28号广告栏)其它刊物如《游戏杂志》、《消闲钟》、《香艳杂志》、《眉语》等也有类似的表述。即使从这些刊物的名字上也可以看出此类刊物的品位和倾向。他们强调读者在阅读时的享受,至于读者阅读此类小说能受到多大教益或此类作品能对国家和民族产生哪些有利的影响,他们就忽略不计,或不屑一顾了。
(二)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在总体上具有浓厚的脂粉气,这是它们受“正统”文人非议的重要原因。在语言上,他们追求“无字不香,无句不艳”,大量撷取古典诗词中凄艳的词句,常常采用骈文的形式极尽排比铺张之能事。有时作者故意卖弄自己的文才,在小说中夹杂大量诗词,使小说中充满了无病呻吟的陈词滥调。鲁迅讽刺说:“北方人可怜南方人文弱,便教给他许多拳脚……南方人也可怜北方人简单,便送上许多文章:什么‘……梦’‘……魂’‘……痕’‘……影’‘……泪’,什么‘外史’‘趣史’‘秽史’‘秘史’,什么‘黑幕’‘现形’,什么‘淌牌’‘吊膀’‘拆白’,什么‘噫嘻卿卿我我’‘呜呼燕燕莺莺’‘吁嗟风风雨雨’……”(注:《鲁迅全集》第1卷,第364页)也有时作者为了语言的华丽,不惜歪曲人物的心理,因此尽管小说中出现了大量的心理描写,一般都是隔靴搔痒式的意象罗列。小说中的人物也一般为知识分子,这除了受作者生活视野的限制和传统才子佳人小说的影响之外,有时也是为了语言上的浓艳。因为作者在对知识分子进行描述时尽可以施展自己的文才。对“香艳”风味的自觉追求,给这一流派的声誉带来了恶劣的影响。《礼拜六》在自己的广告上公开宣称“宁可不娶小老婆,不可不读《礼拜六》”,把自己办的刊物比做“小老婆”,正是经济利益驱动的结果。也难怪一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将其称为“文娼”:“我以为‘文娼’这两个字,确切之至。他们象‘娼’的地方,不止是迎合社会心理一点。我且来数一数:(1)娼只认得钱, ‘文娼’亦知捞钱;(2)娼的本领在应酬交际,‘文娼’亦然;(3)娼对于同行中生意好的,非常眼热,常想设计中伤,‘文娼’亦是如此。所以什么《快乐》,什么《红杂志》,什么《半月》,什么《礼拜六》,什么《星期》,一齐起来,互相使暗计,互相拉顾客了。”(注:C.S.《文娼》, 陈荒煤主编:《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 福建人们出版社1984年8月出版,第740页)
(三)然而,需要指出的是,鸳鸯蝴蝶派的小说作家并非都是堕落文人,也并不都是逐香猎色的轻薄之徒。他们中许多人像张恨水、包天笑等都是有着强烈正义感的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在历史的危机关头,鸳鸯蝴蝶派的作家们也能够挺身而出,用他们的笔配合政治上的救亡运动。他们的刊物出过许多爱国专号、国耻纪念专号;有的报刊在五卅运动时期拒绝刊登英商广告;在“九一八”事变时拒绝刊登日货广告。还有不少作家创作了大量的“国难小说”,起到了较好的宣传作用。严峻的政治形势和国破家亡的灾难,常常使他们的言情小说带上时代的印记。《红》杂志的编者在第四十期的《编辑者言》中提醒读者:“上一期《国耻增刊》所载的文字,诸位切不可当它是游戏文字。实在是时时应该读的血泪文章。”张恨水就曾宣称要借小说达到“鼓励民气”的目的。在世纪之交的小说草创时期,有些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家曾是著名的翻译家他们的译作为世纪初文学的发展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二、中西文化交流中的病态产儿
鸳鸯蝴蝶派产生于本世纪文化转型的初期。自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就主动地对西方文化进行选择,到维新变法时期,西方文化已开始渗透到中国文化的各个层面。在文学界,大量的西方文学作品被翻译到中国来,使这一时期的文学也带上了西方文化的印记。在这时产生并逐渐成型的鸳鸯蝴蝶派小说正是中西文化交流这一大文化背景的产物。
从其创作的总体风貌来看,鸳鸯蝴蝶派的言情小说不具有明显的西化特征。他们既不像小说界革命时期的小说家那样明确表白以西方文学为师法对象,也不像五四时期的作家那样直接横向移植西方文学的创作手法。尽管如此,中西文化的撞击依然在其创作中留下鲜明的印记。也许当文学艺术界的主流派醉心于模拟西方的时候,鸳鸯蝴蝶派的陈词滥调本身就表明了他们对西方文化的态度。
鸳鸯蝴蝶派的许多具有广泛影响的言情小说基本上用的是文言骈体形式创作的,这显示了某些小说家故意使小说向诗词靠拢的愿望,以及对小说“雅化”的追求。可许多该流派的言情小说已采用了典范的白话文和新式标点。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大部分作家像张恨水、文宗山、范烟桥等都积极地采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成果,规范地使用新式语法和标点,其语言的干练圆熟与五四作家相比并不逊色。
在小说的情节和人物命运的设置上,鸳鸯蝴蝶派的许多作家明确表示对传统的大团圆结局的反感。但他们在创作中很难避免这一根深蒂固的创作模式对他们潜在的影响。言情小说中的主人翁常常是男性知识分子和大家小姐或深通诗书礼义的名门淑女。知识分子由状元变为才华横溢的作家或文人,其实仍然是才子的化身。而女性无论出身如何(一般出身高贵),外表总是“弱柳拂风”、“齿白唇红”,其实依然是传统“佳人”的翻版;在作品结局上,鸳鸯蝴蝶派的言情小说把传统的大团圆几乎都改成了悲剧。汗牛充栋的凄惨故事成为世纪初爱情文学的奇观。把喜剧统统改成悲剧,是为了避开传统,也怕被指责为因循守旧,说明从作家到批评家都存在着强烈的创新冲动。但他们也许意识不到,当几乎把所有的喜剧都换成悲剧时,同样也会陷入新的程式化之中。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亦步亦趋是模仿,反其道而行之也是模仿。当然如果把铺天盖地的悲剧作品都理解为逆反心理的结果,也并不恰当。悲剧的产生与近代社会局势的动荡和知识分子生活的艰难也有很大关系。不过无论怎样,众多的以悲剧结尾的作品真正称得上优秀悲剧的着实不多,这说明悲剧只是处理素材的一种手段,还没有能够渗透到作家血液中,也没有成为作家把握生活的内在方式。
在文学渊源上,鸳鸯蝴蝶派的消闲娱乐倾向和拜金主义主张同样是中西文化畸形结合的产物。在封建社会的文学史上,诗文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小说处于文坛的边缘,没有资格与世道人心、社稷安危发生联系,它的职能只是供人们消闲和娱乐,借以打发多余的时光。古代小说尽管不能像近代小说一样可以直接给作家带来经济利益,但说书者为了吸引观众,也会以听众的兴趣为转移,这不可能不对小说的作者产生影响,从而形成了迎合世俗的小说创作风气。鸳鸯蝴蝶派正是对这一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朱自清指出:“在中国文学的传统里,小说和词曲(包括戏曲)更是小道中的小道,就因为是消谴的,不严肃。不严肃也就是不正经;小说通常称为‘闲书’,不是正经书。……鸳鸯蝴蝶派的小说意在供人们茶余饭后消遣,倒是中国小说正宗。”(注:朱自清:《论严肃》,《中国作家》创刊号,1947年10月)鸳鸯蝴蝶派将小说世俗化(有时也是庸俗化)的过程中西方文学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晚清译界由于自身的盲目性,把西方的通俗小说像《华生包探案》等都当作西方文学的杰作大加鼓吹,对当时的文学界产生了严重的误导。事实也证明当时的文学界还没有形成一套明确的文学观念,通俗文学和严肃文学的界限还不够清晰,再加上对西方文学缺乏全面的了解,致使在选择上出现失误。言情小说自然也就堂而皇之地以正统文学自居。另一方面,言情小说的悲剧结局也明显地受到了《茶花女》的影响。《茶花女》的结尾,男女主人翁均以死而告终,使小说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玉梨魂》的结尾带有《茶花女》的印记,但法于正而得于偏,《茶花女》的悲剧结尾,以沉重的悲愤,控诉了等级观念和家长制对爱情的禁锢,具有鲜明的反封建色彩;而言情小说(如《玉梨魂》)处处以“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古训作为最高的道德律令,来规范主人翁的言行,使情与礼的冲突最后以情的失败成全了礼的权威地位,大大削弱了作品的批判力量。简单地说,《茶花女》在情与礼的对抗中,以情的悲剧来昭示礼的罪恶,而《玉梨魂》却是以对情的克制来显示礼的崇高,这二者有着根本的区别。作者似乎也意识到了爱情的神圣,但在礼的面前,爱情显得脆弱不堪,只能使人“同声一哭”,还构不成对礼——这一至高无上的理性原则的挑战,悲剧的根源最后只能归结为“天地不仁”。正如时人所说:“附天地不仁,而玩弄男女,使男女姻缘错误,以是而男女感情随苦,以是而男女以爱情以死。”(注:周亮夫:《〈雪鸿泪史〉序七》,《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小说集6卷》,上海书店1991年4月第1版,第607页)这无疑放过了对爱情真正凶手的批判,把读者引向了人生无常的感叹之中,在封建文学史上,这早已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可以说,言情小说尽管效法《茶花女》,却没有能够展示个性主义这一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主导精神。它还不能像五四时期的作家那样,以鲜明的反封建思想捍卫爱情的尊严。
总之,鸳鸯蝴蝶派仍然是中西文化结合后的产儿,只是这个产儿由于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最终呈现出畸性状态而被后人诟病。
三、鸳鸯蝴蝶派的历史地位
作为一个庞大的文学流派——鸳鸯蝴蝶派是20世纪中国文学不可忽视的存在。可长期以来,由于一些非文学因素的干预和影响,一直未能对其作出一个中肯的评价。随着社会的发展,今天重评鸳鸯蝴蝶派的时机已经成熟。
在研究鸳鸯蝴蝶派时不能仅仅以文学研究会的是非为是非,应该把鸳鸯蝴蝶派放在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一大的背景下重新进行考察,以便还其本来面目。长期以来,文学史上把文学研究会对该派的批判当作对鸳鸯蝴蝶派的评价的终极结论。事实上,文学研究会对鸳鸯蝴蝶派的批判既包含着文学主张之间的冲突,也不可排除宗派意识的干预作用。今天,我们必须也应该剔除这些非文学因素的干扰,并以宽容和公正的态度进行仔细的分析和评价。鸳鸯蝴蝶派与文学研究会在文学的社会作用问题上,是冰炭不容的,这成为他们产生分歧的焦点。文学研究会是功利主义的文学团体,他们主张:“把文学当做高兴时的游戏和失意时的消遣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是于人生很切要的工作,正象劳农一样。”文学研究会的理论家茅盾认为:“他们(指《礼拜六》派的文人——引者注)把人生当做游戏,玩弄笑谑;他们并不想享乐人生,只把它百般揉搓使它污损以为快,在这地方尽够显出病理的状态来了,(幸恕我举出狂人喜弄不洁的事来作例。这样的下去,中国国民的生活不但将由人类的而入于完全动物的状态,且将更下而入于非生物的状态里去了。”(注:茅盾:《真有代表旧文化旧文艺的作品吗?》,《小说月报》第13卷第11号)在文学主张上与文学研究会有分歧的创造社在批判鸳鸯蝴蝶派的文学倾向上与文学研究会走到了一起,成仿吾在创造社诸成员中是较早向鸳鸯蝴蝶派发难的,他在《歧路》中说:
这些《礼拜六》,《晶报》一流的东西,虽然也是应运——应恶浊的社会之要求而生的,然而他们已经积成应运以上的流毒了,他们的罪恶,可比天上的繁星,我现在只略举其大一点的:
第一,他们是赞美恶浊社会的,他们阻碍社会的进步与改造。
第二,他们专以鼓吹骄奢淫佚为事,他们破坏我们的教育。
第三,他们专以丑恶的文章,把人类往地狱中诱惑,他们是我们思想界和文学界的奇耻。
总上所述,无论是文学研究会还是创造社,他们对鸳鸯蝴蝶派的批判都集中在思想内容和社会效果方面。在他们看来,鸳鸯蝴蝶派作品的思想内容是:“骄奢淫佚”、“玩弄笑谑”,以至于“流毒”四播,“把人类往地狱中诱惑”。这种只攻一点不及其余的作法,在当时有着致敌于死命的威力,便毕竟不能成为文学史的定论。鸳鸯蝴蝶派的游戏文字中不乏香艳的文字描写,但给它戴上“诲盗、诲淫”的罪名不能不说是有些冤枉的。他们中的大部分名家在创作时态度还是非常严肃的。由于文化观念的保守,他们恪守着“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处世原则,对两性关系的描写非常谨慎,仅就这一点来看,与五四作家相比他们要迂腐的多。我同意一位论者的说法:“五四作家批评鸳蝴作家‘诲淫’,可以说是一种不必要的误解。几个主要的鸳蝴作家,其言情小说的毛病不但不是太淫荡,而且是太圣洁了——不但没有性挑逗的场面,连稍为肉欲一点的镜头都没有,至多只是男女主人翁的一点‘非分之想’。”(注: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1卷,第214页)自然,作为一个驳杂的文学流派难免鱼龙混杂,一些末流小报也登载一些不堪入目的淫秽之作,然而这是每个时代都有的,它不能代表鸳鸯蝴蝶派文学创作的主流。就徐枕亚、吴双热、李定夷等几个主要的言情小说家的创作来看,不仅无“诲淫”的情节,他们也并不完全赞成把文学当做纯粹的娱乐品。吴双热在为《玉梨魂》写的《序》中称赞该作“居然强作庄严,期发乎情至乎礼义耳。未许文君志夺,调红粉而重整恩情;宁教司马魂消,抚青衫以徒捐涕泪。”观念自然是陈旧的,也不敢越礼义之轨,但依然顽强地显示着作者在思想上的追求。《玉梨魂》的结尾,何梦霞投笔从戎,体现出“是七尺奇男,死当为国;作千秋雄鬼,生不还家”的英雄气概,写出了知识分子在国难当头时以天下为己任的历史责任感。吴双热在为自己的《孽冤镜》写的《自序》中也表白:“嗟乎!《孽冤镜》胡为乎作哉?予无他,欲普救普天下之多情儿女耳;欲为普天下之多情儿女,向其父母之前乞怜请命耳;欲鼓吹真确的自由结婚,从而淘汰情世界种种之痛苦,消释男女间种种之罪恶耳。”(注:吴双热:《〈孽冤镜〉自序》,《孽冤镜》,1914年民权出版部出版)也许其作品与其目的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间隔,而这创作目的本身并非全然是娱乐和游戏。所以应对这些名家进行独立的评价。
鸳鸯蝴蝶派的趣味主义和庸俗化主要体现在他们所办的报刊上。这一流派的一些主要刊物都毫不掩饰自己趣味至上的倾向。颇负盛名的言情小说家李定夷在为《消闲钟》写的《发刊词》中也同样使用了许多诱惑性的语言来吸引读者。由于鸳鸯蝴蝶派的报刊众多,所以刊物为了生存,展开竞争,纷纷以迎合小市民的欣赏习惯为能事。有些报刊为了引起社会的关注,向读者搞一些无聊的征集活动。《红玫瑰》提出“向女子求婚时,用什么方法,是最能得到胜利的”这一无聊的问题,让读者回答,并且“答案的性质,须趋向于滑稽的”。类似的活动,几乎成为刊物促销的手段。著名的《礼拜六》周刊,还经常刊登一些读者写的“《礼拜六》是我的情人”、“《礼拜六》使我害了相思病”、“《礼拜六》是我的良伴”等肉麻的捧场文章,对读者进行煽情。既然处处以满足读者——尤其是下层市民的阅读需要和猎奇心理为最高目的,就很难保证刊物的质量。此等刊物的商业化和文学的世俗化是资本主义经济投机手段和封建文化糟粕相媾合的产物。但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其刊物的品味与具体某一个作家的创作特点之间并不总是一致的。像徐枕亚,其言情小说的质量也许并不高,把他放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进行考察,他并不醒目,但其对言情小说的态度还是很严肃的。他谈到作品的感染力时说:“阅者纸上千行泪,乃著者笔头一滴血换来的也。质言之,非文人之笔墨足以感人,实文人之至情足以感人耳。”(注:徐枕亚:《〈孽冤镜〉序》,《孽冤镜》,1914年民权出版部出版)这同无关痛痒地制造故事以资消遣的趣味主义是有区别的。徐枕亚文学创作的核心问题是“情”,在鸳鸯蝴蝶派中他是最具代表性的泛情主义者。徐枕亚所说的“情”,不仅仅指男女性爱之情,也包括来自生活各个方面的体验和感受。徐氏终生嗜酒,母亲专断,两个夫人先后病逝,都在他的感情上留下很深的创伤,最终都渗透到他的创作之中。其作品以男女之情为主,有着“不得已托之美人香草以自娱”的因素,早有论者指出,《玉梨魂》就带有明显的自传性质。但情为慧根,亦为痴魔,它在成就徐枕亚的同时也限制了他的视野,因此徐枕亚的文学创作并没有获得长足的发展。即使如此,他的泛情主义对纠正梁启超的文学工具论和贯穿整个世纪的文学功利主义观念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收稿日期:1999—02—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