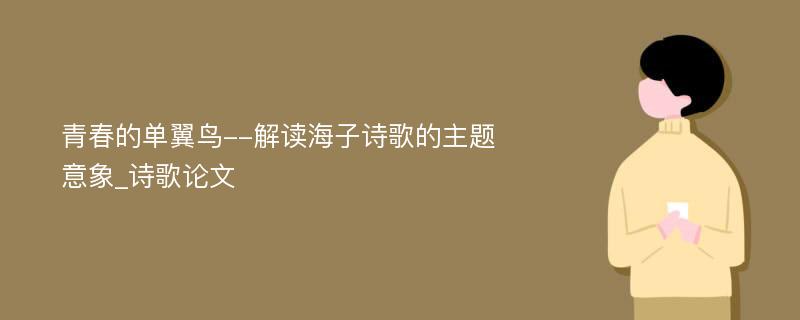
青春的单翅鸟——海子诗歌的主题意象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象论文,海子论文,诗歌论文,青春论文,主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28X(2000)03-0001-08
海子,原名查海生,1964年生于安徽省怀宁县高河查湾,1979年入北京大学法律系就读,毕业后在中国政法大学执教,1989年3月26日在山海关附近卧轨自杀。在不到7年的创作生涯里,海子写下了大量的诗歌作品。已出版的作品有长诗《土地》(春风文艺出版社,1990)、《海子的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和《海子诗全编》(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99)等。作为八十年代后期新诗潮的代表诗人,海子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地位十分重要。骆一禾认为“海子是我们祖国给世界文学奉献的一位有世界眼光的诗人”[2](P18),谢冕称“他已成为一个诗歌时代的象征”[2](P2),张炯主编的《新中国文学五十年》评价说:
他创造了仅仅属于他自己的意象系列,他的诗歌语言与前此流行的新诗潮的语言全然有别。他建立了属于自己的诗歌风格。他是当代最具独创性的一位诗人。[3](P10)
海子诗歌的意象并非支离散碎,其中有着贯穿始终的主题意象,这一点已为不少有识之士所肯定。如在《试论海子的诗歌创作》一文中,邹建军指出海子的诗是“既有闪光意象的诗句而又有完整结构的艺术生命体”[2](P240)。但海子诗歌的主题意象究竟是什么?目前研究者对此分歧颇大。在上文中邹建军认为是“麦子”:“‘麦子’意象之于海子,犹如‘太阳’意象之于艾青,‘雨巷’意象之于戴望舒”[2](P243);在《海子〈亚洲铜〉探析》一文中,奚密提出了“火”:“以火为中心,诗人创造开展出许多组意象;这些群组之间又互相联系,形成一复杂庞大的象征体系。”[2](P87);在《海子诗歌:双重悲剧下的双重绝望》一文中,宗匠认为海子诗歌中存在两类相对抗的意象:一类是麦子、麦地,一类是太阳(阳光)、月亮(月光),“这两类意象的相互碰撞、物质与精神的永恒对抗,构成了海子诗歌的基本主题,也即生命痛苦的主题。”[2](P151);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提出“麦地、村庄、月亮、天空等,是海子诗中经常出现的、带有原型意味的意象”[4](P309);在《海子:诗人中的歌者》一文中,王一川强调“‘远方’是海子诗反复出现的重要形象’[2](P248)。本文不惮冒昧,就此作深一步的探讨。
一、青春远行
本人从海子具有代表性的诗歌作品中提炼、概括出“青春远行”作为海子诗歌的主题意象,海子诗歌(尤其是其抒情诗)就是紧密围绕着“青春远行”这一主题象意来展开的。这个主题意象统贯着他的全部作品,从中又生发、延展出其他一系列诗歌意象,如:火、太阳、水、阳光、月亮、天空、远方、麦子、麦地、草原、黄昏、黑夜、姐姐、姐妹……。诚然,“青春远行”作为一个概念并不直接见于海子的诗歌文本中(海子诗歌中“青春”、“远方”出现的频率很高),但它却如同种子,播洒在海子诗歌的每一块“麦地”;它统摄着海子诗歌的其它意象,浸透在诗人创作情感的方方面面,贯穿其诗歌生涯的始终。诗人的一生与此纠结在一起,他的生与死都与此有着脱不开的干系。围绕这一主题意象所涉及的相关问题是:
1.WHO——即“远行”的抒情主人公是“谁”;
2.WHEN——即抒情主人公“何时”进行自己的“远行”;
3.WHERE——即抒情主人公的“远行”去往“何地”;
4.WHY——即抒情主人公“为何”要进行“远行”;
5.HAO——即抒情主人公“如何”进行“远行”。
可以说,海子诗歌就是紧紧围绕这五个问题展开的,诗人短暂而闪光的一生就是对这五个问题的解答,最后又以卧归自杀这种奇特的方式为此划上一个并不完满且令人忧伤不已的句号。
细读海子的诗歌,人们不难看出诗人的歌吟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青春的歌吟。呈现在我们脑海的是这样一个抒情主人公形象:他来自南方的乡村,对大地、村庄、麦子有着天然的情感联系。在《活在珍贵的人间》中他写道:
我
踩在青草上
感到自己是彻底干净的黑土块
这种对土地的情感,不可能是一个在都市生长的人所具有的,它只能出自一位自幼赤脚走在田埂和青草地上的农家之子之手,它混杂着诗人对少年时代乡村生活的鲜活而美好的回忆。海子对于故乡有着永远割不断的“情结”。在他16岁到北京上大学之前,海子一直生活在农村。他曾自豪地对朋友说:“乡村生活至少可以让我写上十五年。”因而乡村以及与此相关的诗歌意象(村庄、大地、麦地、雨水、青草、草原、河水、麦子等)大量进入他的诗篇绝不是偶然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海子虽然醉心于抒写乡村,但他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乡村田园诗人,像中国古代的陶渊明和美国诗人弗洛斯特那样。对于海子来说,乡村只是他的生长地而非他的文化身份,作为一个工作和定居于都市的知识分子,他本质上已经不是个农民了。1989年寒假他回乡探亲,家乡的现实状况“给他带来了巨大的荒芜之感”,这个乡村的歌者感觉自己“完全变成了个陌生人”。[2](P30)可见,他所歌吟的乡村只能是美化了的记忆的、想象的乡村而绝非是现实的乡村,这种歌吟最终止步于远方游子对故乡作超越时空的深情怅望时的那一份“乡愁”。在此我不同意学友谭五昌的一个观点,在《海子论》一文中他提出:
海子爱与美的理想在现实生活中几乎处处落空的尴尬境况,导致他产生精神强烈的逃亡冲动,然而一味的精神逃亡必然又会导致心灵的无限疲累,而且也无法寻求到灵魂的归依……这样,当生存于都市背景的海子把目光转向田园(乡村)时,一种浓郁的田园情怀便不可遏制地萌生了。[2](P194)
按照这一阐释逻辑,海子成了一个厌倦都市生存现实的逃避者,而乡村田园则成为他的精神避难所了。我反对把海子解读成这么一个逃避现实的可怜虫角色,海子决非是个泯灭了现实热情的隐士陶渊明或王维,对于他们来说,田园情怀确乎是厌倦现实、厌倦官场的逃亡冲动所导致的结果,“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陶渊明《归园田居》);然而海子始终生活在北京,他既没有像陶渊明那样返回故里躬耕田亩,也没有像王维那样在京郊辋川拥有别墅。况且在他诗歌中也找不出任何赞美“隐居”和“逃亡”的诗句。自称“浪子”的海子毋宁说更像那高歌“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王维《少年行》)的意气风发的青年王维或是放言“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李白《上李邕》)的豪情满怀的青年李白。而且海子曾明确表示他非常讨厌陶渊明等东方诗人身上的那种文人气质,“他们苍白孱弱,自以为是。他们隐藏和陶醉于自己的趣味之中。”[1](P897)对于海子来说,田园情怀不是逃亡冲动所导致的结果,毋宁说,那是一个生长于乡村的农家子所天然具有的、永远割不断的情怀。实际上,对于海子来说,故乡田园就是他进行青春远行的始发地。也就是说,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春天的日子里,我们的抒情主人公怀着眷恋之情,出于追求远大理想和不朽荣耀的崇高目的,收拾好简朴的行装,挥手告别故乡的山川草木,独自踏上了青春远行的漫漫旅程。总之,海子的诗歌生涯的逻辑起点虽然是在北京,但他诗歌的情感起点却不是在北京,而是在故乡——但又不是他现实的贫瘠的故乡,而是经过美学提升之后的记忆的、想象的“故乡”,即生命的依托和精神的家园(这一点可以说明海子身在北京,但直接描写都市生活和感受的诗篇几乎没有)。他写道:“我要在故乡的天空下/沉默不语或大声谈吐/我要在头上插满故乡的鲜花”(《浪子旅程》);有时他又将它径直称作“土地”,如长诗《土地》;或“大地”,如“香味,来自大地的无尽忧伤”(《北方的树林》);或“村庄”,如“村庄,五谷丰登的村庄,我安顿下来”(《村庄》);或“麦地”,如“有时我孤独一人坐在麦地为众兄弟背诵中国诗歌”(《五月的麦地》)。
从某种意义上说,海子短暂而光辉的一生可以看作一次又一次的“青春远行”。而他的第一次“青春远行”,则不能不从他15岁由安徽那个偏僻的乡村千里迢迢来京求学并定居于此算起,这次“青春远行”恰似“怀抱四方之志,乃仗剑去国,辞亲远游”(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从四川跑到都城长安的青年李白。不同的是,李白居留长安数年赢得天子的降阶相迎和“谪仙诗人”的清誉,而海子却全方位地饱尝京城“居之不易”的苦涩。这与他的自身条件有关。海子身材矮小,性情似女性一般内向、柔弱、温和,还带着些自卑,并有着浓重的“自恋”倾向。在《明天醒来我会在哪一只鞋里》他写道:
我不声不响的
带来自己这个包袱
尽管我不喜欢自己
但我还是悄悄打开
“不声不响”、“悄悄打开”这里描绘的通常是一种女人(尤其是少女)所具有的性格特征。甚至“不喜欢自己”的自卑口吻也分明烙上了“第二性——女人”的性别烙印,毋宁说,它简直就是一个少女在进行内心独白。海子的抒情诗偏爱选用“静静地”、“美丽”、“安详”、“飞翔”、“忧伤”、“月亮”、“女儿”、“姐姐”等音节柔和的字眼,这也能说明他的女性化倾向。从这个角度读解海子,我们对他诗中大量出现的“姐姐”、“姐妹”等词的所指也就不难理喻了。类似诗句还有:“贫穷孤独的少女 像女王一样 住在一把伞中/阳光和雨水只能给你尘土和泥泞”(《雨》)、“萨福萨福/亲我一下”(《给萨福》)、“今夜我只有美丽的戈壁 空空/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日记》)和“我是中国诗人/稻谷的儿子/茶花的女儿”(《诗人叶赛宁》)等。除了像《四姐妹》等少数诗中的女性实有所指——他爱过的四位女性,不少实际上就是指称抒情主人公自己。海子实际上是戴上女性人格面具(阿尼玛面具)来进行抒情,其情形恰似“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金昌绪《春怨》)之类的中国古代“代言体”诗。除了戴上女性人格面具外,将自我进行裂变也是海子常用的诗歌修辞手法。例如他将自我想象成他所崇敬的诗人叶赛宁:“和另一位叶赛宁分手/用剥过蛇皮蒙上鼓面的人类之手/自杀身亡”(《绝命》);有时又想象成从天堂下降到凡尘的耶酥:“就让我歇脚在马厩之中/如果不是时辰不好/我记得自己来自一个更美好的地方”(《让我把脚丫搁在黄昏中一位木匠的工具箱上》);有时还将自我分裂为多个:“春天,十个海子全部复活”(《春天,十个海子》)。
海子天性善良、敏感但又易受伤害。他自命天才,志向高远,但处理复杂现实问题的能力则近乎“弱智”。这在这种情形下,海子对都市生活的极不适应是不言而喻的。海子对都市的失意和迷惘在他的一些诗中有所反映,如《浪子旅程》:
我本该成为
迷雾退去的河岸上
年轻的乡村教师
……
但为什么
我来到了酒馆
和城市
我要还家
我要转回故乡,头上插满鲜花
值得注意的是诗题“浪子旅程”。显然,海子是把城市(在此指北京)仅仅看成自己“青春远行”中的一站,而非终点(否则就与他的“浪子”称号名实不符了)。确实,对于海子来说,他最好的命运就是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回到他所挚爱的乡村过一种恬静、简朴的教书和著述生活,像他所推崇的那个“有脑子”(《梭罗这人有脑子》)的美国作家梭罗一样,定居北京则属于抉择性错误。海子不是诗人波德莱尔,波德莱尔是上帝出于抒写巴黎的需要而安排他生于巴黎的,他属于巴黎,而海子则不属于北京。因此他孤独、苦闷,时不时地用酒来麻醉自己:“在什么树林,你酒杯倒倾/你和泪饮酒……”(《夜晚,亲爱的朋友》)。在《浪子旅程》的结尾处,海子虽然喊出了“我要还家”,但却没有回去。为什么呢?因为他已回不去了。且不说现实乡村物质的贫困和信息的闭塞,更重要的是他不甘心放弃自己“以梦为马”的宏大诗歌抱负:“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我选择永恒的事业”(《祖国,或以梦为马》),而这是中国的现实乡村所无法给予的。海子还有着青年人的虚荣心:他不能窝窝囊囊地回去,而是要“头上插满鲜花”地荣归故里,让故乡为有他而感到骄傲。都市的生活现实虽然处处不尽人意,但是一个天才必须学会忍受,虽然为此他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况且,比北京更遥远的远方还在声声召唤着他。这个道理是由“瘦哥哥凡高”启示给他的:凡高为学画从荷兰的乡村来到巴黎,但巴黎只是他理想行程的一站,而非终点,不久他就离开巴黎,来到那阳光暴烈,长着麦子,盛开着向日葵的乡村阿尔。在《阿尔的太阳——给我的瘦哥哥凡高》中他写道:“到南方去/到南方去/你的血液里没有情人和春天……”
于是海子将可怜的积攒放进背包(其中还装着他自费打印的诗稿以备送给可能需要它的诗友),开始他第二轮的“青春远行”,这次他远行到更遥远、更荒凉的地方——四川、甘肃、青海、西藏。这就是一个“浪子”的宿命:“浪子”虽然恋家但又命中注定不属于家。他写道:
我要做远方的忠实的儿子
和物质的短暂情人(《祖国,或以梦为马》)
哪辆马车,载你而去,奔向远方
奔向远方,你去而不返,是哪辆马车(《夜晚 亲爱的朋友》)
远行中,他饱尝了孤独的滋味:“青海湖上/我的孤独如天堂的马匹”(《七月不远——给青海湖,请熄灭我的爱情》);体验到一种混合着幸福感的痛苦:“远方的幸福 是多么痛苦”。(《远方》)
海子是个极端情绪化的人,海子的情绪具有纠葛变幻、阴晴不定的特征。黎明时他通常情绪高昂:“我是一个完全的人我是一个无比幸福的人/我全身的黑暗因太阳升起而解除”(《日出》);在雨天他觉得自己是位“住在一把伞中”独守孤独的少女:“你在伞中,躲开一切/拒绝泪水和回忆”(《雨》);黄昏时分他跌入忧伤、痛苦的低谷:“这个黄昏无限痛苦/无限漫长 令人痛不欲生”(《秋日黄昏》);黑夜则他总让他想到死亡:“这是一个黑夜的孩子,沉浸于冬天,倾心死亡”(《春天,十个海子》);恋爱中的他高喊:“活在这珍贵的人间/人类和植物一样幸福/爱情和雨水一样幸福”(《活在这珍贵的人间》);失恋时的他情绪低落:“我们坐下 感受茫茫黄昏/莫非这就是你我的黄昏/麦田吹来微风 顷刻沉入黑暗”(《北方的树林》);有时坚信自己终将成功:“我知道自己终究会幸福/和一切圣洁的人/相聚在天堂”(《给母亲》组诗);有时又因前途渺茫而大放悲声:“我站在这里,落满了灰尘,四年多像一天,没有变动”(《遥远的路程:十四行献给89年初的雪》)、“我年华虚度 空有一身疲倦”。(《祖国,或以梦为马》)
然而海子最青春、最纯洁的一次表白莫过于这首《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
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
告诉他们我的幸福
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
我将告诉每一个人
的确,这是诗人最感人至深的内心独白,它因其真率的情感流露和近乎无技巧的技巧而赢得巨大声誉。从摘录的这两段看,海子似乎要放弃自称“孤独的僧侣”(《无名的野花》)似的生活,放弃自己“青春远行”的计划和远大的诗歌抱负,与世俗所谓的“幸福”准则(无非是乘年青拼命赚钱,盖上一栋宽敞的房屋;陶醉于买菜、做饭等日常琐事和利用现代化交通工具游山玩水的休闲乐趣,在其中消磨意志,悠游卒岁)妥协,与家乡那些因不理解而导致情感隔阂的亲人们(海子家人对他的事业至今无法理解;他的死使其原本贫寒的家境雪上加霜)和解。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海子就不是海子了。那么,海子的上述抒情抑或是矫情和媚俗的“伪抒情”?否!人是个矛盾的、复杂的多面体,即便伟人也并非身上的每个细胞都超凡脱俗,作为一个生活才刚刚开始的青年,海子憧憬美好幸福的生活是无可厚非的。一个人成为英雄还是成为孬种通常只在刹那间的选择意愿。问题的关键不是他是否曾有过放弃远行、悠游卒岁的念头,而是他追求身后不朽荣耀的愿望最终压倒了这种庸常之念,最后他选择了走上诗歌祭坛而没有成为“走下十字架的耶酥”(卡赞扎斯基语)。在这个意义上,我激赏骆一禾对海子的评价:“他是一位诗歌烈士。”[2](P12)
总之,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知道,“青春远行”里的“青春”实际上可以作以下双重读解:它既是作为“远行”的修饰语出现,构成“青春的远行”这一偏正词组,又以主词的面目出现,构成一个主谓结构的词组。因而,首先“青春远行”必须是以青春的名义来进行的。确乎,要进行海子式的远行,光凭诗才是远远不够的,唯有血气方刚、无牵无挂的年青小伙子才有如此充沛的体能、激情、胆量、勇气和意志力来进行这样一场近乎玩命似的较量。其次,“青春远行”在目标指向性上具有特殊性。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奥德修斯(罗马名字叫尤利西斯)曾在海外飘泊了十八年,但他的目标指向性从不含糊:回家!回到爱妻潘奈洛佩和爱子贴雷马科身边去!像这种飘泊就属于成人的飘泊而不属于“青春远行”。与这种成人的飘泊不同,海子式的“青春远行”在本质上是一种“浪子”的远行,其目标指向性不是指向“家”,而是指向遥远的“天边外”(尤金·奥尼尔语)。再次,“青春远行”在本质上是以青春作赌注的一种美学历险,其结果往往不是奥德修斯式的肤浅的喜剧性大团圆,而是悲剧性地“死于中途”(《泪水》)。
二、因飞得太高而陨落
海子自成体系的诗学观中有一个独特的理论。在论文《诗学:一份提纲》里海子把诗人分为两类:一类是体现了伟大的人类精神,成为“人类的集体回忆或造型”的亚当型巨匠,他们是诗坛之王,其代表人物有但丁、莎士比亚、歌德等;另一类是从亚当挣脱出来的夏娃型诗人,也叫浪漫主义的王子型诗人,其代表人物如雪莱、普希金、叶赛宁、荷尔德林、爱伦·坡、马洛、韩波、克兰、狄兰……,其中浪漫主义之父“卢梭是夏娃最早的咿呀之声”[2](P286)。海子以中国古代皇子夺嗣,成者继位败者不得善终的奇特眼光来看待这些具有纯洁气质的浪漫主义才子:“(他们)一直由自由的个体为诗的王位而进行血的角逐……最优秀最高贵最有才华的王子往往最先死亡”[2](P289)。海子哀叹道:
他们是同一个王子的不同化身、不同肉体、不同文字的呈现、不同的面目而已……他们悲剧性的抗争和抒情,本身就是人类存在最壮丽的诗篇。他们悲剧性的存在是诗中之诗。他们美好的毁灭就是人类的象征。[2](P289-290)
对于诗化人生的浪漫主义诗学原则的践履,使他自觉地从心灵深处催生出生命的悲剧意识,因而,悲剧性结局也就成为海子无法逃脱的宿命。海子自命为一个浪漫主义王子型诗人,但他的野心让他不满足于当一个像陈思王曹植那样郁郁而终的王子,因而他又开始了新的远行。这是他最后一次“青春远行”。与以往的几次远行不同,这次要去的地方比遥远的西藏还要遥远,而且危险系数极大,“更远的地方,更加孤独/远方啊 除了遥远 一无所有”(《远方》)。海子将自己悲剧性地死于中途的宿命预示给我们:“一切死于中途 在远离故乡的小镇上/在十月的最后一夜”(《泪水》)。尽管充满危险,但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计划;相反,他的灵魂甚至渴望这种冒险,连受伤、死亡也不能动摇他的意志:
有一只天鹅受伤
其实只有美丽吹动的风才知道
她已受伤。但她仍在飞行(《天鹅》)
轻雷滚过的风中
死者的鞋子,仍在行走(《天才》)
这次“青春远行”并非指称任何空间意义上的远行,而是一次美学历险,即由王子型诗人向诗歌之王的飞升。海子凭着青春的激情、执拗和锋芒热切地向往和追求诗歌王位,实现“从夏娃到亚当的转变和挣扎”[1](P895)。尽管海子明知这一目标对于他来说“可望而不可及”[1](P897),但对于王座的痴迷和贪恋使他不顾一切。正如他在《夜色》中写道:
在夜色中
我有三种受难:流浪、爱情、生存
我有三种幸福:诗歌、王位、太阳
虽然虚荣心曾经诱使海子干过私自封“王”的把戏,如在写于1987的短诗《秋》中他径直加封自己为王:“秋天深了,王在写诗”。但毕竟“偷来的锣鼓敲不得”,这种不光彩的把戏只能偷偷地玩上一把,但这回他却要来真格的了。海子用来角逐王座的是他总题为《太阳》的长诗(他又称为“大诗”或“真正的史诗”),已写出或接近完稿的共有七部,按骆一禾在《“我考虑真正的史诗”(〈土地〉代序)》中的排列是:诗剧《太阳》;诗剧《太阳·断头篇》;诗剧《太阳·但是水,水》;长诗《太阳·土地篇》;第一合唱剧《太阳·弥赛亚》;仪式和唱剧《太阳·弑》;诗体小说《太阳·你是父亲的好女儿》。而西川在编辑《海子诗全编》时却将《但是水,水》抽出,另补入《大扎撒》的残稿。
骆一禾在谈到《太阳·七部书》时说:
《七部书》的意象空间十分浩大,可以概括为东至太平洋沿岸,西至两河流域,分别以敦煌和金字塔为两极中心;北至蒙古大草原,南至印度次大陆,其中以神话线索“鲲(南)鹏(北)之变”贯穿的……他在结构上借鉴了《圣经》的经验,包括伟大的主体史诗诗人如但丁和歌德、莎士比亚的经验。[2](P4)
尽管骆一禾把《七部书》推崇为海子“最主要的贡献和作为一个世界文学性的诗人最主要的方面”[2](P19);尽管他固执地认为“说海子的长诗没有短诗好,这是一种非常外行的话”[2](P15),但我仍然坚持这种“外行的”主张。既然“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一种通例,那么极有可能这种主张就是对的。细读海子的长诗,最让我无法忍受的是它们自我膨胀式的虚张声势和天马行空式的凭虚蹈空。海子长诗最大的一个问题是经验的匮乏和超验想象的膨胀,理性的欠缺和激情的过溢,二者之间的不平衡势必导致整个长诗成为一个空有大而无当的架构却缺少血肉的骨骼标本,而不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有机整体。也就是说,海子的诗歌创作实际上是单翅飞行的。他的史诗架构如此之大,凭着他一己的才华显然是无法架驭的。海子虽然声称“我相信天才、耐心和长寿”(《草原上》),但事实上后两点他根本没有做到。虽然海子青春的才情光彩四溢,但他缺少生命充分展开之后的那种丰盈和厚重。一个如此年轻的诗人,创作生涯仅有短短五年,可他除了大量的抒情诗外,竟然还创作了七部长诗,其心态难道不是浮躁反常吗?歌德曾深为雨果的粗制滥造感到惋惜:“他那样大胆,在一年内居然写出两部悲剧和一部小说,这怎么能不愈写愈坏,糟蹋了他那很好的才华呢!”[5](P248)海子的胆大妄为难道不甚于雨果吗?歌德凭着过人的才气和青春的激情在短短四周时间内写出他《少年维特的烦恼》,但为什么他迟至七十五至八十二岁,值到饱经人事沧桑之后才完成史诗性巨著《浮士德》的第二部呢?不就是囿于经验阅历的掣肘嘛!海子那么崇敬歌德,自称“现在和这两年,我正在向歌德学习精神和诗艺”[1](P882),但为什么听不进歌德的这一忠告呢?此外,我看不出《七部书》之间有什么严密的逻辑结构(谁能说清楚它们的正确排序?),海子硬把几个支离破碎互不关联的东西塞进《太阳》这一总标题下,难道没有拼凑之嫌吗?在阐述长诗《土地》的立意时海子说:
在这一首诗(《土地》)里,我要说的是,由于丧失了土地,这些现代的漂泊无依的灵魂必须寻找一种代替品——那就是欲望,肤浅的欲望。[1](P889)
但如果没弄错的话,我记得这一主题早在1922年就被英国诗人艾略特写进《荒原》这部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奠基作了,海子再写它是否真有必要?
古希腊神话中的安泰之所以具有非凡的力量,其奥秘在于他脚踏大地,一旦他的双脚离开大地,死期也就拉踵而至。海子固然是个天才,但不幸的是他犯了安泰同样的错误。在他的抒情短章里,海子热衷于描写虚幻的飞升:
单翅鸟为什么要飞呢
我为什么
喝下自己的影子
揪着头发作为翅膀
离开(《单翅鸟》)
黎明
我挣脱
一只陶罐
或大地的边缘(《黎明 一首小诗》)
这不禁使我想起一个古希腊的传说,一个因飞得太高而损落的青年的传说:
流落在克里特岛的艺术家狄达洛斯思念故乡雅典,他不顾国王米诺斯的阻拦决心逃走,为此他收集鸟羽用线缝腊封的办法做了一大一小两副鸟翼。当他把小鸟翼缚在儿子伊卡洛斯身上时他叮嘱说:“记住,如果飞得太低,鸟翼沾到海水会变得沉重,你就会被拽进大海,要是飞得太高,翅膀上的羽毛会因靠近太阳而着火。”
年青的伊卡洛斯跟着父亲兴高采烈地飞呀飞呀,但不久他就骄傲起来。他忘记了父亲的叮嘱,竟操纵着鸟翼朝着高空——太阳所在的地方——飞去。于是惩罚终于降临:强烈的阳光烤化了封蜡,鸟翼完全散开,他一头栽进大海,大海在瞬间就毫不留情地取走他的青春他的生命。
这不正是海子这只青春的“单翅鸟”悲剧命运的真实写照么?
收稿日期:2000-09-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