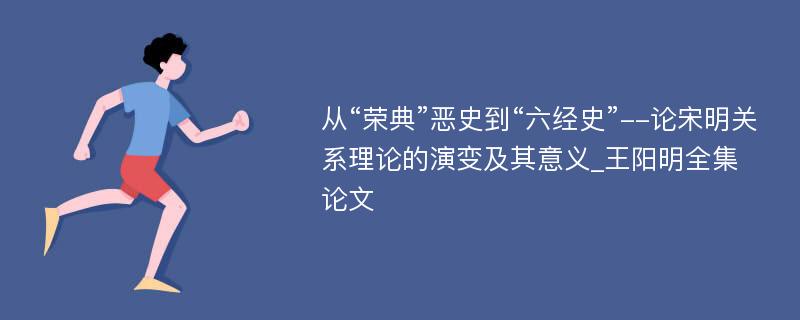
从“荣经陋史”到“六经皆史”——宋明经史关系说的演化及意义之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义论文,关系论文,荣经陋史论文,六经皆史论文,宋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史关系的问题,是中国古代学术史中的一个重要论题。由于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涉及史 学在中古时期的发展中,力图摆脱经学的笼罩获得“史学自主”的理论问题,所以前贤学者 ,对此有过不少的讨论,尤其是对清代史学理论家章学诚提出的相关理论,论述得尤多。本 文考虑到这一命题在学术思想史中,往往因学术语境的不同而表现不同内涵的复杂特点,试 将此论题,置于思想学术史的演进过程当中,考察其提出的学术思想史的渊源及其演进的内 在理路,从一个新的角度对其予以阐释,进而揭示它在史学史中的意义。
一
经史关系的讨论,虽然很早就有学者提及,但是真正展开对二者尊卑关系的讨论,实际是 从宋代开始。对此,清代的钱大昕曾有所论述。《廿二史札记》钱大昕《序》云:
经与史岂有二学哉?……初无经史之别,厥后兰台、东观,作者益繁,李充、荀勖等创立四 部,而经史始分,然不闻陋史而荣经也。自王安石以猖狂诡诞之学要君窃位,自造《三经新 义 》,驱海内而诵习之,甚互诋《春秋》为断烂朝报。章、蔡用事,祖述荆舒,屏弃《通鉴 》为元祐学术,而十七史皆束之高阁矣,嗣是之道学诸儒,讲求心性,惧门弟子之泛滥, 无 所归也,则有诃读史为玩物丧志者,又有谓读史令人心粗者。此特有为言之,而空疏浅薄者 托以藉口,由是说经者日多,治史者日少。彼之言曰:经精而史粗也,经正而史杂也。
按照钱大听的观点,在学术的发展中,虽然早就出现了经、史分途,但是始终“不闻陋史 而 荣经也”。直至宋王安石废汉唐经注,倡言新学,“诋《春秋》为断烂朝报”,其后则又有 理学的兴起,“诸儒讲求心性,惧门弟子之泛滥无所归也,则有诃读史为玩物丧志者”,发 展至此,经与史在地位上才出现尊卑高下的差异。(注:宋代之前,虽有隋王通提出“昔圣人述史三焉”,即“六经”中的《尚书》、《诗经》及《春秋》三经“同出于史”的观点。但是王通此说实质意图是强调三经的体裁与立意的不同,并未提出经史尊卑的问题。所以他结论说:“此三者同出于史,而不可杂也,故圣人分焉
。”见王通《中说·王道》篇。)
我们说,钱大昕的论述虽然明显带有清人基于汉学立场对宋人学术批判成分,但也确实在 某种程度抓住了经史关系变化的关节所在,即理学的形成和发展对于人们经史关系的认识产 生有很大的影响。史称:“自王氏之学兴,士大夫非道德性命不谈。”(注:赵秉文:《滏水集》卷一《性道教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册119 0
。)王安石作为北宋著 名思想家、政治家,虽然一直受着理学中人的批判,但是其开启一代学风,在一定意义上促 进理学发展之功,却是学术思想史不争的事实(注:如钱穆先生即云:“(王)安石虽是宋学初期的人物,但他实已探到此后宋学之骊珠。” 见钱穆《宋明理学概述》,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版,第23页。)。钱穆先生认为王安石对待读经的态度是“ 在致我之知以尽圣,然后于经籍能有所去取。此见解,竟可谓是宋人开创新儒学的一条大原 则”。(注:钱穆:《宋明理学概述》,第22—23页。)所以在一定意义上,钱大昕是以王安石为经史关系观念发生变化之橥,揭示了学术 思想演化中,理学思想的形成对经史关系观念影响的内在理路。
然而王氏之时,理学的基本观点和理路还只是初露端倪,所以在经史关系认识方面还未显 现什么值得注意的影响,而至以二程为代表的理学家时,受佛教华严宗,尤其是华严禅理事 说 的影响,则开始涉及到“理”与“事”之关系的讨论,并将这观念引入到经史关系的讨论, 形成其强调读经穷理,置经学于一切学术之上的观点。据《上蔡先生语录》卷之中载,程颢 曾批评学生谢良佐爱好史学,“举史文成诵”,是“玩物丧志”。在二程的观念中,即使是 “六经”中的《春秋》,因为是依鲁史改编的史著,也是形而下之“用”,而非形而上之“ 体”。认为:“盖《春秋》圣人之用也。《诗》、《书》、《易》如律,《春秋》如断案, 《诗》、《书》、《易》如药方,《春秋》如治法。”(注:《程氏外书》卷九,《二程集》,中华书局点校本1981年版,第401页。)正是在这种思路的支配下,他们“ 尝语学者,且先读《论语》、《孟子》,更读一经,然后看《春秋》,先识得个义理,方可 看《春秋》”(注:《程氏遗书》卷十五,《二程集》,第164页。)。表现出明显的荣经陋史的倾向。
二程以后,其荣经陋史的思想,继续为他们的门人后学所接受,尤其是集理学之大成的朱 熹,在二程观点的基础上又有所发挥。与程颢一样,朱熹也强调读书必须“以经为本” ,“先经后史”,他批评同时学者吕祖谦道:“缘他先读史多,所以看粗着眼。读书须是以 经为本,而后读史。”而当他的学生问起吕祖谦的学术时,他不无轻蔑地说:“伯恭于史分 外仔细,于经却不甚理会。”学生不解地问:吕祖谦不“也是相承那江浙间一种史学,故凭 地”?而他对这追问显然很不满,所以不无情绪地答道:“史什么学?只是见得浅!”(注:《朱子语类》卷一二二,中华书局点校本1986年版,第2950—2951页。)因为 在他看来:“看史只如看人相打。相打有甚好看处?陈同甫一生被史坏了,直卿亦言,东莱 教学者看史,亦被史坏。”(注:《朱子语类》卷一二三,第2965页。)“故程夫子教人先读《论》、《孟》,次及诸经,然后看史, 其序不可乱也。”(注:《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五《答吕伯恭》,上海,涵芬楼影印本。)可见钱大昕所谓“诃读史为玩物丧志者,又有谓读史令人心粗者”,是 完全具有历史根据的,而所指就是二程、朱熹一系的理学学者对经史关系的理解。
我们说,钱大昕虽然意识到了理学的发生发展对荣经陋史的学术倾向具有重大的思想影响 ,但是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的观念?这种思想观念的哲学依据是什么?作为一位考据学家,钱大 昕并没有作出进一步的追问。然而这也正是我们所要论述的最关键的问题所在。
溯本追源,以二程和朱熹为代表的宋理学家,之所以认为经尊史卑、经精史粗,强调读书 先读经再读史,以经统史,其根本是与他们“理一分殊”的理学思想分不开的。程朱理学体 系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在改造佛教华严宗和禅宗理与事理论的基础上,突出地强调“天下只有 一个理”(注:《程氏遗书》卷十八,《二程集》,第196页。),认为这个超验抽象的、普遍的“理”,是独立于具体经验事物之外,从事物外 部 决定并制约着具体的、特殊性的事物的存在,从而构成其理气相分,道器相离,普遍外在特 殊的二元世界观体系:一个形而上的“理”的世界,“若理,则只是一个净洁空阔的世界 ,无形迹”(注:《朱子语类》卷一,第1页。);一个由超验之“理”分殊的具体的芸芸世界。其中,作为这经验的芸芸世界 ,在它存在和不断展开于时间的过程中,也就是它对“理”不断体现的过程,而这芸芸的经 验世 界形而下的属性,必然决定了其对“理”之展现或反映的不完全性。事实上,二程、朱熹等 人正是从他们这一基本的理学观点出发来理解经史关系的,他们之所以“荣经陋史”,强调 经对史的统辖意义,是因为他们认为经是天理的体现:“‘六经’是三代以上之书,曾经圣 人之手,全是天理。”(注:《朱子语类》卷十一,第190页。)只有“以经为本”,在从“六经”中汲取天理“而后读史”,才能 “陶铸历代之偏驳,会归一理之纯粹”(注:李方子:《资治通鉴纲目后序》。),求得“天理之正,人心之安”,进而达到格物致 知、体察形而上之天理的目的。因此,程、朱等人荣经陋史的经史观,从一定意义讲,也正 是他们“理(道)统于气(器)”、“理一分殊”等基本理论在经史关系的问题上的逻辑推绎。
二
我们认为,从“荣经陋史”到“六经皆史”的理论转变,在理论上实质存在有二大基本观 念上的突破:一是需要对形而上的“道”与形而下的“器”是否具有统一的关系,普遍真理 与 具体事物之关系是超然于外还是内在其中认识上的突破;一是需要对“六经”是一切真理渊 薮,具有绝对的思想权威地位之神话的突破。其中后者,实质也是前一观点进一步发展的结 果。
事实上,在二程和朱熹等为代表的理学家倡言“荣经陋史”的同时,甚至之前,已经有一 些 学者提出经亦史的观点,而且这些学者很多也是从“道”与“器”、“理”与“事”之关系 的高度对经史关系展开讨论的。例如早在北宋时,苏洵就提出过“经以道法胜,史以事词胜 ”,经史“体不相沿,而用实相资焉”的观点(注:苏洵:《嘉祐集》卷八《史论上》,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四库全书》本,册1104。)。南宋时,叶适也认为“经,理也;史,事 也”,而且同样认为“专于经则理虚,专于史则事碍而不通”(注:叶适:《叶适集·水心别集》卷十二,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21页。)。入元,这种观点得到进一 步发展,当时有郝经、刘因等,提出“治经而不治史,则知理而不知迹;治史而不治经, 则知迹而不知理”等观点,(注:郝经:《陵川集》卷十九《经史》,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四库全书》本,册1192。)甚至在此基础上提出“古无经史之分”的观点等等。(注:刘因:《静修先生文集》卷一《叙学》,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四库全书》本,册1198 。)从这些 论述人们可以感觉,这些人似乎意识到绝对之“理”与经验之“事”,事实上存在着相互依 赖的关系而并不能截然分开,所以他们才会得出经史“体不相沿,而用实相资焉”,甚至“ 古无经史之分”的结论。这实际也是理学在程朱以后,理学学者竭力弥和程朱完全离析道器 、二分心理的理论缺陷,而出现和会朱、陆(九渊)的一种哲学倾向。但是我们也应看到,上 述这些学者对“道”与“器”、“理”与“事”的统一关系并没有在理论上作出明确的说明 ,所以他们对于经史关系的论述,在理论上并没有导致突破性的进展,自然也没有什么重大 的学术影响。
对经史关系的认识在理论的层面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是明中叶的王阳明。
关于王阳明与程朱等人在经史关系认识的对立,钱钟书先生已有所注意。但是钱先生仅仅 认为,王阳明“五经亦史”的观点,只是前人“言不尽意”及庄子糟粕“六经”等观点的翻 版,而没有对其各自的观点作出更深层的哲学追问。(注:参见钱钟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增订版,第263—266页。)事实上,王阳明与程朱等人之间经史 关系说的对立,并不仅仅是所谓意义与语言表述的问题,更有着深刻的认识论上的歧异。
史载,明正德七年(1512)年底,王阳明升任南京太仆寺少卿,随即返乡归省,途中与弟子 徐爱讲学。当时徐爱问:“先儒论‘六经’以《春秋》为史,史专记事,恐与‘五经’事体 终或稍异。”对此,王阳明回答说:
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史,《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 是包牺氏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 谓异?
“五经”亦只是史。史以明善恶,示训戒。善可为训者,特存其迹以示法;恶可为戒者, 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其奸。(注:《王阳明全集》卷一《传习录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0页。)
王阳明这里所说的“五经”,实际也就是“六经”,故所谓“五经亦史”,也就是“六经 皆史”,因此这也是古代学术史上对“‘六经’皆史”的第一次,也是最明确的说明。但是 值得提出的是,王阳明所阐述的经史关系的理论价值,不仅仅在于其明确提出了“五经亦史 ”的观点,因为这种说法前人早已有所涉及,而在于他空前明确地将“事”与“道”统一起 来,并以此理论为基础说明经与史的统一关系,因而形成了对古代经史关系认识的大突破。
王阳明之所以提出“五经亦史”的观点,其理论前提,一是他对所谓“理”或绝对的理解 ,一是在对“理”的理解基础上形成的对所谓“六经”的理解。
从对“理”的认识角度来说,与程、朱等人所谓“性即理”,“析心与理为二”,将理视 为 超然于经验事物之外的绝对存在的观点相反,王阳明认为“心即理”,(注:《王阳明全集》卷一《传习录上》,第2页。)认为“心外无物, 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注:《王阳明全集》卷四《答王纯甫二》,第156页。)即所谓的“理”,不是超验抽象地存在于 经验事物之外,而是内在于作为普遍之理与个体意识相统一的,具有道德渊薮和本体意义的 “心”里,从这种认识出发,自然无论是表现为普遍意义的圣人所作之“六经”,还是表现 为具体经验过程的历史,都是混融如一地存在于体现为良知良能的人的心中,所以在这意义 上“事即道,道即事”,特殊体现着普遍,普遍内在于特殊。因为在王阳明看来,“其事同 ,其道同,安有所谓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经史一也”,二者统一地同具吾心。这样 ,这一认识论上的转变,无意间便为“六经皆史”的理论提供了理论依据。
从对普遍之“理”的理解基础上形成的对“六经”价值的理解来说,由于王阳明以世界统 一于意识的主观唯心主义诠释经史关系,所以程朱理学理论中被奉为天理所在的“六经”, 在王学中则只是被视为一种“致良知”的工具,从而把“六经”的权威置于主体的理性之下 。 所以王阳明说:“‘六经’,吾心之记籍也。而‘六经’之实则具于吾心,犹之产业库藏之 实积,种种色色具存于其家,其记录者特名状数目而已。”(注:《王阳明全集》卷七《稽山书院尊经阁记》,第255页。)即相对人人具足的良知来说, “六经”不过是个登记财产的帐簿而已,而阅读过帐簿并不等于真正拥有了财产。同样,阅 读过“六经”也不等于体认到了自我的良知,完成了对天理的认知。应该说王阳明“五经亦 史”的论述,其主旨并不是要提高史学价值,只是认为以“六经”为代表的知识,如果不融 入作为个体内在意识的“心”中,是不可能化为道德行为的。但是由于他将“经”仅仅被视 为登记财产的帐簿,使得“经”的权威被大大降低,从而为作为经验的史的地位的上升留 出了空间。于是,王阳明讨论修养途径的初衷,转而成了后来史学最终摆脱经学的笼罩,获 得“史学自主”(autonomy of history)的理论依据。而这又在无意之间为古代经史关系的 认识构筑了一个突破点。
王阳明对经史关系的论述,随着其主要哲学著作《传习录》于正德十三年(1518)刊刻,及 整个王学社会影响的扩大,推动了后来对经史关系的讨论。王阳明之后,其再传弟子,南中 王门中的史学家薛应旂,曾在王阳明论述的基础上对“五经亦史”作出进一步的演绎。不 同的是,薛应旂的论述,已不再像王阳明那样,主要是讨论道德修养问题而发,而是直接 针对朱熹尊经抑史的观点进行的批驳,即其意已是专意讨论史学问题了。薛应旂说:
古者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经史一也。后世史官咸推迁、 固,然一则退处士而进奸雄,一则抑忠臣而饰主阙,殆浸失古意而经史始分矣。朱晦翁谓吕 东莱好读史遂粗着眼。夫东莱之造诣不敢妄议,若以经史分精粗,何乃谓精义?入神之妙, 不外于洒扫应对之间也!(注:薛应旂:《宋元通鉴》卷首《凡例》,明天启刻本。)
薛应旂这里所针对的是朱熹批评吕祖谦“好读史”,认为“经精史粗”,多读史无益于 人的道德修养的观点所发的议论。其中他所谓“经史一也”的观点,包含二层意思:一是经 与史的起源是同一的;二是经与史的本质意义是同一的,而经与史的分途只是因为后之史的 叙述中没能很好地体现“道”(理),“浸失古意”的结果。这实质正是王阳明“事即道,道 即事”,道内在于事,事亦体现道观点的演绎。
薛应旂经史观与王学的理论联系,可从薛氏对“六经”与心的论述中体察到,薛应旂说 :
人之言曰:圣人未生,道在天地;圣人既生,道在圣人;圣人既往,道在“六经”。是“ 六经”者,固圣人之道之所寓也,然其大原则出于天,而夫人之心,则固天之心也。人能会 之于心,则圣人之道,即吾人之道,有不在“六经”而在我者矣。(注:薛应旂:《方山先生文录》卷十六《折衷》,明刊本。)
人人存其本心而形气不扰,则“六经”可无作也。于是乎可以知圣人作经之意也。《易》 以道化,《书》以道事,《诗》以达意,《礼》以节人,《乐》以发和,《春秋》以道义。 先后圣哲,上下数千年,究其指归,无非所以维持人心于不坏也。(注:薛应旂:《方山先生文录》卷十六《原经》。)
在上述引文中,可以看到薛应旂的论述所展现的经、史及心相互关系的逻辑思路是:一 、“道”是历史的产物,它在历史过程中展开,并被记载在典籍(“六经”)之中;二、作为 主体意识的人心就是天之心,就是圣人之心,“圣人之道,即吾人之道”,因此作为“圣人 之道之所寓于”的“六经”,也必然存在于人的心中;三、远在圣人制经之前,道已存在于 天地,“六经”远远不能取代与天相埒的“心”体现的道的全部内容,“六经”有限,而道 无限,所以“人能会之于心,则圣人之道即吾人之道,有不在‘六经’而在我者矣”;四、 这“不在‘六经’而在我者”,就是作为世界本体和道德本原的吾心或良知,如果“人人存 其本心而形气不扰”,保持先天良知的本真,“则‘六经’可无作也”,因为“先后圣哲上 下数千年,究其指归,无非所以维持人心于不坏也”。这样,按照薛氏推绎的逻辑,所谓的 “ 六经”不再是,也不可能是全部的天理所在,它与上下数千年一切维持人心不坏的说教,包 括体现了良知本真的史,在意义上完全一致的,都是使主体致良知、复本真的中介或工具, 于是“经史一也”,价值等同,既没有三代所制与后世所作的高下差异,也没有经精史粗的 区别,“入神之妙,不外于洒扫应对之间也”,无论“理学政治,论次旧闻,凡事关体要, 言涉几微者”,只要人们能够会之于心而“自得之”,就都与圣人所制的“六经”一样,具 有同等价值,于此人们自然也就“庶无伯恭之累也”。(注:薛应旂:《宋元通鉴》卷首《凡例》。)于是,理气合一,道器合一,知行 合一,道亦是事,事亦是道,即“‘六经’,皆史”,“经史一也”。所以薛氏结论说:“ 苏洵氏谓:‘经以道法胜,史以事词胜’。而世儒相沿,动谓经以载道,史以载事。不知经 见于事,事寓乎道,经亦载事,史亦载道,要之不可以殊观也。”(注:薛应旂:《宋元通鉴》卷首《凡例》。)循着王阳明的心学理论 及其经史观,进一步发展了苏洵等人的观点,认为作为真理的“经”(道)与作为经验的“史 ”(事)是统一并展现于具体之过程的,从而在理论上将史提高到了与经相埒的地位。(注:薛应旂的论点可从明代思想的殿军刘宗周的论述中得到解说,刘宗周《论语学案一·里 仁第四》云:“一贯之道即天地之道,非圣人所得而私也。圣人自任以为吾道者,圣人从自 己心上看出此道,满盘流露,一实万分。盈天地间万事万物,各有条理,而其血脉贯通处, 浑无内外,人已感应之迹,亦无精粗、大小之殊,所谓一以贯之也。”见《刘子全书》卷二 十八。中华文史丛书之五十七,台湾华文书局影印清道光本,第2363页。)
如果说作为王学中人的薛应旂还基本是循着王阳明以心说理,心理不二,道事相即同具吾 心等观点的思路阐述经史关系,那么当时一些学者则在接受王阳明以统一道事说经史关系的 观点的同时,开始抛开心学的理论思路来论述经史关系的问题,例如丰坊便曰:
人有言:经以载道,史以载事。事与道果二乎哉?吾闻诸夫子:“下学而上达。”子思亦云 :“率性之谓道。”性也者,天理也;道也者,人事也。人事循乎天理,乃所谓道,故古之 言道者,未始不征诸事也。言道而遗于事,老之虚,佛之空而已矣!故曰:“我欲载之空言 ,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者也。”空言美听,而非践履之实用,行事有迹,而可以端趋舍 之涂,是故《诗》、《书》已删,《礼》、《乐》□正,必假《鲁史》修《春伙》,以为《 诗 书礼乐》之用,必征诸行事而后实也。经与史果二乎哉?繄“六经”赖夫子而醇,诸史出于 浮士而杂,非经史之二也,存乎其人焉尔!(注:丰坊:《世统本纪序》,见黄宗羲《明文授读》卷三十一,齐鲁书社影印《四库全书存 目丛书》集部,册401。)
稍后的沈国元也说:
经以载道,史以纪事,世之持论者或歧而二之,不知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因事之得 失成败,可以知道之万世无弊,史之所系綦重矣。(注:沈国元:《二十一史论赞》卷首《自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册148。)
在他们看来,道与事,具有普遍性的真理与具体的经验存在只能是相互依存而不可分离, 即道无不在并散于具体事之间,言道决不可遗于事,人事徇乎天理也就是道,因此,无论是 经还是史都是道事俱载,二者就没有什么尊卑的差别,没有什么可荣可陋的必要。可以看出 ,丰坊和沈国元的论述与薛应旂的相关论述显然不同,他们并没有从存在统一于意识的心 学 观点出发来探讨经与史的关系问题,然而他们在关于事与道相统一这一点上,仍表现出与王 阳明,“道即事,事即道”观点的理论联系。丰坊等人这种扬弃心学立场的对经史关系的阐 释,对于史学地位的提升,应该说更有实质性的价值。
当然,王学对经史关系说的影响,除道与事相统一,普遍内在于特殊,并表现于具体过程 中等理论影响外,还表现于王阳明所鼓吹的“良知”说,对张扬自我、蔑视权威的个人主义 精神的激发。王阳明曾经对他的学生说:“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底准则,尔意念着处, 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注:《王阳明全集》卷三《传习录下》,第92页。)认为“学贵得之心,求知于心而非也,虽言 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 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注:《王阳明全集》卷二《传习录下》,第76页。)王阳明的这些论述虽然仍是从其“心即理”的心 学理论出发,旨在强调道德践履的主体自主性和内在之知对于行为的指导意义,但是它也确 实 极大地启发、鼓舞了一代学者,其中一些学者,循此更向异端发挥,以致于在对待“六经” 价值的问题上,也出现新的、否定其权威地位的认识。例如史学家王世贞就声称:“吾读书 万卷而未尝从‘六经’入。”(注:李贽:《续藏书》卷二十六《王世贞传》,中华书局排印本1960年版,第514页。)唐顺之也说:“语理而不尽于‘六经’,语治而不尽‘六官 ’。”(注:唐顺之:《荆川先生文集》卷十《杂编序》,清光绪年江南书局重刻本。)而‘异端之尤’的李贽在其《童心说》中更放言:“更说什么‘六经’,更说什么 《语》、《孟》乎?夫‘六经’、《语》、《孟》,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其臣子极 为赞美之语。又不然,则其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 见,笔之于书。后学不察,便谓出自圣人之口也,决定目之为经矣,孰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 乎! 纵出自圣人,要亦有为而发,不过因病发药,随时处方,以救此一等懵懂弟子、迂阔门徒云 耳。药医假病,方难定执,是岂可遽以为万世之至论乎?然则‘六经’、《语》、《孟》, 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从史料学的角度将“ 六经”的灵光抹了个精光。而在这些人的身上,王学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其中唐顺之与薛 应旂同属南中王门,李贽曾拜泰州学派座主王艮之子王襞为师,亦为王门泰州学派中健者 ,至于王世贞虽非王门学人,但是也深受王学的影响,他曾经自道说:“余十四岁从大人所 得《王文成公集》读之,而昼夜不释卷,至忘寝食,其爱之出于三苏之上。稍长,读秦以下 古文辞,遂于王氏无所入,不复顾其书。而王氏实不可废,”并云:“王文成公之致良知, 与孟子之道性善,皆于动处见本体,不必究折其偏全,而沉切痛快,诵之使人跃然而自醒。 ”表明他对王学的一定认同。(注:王世贞,《弇州山人读书后》卷四《书王文成公集》一、二,明刊本。)
“六经”权威地位的否定,既是史学地位获得提高的重要前提,也是经史关系讨论取得突 破性进展的前提。随着相关讨论的展开,人们对于经史关系的认识,也越来越脱开原王阳明 提出问题的理学语境,逐渐转换为仅就史学本身讨论的理论问题。在当时的有关论述中,晚 明大史学家王世贞的论述最具有史学理论的价值。例如王世贞曾从纯粹史料的角度论到“稽 古史即经也”,即考核古史不能离开“经”。他认为由于上古的历史文献从春秋战国以 来,因为“日寻干戈,若存若亡,迄于秦火,遂茫不可迹”,于是《春秋》等作为“焰而犹 存” 的文献,便格外值得珍重,“故史也而尊曰经”(注:王世贞:《纲鉴会纂序》,见《纲鉴会纂》万历刊本卷首。)此外,王世贞还对王阳明“事即道,道即 事”,道内在于事,事体现着道的观点作出新的阐释,认为“史不传则道没,史即传而道亦 系之传”,把史作为“道”得以流传的根本条件,而将史学地位进一步提高。王世贞比较经 与史的价值说:“经载道者也,史纪事者也。以纪事之书较之载道之书,孰要?人必曰经为 载道之书,则要者属经,如是遂将去史弗务。嗟乎!智愈智,愚愈愚,智人之所以为智,愚 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认为由于人们重经轻史,“遂将去史弗务”,致使出现“ 愚愈愚”的局面。所以王世贞鲜明地提出:“史学在今日倍急于经,而不可以一日而去者也 。”(注:王世贞:《纲鉴会纂序》,见《纲鉴会纂》万历刊本卷首。)
三
自明代中叶王阳明从心学理论出发,明确提出“五经亦史”以后,到了晚明,所谓“六经 皆史”、“经史一也”的观点已经越来越深入人心,有关这方面的言论可以说俯拾可得,如 :
——所谓“前七于”之一的何景明《汉纪序》云:
夫学者谓经以载道,史以载事。故凡讨论艺文,横生事理,而莫知反说讫无条贯,安能弗 畔也哉!《易》列象器,《书》陈政治,《诗》采风谣,《礼》述仪物,《春秋》纪列国时 事,皆未有舍事而议于无形者也,夫形,理者,事也;宰事者,理也,故事顺则理得,事逆 则理失。天下皆事也,而理征焉,是以经史者皆纪事之书也。(注:《何大复先生集》卷三十四,清乾隆赐策堂刻本。)
——徐中行《史记百家评林序》云:
夫《易》始疱牺,《诗》逮列国,及《礼》、《乐》之治神人,何者非事,何者非言,何 者 非记而不谓之史?故《易》长于史,《诗》陈于史,《礼》、《乐》昭于史,老聃居柱下, 夫子就繙十二经,经藏于史,尚矣!(注:《天目先生集》卷十三,明代论著丛刊第三辑,台北: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有限公司。)
——闻人诠在《重刻旧唐书序》中云:
书以记事,溲闻为聩,事以著代,间逸则遗,是故史氏之书与天地相为始终,‘六经’相 为表里。疑信并传,阙文不饰,以纪事实,以昭世代,故‘六经’道明,万世宗仰,非徒文 艺之夸诞而已也。(注:转引自杨翼骧《中国史学史编年》第三册,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88页。)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五《史一》云:
史之与经,上古元无所分,如《尚书》之《尧典》,即陶唐氏之史;其《舜典》,即有虞 氏之史也;《大禹(谟)》、《皋陶谟》、《益稷》、《禹贡》,即有夏氏之史也;《汤誓》 、《伊训》、《太甲》、《说命》、《盘庚》,即有殷氏之史也;《秦誓》、《牧誓》、《 武成》、《金滕》、《洛诰》、《君牙》、《君奭》诸篇,即有周氏之史也。孔子修书, 取之 为经,则谓之经;及大史公作《史记》,取之为五帝三王纪,则又谓之史,何尝有定名耶! 陆鲁望曰:《书》则记言之史,《春秋》则记事之史也。记言、记事,前后参差,曰经、曰 史,未可定其体也。(注:见《四友斋丛说》,中华书局排印本1959版,第41页。)
——李贽的《经史相为表里》云:
经史一物也。史而不经,则为秽史,何以垂戒鉴乎?经而不史,则为说白话矣,何以彰事实 乎?故《春秋》一经,春秋一时之史也。《诗经》、《书经》,二帝三王以来之史也。而《 易》经则又示人以经之所自出,史之所从来,为道屡迁,交易匪常,不可以一定执也,故谓 “六经”皆史可也。(注:《焚书》卷五,燕山出版社《李贽文集》本1998年版,第258页。)
——顾应祥《人代纪要自序》云:
自夫书契既立,人文日开,于是乎始有简册以纪之。唐虞有典,三代有书。以其载道而谓 之经,以其纪事而谓之史,其实一也。《春秋》者,鲁国之史也,孔子取而笔削之,遂得与 经并传,其余并传者多矣。(注:分见顾应祥《人代纪要》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明刊本)
——《人代纪要》的汤明善《序》云:
史,一经也;经,一理也。吾心之中万理咸备,以心之理而观经,则理不在经而在心;以 经之理而观史,则史不以迹而以理……其迹参乎史,其理准乎经,进退予夺森然……曰政以 代 殊,理本则一。(注: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嘉靖刊许诰《通鉴纲目前编》卷首。)
——许诰《通鉴前编序》云:
经以载道,史以纪事。因行事善恶以示劝戒,是史亦载道也。(注:《有学集》卷三十八,四部丛刊本。)
——史学家钱谦益《答杜苍略论文书》云:
“六经”之中皆有史,不独《春秋》三传也。
……
这些都表明,明代中叶以后,尽管所阐述问题的基点不尽是心学的立场,但是在王学以“ 事道统一不二”理论阐释经史关系的影响下,所谓“六经皆史”、“经史一物”、“经史一 也”等“对经史关系的新的看法”(注: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0页。),已开始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这一新的经史关系认 识的史学学术意义,在于它抹去罩在“六经”上的神圣灵光的同时,提高了史学的价值和地 位,强化了人们的历史意识。从学术发展的角度讲,这种经史关系观的积极意义有二:
——第一,对于史学本身来说,“六经皆史”说的明确提出,在促进史学摆脱经学束缚, 提高史学地位的同时,史学本身也因其学术自主地位的强调,促进了人们对史学学科的深入 认识。例如晚明的史学家王世贞便是在“经史一也”观念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打破经史关系 的讨论格局,就史学之本身提出“天地间无非史而已”的命题。(注: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四四《艺苑卮言》。)王世贞所谓“天地间无非 史而已”,也就是说天地之间无一不是史的内容,从而将史学的范围扩大到无所不包的程度 。这个命题实际早已超越了经史关系的讨论,而成为纯粹对史学范围的认识。事实上,作为 一个优秀的史学家,王世贞对于史学本身所应有的独立价值,也是有着相当清醒的认识,他 已经意识到,“史”事实是具有“经”所不能替代的独立价值,是人们了解客观历史的不可 或缺的依据。联系王世贞“吾读书万卷而未尝从六经入”及上述“天地间无非史而已”等一 系列有关论述看,这种对于史之独立价值的积极认识,显然得力于其对于经史关系的新理解 。而后来黄宗羲提出的“言性命者必究于史学”等观点,事实上也是基于对史学具有独立价 值的学术观念。为这种观点注脚的是朱之瑜的相关论述。朱之瑜认为经史相较,是“经简而 史明,经深而史实,经远而史近”,因此在他看来,“得之史而求之经,亦下学而上达耳” 。这样便形成了与程朱等宋儒相反的经史关系和致知的路径。(注:朱之瑜:《朱舜水集》卷八《答奥村庸礼书第十一》,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74页。)
——第二,对于经学来说,“六经皆史”说的明确提出,极大促进了明中叶以后的学者, 以文献学的眼光看待传统的经书,以史学方法考证经书,促使学术研究由考经向考史的方向 展开,而这正是后来清代学术的基本特点。清张之洞说:“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 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注:《书目答问补正》附录二《姓名略序》,中华书局重印范希曾补正本1963年版,第221页 。)而由经学入史学的首要条件,就是将经学史学化,降低 经的神圣地位,摆脱以准宗教观念对待经的思想束缚,代替以史学的眼光去看待经和研究经 。因此,从宋代程朱等人的“荣经陋史”,到明代中叶王阳明等人“六经皆史”说的明确提 出,在某种意义上,不啻是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史上的一次观念革命,它为中国古代学术在清 代的进一步发展,廓清了观念认识上的障碍。
当然,与王阳明等学者从以心统一世界的立场出发所提出的“六经皆史”不同,清人更多 的是从文献学的立场理解“六经皆史”的。但是从思想发展的层面看,清人对经史关系的理 解,又不能不追索到明中叶以来的心学家对于经史关系的探讨,尤其是王阳明以事不离道, 道在事中,道器合一,及“六经”并不代表全部之道等观点来阐释经史关系的基本思路。王 阳明这一思路的影响,在清章学诚对“六经皆史”的有关论述之中,也仍然是依稀可辨。如 章氏《文史通义》卷二《原道中》便云:
《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不离器,犹影不离形,后世服 夫子之教者自“六经”,以谓“六经”载道之书也,而不知“六经”皆器也,……夫天下岂 有离器言道、离形存影者哉?彼舍天下事物、人伦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固不可言夫 道 矣。(注:章学诚:《文史通义》,中华书局叶瑛《文史通义校注》本1985年版,第132页。)
当然,我们说,章学诚论述的语境及其随之而来的意义较之王阳明又有了新的变化,即不 再是针对程朱之学离析心、理为二物,视道为超然于经验之外的绝对而发的争辩,而是针对 清 乾嘉学者不问政事埋首饾饤考据之学的倾向,呼唤传统即事以言理、即器以明道的经世 精神,所以章学诚说:“‘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 先王之政典也”,“六经”皆先王经世之籍也。(注:章学诚:《文史通义》,第1页。)而这则又涉及到对经典文本的阐释与解读 的理论问题,因篇幅的关系,则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列。
标签:王阳明全集论文; 读书论文; 王阳明论文; 观点讨论论文; 四库全书论文; 心学论文; 朱子语类论文; 宋明理学论文; 国学论文; 理学论文; 宋元通鉴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