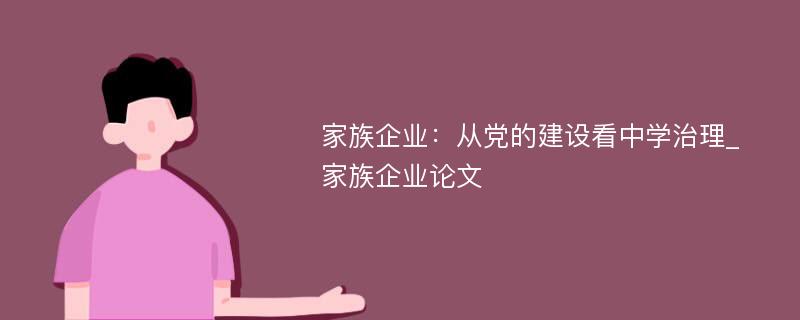
家族企业:从党建中学治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党建论文,家族企业论文,中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不久前,天通股份董事长潘建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前些年国美电器的“黄陈之争”和雷士照明的“吴长江事件”给他带来的最大担忧,是家族企业在经营过程中遭遇到任何变故,职业经理人和外部战略投资者都可能会争夺公司控制权,最终给家族利益和企业经营带来重大的伤害。 潘建清这个担忧在家族企业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普遍性。中国证券市场2004年开设中小企业板和2009年开设创业板,开启了优秀家族企业走向资本市场的浪潮。在A股市场上市的家族企业由2010年的305家增加到2013年的711家,家族企业占A股所有上市公司比重也由2010年的28.2%上升到2013年的49.7%。随着中国家族企业由创始人及其家族所有的单一治理结构向多个利益相关者共生的多元化治理结构的演进,其人力资源和资本向社会开放已成为趋势。 面对全新的多元化治理结构,家族企业创始人沿用以往的经验已无法有效解决企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深层次治理问题,从而导致家族企业创始人与利益相关者之间出现的矛盾冲突频频发生。 为此,家族企业创始人需要培养一种新的能力——治理能力——来应对,但治理能力对于家族企业创始人来说是陌生的,因为这是一种政治能力。也正因此,只有向政治组织才能真正学习到这种能力。 治理与管理有本质区别 公司治理,是源于西方现代企业理论的概念,通常指明确公司不同利益相关者的权力、责任,建立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分配和平衡的制度安排。一些学者也分别从不同的视角提出了关于公司治理的定义,但这些定义基本都包括三个关键词,即:权力制衡、利益分配、关系协调。 由此引出了另一个问题:作为经济属性的企业组织有没有政治?从上述三个关键词分析可以得出结论:企业也有政治,关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力制衡、利益分配和关系协调就是企业最大的政治。家族企业所要培养的治理能力就是处理好在治理结构层面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权力制衡、利益分配和关系协调问题的能力。这种治理能力本质上就是一种政治能力。 企业治理能力这种政治属性,使它与一般的企业管理能力有着本质的区别:管理一般是指自上而下的纵向、单向、垂直管理,具有刚性特征;治理则指处于横向的多元化的利益主体之间如何进行权力制衡、利益分配和关系协调,具有柔性特征。 而论及政治能力,首先应该想到的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理论、机制、方法和经验,可以为企业家在解决企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所吸收和借鉴。其中,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党的建设,就集中体现了中共完备的治理机制和高超的治理能力。 中国革命时期党的建设的内涵包括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三个方面。其中对于组织建设来说,中国企业家往往学习借鉴更多的是其纵向管理这个维度,而对其横向治理维度关注甚少。 党的建设对于中国企业家最大的借鉴意义,在于始终把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矛盾和问题放在治理层面来加以解决,最大限度地减少个人领导魅力和私人关系在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中所起的作用。 党建治理难题家族企业也会遇到 在中国革命时期,党建也面临着类似如今家族企业所遇到的问题。在1945年“七大”之前的中国革命中前期,党内在治理层面始终贯穿着三类主要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治理关系: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本土成长的政治家;以朱德、刘伯承为代表的出身旧军阀的职业军人;以王明为代表的具有留苏经历的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理人。 与职业军人的治理关系 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时期,党建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处理与职业军人的治理关系。两对利益相关者在治理层面的冲突表现为两个方面:农村包围城市模式和单纯军事斗争思想之间的冲突,“游击主义”和片面军事正规化之间的冲突。 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提出了适合国情的建立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这一革命模式,军事只是配合实现政治目的的手段;一部分职业军人则主张单纯军事斗争思想,不赞成创建根据地,热衷于攻打城市,甚至主张以军领政。 在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坚持军队组织和军事行动的灵活性和务实性,而个别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的职业军人和外国军事顾问则视之为“游击主义”,主张军事组织和军事行动的正规化和专业化。后两种思想在党内一度占据上风,使得毛泽东在1929年红四军“七大”上落选前委书记和1932年宁都会议上被解除军权,并成为1929年东江失利以及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原因之一。 党建中遇到的政治家与职业军人之间的治理问题,中国家族企业在引入外部职业经理后也同样会遇到。家族企业创始人与职业经理高管在治理层面的冲突也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商业模式与单纯业绩导向的冲突,创业导向与职业化之间的冲突。 对于这两方面的冲突,当事人和舆论往往从孰是孰非的视角去看待,从而得出要么是家族企业组织形态落后,要么是职业经理高管市场不成熟的负面结论。而这两方面冲突的成功解决也依赖于创始人和职业经理高管个人的素质和意识,即使是成功的解决案例也只是个案,而不具备普遍复制性。 与共产国际代理人的治理关系 在中央苏区时期和延安时期,党建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处理与共产国际及其代理人之间的关系。在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之前,中共是共产国际的支部,当时以王明为代表的中央领导人大多具有留苏背景,这些人更多的是代表共产国际的意志。这一时期党内两对利益相关者在治理层面的冲突也表现为两个方面:长远发展利益和短期利益的冲突,独立自主发展还是依赖外部资源主导? 在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考虑的是中国革命的长远发展利益,认为中国革命是一个由弱到强的长期艰苦过程;作为共产国际代理人的王明等人则出于短期业绩压力,要求红军攻打大城市,过早地实行正规战、阵地战,对根据地的资源涸泽而渔。 而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坚持独立自主发展,壮大根据地和军事力量,以王明为代表的留苏领导人则主张“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其背后代表了拖住日军使之无力北进的苏联利益。在这次冲突中,王明一度占据上风,使毛在一段时期内陷入孤立。在王明的影响下,南方的新四军失去发展敌后武装和根据地的大好时机,也导致了“皖南事变”这一巨大的军事挫折的发生。 政治家与共产国际代理人之间的治理问题,家族企业在引入战略投资者后也同样会遇到。二者在治理层面的冲突也集中表现为两方面:企业长远利益与短期业绩回报之间的冲突,创始人与战略投资者关于企业主导权的博弈。 如果创始人作为资本方在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的治理冲突上能够掌握最终主导权,治理冲突就会表现为同质的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博弈的结果通常以“火并”的方式,要么是联想式的作为战略投资者的TPG、GA和新桥退出,要么是上海家化式的作为创始人的葛文耀下课。创始人以往的强势作风很难在资本与资本的博弈中发挥积极作用。 党建治理机制对企业家的借鉴 中共党建所体现出的完备治理机制和高超治理能力,有着深厚的唯物辩证法的哲学基础。在中国革命中前期,党的建设运用辩证法的成功之处在于始终把本土政治家、职业军人和共产国际代理人这三大利益相关者整合成一个对立统一的革命共同体,这一共同体内三个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斗争和联合关系始终处于动态的流动、位移和转化过程中,并推动着中国革命事业向胜利发展。 正是在这辩证的发展过程中,党的建设形成了对于职业军人和共产国际代理人不同的治理机制和治理能力。 对职业军人的治理 在中国革命的中前期,对职业军人的治理机制和治理能力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一是共产国际权威的制衡。党内在井冈山时期处理与出身旧军阀的职业军人之间的治理关系时,共产国际的权威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这场争论中,1929年中央的“九月来信”起到了仲裁作用,明确支持了毛泽东,并通过召开红四军“九大”(即古田会议)克服了党内单纯军事思想,并调整了党内职业军人与政治家的治理关系。 二是政委制度。政委制度是党的建设中解决与职业军人之间的治理关系的一项重要机制。政委制度是一种治理机制,而非管理机制。从治理角度讲,政委是某一政治集团在另一组织里面的权力代表,通过权力行使来实现该集团的意志,并维护该集团的政治利益。 以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前做一个研究截面,可以发现军事长官基本是出身旧军阀的职业军人,而政委这个系统,无论是高层的留法、留苏干部,还是中基层的工农干部,都是非军人出身的党务人员。政委制度是中共在党建中对辩证法的成功运用,是一个奇特的双首长制度。 从公司治理视角看,执行董事某种程度上相当于企业的政委,是董事会在企业经营层面的权力和利益代表。一些家族企业采用经营层双首长制,某种程度上也起着政委的作用。 2013年5月,新希望六合董事会任命来自并购前六合集团的职业经理高管陶煦担任总裁,同时任命华南理工大学教授陈春花担任CEO兼联席董事长。在刘永好之女刘畅担任董事长、第二代接班这一敏感时期,面对来自前六合集团的强大的职业经理团队,新希望请来理论、实践两栖学者陈春花担任CEO,形成经营层的“陈-陶双首长制”,其用意不言而喻。 对共产国际代理人的治理 总的来看,共产国际对于中共的成立、发展所起的作用是正面积极的。但是共产国际也给中国革命,主要是中央苏区后期和延安前期带来了巨大损失。处理与共产国际代理人的治理关系难度,远远高于处理与职业军人的治理关系难度,中共直到1945年“七大”才彻底从机制上解决了这一问题。 一是忍耐与有限妥协。在中央苏区时期,作为本土政治家的毛泽东对于共产国际代理人的一些错误路线保持着极大的忍耐妥协,即使被剥夺军权,仍然将自己的活动限定在党的治理架构中,等待时机。 即使在长征初期,王明路线被证明破产,广大中基层干部强烈不满的形势下,毛泽东仍然保持克制,在遵义会议上仅对领导层进行有限度的反思(仅限于军事路线,不涉及政治路线)和调整(仍然由共产国际代理人担任总书记),保证了党在治理层面的团结。 在延安初期,毛泽东已成为党内军内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但在王明回国后的一段时期,为了顾及共产国际,在高层领导合影时,毛泽东仍然选择站在右后边,而让王明端坐第一排。 相反,很多企业创始人在面临战略投资者的压力时就很难做到这一点,仍然保持着在单一治理结构时期的说一不二、有你没我的强势作风。 上海家化的葛文耀在与平安信托的冲突中就不能忍耐,甚至在微博上公开发表微词,最终导致葛文耀、王茁等创业团队彻底出局。 二是掌握意识形态解释权。对于治理问题中的长远利益和短期业绩回报这对矛盾,可以靠忍耐妥协和有限度的调整加以解决,但是对于治理层面涉及独立自主和依赖外部力量主导这对矛盾,靠上述方法就无法根本解决。党的建设对于企业解决治理问题特别是与战略投资者的治理关系的最大贡献,就在于提出了意识形态解释权在治理关系中的作用。 在中国革命时期,意识形态解释权就是对马列主义经典的解释权。在党内三大利益相关者形成的三角治理结构中,掌握意识形态解释权对于谁最终掌握主导权起决定作用。毛泽东正是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式掌握了党的意识形态解释权,并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破除了王明等人所掌握的教条。 企业治理也是这样。西方现代治理理论只提出了经营权和决策权两大权力,但对于中国家族企业创始人来说,要根本解决与战略投资者的治理问题,还需要掌握第三种权力——意识形态解释权。在双方以资本为形态的物质力量势均力敌时,最终掌握主导地位者一定是掌握精神力量的一方。在家族创始人与战略投资者在治理层面博弈的过程中,谁能掌握意识形态解释权将起到决定性作用。 企业创始人即使掌握了经营权,在董事会拥有了决策权,也并不意味着与战略投资者在治理层面的博弈能够长期稳固地掌握主导权。如果没有掌握意识形态解释权,即使像一手创立上海家化、功勋卓著的葛文耀,在战略投资者进入后,也避免不了出局的命运。 对于企业这样的经济组织,意识形态不能狭义地视为一个政治概述。一切有关企业经营理论、人生哲学的思想都可以广义地视为意识形态。 从这个视角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很多企业家如万科的王石、格力的董明珠热衷于出书,或者像华为的任正非不断地撰写内部文章。这些企业家的所作所为本质上也是一种对企业意识形态解释权的掌握。掌握意识形态解释权的方式,甚至并不局限于出书撰文,诚如王石那样攀登世界诸多山峰也是一种以行为艺术的方式掌握企业的意识形态解释权。 中国家族企业创始人对于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治理问题,往往习惯于从中国古代权谋文化中寻找解决方案。但正如毛泽东所说,这种权术“有效但也有限”。中共在长期的革命历史中所形成的“红色基因”,能给中国家族企业提供一种软实力和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