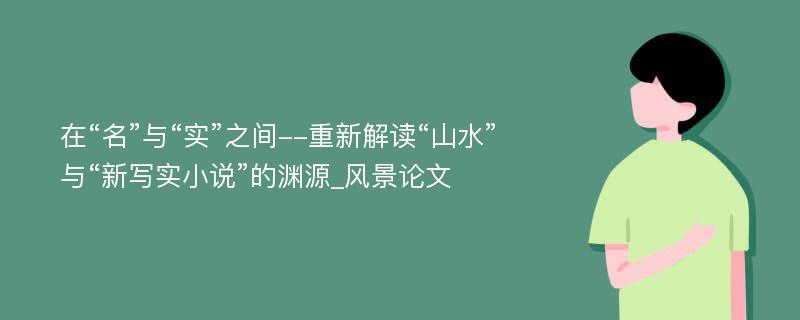
在“名”与“实”之间——重释《风景》兼及“新写实小说”的“起源性”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起源论文,风景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87年,方方完成了新作《风景》,与她此前的小说相比,《风景》“并没有刻意追求什么,对发表后的反应也没有特别的期望,所以也没有去选择发表的刊物,只在湖北一家文艺出版社办的一本名为《当代作家》的刊物上发表出来便算完了。”①但是,一年之后,《小说选刊》和《中篇小说选刊》相继转载了这篇小说,于是《风景》声名鹊起,受到评论家的热烈追捧并被视为“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品。在有的文学史家的眼里,《风景》至今依然是方方“最好的作品之一”②。所以无论从文学史的角度还是作家论的角度看,重释《风景》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而抛开20年前由于潮流化的命名所造成的诸种历史“误读”,将《风景》这一文本重置于其产生的历史语境中,检视其中描绘和建构的独特的时代景观、重审其独特的叙事姿态便是可供尝试的一条道路。在《风景》诞生的80年代中后期,“改革开放”的洪流以战无不胜的力量改造和重构着种种社会图景。这时候,从封闭到开放的狂喜已然退潮,随之而来的是“冷静”的历史审视、自我反思以及感应着时代巨变出现的文学姿态的调整。在“改革”大潮中诞生的《风景》深深打上了种种时代的印痕,这不仅仅指其总的观念结构、叙述姿态,还包括其对“历史”和“现实”的剪裁和取舍、重释和改写。而通过对文本的“还原”性解读和对文本的“名”与“实”之关系的辨析,进而重勘“新写实小说”的“起源性”问题,也是我们重新进入为文学史所定型的“新写实小说”的一个有效途径。
汉口:城与人的“互动”
在“新写实”小说作家当中,方方是最早尝试将视角伸入历史深处,力图在较为广阔的时代风云变幻中叙述家族历史、命运沉浮的作家。方方于1957年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虽然她的父辈们并不喜欢武汉这个城市,但方方却对这座城市情有独钟,“闭着眼睛,我就能想象出它曾经有过的场景。”在她关于武汉历史风物的描述中,不难发现她对这座城市除了历史的冷静审视以外,更多的则是情感上的依赖。“它的历史沿革,它的风云岁月;它的山川地理,它的阡街陌巷;它的高山流水,它的白云黄鹤;它的风土民情,它的方言俚语;它的柴米油盐,它的杯盘碗盏;它的汉腔楚调,它的民间小曲。如此如此,想都不用去想,它们就会流淌在我的笔下。古诗云: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武汉就是我的敬亭山。”③而《风景》正是以独特的视角回溯她对这个城市和生活在其中的底层市民的理解。在《风景》中,方方超越了对城市与人、“现代”与人关系的单向度书写模式,而是在城与人相互作用、相互缠绕的复杂关系中展开独特的人生故事。小说中的汉口绝不是一个可以游离于人物命运之外的抽象背景,也绝不可被其他城市所置换;而父亲一家三、四代的命运传奇也只能在汉口这个独具特色的城市中展开和上演,我们对小说的理解也只能在这种城与人的互动关系中才能展开。
《风景》中人物命运的浮沉总是与汉口的文化性格和历史变迁紧密相连。“地处汉江之汇的武汉三镇,码头的发展与城市经济的发展同步。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汉口仅有码头8座……汉口开埠以后,随着租界的建立和长江近代轮运的日益发展,长江沿岸相继拓建了一批近代轮运码头,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类码头发展到14个,其中8个在租界内,6个在与租界相连的江边。”④从这个意义上讲,人们将汉口视作一个码头城市是无可非议的。小说中的祖父正是在汉口近代化的过程中踏上了他的漫漫征途,与这个城市中独具特色的码头结下了不解之缘,并参与到对汉口的码头文化的构建当中。祖父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从河南周口逃荒来到汉口,开始了在汉口打码头的生活。“祖父是个腰圆膀粗力大如牛有求必应的人”,因为祖父具有一个码头工人特有的身体素质和性格特征——“英勇和凶悍”,于是,他很快便与码头融为一体。“祖父是打码头的好手。洪帮所有的龙头拐子都对他倍加赏识。”⑤也正是祖父的“英勇和凶悍”将他送上了死路。“为祖父哀伤洒泪的人几乎是一望无边。父亲至今也没想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父亲猜测大约是祖父善打码头的缘故。”祖父的生活道路和人生模式赢得了父亲的高度赞同,于是,父亲在祖父死亡之后加入了打码头的行列,开始了另外一段“辉煌、灿烂”的人生。在父亲的生命中显现出独特回忆价值的是“民国三十六年轰动武汉的徐家棚码头之争”,码头上的父亲尽显其“英雄风采”。
码头不仅给父亲提供了谋生的场所、经济的支援,更是父亲展示自我、实现自我的舞台。父亲只有在码头上才能产生一种深深的自我认同感。所以,即便他回到家里,也总是以一个码头工人的姿态面对妻子、儿女和邻居。尽管母亲同父亲结婚四十年而挨打数“已逾万次”,“可她还是活得十分得意”。在对母亲施虐的过程中,父亲是否在潜意识中产生了空间上的混乱感将家当作了码头呢?他是否同时体验到了打码头的快感呢?而对自己的孩子,父亲更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给他们讲述“他的战史”。这时候所有的儿子都必须老老实实坐在他的身边听他进行“传统教育”。父亲说:“给老子坐下,听听你老子当初是怎么做人的。”这时候父亲又俨然是一个深知人生要义的教师,而他所能传授的仅仅是他在码头上的“英雄”行为。除了妻子和儿女,“所有的人都能证明父亲是这个叫河南棚子的地方的一条响当当的好汉”。也就是说,码头早已不是外在于父亲的谋生场所,它早已融化为父亲生命的组成部分,成为父亲最重要的精神支柱。父亲因码头而获得深刻的自我认同,而码头也因为父亲们的存在而维持着运转,并进入到汉口的历史中成为其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一个商业都会,汉口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⑥移民是汉口历史上自古就有的现象,但是,规模空前的移民浪潮则出现在1861年汉口开埠之后。祖父正是在这种移民浪潮中逃荒来到汉口,而他们的居住地也因此被称作“河南棚子”。虽然河南棚子一直是汉口“下层人”聚居的地区,其居住环境相当恶劣,“京汉铁路几乎是从屋檐擦边而过。火车平均七分钟一趟,轰隆隆驶来时,夹带着呼啸而过的风和震耳欲聋的噪音。”但是,父亲早已习惯了这种喧嚣和噪音,并把它当作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甚至感到“没火车叫他是睡不着觉的”。除了外在环境恶劣以外,父亲一家的居住条件也相当差。只有十三平米的板壁房的简陋程度并没有给父亲以自卑和不满足,却恰恰令父亲倍感骄傲。所以他每每向自己的拳友们说他是河南棚子的老住户。但是,老汉口人“提起河南棚子如果不用一种轻蔑的口气那简直是等于降低了他们的人格”。父亲在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码头)和相对封闭的环境中(河南棚子)中保持着独立和对自己地理位置和社会位置的强烈认同。在这种深深的认同感中,作为移民的父亲很快便与汉口融为一体。裘德·马特拉斯曾指出:“都市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移民现象。”⑦而汉口正是有了父亲这样的移民才加快了其都市化进程。
《风景》对汉口地理图景的呈现具有高度的写实性,“某些细节的真实程度恰如巴尔扎克笔下的伏尔盖公寓,可以按图索骥地去寻找。”⑧小说中对这种真实的地理位置的事实区分和价值呈现是随着城市的发展而改变的。比如,老汉口时代的河南棚子位置较为偏远,而如今却“差不多是在市中心的地盘上了”。建于1903年的老汉口火车站最终为新火车站所代替,“穿越城市的铁路要改为高质量的公路,公路两边的破旧房屋全部拆除,重新起盖高楼大厦。”这种从中心到边缘、破旧立新的改变深深打上了时代更替和现代化的印记。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城市居民的父亲一家因为诸种原因在80年代分居于城市的不同角落:五哥六哥因为娶了汉正街的姑娘当了上门女婿而进驻汉正街这个“自古便是商贾云集之处”;七哥因为娶了“水果湖”的高干之女而晋升神速,很快地调到了团省委,分到了宽敞的房子,并成为晴川饭店的常客;小香和大香姐姐分别居于黄孝河边和三眼桥这些“汉口下层人历来所居之地”。从城与人的关系角度看,城市居住空间同时兼具物质空间和社会系统的特征,它不仅仅是城市地域空间内建筑的空间组合,同时也是人们居住活动所整合而成的社会空间系统。所以,父亲一家居住空间的分布是80年代社会分层的表征和结果。总之,百年汉口空间区域在和父亲一家的紧密互动中呈现自己生动鲜活的历史。
“历史”:压缩与放大
从空间、地域文化的角度展示父亲一家的生存状态和命运沉浮的同时,《风景》将这一故事深深地植根于20世纪中国历史变迁的广阔背景之中,在80年代的视野中对历史进行了重新的择取、剪辑和排列组合,并从这种“历史”筛选中展开与80年代的广阔对话。正如戴锦华所说,“或许对于一部文本范例,重要的不是它讲述了什么,而是它如何讲述,以及它巧妙的有意识的省略。”⑨
《风景》中对父亲一家命运浮沉故事起点的设置是耐人寻味的。小说明确标示出祖父逃荒抵达汉口的时间——光绪十二年(1886年),而《风景》的写作及其故事的终结都是在1986年。从故事的开始到结束恰恰是一百年的时间,在一个世纪的历史长河中叙述汉口和底层家庭的时代变迁显然是一种颇有野心的文学实践。同时,这个故事的起始时间也暗示出小说中的故事与汉口的近代化过程的密切关系。“从1861年汉口开埠到1911年辛亥武昌起义爆发,武汉三镇从封建市镇转化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型的近代都会,在扭曲中经历了早期的不成熟和近代化。汉口开埠、张之洞的洋务新政,构成这五十年间城市发展的两个节点。”⑩也就是说,《风景》中的祖父和1889年起任湖广总督的武汉地区早期近代化设计者张之洞几乎是同时抵达汉口并加入到对汉口近代化的创造之中(尽管历史功绩不同)。从人与历史关系的角度来看,《风景》中祖父一家三代的命运都是在张之洞新政的语境中发生的,张之洞事实上是小说中一个缺席的在场者。谙熟武汉历史的方方却对这一重要人物及其举措只字不提。如果我们对照小说中对其他与武汉和父亲有重要关系的政治事件的叙述,便可知在暗示祖父一家命运与汉口近代化过程的历史联系的同时隐去对宏大政治事件的叙述是一种有意为之的创作策略。作为一个被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构建为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代表先进生产力和社会发展方向的工人阶级的一员,小说中的父亲与中国现代史上的诸如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抗日战争、新中国成立等种种革命和建设事件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关联。无论世事如何变迁,父亲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始终保持着高度的延续性,他始终在自己的生活轨道上较为自足地生活着。
这种祛除政治事件对人物命运介入的叙述策略也通过细节展现出来。在祖父和父亲漫长的生命旅程中,为小说所捕捉到的历史细节仅限于30年代祖父的打码头的事件和民国三十六年父亲参与的“徐家棚码头之争”,祖父一家在漫长的岁月中粗糙而平静地生活着,凭着一身勇敢和鲁莽在码头上打拼,在河南棚子的板壁房中栖居。通过将历史充分个人化和细节化的叙事方法,方方祛除了宏大的历史叙事对人物的干预。仅有的一次关于政治事件的讨论发生在三哥与父亲之间。三哥提出问题的方式很有趣:“三哥总说爷爷若一来便当兵,没准参加辛亥革命,没准还当上一个头领,那家里就发富多了。说不定兄弟姊妹都是北京的高干子弟。”三哥的话马上引来父亲的强烈反驳,“父亲说若不像祖父那样活着那活得完全没有意思。”由于父亲对码头工人这一职业和生活方式有一种强烈的自我认同感,在他看来,政治和时代更替与码头工人无关。直到政府要求孩子们上学时,父亲才感叹道:“让人都学了文化码头还办不办?”这种叙事通过个体经验和日常生活细节的强化以及对中国现代史中的重大政治事件的悬置,对历史进行重新编码和改写,“个人生活的情节不能推广、不能转移到整个社会(国家、民族)的生活中来。”(11)同时也为重新叙述汉口和父亲一家的“历史”找到了另外一个有效的途径。
对父亲一家而言,从1886年祖父抵达汉口到20世纪60年代的“历史”是一个整体,他们总是在“历史”之外既定的轨道上稳定而粗糙地生存着。但无论如何,父亲一家无法逃脱中国当代“历史”的“规训与惩罚”。首先的冲击来自于60年代。1961年是一向骄傲的父亲与“历史”事件发生碰撞并深受影响的开始。小说中强调父亲和母亲在这一年因为饥饿而停止了他们生育一个排的“雄伟”计划,同时他们的第八个儿子也夭折了。当维持最低标准的生存基础受到威胁的时候,父母亲相对自足自然的生活状态被打破,他们的命运不得不与当代“历史”发生关联。除了1961年的饥饿之外,在方方稍显仓促的叙述中,流露出建国后教育制度对父亲一家的深刻影响。孩子们的上学并不是出于自愿,也非父亲“情愿”,而是政府要求的结果。“父亲说政府怎么糊里糊涂的?让人都学了文化码头还办不办?”应该说,父亲对政府政策的关注角度是独特的,视码头为全部生命依托的他只能从码头兴衰的角度关注这一历史事件。但是作为政府的一项政策,教育制度与父亲对码头前景和儿女们人生的期待背道而驰。因为基本的生存和人生规划受到制度变革的规约,父亲一家自足的生存状态在一步步地为“历史”所破除,中国当代史在悄然改造着父亲一家的生存方向。
从叙述速度上看,小说对“文革”前的历史进行了“压缩”式处理,而对“文革”及80年代的历史叙事则放慢速度进行了“放大”。作为80年代文学潮流和书写模式更迭的参与者,方方是一个具有清醒文学史意识的作家。“其实我在1986以前,也学着人家玩了一些花招。总想这个也去试试,那个形式也去试一下。玩了几样花招后,反觉得什么都不灵觉得什么都没有意义。这些作品自己觉得其实都看不得。”(12)这使她的“文革”书写有意地与以往的“文革”叙事保持了距离。无论是“伤痕”还是“反思”小说,都以后设的历史观念在模式化的故事讲述中证明“新时期”的辉煌。与众多关于这个年代的惨痛记忆不同的是,方方对二哥、三哥、七哥“文革”中遭遇的讲述与这些书写模式相去较远。善良而多情的二哥在“文革”前救了来自知识分子家庭的杨朦的命,于是他开始走进这个迥异于自家的家庭并深深地爱上了杨朦的妹妹杨朗。“文革”中父母投湖自尽,无助的杨朦兄妹找到了“河南棚子”。
此刻父亲已经下了床。他用脚踢着正趴在地铺上听杨朦说话的三哥四哥五哥,嘴上说:“起来起来,今晚都去找人。”父亲转身对杨朦说:“让二小子陪姑娘,这几个小子都派给你,你尽管指使他们。”杨朦说:“伯伯我该怎么感谢你呢?”父亲说:“少说几句废话就行了。”
在这个危险的时刻,父亲再次以码头工人的行为方式解决了来自知识分子家庭的杨朦兄妹的难题。在料理完父母的后事之后,杨朦兄妹被卷入到“上山下乡”的洪流中去,而二哥则主动放弃了留在城里的机会,随着杨朗下乡。在二哥无微不至的照顾下杨朗生活得如意快乐。但是有一天杨朗决绝地要和二哥分手,因为她通过自己的贞操换来了进城的机会。等待二哥的是“生如蝼蚁,死如尘埃”式的彻悟以及彻悟后的自杀。而随着二哥下乡的三哥也在二哥血的教训中坚定了终生不娶的念头。在此,知青“上山下乡”故事中知青内部的差异得到了强化,一个来自下层的知青以无比的真诚和善良向来自于知识分子家庭的知青靠近,后者在不拒绝前者带来的利益的同时,又选择了“适当”的机会和理由抛弃了前者。父亲式的以经济基础和生活方式为据对人进行分类和切割的方法被证明是有效的。二哥的遭遇以血的教训证明了父亲的一句话的“真理性”:“鼓起骨气就是不要跟有钱人打交道,让他们觉得你是流着口水羡慕他们过日子。”在此,方方在父亲的立场上对二哥的“文革”遭遇给予了令人警醒的解释,对知青内部的差异性及其关系给予了尖锐的揭示。
在单一的知识分子视角之外,方方借助于下层的眼光发现了“文革”中的另一种知青故事,对文学史中模式化的知青故事进行了改写。这种思路也在七哥的知青身份和命运沉浮的互动中得以体现。“文革”前的七哥基本属于游离于“历史”之外的流浪者。他从五岁便开始捡菜,在患难的路上遇见了同病相怜的够够。这个同样来自于下层的女孩子给了他的童年唯一的温暖。无奈够够最终因车祸长眠在铁轨上。1974年,七哥的命运和“文革”发生了联系,他成为“上山下乡”运动中的一名知青。从城市到农村的空间位移给七哥带来生活上“反向”的巨大落差:他因此第一次住进了较为宽敞的房子,“有生以来第一次在正经八百的床上睡觉”。而七哥的精神危机也发生在这些年。当村民们发现梦游的七哥正是给他们带来极大恐惧的“鬼”时,最好的办法是将七哥送走。于是,1976年,七哥又一次借政策之光被“推荐”上了“北京大学”。七哥的人生发生了重大转折,“文革”将他从幕后推到前台。方方通过对七哥遭遇的处理反思“文革”中知青命运的多元性,在弥漫着痛苦的遭际背后,定会有一种机会垂青像七哥这样“苦大仇深的码头工人的后代”和令人厌恶的梦游者。
如果说父亲一家与建国前的“历史”较少关涉,与50至70年代的“历史”局部碰撞的话,他们与80年代转型的“历史”互动却是激烈的整全的。
父亲母亲因为退休而逐渐从家庭的前台走向幕后,陪伴其一生的汉口火车站因为新的火车站即将诞生而“结束了它的使命”,包括河南棚子在内的“公路两边的破旧房屋全部拆除,重新起盖高楼大厦”,“历史”无情地摧毁了伴随父母亲一生的居所,改造了与其相守一生的历史陈迹。三哥因为突发的海难改变了自己“水手”的职业,成为了补鞋者;四哥因为身体的残疾继承了父业;作为80年代的青年,七哥不择手段地通过裙带关系成长为官员;五哥六哥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辞职干起了个体户,终于从贫穷落后的河南棚子走向了富裕繁华的汉正街;大香小香姐姐则未能摆脱“下层”的命运,最终将家安在了黄孝河边和三眼桥这些“历来下层人居住的地方”。时代的结构性转折剧烈地改变着每一个人的生存处境和命运,作为大时代的一分子,父亲一家终于被时代洪流裹挟着前进,成为大时代棋盘上的一粒棋子,或者落寞或者兴奋但最终却不能不与“历史”发生碰撞。
家庭:代际冲突与秩序重组
《风景》在广阔的历史视野中勾勒出汉口的百年风云,而居于小说中心位置的始终是父亲一家琐碎的生活细节,正是家承载着诸多城市变革的讯息。小说中涉及到父亲一家四代人的生活,从代际承传的角度看,无论从职业还是生活理念上父亲和祖父之间保持着前后的统一。父亲以父子相承的方式继承了祖父码头工人的职业,也誓死维护祖父和自己的生存之道,他甚至认为“不像祖父那样活着完全没有意思”。在儿女们长大之前,父亲一直是家里绝对的权威,这一阶段的家庭生活虽然粗糙却基本平静。
父子间最初的冲突都起源于十三平米的板壁房,虽然冲突的形式和性质各异,但是大哥和二哥对父亲的反抗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随着儿女们的成长,十三平米的板壁房实在无法容纳父亲一家。于是,大哥只能借宿在邻居白礼泉家。这个在武钢上班的家境较好的邻居之妻却又爱上了大哥。因为三角恋爱而起的吵闹最终激烈化,已经征服了白礼泉之妻的大哥异常骄傲,他向白礼泉挑衅,但是却被对方轻易地制服:
白礼泉说:“好吧。那房子是我的,我要收回。你娶她吧,让她住在你们那个猪窝里。跟你的父亲住一起,跟你的兄弟住一起……”白礼泉的话像是砸在大哥胸口上的石头。大哥突然脸色苍白,眼泪差点儿没落下来。
一向以凶悍著称的父亲看到这一幕后难免奚落大哥,并上前扇了大哥一个耳光。被激怒的大哥和父亲“扭打成一团”,并咒骂父亲说:“世界上像父亲这样愚蠢低贱的人数不出几个。混了一辈子,却让儿女吃没吃穿没穿的像猪狗一样挤在这个十三平米的小破屋里。这样的父亲居然还有脸面在儿女面前有滋有味地活着。”像父亲一样以凶悍著称的大哥在“房子”面前马上显现出颓败的姿态,并将这种刺激转化为与父亲扭打的动力,而父子之间的冲突最终落在了这个曾让父亲为之骄傲的居所。争吵虽然很快结束了,但父亲在家里的权威却分明受到了挑战,这种挑战不仅仅指向房子本身,同时也指向父亲粗糙的生活方式。但是,这种挑战因为大哥与父亲在职业和精神上的深层同构而只能停留在打斗层面,试想,如果作换位思考的话,大哥能比父亲更出色吗?
作为家中文化程度较高的一员,二哥对父亲的反抗起源于因另一种生存状态的发现而引来的心理震撼和自我反思。当二哥第一次来到为他所救的杨朦家的时候,惊异感油然而生。自家房子与杨朦家房子的强烈对照打破了二哥内心的平衡,而且杨家“相亲相爱”、“民主平等”、“文质彬彬”、“温情脉脉”的“另一种活法”令他吃惊令他“陶醉”。新的生活参照系建立起来之后,一种新的生活理念刺激着他,使他开始对父亲及其生活方式充满怀疑和厌倦:
二哥将七哥放在床上,撩开盖在他腿上的布,对父亲说:“他也是条命,你也不要太狠了。他的腿伤口烂了,长了蛆。你要想让他活,就不能再让他睡床底下。里面又湿又闷,什么虫都有。”父亲看了看七哥,冷冷地说:“他是老子养出来的,用不着你来教训。”二哥说:“正因为他是你的儿子我的弟弟,我才要求你好好保护他。”父亲顺手重重地给了二哥一耳光。父亲说:“让你读点书你就邪了,在老子面前咬文嚼字。你给我滚。”
如果说大哥与父亲的冲突主要是一种冲动式的身体冲突的话,二哥对父亲的反抗则带有更深层的精神因素和理性特征。二哥的话语是建立在人道主义基础上的“现代”话语,它的主要特征是对个体的平等、独立、自由地位的寻求;而父亲的话语则是以长者为本位的强调服从和专制的“传统”话语。所以,二哥和父亲的冲突与其说是一种对待七哥这样的具体问题的争辩,不如说是分属知识分子和工人、上层和下层的不同系统话语间的争辩。二哥争辩中虽然取得了暂时的胜利,但最终却在“文革”中因追随杨郎而自杀。于是,这种人生结局就具有着象征意味:这不仅仅是作为个体的二哥的死亡,更是在当时遭受排挤和打压的知识分子话语的失败。而父亲实际上是父子冲突中最终的“胜利者”,他“对二哥的死愤愤然之极,每逢二哥忌日父亲便大骂二哥是世界上最没出息的男人,混蛋一个却装得像个情种。然后接下去必然骂这都是读书读木了脑袋”。大哥和二哥对父亲的反抗都无果而终,其中深层原因便在于父亲产生自我认同的社会基础尚未破除,父亲和他代表的话语在当时尚居于主导地位,工人的身份及其话语还具有自明的优越性。
吉登斯在论及自我认同时提出了“本体性安全”的理论,这一术语指的是:“大多数人对其自我认同之连续性以及对他们行动的社会与物质环境之恒常性所具有的信心。”(13)而五哥、六哥和七哥最终能够完成身份转换以及“弑父”的“历史重任”,正是因为“改革开放”中的社会为他们提供了身份转变的机会和保持自我认同的“信心”。无论从体格、职业还是精神上看,五哥和六哥都全面继承了父亲。但是随着80年代“下海”经商渐成风气,于是五哥辞掉了“工资不算低”的泥瓦工,六哥也辞去了运输公司汽车修理工。五哥凭借狡猾和投机终于忝列汉正街万元户之一,“六哥自然也不例外”。五哥和六哥不仅实现了从工人到个体户的身份转变,还将家从河南棚子移到了汉正街。五哥的女朋友不满河南棚子的“屁点破屋”,和父亲起了冲突,五哥“跳起来对父亲乱叫了一通便又噔噔噔地去追赶那女朋友”。父亲不得不感叹“日月颠倒了,颠倒了”,但五哥还是做了汉正街的“上门女婿”,六哥也紧随其后成为“倒插门”女婿。偶尔回河南棚子的五哥六哥带来“花团锦簇且粉团团的孙辈们”,父亲说“人要是像这么养着就会有一天变成猪”。面对五哥赌钱的豪语,“父亲怀疑五哥和六哥是不是他的儿子了”。
作为80年代“改革开放”历史潮流中的“弄潮儿”,五哥和六哥实现了转变,而父亲则只能在慨叹声中无奈地被历史所遗弃,从而变得“落寞”和“痛苦”。这种父子秩序的位移不仅指向代际之间的普通流动,同时也是新时代经济身份对政治身份的胜利表征。
在家庭秩序重组的过程中,经过代际冲突和同代人之间的较量,最终替代了父亲中心位置而成为家中轴心人物的是七哥。七哥从出生到长大一直都伴随着一种深刻的焦虑,小的时候备受一家人的(大哥二哥有时照顾他)虐待使他濒临精神分裂的边缘。“文革”中因为梦游而惊吓了村民却又阴差阳错地被“推荐”上了大学。大学里同宿舍的苏北佬假借女朋友亡故而出名的事情被七哥发现,于是苏北佬给七哥“上了一课”:“苏北佬说干那些能够改变你的命运的事情,不要选择手段和方式。想人们对你的卑微的地位而投去的蔑视的目光,想你的子孙后代还将沿着你走过的路在社会的底层艰难跋涉。”对于七哥来说,苏北佬的话犹如醍醐灌顶,“一切噩梦已过”。毕业后的七哥在一所中学教书并与一名大学教授的女儿恋爱,但是当他有一次偶然遇见了家住“水果湖”的高干之女之后,七哥马上完成了自己人生的转折:和教授的女儿分手,和虽不能生育却能令自己“进入上层社会”并仕途畅通的高干之女结婚。通过种种“努力”之后,七哥终于从“睡在床底下”的“小七子”变成个“人物”,从家庭的最边缘走到最中心。
在顺利实现身份转换之后,七哥在家中的角色期待发生了质的变化。他一进家门“就狂妄得像个无时无刻不高翘起他的尾巴的公鸡之状态”,“就像一条发了疯的狗毫无节制地乱叫乱嚷”,而“父亲得忍住自己全部的骄傲去适应这个人物”。大香小香姐姐都争相将自己的儿子过继给七哥,而七哥决绝地从孤儿院领养了一个孩子后“扬长而去”。父亲“想骂人而终未骂出”,因为在父亲的眼里“七哥是政府的儿子而不是他的”。尽管五哥六哥讽刺七哥“费心思往上爬不如费心思赚点钱”,并故意把儿子的脸亲得“叭叭”响以刺激七哥,但是七哥在组织个体户们座谈时仍然居于中心并侃侃而谈。这种位置和姿态实际上意味着七哥对五哥六哥的统摄权。至此,七哥终于通过不择手段的努力而代替父亲成为家中新的权威人物。而与此同时,他决绝地与令他作呕的家进行告别。位于高处的七哥成了一个多重人格的人,他“穿上西装打上领带便仪表堂堂地像个港商”,“戴了副无边眼睛便酷似教授抑或什么专家”,一进家门便“疯狗气”十足。也许在精神上与父母亲和兄弟姐妹划界并没有那么容易,但是通过从孤儿院领养儿子,七哥终于从血缘上完全拒绝了父亲和家庭,成为这个家庭最决绝的叛逆者。历史地来看,七哥的“弑父”最终发生在新旧交替的80年代,作为某种类型的时代青年,七哥对父亲的胜利是全面的胜利:从物质基础到话语类型,从经济收入到社会地位,七哥以“新人”的姿态和优势战胜了“旧人”。正如巴赫金所说的那样:“这里的成长克服了任何的个人局限性而变为历史的成长。所以,就连完善的问题,在这里也变成了新人同新历史时代一起在新的历史世界中成长的问题,这个成长同时伴随着旧人和旧世界的灭亡。”(14)于是,我们看到小说结尾是城市的一派以新胜旧的景象。
“新写实小说”的“起源性”问题
《风景》通过对父亲一家与汉口文化关联的重新书写,凸显作为码头工人的父亲的非阶级性面向的同时,在百年汉口近代化的历史视野中,悬置中国现代史中的重大政治事件和父亲一家的关联,从日常生活的角度关注父子移位和兄弟姐妹的分化等家庭秩序的重组,以凸显80年代历史的结构性巨变。但是,一旦文本被纳入到为文学史所定型的“新写实小说”的麾下,我们便习惯在“零度写作”、“还原生活”、“读者的诞生”这些为文学史所整合的文学思潮的共性层面来理解这个文本。这种流行的理解方式实际上忽略了“新写实小说”的“起源性”问题。
《风景》原本发表在湖北的地方刊物上,“人们发现这篇小说的价值是通过一年后转载这篇小说的《小说选刊》”(15)。该刊于1988年第1期最早将《风景》与《烦恼人生》相提并论,并提出两篇小说的共同特点是以武汉三镇为背景描写“改革浪潮中”“城市的变化”(16);随后,该刊在第3期率先指出《新兵连》与《塔铺》的共同特点是“擅长于在日常琐碎事件中写群体的众生相”(17)。1988年3月,《小说选刊》举办“刘震云作品讨论会”,会上雷达等批评家首次将刘震云与李锐、刘恒、朱晓平等人的作品视为同一类型的创作,认为他们“在向我们今天的创作提供了一种可能(他们也正在完善这种可能):我们可以较为冷静、从容地面对我们的生存,而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18)紧接其后,雷达的《探究生存本相 展示原生魅力》一文对后来被命名为“新写实小说”的文学思潮进行了初步的概括和总结。在该文中,作者进一步扩大了文本的范围,认为包括《风景》、《曲里拐弯》(邓刚)、《烦恼人生》(池莉)、《狗日的粮食》《白涡》(刘恒)、《塔铺》(刘震云)、《黑砂》(肖克凡)、《红橄榄》(肖亦农)等在内的一批小说“在把握现实的内在精神上,再以肉体直搏民族的生存状态和生存本相上,在正视‘恶’、‘丑’、并将其提升到审美层次上,以及在对美的价值判断上”“却不无某种不约而同的潮流性变化”。(19)之后,1988年10月《钟山》杂志与《文学评论》联合召开的“现实主义与先锋派文学”的讨论会上,“新写实小说”被作为重要的文学现象提出。随后,《钟山》于1989年第3期开辟“新写实小说大联展”专栏集中推出了包括赵本夫、朱苏进、苏童、刘恒、刘震云、方方、池莉、范小青、王朔、周梅森等人的小说。《钟山》卷首语上说:“所谓新写实小说,简单地说,就是不同于历史上已有的现实主义,也不同于现代主义‘先锋派’文学,而是近几年小说创作低谷中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学倾向。这些新写实小说的创作方法以写实为主要特征,但特别注重现实生活原生形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新写实小说仍可归为现实主义的大范畴,但无疑具有了一种新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善于吸收、借鉴现代主义各种流派在艺术上的长处。”(20)这种理论描述存在着含混不清的特征,却恰好说明了作为一种有异于思潮归纳的文学策划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稍后,曾参与策划“新写实小说大联展”的王干则说得更加明确:“后现实主义实际上超越了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既有范畴,开拓了新的文学空间,代表了一种新的价值取向。”(21)他认为这些小说存在三个方面的“超
越”:“还原生活本身”、“情感零度写作”、“作家与读者共同作业”,即反对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对生活进行本质概括,消解作者的主体对文本的干预,反对作家对读者的“意义导读”。而《文学评论》1991年第3期刊登了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当代文学研究室“新写实”小说座谈会辑要。时为文学研究所长、《文学评论》副主编的张炯在“引言”中首先对“新写实”作家和主要篇目做了限定:刘震云、刘恒、池莉和方方及其代表作。其他成员则对这种文学思潮做出各异的阐释和解读。由此可见,“新写实小说”的命名是批评家和文学杂志、思潮总结与文学策划、作家与读者……博弈的过程:这是对各异的文本差异性和丰富性的理解与认知的过程,同时也是在求得最大公约数的基础上对不同的文本进行简化和抽绎的过程。
如今的文学史则已将“新写实小说”复杂的命名过程中对文本的各异的理解过滤、纯化,剩下的仅仅是为张炯所定型的刘震云、刘恒、池莉和方方的代表作以及以王干的批评为主导的文学思潮的“典型特征”。尽管这些特征在理解这类文本时仍具有一定的有效性,但是一旦这些“典型特征”成为自明的文学史常识,就会自然而然地左右专业读者的致思路经和感受方向。“新写实小说”内部的巨大差异就会被一种先在的“本质”所遮蔽而变成铁板一块。尽管任何文学思潮的命名总是包含着对具体文本的独特性的遮蔽,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对文学思潮的“本质”特征的必要的警惕,而是颠倒了过程和结果的历史顺序,用追认的思潮之“名”去理解文本之“实”、用后设的“本质”特征去理解先在的文本的话,无论是具体的文本解读还是文学史思潮的研究,必将因为颠倒了思路而走向歧途。从这个意义上说,将包括“新写实小说”在内的一切文学思潮理解为一个逐步建构的过程而非本质化的结果、一个历史的产物而非逻辑的集合便成为一种必要的研究常识。而这也正是本文解读《风景》进而思考“新写实小说”的“起源性”问题的致思路径。
注释:
①⑧(15)於可训:《方方的文学风景》,见《祖父在父亲心中》,江苏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364页。
②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01页。
③方方:《我心中的武汉》,《城乡建设》2006年第2期,第68页。
④⑥⑩皮明麻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721、606、721页。
⑤文中所引《风景》,见《祖父在父亲心中》,江苏文艺出版社,2003年。
⑦裘德·马特拉斯:《人口社会学导论》,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13页。
⑨戴锦华:《红旗谱——一座意识形态的浮桥》,《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唐小兵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09页。
(11)(14)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三卷,钱中文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07页、440页。
(12)方方:《我写小说:从内心出发——在苏州大学的演讲》,《当代作家评论》2003年第4期,第20页。
(13)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80页。
(16)《小说选刊·编后》,1988年第1期。
(17)《小说选刊·编后》,1988年第3期。
(18)斯冬:《展示出生活的原型——刘震云作品讨论会综述》,《小说选刊》1988年第6期。
(19)《文艺报》,1988年3月26日。
(20)“新写实小说大联展”,《钟山》1989年第3期。
(21)王干:《论近期小说的后现实主义倾向》,《北京文学》1989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