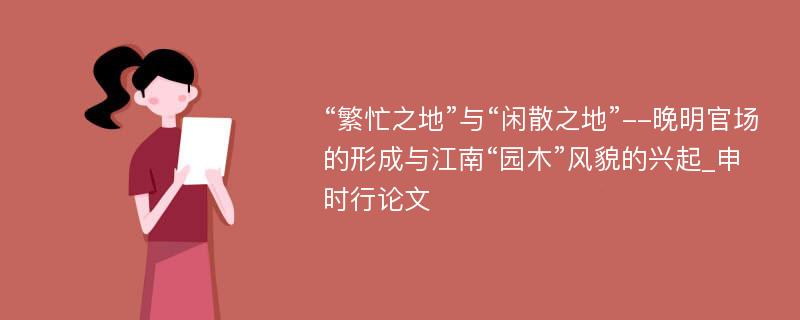
“忙处”与“闲处”——晚明官场形态与江南“园林声伎”风习之兴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风习论文,江南论文,官场论文,形态论文,园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85(2008)01-0128-08
一、明代政治制度的特质与晚明士风迁换
政治和文艺向来为中国传统士大夫致力的两端,前者体现“士志于道”、“学而优则仕”的儒家价值取向,后者昭显士阶层与生俱来的文化身份。政与艺的彼此渗入干预塑造了传统士大夫特定的人生形态和精神空间,并外化为整体性的社会景观——一个时代的文艺与一个时代的政治由此呈现出殊为密切的关系。晚明江南“园林声伎”风习的兴起,便联系着彼时特殊的政治与官场形态。
明代政治制度的特征体现为空前的中央集权,这一制度乃是由开国之君朱元璋设定的。《剑桥中国明代史》言:“在中华帝国历史上,没有其他本土统治者象洪武帝那样蔑视、不信任和虐待他的官员——特别是文官。”[1]朱元璋立朝“以重典驭臣下”、废除丞相(洪武十三年因胡维庸案废除丞相,从此终明一朝不设丞相,后朱棣设内阁,实为皇帝秘书处),将大权揽于一身,他和继任朱棣推行的厂卫制度、廷杖、诏狱终明一朝给朝臣和士人带来浓重的心理阴影。明王朝的政治高压还辅以思想钳制,此即理学治国、“八股取士”建立的道德秩序。然而,高压与钳制必然招致反向的力量,明中叶以后,这一制度危机渐显,皇帝怠政、内侍擅权屡屡发生,文官集团的矛盾亦愈演愈烈。此中困局,正如黄仁宇《万历十五年》所揭示:在权力争斗中的权力失效,在道德泛滥下的道德虚无。万历政坛的缺官现象向为史家所乐道,如《明史》言:“时神宗怠于政事,曹署多空。”[2]卷二百二十五今人谢国桢进一步解释:“万历中叶以后,因为言官的纠纷,铨部已失去了效力,自用掣签法后部权日轻,只要经言官的弹劾就不辞自去,政治已茫无头绪,所以发生了缺官的现象。”[3]无论是皇帝的怠政还是文官集团的斗争,其引发的官员对体制的离心力皆毋庸置疑。
政治和官僚制度弊端百出的时节,也正当明代社会风气和士林风习发生迁换的时候。朱元璋借“程朱理学”建立的禁欲社会,受到不断发展的商品经济的有力挑战,社会生活由简朴端肃渐趋尊崇富侈、热烈活跃,市民文艺蔚然兴盛,“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侈靡相高。”[4]应运而生的“阳明心学”及其后学,则在思想领域掀起了一股反禁欲、追求个性解放的潮流。“士贵为己,务自适”[5]等富有异端色彩的论说,在士林中激起强烈反响,召唤着他们于政治道德之外寻求任性适情的人生。晚明士人之于生活上趋向享乐、情性上趋向放纵、品格上趋向狂狷,实乃仰赖了壮大的市民社会为土壤,王学左派的理论为旗帜。这一动向,加剧着他们对政治目标和官僚机制的离逸。
明代“士多出江南”,商品经济的首善之地也恰在江南,江南成了观察晚明社会转型和士风转向的特殊地域。江南,亦是士文化传统深厚的地域,东晋以来“江左风流”的标举,提示了一种于政事荒败之际隐逸山水、藏身艺术而别立精神空间的可能——那也正是“园林声伎”的历史源头。此一传统和晚明社会现实取得了接应:以当年王谢士族的“江左风流”为精神前导,以活泼新鲜的世俗生活为现实指向,精神标高与物质享乐两不相妨。由是,与北国京城遥遥相对、富庶、安闲、美丽的江南,诚为众多明代士人地理上和精神上的双重故乡,一旦他们的政治生命走向困厄与黯淡,这里还有家园,还有人生的另一番意趣。
明代“园林声伎”的风习即是由江南退休官员推动的,他们由衙斋而园林、由政事而艺事、由“忙处”而“闲处”,融市民文艺于文人高致,在风花雪月和诗酒声歌中消解着那曾经的壮心和忧心,同时自觉不自觉地完成了一种文化构建。此时流行的伎乐,为中国戏剧史上最优雅的昆曲,而明王朝,就是在这样优雅的声歌中崩解灭亡了的。
二、晚明江南“园林声伎”风习之叙要
如前述,中晚明社会,官僚制度松动的表现之一是罢官辞官的随意化。某种程度上,它造就了以输送科举人才著称的江南地区退休官员队伍的庞大。这支庞大的队伍,就是沉吟“园林声伎”的生力军。
不做官的自由肯定是一种可贵的自由,熟悉“酷政”的明代人尤其深味这点。主动致仕、功德圆满地引退、不得已地丢了官,构成晚明人脱离官场的三种形式,而这三者的界限有时殊难分辨。嘉隆年间,松江人何良俊在南京翰林院孔目的位置上“居三年,遂移疾免归”[6]451。从此过着蓄养声伎、宾客盈门的自在生活。而何良俊钦慕的前辈、吴中四子之一文徵明也是在一个小官的任上辞职里居的。到了万历年间,这一类情形发展得更为普遍。辞官与丢官往往基于相似的行为动因。《列朝诗集小传》叙述屠隆:“在郎署,益放诗酒,西宁宋小侯少年好声诗,相得欢甚,两家肆筵曲宴,男女杂坐,绝缨灭烛之语,喧传部下,中白简罢官。”[6]445几乎在同时,吴江人顾大典也因“为郎时,放于诗酒”,获罪“坐谪”禹州知州,顾“遂自免归”,后“再起开州,不就”①。去官本身固然不是什么愉快经历,但无论屠隆还是顾大典,他们去官后的生涯似都相当潇洒。屠隆创作传奇三种皆在罢官还乡后:“园居无事,技痒不能抑……意兴偶到,辄命墨卿,《昙花》、《彩豪》纷然,并作游戏之语。”[7]2986册顾大典亦家有园池:“清音阁在园中一隅。登楼远眺,则粉堞雕甍,逶迤映带。眺视则园景可得十之八九,竹树交夏,不风而鸣,淙淙琤琤,天籁自发。因以名吾阁,盖取左思《招隐》语也。”②顾退隐后“颇蓄歌妓,自为度曲”,“所蓄家乐,皆自教之”[8]卷四,他的身后留下了《清音阁传奇》四种。
也许可以这样说,中晚明士人戏剧的兴盛是和官场风气的怠惰相为因果的,在这背后反映着深刻的观念迁换。万历年间,地方官每以“仙令”自诩或相高,屠隆、顾大典还有稍后的袁宏道、汤显祖都在此例。所谓“仙令”,身为令而貌似仙,其实是以自在性情挑战为官准则——尽管不无政治期许,他们却已然难以忍受官员身份的固有束缚。屠隆曾在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里给友人写信抱怨为官之苦:“……独不佞沦于粪壤,即今青阳之月,蓬诟而对囚徒,夭桃刺眼,鸣鸩聒人,坐惜春光,掷于簿领。”[9]人生职责和人生趣味出现分离,这种洒脱而痛切的笔墨是当时流行风调。后来的袁宏道、汤显祖都深受影响,袁氏的《去吴七牍》,汤氏的《牡丹亭》,盖是将此种风调推向极致。至此我们也可以看到阳明心学的作用力。当解放了的性情和体制发生着越来越剧烈的冲撞,其结果就是一部分人从体制中撤离,放逐于任性适情的生涯。
通常认为:明代社会前后之变起于正德,蓄势于嘉靖、隆庆,滔滔汩汩、冲波决堤于万历,而政治危机也于此间逐步加深。当政治上陷入无可为时,强烈的政治热情也就失去了指向,不仅是那些不得志的小官,名官大僚也常常面临退隐的诱惑与选择。
万历十九年(1591),申时行在做了九年的首辅位置上致仕,以57岁年龄回到家乡苏州里居。关于申时行,我们知道汤显祖曾上疏指责他“柔而有欲,又以群私嚣然坏之”[10],但汤氏的政治洁癖是出了名的,大部分人持论未必这样严苛。申能在张居正的巨大阴影下(张居正“威权震主,祸萌骖乘”,明神宗实录)从容斡旋、全身而退,让时人多感钦佩。申曾将自己的身居高位比喻成雪中之竹:“亦知刚易折,无乃重难持。”又云:“岁寒不自保,抗节使人疑。”[11]据说,江南才子钱谦益曾以词林后辈身份到苏州向申请教为官之道,申坦言:“安分身无辱,闲非口莫开”,“温柔终益己,强暴必遭灾”③,钱为之感慨:“太平宰相,风流弘长”[6]544。以常规眼光来衡量,申的政治生涯可谓充满荣耀、极尽圆满:状元及第,宦途通显,位极人臣,泽被后代。而他当年不过是苏州陋巷里的一介贫寒书生。这样的经历简直像戏曲小说中贫士得志的原型,代表了世俗社会的最高理想。他还能求什么?申的聪明在于他守分寸知进退。以57岁的年龄退休,还有时间和精力享受人生,申时行将他的退休生涯称作“赐闲”。
“闲”,这是一个晚明人酷爱的字眼,追摹晋人风范,意味深长而又心照不宣。且看屠隆的“手提着闲中风月,一任他乌兔奔忙”④,汤显祖的“忙处抛人闲处住”⑤,沈璟的“一片闲心休再热”⑥……“闲”,反复强调出一种姿态,一种人生从正统路上游逸开的姿态,一种失意或者不合作的姿态。相比较政坛小人物的牢骚,申时行的“赐闲”来得雍容、淡定、和平,然而就其本质则是相同的,都是人生由传统的事功领域向放浪或隐逸的自我空间的撤退,“忙处”不可为,遂有了“闲处”的刻意经营。
申时行显然是深谙闲中意趣的。现在他不再是那个殚精竭虑的台阁首辅,而是安富尊荣的地方元老。不要忘了他原本是个文人。时人认为他是明代历任首辅中文才最好的一位,是一个典型的苏州人,在词采风流和赋性闲逸方面颇有造诣。申的气度情调常常让人想起唐代的裴、白。申家在苏州的邸宅有八大处,“分金、石、丝、竹、匏、土、革、木。(申)衙前、百花巷各四大宅。”[12]另外,申还买下了一个自宋代传下的旧园,名为乐圃,增建赐闲堂、鉴曲亭、招隐榭诸胜,并赋诗表明心迹:“栖迟旧业理荒芜,徙倚丛篁据槁梧。为圃自安吾技拙,归田早荷圣恩殊。山移小岛成愚谷,水引清流学鉴湖。敢向明时称逸老,北窗高枕一愁无。”[13]乐圃成了申时行最重要的栖身养老之地,他交往王稚登(伯毂)等地方才士,诗酒倡和、游园赏曲主要就在这儿。园名乐圃,邸宅以八音命名,显示出申时行对声伎非同一般的爱好。申自里居以来即广蓄声伎,遍征梨园,财力闲情所致,申家班成为当时苏州最好的家班,潘之恒《鸾啸小品》将其列为苏州“上三班”之首。时人或曰:“余素不耐观剧,然不厌观申氏家剧。”⑦围绕着申衙和申家班的传说不可胜数。申时行的退居生涯长达23年,这位“太平宰相”创造了“富贵风流”的传奇。申氏家班传至三代犹声誉不衰。而申精心营构的乐圃,在清中叶转到了其时状元尚书毕秋帆的名下,身份与趣味的相近让毕不免以前贤自比,然而时过境迁,毕已经没有了申时行那样的时运——这是后话。
申时行的例子表明了从政治脱身出来的士大夫营构自我世界的热情,他的选择代表了万历年间官员的普遍选择。在江南,政治竞逐微妙地转化为风雅上的竞争,构成了士林文化中有趣的一面。万历一朝,由此成为“园林声伎”真正崛起并获大发展的时段。
王锡爵、余有丁与申时行系同科进士(明嘉靖四十一年,即1562年),三人占据了当年科考的前三甲位置,万历朝共事台阁,致仕居家后,又皆优游园林声伎。王锡爵曾在第一时间让家乐搬演了汤显祖的《牡丹亭》,反应之敏捷令汤氏亦感吃惊。里居太仓,王得以延请著名曲师如魏良辅弟子张野塘、赵瞻云教习家乐,凡有客至,这位前相国必“置酒家园相款”并出示家乐演剧。余有丁的退休生涯同样充满闲情逸致:“每四方名士至,辄相延接,与极游湖山佳处,既载肴觞,兼携丝竹……江左风流, 自许谢安、王俭。”[14]卷十八我们从这三位同年同僚的经历中,看到的是风习相袭的力量。
申时行家班中的一位名艺人沈娘娘,后来成了钱岱家乐的教师。钱岱是常熟人,万历初从御史位上疏请终养,过着极尽奢华逸乐的生活:妓妾数百,园林“小辋川”据称耗时20年。“春时小辋川花丛如锦,侍御日偃息其间。令诸妓或打十番,或歌清曲。张素玉中坐司鼓,余女团栾四面,笙歌相间,几于满谷满坑。……秋时或游小辋川,或坐四照轩。遇枫叶,则登挹翠亭,列酒肴,命诸妾或唱《红梨记·花婆》曲一阙。每一阙,则侍者进醇醪一杯。颓然独坐。至暮,则张灯亭上,弦管齐发,和以清讴,都人士女每从城西山上遥望之,以为不减谢安。”[15]钱的豪奢与颓废都令人惊乍,但那却被视为一种对政治的负气:“岱有经世材,而不得施用,故以园林第宅、妙舞娇歌消磨壮心,流连岁月。”⑧显然,这一理由在那个时代是被广泛接受的。
华亭人范允临为其岳父母做的行状颇有特色。范的岳父是官至太仆寺少卿的徐泰时:“公(徐泰时)遂挂冠归里门,归而一切不问户外,益治园圃,亲声伎,里有善累奇石者,公令累为片石云峰。杂莳花竹,以板舆徜徉其中。呼朋啸饮,令童子歌商风应 之曲,其声遏云。……于是益置酒高会,留连池馆,情盘景遽,竟日忘归。……后方曳缟、衣绮、粉白黛黑者动十计。丝竹管弦日日盈耳,而董宜人若弗闻也。”[16]行状而写得如此摇曳生姿,可以想见这对翁婿同调相亲,同时也再次表明:由官场失意而投身园林声伎,是多么合情合理。徐泰时所卜筑之园林,时称东园,即今留园。
多半不无受到乃翁的影响,范允临自己亦是“神仙中人”。许多年以后,遭遇了国破家亡的张岱追忆前朝旧梦,世交前辈范允临和邹迪光的风雅生活宛然在目:“范长白(允临)园在天平山下……开山堂小饮,绮疏藻幕,备极华褥,密阁清讴,丝竹摇飏,忽出层垣,知为女乐。……”[17]卷五“愚公先生(邹迪光)交游遍天下,名公巨卿多就之,歌儿舞女,绮席华宴,诗文字画,无不虚往实归。名士清客至则留,留则款,款则饯,饯则尽。”[17]卷七邹、范两人在万历年间皆享有盛名,殆因他们将园林声伎这种生活方式经营到了极致。邹迪光和范允临直接影响了张岱的祖父张汝霖,后者乃状元张元忭之子,官僚家庭出身,完全能够建立起一样的生活模式。
相似的情景被反复描绘着,我们看到一个巨大的声色场在士大夫的私人空间和社交生活中铺开。这里释放的是恒久存在于传统文人教养体系和精神世界的东西,向来的压抑都像在为今天的潮流蕴蓄充沛力量。然而,制衡的力也是不可忽略的,声色夸炫中总有回避不了的价值追问。张岱在描绘邹迪光“愚公谷”的精美时,忍不住感慨了一句:“故居园者福德与罪孽正等。”[17]卷七“愚公谷”主人、“梨园两部,尤冠绝江南”的邹迪光在看了屠隆的《昙花记》之后竟然奉佛罢戏⑨。而以狂放不受绳检著称的屠隆,实则是矛盾的内心充满戒律的人,他曾经这样评价“小辋川”的主人钱岱:“钱先生园中之室,什不能当右丞(王维)二三。右丞好禅,孤居三十年,而钱先生旁多声伎,此似有不尽同者。然先生潇洒超迈,此中旷然,傥一朝尽斥声伎,而清虚寂寞进于禅喜,遂据大士莲花座,余又何能量达人也。”⑩此话颇能反映屠隆的价值取舍。屠隆何以写出《昙花记》?他要传达这样的体验:“风流得意之事,一过辄生悲凉;清真寂寞之乡,愈久愈增意味。”这是声歌放纵之后的自警——即便逃离了政治的重荷,依然要背负道德的宗教的质询。“闲处”,并没有永远的轻逸。
政治的重荷又岂能轻易逃脱?失控的晚明政局为士的自由提供空间,但问题是:建筑在混乱中的自由能持续多久?风习在继续,如炽如沸,时运却改变了。天启、崇祯,国势江河日下,士大夫已然无法安享申时行式的“太平”,忙与闲的选择将更加艰难,而他们留连于泉石声歌的心灵,将经受来自时代的越来越严峻的考验。
祁彪佳生活在明王朝的最后四十余年,他以末世忠臣的形象彪炳史册,无论在气质还是际遇方面,他都被视作明代的文天祥。同乡张岱为祁彪佳所作《像赞》开头两句:“德裕园亭,文山声伎”,高度隐括了祁氏的身份和情调。祁是儒者,也是文人,在他身上既结合着士阶层的种种特质,也格外清晰地显现出这一群体之政治与文化人格的矛盾纠缠。
以个人的禀赋条件而言,祁彪佳几乎可以拥有最完美的人生。他出生在一个典型的“诗礼簪缨”的封建家族,从小接受严格儒家教育为入仕作准备,20岁即中进士,从此步入仕途。也许是秉承了父亲祁承熯(夷度公)的“持身养性”之学,祁彪佳初入官场即少年老成,气度不凡。据说他出任福建兴化推官时,吏民欺生,故意刁难,然而祁从容应对,树立了权威。此后他的政绩让朝野仰目:“民风利弊,狱情钱谷,无不洞若观火,迎刃而解”(《年谱》)[18]。作为一个认真而出色的官员,祁彪佳颇受崇祯信赖,屡获升迁。不过,也是因为认真的缘故,他对时局有深切洞察,指陈时弊、建言献策更是不计利害,终于,他在担任苏松巡抚时得罪了当时的首辅周延儒,这一次他彻底看清官场黑幕,愤而辞官。如果将祁彪佳43岁的生命以入仕为界分为前后半生,那么,他的后半生恰好一半在官任上,一半退隐在家。祁彪佳的隐居总共有三个时段:1628年——1632年,丁父忧;1635年——1642年,因周延儒事,以奉亲名义辞官里居;1645年,知南明小朝廷事不可为,重回绍兴故里直至殉节。
绍兴自古文物风流,生活在一个文化氛围浓郁的大家庭,祁彪佳自然也习染了那些文化癖性:他好藏书、好园林、好词曲。父亲祁承熯留下的藏书“甲于大江以南”,以好学著称的钱谦益也曾屡次去信向祁彪佳借书。祁自幼读书于家园密园,经常游览兰亭等家乡名胜,染上“泉石之癖”。至于戏曲,明末的越中乃吴中之外又一戏剧中心,祁氏兄弟及与他们过从甚密的张岱兄弟无一不是戏迷,祁彪佳本人屡称“素有顾误之癖”,还乡守丧那年亦“多为音律所误”,可见此中爱好已深深植入性情。事实上,祁的文人天性并未为其严肃官员的面目遮盖:他为京官时即经常观剧,而且四处收购词曲剧本。作为一个文才出众的人,他欣赏词采风流的戏曲家袁于令,并对沈璟家族的戏曲造诣深感兴趣。祁彪佳完全可以为自己营建起一种精致的退休生活,情况也的确如此。还乡不久祁彪佳即致力修筑寓山别业,这一工程因为他超乎寻常的爱好而旷日持久,了无穷期。此外读书问道之余,他将大量时间用于和从兄弟及张岱等家乡友人往来,在彼此的家园中游赏、饮酒和观剧:“光中上人遣其徒至……举酌演戏及暮与之游寓园更游密园乃别。”(《山居拙录》8、11条)[18]“于四负堂观《千金记》,已,小坐浮景台,观花火,主客之情甚畅,子夜送之。”(《山居拙录》9、18条)[18],“邀张宗子、介子至,平子后至。举五簋之酌已,与同游彤山,再至寓山,燃灯月下,月色甚皎,小酌于妙赏亭,听介子所携优人鼓吹,又登远阁望月。”(《自鉴录》8、14条)[18]除了这种典型的士大夫式的文酒过从,祁彪佳还经常在家园中奉母观剧。他的居家生活另一位重要伴侣是妻子商景兰。商出身名门(尚书商周祚之女),文学素养极高,“祁商作配,乡里有金童玉女之目。伉俪相重,未尝有妾媵也。”(《年谱》)[18]祁常携商景兰登临寓山,或泛舟旅行,所到之处亦少不了赏曲观剧。
我们可以说祁彪佳的私生活领域一切都优裕、美满、和谐,然而,他的退休生涯却一开始就潜藏了不安与危机。不要忘记祁的致仕始于1635年——距明亡仅有十年,也不可忽略他此时才33岁,正值年富力强之际。无论是园林声伎还是禅宗性理都无法消解祁彪佳的郁闷与苦痛,在表面的闲逸生活下,他心灵深处的自我拷问无有宁时。寓山别业的重要建筑“四负堂”,即名自“负于君、亲、己、友”之意。《归南快录引》:“予谫陋甚,无用世才。……复自念予之所以切于求归者,夫岂真能超然自得,可以芥视轩冕乎?”[19]275《居林适笔引》:“乃若营精藻翰,溺志歌舞,有意以为之者,皆苦因也。”[19]276《辛未春日悔语》:“祁子拂几静坐,俯而思,茫然若有所思,戚戚然若无以自容。作而言曰:‘日月逝矣,人寿难期。性有同然,谁甘中诿?’”[19]314《弃录》小引:“予至乙亥归,至此已五载,不为不久,杜门不预户外事,不为不暇。以此易逝之光阴,正当为有用之学问,乃碌碌土木,迄无已时。……五载杜门,吾欲举一事之有益于身心者不可得,岂不愧哉?予之愧多矣。所贵乎愧者,以其能悔也;所贵乎悔者,以其能改也。愧而不悔,悔而不改,直为自弃而已矣。”《小捄录》:“光阴如驹过隙,于今岁尤见之,而季冬一月愁肠苦趣,日如处漏舟,如在焦釜,不堪为人言也。”(12、29条)[18]欲有所为而不知何所为,欲有所为而知其不可为,时光匆促,人生有限,念之则动魄惊心啊。
无疑,祁彪佳是深于自省的,以上文字也映照着《宜焚全稿》中那个殚精竭虑、焦心如焚的政治家面貌。生活在王朝末年的祁彪佳始终没有、也几无可能从“忙处”脱身。一方面是不能泯灭的救世心:保持与北方的频繁通信,忙于地方公益事业, “立赈灾法,……活饥民无数”(《祁公世培传》)[18];另一方面,我们有理由认为,当政治无可为之际,祁彪佳试图于文化建构中实现另一种价值。正是在退休生涯中,他撰写了《越中园林志》和《寓山注》,二者不仅具有园林学价值,亦且是明末散文精品。从《寓山注》中常可读出作者心绪:“自有天地,便有兹山,今日以前,原是培嵝寸土,安能保今日以后,列阁层轩,长峙乎岩壑哉?成毁之数,天地不免。”那是对兴亡的宿命感悟,是挥之不去的清醒与悲哀。对戏曲,祁彪佳逐渐由单纯的“顾误之癖”转而到寄予社会功用的期望。巡抚苏松时,他就曾折节拜访冯梦龙,嘱他编辑曲坛领袖沈璟及子侄的传奇;还乡伊始的1635年秋,他自己着手类似的工作:“坐书室竟日不出户,整向日所蓄词曲,汇而成帙。”(《归南快录》11、4条)[18]大约在1637年,他完成了传奇《全节记》的写作,这部以苏武为主人公的剧作似可看作祁彪佳的政治预言与遗言,祁彪佳在序中写道:“子卿奇迹,《史》、《汉》业有全传矣。文人学士,无不扼腕而想见其人。然妇竖不识也。于是谱之声歌,借优孟衣冠,以开子卿之生面。……试一演之,穷愁萧瑟之景,与慷慨激烈之慨,历历如睹。令观者若置身其间,为之歌哭凭吊,不能自己。今而后不特图书记籍有子卿,即村落市廛妇竖之胸中,亦有子卿矣。”字里行间,透露出祁彪佳此际已由事功的期许转为精神上的自救与救世。完稿于1640年的戏曲文学评论集《远山堂曲品、剧品》亦体现了相同意旨:两书重视作品思想内蕴的品鉴、重视著录时事剧,《曲品》著录时事剧竟达40多种。不过,祁彪佳显然不是冬烘先生,他看不上那些空洞说教而“气格未高”的作品,比如评说《忠孝记》:“段段衬贴忠、孝二字,所以绝无生趣。”[20]《远山堂曲品、剧品》既表现出祁彪佳的艺术眼光,又从另一向度昭示了他的政治阅历和人生思考。
1642年,祁彪佳于王朝危难中被再度起用,“知不可为而为之”,在政治生涯中写下最后悲壮一笔。1645年6月,拒绝了清廷的利诱收买,祁彪佳自沉于寓山园池,绝笔诗云:“图功为其难,殉节为其易。我为其易者,聊尽洁身志。”(《年谱》)[18]祁彪佳的清醒和理性始终超出同时代的大多数人,因此他也必然承受比一般人更为沉重的道德和心理负荷。这是他日记中关于戏曲的最后一条记录:“薄暮抵寓山,知止祥兄已从南都避难归,亟至旧宅看之。止祥兄尚有歌者携归,时文载弟留酌,遂欲演戏,予力阻而罢。”(《乙酉日历》6、1条)[18]穷途末路之际,而士夫的癖性殊难自解,的确是可慨可叹的。祁彪佳在殉节前还再度检点自己的“泉石之癖”:“至寓山,登四负堂,顾谓公子曰:而翁无大失德,唯耽泉石,多营土木耳。昔文信国临终贻书其弟,瞩以所居文山为寺。吾欲效之,汝当成吾志。”(《年谱》)[18]祁之自沉于自己精心营构的园池,看起来像一个时代的隐喻。在祁彪佳殉节之后,从兄祁止祥罢戏奉佛,一代名士张岱“披发入山”,遵祁遗嘱修《石匮书》,并写下那些风情卓绝而又伤世自伤的小品。
祁彪佳代表了正统士大夫对“园林声伎”之癖的自我审视。这样的自审并不罕乏,然而它不足以改变肆荡的时代风习。明末政坛党争激烈,士大夫各守政治立场与社群关系,唯园林声伎的癖好并无二致。而党争所导致的政局变幻和士之朝野身份变更,使“忙”与“闲”的转换更为频繁,园林声伎故而既是“闲”的标志,也常常成为“忙”的遮掩。
阮大铖以奸邪狡猾著称于明末政坛,而其文艺才华也盛称一时。崇祯年间,阮大铖因名列“阉党”而废弃家居(安徽怀宁),后又为避兵乱寓居南京。在时为南方政治中心的南京,这位不折不挠的政治钻营者再度燃起竞进之心。他构石巢园,置办家乐,打扮出流行的隐逸面貌,藉以亲近虽以清流自居,其实亦多“名士风流”的东林、复社。阮常作出优游园林的恬退姿态:“岁月遂得林壑有,云山安得是非存?”他为计成《园冶》写叙也不忘自我表白:“余少负向禽志,苦为小草所绁。幸见放,谓此志可遂。”(11)这种言不由衷的表白当然并不让人信服。阮还惯用声伎收买人心。他在戏曲方面堪称全才,亲授家优以自己所编的《石巢四种曲》,水平之高连见惯了世面的张岱都连呼出色,当时号称“金陵歌舞诸部甲天下,而怀宁歌者为冠”(12)。冒襄等复社名士曾以“白金一斤”聘阮氏家乐演《燕子笺》,不过,戏虽然看了,阮的拉拢企图却再次落空。这一事件传为笑谈,且长存于复社诸人的记忆中:
诸先生闻歌者名,漫召之,而怀宁者素为诸先生诟厉也。日夜欲自赎深念,固怀未有路耳。则亟命歌者来,而令其老奴亦来,是日演怀宁所撰燕子笺。而诸先生固醉,醉而且骂且称善。怀宁闻之殊恨(13)。
大约阮大铖的人品实在低劣,所以机心易被识破。不过在那个声色沉酣的时代,阮引以自恃的戏曲才华最后还是在他的竞进之路上派了用场。结通马士英,骗得弘光朝福王的信任(阮以吴绫写《燕子笺》等剧呈送皇宫,福王大悦,后封阮为兵部侍郎),戏曲都有润滑之功。至于迎降清军,为清军唱曲佐酒,则更是政治小丑的作为了。然而,明末人不管怎么不齿于阮氏为人,对他的戏曲造诣却都交口称道,格调不高而技巧精熟的《石巢园四种曲》流行一时,“梨园子弟争演唱之”[21]。清孔尚任在历史剧《桃花扇》中塑造阮大铖其人,园林声伎亦为重要底色:
(末巾服扮杨文总上)……今日无事,来听他(指阮大铖)《燕子》新词,不免竟入。(进介)这是石巢园。你看山石花木,位置不俗,一定是华亭张南垣的手笔了。(指介)【风入松】花林疏落石斑斓,收入倪黄画眼。(仰看读介)咏怀堂,孟津王铎书。(赞介)写的有力量。(下看介)一片红毹铺地,此乃顾曲之所。草堂图里乌巾岸,好指点银筝红板。(指介)那边是百花深处了。为甚的萧条闭关,敢是新词改,旧稿删[22]?
且看孔尚任并不用漫画手法写阮大铖的出场,却用了几分力气去铺叙那园林声伎中的文人意趣,而且流露出欣赏口吻。这是颇耐人寻味的。又清代的全祖望某日游园,忽然想起这园林就是当年阮大铖住过的,遂发感慨:“尚有怀宁墨,能污贞士魂。”诗后附注:“阮尚书大铖与文舍人启美尝偕寓兹园倡和。阮文臭味不同,而以丝竹之好相连缀。”[23]全氏的这一发现很能给我们启示:忠奸殊异如文震亨与阮大铖,于“闲处”的情调却如此接近。——文化癖性与政治品格乃至人格操守似乎并无太大关系。
但士之文化癖性的形成却联系着政治动因。正是在政治的缝隙中,一个朝向着独立的文化空间迅速伸展,政治的缺陷成全了文化的建构。“园林声伎”既为时代的潮流,也为时代的病症。
收稿日期:2007-09-10
注释:
①乾隆《震泽县志》小传。
②见《谐赏园记》,《震泽县志》卷三十六。
③《申氏世谱·百字铭》,引自吴仁安《明清江南望族与社会经济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第12页。
④《乌栾》《娑罗馆逸稿》卷一。
⑤《牡丹亭》开场《蝶恋花》。
⑥《红蕖记》开场。
⑦郑桐庵《周铁墩传》,见褚人获《坚觚十集》卷一。
⑧《海虞别乘》卷二《邑人》“钱岱”。
⑨见邹迪光《余阅搬演〈昙花〉传奇而有悟,立散两部梨园,将于空门置力焉,示曲师朱轮六首》组诗,见《调象庵稿》卷二十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159册,齐鲁书社,1997。
⑩《康熙常熟县志》卷十四《园林》“小辋川”条辑录屠隆《小辋川记》,康熙二十六年刻本。
(11)见《园冶图说》,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第13页。
(12)见陈维崧《奉贺冒巢民老伯暨伯母苏孺人五十双寿序》,《同人集》卷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385,齐鲁书社,1997。
(13)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