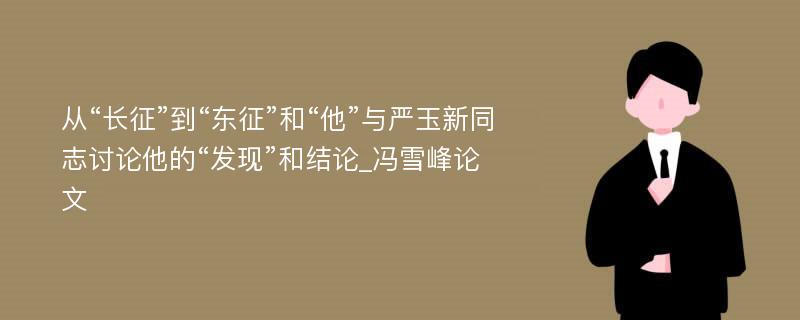
从“长征”贺“电”到“东征”贺“信”——与阎愈新同志商榷其“发现”与论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论断论文,同志论文,发现论文,阎愈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延续,中国现代文学史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史料的发现、考证与判断工作,已与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史料的同一工作,具有相近的意义与难度。六十多年前鲁迅与茅盾联名致电中共中央祝贺长征胜利这一壮举,由于留下的史料不详,电文没有原始资料因而至今众说纷纭一事,足以说明这个问题。1986年阎愈新同志发表《鲁迅致红军贺信的新发现》〔1〕后,1996年又发表了《60年前鲁迅、 茅盾致红军贺信之发现》〔2〕。两次都由新华社、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及许多地方的多家新闻媒体、许多学术刊物与小报当作大事“炒”得沸沸扬扬;似乎几十年前的这桩公案已一举判明。全不顾两度“炒作”的《新发现》与《之发现》其内容前后矛盾(前文认定的两段信文被后文“发现”的全信否定了一半);两文所作的“结论”许多又是“妄断”。去年“炒作”的声势远大于十年前。一致认定:至此已经了结了这个公案。对此,著名鲁迅研究专家朱正摇着头对我说:“起码我写文章是不会引用和确认的。”我认同朱正这种严肃的态度。盖因《新发现》、《之发现》均存在很多疑点。
建国后最早披露且多次谈到鲁迅、茅盾的“长征贺电”的人,是与鲁迅、茅盾交谊最深、合作时间较久,且与此贺电有直接关系的冯雪峰。1951年他在《党给鲁迅以力量》〔3 〕一文中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鲁迅“和茅盾先生共同转转折折地送去过一个给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庆贺长征胜利的电报”。1952年他又在《回忆鲁迅》一书〔4〕 中说明:1936年4月上旬他从山西前线调瓦窑堡接受党中央特派员任务后, 在他4月20日左右启程赴上海“动身的前几天”,鲁迅、茅盾的电报“才 转到瓦窑堡”。1974年9月2日他回答上海纪念馆来访的同志时又说:“1936年4月,党中央在陕北也是收到”鲁迅、 茅盾的贺电“才派我去上海,去找他们”。〔5〕“文革”当中他在《有关1936 年周扬等人的行动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经过》中,详细介绍了临行前洛甫(即张闻天,遵义会议上决定由他取代博古,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在中央负总责)向他交待的四项任务中,第三项是“了解和寻觅上海地下党”。他特别强调:“务必先找鲁迅、茅盾等,了解一些情况后,再找党员和地下组织。”〔6〕 冯雪峰的上述诸说法纵跨二十多个年头,但说法完全一致。主要当事人除鲁迅已经逝世,其余当事人如茅盾、史沫特莱、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及阎愈新据其文章写“新发现”的杨尚昆等当时都健在。他们从未对冯雪峰的说法提出任何异议。茅盾还在多处谈话中对冯雪峰的说法予以证实。
当时史学界、文学界通常确认的贺电文字,只有由16个字两个标点组成的一句话:“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此话最权威的引用者,是冯雪峰领导的曾出版十卷本《鲁迅全集》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他们把此话作《鲁迅书信集》的卷首语:标题是《致中共中央》。该书注曰:“此件为鲁迅获悉中国工农红军经过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发的贺电,是通过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发出的。时间大约在1935年11月间。电文据1947年7月27 日《新华日报》(太行版)载《从红军到人民解放军——英勇斗争二十年》所引抄存”。上述许多健在的当事人对此注也从未否定过。
最早说这句话不是出自“长征贺电”,而是出自“东”征贺“信”者,是樊宇。他在1956年10月15日《文艺报·鲁迅纪念专号》第22页一篇补白文章中说:他的“旧日记”中有抄自“1947.7.27 新华日报载”的一段话:“红军东渡黄河,抗日讨逆,……鲁迅先生曾写信庆贺红军,说‘在你们的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此话与《鲁迅书信集》所引,多一个“的”字;但出处及日期是相同的。《新华日报》(太行版)所据为何?阎愈新说他1984年8 月曾在太原访过该报当时的“社长史纪言和有关人员,都说不清楚”这句话的来历。而编发此消息的“樊显正已于1975年去世”。无从查询了。关于与此话一句不差的文字的来历,包括从事查找工作几十年的阎愈新同志在内,迄今尚无人找到原始出处。因此只能存疑并继续查找。但由于主要当事人早已确认了此话真实可靠,在没有充分证据前,是不能随意否认或推翻的。考虑到战争时期当时陕北与太行之间通讯不便,该消息把“长征”说成“东征”所据确否,同样地尚待查证,决不能说这就是定论。后来学界仍称“长征贺电”,也是有道理的审慎态度。
事情到了1979年出现了突破,著名的史料专家唐天然在6月9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新发现的鲁迅佚文》并附印了他的根据:1936年10月28日延安《红色中华》报第3版追悼鲁迅的纪念专版的照片。 该版(油印)以《鲁迅先生的话》为题刊用两段鲁迅语录的第二段注明出处为“摘鲁迅来信”。其话是:“英勇的红军将领和士兵们,你们的勇敢的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国民众期待你们更大的胜利,全国民众正在努力奋斗,为你们的后盾,为你们的声援!你们的每一步前进,将遇到极热烈的欢迎与拥护。”唐天然的学术态度十分严谨,他断定“贺信全文较长”。这段话是“长征贺电”文字中的一段,而《新华日报》太行版所摘的那句名言是另外段落中的一句。“所以互不衔接”。但他并未对祝贺“长征”一事提出置疑。对于是“来信”还是“来电”他主张姑且“存疑”。虽然唐天然同志作出的是重大发现,但他并未大事张扬,更未进行“炒”作。至于这一“发现”是否确证,尚待进一步考证查实。
阎愈新同志1984年赴山西查《新华日报》太行版《新华日报》引文来源时,发现了1936年9月15 日《火花》(油印版中共河北省委编)载杨尚昆1936年7月24日写的《前进! 向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前进——纪念1936年的“八一”》。此文谈“东征胜利”的社会反响时说:“朋友们赞扬我们,期望着我们更大的胜利。”接着引用了唐天然所发现的那段文字。文章在指出“这是我们的战友们对我们的赞扬,是全国一切不愿意做亡国奴的人们对我们的希望”之后,杨尚昆“又引用下列一段话”:“对于你们,我们那英勇的伟大的民族解放的先锋队,我们是抱着那样深刻的敬仰,那样热烈的爱护,那样深挚的期望,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的光荣和幸福的未来。只要想到你们在中国那样无比的白色恐怖进攻下,英勇的,顽强的,浴血苦斗的百折不回的精神,就是半身不遂的人也会站起来笑!”阎愈新就据此写了《鲁迅致红军贺信的新发现》一文,先后在《鲁迅研究月刊》和《解放军报》发表。此文经过前面提到的“炒作”,引发了第一次“轰动”。
但是阎愈新同志的结论下得太早了。他一方面承认:“杨尚昆文章中没有说明来历。”但没从杨尚昆同志那里取得根究问底的直接证明,仅凭“第一段引文《红色中华》1936年10月28日刊出时,已注明‘摘鲁迅来信’”这一孤证,就认定关于出处这一说明真确无疑。他又判定“第二段引文中‘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的光荣和幸福的未来’一句,与太行版《新华日报》所引,意思完全相同。只是文字小有出入。”于是就武断地下了结论:“这两段引文,已是鲁迅贺信中的主要内容。”这结论显然下得太轻率了!第一,这两句话有明显差异:后句少了个“,”号,与“光荣和幸福”这个词组;还多出“中国”这个关键词;“‘将’来”与“‘未’来”又有一字之差。再粗心的编辑,面对如此重大的电文,也不致出这么多差错。第二,两句话的“意思”并不“完全相同”。这一点阎愈新不至于看不出来。因此他根据这段文字包括了这句与一向被认定是鲁迅、茅盾“长征贺电”电文相近的话,就认定全段文字是鲁迅、茅盾之笔。是否有些武断?事情非常明显:文字有别,意思有别,两句话虽颇近似,也完全可能出自不同人的手笔。古今中外,这类先例比比皆是。以此不可靠的论据判定全段文字出于鲁迅、茅盾长征电文,真是有点悬乎!
所幸阎愈新同志具有锲而不舍精神。10年之后,他在《之发现》一文中,否定了他的《新发现》中对这段话的误认,他说:“现在证实,这句话并非鲁迅、茅盾信中语,而最早的出处是《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来信》中”语。“两者文字小有出入,是由于辗转抄引之误”。阎愈新的自我纠正是必要的。但他又犯了轻于下结论的老病:“这句话”应该改作这“段”话;他作的“辗转抄引之误”的结论,并无真凭实据。但他轻而易举地用了这么6个字, 既给“辗转抄引”者加上失“误”的过失;又排除了这两句并不完全相同的话出于两个不同人之笔的这种可能性。当然阎愈新取消了10年前他曾把这段话的版权授予鲁迅、茅盾的老“决定”,是因为他又有了“新发现”。
1995年8月2日阎愈新在1936年4月17 日中共西北中央局机关报《斗争》(油印)95期上发现封面列有:“4, 中国文化界领袖××××来信”〔7〕。全文如下:
读了中国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中国共产党《告全国民众各党派及一切军队宣言》、中国红军为抗日救国的快邮代电,我们郑重宣言:我们热烈地拥护中共、中苏的号召,我们认为只有实现中共、中苏的抗日救国大计,中华民族方能解放自由!
最近红军在山西的胜利已经证明了卖国军下的士兵是拥护中共、中苏此项政策的。最近,北平、上海、汉口、广州的民众,在军阀铁蹄下再接再厉发动反日反法西斯的伟大运动,证明全国的民众又是如何热烈地拥护中共、中苏的救国大计!
英勇的红军将领们和士兵们!你们的勇敢的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国民众期待你们的更大胜利。全国民众正在努力奋斗,为你们的后盾,为你们的声援!你们的每一步前进将遇到热烈的拥护和欢迎!
全国同胞和全国军队抗日救国大团结万岁!
中华苏维埃政府万岁!
中国红军万岁!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 ××
一九三六、三、廿九
于是阎愈新排除了杨尚昆文章中的第二段引文是鲁迅、茅盾所为;根据是认定他“新发现”的这封信是鲁迅、茅盾所为,但其中没有这第二段引文。这样他就轻而易举地推翻了他10年前如获至宝、认定杨尚昆那两段引文都是鲁迅、茅盾“东征贺信”中语且是“主要内容”的“重大发现”。当年的认定固然轻率,而今的否定依旧轻而易举。阎教授的锲而不舍精神和他下结论时的轻率态度,形成巨大反差。
遗憾的是这个老毛病在他认定此信系鲁迅、茅盾手笔这一“结论”中再次复发。因为他说这封信是鲁迅、茅盾所为,比他批评唐天然同志那篇文章所下的“根据不足”的结论更加“根据不足”!
阎愈新的新结论根据有二:其一就是此信的第二个自然段曾被前面提到的最早由唐天然所发现的1936年10月28日《红色中华》所引鲁迅语录第2段所注的出处是“摘鲁迅来信”。 这时阎愈新不再说唐天然“根据不足”了。但是他又忽略了一个重大事实:他发现的这封完整的信署名为“×× ××”两个人;而非“鲁迅来信”中之“鲁迅”一个人。由此可见《红色中华》的“摘”引者态度是否严谨,大可置疑。其二,阎愈新还根据“1936年5月20日,林育英(即张浩, 当时一度被视为共产国际代表)、洛甫(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领导人联名发给正在长征途中的二、四方面军领导人”的内部长电中,郑重谈到鲁迅、茅盾等的来信:“红军的东征,引起了华北、华中民众的狂热赞助,上海许多抗日团体及鲁迅、茅盾、宋庆龄、覃振等均有信来,表示拥护党与苏维埃中央的主张。”就断定这里所说“鲁迅茅盾等的来信”就是他新发现的这封完整的信。那“×× ××”四字就是鲁迅茅盾。〔8〕至于为什么以“×”代名, 阎愈新的解释是“因当时鲁迅、茅盾居住在国民党统治区上海”。他又认为《红色中华》只注明“摘鲁迅来信”,而未注明茅盾,“同样出于茅盾尚在上海之故。”这就十分奇怪了:难道《红色中华》编者隐去茅盾姓名是因为“茅盾尚在上海”却注出鲁迅姓名,是认为鲁迅“不在”上海吗?
他的第一个根据,是个孤证,且多可置疑处,上文我已经说过了。限于篇幅,不再重复。关于第二个根据,阎愈新并未提供原文。他文章中的引文,是转引自程中原1986年12月15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关于鲁迅来信的一封内部长电》一文。但阎愈新只引了“长电”的下半,而略去其前还有一句“党的12月政治决议及七次政治宣言……均得到全国广大人民包括知识界最大多数人的同情和拥护”这上一半十分重要的话。和阎愈新同志一样,我也没见到“长电”全文,只读了程中原的大作。但这不妨碍我们看透阎愈新删去“长电”前一句话的明显意图:他之所以抽掉“长电”叙述包括鲁迅、茅盾在内举国上下对“党的12月政治决议及七次政治宣言”所代表的“党与苏维埃中央的主张”“表示拥护”的“宏”观内容与“泛指”内涵,是想把“主旨”定位在针对“东征”表示祝贺的“微”观内容与“特指”内容上;从而否认鲁迅、茅盾另有“长征贺电”;从而证明:长期以来,包括当事人茅盾与主要知情人冯雪峰所说的“长征贺电”,是因“记忆有误”,把“东征贺信”“指鹿为马”了!
但是,阎愈新在《之发现》中抄示的他新发现的这封信,隐去了署名,代之以“××××”,这四个“×”到底是何人?能否据《红色中华》所谓“摘鲁迅来信”和“文化界领袖”(当时被称作文化界领袖者多矣!鲁迅只是其中的一人。而茅盾当时尚未能忝列其中,只是被视为左翼文坛领导人之一),就轻率地判定为鲁迅、茅盾?这四个“×”在阎愈新《之发现》一文所附《斗争》95期封面的“图示”上是“××××”,而不是阎愈新文章抄录时所示的“×× ××”。即便正文确是“×× ××”,是否被隐去姓名的两个人的姓名就一定都是两字组成者?在这里姑且存疑。单就他删去的“长电”前一句话及他所根据的程中原文,就有不少可置疑处。
从程中原《关于鲁迅来信的一封长电》一文可知,他是读了阎愈新第一篇文章即《新发现》后,对阎愈新判定的杨尚昆文章两段引文都是鲁迅“来信”的结论信以为真之后,才发现中央致二、四方面军这封长电的。他的文章并未全文抄录这长电,只是摘“其中”“论国内外政治形势”的一段。据程中原同志判断:“鲁迅来信的主旨”“是在拥护党的主张”。这判断是正确的,但他可能是受阎愈新《新发现》的影响,也认为“鲁迅这封来信是他得知红军渡过黄河进行东征之后写的,并不是获悉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所写的”;借用阎愈新批评唐天然的话说:这判断也是“根据不足”!证据不用另找,就在程中原所引“长电”这一段文中。此段先论“党的12月政治决议及七次政治宣言……均得到全国广大人民包括知识界最大多数人的同情和拥护”。这是讲“大”的“形势”。下边才谈到“红军的东征引起华北、华中民众的狂热赞助”这个“小”“形势”。这“大”“小”两者,是这段电文提出的论点。然后例举了“上海许多抗日团体及鲁迅、茅盾、宋庆龄、覃振等均有信来,表示拥护党与苏维埃中央的主张。”这里的着重号是我加的。因为这句话明明白白说清了所谓“鲁迅来信”的主旨具有针对大形势致贺拥护的宏观性、泛指性内容(表示拥护党的主张);而不一定能证明阎愈新、程中原所认定的仅仅针对“东征胜利”这微观性、特指性内容(祝贺“东征”胜利)。“长电”的例证除鲁迅等的来信外,还例举了李济深、冯玉祥等“南京政府内部”等“联共反日”派、上海“三十余种”进步刊物、马相伯、何香凝等上海示威游行领袖、“赞助反日运动”的“许多外国记者”以及“从蓝衣社、国民党起至国家主义派止,全国几十个政治派别”等等政治性质并不相同的六个方面的例子,意在说清“所有这一切都证明”:“党的12月政治决议及七次政治宣言……均得到全国人民包括知识界最大多数人的同情和拥护”,“我党与各党各派的统一战线正在积极组织中”。从这个宏观性、泛指性“主旨”来看,鲁迅、茅盾的“长征贺电”当然要被例举出来作为首要的证据。怎么能把鲁迅、茅盾此举硬性限定在“长电”谈“小形势”的电文中微观性、特指性的“东征”一举之中?因此,阎愈新的两个根据,起码第二条很难成立。从这个情况看来,阎愈新和程中原两同志好像是在相互贻误!
即便抛开这一切不谈,单就阎愈新《之发现》提供的用黑体字印出的题为《中国文化界领袖×× ××来信》本身作鉴别,就有很多令人置疑之处。第一当然仍是《红色中华》所谓“摘鲁迅来信”,与阎愈新发现的此信文末署名为两人并不符合,即便符合,也仅仅是个孤证。考虑到战争年代油印刊物所处的种种条件,仅凭陕北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引的一条语录就要坐实中共西北中央局机关报《斗争》发表的这封隐名方式的“来信”中这“××××”一定是鲁迅茅盾,显然又应了阎愈新批评唐天然的那句话:“根据不足!”
第二,这封“来信”没有抬头。从引文中看,第二段直呼“英勇的红军将领们和士兵们!”这口气不像是致中共中央或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的。而当事人茅盾、主要知情人冯雪峰都说是向中共中央电贺长征、而非电贺“将领们”与“士兵们”!
第三,正如赞成阎愈新的观点、发现并亲自编发了阎愈新的《之发现》一文的《新文学史料》资深编辑张小鼎所说:“贺信的用语措词、文笔风格似又与鲁迅极富个性的独特文风相去甚远。那么是否有可能是经鲁迅同意,委托别人代笔起草尔后发出?”〔9 〕至今又未有任何蛛丝蚂迹可寻!鲁迅的文章由人代笔的只有临终前他病中实在不能执笔,才由他口授、请冯雪峰记录或代笔,再由他亲自修改定稿的《答徐懋庸》等极少的几篇。而电贺长征或东征时,鲁迅正健笔如椽。这么重要的政治电文怎会劳人代笔?鲁迅愈到晚年,文风特征愈鲜明突出。此信风格与鲁迅文风毫无共同之处。尤其文末的“四呼”“万岁”,在鲁迅一生,从无先例!说是鲁迅之笔,实在透着冒失!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此信中包含的中共与红军的信息量大得惊人。仅中共中央文件就提到三份,对红军东征的山西战况也了若指掌!鲁迅对这些文件与消息到底从何处得知?当时不仅鲁迅,就是整个上海地下党和文艺界地下党组织,都和远在陕北的中共中央失掉了联系,不是别人,而是冯雪峰被指派为中共中央特派员赴上海,冯雪峰说:是因为当时中央刚收到鲁迅、茅盾的长征贺电,而冯雪峰和鲁迅、茅盾关系密切,因此是最佳人选。冯雪峰写道:“中央给的任务是四个:1, 在上海设法建立一个电台,把所得到的情报较快地报告中央。2, 同上海各界救亡运动的领袖沈钧儒等取得联系。向他们传达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同他们建立联系。3, 了解和寻觅上海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替中央将另派到上海去做党组织工作的同志先做一些准备。4,对文艺界工作也附带管一管, 首先是传达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四个任务中,当时中央指示说,前两个是主要的。我记得第一个任务是周总理亲自交给我的,并交给了我密码,”“第二个及第三、四个任务是洛甫(张闻天)〔10〕交给我的。行前,洛甫曾几次嘱咐我说:到上海后,务必先找鲁迅、茅盾等,了解一些情况后,再找党员和地下组织。派你去上海,就因为同鲁迅等熟悉。”〔11〕这段话证明冯雪峰几十年后回忆往事如此细致具体,这起码说明了两点:一是冯雪峰具有相当可靠的记忆力,对他动身前鲁迅茅盾的“长征贺电”才到陕北,并导致派他以特派员身份赴上海这样的大事,决不致像阎愈新所推测的那样,会把“东征贺信”读记成“长征贺电”。二,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知道与中央失去联系的上海地下党和党外进步人士,对党中央的新方针新政策不甚了了,因此才把“传达”的任务放在“主要”位置。夏衍就说过:直到他们根据肖三从莫斯科来信决定解散左联,根据从一家外国书店买到的一份第三国际机关报《国际通讯》(英文版)读到共产国际七次代表大会上季米特洛夫、王明的报告才提出了“国防文学”口号的“1935、1936年,我们这些和党中央失去了联系的人,根本不知道遵义会议对王明、博古的批评,更没有可能知道王明所犯的路线错误”〔12〕。鲁迅茅盾怎么可能像阎愈新认定的这封信中所表现的这样,不仅对遵义会议上改组后的中共中央及其颁发的许多中央文件,还对东征的情况如此迅速及时地了若指掌?阎愈新列举《红色中华》及上海报纸报道“东征”的材料是想证明鲁迅等了解情况。《红色中华》鲁迅看不到因此没有证明作用。上海各报的报导,其政治倾向多是支持中央军与阎锡山部如何“援晋”“迎剿”红军。鲁迅、茅盾固然常从报刊字缝中看我方动态,但仅凭这些,就驰书中共中央遥致祝贺,对这种政治大事正式表态,鲁迅、茅盾岂是这种“听见风就是雨”的冒失莽撞、轻举妄动之人?
第五,红军东征始于1936年2月20日,终于5月5日。 阎愈新发现的此信尾注明此信写于同年3月29日。那时东征还远未结束, 而红军长征早已到陕北,信息传到上海却要滞后很久。雪峰离开陕北赴上海是4 月20日。支持阎愈新的观点并编发此稿的张小鼎是位细心人。他在上述文章中问道:“贺信是怎么传递到陕北的?”“过去有一种流行说法是为了避检查,由史沫特莱设法通过巴黎《救国时报》辗转寄给陕北。现从时间上看,从写信到刊出文字,前后仅半月,似不太可能,倒是直接由秘密渠道带陕北可能性更大”。小鼎所说的“仅半月”,还得扣除从收到“信”(电?)到决定刊出的上上下下决策公布与编发等时间,实则途中只有10天挂零。如果在今天的信息时代,是足够了。然而细心如小鼎,也有“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的时候:他忽略了当时上海地下党与陕北中共中央失去联系,党和鲁迅都无此可传递信息的“秘密渠道”。这渠道是派冯雪峰去建立的。因此不能排除史沫特莱提供长征到达陕北,建议鲁迅、茅盾致电祝贺,并由她设法由巴黎转寄陕北的“流行说法”。即便当时存在上海陕北间的“秘密渠道”,要穿过蒋敌伪多重严密封锁区,即便乘“专车”。十天时间能从上海送到陕北吗?
第六,此信长达四百余字。作为与鲁迅联名致电中央的茅盾,居然直到逝世,从未见到全文!鲁迅对茅盾一向尊重。连自己署名写的文章还常与茅盾通气或出示茅盾共同商量。两人议定了向中共中央联名致信及其内容,写成后居然不给茅盾过目,就贸然发出,这像是鲁迅办事的方式吗?过去说电文只是“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16个字两个标点,因为事前已经商定内容,不请茅盾过目就请史沫特莱代为发出,这说法尚属可信。若说这四百余字的长信,不经茅盾过目竟然发出,说这是鲁迅所为,这信又是鲁迅和茅盾联名致中共中央的重要表态;此说是否真实可信?纵观鲁迅一生,从未如此行事!
阎愈新在《之发现》长文开端,有个“作茧自缚”之举:他详列了茅盾四次谈及他从未见过电文,更未参与起草的具体说法。1996年7 月在纪念茅盾诞生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他提交了《之发现》作为会议论文,并在大会发言时择要宣读。然后在回答提问时,他试图从自作的“茧”的束缚中解脱自己。他的说法是:茅盾这未见电文未参与起草的多次解释,是“出于谦虚”。我当场即席发言,要求在座的知情人就“出于谦虚”说即席评议。茅盾的儿子韦韬当即发言不同意这种解释。他证明:茅盾生前否认看过电文和曾参与起草这信,不仅见诸文章和答问,对他本人及其家人也一再说过。在场的茅盾的儿媳陈小曼证实韦韬的话。因为她也多次听公公当面如此说过。张小鼎也发言,否定阎愈新的“出于谦虚”说。他说:因为他是1975年4月26 日在北京鲁迅博物馆举行的座谈会上亲聆茅盾叙述自己和鲁迅议定发电但未见电文、是由史沫特莱由巴黎辗转发往陕北等等讲话的在座的出席者。此后,小鼎在《中华读书报》发表的上述文章中又谈到:“至于执笔人,茅盾生前在一些书信、文章中多次谈到鲁迅确曾就联名写贺信〔13〕问题征询过他的意见,他当即欣然同意,但贺信〔14〕具体内容以及如何发出?他则并不清楚。二十年前,笔者也曾有幸当面聆听过他对此问题的明确答复,与文章书信观点一致。”这里我要强调两点。第一,茅盾一再说过,长征胜利的消息是史沫特莱告诉鲁迅的;发贺电也是她提的建议。第二,茅还说过,贺电是由史沫特莱转发出去的。至于“史沫特莱如何转发此电……只能猜想史把电文弄到巴黎……然后再转到陕北”。〔15〕这些情况再一次说明,阎愈新同志实在太急功近利了!为作结论,他常常把猜想和推断当作立论的根据。对于一位资深学者说来,这是令人感到遗憾的。
从以上的材料和分析中不难看出:一,唐天然、程中原、阎愈新三位同志在研究与发现鲁迅、茅盾祝贺中共中央这一重大举措问题上,各自作出一定的贡献。尤其是阎愈新同志,几十年如一日,那锲而不舍的精神,实在令人钦佩和敬重。二,阎愈新同志发现的这封信的作者,到底是否鲁迅和茅盾,目前尚不能作确切的结论。但从上述种种情况看,我认为可信性是不大的。三,几十年来,从冯雪峰始、包括当事人茅盾在内,都确认鲁迅是从史沫特莱那儿得到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消息,是她提议驰电致贺,经鲁迅、茅盾议定联名致电及电文内容,由鲁迅拟文,茅盾未参与也未见过电文,电文由史沫特莱设法经巴黎转陕北的“长征贺电”的这些公认的说法,迄今没有充分证据可予否定。退一步说,即便阎愈新发现的此信是鲁迅所为,也不足以否定另有“长征贺电”曾经存在的这个公认的史实。四,阎愈新同志《之发现》和《新发现》两文,在论证根据、论证方法、论证过程中,暴露出急功近利,把推断、猜想当证据等等问题,这对澄清这段现代文学史上重大事件,产生了不好的影响。阎愈新同志既推进了问题的研究,也平添了一些混乱。他的结论下得过于轻率。大抵与此有关。
最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新华社和许多报刊,尤其是新华社,对阎愈新《之发现》、《新发现》前后相互矛盾、论证多不可靠的两篇文章,竟然两度“炒作”,人为地造成轰动效应。而对自己两次报道相互矛盾处,又不自行纠正。作为党和国家的喉舌与权威代言者,不能认为这是一种严肃的负责任的态度!
注释:
〔1〕此文分别刊于同年4月《鲁迅研究月刊》和同年7月31 日《解放军报》;以下简称《新发现》。
〔2〕分别刊于同年《新文学史料》第3期与《新文化史料》第6 期;以下简称《之发现》。
〔3〕刊于同年6月5日《文艺报》。
〔4〕195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5〕1980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3期208页。
〔6〕《雪峰全集》4卷506页。
〔7〕该文发表时附印了封面照片。
〔8〕这里说的是“文化界领袖”而非文学界领袖;若把“××××”断定是文学界领袖尚差强人意;文化界领袖多矣;焉知“××××”或“×× ××”一定就是鲁迅、茅盾?
〔9〕《关于鲁迅茅盾联名致中共中央的贺信》,1996年11月6日《中华读书报》,以下引张小鼎的话,亦出此文。着重点是本文作者所加。
〔10〕张闻天这时任中共中央书记,是遵义会议上决定他取代博古在中央负总责的。
〔11〕《雪峰文集》第4卷第506页。
〔12〕夏衍:《懒寻旧梦录》293页,308页。
〔13〕“贺信”当是“贺电”,茅盾生前一直说是为庆祝长征胜利发出贺电,从未说过是“贺信”。
〔14〕〔15〕舒乙:《茅盾先生的解疑信》,海外版《人民日报》1992年5月26日。
标签:冯雪峰论文; 红军长征论文; 红军东征论文; 长征小报论文; 陕北红军论文; 鲁迅论文; 新华日报论文; 茅盾论文; 斗争论文; 史沫特莱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