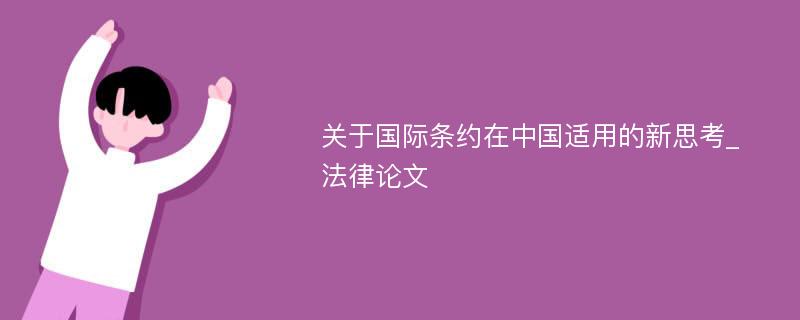
对国际条约在我国适用问题的新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在我国论文,条约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全球化是20世纪发生的重大的经济事件之一。在这个原动力的推动下,国际社会的合作关系日趋加强,大量的国际条约也随之订立。伴随着中国加入WTO,与国际接轨的步伐日益加快,国际条约在我国适用的问题也相应地更加突出。但遗憾的是,国际条约如何在我国国内适用的问题,长期以来只是局限于理论层面的探讨,尚未有明确的立法。著名国际法学家凯尔森曾说过,“国际法之转化为国内法是否有必要的问题,也只能由实在法回答,而不能由关于国际法或国内法的性质或它们的相互关系的一种学说来加以回答”。(注: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414页。)的确,由于学理解释效力的局限性,缺乏法的明确指引功能,自然会导致国内司法实践在这一问题上的不一致,所以诉诸于实在法予以解决的必要性已日趋迫切。笔者在本文中,试图从一个崭新的视角一一将国际条约在国内的适用区分为两个层次(第一次适用和第二次适用)进行审视,以期为国内立法界提供一孔之见。
一、研究国际条约在国内适用问题的新视角:一分为二式
国际条约在国内如何适用的问题绝非一个新命题。国际上早有争议,各国实践也自有不同。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我国国际法学界,有关国际条约和国内法关系问题,以及国际条约在我国适用方式问题的探讨也日益活跃了起来。学者们各抒己见,众说纷纭,主流观点不外乎两派:或认为国际条约在国内的适用是以直接式为主,(注:李浩培:《条约法概论》,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第384页;王铁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王铁崖:《国际法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0页;朱晓青:“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法学研究》,2000年第2期。)或认为国际条约在国内的适用是以间接式为主。(注:肖扬:《必须努力做好入世的涉外案件审判工作》,http://sinolaw.net.cn/news/yaowen/11/21/ywo4.htm.)两者观点迥异,相持不下,但悉心辨别,发现其共同之处都在于将国际条约在国内的适用视为一次性行为。倘若改变这个思维定势,寻求一条蹊径,是否会别有洞天呢?
笔者注意到国际条约在国内的适用,应存在两个层面上的内容。从国际法层面上看,国家将条约引进国内,从而对本国而言,形式上承担了条约义务。从国内法层面上看,国内司法机关在司法实践中适用被引进到国内的条约,从而在实质上承担了条约义务。宏观地看,这两个层面在时间上是相继的,在内容上是连贯的;而微观地分析,两者又各有其内涵。正是这一区分为笔者研究该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本文便是循着这两个层面,分别将其定义为第一次适用和第二次适用,展开论述。
二、国际条约在我国第一次适用的方式研究:转化式
根据“约定必须遵守”这一习惯规则,同时也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规定,适用条约是缔约国的义务。而一国将国际条约引入其国内的法律体系,就完成了第一次适用。在这个过程中,适用的主体名义上是国家,实际上是国内立法机关,适用的效果是使国际条约的效力被一国确立。
(一)各国实践之考察
国家采用什么方式将国际条约引进到国内法律体系,这纯属一国内部的问题,正如国际法学者亨金(Louis Henkin)所言,“一般说来,只要一国履行了它的(条约)义务,它是如何履行的,国际法并不关心”。(注:亨金:《国际法:案例与材料》,1980年英文版,第116页。转引自王丽玉:“国际条约在中国国内法的适用”,载《中国国际法年刊(1993年)》。)实践中,各国的法律规定和做法不尽相同,大体上有以下三种方式;(注:姜艳:“论条约在国内的适用”,《律师世界》,2001年第8期,第38页。)第一种,转化式,是指必须通过国内立法机关以一定的立法程序将一项国际条约内容制定为国内法后,条约才能在国内适用。采用这种方式的最典型的国家是英国。“在国际法上对联合王国有拘束力的条约本身并不影响本国法律或形成本国法律的一部分。”(注:詹宁斯、瓦茨修订:《奥本海国际法》第1卷第1分册,王铁崖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35页。)按照英国宪法,缔结和批准条约是英王的特权,而议会却拥有立法的垄断权,所以,凡条约必须先获得议会承认,由议会通过一项与条约内容相一致的法令后,该条约才能在英国具有法律效力,并由英国法院适用。“比利时国会号案”(注:李浩培:《条约法概论》,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第381-382页。)即是典型判例;第二种,并入式或采纳式,是指国际条约在国内发生效力,不需要经过转化环节。通常做法是,由国家宪法规定只有得到了国家立法机关的同意或批准才能参加一项条约,这样,已经参加的条约可以视为本国法律的一部分由国内法院直接适用。法国、瑞士、荷兰等欧洲大陆国家即是这样实践的;第三种,混合式,即兼采转化式和并入式将条约引进国内的法律体系。通常做法是,针对不同性质或内容的条约,分别采用以上两种方式。如美国,按一定的标准将条约区分为“自执行条约”和“非自执行条约”两种类型,前者是指“条约经国内法接受后,无须再用国内立法予以补充规定,即应由国内司法或行政机关予以适用”;(注:李浩培:《条约法概论》,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第386页。)后者则如转化式做法,需要通过一个履行条约的立法后才能在国内适用。这种方式经“福斯特诉尼尔森”的判例(1929)而在美国确立,到如今逐渐完善。根据其区分标准,需要立法执行的明文规定,或者条约涉及必须经美国国会立法才能实施的政府行动,诸如需要美国支付金钱的条约、规定关税的条约、条约涉及变更美国领土事宜的条约等,都属于“非自执行条约”。(注:万鄂湘、石磊、杨成铭、邓洪武:《国际条约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87-188页。)
(二)我国的理性选择
以上三种方式自然是各有优劣,那么我国立法中应该采用哪一种呢?笔者认为,在进行理性选择时,必须考虑几个因素。第一,主权至上原则是处理国际问题的基本原则。自“国际法之父”格劳秀斯以其名著《战争与和平法》为近代意义上的国际法确立和发展国家主权原则奠定理论基础,再经过几百年的国家实践和国际实践,国家主权原则成为国际法的坚固的基石已成公论。国际条约的订立虽然也是国家主权行使的结果,但它不是单一主权者意志的体现,而是“协调意志”的反映。作为对内主权内容之一的立法管辖,应强调主权单一和主权至上原则。第二,我国实行立法权独立原则。按照我国法制建设的十六字方针,“有法可依”和“执法必严”是相对独立的环节,也就是立法与司法是相对独立的,这就要求立法权相对集中,即集中到立法机关。另外,根据我国《宪法》和《缔结条约程序法》的有关规定,国际条约的谈判和签署是由外交部和国务院的有关机构进行的,他们清楚地了解条约的谈判过程、细节、焦点,有时还有中、外文的解释的不同等,(注:张晓东:“也论国际条约在我国的适用”,《法学评论》,2001年第6期,第79页。)而集中立法权,并由立法机关在条约转化过程中参考这些部门的意见,可以使国际条约的内容在国内得以较正确地适用。第三,我国是大陆法系国家。这就决定了我国法官在司法活动中,需要适用制定法,而不能造法,包括解释法律。立法的明确将有助于司法质量的提高。
基于以上考虑,笔者认为,在国际条约在国内第一次适用的方式问题上,我国宜采用转化式,将其微观化,具体可以采取以下几种形式:第一种形式,以另外新的单行文本予以转化。根据我国《缔结条约程序法》,国际条约一般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批准或国务院核准或既无须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批准也无须国务院核准,那么,针对这三种情形,可以分别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决定”或“决议”的形式、国务院以“决定”的形式、其他部门以“通知”的形式将其转化为国内法。第二种形式,结合国内法的相关规定予以转化。这种方式主要是通过准用性规则来实现的。如我国现行《专利法》第20条第2款和第3款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的有关国际条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的有关国际条约”即属此类。第三种形式,通过制定新的国内法或改变现行国内法予以转化。有些国际条约并不直接为私法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等)创设权利,而是通过对缔约国施加义务,要求其再通过国内措施从而保护私法主体的权利,如《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TRIMS)、《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等。对于这类条约,考虑到在第二次适用过程中,不能为私法主体直接援引,所以它们的转化需要由这些条约的决定批准机关及时对有关国内法作出相应的修改或补充。
笔者认为,国际条约在我国的第一次适用,其性质实为它的效力被国家确立的过程,相当于在国内的立法过程。所以,这个问题应该由《宪法》和《立法法》予以明确。
三、国际条约与国内法关系的理论思考:一元协调论
经过国家的第一次适用,国际条约被引进到国内的法律体系后,势必会与国内法发生一定的关系。作为一个附带问题,我们需要考察它们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这是个长期存在争议的命题,理论界主要存在着三种不同的学说——即“国际法效力优先说”、“国内法效力优先法说”、“国际法与国内法效力平行说”,以及两大派别,即“一元论”和“二元论”。笔者认为,国际条约与国内法属于同一法律体系,并且在这一法律体系中,互为协调的关系,此之谓“一元协调论”。
(一)一元性:同一法律体系
首先,从作为法的实质方面来看,国际条约和国内法是相同的。其一,从两者的性质上看,它们都是法。国内法的法律性质自不待言,而对于国际条约来说,情况如何呢?“任何条约,不论是他(笔者按:特里派尔)所说的契约性条约还是立法性条约,都为当事国创立法律,即创立国际法规则”,(注:李浩培:《条约法概论》,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第34页。)“任何条约的主要职能都是创造法律”。(注:凯尔森:《国际法原理》,王铁崖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269页。)所以,国际条约与作为国家意志的国内法从本质上是统一的。(注:张晓东:“也论国际条约在我国的适用”,《法学评论》,2001年第6期,第73页。)其二,从作为法的效力来源上看,两者都是主权意志的表现。国内法体现国家主权意志可以从法的本质(注:张文显:《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49-54页。)以及主权对内的权力内容(注:王铁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125页。)中得以反映。国际条约也是国家行使主权——对外行使主权,从而形成与其他主权的协调意志而订立的。
其次,从作为法的被使用的主体上看,两者都可以为私法主体所用。虽然对于国际法是否能直接拘束个人仍是理论上有争议的一个问题,(注:王铁崖:《国际法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81-184页。)但在经济全球化运动的作用下,国家间在各领域内的融合日益紧密,民商事条约和司法协助条约更多地形成,私法主体(既包括外国方,又包括内国方)能通过意思自治而直接选择国际条约作为规范其法律关系的准据法已是实践中不争的事实。
再次,从作为法在国内形成效力的程序来看,两者都承认国内立法机关的行为。国内法由立法机关或其授权机关制定,国际条约则由立法机关或其授权机关转化。由此,国际条约与国内法是可以也应该同属于一个法律体系的。
(二)协调性:互为协调关系
进一步分析,在这个同一的法律体系中,国内法与国际条约是否存在孰优孰劣的关系呢?也就是说,是否可以采用“优先说”(即国际法优先说或国内法优先说)呢?笔者不赞同这种观点。首先,“优先说”不具有比较基础。国内法是一个包容对象很广泛的整体概念,不同的对象有不同的效力,而国际条约则是一个范围相对狭小的概念,两者不具有对称性,所以不具有在同一层次上比较的可行性。至于在这个总的法律体系中,国际条约位次如何,这是可以比较的,本文将在第四部分中分析。其次,国民待遇原则的发展也对“优先说”提出了质疑。国民待遇原则的基本含义是指一国在经济活动和民事权利义务等方面给予其境内外国国民以不低于其本国国民所享受的待遇,(注:余劲松、吴志攀:《国际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76页。)它是与差别待遇相对的。国民待遇作为一种法律规范,是经过长期的历史实践而形成的,(注:赵维田:《世贸组织(WTO)的法律制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9页。)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其发展尤为瞩目。二十世纪中叶,国民待遇原则作为一项重要原则被确定在GATT框架中。此后,伴随着多轮的谈判历程,它不断地渗透入WTO的其他领域,如服务贸易领域、投资领域、知识产权领域。而正是由于WTO这些协议的“一揽子”性质,使得该原则的适用具有更大的普遍性和强制性。如果只是简单地用“优先说”来默认国际条约与国内法的保护标准或具体规定的不相同,那么由于国际条约与国内法适用范围各异,“这就有可能导致司法实践的不一致,就会造成相同的事项仅仅是因为诉讼所涉及的当事人不同,而适用不同的法律作出不同的判决。”(注:万鄂湘、孙焕为:“论多边商贸条约在中国的适用(2)”,《中国对外贸易》,2001年第8期,第15页。)这样,在一国境内,差别待遇就会顺理成章地存在并且会很普遍。那么,国民待遇原则只会蜕变成单方面的“超国民待遇”,这当然是对主权平等要求的偏离和曲解。
相比之下,“协调论”是合宜的。第一,根据国际法原理,国家应受自愿承担的条约义务的约束,“于是国家就有义务使它的国内法符合其承担的条约义务”,(注:慕亚平、周建海、吴慧:《当代国际法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4页,第488-489页。)如可以通过对国内法的修改或补充从而符合条约的规定。第二,它通过对国际条约与国内法的保护标准或具体规定的不相同这一情况,主动作出调整,从而可以较好地解决“超国民待遇”的问题,更好地体现国民待遇原则。第三,它也有利于更好地实现与国际接轨的目标。经济全球化运动提供了一个国际平台,加强了各国之间的合作关系,也一定程度地导致法律全球化。采“协调论”可以为与国际接轨创造较平和的心理基础。
四、国际条约在我国第二次适用的具体问题探讨
由上述,国际条约经转化后,已经成为国内法律体系的一部分。而在国内层面上最通常意义上的法的适用,就是指国家司法机关依据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具体应用法律处理案件的专门活动。(注:张文显:《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365页。)此即国际条约在国内的第二次适用。对此,笔者认为,应该明确几个具体问题。
(一)国际条约适用的一般原则。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特别法优于一般法以及新法优于旧法等法的适用的一般原则,在此同样适用。这里我们有必要先解决国际条约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效力层次定位的问题。笔者认为,首先,从理论上说,国际条约应该低于宪法。从实践上看,这也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通行做法。(注:姜艳:“论条约在国内的适用”,《律师世界》,2001年第8期,第42页。)其次,国际条约与其他法律渊源的效力层次的比较,则应根据条约的转化机关来确定。
(二)公共秩序保留是国际条约适用的指导原则。作为国际私法上的重要制度,公共秩序保留一方面具有排除外国法适用的否定或防范的消极作用,另一方面又具有直接适用内国法中强制性规范的积极作用。另外,就国际条约本身来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了一种新趋势,几乎所有的国际私法公约订立了公共秩序保留条款,允许缔约国在认为根据条约中的规定适用某外国法会与自己的公共秩序相抵触时,可以援用这种保留条款来排除公约中的规定”。(注:韩德培:《国际私法新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20页。)所以,在适用国际条约时,有必要把握公共秩序保留这一指导性原则。
(三)当事人意思自治是国际条约适用的协调原则。自杜摩兰在《巴黎习惯法评述》中明确提出“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思想以来,到19世纪中叶以后,在合同法律适用领域,当事人意思自治说逐渐取得了主导地位,已发展成为在世界范围内确定合同准据法的首要原则。(注:石慧:“尼日利亚国际技术转让合同中法律‘选择’问题的评析”,《湘江法律评论》(第5卷),第577页。)在国际民商事领域中,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所确立的以国际条约作为准据法应该成为适用国际条约问题的协调原则。
当然,在适用国际条约的司法实践中,识别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作为一个法律认识过程,识别对于正确地适用法律、处理案件都有重要的意义。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通过识别,确定条约在什么范围内适用。条约和一般国内法一样,都有其适用的范围,如《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就适用于当事人营业地位在不同国家(包括缔约国和在一定条件下非缔约国)之间的货物买卖合同的订立及双方权利义务关系(当然,我国在加入此公约时对适用范围还作了一定的保留)。另一方面,通过识别,确定条约能否被适用。正如本文第二部分中所论及的,有些国际条约并不直接为私法主体创设权利,而是通过对缔约国施加义务,要求其再通过国内措施从而保护私法主体的权利,如《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TRIMS),那么对此类条约,国内司法机关则应通过适用相关的国内法将其予以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