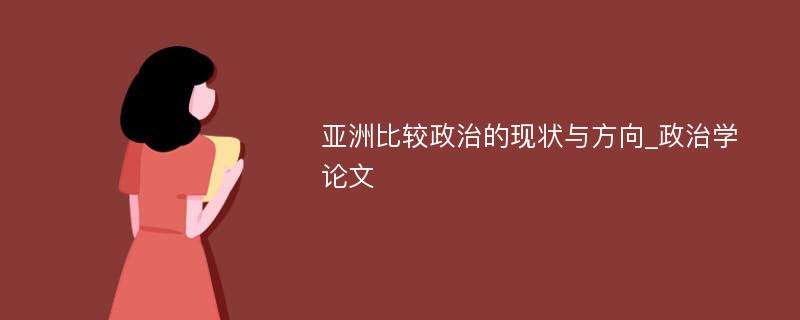
亚洲比较政治学的现状与方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亚洲论文,政治学论文,现状论文,方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 在《比较政治学方向辨析》(Debating the Direction of Compatative Politics,2007)一文中,杰拉尔多·蒙克(Gerardo Munck)和理查德·斯奈德(Richard Snyder)对比较政治学的范畴、目的和方法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与定量研究方法已经在这一领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流行观点相反,比较政治学仍然主要依赖定性研究。此外,研究的地理范畴主要集中于西欧和拉丁美洲,且多数研究是实证的,而非生成理论(theory-generative),主要采用描述性分析法而不是因果分析法,缺少正式假设(formal hypotheses)。实证研究则主要表现为对单一国家的个案研究以及二手的数据来源,且多数研究缺少与决策的相关性。另外,身处美国的男性教授是这一学科的主力研究者。受到蒙克和斯奈德的启发,我们采用类似的方法进行分析,以期了解他们对这一学科的整体观察是否与东亚比较政治研究的状况相符。 蒙克和斯奈德的《比较政治学方向辨析》 蒙克和斯奈德(2005、2007)①对比较政治学现状的分析基于三份重要的专业刊物②,将1989~2004年的刊期编码为29个不同的变量,编码的论文总共为319篇。 尽管蒙克和斯奈德称,比较政治学的学者“即使做不到完全平衡,也努力确保研究领域覆盖世界各个地区”,但事实上,有关西欧(41%)和拉美(27.2%)的研究在被编码论文中占据多数。他们还指出,有一些特殊地区尚未被覆盖,比如东南亚、南亚和加勒比地区。而鉴于这些地区庞大的人口数量,这种遗漏对学科发展而言是很大的缺陷。此外,大中型的研究成果很少(被编码论文中涉及5个或更多国家的研究不到25%),而单一国家的个案研究占到45.7%,就此而言,这一学科在本质上仍然是非比较的。 从研究方法来看,并不像一般所认为的,即定量研究方法的广泛采用已经成为政治学研究的常态,实际上,44.3%的编码论文采用的是定性方法,大约是采用定量分析方法的论文数量的两倍。其余则被编码为混合型,其中以定性方法为主的论文比以定量方法为主的论文略多,分别为19%和13.1%。 就研究目标而言,让人意外的是,很少有研究偏重于理论分析(仅为4.4%),相反,近一半研究(49.8%)是经验分析(而不是经验分析与形成理论相结合)。蒙克和斯奈德还证实,半数以上的论文是描述性研究(52%)而不是因果研究。由此得出的结论也相当令人惊讶,即“没有证据显示比较研究的学者寻求开发(各种理论的)范式或将其应用于比较政治学领域”。此外,蒙克和斯奈德发现,被编码论文中很少有在定性分析中提出了清晰的、可充分验证的假设,定性研究的论文中1/5完全没有假设,70%的论文仅仅提出了部分假设。 在此文章之前,蒙克和斯奈德还曾提出过另一个值得注意的观察结果,即明显的性别偏差和美国学者的主导地位。在2005年的分析中,蒙克和斯奈德揭示,编码论文中有74.9%是男性学者撰写的,只有18.1%的论文作者为女性,7.2%为男女学者合作撰写。此外,更令人震惊的数字是,89.2%的论文作者为美国学者,其次是来自西欧和加拿大的学者。合作撰写的文章很少,绝大多数为独著(74%),22%为联合署名,而有多个作者的文章仅占3%。 最后,研究还发现,几乎没有研究与决策者有直接的关系,如以“向公共政策制定者进言,或是为决策圈的辩论提供相关结果的方式”。蒙克和斯奈德推测这可能是因为比较研究学者为更具政策相关性的研究选择了不同的发布渠道。 在解释只选择三种主要的比较政治学刊物的根据时,蒙克和斯奈德承认其选择仅仅是“有关比较政治学总体研究的一个有限样本”,而“其他途径出版的比较政治研究成果可能会呈现出差异”,例如,区域性学术刊物可能会带来不同的发现。作为对蒙克和斯奈德的回应,马奥尼(Mahoney)主张,“我们需要观察其他刊物,以推进对比较政治学领域的研究成果更为综合的认识”。③ 有鉴于此,我们尝试检验蒙克和斯奈德的结论能否扩展至区域性刊物。从他们的主要观察中我们选择以下诸项进行验证。 (1)东亚比较政治学研究主体的实证范畴主要是单一国家的个案研究,因此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比较研究。 (2)与比较政治学偏好定量分析的先入之见相反,有关东亚的多数研究是定性的。 (3)绝大多数研究是分析性的,而非形成理论的。 (4)多数研究为独著,且作者为北美、英国和澳大利亚的男性学者。④ 为了检验上述假设,我们从以下8种比较政治学刊物中收集数据:《亚洲概览》(Asian Survey)、《当代亚洲期刊》(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亚洲政治学学报》(As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现代亚洲研究》(Modern Asian Studies)、《批判亚洲研究》(Critical Asian Studies)、《东亚研究期刊》(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太平洋评论》(Pacific Review)和《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这8种刊物中的7种属于比较政治学刊物,而《现代亚洲研究》更偏重于比较史学。选择它是作为一种对照,以检验从政治学刊物中得出的结果是否在本质上与有关亚洲的更为宽泛的比较分析有所不同。在进行选择时我们排除了所有专门研究单一国家的刊物,如《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而除了《现代亚洲研究》之外,我们也剔除了所有非政治学的刊物。由于我们关注的是比较政治学,所以国际关系类刊物也被排除在外。 研究结果:几乎没有比较研究? 单一国家个案研究还是比较分析? 在本次研究编码的所有论文中,绝大多数(75.5%)是单一国家的个案研究。也就是说,明确的比较研究不到全部论文的1/4。数量居其次的是两个案例之间的比较(11.5%),第三位的是有关大国的研究,占6.1%。此外,针对小国或中等国家的研究很少,仅有17篇论文,即3.7%。虽然这一结果并不出乎意料,或者说与蒙克和斯奈德的研究结果一致,然而单一国家研究在这一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程度仍然令人惊讶。在蒙克和斯奈德的分析中,单一国家的个案研究在全部论文中不到一半(45.7%),而在这里则占到全部研究的3/4。对于单一国家个案研究一直存在方法论上的批评,其中之一是,它“对于比较分析的价值有限,因为这类研究既不存在直接比较,也不能超越个案推而广之”。指出这一点并不是说从单一国家的个案研究中不能有所收获。个案研究如果在方法论上非常精确的话,还是可以对比较政治作出重要贡献。正如耶林(Gerring)所证实的,如果单一国家个案研究表现为一个关键个案、“最大可能”个案或是“最小可能”个案,来证实或是驳斥一个普遍理论或假设的话,其从方法论角度而言是最为合理的。⑤这类研究还为验证因果机制提供了机会。然而问题在于,正如我们的数据所揭示,单一个案研究中绝大多数采用了叙述性方法。在这种情况下,除非个案在更广泛的人口范围内具有相关性,否则除了特质分析,它几乎不能在个案之外得到利用。在我们的样本中,的确很少有这样的案例,可以被推演以证实或是驳倒一个理论。 那么,为什么单一国家个案研究如此流行?这或许是特殊本体论和认识论立场在关于亚洲的比较政治领域中相对强势所造成的结果。鉴于多数选择定量研究方法的研究者坚持明确或绝对的实证主义认识论立场,即认为观察、体验、推论和验证的科学方法对于比较的社会研究和自然科学来说没有什么不同,但对于选择定性研究方法的人来说则不尽然。之所以热衷于定性的方法,是因为这些人持有一种解释主义的认识论,认为社会是一种异常复杂的建构现象,因此其中的客观性大多不过是错觉而已。基于这一立场,他们的研究战略也总是呈非结构化,在研究进程中可以对假设进行修改,利用个案研究和参与式观察来彰显格尔茨学说(Geertzian)有关社会现象和社会现实的“深描”(thick description)。⑥对这些学者来说,在循“抽象的阶梯”而上时,大国的规模显然意味着每个个案会缺乏集中度和透彻性。研究的国家越多,分析的变量反而越少,这些国家会从“特定背景”中抽离出来,变得愈发抽象。较之主流政治学,传统的研究方法(例如民族志)可以使区域研究者更直观和方便地开展区域研究。 跨学科研究:多个学科比单一学科更好? 本研究选取的刊物中,有若干份明确表示自己为跨学科的刊物。由于没有完善的手段进行确认,对论文跨学科性的衡量问题重重。鉴于此,我们选择了两种间接测量的方法。第一种方法是对作者的专业学科进行编码,并测量一份特定刊物中某学科作者的论文占有多大比重(某一学科的集中度越高,这一刊物的跨学科性就越低)。第二种方法是计算作者的数量。我们再次承认这是一个不完善的测量方法,因为跨学科工作也可以由一位学者完成,况且联合署名也不能保证就是跨学科研究。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认为,联合署名在原则上是出于一种愿望,即将更多的方法论技巧、理论进路和其他的专家意见引入研究。因此,联合署名对于确定跨学科与否是一个具有操作性的替代方法,尤其是在与第一个替代方法合并使用时。 基于上述方法,我们的研究几乎没有发现跨学科研究的证据。通过对学科编码,我们发现,68.1%的论文来自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紧随其后(13.7%),历史学家占5.4%,经济学家占3%。虽然研究者普遍受到其自身学科的束缚,然而他们很少从事合作研究这样一个事实(84.2%的论文是独著)表明,关于亚洲的比较政治研究若想成为一个跨学科领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尽管如此,我们的结果还揭示出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化。在8种样本刊物中,政治学作者占最大比重的是《东亚研究期刊》(96.4%)、《太平洋评论》(92.6%)和《当代亚洲期刊》(91.7%),而比重最小的是《批判亚洲研究》(27.9%),《太平洋事务》为46.2%,《现代亚洲研究》为46.4%。其中《现代亚洲研究》的作者中政治学家人数最少,因为该刊是纯粹的区域研究杂志,所涉学科为历史、社会学、经济学和文化研究。《批判亚洲研究》和《现代亚洲研究》的学科覆盖最为广泛,没有它们的贡献,偏重于政治学的情况会更为明显。相反,尽管明确宣称为跨学科刊物,《东亚研究期刊》被编码的28篇论文中有27篇是政治学家所撰写的。 另一个引人注意的特点是,不管其学科倾向如何,在近2/3的论文中(63.6%),研究的观察单位是国家,而不是任何次国家范畴(5.0%)或区域性组织(18.9%)。这一发现与蒙克和斯奈德的研究一致。此外,多数论文讨论的是分析对象国的国内政治,有21.7%的论文将此作为主要论题,19.1%的论文主题集中于国际体系,其他题目则从人物传记到环境政策都有所涉及。 定量方法与定性研究:有细节,无数据? 在社会科学领域,特别是政治学领域,存在一种普遍的看法,即定量研究方法不仅成为规范,而且实际上已经成为霸权。的确,有些人面对这种趋势颇感遗憾,而另一些人则提出尖锐的批评,指出这种倾向“排斥可靠的定性研究,而支持那些可怜的博弈论者和不成功的经济学家采用的晦涩的数学模型”。 2011年,马利尼亚克(Maliniak)等人对国际关系领域中12种主要刊物进行了研究,并对美国大学中的教职人员开展调查。他们的研究发现,截至2011年,在重要的国际关系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多数采用的是定量方法(53%),而且研究国际政治经济的文章高达71%。这样的数字引导其得出结论,即“如果美国的国际关系学术成就以重要的理论差异和较弱的——但仍然是显著的——方法论差异为特征,那么很明显,占支配地位的认识论就是实证主义”。 尽管存在这样的趋势,但不管是蒙克和斯奈德的研究,还是我们的研究,都没有在比较政治学抑或亚洲研究中发现任何可以得出此类结论的证据。正相反,我们的研究揭示,绝大多数有关亚洲的研究(81%)属于定性研究,只有30篇论文(6.5%)算是采用了定量方法。另外,11.9%的文章采用混合的方法。有趣的是,在8种刊物中唯一的例外是《东亚研究期刊》,其中多数论文采用了定量方法,占53.6%。而且,这一结果构成了本分析中所有定量研究论文的一半以上。 很明显,这些结果推动了相关的探究,即为什么关于亚洲的比较研究中不大采用定量的方法?除了之前讨论过的有关认识论的问题,在涉及从事大国研究的能力局限时资源困难也常常被提到。尽管对来自一些国家的数据的可靠性依然存在争论,但目前已经有了一些区域性的数据库,最知名的是亚洲民主动态调查系列(Asian Barometer)和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数据库。虽然未能覆盖东亚全部17个国家,但是利用这两个数据库意味着其中12个国家的数据是可以获得的。此外,有越来越多的源自国际组织的数据,如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和亚洲开发银行,以及民间非营利研究机构如皮尤研究中心,还有各种民间的研究公司。 由于我们承认认识论的挑战和深描方法所能带来的贡献,因此并不主张有关东亚的社会研究一定要采用定量方法而不是定性研究。单一的定性的个案研究也可能非常有意义,如果它被用来证实或反驳宽泛的理论概括,或用来验证因果机制,或是“与跨案例研究相结合”。混合的方法也很有用,因为“它们可以发现一些独特的差异,是采用单一方法有可能忽略掉的”。无论如何,有关亚洲的比较政治的研究结果是明确的,尽管发表在美国主要政治学刊物⑦上的比较政治学论文多数采用定量方法(88.2%~93.3%),但与关于亚洲的比较政治的论文情况并不一致。 形成理论(theory-generation)抑或以分析为主 研究结果显示,多数论文采用的是经验分析(67.5%),而非利用某种理论框架开展研究(12.1%),这与蒙克和斯奈德所发现的结果是相吻合的。⑧只有《太平洋评论》(33%)、《现代亚洲研究》(19.0%)和《太平洋事务》(17.9%)这三种刊物有超过15%的论文借鉴了某种理论视角。尽管有些作者的文章的确很规范(3.5%),但这类论文很少偏重比较研究,而是集中发表在《现代亚洲研究》(11.9%)、《批判亚洲研究》(9.3%)、《亚洲政治学学报》(6.7%)和《批判亚洲研究》(9.3%)上。 我们同意蒙克和斯奈德以及威贝尔斯(Wibbels)的观点,即理论框架的缺乏可以归咎于(至少是部分)方法论的不完善。然而,缺乏理论性的另一个原因也可以简单地理解为“比较政治学的统一的理论框架”尚不存在。方法论不完善的论文最为通常的表现形式是不能提出明确的假设、进行详细的方法论描述或对因果推论进行验证。此外,研究还发现许多实证研究是依赖匿名的精英访谈,对访谈内容的引证通常是为支持研究者所希望强调或是确证的观点,而且,这类访谈内容也很难独立地加以验证。 学者队伍:作者的性别和国别 本研究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发现与论文作者有关。我们发现绝大多数的论文作者是男性研究者,占到72.2%,这与蒙克和斯奈德的研究发现(75.1%)非常接近,而如果将男女作者合著的论文也包括在内,比例则上升到77.2%。女性作者的论文在所有发表论文中仅占20.6%。有趣的是,《批判亚洲研究》的多数作者是女性(55.8%),《现代亚洲研究》的女性作者占到1/3(33.3%),而《东亚研究期刊》的女性作者为1/4(25%)。显然,在其他5种刊物中女性作者很少,但是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批判亚洲研究》和《现代亚洲研究》都自称为后经验的(postempirical)和跨学科的,而《东亚研究期刊》则是本研究所涉刊物中最偏重定量方法和实证研究的。 至于研究者身处哪些国家,我们发现美国的大学和学院并没有占到绝对的优势。蒙克和斯奈德调查的所有论文中75%是由北美地区的学者发表的,而在我们的调查中这个比例只有34.7%。第二大较为集中的作者群即为亚洲的学者(27.1%⑨),西欧占17.4%,澳大利亚占11.3%。即使澳大利亚的数字与其人口比重似乎有些不成比例,但是这个结果也并非出人意料。由于在地理上靠近亚洲,澳大利亚是几个具国际声望的亚洲研究中心的所在地,包括莫道克大学的亚洲研究中心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亚太学院。而且,作为一个英语国家,澳大利亚的学术人员在北美和西欧的英文刊物上发表文章更为容易。 与我们的预期相一致,63%的被编码论文由我们所谓的大西方(wider West)的学术机构学者所发表,也就是美国(30.6%)、加拿大(4.1%)、澳大利亚(11.3%)和西欧(17.4%)。亚洲学者的论文数量略高于总数的1/4,但明显少于北美的34.7%。考虑到世界排名前100位的大学只有14所在亚洲,这一比例仍然高于我们的预期。此外,在125篇来自亚洲大学的学者发表的论文中,只有13名作者(10.4%)是在亚洲获得的博士学位,其余多数是在西欧和北美获得博士学位。这也在预料之中,因为我们采集数据的刊物均为英文期刊,而在这些刊物上发表论文的更可能是在英语国家接受教育的人,或者是西欧和北美旅居东亚的学者。 本文数据进一步证实了蒙克和斯奈德的许多研究结论。我们的研究显示,发表在所选8种刊物上的论文中绝大多数是定性的和实证的,很多缺少明确的理论框架,而且,提出明确假设的文章只占很小一部分。上述结果累积起来就带来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从技术的角度而言,在我们编码的论文中只有少数可以被看做以“社会科学”为特征。可见,“研究生们对方法论不断增长的需求,与比较政治学的描述性基础之间存在令人惊讶的分歧”。不管采用的是定量方法抑或定性方法,数据集(dataset)中的绝大多数论文并没有尝试进行任何因果推论,相反多数是叙述性的。因此,我们同意威贝尔斯的评论,即“比较政治学是这样一个领域,其口头宣称是社会科学的,但实际上却有着很大差异”。因此我们呼吁对为什么存在这一相悖的情况(disjuncture)进行研究,并就缺少“形式上科学的”研究究竟是不是学科劣势进行讨论,不仅局限于东亚的比较分析,而且针对作为一个整体的比较政治学。 原文题为“The State and Direction of Asian Comparative Politics:Who,What,Where,How?”,刊载于《东亚研究期刊》(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2014年第14卷。译文有所删节。 注释: ①2007年的论文发表于《比较政治研究》(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是2005年在华盛顿召开的美国政治学会年会呈交论文的编辑版本。会议论文包括数据、表格和分析,这些内容在2007年的刊物版本中被删除了。 ②这三份刊物是《比较政治研究》(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比较政治学》(Comparative Politics)和《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 ③James Mahoney,Debating the State of Comparative Politics:Views from Qualitative Research,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Vol.40,No.5,2007,pp.32-38. ④我们还有兴趣探究这一偏差究竟仅是所在地的偏差,还是民族以及教育地点的偏差。于是我们尝试对所有亚洲的作者,依据其获得博士学位的国家进行编码。但由于我们不能收集到这一变量的完整样本,因此未能将其列在文中。依据不完整的数据,绝大多数作者是在北美和西欧国家获得博士学位的。 ⑤John Gerring,Is There a(Viable)Crucial-Case Method?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Vol.40,No.3.2007.pp.231-253. ⑥“Geertzian”指的是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在其1973年出版的《文化的解释》(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一书中首次采用和倡导的方法。 ⑦这些刊物是《美国政治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美国政治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和《政治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s)。 ⑧蒙克和斯奈德还建立了聚合选项。通过将经验分析(49.8%)与理论形成和经验分析相聚合,经验分析在其数据集的所有论文中占到95.6%。而当理论形成与理论形成和经验分析相聚合时,只有50.2%涉及“某些”理论。参见Gerardo Munck & Richard Snyder,Debating the Direction of Comparative Politics:An Analysis of Reading Journals,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2007,Vol.40,No.5,p.11。 ⑨尽管没有对亚洲特定国家和地区分别进行编码,但结果显示中国香港(其中香港城市大学尤其突出)、日本和新加坡的人数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