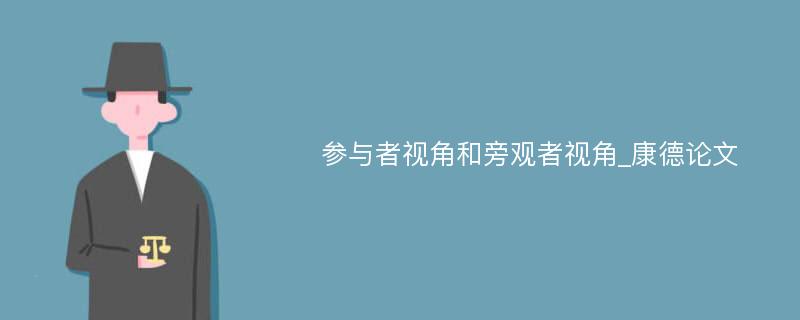
参与者视角与旁观者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角论文,参与者论文,旁观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为了判定“任性”(Willkür,arbitrariness,一译“选择自由”)是否自由的体现,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曾经提出两种关于自由的判定标准(以下简称“判准”),一种可称为“自我决定判准”(Self-determination Criterion),关注主体在活动所构成的因果序列中是否充当第一因,强调只有理性自我决定的活动才是自由的体现,而任性不是理性自我决定的活动,所以任性不是自由之体现。[1](P25-26)另一种是“智性主义判准”(Intellectualism Criterion),重视主体能否认识并选择理性对象,强调只有以理性因素为对象的活动才是自由的体现,而任性以感性因素作为自身对象,所以任性不是自由之体现。[2](P26-27)自我决定判准强调主体和自律,智性主义判准关注对象和他律,两者之间似乎存在显著的矛盾与对立。① 我们之所以会认为黑格尔关于自由的两种判准之间存在这样的矛盾和对立,是由于我们忽视了黑格尔在“形式理性”和“具体理性”之间所作的明确区分,误将上述两种判准中的理性概念理解为没有自身内容、无法在活动中进行自我决定的形式理性。相反,如果我们选择将上述两种判准中的理性理解为拥有自身内容、能够在活动中进行自我决定的具体理性,智性主义判准就可以被解读为自我决定判准的一种变体,表面上相互矛盾的两种判准即可统一为自我决定判准,其间的矛盾亦可以自然化解。问题在于,引入形式理性和具体理性的区分是一把双刃剑,它在化解自我决定判准和智性主义判准之间矛盾的同时,亦带来了异常棘手的难题。其中最为显著的是形式理性和具体理性在任性阶段下不能兼得并备所引发的自我决定判准对于任性的适用性难题。 在笔者看来,区分两种理性所带来的自我决定判准的适用性难题,其本质上是一种误解,因为黑格尔在讨论任性是否自由之体现时,曾同时使用了“参与者”与“旁观者”双重视角。参与者视角的有限性使得在任性阶段只有形式理性,我们无法使用自我决定判准对任性行为加以判定;而依据全能的旁观者视角,我们可以提前使用理性阶段所发展出的具体理性,将自我决定判准运用于任性阶段,从而克服自我决定判准对于任性阶段的适用性难题。根据这一思路,本文计划分为下述三个部分:(1)概述两种理性各自的特性,形式理性意指无需发展实现的先天自然属性,具体理性意指需要发展实现的后天社会属性;(2)阐明区分形式理性和具体理性为什么会引发自我决定判准在任性阶段的适用性难题;(3)论证引入参与者与旁观者双重视角理论,对于克服自我决定判准适用性难题所可能具有的积极意义。 一、两种理性的区分 讨论黑格尔对于理性的区分,必然要涉及黑格尔对“自我决定”(Selbstbestimmung,self-determination)这一核心概念的认识。相比于康德,黑格尔对自我决定概念的讨论更为复杂。黑格尔一方面肯定了康德式进路,承认从作为构成活动之因果序列的主要动因入手理解“自我决定”概念这一进路的优势,强调主体在因果关系中充当第一因对于自由实现的重要性;另一方面,黑格尔亦认可亚里士多德式进路,吸收了从潜能和现实切入解读“自我决定”概念进路的长处,认为主体在对象中的自我表现(self-expression)构成因果关系最为显著的体现。基于对“自我决定”概念的这样一种复杂理解,黑格尔不满康德对实践理性所作的纯粹“形式性”(formalism)、“空洞性”(emptiness)、局限于抽象“自我反思能力”(abstract reflection)的界定。在黑格尔看来,康德所追求的是一种缺乏自身内在内容的形式理性,这种形式理性即便侥幸有可能在康德式活动的因果序列中充当首要动因,却断然不可能在亚里士多德传统所要求的从潜能到现实的表现过程中充当首要动因。[3](P25-26)因此,黑格尔主张在形式理性和具体理性之间作出区分,认为只有拥有自身内容的具体理性,才既有可能在活动的因果序列中充当首要动因,亦有可能将自身潜能实现在对象之中。换句话说,黑格尔认为,只有具体理性,而非形式理性,才真正能够进行自我决定。② 综合黑格尔的相关论述,我们可以总结出形式理性和具体理性的两大重要区别:(1)形式理性没有自身内容,无法作出自我决定;③具体理性拥有自身内容,能够作出自我决定。(2)形式理性是一种自然属性,通过主体的自我反思即可获致;具体理性是一种社会属性,只有经由发展实现才可获致。考虑到与本文论题的相关度,这里将重点讨论两种理性之间的第二个区别。 形式理性意指主体从一切对象中抽象出来,或者用黑格尔本人的用词,从一切“定在”(Dasein,existence)中抽象出来,维持在自我同一状态中的反思能力。④在黑格尔看来,进行这种抽象是主体的一种先天自然能力,无需经由社会陶冶或发展实现。对于形式理性的这一特性,我们从黑格尔关于自由发展三个阶段的划分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将自由分为“普遍性—特殊性—个体性”(universality,particularity and individuality)三个阶段,认为普遍性是自由的起始阶段,而充当这一起始阶段之核心的正是形式理性概念。[4](P13-14)这充分说明,形式理性所代表的自我反思能力,属于主体的自然属性,无需经由复杂的发展过程,只要主体反身以求,就可以获致这种理性。 与之相对,在黑格尔看来,与缺乏自身内容的形式理性不同,具体理性是一种拥有自身内容,即拥有自身的“自我筹划”(self-projecting)与“价值追求”(value-pursuing),从而能够进行自我决定的理性。内容要素的引入使得我们自然要有此一问,具体理性从何处获得了自身的内容?在黑格尔那里,具体理性从自身的发展实现过程中获得了内容。与表现为主体先天自然属性的形式理性不同,具体理性是主体的一种后天社会属性,借由社会的教化与陶冶,主体将外在的规范加以内化,从而获得自身的内容,最终发展成为非形式的、有内容的具体理性。⑤黑格尔关于意志发展阶段的划分,可以看做是对于这一点的明证。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区分了意志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自然意志—任性意志—普遍意志”(natural will,arbitrary will and universal will)。自然意志表示意志尚未意识到自身与自然冲动之间的区别,表现为意志与各种自然欲望和偏好的直接同一[5](P22);任性意志表示意志业已意识到自身与外部定在和内部冲动之间的不同,并且能够从一切定在和冲动中抽象出来,维持在单纯的自我反思之中[6](P25);普遍意志表示意志进一步超越反思阶段,上升至普遍性阶段,并且能够以普遍性内容作为自身的对象。[7](P30)黑格尔这里所谓的普遍意志,即是本文所谓的具体理性,作为一种拥有自身内容的后天社会属性,具体理性不是单纯借助反思即可获致的理性,而只有在意志发展的最高阶段才可获致。⑥ 简言之,黑格尔不仅从有无自身内容出发区分了形式理性和具体理性,而且还从是否有其实现过程切入区分了形式理性和具体理性。与形式理性不同,在黑格尔看来,具体理性不是主体先天的自然属性,而是需要经由社会环境的陶冶才能产生出现的后天社会属性。也就是说,在黑格尔所划分的“自然意志—任性意志—普遍意志”三阶段中,只有到了普遍意志阶段,具体理性才得以产生出来;而在本文所讨论的任性阶段,只有缺乏自身内容、无法进行自我决定的形式理性,尚未发展出具有自身内容、能够进行自我决定的具体理性。 二、任性与自我决定判准的适用性难题 细心的读者可能会指出,既然黑格尔区分了形式理性和具体理性,并且一方面认为缺乏自身内容的形式理性不能,拥有自身内容的具体理性才能在活动中进行自我决定;另一方面认为具体理性是一种需要发展实现的社会属性,任性阶段只有形式理性,尚未发展出具体理性。那么,黑格尔在原则上理应可以运用“自我决定判准”,根据大前提——只有理性自我决定的活动才是自由的体现,外加小前提——任性阶段的形式理性不能在活动中进行自我决定,得出结论——任性不是自由之体现。 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其原因在于,黑格尔虽然从是否具备自我决定能力出发区分了形式理性和具体理性,但其关于形式理性不能进行自我决定、具体理性能够进行自我决定的讲法,却并非绝对的。换句话说,形式理性和具体理性的区分,更多的是通过两相参互对比得出的。一方面,只有参照具体理性,黑格尔才能说形式理性不能进行自我决定;另一方面,也只有对比形式理性,黑格尔才能说具体理性能够进行自我决定。但是,如果局限于任性阶段,黑格尔就只有形式理性,而没有具体理性,即无法同时获得两种理性,并通过参照对比得出何者能够、何者不能进行自我决定。因而,在任性阶段,黑格尔原则上不能运用自我决定判准,对任性是否是自由之体现作出判定。反过来,这也就等于说,自我决定判准的适用需要预先满足一定的条件。 条件1——自我决定判准要能够适用,在构成主体活动之原因的诸多因素之中,有且只能设定一种因素与主体相互同一。自我决定的核心在于强调主体行为的动因本诸主体自身的因素,而非受制于外在的因素。确切来讲,只有与主体同一的因素在主体活动所构成的因果序列中充当首要原因(或第一因),此一活动才能被称为自我决定的行为。而与主体相互同一的因素只能有一种,否则主体本身的自我同一性(self-identity)就难以建构。为了更好地理解黑格尔,这里我们以康德为例,与黑格尔作一对比。在康德那里,能够在活动因果序列中充当首要原因的备选因素有三类:一是独立于主体的外在因素,比如物理自然力或宗教政治权力;二是主体内部的感性因素,比如主体欲望与偏好;三是主体内部的理性因素,比如实践理性。在康德看来,不论是外在因素还是感性因素,都是与主体自我不相同一的因素。只有实践理性因素才是主体的核心,才是与主体两相同一的因素,所以,只有实践理性充当首要原因,活动才称得上自我决定活动,称得上自由。对唯一能够与主体相同一的实践理性的强调,是康德哲学的最大特色,这使得康德对自我决定的讨论能够满足条件1。 黑格尔关于自我决定判准的讨论,能够满足条件1吗?回答是不能。因为在构成主体活动原因的诸多因素中,黑格尔至少同时设定了两种因素——形式理性和具体理性——与主体相互同一。黑格尔虽然没有明确指出这一点,但我们只要分析一下其在“任性意志”和“普遍意志”之间所设定的先后发展关系,就可以得出这一结论。在黑格尔那里,任性意志阶段只有表现为先天自然属性的形式理性,作为后天社会属性的具体理性要到更高的普遍意志阶段才能够出现。而问题在于,一方面,如果我们仅仅局限于任性意志阶段,则没有理由认为形式理性不是与主体相等同的因素[8](P24);另一方面,如果任性意志阶段进一步发展至普遍意志阶段,我们同样必须承认具体理性亦是与主体相互同一的因素。[9](P32)这样一来,在黑格尔那里就至少存在两种因素可以与主体相互同一。虽然黑格尔对自我决定的理解与康德稍有不同,即相比康德式强调在活动所构成的因果序列中,何种因素充当主要原因或第一因的自我决定理解,黑格尔更加关注亚里士多德传统从强调潜能和现实入手所展开的自我决定理解⑦,即主体在活动序列中充当首要原因,意味着主体将自身潜在的内容通过活动加以对象化和现实化。[10](P18)但对于自我决定理解上的这层差异并不能证明,黑格尔将形式理性和具体理性两种因素同时设定为与主体相互同一的做法是成立的。亚里士多德传统强调潜能与现实的自我决定理解,与康德传统强调原因与结果的自我决定概念之间并不必然构成对立关系。从更广泛的立场来讲,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潜能与现实,同样可以视为以主体在行为中充当首要原因为关注点,即视为康德式自我决定的一个子类。⑧因而,不论是康德传统,还是亚里士多德传统,只要谈及自我决定,原则上都得承认有且只有一种因素能与主体相互同一。 条件2——自我决定判准要能够适用,与主体或同一或不同一的诸多因素之间必须是“并列式呈现”关系。诸多因素“并列式呈现”对于自我决定来讲之所以重要,其原因在于,只有当所有因素一时毕集、同时呈现,我们才能通过对比做出何种因素与主体相互同一的判定,否则我们的判定就可能因为未曾考虑到所有因素而是不完备的、成问题的。仍以康德为例。在康德那里,充当自我决定原因的诸多因素是“并列式呈现”的,不论是外在因素、感性因素,还是理性因素,对于康德来讲,都可以经由自我反思直接获致,因而都是当下呈现、一时具备的。得益于这种“并列式呈现”方式,在依据自我决定判准判定何种因素与主体相互同一时,康德所面对的是完备的全部相关因素,因而可以通过对这三种因素加以参照比较,判定出其中只有理性因素才能与主体相互同一,才是主体活动的第一因。据此,康德式自我决定显然亦满足条件2。 与康德不同,黑格尔关于任性阶段的自我决定论述无法满足条件2。其原因在于,在呈现主体活动的诸多因素时,黑格尔选择了与康德截然不同的呈现方式。对黑格尔来说,姑且不论外在因素和感性因素,即便说形式理性和具体理性业已构成了自我决定诸多因素的完备序列,但是,黑格尔并未选择用康德式的“并列式呈现”方式将它们同时呈现,而是选择了“继起式呈现”的方式,将它们按时间顺序分别予以呈现。按照黑格尔对任性意志阶段和普遍意志阶段的区分,先有任性阶段的形式理性,后有理性阶段的具体理性。我们在任性阶段所能够获致的仅仅是形式理性,而无具体理性。黑格尔对诸多因素采取“继起式呈现”方式的结果是,分阶段来看,不论是形式理性还是具体理性,由于自身的唯一性,在其所属的具体阶段上都是与主体相同一的因素。但从整体来看,形式理性与具体理性两相比较,似乎又只有后续的具体理性才是主体真正的自我,才能与主体相互同一。在这层意义上,我们似乎可以说,在任性意志阶段,形式理性既是又不是自我决定的首要原因。⑨也就是说,由于黑格尔对自我决定的诸多因素采取了“继起式呈现”而非“并列式呈现”,导致在依据自我决定判准对任性阶段的主体活动进行判定时,无法同时面对自我决定所涉及的所有因素——形式理性和具体理性,从而无法判定出何种因素与主体相互同一。因此,黑格尔关于任性的论述同样不能满足条件2。 简言之,黑格尔要运用自我决定判准对任性是否自由之体现作出判定,需要同时满足两个条件,条件1——在构成主体活动之原因的诸多因素中,有且只能设定一种因素与主体相互同一;条件2——与主体或同一或不同一的诸多因素之间必须是“并列式呈现”关系。但是,由于黑格尔区分了形式理性和具体理性,并且认为两者之间呈阶梯式先后发展关系,这使得他既设定了两种理性与主体相互同一,又无法对这两种理性加以“并列式呈现”,进而使得其关于任性阶段“自我决定”的论述,既不能满足条件1,亦无法满足条件2。换句话说,黑格尔不能使用自我决定判准作为判定任性是否自由之体现的标准。 三、“参与者”与“旁观者”双重视角 由上述可见,只有设定唯一因素与主体自身相互同一,并且同时并列呈现出其他全部因素,才能判定一种活动是否主体自我决定的结果。可惜,黑格尔在讨论任性时,设定了形式理性和具体理性两种因素与主体相同一,并且对两种理性采取了继起式而非并列式呈现方式,由此引发了自我决定判准对于任性阶段的适用性难题。不过,从《法哲学原理》导言中我们发现,黑格尔确实曾把自我决定判准用做判定任性是否自由之体现的标准:“既然只有自由的自我决定(self-determination)中的形式要素才是内在于任性的,而另一个要素是给予任性的,那么,被认为自由的那任性,的确可以叫做一种幻觉。”[11](P26)这显然与我们关于任性阶段不能使用自我决定判准的论断相矛盾。应当怎样解释这种矛盾? 在笔者看来,解释这一矛盾的关键在于指出,黑格尔在讨论“任性”时,同时使用了两种不同的视角——“参与者视角”与“旁观者视角”(Participant's Perspective and Observer's Perspective)。⑩虽然黑格尔在行文中没有明确区分这样两种视角,但在讨论“任性”时,与《精神现象学》的“自我意识”章一样,黑格尔实际上使用了双重视角。也正是依据双重视角,黑格尔克服了自我决定判准不能适用于任性阶段的难题。具体而言,参与者视角是指主体从属于某一特定发展阶段所持的有限视角。受制于这种有限视角,主体只能从其所从属的具体阶段进行观照,比如在任性意志阶段,主体只能观照形式理性,而无法提前观照后续阶段的具体理性;而在普遍意志阶段,参与者视角又只能观照具体理性,而不能回顾前一阶段的形式理性。与之相对,旁观者视角意指一种全能的上帝视角,它是一种能够超越主体特定发展阶段的无限视角。得益于这种视角,主体即便身处特定的意志发展阶段,亦可以同时观照全部其他阶段,比如在任性意志阶段,虽然原则上只有形式理性,但只要运用旁观者视角,主体同样可以提前观照普遍意志阶段的具体理性,而在普遍意志阶段的情况也是一样。 进一步讲,黑格尔对任性的具体讨论分为两个步骤。首先,黑格尔从参与者视角出发,将任性阶段的主体理解为形式理性的承载者。一方面,鉴于在任性阶段只有这样一种形式理性,而无具体理性,黑格尔没有理由不认为相比欲望和偏好所代表的感性因素,形式理性是可以与主体相互同一的唯一因素;另一方面,由于任性阶段只有形式理性所代表的理性因素以及欲望、偏好所代表的感性因素,黑格尔同样没有理由不认为任性阶段已经对构成自我决定原因的全部因素作了完备的并列式呈现。换句话说,只要局限于参与者视角,黑格尔就有理由认为任性阶段业已满足自我决定判准所需要的两个条件:条件1——设定唯一因素与主体自身相同一;条件2——对所有因素进行并列式呈现。根据这种推论,黑格尔原本可以运用自我决定判准将任性直接视为自由之体现。 可惜,实际情形并非如此。黑格尔明确指出,任性并非自由之体现。(11)“普通人当他可以任性而为时,就信以为自己是自由的,但在这种任性中他恰是不自由的。”[12](P27)为什么会这样?个中原因在于,在考察任性时,黑格尔除了运用参与者视角,还同时运用了旁观者视角。参与者视角由于受制于自身所处的具体阶段,在任性阶段只能观照形式理性,并且在表面上满足了自我决定判准所需的两个条件,形式理性是与主体相互同一的唯一因素,自我决定所涉及的所有因素都已得到了并列式呈现,符合自我决定判准的要求,从而得出任性即是自由之体现的错误结论。与之相对,黑格尔一旦运用旁观者视角,得益于旁观者视角能够超越自身所处的具体阶段,同时观照不同阶段的全能型上帝视角这一特性,使得身处任性阶段的主体不仅能够观照形式理性,而且可以提前观照原则上只有发展至普遍意志阶段才会出现的具体理性。[13](P25-26)通过将这两种理性参互对比,主体最终会意识到:一方面,形式理性是一种缺乏自身内容的空洞的、中性的理性,这种理性不能与主体相互同一,真正能够与主体相同一的是具有自身内容的具体理性;另一方面,由于发现了具体理性,参与者视角下所谓能够并列呈现自我决定所涉及的所有因素的观点自然不能成立,因为在感性因素和形式理性之外,还必须加上旁观者视角观照的具体理性。[14](P30-31)所以,只有旁观者视角下的任性阶段,才能既真正满足条件1,亦真正满足条件2。并且,只有依照旁观者视角,黑格尔才有理由断言,依据自我决定判准,任性不是自由之体现。 简言之,虽然黑格尔在行文中没有明确透露,但根据本文的推理,黑格尔在讨论任性时,实际上沿用了其在《精神现象学》“自我意识”章所使用的两重视角——参与者视角与旁观者视角。当黑格尔承认任性阶段只有形式理性时,他所使用的正是有限的、受制于特定具体阶段的参与者视角,这种视角既无法设定唯一因素与主体相同一,亦不能对自我决定所涉及的全部因素进行并列式呈现,因而无法使用自我决定判准对任性是否自由之体现加以判定,或者说将之误判为自由之体现;相反,当黑格尔明确断言任性由于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对立而表现为一种不自由时,他所使用的是无限的、超越具体阶段的旁观者视角,这一全能视角帮助黑格尔从任性的后续发展阶段,即普遍意志阶段提前“征用”了其所需的具体理性概念,证明只有具体理性才是与主体相等同的唯一因素,并且并列呈现出自我决定所涉及的全部因素,从而使得自我决定判准在任性阶段的运用成为可能,判定任性并非自由之体现。 除此之外,值得一提的是,黑格尔对于任性所表现出的既肯定又否定的复杂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即是源于其双重视角理论。大体来讲,当黑格尔持旁观者视角时,他对任性的看法会相对比较消极。比如在本文所讨论的部分,即《法哲学原理》的导言部分,黑格尔由于持旁观者视角,因而倾向于判定任性不是自由的体现;相反,当黑格尔持参与者视角时,他对任性的看法则会相对比较宽容,比如在该书的“抽象法”一章中,黑格尔认为部分程度上既是自我决定亦是自我实现之体现的私有财产权,就是建基于任性概念之上。又比如,仍是在该书的“市民社会”一章中,黑格尔认为对任性的承认是基督教对现代西方世界最为根本的贡献,并且严厉批评了对任性采取完全拒斥态度的柏拉图意义上的理想城邦。所以,尽管我们一般会说黑格尔批评任性、断言任性并非自由的体现,但这并不等于说黑格尔对于任性持完全否定态度。黑格尔对任性的具体评价,因其在旁观者视角和参与者视角之间的取舍而定。 明确区分形式理性和具体理性是黑格尔对康德之后德国哲学的一大发展。借助这种区分,黑格尔成功洗脱了自身自由理论在自我决定判准和智性主义判准之间犹疑不定的嫌疑,但是,对于理性的这种区分同时也为黑格尔带来了自我决定判准对于任性的适用性难题。因为要想运用自我决定判准,任性阶段必须既要能将形式理性和具体理性同时并列呈现,亦要能够确定其中只有具体理性才是与主体相互同一的唯一因素。遗憾的是,在黑格尔的相关论述中,具体理性是一种需要发展实现的后天社会属性,其在任性阶段尚不存在,这导致黑格尔无法运用自我决定判准对任性是否自由之体现作出判定。 但黑格尔在任性阶段确实运用了自我决定判准,并据之断言任性不是自由之体现。对于这一显著的矛盾,笔者认为可以解释为,黑格尔之所以能够将自我决定判准运用于任性阶段,是因为他在论述任性时,并没有仅仅局限于形式理性,而是提前从任性发展的后续阶段借用了其所需的具体理性概念。使黑格尔对具体理性的提前借用成为可能的,正是他在分析任性阶段时运用的参与者和旁观者双重视角理论。也就是说,黑格尔借助双重视角理论,在任性阶段完成了对尚不存在的具体理性的提前“预支”,不但促成了形式理性和具体理性的并列式呈现,而且肯定唯有具体理性才是与主体相互同一的因素,满足了运用自我决定判准所需要的两个条件,从而解决了在任性阶段自我决定判准不能成立的理论难题。 ①本文有关黑格尔的引文,主要引自《法哲学原理》中文译本(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个别地方在译法上参照了德文版本(Hegel.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 Verlag,1970)和英文译本(Hegel.Elements of the Philosophy of Righ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并作了改动。 ②虽然不少黑格尔研究者,比如Patten,Franco等人,曾经留意到黑格尔在两种理性之间所作的区分,但是,他们大多认为两种理性实质上都源于康德式排斥内容的实践理性,因而未能将这种区分明确为缺乏自身内容的形式理性和具有自身内容的具体理性,更无从深究这两种理性之区分所隐含的对于康德式实践理性的激烈批评,即黑格尔以具体理性对应自身所谓的真正理性,以形式理性对应康德的实践理性,批评其形式性和空洞性。参见Alan Patten Hegel's Idea of Freedo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p.44-45; Paul Franco Hegel's Philosophy of Freedom.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9,pp.164-165. ③不过,单纯从理论上讲,我们仍可以有此一问,既然形式理性由于自身的形式性与空洞性无法作出自我决定,那么在任性活动中真正构成决定因素的是什么?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对此未作明确的阐述,但在其他文献中,比如在《美学讲演录》等著作中,黑格尔明确指出在任性环节中充当自我决定因素的不是意志的理性,而是冲动。“当然,‘任性’(Willkür)经常也被称为‘自由’,但‘任性’只是非理性的自由,选择和自我决定并非源于意志的理性,而是源于偶然的冲动,以及其对感觉和外部世界的依赖。”参见Hegel.Aesthetics:Lectures on Fine Art.Oxford:Clarendon Press,1975,p.98. ④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曾从正反两方面论述了“反思”(Reflection)概念。鉴于“反思”构成“形式理性”的核心,因此,对“反思”的复杂态度也反映了黑格尔对“形式理性”的复杂态度。“反思,即自我意识形式上的普遍性和统一,是意志对于它自由的抽象确信,但它还不是自由的真理,因为它还没有以自身为内容和目的,因而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还是各别的。”所以,我们也应当预先指出,黑格尔虽然批评“形式理性”,但其并未就此否认“形式理性”的积极意义与正面价值。参见黑格尔:《法哲学原理》,2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Robert Pippin.Hegel's Practical Philosoph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23. ⑤不过,如果我们认可泰勒式关于“精神”(Geist,spirit)自我发展、自我塑形,理性的内容都是由精神自然生发而来的说法,那么我们当然有理由认为,具体理性的内容并非来自于“社会”,而是来自于“精神”。参见Charles Taylor.Hegel and Modern Socie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p.40. ⑥严格来讲,如果仅仅依据1821年通行本《法哲学原理》“自然意志—任性意志—普遍意志”三分法,我们有可能会漏看黑格尔在“形式理性”和“具体理性”之间所作的明确区分,因为正如Pippin所指出的那样,黑格尔本人虽然反对将理性等同于个体的反思能力,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自己在《法哲学原理》导言中对理性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却正是如此。(参见Pippin.Hegel's Practical Philosophy,p.22)在本文看来,相比通行本《法哲学原理》对于意志发展的三分法,《1818-1819法哲学讲演录》关于“任性意志”(arbitrary will)和“普遍意志”(universal will)的两分法,反而把“形式理性”和“具体理性”的区分突显得更为显著。参见Hegel.Lectures on Natural Right and Political Science:The First Philosophy of Right.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pp.325-326. ⑦在Wood,Pippin等人看来,黑格尔对于自我决定所作的这样一种“潜能—现实”式理解,使得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将欲望和偏好等感性因素成功综合进自由概念之中。换言之,Wood等人认为,如果任性能被合理地整合进主体关于“自我同一性”(self-identity)的“计划、筹划和价值”(plans,projects and values)之中,任性亦可以成为自由的表现。参见Allen Wood.Hegel's Ethical Though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pp.48-49; Pippin.Hegel's Practical Philosophy,pp.138-139. ⑧对于能否用康德式自我决定来定义黑格尔的自由概念,学界是有争议的。比如:(1)Pippin认为,黑格尔式自由概念的关注点不在于主体能否在活动中充当第一因,而在于主体的活动“能否融入主体对自我的整体理解”(be fitted into an overall understanding of who I am),黑格尔式自由概念因而不能用康德式“因果关系”(causation)主导的自我决定来解读。(参见Pippin.Hegel's Practical Philosophy,pp.24、136)(2)Wood同样认为不能用康德来解释黑格尔式自由概念,不过他给出的理由恰好相反。在Wood看来,通过区分“自由和自律”(freedom and autonomy),康德将自律对应于主体自我立法层面的自我决定,而将自由等同于主体在不同选项之间进行选择的能力或可能性(capacities or possibilities)。与康德不同,Wood认为黑格尔取消了康德的这一区分,将自由径直等同于自律,所以Wood断言不是康德,而是黑格尔率先将自由定义为自我决定。参见Allen Wood,Hegel's Ethical Thought,p.39. ⑨许多黑格尔研究者,比如Patten,Franco等人,之所以未能提出任性阶段的自我决定判准能否成立的问题,是因为他们未能留意到,在任性活动中充当主体的仅仅是形式理性而非具体理性,而形式理性由于自身的形式性与空洞性,原本不能充当自我决定的主体。当然,针对这一指摘,Patten的拥护者可能会反驳说,在Patten那里,黑格尔的理性并不完全是无内容的,其至少是有一个内容的:“一个摆脱了所有给定的权威和欲望的主体仍然有一个行动理由:他有理由确立并维持其自身的自由和独立。”Patten正是以这一点为基础构建了自身对于黑格尔哲学的“公民人文主义”(Civic Humanism)解读体系。(参见Patten Hegel's Idea of Freedom.pp.102-103)考虑到Patten对于黑格尔理性概念的这种解读完全以《法哲学原理》的一个孤证为基础,本文不予采信。 ⑩“双重视角”理论并非本文的首创,在本文之前已有黑格尔研究专家指出,黑格尔在论述“自我意识”一章时,同时使用了双重视角。比如霍耐特就曾指出,在《精神现象学》的“自我意识”一章中,黑格尔同时使用了“旁观者哲学家视角”和“参与者主体视角”(the perspective of both an observing philosopher and the subjects involved)(参见Axel Honneth."From Desire to Recognition:Hegel's Account of Human Sociality".In Moyar and Michael Quante(eds.).Hegel's Phenomenology of Spiri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p.76-90)。Pinkard亦曾指出,黑格尔在讨论主奴关系时,曾区分了“主观视角”(the subjective point of view)和“客观视角”(the objective point of view)(参见Terry Pinkard.Hegel's Phenomenology:The Sociality of Reas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p.55-63)。问题在于,不论是霍耐特还是Pinkard,都没有将《精神现象学》的两种视角理论拓展应用到对《法哲学原理》“任性”问题的解读中来,亦即未曾留意到两种视角理论对于我们解读黑格尔的“任性”概念所可能具有的积极意义。 (11)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认为,对于康德来讲,任性(选择自由)即是自由。对于黑格尔的这种看法,Wood在其编辑的剑桥版《法哲学原理》英译本的“附释”中加了这样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注释:“康德确实认为,唯有‘任性’(Willkür,一译选择自由)而非‘意志’(Wille)才是自由的。但是,他并未借此指出当我们任性而为时,我们最为自由。相反,他指出我们的自由在于我们对准则作出选择的能力,而非在于对我们的选择能力进行立法的意志能力。”参见Hegel.Elements of the Philosophy of Right.p.3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