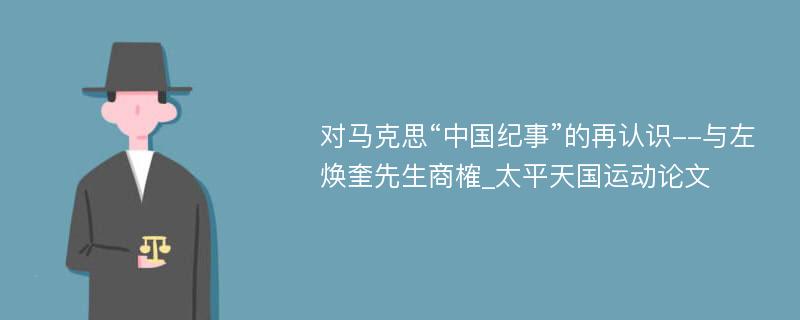
马克思《中国记事》一文再认识——兼与左焕奎先生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再认论文,马克思论文,一文论文,中国论文,左焕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597(2003)01-0125-05
关于太平天国运动的评价问题应该说是旧题重谈,已多有学者论及。近读左焕奎先生发表的《太平天国究竟如何?》一文(载《随笔》2000年第3期,以下简称“左文”),以马克思在《中国记事》一文中对太平天国运动的评价为导引,对太平天国运动发表了一些新见解。文中提出的学术界存在片面美化太平天国运动的倾向的确是存在的,也是应该加以纠正的,但左文在纠偏的同时,对马克思《中国记事》一文的理解发生了偏差,导致有些观点还值得进一步商榷。借此契机,笔者愿就本文谈谈自己的一些粗浅看法,以就教于方家。
一
马克思在其著作中多处论及太平天国运动,但最集中的论述,当是1862年6月下半月至7月初所写的《中国记事》一文(最早载于1862年7月7日《新闻报》,第185号)。不知是何缘故,过去学者们在评价太平天国运动时却鲜有论及。左文引用《中国记事》中马克思的有关论述,对已有太平天国运动的评价大胆提出质疑,这无疑有益于学术的争鸣。为讨论方便起见,现再引列如下:
运动一开始就带着宗教色彩……实际上,
在这次中国革命中奇异的只是它的体现者。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没有任何口号。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老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注:左文于该处引文出现语序倒置,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5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为了描写这些“灾星”,我们把夏福礼先生(宁波的英国领事)给北京英国公使普鲁斯先生的信摘录如下。
显然,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in persona(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正如左文所言,马克思“早就对太平天国运动有着一针见血的评价”,但马克思并非要否定太平天国运动的革命性,对于马克思在《中国记事》一文中对太平天国运动的评价,我们不能断章取义,而应从全文角度整体研读马克思评价太平天国运动的真实意旨,亦如左文所言“尊重历史”、“学术问题,不应屈从一时之需,而应多点客观分析”,如果这样,对于文中马克思评价太平天国的用语——“丑恶万状的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灾星”、“魔鬼的in persona(化身)”等的理解就不会发生偏差了。
其实,马克思早在《中国的和欧洲的革命》(最早载于1853年6月14日《纽约每日论坛》,第3794期)一文中就论及太平天国运动,说“在中国,起义连绵不断,已有十年之久,而且现在已汇合成为一种强有力的革命”。并大胆地预先断定说:“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制度的那装满着炸药的地雷上,并引起早已成熟了的总危机的爆发,这种危机,当它传播到英国国境以外去的时候,就会直接在欧洲大陆上引起政治革命”,将中国的太平天国革命和印度的1858~1859年的大起义与西方大革命相提并论。在《中国记事》一文中更是开宗明义,首先就把太平天国运动标示为“革命”,说“在桌子开始跳舞以前不久,在中国,在这块活的化石上,就开始闹革命了”。“活的化石”也就是被恩格斯所称的“世界上最古老国家的腐朽的半文明制度”[1](p16),马克思以其作喻,其喻意是中国封建制度已落后于欧洲资本主义制度整整一个历史阶段,且弥漫着腐烂的气息。对于爆发于这块古老化石上的革命的起因,马克思作出了全面科学的阐释。“运动发生的直接原因显然是:欧洲人的干涉,鸦片战争所引起的现有政权的震动,白银的外流,外货输入所引起的经济平衡的破坏,等等。”[2](p545)热情欢呼中国即将到来的“社会变革”,指出“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威权,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1](p3)亦如恩格斯所说:“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垂死的挣扎,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3](p234)敏锐地察觉到中国爆发推翻旧王朝革命的条件已渐趋成熟,认为革命是顺应历史潮流,理直气壮地宣称:“中国是被异族王朝统治着。既然已过了三百年,为什么不来一个运动推翻这个王朝呢?”[2](p545)对爆发于腐朽王朝里的太平天国革命予以了舆论上的大力支持和充分肯定。但马克思在支持和肯定这次农民运动的同时,又站在时代的峰巅,不随意拔高这次农民运动的历史地位,对有农民阶级领袖发起和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作出了科学的认识和评价,认为“这种现象本身并不是什么特殊的东西,因为在东方各国,我们经常看到社会基础不动而夺取到政治上层建筑的人物和种族不断更迭的情形”,“运动一开始就带着宗教色彩,但这是东方运动的共同的特征”[2](p545),把它科学地定位于旧式农民战争的范围。意在说明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更的终极原因,均取决于时代的经济,而任何经济制度又都有与它相应的上层建筑。在地主经济和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的19世纪中叶,以推翻专制腐朽的晚清王朝为己任的太平天国革命,因其没有创造出新社会的物质条件,所以它不可能摆脱阶级和时代的窠臼。太平天国的英雄们虽然举起了反帝反封建的大旗,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但其本身固有的农民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也会在取得阶段性胜利后暴露出来。马克思所言“实际上,在这次中国革命中奇异的只是它的体现者”,在行文中起着承接上文总领下文的作用,其“奇异”二字就意在点明太平天国革命阶级和历史的局限。
太平天国起义爆发的时代,由于列强的入侵,中国内部的经济结构、阶级关系已开始发生变化,但当时中国的封建经济仍然占统治地位,还没有出现新的阶级力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而农民阶级又不是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小农经济一方面受封建经济的压榨和排斥,不断出现分化和破产,另一方面它又是地主阶级的补充或附庸,是封建统治赖以存在的条件,其目的不是“保证”农民有生活资料,而是“保证”地主有劳动力。[4](p158)所以农民阶级的这种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在政治上没有独立的道路,正如马克思所说,农民是一个阶级又不是一个阶级,“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5](p693)。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与历代农民起义发生的外部条件尽管有所不同,但它始终是在没有新的阶级介入和领导的条件下发生、发展和失败的,随着军事斗争的胜利、地盘的扩大,农民阶级固有的弱点便会充分暴露。太平天国运动不可能超越自己所处的时代给予的限制,如《天朝田亩制度》颁布后,由于它超越时代的空想性,在太平天国控制的大多数地区并没有付诸实施,而是“照旧缴粮纳税”[6]。同样,太平天国时期的农民阶级,其社会观也不可能摆脱封建皇权主义的羁绊,如洪秀全、杨秀清等,一方面倡导平等思想,提出“普天之下皆兄弟”、“上帝视之皆赤子”[7]的思想,另一方面却又按照封建帝王将相的规格铺排自己的生活,封建制度被当成一种传统的习惯势力加以继承下来,并极力加以维护。其宇宙观也不可能跳出有神论的唯心主义的束缚,如洪秀全自称上过天,皇上帝曾赐他宝剑、金玺,命他下凡做“真命天子,斩邪留正”,把自己变成了神,成为天父上帝的次子、天兄耶酥的胞弟、奉天承运的人间君主。现实的社会存在决定了农民在反封建斗争中不可能获得先进的思想武器,从而提出切实可行的斗争纲领,亦即他们努力奋斗的任何成果都不可能超越与其小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封建阶段,他们在各方面的封建化是必然的,他们的斗争仅仅是努力去接近目标,而不能有效地实现目标。太平天国运动最终的归属自然是“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没有任何口号”。对于这种新旧封建王朝的更替,毛泽东同志也有一个类似的论断,说:“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8](p625)列宁将其形象地表述为:“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在历史上,凡是不懂得、不认识自己真正的实质,即不了解自己实际上(而不是凭自己的想象)倾向于哪些阶级的人们、集团和派别,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事情。”[9](p459)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与我国历史上历次农民运动一样,它不可能解决革命的根本问题,失败的命运无法避免,只能充当“改朝换代的工具”。但这不是太平天国领导人的责任和过错造成的,而是旧式农民起义的必然归宿。
二
我们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应立足于他们是否超越了前代,是否推动了历史前进。正如列宁所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10](p150)左文认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发表了《共产党宣言》的年代,上帝教显然不是当时最先进的意识形态”,这句话本身并不错,如果从宗教教义的严密性而言,说上帝教“甚至比不上它的直接对手儒学或基督教”也不为过,左文误在矫枉过正,进而形而上学地批判洪秀全“弄本《圣经》当‘天书’,七拼八凑地搞了个‘拜上帝教’,利用当时水深火热的民众情绪,‘拉杆子’搞太平天国运动以求一逞,将‘革命起义’误导为‘妖魔暴乱’”。的确,上帝教由基督教衍化而来,但洪秀全并没有全封不动地把它搬过来,而是站在农民的立场上,集中了农民的智慧,总结了农民斗争的经验,根据历史的具体条件和具体斗争形势,凭借基督教的外衣和某些思想材料,并结合我国一些固有的宗教习惯,创立了一个适于形势需要、能为广大农民所接受的、有革命精神的上帝教,它模糊而曲折地反映了客观现实,反映了广大群众的革命要求,是宗教迷信与小生产者封建意识相结合的系统理论。不可否认,它在通过宗教的外衣放射出革命光芒的同时,也存在着很大的缺陷,但作为农民阶级一分子的洪秀全只能走到这一步,再也不能前进了,但这已经使洪秀全超出了历代农民起义的前辈领袖。太平天国运动最终虽然失败了,但斗争的结果是它为中国社会前进开辟了道路,它的前途是“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11](p265),这也是这次农民起义能够达到历史上农民起义最高峰的原因所在。
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在“天父天兄天王”的旗帜下,其反侵略反压迫的进步性有着集中的反映。太平天国在和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中,虽非常缺乏国际知识,但坚持反对外国侵略,并且没有盲目的排外主义,坚持反对鸦片走私,欢迎正当的贸易。对此夏福礼的信中也有表露:“不错,太平军同外国人正式交往时,比清朝的官吏要好些,他们做事比较直爽,态度坚决认真,但他们的优点仅限于此。”[3](p546)当外国侵略者以协力败清为诱饵,妄图分我疆土时,洪秀全当即予以驳斥:“我争中国,欲想全图,事成平分,天下失笑,不成之后,引鬼入邦。”[12](p838)断然拒绝侵略者的领土要求,伸张了民族正义。就连曾国藩都看到,“夷人畏长毛,亦与我同”。[13]其斗争水平比几十年后的义和团运动高出了许多。左文以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处“在那‘鹰眼四集寰向吾华’的国际形势下,维护国家统一,团结一致,抵御外侵,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应是衡量爱国与否的主要政治标准”为前提,提出“历史的教训是‘内乱’往往带来的是‘内耗’”,进而认为“从这样的历史环境下来评价,对太平天国这段历史,也不应全部肯定,更不应随意拔高”。左文虽未明言,但字里行间却已把太平天国运动归之为“无益于国家整体实力的加强,更无益于中华民族团结一致对付入侵的强敌”,全然不顾太平天国的失败是中外反动势力共同绞杀的事实。按左文的逻辑推断,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战败,太平天国的领袖们似也应承担一份责任,读来令人费解。左文实际上陷入了一个自设的误区:借口不要“脱离当时历史条件,不作具体分析,说好一切都好,说坏一切都坏,随意美化或丑化,搞绝对化的‘一点论’”[14],离开“质”的界限去对待客观事物,造成了主观世界的混乱。试问,左文既然将太平天国革命归之为“内乱”、“内耗”,岂不是要肯定清政府“借师助剿”的“创举”?岂不是在实质上否定了太平天国运动的革命性?
太平天国运动果真如此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太平天国既捍卫国家主权、民族独立,又高举“奉天诛妖,斩邪留正”的大旗,其业绩彪炳史册。太平天国通过与侵略者兵戎相见,对侵略者的本性及其对中国人民的危害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如李秀成总结出“防鬼反为先”[12](p839)的思想,洪仁玕沉痛地认识到“我朝祸害之源,即洋人助妖之事”[12](p853)。虽然太平天国提出的“妖”、“邪”还不可能是一个明确的阶级概念,但它把清朝皇帝、官吏、劣绅视为“妖”,把当时社会存在的赌博、吸食鸦片、奸淫等丑恶现实列为“邪”,将其作为打击对象和清除目标,无疑具有反封建统治的正义性。
三
在太平天国革命时期,起义农民沉重地打击了豪绅地主。据曾国藩情报机关编纂的《贼情汇纂》记述,太平军凡攻城略地,对为敌的兵勇吏役“必残杀脔割,以逞其意”,“以天下富室为库,以天下积谷之家为仓,随处可以取给”。[15]太平军所到之处,在政治上消灭了地主阶级地方政权,扫荡了团练,镇压了官僚豪绅;在思想上揭露和斥责了清廷的黑暗,宣扬了平等的思想;在经济上用贡献、打先锋、派大捐等方式,剥夺了地主浮财。所有这一切给予各地农民群众以极大鼓舞,为此,曾国藩惊呼“江西民风柔弱,见各属并陷,遂靡然以为天倾地坼不复,作反正之想,不待其迫胁以从,而甘心蓄发助战,希图充当军帅、旅帅”[16]。但单纯的农民革命好像是一场暴风雨,可以给封建秩序以严重的破坏,但它不是按明确的阶级路线,有计划有策略地进行,而是在革命现实需要的引导下进行的。正如列宁所说:“农民过去的全部生活教会他们憎恨老爷和官吏,但是没有教会而且也不能教会他们到什么地方去寻找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17](p181)农民阶级毕竟是一个自在的阶级,不是一个自为的阶级,在其革命过程中种种矛盾和局限性不可避免地会暴露出来。
天京事变后,为抵抗清军乘虚而入,太平军招收了大股的游民以补充兵力,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太平军组织的松散和纪律的松弛,给了游民意识滋长以适宜的气候和土壤,这时的太平军已无力改造游民,反而不断受到游民习气的腐蚀,游民扰乱民间的事时有发生。《李秀成自述》中就谈到太平军正规部队扰民之事:“刘、古、赖三将杨辅清害起,百姓死者此等之人。主不问政事,不严法章,不用明才佐政,故而坏,由此等之人坏起。后坏民是陈坤书、洪春元之害。陈坤书是我部将,我有十万众与他,此人胆志可有……而害百姓者,是此等之人也……害民烧杀,实此等人害起。前起义到此,并未有害民之事,天下可知!”扰民事件自辅王“杨辅清害起”,说明辅王的部队比忠王的部队腐化得更早一些。游民习气对太平军的腐蚀已非个别现象,以至“盗贼蜂起,逢夜间城内炮声不绝,抢劫杀人,全家杀尽,抢去家内钱财”。天京城内也有公然抢劫的事件发生。对于游民问题毛泽东同志有过一段精辟的论断:“这个阶层是动摇的阶层;其中一部分容易被反动势力所收买,其另一部分则有参加革命的可能性,他们缺乏建设性,破坏有余而建设不足……”[8](p646)为了争取生存权利而自发组织起来,在革命形势出现的时候,他们有的成为革命的积极参与者,通过革命形式发泄对现实社会秩序的仇恨,而他们的行动往往只限于经济的要求,缺乏远大的政治目标。所以,马克思从太平天国革命是没有先进阶级领导的自发群众斗争,它没有可能从根本上彻底改造游民阶层的破坏性角度出发,说“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
此外,太平天国实行的一些过激政策,也人为地制造了社会动乱。在太平军内部,自金田起义开始实行男女分营,这种营馆制度一直坚持到后期。据潘锺瑞《苏台麋鹿记》载:“金陵之陷也,贼勒民分别男女设馆,不许同室,而日给以米,男之精壮者为牌面,老幼为牌尾。至苏城却不尽沿此例,间或设立女馆,无非虚言恫喝,尽将人家妇女赶逐,逼至一处,平素不出闺门不惯行走者,已极艰苦,而粒不给,多至饿死,或借立馆为名,诡词欺骗,许妇女随身携带包裹,既驱入馆,则遍收财物以去。故有今日立馆明日便散者,有早晨设馆午后旋逐者,有驱出此馆引入彼馆而两处皆空者,这边走,那边走,无所适从,哭声载道,而彼方恣观而窃笑之。”[18]使得城市居民怨声四起,“有子有孙不能顾,有父有兄不同住,起居饮食各自谋,疾痛苛痒向谁诉?[19]破坏了人们的天伦之乐,造成了粮荒,加之上文所言游民扰民,最终导致“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老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至于左文提及的马克思用语——“灾星”、“魔鬼的in persona(化身)”,则要根据上下文整体来理解。请注意,马克思在用“灾星”一词时为引起读者注意不仅打上了引号,而且用复数指示代词“这些”而非单数指示代词“这个”进行了限定,很显然,马克思文中的“灾星”一词是特指上文所言太平天国革命中表现出的一些阶级的和历史的局限性。而马克思关于“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in persona(化身)”的论述,则是马克思对太平天国革命的批判总结。但马克思对太平天国革命的批判又是站在一定历史高度的,它申论说:“但是,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阐明了“这类魔鬼”即太平军在革命中表现出的阶级和历史的局限的产生有着历史的特殊性和必然性。
通过以上讨论,我们不难发现只有透过现象看本质,避免望文生义,才能对马克思《中国记事》一文有一个正确的释读,从而准确地把握马克思关于太平天国运动评价的论述。片面美化太平天国的倾向是不科学的态度,但只强调或者只看到其缺点,同样是不符合客观事实和不能揭示规律的。
[收稿日期]2002-11-02
标签:太平天国运动论文; 太平军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历史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清朝论文; 洪秀全论文; 革命论文; 太平天国论文; 远古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