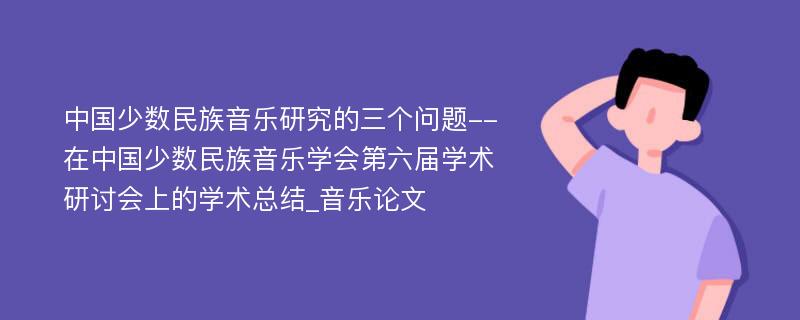
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三题——在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第六届学术研讨会的学术总结发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民族音乐论文,少数民族论文,第六届论文,学术研讨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工作向广度和深度发展,研究队伍日渐壮大,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是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第六届学术研讨会的显著特色。这次研讨会的论题广泛,中外学者聚集一堂,学术气氛浓烈,通过小组宣讲论文,大会发言交流,以及大小会议自由讨论,把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的学术研究活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特别是少数民族音乐史、宗教祭祀音乐及壮侗语族音乐三个专题的深入研究,无论是在研究问题的方法论方面,还是在少数民族音乐的理论建设上,均比以往的水平有明显的提高和进步。这里,仅就这三个方面谈一些粗浅看法。
关于少数民族音乐史研究
系统的编纂中国55个少数民族的音乐通史,是一件前无古人、具有开创性质的巨大工程。这是我国社会主义音乐事业的需要,是中国音乐史学建设的重要内容。如果说前几年在论证编纂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时,尚存在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认为时机还不成熟;那么,现在对如何加速编纂少数民族音乐史的进程,已成为音乐界的共识。人们不仅在认识上统一了看法,而且参加撰写史稿的学者们,近几年来,奋发努力,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令人高兴的是,自1993年8月在抚顺举行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第五次学术研讨会上,一部分史稿撰写者提交一些成果,井交流编史经验心得后,两年来又有一批民族的音乐史脱稿。截至目前为止,已有壮族、蒙古族、裕固族、白族、回族、水族、鄂伦春族、京族、土族、土家族、藏族、侗族、傣族、赫哲族、德昂族、朝鲜族、维吾尔族。仡佬族、彝族、畲族等20个民族的音乐史已全部完成或基本上完成;西夏、辽、金三个在历史上己消逝的民族的音乐史稿也完成交稿。预计今年底可望完稿的有瑶族、仫佬族、俄罗斯族、布依族、景颇族、傈僳族、苗族、布朗族等8个民族的音乐史稿,此外,高山族、纳西族、保安族、东乡族、满族、达斡尔族等民族的音乐史稿,均在积极筹划中,有的已动笔。
在不长的时间内,就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实在令人高兴。这样,我们就有可能按原订计划分上、下两册分期出版。史书编委会今年底以前将对先期完成的占55个少数民族一半的28个民族音乐通史进行审定,或加工充实,或组织力量修改,力争明年第一季度编成上册交付出版社出版。如果工作进展顺利的话,明年底,我国第一部少数民族音乐史的上册就可面世。这无疑是我国音乐史学建设的重大成果。
在此基础上,我们将继续抓紧下册的编纂工作,我们深信,在广大音乐家的关注特别是撰稿学者的努力下,全部少数民族音乐通史的编纂工作,在1997年完成是有把握的。当然,上下册的这种编辑体例并非“理想”的方法,理想的方法是待全部史稿完成后,按语族或地域分类编排;但我们采取了“现实”的方法,即将先期完成的史稿编入上册,尽快出版,以满足广大读者对各少数民族音乐通史的迫切需求。
编纂少数民族音乐史是一件十分艰巨的工作。近几年来少数民族音乐史的撰写实践证明,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史稿的撰写工作必能有所突破。许多民族的史实不仅有新的发现和发掘,而且撰稿者的历史意识,史学观念、理论思维,均引起了许多变化。发现了许多新资料,寻找到有价值的新方法,进而形成了新的见解。这些都有力地推动编史工作的进展。另一方面,我们虽有司马迁编著《史记》以来众多史书的经验可资借鉴,又有一些音乐学者编纂汉族音乐史的心得可供参考;但鉴于少数民族音乐史的编纂是崭新的事业,加之各兄弟民族音乐史料奇缺,又缺乏专门从事撰写少数民族音乐史的史学家,因此,在这几年间所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是可想而知的。为了进一步提高少数民族音乐史的编撰质量,需要我们对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
一、少数民族音乐史的分期问题
对各少数民族音乐史的分期是否得当,是史稿成败的关键之一,也是史稿的编写框架是否科学的一大前提。
由于各民族社会发展历史的不同,音乐史的分期也应各有特点。
分期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各少数民族音乐史的断代是否需与汉族相应的断代一致?从已完成的近20部少数民族音乐史来看,这个问题已得到了回答。即与汉族历史相一致的,当然可以采取对应的办法。但事实上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社会发展历史存在诸多的差异。如同是原始社会,然而各民族经历的年代却有长有短。有的少数民族的历史发展阶段各有其独特之处,如侗族没有经历过奴隶社会,彝族(四川凉山)则没有经历过封建社会,它“一步跨千年”,从奴隶社会直接进入到社会主义时代;北方一些马背民族所经历的社会历史显然与中原农耕社会存在不少差异。这样的事例是不胜枚举的。
因此,各民族音乐史的分期,应当按照各民族的实际情况来确定。只有这样,各民族的音乐史才能写出自己的个性和特色。
二、史稿撰写中史与论的关系问题
这里所说的史与论的关系,包括两方面的意思:一是音乐历史与音乐概论写法的区别:二是史与论点的关系问题。
关于音乐历史与音乐概论写法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因为许多少数民族的音乐史料十分缺乏,出土的音乐文物也不多,这就造成纵的历史叙述常常过于简略,而横向上对各种音乐品种,如歌种、乐种、曲种、剧种和民俗音乐的介绍却很详尽。这样的史稿,实际上成了××民族的音乐概论。
我们认为,写史的变迁发展,一定要尽可能地占据史料和口碑材料。
对一些音乐发展较丰富的民族的音乐,特别是本世纪50年代以后,可采取民间音乐和专业音乐两条线索进行编写,更能清楚的看出音乐发展的面貌。
其次,史与论的关系还表现在对两者的辩证认识上。对“论从史出”、“以史带论”、“史论结合”这些观点在少数民族音乐史如何正确处理,是一件需要认真研究和对待的问题。
在我们看来,从认识的根源来说,“论从史出”是符合客观事实的。因为,历史理论不是从某些史稿撰写者头脑中凭空产生的,而是来源于各民族的音乐历史实际。只有深入各民族音乐历史实际,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从这个意义上讲,“论从史出”对于纠正那种不愿在史料上下苦功夫,只从框框条条出发的倾向,无疑是有积极作用的。但“论从史出”这个提法,没能明确说明理论在史稿撰写中的指导作用,如果拿“论从史出”作为拒绝正确理论指导的借口,那是对史论关系的莫大误解。
“以论带史”的观点在语义上可能使人产生某种含混,如果据此认为可以把理论观点驾临于历史实际之上,能“带”着历史随意转动的话,显然,这种提法是很偏颇的。但若把“以论带史”理解为理论对音乐史学具有指导作用,则尚有可取之处。
我们主张“史论结合”的办法,即科学理论要与各民族音乐历史实际紧密结合起来。遵循这一原则,少数民族音乐史的研究和撰写工作,一定能达到科学性、学术性均较完美的质量要求。
三、处理好跨国境、跨地域的少数民族音乐史稿的编纂工作
我国许多兄弟民族的居住现状,是按照各民族世世代代的分布而居的。除了赫哲族、羌族、门巴族、珞巴族、东乡族、保安族、水族、仡佬族、仫佬族、土族等十余个民族,是集中居住在某一个省(区)外,大多数民族的分布,都是跨越国境,或跨省(区)、或在本地域内跨越地、州、县。这种复杂的情况,自然给音乐史的编纂工作带来不少困难之处。
处理好跨国境、跨地域的少数民族音乐史编纂的关系,既是工作问题,也是学术问题,亦是直接关系到各民族音乐史成败的重大问题。
对外来民族的音乐史撰写,我们已经寻求到了妥善的方法,对朝鲜族、俄罗斯族、乌孜别克族、京族的音乐史撰写,是从这些民族迁入中国境内写起。至于这些民族以往的音乐历史渊源,则可视需要而写,或在前言中概略的勾画,或在正文的某些章节中涉及。
跨国境同族异流(布)民族的音乐史稿,似可参照前述外来民族的办法对待,即一个民族跨居几国的,如北方的蒙古族、哈萨克族、维吾尔族,南方的壮族、苗族、侗族、瑶族、傣族、景颇族等,在我们的史稿中只写中国境内的这一民族的音乐发展史。当然涉及到境外的同一民族的音乐,亦应在以我为主的前提下有选择的写入,以使读者对同一个民族的音乐发展史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对于我们撰写各民族音乐史来说,感到难度最大的是国内跨地域的民族。由于这次撰史的时间紧迫,经济力量有限,不可能组织编纂组对这些民族的音乐史进行集体撰写,也难于重新深入各地访问调查,而采取由执笔者独立撰史。这对于资深的学者来说,尚可驾驭,但对一般的学者而言,则会感到困难。比如,藏族横跨五个省(区)的广袤藏区,藏族音乐史不仅要介绍藏族的大本营西藏的音乐发展情况,也应对分布在青海、四川、甘肃、云南的藏族音乐历史状况有所反映。苗族也是这佯,苗族音乐史应写出黔、湘、川、桂等省(区)苗族音乐的全貌。又如彝族分布在川、黔、滇诸省,一部完整的彝族音乐史,亦应全面书写出这三个省彝胞共同创造的音乐历史。土家族的音乐情况也比较复杂,除了横跨川、黔、鄂、湘四省广大地域外,比起其他兄弟民族来说,还有其更为复杂之处。近十多年来,随着民族政策的落实,成千上万的土家族同胞寻宗认祖,使这一民族的队伍剧增成为我国人数最多的少数民族之一。这种情况,要求音乐史家,特别是撰稿学者要更进一步调查了解土家族音乐的历史渊源及流布情况,这便增加了撰史的难度。其他跨省(区)的民族无不如此。这就要求执笔的学者广采博纳,尽可能地占据史料,利用各种方式,或向有关人士征集材料,或广泛查阅史籍及建国以来出版(内部的、公开的)的文献书籍,包括80年代以来编纂的各种民族音乐集成的资料本及正式出版的卷本。
至于某一省(区)内分布在各地、州、县的民族,可能比跨省界的民族音乐史的撰写要便利一些,不过,其难度也是十分显然的。如傣族,在云南就分布在西双版纳、德宏两个自治州及红河州的部分地区。如何全面反映中国境内的傣族音乐史,也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现在己有两部傣族音乐史脱稿。将两部合二而一,综合加以编纂,是妥贴的办法。另如羌族,除了主要聚居在四川省茂汶羌族自治县外,周边的县(市)也散居着许多羌族同胞,撰稿者的目光必然会全面审视这一古老民族的音乐纵向的发展史和横向的传播面,写出一部有学术价值的羌族音乐史来。
编纂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过程中,涉及的问题很多。以上仅是近年来少数民族音乐史研究和撰写中遇到的比较突出的主要之点,只有处理好这些问题,各民族音乐史才具有独特的个性和特色。
关于宗教祭祀音乐研究
各民族的宗教祭祀音乐研究,是近几年来我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之一。
如果说,80年代我们对宗教祭祀音乐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那末,90年代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则已逐步深入,并取得阶段性的成果。
宗教是我国诸多少数民族精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人民群众对宗教的信仰已成了他们重要的精神依托,或者可以说是他们精神力量的重要支柱。
不少民族音乐学家对宗教音乐进行研究都有正确的指导思想。他们一方面把宗教音乐作为宗教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也把宗教音乐作为各民族传统音乐的重要内容。可以说,忽视对宗教音乐的研究,是缺手缺腿的不完整的传统音乐研究,也不可能全面地反映一个民族的音乐发展历史。
宗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政治文化现象。我们认为,宗教作为一种文化,具有多方面的内容和多种层次的结构,其历史价值表现为多义性和多重性。我们应当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把宗教作为一种历史积淀的文化现象,作为各民族历史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一部分加以考察和研究,把宗教祭祀音乐作为各民族传统音乐的组成部分进行考察和研究。这些不仅有着资料价值、认识价值,更有意义深远的多功能和多学科的学术研究价值。
我国各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十分广泛,既有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道教,信仰覆盖面最广的是各民族崇尚的原始宗教(或称前宗教、准宗教)。音乐在这些宗教祭祀活动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提交此次研讨会的23篇论文,从各种角度讨论了宗教音乐与宗教、宗教祭祀音乐与民间音乐、宗教祭祀音乐与社会的关系,还对宗教祭祀音乐的沿革、现状及流传方式、音乐形态、乐器等发表研究心得和成果。
我们对宗教祭祀音乐的研究,具有如下特点:
一是遵循唯物辩证法的思维方式,探究宗教祭祀音乐形成的远因和近因,以及宗教祭祀音乐的社会功能和审美价值。
二是把宗教祭祀音乐作为一种综合性的文化进行审视。在许多少数民族中,宗教祭祀的神职人员正是该民族高文化水平的代表者,他们既是宗教的传播者,又是宗教祭祀音乐的创造者。他们常常从民间音乐中吸取养料,或者将传统的宗教祭祀音乐与当时流传的民间音乐融合在一起。有的民族的民间音乐可能已经失传,但还保存在寺院或祭祀活动中。今天我们要寻觅传统民间音乐,还必需求助于宗教祭祀神职人员,从他们那里收集到活着的民间音乐。
鉴于宗教祭祀音乐是一种十分神奇的社会文化现象。我们对宗教祭祀音乐的研究,除了要掌握多种学科的知识外,还应保持清醒的头脑。因为我们不是为研究而研究,研究的目的是为了从宗教祭祀传统音乐中了解各民族的音乐财富,进而分辩哪些值得继承借鉴,哪些应当予以扬弃。
宗教祭祀活动的复杂性在于,它既有迷信的一面,又有纯朴善良信仰的一面。因此,研究宗教祭祀音乐,应当防止简单化,或一概崇之为经典之作,或不分清红皂白地斥之为封建迷信的产物。这两种看法都有其片面性,值得今后研究工作重视。
关于壮侗语族音乐研究
把壮侗语族诸民族的音乐作为一个专门课题进行探讨,是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向纵深发展势头的一个标志。
壮侗语族跨越东南亚、西亚六个国家的民族,在我国则有桂、黔、湘、滇、海南五个省(区)的壮、布依、傣、侗、水、仫佬、毛南、黎八个民族及茶山瑶、海南临高人及村人。从宏观上研究复盖着八千多万壮侗语族诸民族的音乐文化,探讨它们在音乐上的共性及不同之点,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也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
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为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工作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好机遇。如果说我们过去大多局限于闭封式、个体的、单向的研究方式,近些年来,随着学术交流活动的频繁开展和研究者视野的扩大,对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已逐渐拓展到了同源同根语系、语族、语支的诸民族研究阶段,各地逐渐形成了研究群体,专攻某一语系、语族或语支的音乐研究,已初见端倪,有的已是成果斐然,令人瞩目。
属于壮侗语族的诸民族在同一语族的音乐文化圈内,千百年来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音乐文化传统,至今仍闪烁着熠熠的发亮的光彩。生活在这一语族诸民族的人民群众是如何缔造这些既同源同根、近血缘,又风姿各异的音乐?它们为什么在现今时代的潮流中,在各种现代文化的竞争冲击下,依然保持着艺术魅力,继续在人民群众中流传,成为人们精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食粮?这一切都成了民族音乐学家们孜孜不倦进行探索的奥秘。
大家对壮侗语族音乐的研究成果,比较全面地展示了学者们近年来的收获,内容丰富,观点新颖,文采飞扬,无疑对今后更加深入的研究是一个新的起点。
我们感到在今后研究中,应重视以下两点。
一、处理好研究音乐文化背景与音乐的关系。大家比较重视在分析音乐形态时加强对文化背景的阐述,这当然是值得肯定和提倡的。但另一方面,也有个主次关系问题。就像一个高明的摄影(像)师一样,展现在画面上的主体是十分突出的,而人物或图像的自然背景又是清晰和有层次的,如果主体糊模不清,或者在构图中不显著,我们不能认为这是一张成功之作。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也许与摄影(像)有某些共同之处。如果音乐形态的地位不明确,很难使人们获得音乐分析的深刻印象,但文化背景若过于疏略,则研究容易停留在平面、或浅薄的层次。在对各语族诸民族音乐研究中,既要注重文化背景的共性,更突出由于语族和民族的不同造成的各具特色的音乐形态上的差异,即各民族音乐的个性。
对各种音乐形态的研究,过去比较着重于表层形态的分析,这显然是不够的,还应在深层形态上下功夫,才能把各民族音乐的本质特征揭示出来。
二、对壮侗语族诸民族音乐的研究,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从某种程度上讲,对这一语族的综合及比较研究才刚刚开始。所谓综合比较研究,是一方面把一个民族的音乐放在这个民族悠长的政治、经济、文化(包括民俗)等各种历史中加以论述;另一方面,又要与其他近血缘民族的音乐文化进行横向的比较阐释。在纵横交错,古今比较中全面了解认识一个民族的音乐为什么能独树一帜,而不被别人融化,取而代之的地位。
这次研讨会期间诞生的侗台音乐研究会,可以说是壮侗语族诸民族音乐专题研究的直接产物。我们热切希望,侗台音乐研究更上一层楼。
壮侗语族诸民族音乐研究给我们另一个启示是,按语族音乐综合研究,已成为90年代中期民族音乐研究的必然趋势。我们还可以组织学者对我国分属于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南亚语系、南岛语系的诸民族的音乐进行研究。
再过五年,人类将进入纪元的第三个一千年,我们深信,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研究将随着历史的前进步人新的纪元,迈向新的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