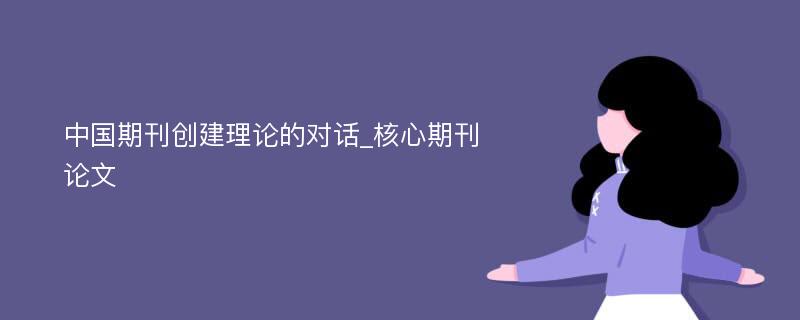
关于创建中国期刊理论的对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期刊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出版广角》记者(以下简称记):隐约记得6年前您曾提出核心期刊这个话题并展开过论述,而且当时还引起了不小的讨论,当初您是怎么想到要提出这个问题的呢?
王振铎(以下简称“王”):这个问题说起来有点巧。1999年,我就中国期刊现状研究中遇到的理论问题概括出5个课题:一是期刊作为文化传播媒介,它究竟是一种什么现象,是社会现象,还是人文现象?是科技现象,还是自然现象?二是当时已经流行甚广的“核心期刊论” (以下简称“核刊论”),究竟是不是科学的期刊理论?三是期刊的生命何在?在于质量,还是在于传播?抑或是在于创构媒介的编辑,即以主编为首的编辑部?四是期刊的定位问题,只有一种定位,还是有多种定位?谁是期刊定位的主体?为谁而定位?五是期刊的总体方针、布阵分类、编辑宗旨、目标对象、发凡起例、个性特色,包括栏目设置与专栏的编创问题,即期刊媒介的编辑创新与发展繁荣应走什么样的道路?或者说我们应当持有一个怎样的期刊发展观?
我带着这些课题在研究生的教学中,写出了《期刊五论》这么一个授课大纲。在给北京的编辑出版学研究生班讲过几次后,讲稿传到了《出版广角》编辑部。那时“广角”的主编好像是刘硕良先生,我们俩还不认识。编辑部采用了“五论”的第二部分,以《质疑“核心期刊论”》为题,发表在“广角”2000年第12期上。在《这一期……》的编者导语中,主编写了一段话:“一家之言听多了,难免会在实际工作中产生偏向。目前‘核心期刊论’在评价杂志、评定职称和评比科研成果时,已有些被奉为真经的意味。王振铎对如此提法和操作的科学性提出质疑,从一个侧面指出期刊评价体系中存在的误区,可读,可思。”编辑意图明确,也颇客观。不久,《南方周末》、《新华文摘》、《电器时代》、《信息平台》等报刊全文转登了《质疑“核心期刊论”》,引起全国几十家报刊更为广泛的讨论。记得当时我接到过一个陌生人的电话,问我发表这篇文章有什么背景。我说我只是研究编辑学出版学的一个教师,不知道有什么背景。后来,我接到一个《质疑“核心期刊论”》的论文获奖通知,还有3000元奖金。但是,6年时光过去,在现实生活中“核刊论”依旧泛滥,并且还出现了新的“核心期刊”制造厂家,“核心”的名目和圈子越来越多,我们的“核心”制造业似乎越来越发达。刊物评优分级、论文评比、职称评定,甚至硕士、博士能不能毕业,依然还都要看是不是“核刊”,或者是不是在“核刊”上发过几篇文章。在“核刊”发表文章所支付的版面费、审稿费、编辑费、赞助费更是变本加厉……我有点不相信什么“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了。有人说现在好像是一个吃喝玩乐的时代,论文讲道、编刊出版、评职评奖似乎也是在“玩”而已,“核心期刊”好像成了那些“玩家”手中的一张牌。
记:从期刊理论上来说,那些所谓的“核刊论”能否站得住脚呢?
王:这个问题恐怕还要从头说起。 20世纪30年代,英国一家图书馆的文献统计学家S.C.Bradford为了解决馆藏科技文献资料如何从众多的杂志上搜集并被充分利用的问题,提出科技文献的聚散分布有一定的规律,登载某些专题文献的期刊可能会被区分出载文数量较集中的核心区与较为分散的相继若干区,呈现出1:n:n[2]的现象,由此奠定了科技文献计量学的基础。它主要解决的是不同学科专业的文献数量分布问题,对科学研究者如何检索某一专业的文献,颇有指导意义。50年后,这一文献计量学理论被我国的图书馆学家译介过来,称为“布拉得福定律”,并生发出一套“核心期刊理论”。“核心期刊论”原本不是媒介传播学所研究的期刊理论,也不是编辑出版学所研究的期刊媒体理论,不能用来作为创办、编辑、管理和评价所有期刊的指导思想,更不能直接用来策划期刊、经营期刊、创新期刊和评估期刊,否则将导致重重荒谬,搞乱国家的期刊管理政策和期刊方阵结构,甚至引发种种期刊腐败现象。一把菜刀“玩”不出十八般武艺,弄不好反而乱了自己的阵脚。
记:但是长期以来,却有不少人误把“核刊论”当成科学的期刊理论,甚至误把它当成科研论文评价理论。更有甚者,还把它误定为专家学者整体学术水平和专业技术职务资格的评聘依据与鉴定指标。尤其是一些掌握一定权力的管理部门及其行政领导者,还据此制定了不少评估期刊、评价论文和评定职称的地方性、行业性、法规性的文件,作为条条框框,误导实际工作,成为“核刊论”大肆泛滥的推波助澜者。
王:不错。“核刊论”原本是情报计量统计理论,属于“文献计量统计学”范畴,为图书馆等信息资料管理部门筛选收集相关文献资料是它的基本特质与主要功能。一个具体真理超出了它的适用范围就会变成谬误。“核刊论”作为“文献计量统计学”中科技文献来源的一个优选统计方法,用于遴选某些科技文献来源的那些数据,只能表明哪种学术刊物登载哪种学科论文的数量和水准,并不能表明这种刊物与其他不同学科、不同类别的刊物之间在本质和价值方面有什么根本性的差别。数据则是质量变化过程中暂时的某些数量指标。比如水在O℃~100℃为液体,高于100℃为气体,低于0℃为固体,其基本品性和质素H[,2]O并无根本区别。我们不能说哪一种温度情况下的水是“核心”水,其他温度条件下的水是“边缘”水。对于判断事物的本质来说,数据不是万能的,也不是惟一的,简单片面的数据或处理不科学的数据更是不足为凭的。“核刊论”把某些科技期刊所载论文的三个统计数据,即某刊所载某类论文的总数量、其他报刊的转载量、引用量 (包括自引与驳引等),作为判断是否是“核刊”的两极化标准,并不是很科学。即使这三个数据都是真实的量,如果该刊跨越期刊生态品类,超出其所属类别、层次、宗旨和特殊性质而蔓延到整个期刊的生态范围,那就如同某些特定地区的某一特有群种入侵到另一个生态领域,会疯狂破坏其生态环境。“核刊论”就好比“文献计量学”生态中的一个“群种”侵入到“编辑出版学”乃至整个传播媒介学的生态环境之中,传染了或排斥了其中原本很好的或发展不太充分的期刊出版群种。虽然目前它还没有来得及侵蚀政治性特强的报纸这一出版群种和传统根蒂特深的图书出版群种,但它的逻辑趋势是要把一切出版物或传播媒介都分成“核心”或者“边缘”,并以这种非此即彼的“两极化”判论,把大多数期刊媒介或者绝大多数出版物推向“边缘化”。显然,这对读者、对整个出版文化结构的发展是没有多大益处的。即使对图书馆选购和收藏学术文献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那也要以对众多“非核心”读物的舍弃为代价。而舍弃了太多的“非核心”,那“核心”还能够存在吗?还能叫“核心”吗?它必将慢慢地或者很快地蜕变以至衰亡。所以,早期“核刊论”的西方研发者在欧美从不越过“图书馆与情报管理学”关于科技期刊文献计量统计的应用范围。而它的中国仿制者却为了扩大其额外效能,比如“寻租”,而应用于社科类期刊、人文类期刊、文化普及类期刊等等“分野”,并且在繁琐的计量统计中,又暗暗附加了不少主观主义的“平衡”、“权重”、“微调”、“特定”等等“影响因子”,使数据的“量”在显示其“质”的程度上大打折扣。目前中国几家“核刊论”的评“核”指标已由西方原来的三项,增扩到六项。倘若再加上“后门”、“赎买”、“关系”、“权威”等等因素,其评“核”指标的数量就更多了。而评估指标的元素数量越多,就越容易陷入“测不准原理”。事实上我国目前已有许多单位自定标准、自行发布、自己使用的所谓“核刊”圈子,走进了遍地皆“核刊”的境地。一个果实一个核,期刊怎么会有那么多核呢?从期刊编辑的实际情况看,事实上也是“核刊无核”或“核刊不核”。无论哪一家期刊的编辑都不是尊奉着某一个“核心期刊”转圈圈的,某一个“核心期刊”也都不要想着别的期刊紧紧围绕自己打转转,因为任何期刊都是以办出自己的个性和特色而取得基本生存权的。
记:到目前为止,国内已有几十家报刊发表了上百篇批评“核刊论”的文章,多方面指出“核刊论”在我国期刊界纵横泛滥,扭曲了人们的思想,造成相当严重的混乱,危害了刊物评比、论文评奖、职称评定工作,导致编辑腐败、学术腐败与专业职务人员晋升评定的腐败等不良后果。但是,“核刊论”却依然故我,流毒越来越厉害。谁都可以恣意划定“核心期刊”名单,或者把“核心期刊”更名改姓,随意划定一个“圈子”。凡“圈子”里的刊物,就是不叫“核心”的“核心”,其中发表的文章就可以不加评价地获奖,就可不分青红皂白地算作评定职称的标准依据。这似乎已经形成了恶性循环而无法解脱的“怪圈”! 事情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呢?
王:这都是因为我们没有科学的期刊理论。企图用别人的某一种理论工具来解决自己的一揽子问题,结果往往事与愿违。
“核刊论”原本是欧美提出来并在一些图书情报部门作为文献来源数量统计使用的,并没有像在我国这样超常出轨,导致荒谬,泛滥成灾。而且随着现代信息控制技术水平的提高,筛选和搜集信息工作越来越降低了对“核刊论”的需要。期刊的编辑出版越来越走向人性化。大众化、小众化、专门化、个性化是各类期刊不同的追求向度。期刊作为一种重要的传播媒介,其根本目的是为社会改新、为广大人民多样化的文化需求提供服务的,在我国怎么能越来越变为“制世”、“治人”的“紧箍咒”了呢?我无意探究“核刊论”的制造者、推行者、误用者和被迫执行者的动机与原因,也无意探究有关管理者和行政者的动机和原因,倒是愿意更多地探讨一下我们社会文化中某种陈陈相因的理性和习性,这样更易于弄清我们在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时的不科学态度问题。现实情况是,在某些看起来并不复杂的学术问题上,我们却往往神秘兮兮的将其复杂化,甚至以“量化”的名义将其变本加厉地繁琐化,并将这锁链套在自己的脖子上,越拉越紧。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以科学的发展观来学习西方发展着的某一具体的科学理论与方法,而是习惯不经我们胃液消化,生硬地“横移”,随意“滥用”,这样往往走向荒谬、陷入怪圈而难以自拔。而我们的“党八股”之类的学风,由于图简单、省力气,马虎了事,也是导致“核刊论”走向荒谬、钻进怪圈、乱摆迷阵的又一种巨大的社会自堕力。
记:能不能这样说,“核刊论”是期刊自身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随着新技术的不断发展,期刊界面临的问题将会越来越多?
王:传播学认为,媒介的创新,必然导致媒介理论的创新。期刊作为一种介乎传统图书与现代报纸之间的中档媒介,有其独特的优势,它是20世纪世界文化传播的主导媒介,兼有科学知识、新闻信息、文化商品的综合性特点,人称“20世纪是期刊的世纪。”但随着电脑和网络技术的发展,期刊也疯魔一般飞进电视、网络和超市,成为与其他媒体“链接”起来的21世纪“多媒体”构件之一。看来媒介发展的历史的确是补救性的、累加性的、不断增生传播价值的发展过程,而不同于一般物质技术产品的替代式、淘汰式发展方式。至少在以世纪为时间单元的历史过程中,一种媒介不会完全被另一种媒介所取代。这是几千年来社会文化媒介发展的历史所证明了的一个规律。加拿大传播学家M.麦克卢汉与他的美国学生莱文森一再用“延伸——互补”理论说明了媒介增生的发展逻辑。
在我国,期刊媒介诞生至今仅有 214年,而西方现代期刊也才有340多年的历史。从品种数量方面看,我国期刊还不到美国期刊的半数。年人均期刊订阅数发达国家是10册~30册,我国仅有 2册。其发展的空间还大得很呢!期刊的生命力不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还处在兴旺发展的繁荣时期。我国期刊的发展速度比较缓慢,最近100年间,平均每月增加4种。现在全国正规审批的期刊种数稳定在9000多种,基本上不再增加。但是,有两种现象值得注意:一是期刊的总数量还在增长,期刊印张总数的增长超过报纸印张总数25.87%,超过图书印张总数25.17%;二是相当多的网络期刊、电视期刊、广告性纸印期刊,已经大量出现。如果再加上难以统计确切数量的mooks(国外称之为“杂志书”,我国说是以书号出版的代期刊),新增的期刊品种总数与发行总量恐怕不会小于在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审批登记、给予刊号并核准出版的9000多种期刊数。特别是不少商业广告性期刊,只在工商部门登记后即可印行,进入超市或行业服务领域。网络期刊种量更是疯狂剧增,势不可遏。怎么看待这些期刊现象?怎么评估它们的价值和意义?如何管理与控制这些期刊现象?如何将这种新生的期刊现象与传统的期刊现象联系起来,认识它们共同的本质、特点、功能与价值?在新的历史与技术条件下,我们对传统期刊的理性认知与管理控制,该不该有所反思与改进?如果要写一部期刊史,又该建立怎样一种期刊历史观?如果要站在期刊历史的潮头,指导和引领整个期刊方阵的发展航向又该设置怎样的航标灯呢?
记:是否应该科学地建设起我国自己的期刊理论,才能较好地解决上述种种问题呢?
王:我觉得是的,不但应该,而且必须尽快地以自主创新精神,建设起科学的、富有中国特色的期刊理论,以便较好地解决我国目前期刊评价指标体系的问题,推动我们的“期刊方阵”整体前进。近20年来,我国已经出版了一些研究期刊的论著,分别研究不同种类期刊的专著专论也有不少,这为建设科学的期刊理论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2006年4月,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核心期刊与期刊评价》 (钱荣贵著)的书,对建设中国的期刊理论和制定科学的期刊评价指标体系,作出了勇敢的探索和研究。书中不少论述可圈可点。《出版发行研究》杂志 2006年第4期发表了一篇文章《杂志也疯狂》(作者胡义兰)是专门研究网络期刊的。其以Xplus的大量实例,分析多媒体电子杂志的发展现状。这本书和这篇文章的两位年轻作者都是因为看到了我国期刊生态巨大的演变势头,而感到既有的期刊理念实在是太贫乏、太苍白而着手研究期刊现象、探讨期刊理论的。我们要向这两位年轻的编辑出版学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学习,发扬自主创新精神,建设中国特色的现代科学的期刊理论。我国的期刊领导部门、管理部门、编辑部门、发行和订阅部门以及期刊的作者和读者都需要科学的期刊理论帮助他们更好地从事期刊工作并与各种各类期刊实现共创共享的交流。总之,我们需要通力协作,建设中国特色的科学的期刊理论,保护我们期刊生态的健康发展,推动足以代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方向的“期刊方阵”,打造和创构更多的精品期刊、名牌期刊,形成优秀的重点期刊或权威期刊,促进整个期刊业提高总体质量,全面繁荣,走向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