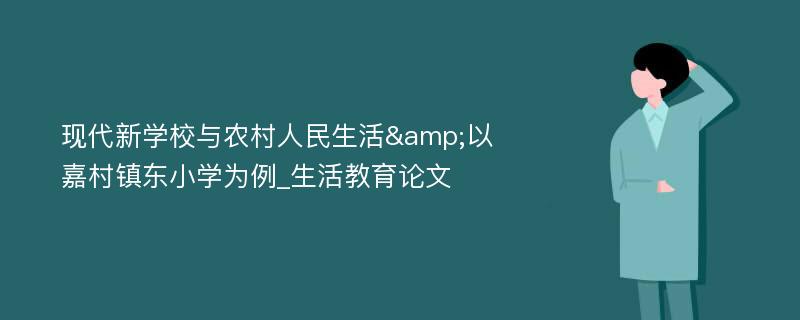
现代新式学校与乡村民众生活——以佳村震东小学为个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个案论文,民众论文,乡村论文,小学论文,学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所办在乡村中的现代新式学校,对于民众的生活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是个很“微观”的问题,但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以让我们细致地感受到现代学校教育对普通民众的影响,从而在一个具体的场域中去观察现代教育变革的大潮到底在哪些方面改变了乡村民众的生活。
关于现代新式学校在乡村社会的推行情况,从民国的时论到当代的研究所构建出来的历史图景总体上是较为悲观的:新式学校与乡村民众的生活方式格格不入,并在乡村的推行中引发了诸多矛盾和冲突,私塾长期存在并与学校展开竞争……这些描述确实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的艰难曲折。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新式学校无法对乡村民众的生活产生积极的影响呢?本文在田野考察所收集到的口述史料和民间文献的基础上,试图就清末创办于浙西南山区佳村的震东小学对村民生活的影响进行描述和分析,以期对上述问题做出探索性回答。
一、佳村的地理、宗族和文化传统
佳村位于浙江省西南部松阳县境北端,瓯江支流松阴溪东北岸。佳村环山靠水,呈带形块状聚落;村东为龙丽公路,公路东侧为低山;村西临松阴溪,由西北向东南流经,溪流以西则是丘陵和山地。故全村呈东西两边高、由北向南低的地形,佳村就坐落在松阴溪冲积而成的河谷低地上。截至2005年,佳村有耕地735亩,山林4936亩;有人口273户、821人①。
(一)松古平原与金衢盆地的交通孔道
佳村中有一条从西北至东南纵贯全村的老街,长约0.5千米,历史上是驿道(永嘉官道)的一段。佳村以南是浙西南山区最早开发的松古平原,以北则是瓯江水系和钱塘江水系的分水岭仙霞山脉。1938年龙丽公路未建成前,人们沿此驿道在佳村渡过松阴溪进入遂昌县境,再翻越两座山岭即可进入金衢盆地的龙游境内。谭其骧认为,这应该是古代衢江流域人民南下开辟瓯江上游的一条通道②。所以,佳村是松古平原与金衢盆地之间的交通孔道。这一地理位置使佳村较早得到了开发,也使得佳村民众较易接受外界的影响。
佳村老街的西北端临松阴溪处有一个小码头,这是佳村亦农亦商传统经济形态的象征,过去佳村民众经营的食盐业和木材业均围绕着小码头和松阴溪展开。食盐来自南面的温州沿海,溯瓯江干流和支流松阴溪上行至佳村后在小码头卸货,分装成小包再改经陆路分运到龙游、江山、兰溪、衢州甚至江西玉山、上饶等地。所以,佳村是一个浙南食盐运往浙中、浙西乃至赣东的水陆转运枢纽。木材业是浙西南山区的传统产业,佳村是仙霞山脉木材转运的集散地之一。木材被砍伐后,先经山溪小涧放流至佳村小码头一带,捆扎好后等松阴溪涨水时顺流而下,至瓯江下游的青田县交售当地木行。1938年龙丽公路通车后,佳村在水路运输方面的重要性有所下降。由于战争沿公路撤退到浙西南的外地人络绎不绝,佳村人又抓住商机在公路沿线办起了小旅馆、茶店③。食盐的逆流而上和木材的顺流而下,使佳村作为一个传统的“物流枢纽”而商业发达,龙丽公路的开通又使佳村成为陆路进入浙西南的一个站点。这种地理和经济条件,使佳村的学校教育事业开展有了较好的物质基础。
(二)主姓宗族村落④
佳村在宋、元时期称为“洪坦”,大多为洪姓人居住,另有叶姓也是大宗族。两大宗族在明代外迁它处。元末以来,刘、张、陈、颜、缪、骆等姓先后迁入,到民国年间形成了“刘为著姓,张次于刘,而陈又次于张,缪姓五传仅二户,颜四骆二,余皆单姓独户”的基本格局⑤。作为“著姓”的刘氏宗族,始迁祖为刘堡,元末明初从青田县九都迁来。作为佳村第一大宗族,刘姓不但人口最多,经济实力最强,文教成就也最高:明清时期有廪生、贡生72人;1949年后,在全国各地任教授、高工的也有20余人⑥。所以,从宗族的角度来看,佳村是一个主姓宗族村落。
刘姓宗族子孙按刘堡的3个儿子伯祥、伯禄、伯贞分为仁、智、信3房。这3房的发展极不平衡:在十世“廷”字辈以前,仁房、智房人数占优,信房则几度一线单传。十一世“国”字辈为信房的转折点,此后信房人丁日渐繁茂,而仁房、智房则每况愈下,分别在十六世和十七世失传⑦。信房从十三世“邦”字辈3个儿子邦诏、邦训、邦诰始,又分为大房、二房和三房。信房的一个明显特点是获得科举功名或者官学生员身份的子孙比其它两房要多。早在第二世“伯”字辈的三人中,房长刘伯贞就是3兄弟中唯一的“少好读书,日浸淫于典籍”的庠生⑧。刘伯贞的儿子刘璿是明景泰四年(1453)己酉科贡元,天顺三年(1459)任福建泉州府知事⑨。这是刘氏宗族成员在科举仕宦道路上的最高成就,也是信房作为“书香门第”的开端,前述获得廪生、贡生资格的72人中,多为信房子弟。
刘氏信房重视文教的传统,也为清末信房“厚”字辈子弟创办新式学堂提供了思想渊源。主姓宗族村落的格局,又使得刘姓宗族的办学设想能够得到其他宗族的赞助和支持。
(三)地方传统文化
宋元时期佳村的洪、叶两族均为地方望族。明清以降,刘姓作为该村第一大宗族非常重视文化教育。比如,家长在将田产分给儿子时会单独留出一份田产,用部分田租奖励子孙读书。每年过年祭祖后祠堂分发“丁肉”(给族内每名男丁的肉)时,除每人一份外,凡考中秀才、廪生、贡生、举人等功名的,都递加增发以示奖励⑩。儒家文化对佳村民众日常生活的影响渗透在很多细节中。比如祭祖活动,为了吸引小辈参与扫墓活动,家长往往会奖赏小辈若干枚铜板,称为“赶路钱”。除了扫墓,祠堂祭祖也至为隆重。祠堂拥有专人管理“忌辰田”,每年的重要节气都有严格的祭祀活动。冬至祭祖时,族内男丁要聚齐吃“祀神饭”。在日常生活中,讲究长幼有序、男女有别。比如村中禹王宫前的大戏台左右两边建有客廊供妇女看戏用,男子则站在中间的空地上。在生活态度上,佳村民众崇尚节俭持家,无论贫富,大都视节俭为美德。佳村还有一个“申明亭”。每当发生民间纠纷时,双方当事人就到这个亭子里申明自己所知的事实和态度,村中士绅和老人则居中调解,并根据村规对过错一方进行劝说或惩戒(11)。
佳村的民间宗教文化也与中国的很多乡村一样丰富多彩。
从面积和人口来看,佳村不是大村落,但其宗教场所非常之多,其中最大、最重要的当属源于明朝的禹王宫。禹王宫坐东朝西,位于老街中段,分大殿、观音堂、夫人堂三个部分,规制宏大,也拥有田产以维护日常运作。虽然禹王宫的主祭神是大禹,但所祭神祇有3大类18尊之多(12),是一座众神杂处的庙宇,典型地反映出民间多神信仰的特点;其功能是满足民众不同的现实需要,“护佑其生活不同情状之痛苦疑难。”(13) 从这个意义上说,以禹王宫为代表的民间杂神寺庙,是佳村民众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乡民不但经常到禹王宫烧香还愿,还在重要节令举办庙会,在宫前大戏台演戏酬神、娱乐大众。所以禹王宫也是佳村及周边村落最重要的民间文娱场所,并兼有临时市场和交流会的功能。在各种庙会中,元宵节灯会是佳村民众最重要的“大型综合活动”。灯会由村中刘、张、陈三大宗族的人所组成的各种名目的会轮流负责。各会都有几亩田,田租可用于灯会开支,并有一名“会首”,各会总称“龙灯会”。灯会从正月十三开始到正月十七结束,期间既有庄严的奉献祭礼仪式,又有欢乐的舞龙和提灯游行,并有连台的戏曲可供观赏(14)。这种大规模的迎神赛会固然会耗费大量金钱,却是乡村民众借助神佛、祖宗,强化村落内部认同意识以及沟通族际、村际和谐,从而构筑社区共同体和地域社会的方式之一(15)。比如为了庆祝元宵灯会,全村每户按男丁人数每人要出白烛1市斤,外地迁入的新立户则为5市斤;如果正月十三晚尚未送上祭品,要按村规罚白烛2市斤(16)。这些规则对于强化村落民众的认同和共存意识是有作用的。灯会期间本村龙灯与邻村龙灯相互交流,亲朋好友互相走动观摩灯会,共享快乐,这对于沟通村际关系也有正面意义。
独特的地理环境和经济条件使佳村在清末创办新式学堂有了较好的物质基础;主姓宗族村落的格局使得刘姓办学的设想能得到其它宗族的支持,从而减少纷争的可能性;根基深厚的儒家文教传统,为新式学堂的创办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源;绵延不绝的民间宗教文化传统强化了村落共同体意识,推动了与周边村庄的良性互动。对于这个20世纪初的浙西南山区小村来说,现代新式学堂的创办不需要政府的强制,而是需要能振臂一呼的领头人。
二、震东小学的发展轨迹(17)
清末风气渐开,浙西南山区各县一批学子开始出国留学(18),据统计,人数最多的是松阳县,有20余人。这20余人中,有近10人专攻师范,佳村的刘姓第十七世孙刘厚体就是其中一位。
(一)清末佳村的新式学堂
佳村现代新式学堂的出现,与当地留日学生刘厚体的努力分不开。刘厚体(1873-1930),字钟玉,又名德怀,少时接受儒学教育,1903年赴日留学,入宏文学院第十三期师范科学习,并加入了同盟会。刘厚体于1906年学成返乡后,“倡导兴学,得耆宿赞助,遂抽拔地方寺产,及殷户乐捐,计常年租谷一百六十担为学产”(19),于2月间主持创办了“公立震东初等小学堂”和“私立震东女子两等小学堂”。
“公立震东初等小学堂”的办学经费主要由寺庙田产、佳村及周边村庄大姓的祠堂田产、私人捐赠三部分构成(20)其中刘氏宗族早年捐赠给附近万寿山“望松寺”的70-80亩田产是最大一宗(21)。所谓“抽拨地方寺产”即此之谓。另据后人回忆周边村落如大石、后周包、邓村等,都捐出田产作为办学经费(22)。该学堂依赖上述地方公产办学,专收男生,学生免缴学费,只需自负书簿费,故冠名以“公立”。这所学堂的校址也选在刘氏宗祠和禹王宫南厢房这两处“公共场所”。至1909年省视学范晋来村视察时,学堂有校舍28间,职员1人,教员5人,学生36人,其中四年级15人、二年级12人、蒙养级(学龄前儿童)9人,不但设齐了《癸卯学制》中所规定的8门必修课程,还开设了图画和音乐两门随意科。所以视学的考语多所褒奖,认为该学堂“学科完全,教授如法,设备编级大致尚属整齐。因堂长办事认真,故教员学生平日罕有缺席。”(23)
“私立震东女子两等小学堂”的创办则主要依赖刘姓宗族内部资源,并在最初仅为宗族内部服务。学堂的办学经费主要来自于刘氏信房中二房的田产,校舍则是刘厚体名为“一亩居”的大宅院。学堂最初有教师共4人,刘厚体任校长,其族兄、贡生刘厚道具体负责,其胞弟刘厚岱、族弟刘厚祚任教师,都是宗族内“厚”字辈的叔伯兄弟。另外,刘厚体的族兄刘厚和、刘厚生等人都曾担任过校董(24)。学堂最早招收的16名女子均是刘姓宗族的女子(年幼女童以及刘姓子弟的妻子或未婚妻),入学者一律不得缠足,已缠者放足(25)。比如当时大约9岁的刘承先之女刘莲香(1897年出生)就是第一批学生;刘福初的继室叶氏(1881年出生)也入学读书;刘厚道之子刘福保的18岁未婚妻周晓蓉也被刘德元从邻村招来入学。学堂按学生基础分为初等、高等两班,不识字的入初等班,有一定文化基础的人高等班。不久学堂招生规模逐渐超出了刘姓宗族的范围,“邻近乡村女子,多前来就学,近者走读,远者寄居界首亲友家。本村居民之青年小女,几乎无人不就学矣。”(26) 到1909年省视学范晋来视察时,私立震东女子两等小学堂有校舍8间,职员1人,教员5人,学生34人,其中高等一年级5人、初等四年级6人、三年级6人、二年级6人、蒙养级11人。课程设置上,《癸卯学制》所规定的8门必修课程中“读经讲经”课未设,但增设了图画、音乐、家事3门课程。省视学对该学堂的严格管理印象深刻:“此堂规则严肃,形式整齐……至于教授除体操一科由领班女生教授外,其余皆由男教员按时走课。然管理均系尊属,尚不致贻流弊。”(27)
1906年正是晚清时期全国掀起第一波兴学热潮之际,地处浙西南山区的佳村在刘厚体等人的主持下一年内办起了两所新式学堂,可谓顺应时势。据统计,1906年浙江全省仅有女子小学堂24所,在堂女生791人(28)。在这样的背景下,私立震东女子两等小学堂的创办和16名女子的入学,规模虽小,也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几年办学下来,这所学堂在破除缠足陋习、转移社会风气方面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前述1909年来村视察的范晋对此大加赞誉:“此堂……凡缠足者不许入学。自开办至今首尾甫及三载,不图佳溪全村已鲜缠足之幼女,转移习俗煞费苦心。”“且该村仅八九十户,综计入学之男女已不下六七十人,风气开通实为处郡之冠!”(29)
(二)民国后“震东小学”的变迁
民国后,佳村的两所学堂改称学校,继续发展。1920年,长期担任校董的刘厚和负责筹划女子学校新校舍。他在禹王宫周边购置了一些旧屋,新校舍落成后,原在“一亩居”求学的女生均搬入,但是依旧保持男女分办的格局(30)。到1925年,震东女子小学逐渐式微,与震东初级小学校合并,改组为“区立震东小学校”,为四二制完全小学,校款由“抽拨寺租九十一担四桶、殷户捐租六十七担”构成,全年经费800圆(31)。由县委派徐仁基(刘姓姻亲)任校长,增聘教员,改革校务,扩充校舍及设备,提高教学水准。邻近乡村学生,多来升入高等班级就学,全校计有男女生百余人,进入兴旺时期。(32)
1940年国民教育制度推行后,学校改名为“佳溪中心国民小学”。除本村学童之外,邻近村庄的适龄学童均在该校就读。1942年5-8月,日军入侵松阳。佳村处于日军必经之路上,学校一度停课。日军撤退后,学校复课,改由刘厚体长子刘福穰任校长。在刘福穰等人的努力下,学校不但恢复了旧观,而且颇有改进。抗战胜利后,学校继续发展,至1945年仍有一至六年级,学生每年参加县运动会均能获奖。从学校布局图来看,校园规划整齐,校舍齐全,有教室、礼堂、教师办公室和宿舍楼、校长办公室、活动室、食堂、操场、花园等功能分区(33)。与当时多数乡村学校比较,佳村震东的小学设施堪称先进。
关于这一时期的学校生活,在当年学生的回忆中充满了快乐色彩。叶根生(1934年生)和钟林根(1937年生)出生在佳村邻近的一个贫穷畲族小村落,他们都是先读私塾(当地人称为“蒙童馆”),再于1947年左右进入震东小学的。两位老人都不约而同地提到私塾学习生活的枯燥和在震东小学读书的快乐。私塾最大的问题是学习时间冗长、内容单调。“一早去把饭放在主人家就开始背昨天教的书,然后先生教新课,然后吃中饭,吃过后就练毛笔字,没一点时间给我。先生管得严,坐在桌边看着我们。”“在蒙童馆诗歌天天要背,毛笔字一天写到晚,数学是不懂的,蒙童馆是不教的。除了练字,还要读三字经、五字经等。上半年老师是不解释的,下半年开始有解释。”“那时蒙童馆里还有孔夫子(牌位),每天要做个揖。(先生)不是一个班一个班教的,年纪大的也在一起。”与私塾这种落后的教学方式相比,震东小学给他们的体验就愉快多了。他们称“在震东小学有得下课,蒙童馆是没得下课”,所以“还是在小学读得舒服些、痛快些”,“在震东小学小孩的玩意多,好玩一点”(34)。上述话语涉及到的是现代学校班级授课制的一些基本特征。相比于私塾,震东小学所体现出来的现代学校制度在时间节奏和内容安排上似乎更为学生所乐于接受。
三、学校在村民生活变迁中的积极意义
对于佳村不同阶层民众子弟来说,震东小学对其人生轨迹所产生的意义是不一样的;而早期的震东女子小学,则极大地影响了部分乡村女子的生活和职业。
(一)士绅子弟:从儒生到专才的转型
从一般意义上讲,中国传统教育培养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通才式儒生,而现代学校教育则强调培养适应现代社会分工需要的专业人才。对于佳村的士绅子弟来说,震东小学是他们接受现代教育的起点,之后,他们中的一些人便循着现代教育体制的阶梯,走上了与他们的父辈所不同的成为专才的道路。在刘姓宗族中,这个转折主要发生在“厚”、“福”、“为”三代人之间。在1945年修订的刘氏宗谱中,“福”字辈共登记了112人,其中有学历记载的13人,这13人中又有11人是刘厚体和刘厚道的儿子。这里我们就以这两个士绅家庭为例来探究这一变迁。
前文已提及刘厚体早年学习儒学,后去日本留学接受新式教育,归国后致力于新式学堂的创办,可以说是一个“半新半旧”的人物。但是从思想基础来看,他仍然深受儒学影响,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难以割舍的感情。最明显的证据是他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眼见儒家学说受到冲击,竟然舍弃公职而投身夏震武门下,执经问道,蓄发服儒,并在家乡尝试恢复儒家礼仪制度(35)。刘厚道也“是一名标准的儒生”。他18岁考中秀才,此后屡试不第,最后以德行学问成了一名贡生。刘厚道一生的事业也是科举途蹇的儒生们通常的选择——以“舌耕”为业。他先教村塾,此后任教于当地各书院。随着新式教育机构的出现,他先负责“震东女子两等小学堂”的校务,民国后又曾到松阳县最早的新式小学——毓秀小学任教。在后人的描述中,刘厚道以其儒家道德和学问广为众人敬仰,“为松遂等县的知名良师之一”(36)。
刘厚体和刘厚道各有7个儿子,除3人早夭外,这11名“福”字辈的男性后代大多接受过现代教育,并有9人成为不同专业领域的专门人才。
刘厚体的长子福穰毕业于浙江省立甲种农业学校,后随父求学于夏震武,之后辗转于绍兴、杭州、长沙等地任教;抗战期间回乡在县农业推广所任技术员;抗战胜利后为重振震东小学而任校长至1949年7月。二子福简少时接受儒学教育,“九一八”事变后投笔从戎,参加长城抗战,之后被选入军校,并参加抗战时期的防空作战;1948年赴台,1966年以上校衔退役。三子福休早夭。四子福遐毕业于贵州防空学校,任高射炮团排长,后因公殉职。五子福五毕业于成都陆军军官学校工兵科,曾任装甲师少校连长,后赴台湾。六子福尝省立第十一中学毕业后于1944年参加“青年军”,抗战胜利后复员求学,1946年考入浙江省医学院,毕业后先后在上海、西安等地的国企任厂医。七子福伦毕业于中央大学水利工程系,1949年加入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在云南玉溪扎根,服务当地农田水利事业,1989年离休(37)。
刘厚道的长子福臻毕业于浙江蚕业学校,初留校任教,后在实业部门任职,曾任民国初年的省议员。次子福保毕业于浙江省立两级师范学校,历任省蚕桑学校、台州中学、处州中学、湘湖师范文史教员及松阳中学校长等职。三子福谦早夭。四子福皆先后在震东小学、省立第十一中学、省立甲种林业学校求学,毕业后赋闲乡居自习中医,行医乡里颇有医名。五子福佐震东小学毕业后经商开办烟行。六子福佑早夭。七子福兆省立两级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毕业,省立蚕桑学校肄业,23岁时病故(38)。
当然,这11名“福”字辈男子教育的起点并不都是震东小学。福臻、福保、福穰、福简4人是两家出生较早的长子、次子,他们既受过传统儒学教育又受过专门学校训练,和他们的父辈一样表现出“新旧过渡”的色彩。福皆、福佐和福伦则是从震东小学开始其教育历程的。福兆毕业于其它小学。福遐、福五、福尝3兄弟的教育起点没有明确资料说明,但是他们和福伦一样都出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佳村,应该也在震东小学接受初等教育。
这11名“福”字辈的子弟中有9人育有33名子女。这33名“为”字辈子女中出生在佳村的约有23人,出生年份在1914年到1939年之间。据族谱记载及后人回忆,这23人绝大部分从震东小学开始其教育历程,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日后成为专门人才,而且在医药行业的特别多。比如刘为纹、刘为经两人震东小学毕业后,即赴杭州人宗文初中,后考入“杭高”,再后一个考入省立医学院、一个考入国立中正医学院。解放后两人均成为医药方面的专家,刘为纹现为西安第三军医大学教授、博导,刘为经则为浙江省医学研究院的研究员,食品卫生专家。另如刘为纯曾任天台国药栽培场的技术指导,刘为绶肄业于国立英士大学医学院,刘为绾是中医主治医生,刘为琼是同济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妇科医生,刘为绚是南京铁道医学院的医生(39)。
(二)普通民众子弟:文化启蒙和身份变化
现代初等教育的基本目的是对适龄儿童普遍地进行基础教育,使他们成为具备一定的文化科学素养的国民。这一目的并不指向受教育者社会身份的变化,但会为身份变化打下基础或者提供可能。
震东小学对于佳村普通民众子弟而言,首先意味着普遍的文化启蒙。在田野访谈和文献资料中,“佳村连捡猪粪的都有文化”这句对佳村文化水准的溢美之词反复出现。捡猪粪是为了做肥田之用,捡猪粪者代表着底层劳动人民。这句话所凸显的,正是震东小学对于提升本村乃至周边村落一般民众子弟文化水准的普遍性。能实现普遍文化启蒙的关键在于震东小学的免费特点。如前所述,震东小学的办学费用来自于地方公产,学生免缴学费。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佳村一带的儿童如果读私塾,一年要交9斗米给先生作为学费。因此,与私塾的费用相比,在震东小学求学的费用是很低的,一般民众家庭都能负担。这一点得到了众多访谈对象的支持。前文提及的叶根生和钟林根所在的畲族村落,“土改”时没有一个地主、富农成分的人。但即便是出生在如此贫穷的山村,他们也能去震东小学读书。其中,钟林根的父母不但供他读完了小学,还供他进入俭公中学(即现在的松阳县第二中学)读了一年初中,直到1953年当地大旱,家中无力负担而辍学。他清楚地记得“那时候小学读书不用钱,初中要钱,我还有丁等助学金。”据钟林根回忆,村中他们这一代人至少有3人去震东小学读过书,而该村直到解放初期也只有10余户人家(40)。一个贫苦的畲族村落也有儿童能去震东小学求学,佳村的儿童入学就更普遍了。1931年出生的刘为藩告诉笔者:“那时候不管家里条件好不好,都会去读的,学堂不用交学费的啊!除了个别很苦的给地主老倌放牛。”(41)
普通民众子弟接受了初等教育之后,大多不可能像士绅阶层的子弟一样继续沿着学制的阶梯向上攀爬,而依然是一个普通农民。但是对于部分人来说,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识多少会在他们后来的人生轨迹上提供一些身份变化的机会。
比如,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识可以帮助一些农民子弟参与到乡村治理中来,担任乡长、保长、甲长、干事等基层公职。传统的乡村社会中,实际的政治控制权掌握在士绅阶层手里,但是士绅往往不会出面担任事务性基层官员,而是物色或者推举宗族中的平民子弟来担任。比如1897年出生的刘福礽,震东小学毕业,曾任乡长;1912年出生的刘为干,初中学历,小时务农,后曾任界石乡乡长和温石乡干事(42)。民国后期,佳村是界石乡的驻地,本身则分为两个保,当保长或者甲长的基本条件就是识字,两个保的保长基本由刘姓宗族的平民子弟轮流担任(43)。除了当保长,平民子弟还可以在乡里当事务员。比如1907年出生的刘福舟,9岁就读于震东小学,13岁(1920年)时因家贫辍学于五年级第一学期,从事农业劳动。1942年辅助当乡长的胞兄刘福初任乡干事4年,并加入国民党(44)。另如1921年出生的刘为屏,震东小学毕业后考入当时内迁到松阳办学的湘湖师范,毕业后去安石乡当了事务员,后又曾在界石乡当事务员(45)。
1949年后,佳村的士绅阶级走向没落,底层民众在政治上得到了“翻身”。乡长、生产队长、会计之类的基层干部,开始大量地由一些具有一定文化的贫苦农民担任。比如1927年出生的张光清,7、8岁进震东小学读书,“读了6年书,毕业后就在家里。没有多少田,就凑着帮帮散工(打短工)。解放后因为说我们最苦,小学毕业的认识几个字,于是乡里就把我叫去做干部了。1950年1月份就入党了,1951年去乡里的,1980年退休。”张光清曾先后在新兴乡、赤寿乡当过总支书记和文书(46)。同样在1927年出生的刘福胜与张光清经历相似,他童年时只在震东小学上了两年半的学就因家贫而辍学了。1950年土地改革时,由于阶级成分好又略有文化,“工作不用自己找的,都是(土改)工作队找上门来要我们做。”他一共担任了37年的乡村干部(47)。又如1928年出生的刘福儒,在震东小学上了3年学后辍学。“土改”时他的成分是贫农,被选拔为生产队会计、民兵连长。由于他受教育时间不长,“虽然认识几个字,但算账难算,数字一多要把账轧平就很吃力了。”不过他还是认为:“认识几个字还是有用的。以前搞集体化的时候,互助组的生产规划都是我做的。有机会用就能发挥作用。”(48)像生产队长、会计这一类基层“职务”,刘福尧、钟林根、刘为藩等受过教育的贫农都在1949年后担任过,1928年出生的刘福堂甚至担任过两个区的区长。
从总体上看,佳村的普通民众子弟大多在震东小学受过教育,这在整体上提升了佳村民众的文化水准。但是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只接受初等教育并不一定会改变他们身为农民的身份;只有少数人在各种条件的机缘巧合下发挥了早年接受教育的作用,并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了其社会身份。正如刘福儒所言,早年所受的教育“有机会用就能发挥作用”。而对于多数没有机会的一般民众子弟来说,则遵循着“用进废退”的规律,早年所受的教育逐渐退化为一种文化印记,并转而对后代寄予新的希望。
(三)乡村女子:身体的解放与职业的获得
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也是女性逐步得到解放并进入职业社会发挥作用的过程。对于这个过程,教育史界已有很多著述予以讨论。略显不足的是这些著作大多以近代社会中那些杰出女性作为叙事对象。那么,除了极少数的精英女性之外,对于绝大多数普通女性、特别是乡村女子来说,女子教育的推行到底对她们的生活意味着什么?
对于佳村的女子来说,“私立震东女子两等小学堂”的开办首先带给她们的是身体的解放。刘厚体从日本回来后,极力劝说所有刘姓宗族的女子都不要缠足,已缠者放足。据刘厚体长子刘福穰回忆,其母周庆琴主动向其父提出“愿即以身先之”,首先响应放足的倡议(49)。学堂开办后,凡是已缠足的入学女子一律放足。前述的18岁女子周晓蓉入学时就放了足,而且放足之后就让她们穿上操衣,上起了体育课(50)。笔者在2006年拜访的百岁老太太刘史贞(1906年出生,刘姓二房“福”字辈刘福初之女)就有一双天足;虽然已百岁高龄,依然思路清晰,表达流畅,生活尚能自理。刘史贞6岁入学,由于家境困难其学业时断时续,直到19岁时嫁入县城的潘姓人家。潘家也是书香门第,刘史贞的公公是晚清贡生,丈夫则是省立第十一师范毕业的教师。嫁入潘家的当天,她的天足就引发了婆婆的震撼。访谈中刘老太太笑着说:“我的脚一伸出花轿,我的婆婆就惊呼‘老天,怎么讨了个畲客婆回来!’”(51)老太太自豪的说:“(女子不裹脚)就我们刘姓人能做到。”(52) 像刘史贞这样早年女子学堂高等班的学生,“非但国文程度佳,且能吟咏赋诗,工楷书,懂数理;能绘画唱歌,精缝纫刺绣”(53)。这些新旧素质兼有的女性对于当时思想趋新的士绅家庭颇有吸引力。地方上就有这样的说法:“要娶佳妇先到佳溪震东女学堂去找”,虽为笑谈,颇近事实,该校多数毕业生嫁入书香门第。佳村民众也对此颇为自豪,乃至于有“佳村女人出嫁外地的是白米,外地娶回的女人是谷糠”的说法(54)。
除了身体的解放,接受教育对于佳村部分女性来说也意味着摆脱家庭主妇这种单一的社会角色,成为职业女性。“私立震东女子两等小学堂”从1906年开办到1925年与震东初级小学校合并,20年间计有18届女生高等班毕业。她们中的部分人继续求学深造,毕业后大多进入各女子学校任教,从而推动了当地的女子教育事业。比如首届毕业生周彭玑曾进入女子工艺学校求学,毕业后于1913任松阳县“成淑女子小学校”校长,为该校的重新开办做出了贡献(该校也创办于1906年,旋因校产流失而中断办学)。周彩星、郑群弟、刘采苹、刘淑姿、周坤仪、陈小爱等人小学毕业后升入省立女子蚕业学校或处州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基本上进入各女子学校任教,其中刘采苹和刘淑姿后来还担任过震东小学校长。另有刘秀竹、刘静贞、刘美姜、刘贞操等毕业生也担任过女子学校教员(55)。上文提到的刘史贞在嫁入潘家后,约在21岁时又去读了女子师范学校,之后曾当过教师,教过算术等课程。
下面是根据1999年修订的刘氏宗谱,对佳村刘姓“为”字辈女性的受教育和职业情况所做的一个不完全统计。在宗谱中“为”字辈共登记了186人,其中有女性54名。在这54名女性中,出生在1907-1940年间的有31名。这31人中有学历记录者20人,其中接受初等教育者6人,接受中等教育者11人,接受高等教育者3人。接受过新式教育的这些乡村女性日后绝大多数从事教师(或校长)、医生(或护师)、行政管理和科技工作(56)。
在争取受教育权男女平等成为一个重大社会问题的现代,佳村的女子由于震东小学的存在而获得了较好的机会——在31名出生在清末和民国时期的女性中,受过不同程度教育的人数至少占到了65%,而这种机会的获得又对她们中大多数人的人生道路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现代小学对乡村民众生活的意义。
四、余论
对于一个村落而言,面对时代的变迁是消极被动还是积极应对,除了受村落所处的地理位置、经济实力这些客观条件影响外,还取决于人的主观努力。地处浙西南山区的佳村,其现代学校教育事业之所以能较早萌芽、发展壮大、并对部分村民的生活轨迹发生积极影响,是与佳村刘氏宗族精英的现代意识和努力实践密不可分的。
在刘姓宗族中,刘厚体是最杰出的一位。在刘姓族人的印象中,刘厚体是一个性格开朗、干练、热情的人,敢想敢做,勇于接受新事物。(57) 这种性格使他在面临时代变局时,能较早地把握机会,走在别人前面。对于佳村来说,刘厚体是个在各方面开风气之先的领军人物。除了创办新式学堂,他还致力于其它社会改造事业,比如剪辫放足、推广蚕桑,还引进很多“洋玩意”,开拓乡民眼界。族人们至今还记得他从日本留学归国时,带回来松阳县第一辆自行车、“洋戏”(留声机)、“铁裁缝”(缝纫机)等等(58)。
中国的宗族向有办理“族学”教育本族子弟的传统,佳村最初的两所学堂都在不同程度上利用了宗族资源,而最初的“私立震东女子两等小学堂”更是一所具有现代教育特征的“新族学”(59)。在佳村,刘氏是最大的宗族,族产相对丰厚;以刘厚体为首的一批宗族子弟在宗族中影响力很大;女子学堂所教科目中,除了传统的“修身”课外,还有算术、格致、历史、地理、体操、图画、音乐等现代课程,并采用班级授课制教学。最重要的是,震东小学从地方公产中筹集办学经费,这意味着村民不用再为办学和子女受教育支付大笔费用,他们把新式学堂当作村里的福祉而不是负担。而村民子女普遍入学,才能普遍地提升民众的文化水准,现代新式学校也才有可能对部分民众的生活产生积极的影响。
正如本文一开始所言,学界对于20世纪前半期现代新式学校在乡村社会的推行情况大多持悲观看法,认为办在乡村的现代新式学校很难对民众生活发挥积极影响。比如费孝通在其名著《江村经济》中就认为,20世纪30年代在江苏开弦弓村的新式学校所提供的“文化训练并不能显示对社区生活有所帮助”(60)。本文所描述的,则是一所现代小学对乡村民众生活发挥积极影响的个案。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震东小学就是一所能给佳村民众“创造幸福生活”的“显灵神庙”,更不意味着震东小学给民众生活带来的影响总是积极和一帆风顺的。学校教育不是万能的,一所乡村现代小学也只有在各种主客观条件比较协调一致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对当地的部分民众发挥一些积极影响。这份基于个案的研究无意扩大结论的普适性,本文的基本目的是试图为现代学校教育与乡村社会发展这幅宏大的历史图景补上一笔较为细致的“生活画面”,并且在这幅“画面”的基础上审慎地提出如下观点供学界讨论:20世纪以来,中国乡村社会对由政府推行的现代教育制度并不总是持抵制与消极的态度,在一定条件下,或从一个更长的时段来看,乡村社会对现代教育制度的“楔入”也许会更宽容、更主动。这种看似相反实乃相辅相成的悖论,其实正体现了中国乡村教育早期现代化进程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收稿日期 2009-02-28
注释
①③⑤⑥⑩(11)(12)(14)(16)(21)(33)(54)(55) 界首村两委会编:《界首文化古村村志》,松阳:未刊,2006年,第9-10页,第104-106页,第217页,第20页,第111页,第95-97页、第120页、第152页、第193页,第207页,第19页、第147-149页、第169页,第148页,第156页,第139-141页、第244页,第226页,第122页。
②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编:《历史地理研究》(第1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4页。
④ 这是根据王沪宁提出的3种宗族模式(单姓村落家族、主姓村落家族和多姓村落家族)而给出的界定。主姓村落家族的特点是一个村落共同体内存在多种姓氏,但以一个姓宗族为主要成员,其他姓氏处于次要地位。详见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项探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9页。
⑦(19)(26)(32)(35)(36)(37)(38)(39)(42)(44)(53)(56)(58) 刘为绾纂:《佳溪刘氏宗谱》(下册),松阳:未刊,1999年,第2卷第51-73页,第3卷第20页,第3卷第21页,第3卷第20页,第5卷第5页,第5卷第1页,第5卷第6页、第21-22页、第24-26页,第2卷第4-5页、第5卷第4页,第5卷第26-28页,第2卷第13页,第5卷第20页,第3卷第20页,第2卷第27-31页,第3卷第8页。
⑧⑨(24)(30)(49) 刘为绾纂:《佳溪刘氏宗谱》(上册),松阳:未刊,1999年,第3卷第22页,第6卷第2页,第2卷第19-22页,第2卷第22页,第2卷第50页。
(13) 王尔敏:《明清时代庶民文化生活》,长沙:岳麓书社,2002年,第12页。
(15) 王振中:《少年胡适及其早年小说(真如岛)》,《读书》2008年第11期。
(17) 本文的“震东小学”是一个通称。因为佳村最先创办的两所学校都有“震东”二字,且在1925年合并为一所学校,并一直延续到20世纪末才因整合教育资源而被裁撤。因此,文中除了必须指出学校全名之处外,一律称“震东小学”。
(18) 从行政区划上说,浙西南山区在清末主要是指处州府下辖的丽水、青田、缙云、云和、景宁、松阳、遂昌、龙泉、庆元、宣平10县。
(20)(50) 刘为绾口述,2006年7月9日,松阳县界首村。
(22)(43)(48) 刘福儒口述,2006年7月9日、10日、11日,松阳县界首村。
(23)(27)(29) 范晋:《松阳县各学堂调查表》,《浙江教育官报》1909年总第8期。
(25)(52) 刘史贞口述,2006年7月13日,松阳县西屏镇。另见《佳溪刘氏宗谱》上册第2卷第30页。
(28) 《浙江省教育志》编纂委员会:《浙江省教育志》,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01页。
(31) 吕耀钤修,高焕然纂:《松阳县志》,“民国”十五年(1926),第5卷第14页。
(34)(40) 叶根生、钟林根口述,2006年7月10日,松阳县上坞源村。
(41)(45) 刘为藩口述,2006年7月11日,松阳县界首村。
(46) 张光清口述,2006年7月13日,松阳县界首村。
(47) 刘福胜口述,2006年7月15日,松阳县界首村。
(51) “畲客婆”即指畲族妇女,她们没有裹脚的习俗。
(57) 据刘厚体的族侄孙刘为绾老先生称,刘厚体的性格是“激进的、而且会跟上潮流的,胆子很大……这种性格对他的儿子们影响很大,他的好几个儿子都投笔从军,最后去了台湾”。刘为绾口述,2006年7月9日,松阳县界首村。
(59) 所谓“新族学”,是指实施近代教育的宗族私立小学(也有少量中学),以近代科学文化知识为主要教学内容,并采用近代教育方法。新族学“非族大祠富而多明学务不能设”,也就是说兴办新族学往往需要望族的雄厚公产和强大的近代宗族精英力量。详见林济:《国民政府时期的两湖新族学与乡村宗族》,《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2期。
(60) 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50页。
标签:生活教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