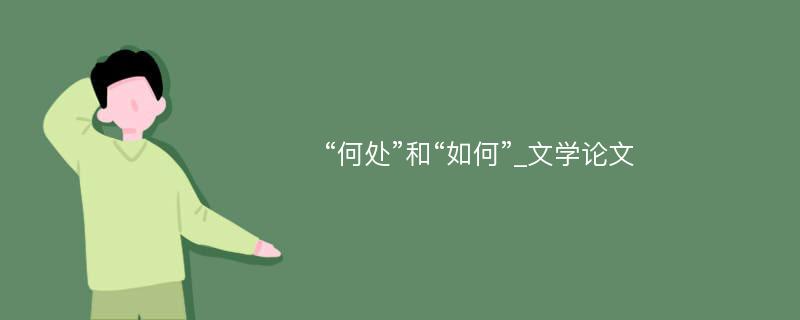
“从何”与“如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以下简称2011年版课标)指出:“阅读教学是学生、教师、教科书编者、文本之间对话的过程。”与《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以下简称实验版课标)不同的是,对话主体增加了教科书编者。与教科书编者对话的既可以是教师,也可以是学生。但由于教师在课堂中地位特殊,其与教科书编者对话,无疑应成为我们优先关注和研究的课题。那么,教师与教科书编者从何对话?又如何对话?这是本课题中必须解决的两个主要的、核心的问题。
一、从何对话:话题与途径
巴赫金认为,对话是“同意或反对关系,肯定和补充关系,问和答的关系”。此解可用于解释不同领域、不同层面的对话关系。但在任何领域展开对话,其前提都是要清楚对话的话题或内容。就教师与教科书编者对话而言,话题或内容具体化为编写意图,而编写意图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去获得、把握。
1.编排体例
现行阅读教学教材都是文选型教材。其中的选文,原为独立创作的文本,教科书编者将它们编成若干单元,再将不同单元组合成整册教材。教学思想、理念不同,对语文课程的认识、理解不同,编排体例就不一致。比如,现行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与旧版教材编写体例不同。人教版新旧教材编写体例的最大区别是:旧版教材以语文训练重点组元,而新版教材则以主题组元。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每个单元(组)包括导语、课例和“语文园地”三大部分。导语揭示主题;课例有四五篇课文,依据共同的主题编辑在一起;“语文园地”大多安排五个栏目:“口语交际”“习作”“我的发现”“日积月累”四个是固定栏目,“宽带网”“趣味语文”“展示台”“成语故事”等栏目中的一个为机动栏目。了解编写体例,把握选文之间、单元或模块之间的组合方式,才能避免游离于体例之外的孤立解读和教学,才能为学生进行拓展阅读提供支点和方向。
2.选文类型
这里的选文类型特指功能类型。功能类型不为选文所固有,而是编者所赋予。不同版本教材中的选文,编者赋予的功能并不完全一致,同一版本教材中所有选文的功能也不完全相同。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中选文的类型有多种,其中以精读课文、略读课文、选读课文为主,此外还有“语文园地”中“日积月累”“趣味语文”“成语故事”等栏目的选文及编进高年级教材“语文综合性学习”中的选文。精读课文的主要功能有三:引导学生学习语言文字,引导学生掌握阅读方法,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略读课文与精读课文在功能上有所不同:后者教给学生阅读方法;前者则要求学生运用阅读方法,借以培养其独立阅读能力。对于选读课文,教师可以根据具体情况上成精读课文或略读课文,甚至放手让学生课后独立阅读。至于“语文园地”各栏目或“语文综合性学习”中的选文,根据出现场合不同,发挥不同功能:“日积月累”“趣味语文”“成语故事”中的选文,主要用以丰富学生的语言积累和文化知识;“语文综合性学习”中的选文,教授重点不在于学“文”,而在于由“文”中信息引发相关的语文学习或实践活动。
3.导读系统
不同版本的阅读教材有不同的导读系统。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导读系统包括单元导语、思考练习、课文注释、精读课文与略读课文之间的连接语、“资料袋”“展示台”以及以学习伙伴口吻出现的“语言泡泡”等。导读系统往往更集中、更具体、更直接地显示编写意图。人教版六年级下册第一单元的导语清楚写道:“学习本组课文,要抓住重点句段,联系生活实际,领悟文章蕴含的道理;在把握主要内容的基础上,体会作者表达感悟的不同方法,并试着在习作中运用。”第一篇课文《文言文两则》课后思考题有:“联系生活实际,你能从这两个故事中悟出什么道理?”第二篇课文《匆匆》课后思考题有:“找出含义深刻或自己特别喜欢的句子……联系生活实际,和同学说说自己的理解和感受。”单元最后的“回顾与拓展”中又有这样的句子:“阅读同一篇文章,不同的人往往有不同的理解和感受。阅读的时候,我们可以联系上下文或结合生活实际,进行独立的思考。”“结合本组课文和以前的语文学习,交流交流对学过的某篇课文的理解和感受,说说自己的见解是怎样获得的,是如何加深的;也可以交流本组课文在表达作者的感悟方面有什么特点,你在习作中是怎样运用这些方法的。”把这些分散在各处的句子串联起来,便可发现,它们遥相呼应,在清楚揭示本单元编写意图的同时,揭示了本单元的教学重点:其一,运用联系生活实际的方法领悟作者从生活中感悟到的道理;其二,学习作者表达感悟的方法。
4.文字改动
文字改动包括修改和删除。近期有人撰文批判现行语文教材,理由之一是“语文教材随意篡改文本原意,其中一些被改得面目全非,甚至只选取了原作写作主题中的一个,很多文章变得毫无营养。原文的精髓和准确、优美的文字都被歪曲或抛弃”。这种情况或许有,但绝不是普遍现象。选文不是为语文教材而写,而作为课文则必须满足教材的特殊要求,因此对选文进行一些文字删改往往是必需的。就现行教材的实际看,文字的改动的确不都是尽善尽美的,个别地方甚至适得其反。但公允地说,大多数地方的文字改动还是满足文字规范需要,适合特定学段学生阅读,切合特定单元主题的。苏教版五年级下册《月光启蒙》有一段文字被编者删去:“母亲患了老年痴呆症,失去了记忆。我赶回老家去看她时,她安详地坐在藤椅里,依然那么和蔼、慈祥,但却不知我从哪里来,不知我来干什么,甚至不知我是谁。不再谈她的往事,不再谈我的童年,只是对着我笑,笑得我泪流满面。”这段文字突出了母爱和感恩,编者将它删去,而留下大量歌谣、谜语,渲染了文学作品给孩子带来的身心上的愉悦,淡化了选文原有的“母爱”与“感恩”的主旨,凸显了选文作为课文的新主旨——文学作品是人成长的精神食粮。
二、如何对话:态度与方式
对话,是交流,是沟通,是碰撞。它意味着对话主体地位平等或人格对等。对编写意图奉若圣旨,一味充当编者的传声筒,不是应有的对话态度,也违背了对话的本义。相反,片面强调教师是教材的创生者,无视或漠视编写意图,自行其是,随心所欲,往往会破坏教材自身的系统性,也糟蹋了教学中最重要、最便利的资源,同样违背对话的实质。
1.理解执行
教材依据课程标准编写,每一册、每一单元教材,从主题和选文的确定和安排到目标要求、教学重点的设定,大多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尽管由于各种复杂的主、客观原因,文章的本意难免存在疏失,但我们不能完全否定教材的科学性。因而,教师与教科书编者对话的第一步,就是理解编写意图,这也是对话的方式之一。对于那些正确的编写意图,或者从课程标准、语文课程与教学科学理论、学生身心特点角度考虑,找不到反对理由的编写意图,必须认真、坚决地执行和落实。
教学《月光启蒙》,没有理解编写意图,不假思索地引入被删除的那段话,并着力渲染母爱和感恩的主旨,这不是与编者对话。有许多课文,当它们还只是独立的作品时,其主旨可能是多元的,往往“横看成岭侧成峰”。进入教材系统后,即使编者未更改其主旨,但在现行主题组元的编写体例下,其主旨也产生一些特定而微妙的变化。因而,与教科书编者对话,不能罔顾单元主题。人教版三年级下册的儿童诗《太阳是大家的》,共有四个小节。第一小节是引子,第二小节写一天中太阳做了许多好事,第三小节与第一小节呼应,是过渡,第四小节写在别的国家,小朋友、小树、鲜花也在等太阳、盼太阳。有位教师执教这一课,着力引导学生品味关键词句,并通过多样化朗读,让学生感受到太阳无私和博大的胸怀。从接受美学角度看,文本意义的生成具有开放性。从《太阳是大家的》中感受到太阳的无私博大,也是对该文本的多元解读之一,这本无可厚非。但该课所在单元的导语是:“地球是人类的共同家园。世界各地的人虽然肤色不同,语言不同,但是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让世界充满爱,让人间充满信任。”教师自己设置的主题很难说存在什么问题,但是考虑到单元主题的要求,教学本课理应让学生明白太阳是大家的——地球上所有的生命都共享着同一个太阳。
2.丰富补充
教材中需要丰富补充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导读系统。阅读教材的导读系统主要发挥导向作用,但要真正全面、深入地引导学生学习,还需要教师将导读系统具体化、细致化,需要教师的创造性劳动。因此,领悟编写意图之后,教师应着力补充和丰富导读系统,以保证教学更有效、更顺利地进行。这是对话的又一形式。
人教版三年级下册第二单元的主题是爱护周围环境,单元导语有两个要求:一是阅读课文看看人们对待动物、植物的态度和做法有何不同,结果怎样。二是留心周围的环境,想想为了保护周围的环境,我们该做些什么。《翠鸟》是本单元的第一篇精读课文,课后思考练习的第三题是:“我们交流交流,下面每组中的两个句子,哪个写得更好,好在哪儿?”将单元导语和课后思考练习结合起来,便可发现,本组课文的教学重点不仅有单元导语中的两点要求,还有对语言文字运用的关注。《翠鸟》课后思考练习的第三道列出两组句子,但本文精妙运用语言文字之处还有很多,所列句子显然不是应关注的全部,教学时不能仅限于此。如:“小鱼悄悄地把头露出水面,吹个小泡泡。”“悄悄”惟妙惟肖地写出小鱼的机灵,“泡泡”的“小”突出了小鱼露出水面之短暂。尽管这样,翠鸟依然能轻而易举将它“叼走”,从侧面衬托出翠鸟动作之敏捷和神速。丰富和补充诸如此类的语言品味教学,既满足了单元导语的两点要求,又强化了对语言文字运用的教学,凸显了语文课程之本色。
3.纠偏救失
尽管教材编者大多是小语领域的专家,其中有的还是资深或权威的专家,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教材编写过程中难免出现一些偏差、过失甚至严重错误。无论是谁,对语文课程与教学的认识都需要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2011年版课标之于实验版课标的诸多变化,反映的正是认识的不断深化。总体上,教材的编写速度赶不上认识不断深入和变化的速度。以不断更新的认识看相对滞后的教材,发现问题就理所当然。现在2011年版课标已经颁布,而配套的新教材尚未面世,以2011年版课标的理念审视旧教材,更易于发现其中的不足之处。面对种种偏差、过失或错误,纠偏救失也是与编者对话。
《手指》是人教版六年级下册的一篇略读课文。在课文前面,编者设计了一段连接语,其核心部分是:“认真读一读课文,想想作者写出了五个手指的什么特点,把自己觉得有意思的部分多读几遍,再和同学交流这平平常常的手指带给我们什么启示。”精读课文与略读课文之间的连接语,大多被教师用作导读。那么,这一连接语导读的方向是否正确?前文已经谈到,本单元的导读系统显示了编写意图:一是用联系生活实际的方法领悟道理,二是学习作者表达感悟的方法。审视这段连接语,不难发现它与整个单元的编写意图有较大出入,这是其一。其二,这是一篇略读课文,这个连接语显然无法引导学生运用前面精读课文中学到的方法进行独立阅读。其三,2011年版课标指出:“语文课程是一门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的综合性、实践性课程。”阅读课文只是理解它说明的道理,显然有失偏颇。面对这些缺失,教师绝不能抱残守缺,而应大胆创生,勇于纠错。我们不妨将以上连接语改为:“作者从手指中感悟到什么道理?把课文中有关句子画出来多读几遍,想一想,生活中还有哪些事物可以说明这个道理?课文全文和写每个手指的段落在结构上都很有特点,你能发现并说出来吗?模仿课文写一篇习作,用上课文构段和谋篇的方法,从生活中选择一种事物来说明你在课文中所感悟的道理。”这样引导学生学习,既紧扣本单元的教学重点,又合乎略读课文的功能定位,同时兼顾“工具”“人文”,强化了“语言文字运用”,整体上优于编者的连接语。
教材无论是编排体例、选文功能、导读系统和文字改动都会出现偏差或失误,但导读系统无疑是问题的高发区。有时单看某个项目的导读内容,似乎没有什么问题,但它与整个系统却不呼应、不和谐,对教师产生误导。贾平凹的《风筝》写“我”童年在秋天里和伙伴们做风筝、放风筝的情景,表现了做风筝、放风筝给孩子们带来的乐趣。这样的选文,放在“民俗”“童年”或“秋天”主题的单元里都合适。人教版教材将它编进三年级上册第三单元“秋天”里,并且在课后安排了“资料袋”,内容有两个要点:风筝的来历、山东潍坊的风筝节。粗看来,其内容似无不妥,但遗憾的是,潍坊风筝节在每年四月。因为“资料袋”的引导,许多教师便在做风筝、放风筝的传统习俗上延伸拓展,使教学与“民俗”主题越走越近,与“秋天”主题越离越远。
当然,掌握对话的话题与途径,把握对话的态度与方式,解决教师与教科书编者对话的这两个主要问题,还只是满足有效对话的基本和必要条件,绝非万事大吉。“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教师与教科书编者对话与此同理。只有全面而深刻地认识语文课程,透彻把握语文教学规律,才能对教科书编者保有充分的理解与尊重,同时保持足够的自尊与自信,从而游刃有余地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