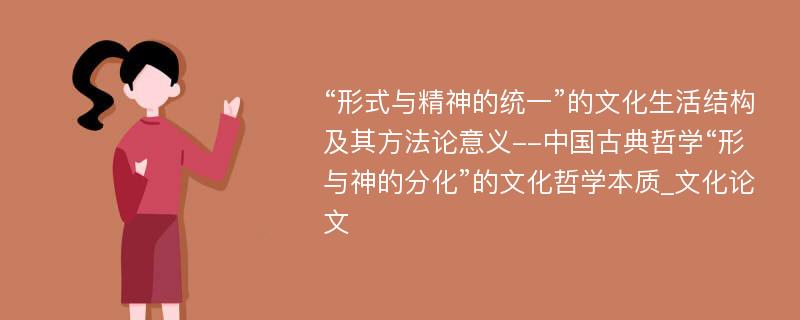
再论“‘形神统一’文化生命结构”及其方法论意义——古典中国哲学“形神之辨”的文化哲学精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形神论文,方法论论文,哲学论文,文化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DOI: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2.001 “形”、“神”和“形神之辨”是古典中国哲学的一对重要范畴和一个重要论题。原是用来对人体生命结构的哲学概括。“形”指形体、肉体,“神”指灵魂、心灵。对于两者关系的辩论,始于先秦,经两汉而终于南朝,由著名哲学家范缜在《神灭论》中作出了总结。他把“形”譬喻为刀之刃,把“神”譬喻为刀刃之利,两者是“质”与“用”的关系,“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是则形称其质,神称其用”,故“形神相即,形质神用,名殊体一”。形具神存,形毁神灭。人的生命体就是“形”与“神”的统一,两者缺一不可。在中医经典《黄帝内经》的《素问·上古天真论》中,也用形神统一论来概括人的生命结构:“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欲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并成为我国中医养生学的基本理论基础。“形神之辨”还是古典中国哲学认识论的重要范畴。“形”指人体五官,“神”指知觉功能。如王夫之在《张子正蒙注·太和篇》所说:“形也,神也,物也,三相遇而知觉发。”是说当形体五官与外物相接而引发感觉、知觉功能,从而产生了认知。 当需特别关注的是,“形神之辨”在历史上还普遍用于绘画、书法、诗歌、小说、建筑等文化领域;这是不同于事实领域的价值领域。就是说,“形神之辨”还具有文化哲学的含义。在这一领域,“神”指文化的核心,即价值观、价值和理想,“形”指主要由语言文字等各种文化符号所构成的丰富多彩的具象和样态。“神”内涵于“形”并由“形”而显现;“形”以载“神”并传“神”。“形”“神”一体,构成了文化生命体。由此,我们提出了“‘形神统一’文化生命结构”这一概念。①这一概念,不仅揭示了古典中国哲学“形神之辨”的文化哲学精义,而且对把握文化的生命本质以及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方法论意义。 一 古典中国哲学“形神之辨”的文化哲学精义 在中国文化史上,最早将关于人体生命结构和认知规律的“形”“神”统一概念用于文化领域的是西汉初年。当时就有思想家和艺术家移用“形神统一”来概括人物肖像绘画这种文化艺术形态的生命结构,从而使“形神之辨”成为美学领域的一对重要范畴。《淮南子》的作者根据其“神贵于形”、“以神为主”、神为“君形者”的观点,认为绘画艺术如果没有“君形者”(神)就不能使人产生美感。《淮南子·说山训》说:“画西施之面,美而不可说(悦);规孟贲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者亡焉。”其原因就是因为这些画作缺失了“神”,强调绘画艺术要在以“形”传“神”。显然,这里所说的“神”就是指通过艺术形象(“形”)而显现的审美价值。东晋大画家顾恺之进而提出“传神写照”的美学命题。《世说新语·巧艺》载:“顾长康画人,或数年不点目睛。人问其故。顾曰:‘四体妍蚩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睹中。’”顾恺之认为绘画传神不在于画人的整个形体相貌,而应着眼于人体肖像(“形”)中最能传神之处(眼睛);唯有画好了人的眼睛才能使人物肖像画作达到“传神”即照示审美价值意境。成语“画龙点睛”,正可作“传神写照”的生动注释。这一“传神写照”、“形以传神”的“形神统一”的审美原则对以后文学艺术的创作和审美评价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宋代大文学家苏轼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②赏画仅见“形”而不识其“神”,就与儿童一般见识。沈括《梦溪笔谈》说:“书画之妙,当以神会,难可以形器求也。世之观画者,多能指摘其间形象、位置、彩色瑕疵而已,至于奥理冥造者,罕见其人。”③很少有人能欣赏画中之“神”(奥理冥造者)。当然,过于强调画作之“神”也失之片面;“画而不似,则如勿画”。应该做到“形神皆备”,如明代李贽所说:“画不徒写形,正要形神在。”④但中国古代绘画艺术的审美原则确有其自己的特点。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学家冯契教授指出:“中国画首先重在表现神、意。”⑤既讲“形神统一”而又重在“传神”,这可以说是对中国传统绘画艺术审美原则特点的一个总结。⑥然而并没有因之而忽视“形”对于传“神”的作用。所谓“传神写照”,正表明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审美原则体现了“形神统一”的文化生命结构。 由人体自然生命结构的形神统一推衍至艺术创作的形神统一,这与其说是一种理论形态的转化,不如说是一个由事实领域到价值领域的飞跃。画中的肖像之“形”不是人的自然形体,也不是对自然形体照相式的写照,而是画家根据审美意象对客体做了取舍后的艺术处理和艺术再造,即画家审美意象的对象化,从而转换成足以传“神”的画像。正如黑格尔所说:“把每一个形象的看得见的外表上的每一点都化成眼睛或灵魂的住所,使它把心灵显现出来”,也就是使画中的“形”成为“心灵的表现”。⑦这里的所谓“心灵”已非自然人的知觉和思维功能,而是画像(“形”)所传的“神”——画家头脑中形成的具有个性特色的审美意象,及其体现于画作的审美价值。一句话,人物绘画艺术的形神统一是画家根据审美意象和审美价值对人体自然生命的形神统一的艺术再造。显然,这是两种不同的“形神统一”。如果说,人体自然的“形神统一”是对人体自然生命结构的自然哲学概括,那么,艺术肖像的“形神统一”则是对人体画像的文化生命结构的文化哲学概括。前者是人体自然生命的事实问题,后者则是艺术审美的价值问题。两者之间确实有一个所谓“事实—价值”的“逻辑鸿沟”。显然,中国古贤不可能意识到直到近代才由英国哲学家休谟提出、直至今天还尚未完全解决的“休谟难题”。不过,古贤却在艺术创作实践中实现了由事实向价值的飞跃;在绘画艺术中以“传神写照”和以“形”传“神”的艺术实践,实现了“形神统一”,由人体自然生命结构向文化艺术生命结构的飞跃。应该指出,不仅人体肖像画如此,凡绘画艺术实践也都实现了由客体对象事实到画作审美价值的飞跃,其画作都包含着“形神统一”的艺术或文化的生命结构。郑板桥在《题画·竹》中总结自己画竹的艺术实践过程,提出画竹的三个阶段,“眼中之竹”——“胸中之竹”——“手中之竹”。“眼中之竹”,就是画家早晨看到的“皆浮动于疏枝密叶之间”的客体的竹。当它映入画家的眼帘,“胸中勃勃遂有画意”,在画家心中生成了“竹”的审美意象。而后“磨墨展纸,落笔倏忽变相”,创作出“手中之竹”,成就了画作,即通过艺术技巧将胸中的审美意象对象化了(变相),完成了“竹”的艺术形象创作。这一过程,正是通过由“眼中之竹”到“胸中之竹”;再由“胸中之竹”到“手中之竹”的两次转化,实现了由事实的竹向价值的“竹”的飞跃。⑧这一论述,十分生动地描述了客体事实到审美价值的转化过程。用“形神”概念来进行概括:“胸中之竹”(审美意象)就是“神”,而最终呈现于画笔下的“手中之竹”,就是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与审美价值即“形神统一”的文化生命体。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在评价顾恺之的画时曾说:“意存笔先,画尽意在,所以全神气也。”⑨“意”或意象,就是先于操笔前在画家心中已形成的对所画对象的理想(冯契先生说:“‘意’就是理想”⑩),画家在画作中将审美的意象、理想对象化,并产生美的感染力——“神气”,达到了以形传神的效果。所以“好的画总是一定情景的结合,表现了某种理想,于是显得气韵生动,形神皆备,有意义有性格。”(11)后来(清)叶燮将绘画艺术的一般规律做了一个概括:“凡遇于目,感于心,传之于手而为象,惟画则然”。(12)但是,正如郑板桥所说:“独画云乎哉”!(13)就是说,不仅是绘画艺术,凡是文化的创造都具有这样的规律。“‘形神统一’文化生命结构”正是中国古代画家艺术实践所表明的艺术或文化创作过程及其规律性的概括,显现了古典中国哲学“形神之辨”的文化哲学精义。 二 “形神统一”:中国哲学语境中的“文化生命结构” “形神统一”由概括人的生命结构的自然哲学转型为用来概括绘画艺术的文化哲学概念,成为表述“文化生命结构”的独特的哲学术语,成为在中国哲学语境中的一个普遍的文化哲学范畴。就是说,我们不可把“形”、“神”及“形神统一”的范畴和命题,仅仅局限于绘画美学,看作只是中国美学史上与“风骨”、“神韵”、“气韵”、“气象”、“意境”、“韵味”等同等地位的一个特殊的美学概念。实际上,它虽由绘画美学提出,但其概括力则远远超出了绘画美学而成为一个高于其他美学概念的文化哲学范畴,具有涵盖文化领域的普遍性,是对各种样态文化的生命结构的概括。其实,“风骨”、“神韵”、“气韵”、“气象”、“意象”、“意境”、“韵味”等概念,都可归属于“神”这一范畴。这里我们不可能穷尽对所有的各种文化形态“形神统一”生命结构的论述,除已论述的绘画艺术,再就传统文化中的诗词、书法、文学、建筑以及学术典籍、礼仪道德的生命结构做一论述,以表明“形神统一”作为文化哲学范畴的普遍性品格。 “诗言志”。(14)“志”主要是指赋诗者的情感、志趣、抱负、理想。后来又提出“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15)把“志”与“情”统一起来。(唐)孔颖达明确认为:“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16)“志”或“情”就是诗人赋诗所要表达的志向、理想和好恶、爱憎的情感,即体现为审美意象,也就是“神”。诗,就是其言(形)与其志或情(神)的统一。正如叶燮所说:“诗与画,初无二道也”。画是“遇于目,感于心,传之于手而为象”;诗是“触于目,入于耳,会于心,宣之于口而为言”。“乃知画者形也,形依情则深;诗者情也,情附形则显”。(17)遇于目、入于耳者,即画与诗的对象,是指“天地万事万物之情状”。当这种“情状”遇于目而感于心或触于目、入于耳而会于心,则形成了创作者的审美意象(情),也就是“神”。它传之于手而为“象”,“象”即画之“形”;宣之于口而为“言”,“言”即诗之“形”,也就是《毛诗大序》所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由此可见,“画者形也,形依情则深”,固然是形与神的统一;“诗者情也,情附形则显”,同样也是形与神的统一。两者“形”虽不同,但都是在传“情”(“神”)。“故画者,天地无声之诗;诗者,天地无色之画”。(18)而且,从“则深”、“则显”可知,在叶燮看来,这一“形神统一”结构,正是诗画生命之所在。 作为中国美学所独有的书法艺术,她与绘画、诗文相一体,同样可用“形神统一”来概括其生命结构。“为书之体,须入其形”。(19)书法是一种视觉艺术,自然有其形态万变的“形”。正是通过千姿百态的“形”给人以形象美的欣赏。但更为本质的东西是内涵于其“形”中的书法家的情意。点画的粗细长短,结体的大小正侧,墨色的浓淡枯湿,通篇的疏密虚实:“若坐若行,若飞若动,若往若来,若卧若起,若愁若喜,若虫食木叶,若利剑长戈,若强弓硬矢,若水火,若云雾,若日月……”(20)都是创作者情意的宣泄,而这就是书法作品之“神”。王羲之的《兰亭序》之所以魅力无穷,正在内含于其中的体现了魏晋风度的作者情意。古今抄写临摹者由于没有了那份魏晋风度的情怀,因而诸多的临摹本只是形似而已,却没有《兰亭序》本有的生命气息。绘画艺术是“传神写照”、以形传神,诗歌作品是以文言志,书法创作同样是以形传神(情),所有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都是形与神统一的生命体。 小说戏剧着重于叙事,都是按一定的创作构思,通过一定的话语、情节、动作、场面来展开对人物性格的描写,而所描写的人物性格又是典型的。文学中的所谓“典型”,就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明末小说点评家叶昼称之为“同而不同”,“同”即共性;“不同”即个性。他点评《水浒传》,认为施耐庵、罗贯中所描写的人物性格都“各有派头,各有光景,各有家数,各有身份”,“真是传神写照妙手”,体现的“是形神皆备的性格”(冯契语)。评武松和李逵二人打虎情景的不一样描写,认为这“正施、罗二公传神处”。又评对郓哥的描写说:“有一语不传神写照乎?”(21)将原来用于绘画艺术的“以形传神”和“传神写照”的概念,引入小说美学的领域。“形神统一”同样也是小说戏剧创作和批评的审美原则。清嘉庆年间有位署名“二知道人”在《(红楼梦)说梦》中论述关于小说“传神”时也说:“盲左、班、马之书,事实传神也;雪芹之书,虚事传神也。”(22)认为史书和小说虽有不同的“形”(或实或虚),但都是“传神”,表明了“形神统一”在中国传统文化史领域所具有的普遍性品格。下面,我们还可以看到在中国古典园林美学的“意境”这一范畴中所体现的“形神统一”创作规律。 园林美学是中国古典建筑艺术的典范,其美学特点集中地表现了审美意境。“意境”,是中国美学特有的审美范畴。从文化哲学的角度来解释,它同样离不开“形”与“神”这对范畴。王夫之十分推崇“意境”。他在《唐诗评选》(卷一)评价刘庭芝《公子行》一诗说:“脉行肉里,神寄影中,巧参化工,非复有笔墨之气”。(23)“神寄影中”说的是一种写诗的艺术创作方法。所谓“神寄影中”的“影”,就是“具体景物溶进艺术家感情和意图而构成的一种新颖独特的景象。”这种“景象”,就是“意境”。(24)它寄托着艺术家的“意”(“神寄影中”),并通过艺术形象(“形”)而显现(传神)。不过,正如叶朗教授所指出:“园林的意境和诗歌、绘画的意境不同。诗歌、绘画的意境是借助语言或线条、色彩构成的,而园林的意境则是借助于事物构成的。但是园境和诗境、画境在美学上有共同之处。这共同之处就是‘境生于象外’”。(25)就是说,园林的美学意境虽以楼、台、亭、阁的实物构成其艺术形态(“形”),但同样体现了“形神皆备”这一美学创作的要求。“轩楹高爽,窗户虚邻;纳千顷之汪洋,收四时之烂漫。”(26)园林中楼阁的一架轩楹一扇窗户却使浏览者从这有限的空间“看”到了大自然的无限风光。它超越了有限的轩楹和窗户艺术形象,却展现了“神寄影中”的美学意境,给人以美的享受。 “形神统一”不仅是美学文化的创作原则和生命结构,而且还是伦理道德文化的生命结构。下文就传统的礼仪道德试做论述。 中国传统的礼仪之作为一种道德形态,是主体通过践行具体的行为规范和行为样式,以表达对客体的“恭敬”、“辞让”(谦让)之心。它有两部分要素构成。一是由语言文辞、形貌姿态和服饰器物等根据宗法等级差别按一定程式、程序所进行的行为样式;一是由一定程式、程序的行为样式所表达的道德要求。前者是礼仪节文,后者则是主体内心的恭敬和辞让的道德价值和道德情感,或曰礼仪道德。两者的关系,《韩非子·解老》用“外”和“内”来进行概括:“礼者,所以貌情也”,“礼者,外饰之所以谕内也。”这里所说的“礼”或外饰之“礼”是指礼仪节文;而所说的“情”、“内”是指道德情感、道德价值,或曰内心道德意识。外饰的礼仪节文用来显现内在的道德意识;“礼仪”就是外在的礼仪节文与内在的道德意识的统一。这有一定的意义,但显得过于直观,未能体现礼仪作为一种文化样态的生命体征。古人也有用“本”、“末”来做概括的。把内心的道德意识视为礼仪之“本”,而外在的礼仪节文是礼仪之“末”,认为“有本然后末从之”,突出了道德意识对于践行礼仪节文的重要性,达到了哲学的深度,具有一定的哲学概括力。魏晋玄学家王弼曾用以概括德性良知和道德规范两者关系,提出“崇本抑末”,认为德性良知是道德实践之根本(“本”),而道德规范只是“末”;讲道德不可执着于道德规范(“末”)。强调了德性良知对于道德实践的重要性,但未能概括道德规范对于表达德性良知及其在道德实践中的作用。显然,“有本然后末从之”的“本末之辨”,没有能概括礼仪节文对表达道德意识及其在礼仪践行中的作用,没有能辩证地全面反映“礼仪”作为一种文化样态的生命结构。值得注意的是宋陈澔的说法。他在《礼记集说序》说:“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孰非精神心术之所寓”。这里所说的“精神心术”就是指人们内在的道德意识(德性),也就是“神”。(27)陈澔的这句话是说,礼仪其“神”即寓于礼仪其“形”。可见,礼仪作为文化的一种具体形态,同样具有“形神统一”的生命结构。 当我们确立了“形神统一的文化生命结构”这一概念,并用这一概念来考察和总结古人的礼仪实践,就可以发现儒家对礼仪实践的一条基本的价值原则——重“神”。儒家更重视礼仪其“神”,而礼仪其“形”之所以必要,在于其能表达践行者的恭敬、辞让之心;为了表达恭敬、辞让之心,礼的仪式节文是少不得的。《礼记·仲尼燕居》载:“子曰:‘敬而不中礼,谓之野;恭而不中礼,谓之给……’子曰:‘给,夺慈仁。’”这里的礼是指礼仪节文。“野”即粗野,举止不文明。“给”,陈澔注:“曲意徇物,致饰于外,务以悦人,貌虽类于慈仁,而本心之德则亡矣。”(28)意思是说,行为如不符合“敬”、“恭”的礼仪节文,就会举止粗野或因礼节表演过度而虚情假意。这是说礼仪之“形”对于显现礼仪之“神”的重要性。 但是,礼仪之“形”毕竟是为礼仪之“神”服务的。儒家强调的是礼仪其“神”,即礼仪所内含的道德情感。孔子就说:“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29)表明了他对没有道德情感而只求礼仪节文的不满。《礼记·檀弓上》也说:“丧礼,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哀有余也。祭礼,与其敬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敬有余也。”认为无悲哀之情,丧事的仪式节文也就没有了价值,成了虚文伪礼。关于祭礼,《礼记·祭统》说:“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于心者也,心怵而奉之以礼,是故唯贤者能尽祭之义。”又说:“是故贤者之祭也,致其诚信,与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礼,安之以乐,参之以时,明荐之而已矣,不求其为,此孝子之心也。”陈澔《礼记集说》注曰:“尽其心者祭之本,尽其物者祭之末,有本然后末从之。”其所说“本”、“末”,我们表述为“神”、“形”;祭者有怵惕敬重之心才会自觉自愿地践行祭礼仪式节文。“心有所感于内,故以礼奉之于外”,同样强调了礼仪其“神”。所以孔子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30)对人的礼敬,难道仅仅是送玉帛而已吗?俗话说,“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正体现了传统礼仪重情(神)的特点,而鄙视那种虚情假意的装模作样的“礼节”、“礼貌”、“仪式”。孔子直言:“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31)明代吕坤也说:“废文不可为礼,文至掩真,礼之贼也,君子不尚焉。”(32)制定礼仪的用意在于表达人们的恭敬、辞让的道德情感,在于以“形”传“神”。但是,如果“人一味在应酬上留意,真意便少”(33),以至于走向虚情假意、装模作样,使礼仪丧失了内涵之“神”,成为虚伪者的工具。即《礼记·仲尼燕居》所谓“薄于德,于礼虚”。而过于繁细的礼仪程式,也会使人忽视对其“神”的关注。宋代大儒朱熹就关注到了这一问题。指出古礼“忒煞繁细”,认为“古礼于今实难行”,“周礼如此繁密,必不可行”。因此,为了防止人们把精力过分地放在礼仪的繁文缛节上而至于使礼仪成为虚文伪礼,朱熹就认为要应“人情趋于简便”的变化,对古礼应作“简易疏通”,提出了“礼,时为大”的观点,(34)同样表示了重“神”的价值原则。 所以,礼仪道德重在主体的内心情感,在于主体具有恭敬、辞让之心,而不在于它的礼仪节文;道德行为之所以具有感动人的魅力,也正在于其内在的“神”。所以荀子说:“诚心守仁则形,形则神,神则能化矣。”(35)认为有真心实意的爱人之心,就会有爱人的道德行为(“形”),而“形则神”,就会使爱人之心产生感人的魅力,从而感动人心——“神则能化矣”。这说明,真正出自诚心的道德行为是道德其“形”与道德其“神”的统一。道德能以感化人心的主要不是其“形”,而是通过“形”而显现的“神”。同理,礼仪之能产生感人的魅力,也在于礼仪其“神”——行为主体的恭敬、辞让之心。 其实,经、史、子、集古代文献也无一不是“形”与“神”的统一。其“形”就是文字典章,其“神”就是内涵于文字典章并通过文字典章而体现的义理和价值观。一部中国传统思想史正是通过经、史、子、集这些文字典章载体而内涵的义理、价值观演变发展的历史,其中就包含着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我们今天之所以要保护中国固有的语言文字和文化典籍,其根本的目的就是要保护、继承和弘扬承载于其中的优秀的义理和价值观。 以上考察虽不全面,也不深入,但已足可证明“形”“神”这对范畴的运用在中国传统文化各领域的普遍性(或曰广泛性)和重要性,就是说,“形”与“神”是中国传统文化史上的一对广泛使用的概念。这是我们用“形”与“神”来概括文化生命结构的历史依据。 这里需要讨论的是,在中国的哲学语境中,除了“形”与“神”,是否还有别的语词可用来概括文化生命结构?关于“外”与“内”、“本”与“末”,前文已有论辩。这里再就时下有人用“体”(形体)与“魂”(灵魂)二词来概括文化“体系”作一评述。当然,“体”、“魂”也是中国人的独特用词。但其所用的语境与“形”、“神”有别。“体”、“魂”多指人体及其生命的事实存在,“形”、“神”则多用于美学等文化领域的价值存在。而且,在中国的语词系统中,“体”与“魂”相对成词,不是常用的语词。“魂”多与“魄”相连,即所谓“魂魄”;“体”与“魄”连用,即所谓“体魄”。成语“魂不附体”,只是形容一个人不知所措的心理状态,显然不具有哲学的意义。现在我们常说的“价值观是文化的灵魂”。这里的“灵魂”一词单用,仅用来表述价值观在文化中的核心地位;如果将“灵魂”用来指文化生命结构的构成要素,那么与“灵魂”相对的就是“形”;这时,“灵魂”一词也就表述为“神”这个词。我们在关于“文化生命结构”上之所以主张用“形”而不主张用“形体”一词,其主要的理由是,“形”,如上所述是自然物的艺术再造,相当于卡西尔所说的文化“符号”(下详),它不是“物理的实体性的存在”,而“仅有功能性的价值”;“形体”则是指自然物或物理的实体,而作为思想性或精神性的文化就不是自然物的“实体”存在,因而用“形体”一词来概括思想或精神文化的生命结构,显然是不合适的。我们认为,用“形”与“神”这一对在传统文化史上一贯所用的具有普遍性的哲学语词来概括文化生命结构,是较为妥当的。 不同领域的文化形态——绘画、诗歌、书法、小说、建筑以及礼仪道德等所说的形、神及其关系都各有所指(个性),但在各不相同的个性中却有着一般的共性。“神”指文化主体的价值观以及由价值观指导下的价值创造,或者说是文化主体的真善美追求及其在创作中所达到的境界;“形”指各种“人化”的文化形态的具体样式。它们作为文化之“形”不是自然物实体性存在,而是表达“意义”(传神)的功能性的“符号”,是文化其“神”融于其中的符号载体。例如郑板桥的画作形态“竹”,即是事实竹的艺术再现或曰艺术符号,承载并传达着郑板桥独立坚强、高风亮节的人格精神。一首题画诗《竹石》有云:“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你东西南北风。”因而给人以人格感悟和美的享受,即荀子所说“神则能化矣”,体现了郑板桥绘画作品“竹”的“形神统一”的生命结构。哲学讲的是事物的“一般”,是对万事万物之个性的抽象和概括。我们提出“‘形神统一’文化生命结构”这一概念,正是在中国哲学语境中对绘画、诗歌、书法、文学、建筑以及礼仪道德、学术典籍等具体文化形态的生命结构的哲学概括。近代思想家梁启超把文明区分为“形质之文明”与“精神之文明”,他在《国民十大元气论》中明确指出:“精神既具,则形质自生,精神不存,则形质无附”。这里所说的“形质”指的就是文化之“形”,“精神”就是文化之“神”。他强调了文化之“神”对于文化创作的重要性。当然,形质不存,则精神也无所寓;“神”融于“形”并通过“形”而显现(即形以传神)。总之,形神统一,缺一不可,构成了文化的生命结构。 当然,要使“‘形神统一’文化生命结构”确立为一种文化哲学的概念,在理论上还需要进一步的论证。 三 “‘形神统一’文化生命结构”的理论论证 如果说,上面所述是对“‘形神统一’文化生命结构”的文化史的和经验的考察和概括,那么,下面则是对“‘形神统一’文化生命结构”的理论论证。就是说,这一由古典中国哲学术语概括的文化哲学概念,具有文化学的普遍性。 文化是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的价值创造,是人的自由自觉劳动的产物,是人的“类特性”即“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或曰“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因而,文化就是“人化的自然界”,简而言之,也就是“人化”。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本质的基本观点。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诚然,动物也生产。动物为自己营造巢穴或住所,如蜜蜂、海狸、蚂蚁等。但是,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属于它的肉体,而人则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36)这是学界在讨论“文化”时经常引用的一段经典文字,表明了马克思对“人”与“文化”以及“文化”之本质和特性的根本观点。马克思认为,蜜蜂、海狸、蚂蚁等动物的生产是按照其本能的支配而进行的,它只生产它自身。因而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不自由的,不可能构造出与己不同的产品来,不能在自己的产品中直观自身。而人则能够普遍地生产,能够按照任何一种物的性能(尺度)来进行生产,因而人可以“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而且还“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使自己固有的尺度对象化,并在对象化的产品中直观自身。就是说,人不仅能自由地按照任何一种客观对象物的性能来进行生产,而且还有目的地根据自己的价值理想来进行构造,从而使产品符合自己的意愿和理想。“因此——马克思才说——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可见,人的劳动生产的产品,是人在自己价值观(也包括审美价值观)支配下按照对象物种的尺度(性能)进行劳动生产的产物,也就是将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了,“成为人自己的本质力量的现实”,并在对象化的现实中直观自身——“肯定自己”,获得“美”的享受和快乐。这一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了的现实,就是由人创造的合乎人的理想目的的“价值”,就是“文化”,马克思称之为“人化的自然界”。 上面所引的马克思所说的这段经典文字,可以使我们认识文化的本质及其生命结构。文化不是自然物,而是人在社会实践中按照人的价值理想和目的对自然物对象进行了改造的产品,因而文化的生命和本质是人在社会实践中作用于并赋予对象物的价值观和价值。人在社会实践中创造了文化,而文化之所以是“文化”,正在于她内涵了文化创造者主体的价值观,价值观是文化的生命所在,没有价值观也就无文化可言。所以说,“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是文化的灵魂——文化之神”。菲利普·巴格比在其《文化:历史的投影》一书中就用“精神”一词来概括文化的价值观。他说:“用‘精神’一词仅仅去意指不同文化的基本观念和价值……在整个历史上,每一种文化都由于独自的风格,亦即一套观念和价值而带上了特性”。(37)这里的“精神”一词与中国哲学话语的“神”完全一致,都是指作为文化之核心的价值和价值观。可见,将文化的价值和价值观视为文化之“神”,如同灵魂之于人的生命,是文化之生命所在。这是古今中外的共同观点。但文化其“神”或“精神”不是独立自存而不可见的力量,而是有其载体或“负荷者”(巴格比语)的,是需要而且可以传达和显现的。这个传达和显现的东西就是“形”,也就是恩斯特·卡西尔所说的文化“符号系统”。这样,如果说,在中国文化哲学的语境中,“形神统一”构成了文化的生命结构,那么,在西方文化哲学的语境中,构成文化生命结构则是“符号”与“精神”的统一。这就是说,对于“文化生命结构”,中西的文化哲学的看法也是一致的,甚至可以说是相同的。 卡西尔作为西方文化哲学的创始人和代表者,在其代表性著作《人论》一书中对其提出的文化符号理论做了系统的论述。他的文化符号理论对于我们认识和把握“‘形神统一’文化生命结构”的普遍性品格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卡西尔区分了“信号”与“符号”。他指出:“信号和符号属于两个不同的论域:信号是物理的存在世界之一部分;符号则是人类的意义世界之一部分。信号是‘操作者’(operators)而符号则是‘指称者’(designatprs)。信号……有着某种物理的或实体性的存在;而符号则仅有功能性的价值。”(38)动物会对信号做出反应,有的动物(如狗)甚至对信号极其敏感,但“这些现象远远不是对符号和人类言语的理解”,而只是由巴甫洛夫的实验所证明的称之为“条件反射”的现象。有的动物(如黑猩猩)用手势或脸部动作可以表达愤怒、恐惧、绝望、悲伤、恳求、愿望、喜悦和玩笑等情绪、情感。然而尽管如此,“它们的这些表达根本不具有一个客观的指称或意义”。与动物有别,只有人类才具有与信号不同的符号系统。这个符号系统,包括概念语言、情感语言、逻辑的和科学的语言以及诗意想象的语言等。除了语言符号,当然还有数字符号(数学)、音符符号(音乐)、各种形象符号(绘画、书法、雕刻、建筑、造型等)、各种行为符号(如表演艺术、行为艺术)等。卡西尔认为:“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并且人类文化的全部发展都依赖于这些条件”。(39)这是说,人类生活的典型特征,就在于能发明和运用各种符号,从而创造出一个“符号的宇宙”——“人类文化的世界”。因为符号(主要是语言)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具有抽象性,也就是具有“普遍适用性”,因而可以用来进行理性思维去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据此,卡西尔认为:“符号的功能并不局限于特殊的情况,而是一个普遍适用的原理,这个原理包涵了人类思想的全部领域”。(40)人类正是具有了这样的各种不同形式语言的符号系统,靠着“符号化的想象力和智慧”,才有可能创造出人类所特有的文化——神话、艺术、文学、哲学、科学、宗教等。“没有符号系统,人的生活就一定会像柏拉图著名比喻中那洞穴中的囚徒”。(41)卡西尔进一步指出:“人类文化并不是从它的构成的质料中,而是从它的形式,它的建筑结构中获得它的特有品性及其理智和道德价值的。”(42)这个“它的形式”,就是文化符号结构。卡西尔认为,正是通过多样、多变的文化“符号”结构,向社会传达着文化所内含着的人类的价值观、价值和理想,使人获得文化所特有的“品性及其理智和道德价值”。用中国文化哲学的语言来说,各种文化“符号”就是各种文化其“形”;它的功能就是传达、从而使人获得文化所特有的价值和理想、即文化其“神”,这也就是“形以传神”。 显然,在卡西尔的文化哲学中,对符号在文化结构中的作用和地位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在他看来,文化的内在价值和价值观本来就是“符号”题中应有之义,因此,所有的文化形式都是“符号形式”。卡西尔说:“正是符号思维克服了人的自然惰性,并赋予人以一种新的能力,一种善于不断更新人类世界的能力。”(43)这样,“我们应该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来取代把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指明人的独特之处,也才能理解对人开放的新路——通向文化之路。”(44)就此而言,卡西尔不仅把文化“符号”提到了“人”之本质的高度,而且对之在文化生命结构中地位的重视,超过了中国文化哲学对“形”的重视;中国文化哲学讲“形”是为了“传神”,强调的是文化其“神”。这正如上文所说冯契教授评论绘画艺术的中西文化差别所做的——可能就是中西文化哲学在关于“文化生命结构”上的理论差别。 值得注意的是,卡西尔提出“人是符号的动物”的这一观点,还具有深一层的涵义。说“人是符号的动物”,也就意味着人作为类的存在本身就是文化的存在,或者说,“人是最重要的文化形态”(45)。这就是说,“文化”是“形神统一”的生命存在,也是说“人”是“形神统一”的文化存在——人运用“符号”在文化创造中使自己的价值观人格化了。这就是说,人不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存在,而且还是文化学意义上的生命存在;人不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形神统一的生命体,而且还是文化学意义上的“形神统一”的生命体。人如果丧失了后一种意义的生命存在,即丧失了作为文化之人格化存在,无异于成了行尸走肉,与禽兽无异。所谓“文化自觉”,归根到底就是每个人自觉到自己也是一种文化的生命存在,自觉到自己是怎样的一种文化存在,从而不断地提升自己的人格境界。这正是“人是符号的动物”的深义所在。 以上论述尚不全面而深入,但已可以表明,我们提出的“文化生命结构”和“‘形神统一’文化生命结构”,具有文化哲学的普遍意义,尽管具有中国文化哲学的民族特点。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提出来进行讨论。这就是,就文化哲学而言,我们提出文化的“形”与“神”以及“形神统一”与“形式与内容统一”这对范畴的关系。我们的看法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适用于宇宙的一切事物。而在文化哲学领域,“形神统一”仅适用于“文化”现象,它更能概括文化“生命结构”的特质。而“形式与内容统一”可以用来概括文化体系结构,却不能确切地概括文化的“生命结构”。或者可以说,“形神统一”是形式与内容这对范畴在把握“文化生命结构”上的特殊形态。 形式与内容是概括事物构成的一对重要的哲学范畴。内容指构成事物的一切内在要素的总和。形式指把事物的内容诸要素统一起来的结构或表现内容的方式。内容是事物存在的基础,形式是表现事物内容的方式。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内容和形式,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体。自然,文化作为社会的事物存在,也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体。但是,文化与未经过“人化”的“自在之物”(即自然物)有别,它是“人化的自然界”,其内容和形式都具有“人化”的特征。因而一般地用内容和形式来概括文化的结构、尤其是文化的生命结构,就不能体现文化结构的“人化”特征。首先,文化的内容是文化的一切内在诸要素的总和,而其核心和体现文化特质的却是价值观和价值。显然,价值观和价值虽是文化的内容,但仅以“内容”这一范畴却不能标识作为文化之核心的价值观和价值。而与“形”相统一的“神”则恰好确当地概括了文化内在的价值观和价值。其次,仅用内容和形式来概括文化的结构,正如现实所表现的那样,会忽视文化的核心而将文化的内容元素化、碎片化。人们出于某种需要,往往以某种所谓的“文化元素”来充当文化本身。如某些剧作者之所为,他们以为加上了中国文化的某些“元素”就代表了中国的文化,就是在弘扬中国文化。而实际效果,很可能背离了中华文化精神,糟蹋了中华文化。其认识上的原因就是没有把握“‘形神统一’文化生命结构”概念,忽视了文化其“神”;而无视文化其“神”,也就不可能在文艺创作中真正把握中国文化的精神和特征。同时,既然“内容”这一范畴不能确切地标识文化的核心内容,那么与“内容”相统一的“形式”也不能确当地显现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价值。就是说,所谓“形式”,与“传神写照”的“形”有别。文化其“形”同样是“人化”的。“传神写照”——“画龙点睛”,画中的“睛”是人体自然眼睛的艺术再现,因而才具有“传神”的美学功能。正如叶昼点评《水浒传》中所描写的人物性格都“各有派头,各有光景,各有家数,各有身份”,称之为“传神写照”。“仁者爱人”是儒家孔子思想体系的“传神写照”;“道法自然”是道家老子哲学思想的“传神写照”;“唯法为治”是法家韩非“法治”思想的“传神写照”……“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是文天祥《过零丁洋》诗篇的“传神写照”;“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是林则徐《赴戌登程口占示家人·其二》诗篇的“传神写照”。自然,卡西尔评莎士比亚的作品,指出“每一个莎士比亚笔下的角色都说着他自己的独一无二的不会弄错的语言。在李尔王和麦克白、勃鲁托斯或哈姆雷特、罗瑟琳或比屈里士那里,我们都听到这种个人的语言,它是一面反映个人灵魂的镜子。”(46)说的也是“传神写照”。这些都是点“睛”之作。但它不是形式之全体,当然也不是对象物的形式,而是“形式”之特殊者。因此,与“神”相对应,我们将作品中的点睛之处,称之为“形”。 正如“内容”包含但不等于“神”,“神”仅指文化的核心内容;“形式”也包含了“形”,但不就是“形”。“形”指最能显现文化其“神”的符号和载体。据此,我们认为“形”与“神”、“形神统一”是形式与内容这对范畴在把握“文化生命结构”上的特殊形态,具有特殊的意义。在文化的创作中,应该引入“‘形神统一’文化生命结构”这一范畴。 文化其“神”是文化的核心,本质上是指价值观、价值和理想信念。这是哲学的一般概括。事实上,不同文化形态的“神”又各有其特色。如哲学的“神”就在于追求真、善、美的统一;文学艺术美学的“神”就体现为志趣、情感、意象、意境、神韵、风骨,体现为文学艺术家的人生观和人生态度等;教育文化的“神”就是培育学生具有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这是教育的根本价值观和所要追求的价值;体育文化的“神”就集中地体现为运动员的竞技风格……凡此种种,表明文化其“神”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范畴,不能作单一化、教条化的理解。 文化其“形”也十分丰富,可以分为几个层次:第一,语言文字。它是表达文化内在价值观和价值的第一和基本的符号系统。“诗言志”。诗人以典雅的精炼词语、优美的文字节奏,创作了意境丰繁的诗篇,表达了诗人的思想情感和人生态度,传达着高尚的价值追求和理想信念。哲人以精到的哲学概念和范畴的语词,以严密的逻辑建构起理论体系,反映了哲人对宇宙万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的认识,显现了哲人对真、善、美的追求。凡此种种,都表现为自具特色的语言符号。而且,都各有一些最能突出地表达其“神”的“形”——语句、概念、范畴。这些语句、概念、范畴往往还具有不可翻译性,如中国文化中儒家和道家的“仁”、“命”、“天”、“道”等基本范畴。语言的“不可翻译性”这种情况正体现了一种文化的民族特殊性,也说明一种文化的“形”与“神”的不可分离性。如果抛弃掉本民族这些语词,或者勉强地换成了另一种民族的语词,该文化的独特性也就丧失了。第二,经典文献和理论学说,即价值体系的理性的系统阐述。“文献”和“学说”应作广义的理解,如儒家文化,既包括《四书五经》、“理学”这样的经典文献和理论学说,也包括老百姓口口相传的故事、俚语和格言。从解释学的观点看,一种独特的“传统”文化存在于对经典文献(文本)的创造性解读之中。第三,人们的生活方式及其包括建筑、器物等物态样式。生活方式之为文化的“形”,是指传递文化价值的社会活动,表现为各种功能性、仪式性、规范性、审美性的社会活动,如学校教育、学术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广播影视、新闻出版、网络互动、道德实践、宗教活动、风俗习惯以及不同物态和风格的建筑、器物等。其中所内含的文化其“神”,正通过其“形”而显现。 总之,“形具神存”,“形毁神灭”;“神”涵于“形”,“形”显现“神”。“形”既是结构性的概念,是“神”的载体,又是功能性的概念,它的功能就是“传神”。而“神”为“君形者”;“形”无其“神”,也就成了无魂的躯壳,于是文化也就丧失了生命活力。“形”“神”统一,“形”“神”一体,正构成了文化的生命结构。关于文化生命结构的这一哲学概括,对文化建设和继承传统文化、保护文物古迹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四 “‘形神统一’文化生命结构论”的方法论意义 我们用“形神统一”概括文化生命结构,较之“内与外”、“本与末”、“形体与灵魂”以及“形式与内容”等范畴,更能体现文化的生命特征。“神以君形”、“形以传神”。凸显了价值和价值观对于文化的核心地位,也表明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形态、样式(即符号)对于显现文化之核心的价值观的能动性和重要性。“形”为传“神”而存在。但是,“形”与“神”是矛盾的统一,毕竟是有差异的两个不同的概念。因而在一定的条件下,在创作实践中,由于认识和审美价值观的偏差,就会出现或重“形”而轻“神”,或重“神”而轻“形”的片面性;或陷入形式主义,或走向教条主义。这些都破坏了文化的生命结构,使文化作品丧失了“神则能化”的价值功能。在社会经济变革或转型时期,由于价值观的急剧变革,需要创造与新价值观相适合的“形”,而原有的“形”往往落后于价值观的变革而成为保守的力量。当然,改造原有的“形”与新价值观的统一,这需要时间,会有一个磨合的过程;也可以引入外来的“形”作为新价值观的符号,但同样有一个磨合、适应的过程。鉴于上述情况,在我国社会主义的现实文化建设的实践中,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应找到更为合适的“形”来显现文化其“神”,努力做到“传神写照”,实现“神则能化”的文化功能。切忌“形”和“神”两者关系的片面化、教条化和庸俗化;在文化的创作中,要充分注意“形”的创意和创新,以适应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在对待传统文化上,形以传神,形以载神,要保护好文献经典、文物古迹。破坏文物其“形”,就会消亡文物其“神”,就是破坏传统文化。因而,为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必须保护传统文化其“形”。显然,文化其“神”与其“形”相统一的辩证法,对于包括继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文物保护的社会主义现实文化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形以传神”,任何礼仪节文的制定都是为了表达主体对客体的恭敬、辞让等道德价值和道德情感;而无其“神”,则再精细周到、豪华壮丽的礼仪节文也只是虚有其名,如古人所说的那样,“薄于德,于礼虚”,成为形式主义的或虚情假意的虚礼、伪礼,致使阿谀奉承成习、奢靡之风盛行。因此,文明礼仪的建设,重要的是培育人们具有恭敬、谦让等道德情感和道德观念,这样才能赋予礼仪以生命气息,也才能使人们自觉自愿地,即真情实意地去遵守和践行合乎恭敬、谦让等道德要求的礼仪节文,达到形与神的统一。同时,由于礼仪其“形”是礼仪其“神”的载体,我们也要重视礼仪节文的作用和礼仪样态的设定,以通过礼仪节文的践行来培育人们的礼仪道德。当然,礼仪节文即礼仪之“形”的设定,也要如朱熹所说的那样,简易、适时,反对繁文缛节、铺张浪费。总之,我们应该在现代文明礼仪建设的实践过程中,根据礼仪其“神”与礼仪其“形”统一的原则,辩证地使礼仪节文与礼仪道德结合起来,达到礼仪其“神”与礼仪其“形”的统一,从而不断提高人们的文明素质。 现在,我们在道德建设上缺的不是作为道德之形的规范,我们已经提出了一整套的道德规范体系,但还是一直讲“一些领域道德失范”。实际情况是,有规范而无规范践行,有的则是种种“潜规则”横行,道德败坏处处可见。为什么?就道德领域而言,关键在于人们缺失了道德其“神”。而没有了道德其“神”,道德其“形”即规范也就成了一堆空壳,写写、说说而已。道德无其“神”,也就没有践行规范的内在动力,就不会有规范的践行。据此,现在的道德建设,重要的是要培育道德其“神”,即如荀子所说的“诚心守仁”。而“诚心守仁则形,形则神,神则能化矣。”道德的建设,关键在于培育主体对道德的内心之“诚”。当然,要达到这种要求,我们在道德教育和制度建构、政策制定上都有许多工作要做。 在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上,把握“‘形神统一’文化生命结构”同样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这里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实质上就是要继承和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之“神”。而“神”寓于“形”以现,因此,为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就要保存和保护好民族传统文化的固有之“形”,包括规范语言文字,整理古典文献,继承传统节庆,保护文物古迹等,因为这些都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神”的重要载体。 一是要保护和规范本民族的语言文字。语言文字是文化的载体。人类文明史表明,“任何文化或文明的主要因素都是语言和宗教”。(47)一个民族的民族语言或文字的消灭必然会导致这个民族的民族文化的消亡。因此,一个民族为卫护自己的文化就一定要保护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所以二次大战后获得独立的原殖民地纷纷恢复本土语言作为国语,以取代原宗主国的语言。现行的中国文字源于殷代的甲骨文,它与古埃及象形文字、古巴比伦楔形文字一样,在各自环境中诞生,但几经演变而传承3000年以上的只有汉字,这是中华文明之大幸。她以其举世无双的方块形态承载着中华文化,为中华文化的生命不息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可以说,每一个汉字所组成的语词、词组和成语,都蕴涵着中华文化之“神”。毫无疑问,我们要十分珍惜和保护自己的母语。“规范和保护国家、民族语言文字”,就是保护传统文化。 二是要传承好民俗节庆。中华民族在文明演进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许多表征着民族风俗和生活方式的节庆——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节、中秋节,重阳节等,它们积淀着深厚的民族心理和文化情结,内涵“和为贵”的人文底蕴:爱家爱国,家和睦邻、尊老爱幼、缅怀先烈、国泰民安,这一切实际上都是传统文化之“神”的具体化和世俗化。就是说,这些民族节庆由承载传统文化之“神”而获得了浓厚的文化气息,而传统文化之“神”则因这些节庆之“形”而得以生生不息。这就是这些节庆传之现今而不绝的奥秘所在。传统文化正由此而保持了生命活力,再一次表明文化其“形”对于文化其“神”重要意义。要重视传统节庆对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以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现在的问题是要防止传统节庆在“洋节”气氛和商业浪潮的冲击下被淡化或异化为单纯的娱乐活动和商品符号,从而消解了其所承载的固有的“神”。因此,保护传统的节庆,使其“形”与其“神”获得现代性的统一,就成了通过传统节庆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关键。 三是要保护好文物古迹。中华传统文化中有着富有特色和极为丰富的文物古迹,它们以(“人化”的)物的和非物的形态历史地沉积着灿烂的中华文化,因此在本质上不是形态物,而是内涵传统文化之“神”的文化体。天安门、故宫、长城、黄帝陵、兵马俑、敦煌石窟以及大量的出土文物,孔庙、佛寺、道观、书院、经文碑刻,历史悠久的楼、台、亭、阁和园林建筑,京剧、昆曲等各种传统剧种,等等。以极其广博而丰富的文化之“形”蕴涵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蕴。今人亲历其境并知晓它们的历史,即会感受到中华文化之恢弘与精深,其承载着的文化之“神”即会在人们的心中鲜活起来,其魅力所致不仅顿生美感,而且会加深对民族的文化认同感。足可见保护文物古迹对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保护文物古迹就是保存历史,保存中华民族的文脉,保存优秀的传统文化。然而痛心的是,大量的文物古迹遭到无情的破坏,而许多仅存的也被单纯地商业化,异化为商品的价值符号,失去了应有的文化魅力,人为地破坏了文物古迹的现代生命力。形毁神灭,形具神存,不难设想,如果没有了文物古迹,完全换成了现代器物和各种风格的西式建筑,势必会在人们的心目中抹去对中华文明的历史记忆,从一个方面消解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这是十分危险的。 总之,“形”以传“神”,保持和增强各族人民的中华文化的认同感,不能仅靠对传统文化之“神”的理论表述,还必须靠传统文化之“形”的感性魅力,这就是人们强烈呼吁保护、拯救文物古迹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缘由。 第二种情况。传承和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不仅要通过保护传统文化其“形”,而且要发掘和总结传统文化中与时代精神相通的“神”,即所谓“古今通理”。(48)如“民为邦本”,“和而不同”,“仁者爱人”,“见利思义”,“诚实守信”,等等。并对其进行现代价值再创造,实现其“神”与其“形”的现代统一。就是说,使优秀的传统文化之“神”与时代精神相融合并通过现代的文化之“形”而得以弘扬。如通过学术研究及其成果的传播和转化,不仅使之与学校教育、新闻出版这些文化之“形”相统一,而且要通过广播影视、文学艺术实现“神”与“形”的现代统一。 影视文化已经成为每家每户每个人的文化大餐,对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具有十分广泛而重要的作用。我们应该创作出具有很强感性魅力的艺术形象(“形”)与传统文化中深厚的文化内涵和人文精神(“神”)相统一的影视大片。一些文化遗产可以产业化,但必须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结合起来,而且重在社会效益,如果只是注重展示感官刺激的文化之“形”,以求吸引更多的眼球,获得更多的利润,而忽视传统文化本有之“神”,其结果必然会糟蹋优秀的传统文化,那只能说是见利忘义,唯利是图了。应该看到,只重文化其“形”,而且只是为了刺激感官引起感性快感的“形”,轻忽文化其“神”,已经成为文学影视创作的一种不良倾向。这种倾向以不同形式同样表现在那些“有票房没口碑”的所谓“历史”大片上。这些“大片”往往唯“票房”是从或唯“奥斯卡”是图,投资动则亿万,“形”象制作精妙绝伦,然所缺少的恰恰就是中华文化的深厚内涵——中华文化之“神”。因而也就不可能真正起到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作用。对于影视业中这种重“形”而轻“神”的制作偏向,理当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文学界、影视界应该创作出既有很强感性魅力的艺术形象(“形”)又具中华传统文化深厚内涵和人文精神(“神”)的剧本和影片。 现在,在“大众文化”成为文化消费之重要形式的情况下,除了影视戏曲,如何创造各种新的与优秀传统文化之“神”相统一的文化之“形”,将成为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即所谓“历史走向大众”。荧屏上各种“文化讲堂”纷纷出现,正为历史走向大众提供了一种途径。这是一种文化之“形”的创新,使内涵深刻的诸子百家和传统文化转化为一种为受众喜闻乐见的大众文化,推动了历史知识和文化经典的普及。当然,让历史走向大众,不只是一种途径,应该创造出各具特色的多样的现代文化之“形”。 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中,应承接和融入优秀传统文化之“神”,如“和而不同”、“见利思义”、“民为邦本”、“仁者爱人”等,使这些优秀的传统价值观、即所谓“古今通理”经由现代转化而寓于并显现于教育活动、文学艺术、电影电视、媒体舆论、电子网络等各种文化样态(“形”),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发扬光大。还应通过现代的制度安排使传统文化中如“中和”、“民本”、“仁爱”、“诚信”、“正义谋利”等价值观转化为现代的治理理念和治理方法,实现传统的优秀文化之“神”与现代文化之“形”相统一。总之,应坚持文化其“神”与其“形”统一的文化哲学方法论,继承和发展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使之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注释: ①作者早在2006年就提出了“‘形神统一’的文化生命结构”这一概念(见《毛泽东邓小平思想研究》2006年第10期),此后在多篇论文中都有所及,但尚欠历史的和理论的深度。就“形”、“神”和“形神统一”确立为文化哲学的概念而言,也有待辨析和论证。因而有必要对“‘形神统一’的文化生命结构”这一概念,做进一步的论述。 ②陈迩冬选注:《苏轼诗选·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其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226页。 ③胡道静、金良年、胡小静译注:《梦溪笔谈全译》卷十七《书画》,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28页。 ④张建业主编:《李贽文集》《焚书·续焚书·诗画》(第一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04页。 ⑤冯契:《人的自由与真善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73-274页。 ⑥冯契教授认为,在中国美学史上,“因为中国人长期发展了表现说和意境理论,所以造型艺术和叙事作品受了抒情的影响,中国画就用来抒情,特别是山水画抒写意境。这里也有一种偏向,人物画起初强调意境,重神似而对形似未免有所忽视。中国人没有像西方人那样去重视对人体解剖和色彩作科学研究,所以人物画的成就不及西方。”(冯契:《人的自由与真善美》,第278-279页。) ⑦[德]黑格尔:《美学》第一卷,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98、201页。 ⑧(13)郑板桥:《板桥题画》,张素琪编注,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06年,第15页。参见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46页。 ⑨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第23页。 ⑩冯契:《智慧的探索》,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97页。 (11)冯契:《人的自由与真善美》,第259页。 (12)(17)《己畦集·己畦诗集》卷八《赤霞楼诗集序》,《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00、401页。 (14)《尚书·尧典》,王世舜《尚书译注》,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8页。 (15)《毛诗大序》,引自唐·孔颖达《毛诗正义》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十三经注疏》(上册),第269-270页。 (16)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卷五十一《昭公二十五年》,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108页。 (18)《己畦集·己畦诗集》卷八《赤霞楼诗集序》,《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01页。 (19)(20)汉·蔡邕语,引自《瀚堂典藏》的电子资源:《经部集成·小学类·文字·其他·古今图书集成字学典(中华书局民国影本.ISBN.978-7-89480-190-6)·第九十卷 书法部选句》。 (21)转引自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88、389页。 (22)清·嘉庆十七年(1812)解红轩刻本,转引自叶朗著《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80页。 (23)王夫之《唐诗评选》卷一《乐府歌行·刘庭芝二首·公子行》,《船山全书》第一四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889页。 (24)朱立元:《艺术美学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第525页。 (25)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42页。 (26)计成著,李世葵、刘金鹏编:《园冶》,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7页。 (27)《荀子·不苟》说:“诚心守仁则形,形则神,神则能化矣。”“形”指有形的道德实践行为,“神”是由道德行为而显现的德性及其魅力。正是行为所产生的道德魅力感化了人心——“神则能化”。 (28)陈澔:《礼记集说·仲尼燕居》。 (29)《论语·八佾》。 (30)《论语·阳货》。 (31)《论语·公冶长》。 (32)吕坤著《呻吟语·谈道》。 (33)申居郧:《西岩赘言》。 (34)《朱子语类》卷八十四。 (35)《荀子·不苟》。 (3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2-163页。 (37)[美]菲利普·巴格比:《文化:历史的投影》,夏克、李天纲、陈江岚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43页。 (38)(39)[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41、35页。 (40)(41)(42)(43)(44)[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第44-45、52、46、78、34页。 (45)薛永武:《从人是最重要的文化形态看文化强国梦》,《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月8日。 (46)[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第287页。 (47)(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47页。 (48)朱贻庭:《“源原之辨”与“古今通理”》,《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1期。标签:文化论文; 艺术价值论文; 人体结构论文; 艺术论文; 礼仪规范论文; 古代礼仪论文; 美学论文; 中国哲学史论文; 意境论文;
